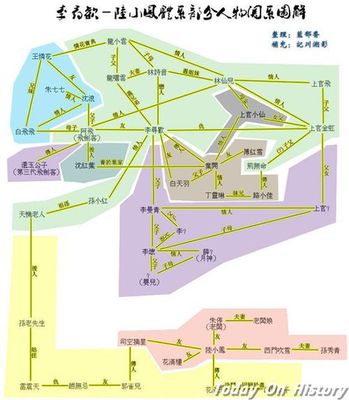转载前言
素来独爱拳学,俗称拳成兵器就,个人认为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拳学来源于战斗,战斗离不开兵器,我看放下武器才成拳更恰当。兵器中钟爱鞭杆及大枪,因为都是练功的好方式,更有助于练拳。看到这篇小说就保存下来,境界很高,于武、于事、于人生、于传统武术之现状的描写表达都入木三分,看后不胜感慨,同老舍先生的《断魂枪》有一比。索性断魂枪也附后。-博主
一个老汉,自打往村口一蹲蹴,他就真正老了。而一群老汉蹲蹴在一起,就显得更老,老得乱七八糟,混沌一片。但仔细看去,却又老得各不相同,尚能分辨。
现在这群老汉蹲在村口的杂货铺子前,有的唠唠叨叨,有的喃喃自语,有的像是在出神地盯着什么,有的在闭目丢盹。他们神情中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恍恍惚惚的。
这时一个人从大路上走来了。
今儿个已是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了,村里出门的后生大多都已回来了。这人又是谁呢?老汉们这时都清醒了,他们睁大眼睛,努力辨认这是谁家的人。但晌午迎面而来的冬日暖阳使他们几乎睁不开眼,手掌搭在额头上也无济于事。这个背着太阳的人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却渐渐长大,渐渐清晰。到了跟前,老汉才看清这是个外乡人,连亲戚都不是,而且谁也不曾见过。
这人一身出门做活的打扮,衣衫破旧。但不同的是衣服却洗得干净,缝补得整齐。脚上的解放鞋裂开的鞋帮也用粗针大线缝住的,只是这鞋太破旧了,纵横交错的粗线中依然露出污秽厚实的粗羊毛毛袜。似乎这羊毛毛袜也是不久才洗过的,只是洗不出它的本色罢了。寒冬腊月里却没戴帽子,头发也是新剃不久,短短的发茬。他背着一个尿素袋子做的行李袋,尿素袋子洗得白白亮亮,行李袋子绑扎得整整齐齐。这人黝黑瘦小,却上下干净清爽,似乎他身上不落灰尘似的。更不同的是,这人手拿一根乌黑发亮的棍。
老汉们看罢这个人,最后目光落在这根棍上。这曾经司空见惯的家什,却使他们更加恍惚了。愣了半天,才想起了这是根白蜡杆子嘛,拳棒手的家什。这久违了的当年在这里多如牛毛的东西,使他们又不禁抬起头来看这个人——果然,他们在来人的脸上也看到了久违了的那种神情:精悍,硬朗。这人对着一堆黑乎乎的老汉说:“众位老家,这就是赵坝吧?”老汉们便一齐点头。这人又问道:“赵鹤鸣赵老师家怎么走呀?”老汉们便一齐回头看他们中的一个老汉。这老汉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艰难地从黑袄黑裤的老汉堆里站了起来。来人也恍然惊道:“你就是赵老师!”“我就是赵鹤鸣,你找我?”来人把行李和棍放在地上,上前一步拱手行礼——这也是很少见的了——毕恭毕敬地说:“我叫毕承信,特地来拜会赵老师的。”老汉抬抬手说:“家里说,家里说。”他领着来人慢慢地往村里走去。老汉们望着两人的背影,半天后才一起恍然大悟地叹道:“柴火行的,柴火行的,柴火行的拳棒手!”
赵家是一院高大崭新的房舍。进大门后来人不禁赞道:“好美气的房呀,赵老师给后人立了大功了!”老汉却叹口气说:“是后人盖的,碎后人领了个建筑队呢。唉,我一辈子连个房都没盖起来,快入土了,儿子孙子却有钱了!”来人望着院子,明白了老汉的心情,偌大的院子全挖成了菜园,收获过的土地在冬日的阳光中静静地缓着,角上的几畦蒜苗却绿油油的。菜园周边是一圈的花花草草,现在多是枯枝,但也有不少碧绿青翠,一看就能想象出花团锦簇时的红火。但这院子,当年却是著名的赵家把式场呀!这人也知道赵家大后人在贩药材,碎后人拉了个建筑队,女婿侄子徒弟们都各忙各的去了,但还是没想到这么有名的把式场说散就散,散得这样彻底!来人真实地目睹了这个事实,吃惊之余,不禁黯然神伤。
他跟着老汉进了上房。屋内却也简单,中堂下是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桌上供着一张老太太的照片,他想这就是同样有名的赵老太吧。屋子的东边是一个大炕,炕边盘着一个火盆。西边的山墙下却放着一口高大结实的棺材,这棺材雕龙刻凤,描花绘草的。来人把行李和棍靠墙放好,然后抚摸着这口棺材,再次赞道:“好美气的寿材!怕是柏木的吧?”老汉听见人赞叹他的老房,这才高兴了,说:“是核桃木的!这是大后人置的,沉着呢,到时候够他们抬的!来,上炕,炕热得很。噢,你吃过晌午饭没有?”“我吃过晌午了,你老人家上炕,我坐底下就好。”来人拿过一只矮凳,低低地坐在离炕不远的地上。老汉盘腿坐在炕沿,拿起火箸,拨开火盆里的灰烬,拨出红红的静静燃烧的火籽。
老汉探身从火盆底下的柴仓里拿出几根细柴,几根苞谷芯子。老汉将细柴搭在火籽上面。轻轻地吹了起来。不一会,细柴轰地着了。老汉又将苞谷芯子搭在火焰上,屋子便烟雾弥漫开来。这火焰红红黄黄混沌一片,而它顶上黑烟如漆,因而火盆上的三角铁架和铁架上的铁壶便也是乌黑如漆。待到浓烟渐渐散尽,火焰的声音也递降成轻轻的呢喃,而铁壶中的哼唱却渐响渐高,渐渐欢快。
这堆火在夏天也这样燃着,来人心想。这屋子高大空旷,却不太冷,正是因为这连绵不断的炉火恒久不尽地燃烧,因而使屋子获得了迟缓深厚的温热。老汉摆开茶盒茶罐,往茶罐里下了一把茶叶,将铁壶里已滚开了的水注进了茶罐,然后将茶罐煨在火边。这小小的鼓腹窄口的粗陶茶罐乌黑乌黑,就如烟火渐渐地渗了进去,茶汁又缓缓地渗了出来,因而成了这种日子的见证一般。一会儿小小的茶罐便滚沸起来,老汉用竹篾子捣着拨着,茶水不断地溢滚上来,空气里弥漫开浓郁的苦香气味。老汉右手执起茶罐耳柄,左手拿起一只小小茶盅,细细地倒出一口红褐色的茶汁来,也只是一口。“来,喝口茶呀。”说罢老汉又给茶罐里添上水,又煨进了火中。老汉的手抖了呀,来人心中叹道。他端起茶盅,深深地呷了一口,然后深深地舒了口气,“赵老师,今年七十八了啊。”“八十了!正月里就八十了,老了!”来人连忙说:“八十了,八十了。”他知道老汉今年是七十八,正月里是七十九了,只是所有的老人都要跳过这个带九的数,直奔后面吉祥的整数。老汉果然老多了,这舞弄拳棒打熬功夫的人,一老起来比起一般的老汉要老得迅速彻底,不成样子。老汉干巴了,腰腿也佝偻僵硬,迟缓吃力。火光中脸上的皱纹如塬上的沟沟壑壑,一把大胡子也凋零得只有十七年前的一半了。他却不知道老汉真正衰老的时间,那是八年前后人徒弟各奔前程,心血汗水渗透的把式场一夜间烟消云散后,老汉一下子就彻底老了。他混在村口的老汉堆里,渐渐地连老汉们也都忘记他赵鹤鸣是什么人了。事实上八年来他连拳棒动也不动,碰也不碰了。
来人将喝完的茶盅放在火盆边上,起身打开自己的行李袋子,拿出两坨黄纸紧紧包裹的小碗状的茶来,放在八仙桌上,“赵老师,没啥拿的,这两个普洱沱茶倒是新茶,味道也好。”老汉点头说:“好。少年,你姓啥?我老了,啥也记不住了。”来人说:“我姓毕,我是毕家崖人。”“毕家崖?毕天澄你怎个称呼?”“他是我二伯。”“噢,你是毕家棍的传人。”“正是。赵老师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老汉端详着来人,这人由于长期在外奔走,面容黝黑消瘦,额头皱纹深沉。“我眼拙哪,记不起来了。少年,你今年多大了?”“四十二了。赵老师,十七年前,就是1978年全省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你棍打的一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你还想不起来?”老汉“啊,啊”两声,仰起头眯着眼半晌,“有点影影,有点影影了。——那次是我正给外地的几个少年说棍呢,一个少年过来,很是无礼,我打了那少年一棍。我念那少年年幼,又是毕天澄的侄子,手下留了情。那个少年是你吗?那你就变多了。我隐隐忽忽地记得那少年白白胖胖的,你现在黑瘦成这个样子了!”
“那少年正是我,那时我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以为天底下除了我二伯毕天澄,下来就是我了。那时我上磅秤就是一百五六,现在不到一百一了。那次我看见你老家正给人说棒呢,不由自主地就脱口而出:‘咦,我毕家崖的人在这儿呢,还敢有人说棒!’在场的人就全都愣住了。我接着一声‘看掌’,就向你一掌撩去,你冷不防只好把头往后仰,我把你的大胡子都撩了起来。你一把把我的手拨开,指着我半天才喝道:‘少年,你想干什么?’我上前行了个礼说:‘赵爸。’你喝道:‘赵老汉!’我又叫道:‘赵爸。’你更是怒不可遏:‘叫赵老汉!’我只好说:‘赵老汉,我毕家崖的人在这儿呢,你就不该说棒!’你怒极而笑:‘好,好!我已好多年没见过有人对我这样说话了,也好多年没挨过棒了,今天我这把老骨头就来挨挨你毕家崖的棒!拿棒!’我拿起根棍,说:‘失礼了!’你喝道:‘少废话,进招!’我一棍劈去,只见你手一翻,‘啪’地一声两棍相交,接着你的棍头已从我的正中划下,将我衣服齐齐划开,纽扣迸飞,皮肉上直直一道血印。接着你一调把,后把已挑在我的裆下。你在我的裆下颠着棍说:‘少年,看清楚了没有?这下可是要命的!’这时,我二伯赶来了,他一把把我扯了出来,伸手就是两巴掌,打完后给你作了个揖说:‘他赵爸,你老家不要和这小畜生一般见识,我给你赔罪了!’
“我当时虽然魂飞魄散,但顷刻间却涌出了一股按捺不住的豪情,我大声说:‘赵师傅,我十年后再来会你!’你笑了:‘啥时候都行,我等着你。你先好好下功夫罢。’前前后后就是这样,这件事情你老家记起来了没有?”
“这些事呀这些话呀,我经得多了,咋都能记住呢。再说说这些话的人虽然多,可再来的却没几个。而今的人连练都不练了!”老汉微微叹口气,只是问道,“你二伯还好?还教徒弟吗?”
“我二伯身子还好,就是心劲倒了。再不教徒弟了,就是本家伙子的,我二伯都不教了。说是而今的人都是眼瞅着钱,再没人来下这个苦了。那次二伯把我领回房间,看了我从领口到胸膛再到肚子上的血印,说:‘老汉手下留情了。狗娃,棍怕老狼啊!老汉今年六十一了,你才二十四岁,你咋能是老汉的对手呢!老汉这一招叫鹁鸽旋窝,老汉的绝招呀。’
“那次观摩会后,我就拿着棒出门了,一边做活挣钱,一边拜师访友,到今儿个已整整十七年了。”
“啊,十七年了!光阴啊……恕我老糊涂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四十二了。”
“四十二了,比我的碎后人大一岁。你叫毕什么?”
“毕承信。”
“噢,承信。来,喝茶,茶薄了,你把这茶叶倒了,我重下些茶咱们喝。我这茶是孙子给我买的茯砖,也不错呢。”
来人把茶罐里的茶根磕倒在门外的柴草堆里,这小小的茶罐依然持续着漫长连绵的温热和茶香。他打开茶盒,里面的茶叶快完了,他就全部都倒进了茶罐。他的手稳定灵活,不慌不忙,茶末子似乎一点一毫都不会洒出来的。他又透了透火心,轻轻巧巧地添上几根在火旁已烤得干透的柴禾和苞谷芯,再给茶罐添上水,轻轻煨进火里。这时火燃得正好,火焰的中心是一个硕大的内核,无论它轻轻颤动抑或摇曳,都显得饱满坚定,明亮耀眼。它的外层,火的外焰,则已经由红变青,由青变无,惟有波动接着波动,舔吞接着舔吞。这才是火焰最高的温度,纯粹的颜色。而它的声音,柔韧,沉着,从容不迫。烟已经全然不见了,烟都散入梁柱椽瓦之间,因而这新房的梁椽都快要熏黑了,这样屋梁椽柱就会更加结实,榫卯就更能闭紧合严。
“来,喝茶,喝呀。你说你出门十七年了?”
“就是。但凡练棍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这些年只有收成播种和过年才在家里,一年在家最多也就三四个月。老婆娃娃意见都大,乡里邻舍说起来也是‘游手好闲,遛鸟儿打拳’这样的闲话。我只有一路上尽量做活,尽量细详,给家里多攒点钱。由于一直拿根棍,被人叫成了‘棒客’!把它的,把土匪的名字安到咱的头上了!”
老汉哈哈笑了,点头说:“甘肃人生得硬,出门不离一根棍。”
“我在车站装车卸货,到工地背料扛包,有时候还胡乱教点拳棒哄上几个钱。为了省几个车钱,一百多里的山路也走过。我不吃烟,不喝酒,只喝一口茶。随身带着一只茶罐,路上乏了,到了有泉水的地方,揪些柴草,煨一罐茶,吃点干粮,再接着走。今年夏忙我正好从陕西岐山棍的窝子里出来,就跟着咱甘肃的麦客,从岐山宝鸡凤翔陇县一站一站往回割,割到家里,家里的麦刚好黄了。这回女人才满意了。”
“这些年你都学了哪些棍?”
“但凡有些名声的,我都学过来了,像四门棍、壳子棍、进山棍、出山棍、疯魔棍、天齐棍、群羊棍……还有好些。”
“你是咋学来的?”
“换来的,没有办法,只有换棍。我拿自家的毕家棍换壳子棍,再拿壳子棍换天齐棍,拿天齐棍换进山棍,就这样一套一套地学了下来。碰见拿啥都不换的,只好动手,对上一场棍,也就学来了。”
“苦吃大了。”老汉叹道。
“刚开始挨的棍多呀,到后就少了。到最后我发现每套棍也就是那么几招,绝的几招。动起手来他就没法藏奸,绝招也就使出来了。这样一招一招地学,一棍一棍地使,近五六年来,比了四五十场棍,再没怎么败过。”“好,好。”老汉点头说。
“我三次用了你老人家的鹁鸽旋窝,都胜了。有一次也将对家的衣裳豁开了。”
“鹁鸽旋窝,鹁鸽旋窝。”老汉低声嘟囔道。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河南客,他的棍足有八尺长,而且握的是左棍式。”
“那是枪呀!”老汉说。
“正是,他使的棍多是枪法。走了几招后,他又是中平枪扎来,我就给搅了一下;他一换势,我顺势单手扎去,用中平枪把他给破了!”
老汉点点头:“中平还得中平破,这暗合古法。”
“还有一次在山西洪家峪的地方,我和对家都滚着棒转圈,对家看见我转到猪食糟跟前了,就突然出棒,我一动,一只脚就踩进了猪食槽中,只能招架,只听见劈里啪啦连响十几下,对家跳出圈,说是平手。我一脚的猪食汤水,狼狈不堪,人家无形地就算赢了。”
老汉眯着眼睛说:“不招不架,就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是十下。”老汉又点点头说,“你现在还能练多少套棍法?”
“起初我只练我毕家三十六棍,以为这就够了。出门后越学越多,都练不过来了,就又慢慢地忘掉了,剩下的又搅成一团,能浑全练下来的真没几套。”
“这就对了。”老汉又点点头说。
“那次我对你老人家口吐狂言,说十年后来找你。出门十年后我才明白了些事。今儿个终于见到你老人家了,已十七年了!”
“十七年了啊!”老汉再次感慨地叹道,“你一十七年荒时废事,花费盘缠,就是为了还这一棒吗?”
来人挠挠头说:“起先是的,后来就不是了……”
老汉继续感慨地说:“这是个没结果的事啊,而今更是个没眉眼的事!吃这么大的苦,到底图个啥呢?”老汉像是在对自己嘟哝。
“还是喜欢这东西。人说吃了五谷想六谷,人是灵物,得吃六谷。比方茶就是咱的六谷,这棍也是咱的六谷,一天也少不下呢。这样想来,这倒是咱的福气了,也就不觉得苦了。”
老汉抬起头望着来人,嘴唇嗫嚅了一下却没发出声来,他似乎被感动了,一直看着来人,半晌才出声说道:“你看咱的这棒,到底是个啥呢?”
来人又挠挠头说:“咱的棒,我常怪怪地想——跟咱的茶有些像呢。”
“对的,对的!”老汉拍着腿说,“是这样的呀!咱庄稼院的棒棒,就是一罐茶呀!起初它拙笨、苦涩,越到后面它的味道越厚、越长、越柔。棍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成了。”
“对的,对的!”来人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我明白了!”![[转载]鞭杆小说-—鹁鸽旋窝作者:苟天晓(来源与网](http://img.aihuau.com/images/30101030/30110824t01d65cdcc4f21a98e4.jpg)
“来,喝茶,把这罐茶喝毕了,咱们到院子里走一遭。”
“不了,不了,赵老师,我来看你,就是为了了个心愿。今儿个又没白来,你老家真叫我全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家,以后就再不出门了。”
“你是不是嫌我太老了?不要紧的。你把我的棍拿出来——就在老房里头。”
来人走到棺材跟前,把棺材盖款款地挪开,取出一根棒来。这根齐眉高的白蜡杆子,跟自己的一样,经过了选材、剥皮、烘干、校压成型,再吊进庄稼院的烟囱里,让草木烟熏烤半个多月,拿出来后再用抹布擦拭,用长满老茧的庄稼人的双手摩挲握弄,最后变得黑红透亮。所不同的是,老汉的这根棍把梢上隐隐泛出殷红,里面似有血丝游动。来人明白,这叫汗透杆红,拿棍人的汗血已渗透进棍中。这只棍经历过多少双手,多少心血!漫长的日子呀!
老汉下炕穿上鸡窝子棉鞋,拿着棍与来人走出屋门,指着院子说:“你看这么大的院子,硬是叫媳妇子挖成菜地了,说是反正没有人再练了。”
来人对这个著名的院子耳熟能详。当年满院子一茬一茬的徒弟在这里耍拳使棒。来人还知道赵师母赵老太太,动不动就往厨房门口的廊沿上一站,破口大骂起来:“羞先人呢,还练把式呢!缸里要面没面,要粮没粮!”这时徒弟们就赶紧找面的找面,背粮的背粮。实在啥也拿不出的,就背些洋芋来,或者出死力气给师父家做活。老汉教过的徒弟足有几百人,并没有挣下钱来,最后连个房都没盖起来。这老两口,老汉舞了一辈子的拳脚,性格却越来越温文尔雅;老太太做了一辈子的家务,性格却越来越刚烈泼辣。来人觉得自己家里的情形与老汉一家很有些相似,起码自己的女人越来越像老太太了。
老汉领着来人拐进房后的一角平地上,这才是赵家原先的菜地。这块小小的平地,只是给老汉仅存的一点象征,一点慰藉,一点回忆罢了。
两人在场子上站定,老汉缓缓地举起棒,成“朝天一炷香”之势,然后点点头,“来吧!”
来人不敢怠慢,连忙凝神聚气,敛身扭步,一条棒围着老汉摆动起来,成“拨草寻蛇”之势。他凝视着老汉,老汉一身黑袄黑裤,黑色的鸡窝子棉鞋,而须发却已如霜。老汉腰身依然佝偻着,两只眼睛却变得黑亮黑亮。这两只眼睛,在沟壑纵横的面容里,如同两口幽深的井,生命最后的精气全部聚到这两只眼睛上了。而老汉举起的棒,来人现在明白了,这棒不只是一只老狼,那是老汉一生性命的静静燃烧的越来越短的一炷檀香。
这人又转着滚了一圈棒。老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等待着。这人脚穿的解放鞋已用细绳仔细绑扎了一圈,以防鞋底脱落。他黝黑,瘦削,硬邦,矫健,柔韧,沉稳。身形一动,就知道他已在功夫的巅峰上。到他这个火候,他本人就是一条了不起的棒了。老汉点点头,又说了声:“来吧。”
来人也点点头,一棍劈去。这一棍,配得上一个在巅峰的大师的一击,力透棍尖,有千钧之势,却沉稳而柔韧。沉稳得攻中带守,以防意外;柔韧得能随发随控,随心所欲。一棍之内四面八方全都被笼盖着。他看见老汉手腕一转,“啪”地一声两棍相交,这声音并不大,来人却感到虎口发麻,他明白这是一股更为柔韧成熟的力加上自己的力递到自己的手心。他手腕一转,棍尖已向老汉正中劈下,这正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鹁鸽旋窝”。但他却感到自己的棍依然被粘着,老汉的棍尖已顺着他的棍削下。他的棍头快要击中老汉的脑门时,老汉的棍尖已削中了他的前锋手。他的右手一阵剧痛,他只能弃棍,但好在他后手依然握着把,他拧身闪出圈外,将棍一转,成“二郎担山”之势,虽是败后求守,却依然气度雄沉,身手矫健。
老汉将棍缓缓上举,依然成“朝天一炷香”之势,静静的,一动不动。
来人将棍扔在地上,看了看受伤的右手,上前喊道:“赵爸!”他声音哽咽,“啊,赵爸!”
老汉依然“朝天一炷香”定定地站着,半天才说道:“他毕哥,”他声音微弱,“他毕哥,扶我一把。”
来人这才发现老汉满面汗珠,须发湿透,面色苍白。他扶着老汉,挟着两条棍,缓缓走回房里,扶老汉上了炕。老汉说:“煮上一罐茶呀。”这人连忙将茶罐里的茶根倒掉,打开一坨他放在八仙桌上的沱茶,用左手掰下一角来,再用左手搓揉起来。他的动作坚定,有力。茶搓碎后,他又用火箸将零散的火籽夹在一起,虚虚地架上柴禾,轻轻地吹了几口,火苗轰地又着了。这会儿他也用右手了,右手依然稳定自如。他的双手虽然也是一层老茧,却并不粗糙,而且整洁,柔韧,不慌不忙,不动声色。他下茶添水,依旧无一点茶末一滴水珠漾出。不一会炉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满屋子又是烟雾,火光,温暖,水壶茶罐和火焰不同声调的哼唱。
依然汗流涔涔的老汉颤巍巍嘘溜溜地喝完第一盅茶后,长长地吐了口气,这才从虚脱中缓了过来。这时老汉的脸洗过一般,白里透出儿童般的红晕,说不出的美气。
“他毕哥,你把两根棍都拿过来。”
老汉拿起来人的棍,“他毕哥,你看你的棍。”只见这棍的棍梢已从正中劈裂。
“啊,赵爸!”
“他毕哥,你这棍用不成了,你把我的这根拿去吧。”
“这怎么能行呢,赵爸!这可使不得……”
“你拿上。这棍,我二爷,我大,都使过。我接上时已过四十五了。你今年才四十二岁,很好。”
“使不得,赵爸……”
“使得。这棍,说穿了,不过是一根柴罢了,‘降龙木本是一根柴’呀。你也看见了,这棍我都放进老房了。你就拿上吧。”老汉这会的神情澄澈透明,连须发也晶莹剔透,“他毕哥,你知道我这一招是啥?”
“这才是鹁鸽旋窝呀,赵爸!”
“很好。最近我一直心神不宁,看来是该无常了。现在我心安了。正月十八他们要给我过寿,家里人多,你也来游上几天。我要是无常了,你帮着把我埋了。”
“赵爸……”这人声音再次哽咽,“赵爸,那我走了。我先回家,正月十五我就来了。”
“你先回家,以后可要好好顾顾家了。”
老汉和一群老汉又蹲蹴在村口杂货铺子门口,看着这人离开。现在夕阳照在这人的背影上,使他的轮廓清晰亲切,甚至有些通体透明的感觉。依然是瘦小的身子,尿素袋子的行李,手里提着一根棍。
老汉混在老汉堆里,又是混沌一片的老汉了。他们现在转过身来,对着渐大渐凉的夕阳,依旧恍恍惚惚地唠叨,感叹,闭目沉思。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个老汉已是另一个人了——那是对大限知晓,诸事安排妥当,就像一盆火已经烧光,他将火籽在灰烬里埋好,让它静静地等待下一盆火点燃的那种人,因而这个老汉浑身上下透着说不出的宁静和安详。
附老舍《断魂枪》
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这是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谁不晓得沙子龙是短瘦、利落、硬棒,两眼明得象霜夜的大星?可是,现在他身上放了肉。镳局改了客栈,他自己在后小院占着三间北房,大枪立在墙角,院子里有几只楼鸽。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给他创出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还时常来找他。他们大多数是没落子的,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有的实在闲不起了,去弄筐果子,或挑些毛豆角,赶早儿在街上论斤吆喝出去。那时候,米贱肉贱,肯卖膀子力气本来可以混个肚儿圆;他们可是不成:肚量既大,而且得吃口管事儿的;干饽饽辣饼子咽不下去。况且他们还时常去走会:五虎棍,开路,太狮少狮……虽然算不了什么——比起走镳来——可是到底有个机会活动活动,露露脸。是的,走会捧场是买脸的事,他们打扮的得象个样儿,至少得有条青洋绉裤子,新漂白细市布的小褂,和一双鱼鳞洒鞋——顶好是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他们是神枪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得到处露脸,走会得赔上俩钱,说不定还得打场架。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老师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教什么?拿开水浇吧!”有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不大明白沙老师是怎么了,心中也有点不乐意。
可是,他们到处为沙老师吹腾,一来是愿意使人知道他们的武艺有真传授,受过高人的指教;二来是为激动沙老师:万一有人不服气而找上老师来,老师难道还不露一两手真的么?所以:沙老师一拳就砸倒了个牛!沙老师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并没使多大的劲!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种事,但是说着说着,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了,有年月,有地方,千真万确,敢起誓!
王三胜——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伙。抹了一鼻子茶叶末色的鼻烟,他抡了几下竹节钢鞭,把场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玩艺儿会几套,西北路上走过镳,会过绿林中的朋友。现在闲着没事,拉个场子陪诸位玩玩。有爱练的尽管下来,王三胜以武会友,有赏脸的,我陪着。神枪沙子龙是我的师傅;玩艺地道!诸位,有愿下来的没有?”他看着,准知道没人敢下来,他的话硬,可是那条钢鞭更硬,十八斤重。
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围。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杀进去。给手心一口唾沫,抄起大刀来:
“诸位,王三胜先练趟瞧瞧。不白练,练完了,带着的扔几个;没钱,给喊个好,助助威。这儿没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象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的扔下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
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的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啊?”王三胜好似没听明白。
“我说:你——有——功——夫!”老头子的语气很不得人心。
放下大刀,王三胜随着大家的头往西北看。谁也没看重这个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象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象两口小井,深深的闪着黑光。王三胜不怕:他看得出别人有功夫没有,可更相信自己的本事,他是沙子龙手下的大将。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臂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的往前拉扯,身子整着①,象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把大衫扔在地上,一点没理会四围怎样笑他。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你说?好,让你使枪吧;我呢?”老头子非常的干脆,很象久想动手。
人们全回来了,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
王三胜努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象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儿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四外已围得风雨不透,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彩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努着眼,木在那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
“还得练哪,伙计!”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走;收了吧;晚饭我请!”
王三胜把兵器拢在一处,寄放在变戏法二麻子那里,陪着老头子往庙外走。后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们骂散了。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王三胜心里说。他脚底下加了劲,可是没把孙老头落下。他看出来,老头子的腿是老走着查拳门中的连跳步;交起手来,必定很快。但是,无论他怎么快,沙子龙是没对手的。准知道孙老头要吃亏,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孙大叔贵处?”
“河间的,小地方。”孙老者也和气了些:“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不容易见功夫!说真的,你那两手就不坏!”
王三胜头上的汗又回来了,没言语。
到了客栈,他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于报仇。他知道老师不爱管这种事,师弟们已碰过不少回钉子,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个脸么?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吗?”三胜的脸又紫了,嘴唇动着,说不出话来。
沙子龙坐起来,“怎么了,三胜?”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沙很客气:
“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纪还轻。”
孙老者有些失望,可也看出沙子龙的精明。他不知怎样好了,不能拿一个人的精明断定他的武艺。“我来领教领教枪法!”他不由地说出来。
沙子龙没接碴儿。王三胜提着茶壶走进来——急于看二人动手,他没管水开了没有,就沏在壶中。
“三胜,”沙子龙拿起个茶碗来,“去找小顺们去,天汇见,陪孙老者吃饭。”
“什么!”王三胜的眼珠几乎掉出来。看了看沙老师的脸,他敢怒而不敢言地说了声“是啦!”走出去,撅着大嘴。
“教徒弟不易!”孙老者说。
“我没收过徒弟。走吧,这个水不开!茶馆去喝,喝饿了就吃。”沙子龙从桌子上拿起缎子褡裢,一头装着鼻烟壶,一头装着点钱,挂在腰带上。
“不,我还不饿!”孙老者很坚决,两个“不”字把小辫从肩上抡到后边去。
“说会子话儿。”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功夫早搁下了,”沙子龙指着身上,“已经放了肉!”
“这么办也行,”孙老者深深的看了沙老师一眼:“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干净了!早忘干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各处逛逛,临走,多少送点盘缠。”
“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屈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象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好!好!”沙子龙在台阶上点着头喊。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不传?”
“不传!”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起蓝布大衫,拉拉着腿:“打搅了,再会!”
“吃过饭走!”沙子龙说。
孙老者没言语。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他独自上了天汇,怕是王三胜们在那里等着。他们都没有去。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胜;反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不要说王三胜输给他,沙子龙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呢,王三胜到底和老头子见了个高低,而沙子龙连句硬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作品赏析
《断魂枪》写于1935年。年初,老舍本想写一部武侠长篇小说《二拳师》,后由于各种原因未写成,便将其中一个最精彩的段落改写成短篇小说《断魂枪》。小说《断魂枪》和《微神》一样是公认的老舍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断魂枪》的文字比《微神》易懂得多,而且意味深长,令人深思。
老舍擅写长篇小说,但短篇也写得精致,《断魂枪》无疑可以进入现代短篇小说的精品行列。《断魂枪》说的是三个拳师的故事,重点写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复杂心态。老舍善于把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和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在短小的篇幅里营造出了大格局。“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这本来可以是平淡无奇的叙述,但放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惊破“东方大梦”的大背景下,内涵和寓意就大不同了。沙子龙的职业更换,他震动江湖的武艺和名声,他行走于荒林野店里的豪放事业,之所以如梦幻般一去不返,与西方列强东侵后引发的中国社会变动密切相关,是历史大变局的反映。
沙子龙显然不是和时代变动正面对抗的人物,他似乎颇识时务,能够与时俱进。既然祖先信奉的神灵都不再灵验,既然“走镖已没有饭吃”,他也就不再留恋保镖的旧业,他不仅及时把镖局改成了客栈,连他的武艺,包括他自创的绝技“五虎断魂枪”,也弃之一旁,甚至旧日镖局里的徒弟前来求教,他也不肯指点传授。
《断魂枪》的核心情节,是号称沙子龙大徒弟的王三胜卖艺场上受辱而沙子龙无动于衷。打败王三胜的孙老者随后登门向沙子龙讨教绝技,沙子龙却绝口不提武艺和枪法。从此昔日神枪沙子龙的威名一落千丈,连以他为荣耀的徒弟们也不再理睬他,但他无半点愠怒。其实他的内心如灼热岩浆。小说两次写到沙子龙在夜静人稀时面对天上的群星一气刺出六十四枪的场面,第一次是简要叙述,是铺垫性的,第二次则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写,且放置在结尾,把沙子龙的无奈和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小说的结构产生了一种张力,可谓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如果《断魂枪》仅仅写沙子龙这一条情节线索,这篇小说最终难免成为一曲为中国传统的技艺和精神悼亡的挽歌。但《断魂枪》里还出现了一位孙长者。就他在卖艺场上显露的身手,以及他给沙子龙的表演,明显是位武林名家。他那深藏不露的性格和沙子龙颇为接近。但他和沙子龙大为不同,他乐观、坚韧,为学习传统的武林绝技而风尘仆仆地奔走江湖。在老舍的艺术构思中,孙老者也许只是作为沙子龙的一个陪衬或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孙老者的出现,却在《断魂枪》悲伤的氛围里增添了悲壮的情绪,使沙子龙的形象得到补充,受到诘问,也使这篇小说由“单声部”叙述变成了“复调”叙述。这种叙事特征,应该不是老舍有意经营的,而是从他的心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烘托和对照的手法。王三胜的鲁莽气盛与沙子龙的深藏不露相对比;孙老者的刚直锐进又与沙子龙的保守愚顽相映照。在对同一个人物的描绘中,或用反差极强的对比,或用先扬后抑等手法去刻划其性格特点。对于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作品并不多用对话和直接的心理剖析,而是通过人物的外形和动作的精确描绘来披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