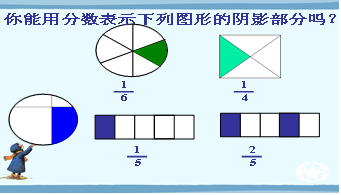“朦胧诗”之我见
——倦客1986年所作论文
注——
近期,朋友文茹先生诗兴大发,佳作迭出,对曾经因诗而喜欢文字的倦客来说,阅朋友佳作美文,不禁心急手痒,蠢蠢欲动,总想网上涂鸦,以和朋友浅吟低唱,谁知电脑码字,脑袋一片空白,江郎才尽,老年痴呆,即使搜肠刮肚,也是灵感全无,激情殆尽,愧对朋友、愧对自己,更是愧对曾经疯狂痴爱的文学贵族——诗歌!无所事事,汗颜不止,回首往昔,将1986年曾写的一篇论文翻出,正好与诗歌息息相关,遂将旧作发在博客,以示对诗歌的奠祭。
“朦胧诗”之我见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大批才华横溢、富有探索和创造精神的年轻诗作者,狂吟他们的新作,无所顾忌地登上正在复苏的中国诗坛。他们那种勇于创新、敢于表现自我的精神,以及在艺术上大胆采用象征、跳跃、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使虚伪空虚的中国诗歌遭受大浪淘沙般的冲击,佳作如雷贯耳,令人耳目一新。
新人的涌现,无疑给沉寂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新的活力,引起了诗人和评论家的关注和重视。一时间,评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褒贬各异,据理力争。爱者爱得发疯,为之振臂呼赞,称其为“新诗的崛起”、“中国诗坛未来的希望”;恨者恨得要死,为之口诛笔伐,斥之为“沉渣泛起”、“诗歌的大倒退”……
几年过去了,雷雨般的争论渐稀渐灭,而以新诗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徐敬亚、李钢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销声匿迹,相反,他们没有作茧自缚,而是用出色的诗作赢得读者的爱戴。前不久,四川的《星星》诗刊以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中国大陆十名“最受读者喜爱的中青年诗人”,舒婷、北岛、顾城、李钢、杨炼、江河等榜上有名。
一
不言而喻,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新诗同样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朦胧诗,它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说起“朦胧诗”,有人便说它是步“西方现代派”后尘、“中国二、三十年代现代派的翻版”。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且定论为时过早。他们未能从总体上去把握“朦胧诗”,只是强调和放大了“朦胧诗”的不足之处。其实,近几年,诗坛所涌现的“朦胧诗”,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派,也不同于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的中国现代派,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它是中国现实土壤中所孕育出的新生婴儿,其第一声稚嫩的呼唤,已是石破天惊,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产生,是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西方政治的急剧变动和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使人们在精神上产生阵阵窒息与颓废,丧失了对世界传统信任和固有的精神支柱,从而产生了追求与幻灭的苦闷与忧郁,而现代派诗歌的出现,正是这种精神颓废、信仰危机的自然流露。表现了人们在梦想破灭、前途渺茫之际所产生的种种郁闷。如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一直被誉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荒原》一诗涌现出大量隐喻交织、一连串看来互不相关的意义,透露出意识流、朦胧、甚至晦涩的手法,加之诗作多“片段化”,运用大幅度地跳跃,起伏不定,意境迷离,主题隐约,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印象。这首诗被评论家称为“划时代的诗篇”,内容上集中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状态。艾略特还有一首题为《空心人》的诗,将人类看成是装在草包里的“空心人”,全诗充满悲观厌世的情绪——“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填起来的/ 靠在一起/ 脑袋瓜装在一包草。”另外,意大利未来主义诗人帕拉采斯基的《我是谁》,说明人生就是充满“疯狂”、“忧愁和悲哀”——“我/或许是一名诗人/ 不,当然不是/ 我的心灵之笔/ 仅仅抽写一个奇怪的字眼:疯狂。”
“文革”十年,使我们的民族蒙受了一场空前灾难,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年轻一代也是在劫难逃。他们蹉跎岁月,失去尊严;他们曾狂热过、追求过、苦闷过,他们经历了浩劫,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人生之路,目睹了人生的动乱和丑恶,经受过严霜酷冰的摧残。当他们从噩梦中醒来,大有“不堪回首”之感慨。于是,年轻的诗作者开始觉醒沉思,开始他们的探索和追求。诗人杨炼向生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是诗人,我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这个生活。生活的复杂和节奏决定了诗的复杂和节奏。对于我,观察、思考中国的现实,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宣告:我的诗属于这场斗争。”(《福建文学》1981年第一期《我的宣言》)。以哲理诗而引人注目的诗人江河说道:“春天,对于诗人,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或某种政治气候的变化。并不是春天到了,人们才开始歌唱。它的热情蓬勃,它对寒冷和空旷的挑战,是诗人素质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象征。”(《上海文学》1981年第三期)。一直在追求真善美的诗人顾城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诗刊》1980年第十期)。顾城又说:“由于渴望,我常常走向社会的边缘。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话,浅浅的脑海里就充满光辉。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福建文学》1981年第一期)。天真单纯的诗人梁小斌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内心进军……心灵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的道路。”(《福建文学》1981年第一期)。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命运,使女诗人舒婷也感受到了不被人理解的苦楚,她用杜鹃泣血的声音呼唤着:“人啊,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诗刊》1980年第十期)。面对纷乱复杂的人生,诗人北岛发出了迷惘:“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诗人徐敬亚也陷入沉思:“曾经有那么多年,我跟在虔诚的朝圣者们中间,默默地走,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声音。”(《诗刊》1980年第十期)。
十年动乱,中国沉浮于一种急遽的社会大动荡中。愚昧、狂热、灾难、野兽般的践踏,丧失人性的颠覆,我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我们对丑恶有了充分的体验,感受和积累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追求真善美,是诗人的天职,也是他们的主题。然而,严肃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美好幻想。由于受骗,由于曾经的无知和狂妄,他们对生活存有神经质的疑虑,心有余悸,他们的诗作往往隐晦曲折,意象含蓄,诗歌的主题交织着紊乱、怯怕、不清晰的思绪,充满着复杂、难以言明的情感。乍暖还寒,迷茫的思想用不确定的语言和形式表达。他们厌弃假大空,疾恶邪恶,开始新的探索,用别具一格的风格向人的内心世界冲击。
这也许就是“朦胧诗”兴起的社会原因。正如诗人公刘所言:“鉴于国家政治生活长期的极不正常,有些诗人既想为人民说话,又须避开文字狱,不得不采取某种隐晦曲折的手法。这是实际存在过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公刘《仙人掌堪余杂感》1981年第一期《星星》诗刊)。
二
另外,客观世界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朦胧隐约、迷离飘渺的景象。如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使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叹;雾里黄山,更有一种云从脚下生,人在画中游的感受;雨中西湖,山色空濛,别具情趣……古今中外,高明的艺术家大都追求这种朦胧之美。明代董其昌说:“摊烛作画,正如隔帘望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法也。”(《画旨》)。
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画面上朦朦胧胧的港口晨雾弥漫,太阳慢慢升起,在雾气之下几乎看不到具体的事物,远处一片模糊迷离。河水中有几只小船、严格地说只是船的符号;而画面中的太阳,也只是个橘黄色的圆点,放射着微辉,投入水面……这一幅根据太阳七色光谱描绘自然界瞬间印象的油画,震惊西方画坛,也使莫奈声名鹤起。
我国古代和现代作家的许多作品,也都创造出风格各异的朦胧意境。如《诗经》里的《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还有唐代李贺的《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李商隐的《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现代大家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笼罩着轻纱薄雾般的荷塘;戴望舒的《雨巷》,何其芳的《预言》,这些佳作都具有朦胧含蓄、引人入胜的格调。当代作家、诗人柯岩曾为汪芜生的摄影作品《黄山》题诗:“不知是云,不知是雾,/哪里是山,哪里是谷?/ 好像山在飘浮,/ 又似云在寻路……啊,黄山,你——/梦中的去处。”(《诗刊》1980年第八期)。
对于当代年轻诗人来说,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过早成熟,现代化生活节奏,又使他们能够勇敢执着地进行探索,他们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思想开始解放,在艺术创作中的探索和追求,远远超过了古人和前辈。他们大但创新,颠覆传统,不注重对客观事物的呆板描摹,而是注重由外在的有限物质世界进入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诗作也不仅仅表达情感,而是带有某些抽象思辩的意味,继而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里。他们义无反顾地冲破古典和谐统一的习惯,标新立异,为了表达某种情绪,以种种变形的、扭曲的、甚至难以捉摸的意象、情节、结构来影响读者,给人一种奇异复杂的心理冲击。他们的朦胧诗,并非对过去现代派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时代特征以及时代在诗人心灵打下的烙印。如顾城的小诗《泡影》、《感觉》和《弧线》,就充分体现这一特征。有的诗的主题,往往印有难言的痛苦和隐隐的伤痕:“在村边,在不长庄稼的地方/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 我生长。看着人们匆匆走过/庄稼仿佛疲倦地躺在大地上/我孤独地生长/ 颤栗着,向太阳诉说/ 使我不安的事情……”(江河《命运——给顾城》)。有的诗则以不屈的呐喊表达诗人对荒唐年代的思考和批判,对理想和光明的追求:“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得刽子手们的高大/阻挡那自由的风。”(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烈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有的诗以高昂的情调反映生活意志,如江河的《纪念碑》和《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有的诗大胆冲破传统禁锢,抒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思念》等;有的诗以赤子之心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前途命运的思考,如王小妮的《我要写一本书》、《假日,在北戴河》,还有杨炼的《沉思》,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李钢的《一个青年》……一大批年轻诗人,在刚刚复苏的大地上,用自己的心灵和才华,抒发着“黄河之水天上来”般的澎湃激情。在这场大合唱的交响中,既有江河的豪放庄重、北岛的凝重沉思,也有顾城的纯净简练、王小妮的率真自然;既有舒婷的委婉忧愤、杨炼的雄浑刚遒,也有梁小斌的童稚淡雅、李钢的灵空新颖……
三
“朦胧诗”在短短几年里,由涓涓小溪汇成今日影响中国诗坛的重要流派,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它所表现出的艺术魅力。诗人在艺术天地里,承受着某些“权威”人士的责难而辛勤耕耘,苦苦探索,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冲破传统世俗束缚,在诗歌的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其特点归纳如下:
其一:隐喻的象征性。象征派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运动,在西方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1886年9月15日,在巴黎的《费加尔报》上,法国一个不大知名的诗人让·莫拉提出了“象征意义”这个名称,要求诗人逃避现实,摆脱自然主义,放弃对自然的复制,努力挖掘人的精神生活,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要求赋予抽象概念以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苏联的亚历山大·勃洛克,英国的艾略特等象征派诗人,都在这方面有较高成就。而在中国,翻开古典诗歌,具有象征意味的杰作俯拾即是,熠熠生辉。像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李贺的《梦天》,早有象征派的雏形。而中国现代派诗人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象征派的美学原则。
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即诗人运用有声有色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使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互相感应契合。艾略特曾简洁地把它总结为“寻找思想的客观对应物”。当代诗人的“朦胧诗”,使象征的表现手法得到了充分发挥,诗人无拘无束,冲破传统表现手法的束缚,着重表现内心的一种深厚的情感,注重抒发微妙的情绪和隐秘的感受。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对现实的梦和爱、寻找自己的道路。”(智利诗人聂鲁达语)。他们不注重外在的韵律,不再煞费苦心地去频凑韵脚,不再拘泥于字数、分行、整齐划一,押韵工对,而是完全推翻传统,采用自由的,散漫的形式,追求一种内在的节奏和神韵,文字的内涵和外延极具张弛,承载着对生活、对人生的开拓和探索。如江河的《纪念碑》(载《诗刊》1980年第10期),全诗没有一句描摹纪念碑的高大肃穆的外貌,完全是从纪念碑象征意义的角度去表现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纪念碑象征着历史、人民,更是象征着斗争和鲜血。再看看诗人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载《长安》1981年第1期):“湖边山丘上/那棵最大的枫树/ 被伐倒了……/ 在秋天的一个早晨/……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 每根草/ 每一朵野花……/ 湖边停泊的小船/ 都颤颤地哆嗦起来……/这一天/整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上/ 飘忽着浓郁的清香/ 清香/ 落在人的心灵上/ 比秋雨还要阴冷/ ……芬芳/使人悲伤……”此诗写于1973年秋天,在那个不能说真话的年代里,四面楚歌,人人自危,那么这首诗的象征意义就可想而知了。梁小斌《雪白的墙》,象征对美好事物的心向往之,舒婷的《致橡树》,象征意对恋人的彼此忠贞。江河这样写道:“土地说:我要接近天空/于是,山脉耸起/ 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诗人用土地象征自然和现实,用天空象征理想和未来,用山脉耸立象征人民的劳动和创造,用洪水退去象征战胜邪恶和灾难。总之,象征手法的运用,使新诗的意境深远,容量扩充,含蓄而又不失深沉,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其二、神秘的潜意识。奥地利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反理性的潜意识学说:自由联想、自我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的力量——给新诗作者以很大的影响。他们特别重视诗的情绪渲染、给予读者潜意识感受,而不过多地追求文字表面意思。他们极力捕捉一瞬间的感觉,用难以诉说的情感去唤起读者的共鸣和反响。我们先读一下舒婷的《落叶》选段(《星星》诗刊1980年第8期):“残月像一片薄冰/漂在沁凉的夜色里/ 你送我回家,一路/ 轻轻叹着气/ 既不因为惆怅/ 也不仅仅是忧郁/ 我们怎么也不能解释/ 那落叶在风的撺掇下/ 所传达给我们的/ 那一种情绪/ 只是,分手之后/ 我听到你的足音/ 和落叶混在一起。/”诗的语言是简练清晰的,但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十分复杂。这首诗到底说明什么?似乎一时难以言明,要用字面意来解释主题更是困难的,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它实实在在地给人一种潜意识的东西,我们都会感觉到这首诗准确无疑地传达出一个人内心的倾诉,字里行间渗透着惆怅、迷惘以及淡淡忧伤的情绪,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作者用“残月”、“薄冰”、“沁凉的月色”、“寒风”、“落叶”、“小路”等景物所浮现出的潜意识,希望加情感的交流和沟通,表达着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和惋惜。再看看诗人李钢的《一个早晨的回忆》:“这时我偶然路过/和你相遇当然是一种巧合/我们似乎对视,时间很短/彼此只留下淡淡的印象/更何况隔着晨雾看不清楚/甚至怀疑对方是否存在(李钢诗集《白玫瑰》)。”作者一时说“我”和“你”相遇,一时又“怀疑对方是否存在”,也许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我和你”的偶遇,而是作者一瞬间的幻觉,或者说是潜意识的表现。诗,不能只是给读者一种原则和概念,而应是一种潜意识的暗示和感受。朦胧诗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学观点,因而不断赢的人们的喜爱。
其三,急遽的跳跃性。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迫使诗歌告别旧体诗的格律模式,一味用绝句、律诗乃至民歌等形式来表现现代复杂生活,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朦胧诗”应运而生,且别开生面,借鉴西方意象派手法,运用大幅度跳跃等特点,在诗歌中,常常采用“三级跳远”式,只为读者提供几个简单的影像,让读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去品读、去体味。它的结构,不是缓缓行进,也不是传统的层层铺垫,而是落差悬殊的石壁陡崖,千尺瀑布。
我们先读读王小龙的一首小诗《给妈妈》:“小时候/ 我抱住妈妈的腿/ 躲着汽车、狗/ 和陌生人/ 现在我长大了/ 可是妈妈/ 如果没有你/ 我还是会害怕/ 汽车、狗/ 和陌生人/ 我不怕/ 我有妈妈。”(载《萌芽》1981年第6期)。这里的狗、汽车和陌生人,三者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自然也不会存在任何联系,但它却暗喻着一个可怕的年代,颂扬了母亲的慈善和高大。这首诗看起来结构零散,思维跳跃,但这种零散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游戏,它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是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串穿起来的闪光项链。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演员陈冲朗诵了这首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再看看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属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横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摘自诗集《双桅船》)。这首诗上下结构没有主线连结,前后跳跃急迫,打乱了一般颂诗的自然规律和前后顺序,且几个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它完全是靠诗人岩浆爆发般的激情,一气呵成,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子情怀,为祖国的贫穷和落后而焦灼痛楚。
“朦胧诗”有时也会吸取小说“意识流”和电影“蒙太奇”等艺术手法,用不和谐的色彩,用零散破碎的形象,打乱时间和空间的顺序,求凝炼,得含蓄,以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目的。
四
有些评论家将“朦胧诗”视为“晦涩古怪”、“含糊不清”,甚至斥之为“颓废”,我以为,失之偏颇,是不公正的。朦胧与晦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朦胧是含蓄的表现形式,含蓄不一定通过朦胧来实现,但朦胧的美一定是含蓄的。我们从以下两首小诗对朦胧与晦涩加以尝试性的区别。
我们先分析顾城这首争议较大的小诗《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这是一首落笔干净、蕴含丰富的好诗。据作者顾城讲,“这很像摄影中的推拉镜头,利用“你”、“我”、“云”主观距离的变幻,来显示人与人之间习惯的戒惧心理和人对自然原始的亲切感”(顾城《关于小诗六首的通信》载《星星》诗刊1981年第10期)。有的读者将《远和近》看成是一首情诗:一对男女青年,眼睛与眼睛相遇,女孩子退去,去看天上的云彩;男孩子心中突涌一种失落,不只是空间距离的拉大。这就产生了不易言明的远与近,两人心与心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表面看,我觉得《远和近》不仅跳跃性强烈,而且形象又不确定,但只要仔细阅读,通过联想,还是可以理解诗歌的内涵和外延的。
再看看另一位青年诗作者的《仿佛》:“仿佛翳暗车窗的人影/ 仿佛玻璃上涂了半截白漆/仿佛天蓝的转椅摇过棕黄的影子/仿佛舞台上早寒的杨枝。”(载《星星》诗刊1980年第10期)。这首诗只是罗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句与句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好似杂乱无章的形象组合,令人难以捉摸,云里雾里,陷于晦涩。
从对以上两首小诗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其一,“朦胧诗”的情趣意境是含而不露,好似雾里观花,别具妙意。而晦涩诗则使人如坠梦游之中,不明事理;其二,“朦胧诗”是含蓄美的主要表现手法。“妙哉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而晦涩诗则是以梦噫般的文字,随心所欲的形象堆砌,令人不可揣度,无法读懂;其三,“朦胧诗”多采用象征、暗喻等手法,形象之间大幅度跳跃,但在象征和被象征之间、跳跃的具体形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晦涩诗象征与被象征之间,跳跃的形象之间,是无逻辑性的,上下前后彼此分割,它的具体形象、细节和内涵也是含混不清,让人无法寻觅。
“朦胧诗”之所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回味无穷,这与它的美学价值有很大关系。王朝闻在《美学概论》这样描述:“作为欣赏对象的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认识生活的成果,也是欣赏者再认识的对象……欣赏者是通过感受、想象、体验、理解等活动,把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再创造’为自己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再创造’对艺术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进行‘再评价’。”“朦胧诗”由于艺术形象的不清晰、主题的不确定性,正可以调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进行艺术形象的再创造。正如诗人公刘索言:“写诗是劳动,读诗何尝不是劳动?……而由初看不懂到终于懂了,不正是一种更激动人心的艺术享受?”(公刘《仙人掌堪余杂感》载《星星》诗刊1981年第1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乐山乐水,不拘一格。明人谢榛曾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妙哉含糊,方见作手。”意大利作家卜迦丘也说过:“如果一件东西好像被罩在一块面纱下而完成,而且出色地完成,那么,它就是诗,而且也只能是诗,不能是别的。”(《异教诸神谱系》)在艺术创造中,演奏家追求弦外之音,画家追求画中有诗,诗人追求诗中有画,所谓“恰是未曾着墨出,烟波浩渺满目前。”
五
探索者迈出的第一步总是勇敢而又幼稚。大江奔流,泥沙俱下。“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自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诗一味追求“自我表现”,“言不及国家前途,思不及民族命运”(诗人流沙河语);有的诗则从“朦胧”滑入极端而近晦涩,文字游戏,孤芳自赏;有的诗在思想内容上存在不容忽视的消极和堕落,艰涩难嚼的诗句,常常透露出理想感情的苍白和失落。有的诗过分追求新奇、梦幻,只图形式而故弄玄虚,画虎不成反类犬。破坏诗的美感,败坏读着胃口。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最后,再谈谈对“朦胧诗”懂与不懂的问题。作为诗歌的新的流派,初起之时总是不被众人理解接受。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作最初只有艾默生赏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遭社会诋毁、政府查禁,而独有雨果表示钦佩;莫奈的《日出——印象》,参加画展受到权威界的嘲笑和非难。对“朦胧诗”读懂与不懂,往往因人而异。这与一个人的学识修养、鉴赏水平、审美习惯以及生活阅历有很大关系。黄庭坚曾讲他儿时读过一首《赠同游》的诗,当时不了解诗的含意,直到自己被贬谪后,读之沉思:“吾年五十八矣,时春晚,忆此诗,方悟之。”(《诗人玉屑》卷六)。
诗人公刘说得恳切客观:“不错,有的诗更好懂些,有的更不好懂些,但如果你认真考察一下青年一代的共同经历,联系一下作品的时代背景,其实是不难懂的。”例如北岛在1974年写过一首诗《人民》:“月亮被撕成闪光的麦粒/播在诚实的天空和土地。”乍一看这首诗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令人费解,但联想到诗的时代背景方可理解诗人的难言之隐:在那发疯的年代里像美好月亮一样的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被暴虐的专制野蛮地撕碎,但撕碎的理想和愿望却化作了闪光的麦粒,又顽强地播在天空和土地上,总有一天它会长出来,因为天空和土地是诚实的。
创新,属于勇敢的探索者,而青年诗人,又是中国诗坛的希望。新诗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循守旧意味着停滞不前。对青年诗人的探索精神,对正在形成流派、且佳作不断涌现的“朦胧诗”,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从而使它健康成长,春华秋实。我以为,既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追求是多种多样,那么就应该让青年诗人有自己自由驰骋的艺术天地。我们不反对传统的、直抒胸臆的作品,但也不能因此排斥“朦胧”性的作品。“水光滟潋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风和日丽的西湖景色固然舒适迷人,但雨雾迷朦中的西湖何尝不给人以更多微妙的遐想?正如李斯特所说:“怎么能够限制一个诗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自己的题材呢?”让我们抛弃过多的偏见,理解年轻一代,对他们的创作和探索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扶持。
还是用诗人舒婷的《也许》,作为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期冀——
“也许我们的心事/ 没有太多的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1986年11月19日初稿于西安静心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