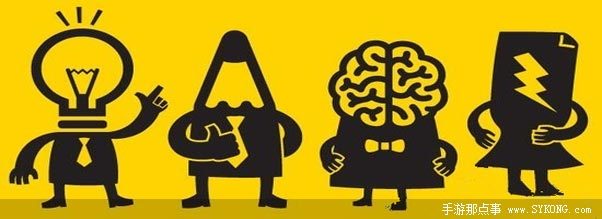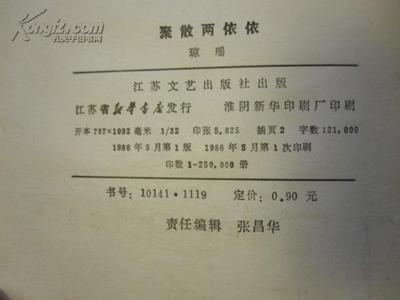凌晨。天色才只有些儿蒙蒙亮。可是,夏初蕾早就醒了。用手枕着头,她微扬着睫毛,半虚眯着眼睛,注视着那深红色的窗帘,逐渐被黎明的晨曦染成亮丽的鲜红。她心里正模糊的想着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像一些发亮的光点,闪耀在她面前。也像旭日初升的天空,是彩色缤纷而绚烂迷人的。这些事情使她那年轻的胸怀被涨得满满的,使她无法熟睡,无法镇静。即使一动也不动的躺在那儿,她也能感到血液中蠢蠢欲动的欢愉,正像波潮般起伏不定。
今天有约会。今天要和梁家兄妹出游,还有赵震亚那傻小子!想起赵震亚她就想笑,头大,肩膀宽,外表就像只虎头狗。偏偏梁致中就喜欢他,说他够漂亮,有男儿气概,“聪明不外露”。当然不外露啦,她就看不出他丝毫的聪明样儿。梁致中,梁致中,梁致中……梁致中是个吊儿郎当的浑小子,赵震亚是个傻里傻气的傻小子!那么,梁致文呢?不,梁致文不能称为“小子”,梁致文是个不折不扣的谦谦君子,他和梁致中简直不像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致中粗犷豪迈,致文儒雅谦和。他们兄弟二人,倒真是各有所长!如果把两个人“都来打破,用水调和”,变成一个,准是“标准型”。
想到这儿,她不自禁的就笑了起来,她自己的笑声把她自己惊动了,这才觉得手臂被脑袋压得发麻。抽出手臂,她看了看表,怎么?居然还不到六点!时间过得可真缓慢,翻了一个身,她拉起棉被,裹着身子,现在不能起床,现在还太早,如果起了床,又该被父亲笑话,说她是“夜猫子投胎”的“疯丫头”了。闭上眼睛,她正想再睡一会儿,蓦然间,楼下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清脆的铃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她猛的就从床上直跳起来,直觉的感到,准是梁家兄弟打来找她的!翻身下床,她连拖鞋也来不及穿,就直冲到门口,打开房门,光着脚丫子连蹦带跳的跑下楼梯,嘴里不由自主的叽哩咕噜着:
“就是妈不好,所有的卧室里都不许装分机,什么怪规矩,害人听个电话这么麻烦!”
冲进客厅,电话铃已经响了十几响了,抓起听筒,她气喘吁吁的嚷:“喂!那一位?”“喂!”对方细声细气的,居然是个女人!“请问……”怯怯的语气中,却夹带着某种急迫和焦灼。“是不是夏公馆?”
“是呀!”夏初蕾皱皱眉,心里有些犯嘀咕,再看看表,才五点五十分!什么冒失鬼这么早打电话来?
“对不起,”对方歉然的说,声音柔柔的,轻轻的,低沉而富磁性,说不出来的悦耳和动人。“我请夏大夫听电话,夏……夏寒山医生。”“噢!”夏初蕾望望楼梯,这么早,叫醒父亲听电话岂不残忍?昨晚医院又有急诊,已经弄得三更半夜才回家。“他还在睡觉,你过两小时再打来好吗?”她乾脆的说,立即想挂断电话。“喂喂,”对方急了,声音竟微微发颤:“对不起,抱歉极了,但是,我有急事找他,我姓杜……”
“你是他的病人吗?”“不,不是我,是我的女儿。请你……请你让夏大夫听电话好吗?”对方的声音里已充满了焦灼。
哦,原来是她的小孩害了急病,天下的母亲都一个样子!夏初蕾的同情心已掩盖了她的不满和不快。
“好的,杜太太,我去叫他。”她迅速的说。“你等一等!”
把听筒放在桌上,她敏捷而轻快的奔上楼梯,直奔父母的卧房,也没敲门,她就扭开门钮,一面推门进去,一面大声的嚷嚷着:“爸,有个杜太太要你听电话,说她的小孩得了急病,你……”她的声音陡的停了,因为,她一眼看到,父亲正拥抱着母亲呢!父亲的头和母亲的紧偎在一起。天哪!原来到他们那个年纪,照样亲热得厉害呢!她不敢细看,慌忙退出室外,砰然一声关上门,在门外直着喉咙喊:
“你们亲热完了叫我一声!”
念苹推开了她的丈夫,从床上坐了起来,望着夏寒山,轻蹙着眉梢,微带着不满和尴尬,她低低的说:
“跟你说不要闹,不要闹,你就是不听!你看,给她撞到了,多没意思!”“女儿撞到父母亲亲热,并没有什么可羞的!”夏寒山说,有些萧索,有些落寞,有些失望。他下意识的打量着念苹,奇怪结婚了二十余年,她每日清晨,仍然新鲜得像刚挤出来的牛奶。四十岁了,她依旧美丽。成熟,恬静,而美丽。有某种心痛的感觉,从他内心深处划过去,他瞅着她,不自禁的问了一句:“你知道我们有多久没有亲热过了?”
“你忙嘛!”念苹逃避似的说:“你整天忙着看病出诊,不到三更半夜,不会回家,回了家,又累得什么似的……”
“这么说,还是我冷落了你?”寒山微憋着气问。
“怎么了?”念苹注视着他。“你不是存心要找麻烦吧?老夫老妻了,难道你……”她的话被门外初蕾的大叫大嚷声打断了:
“喂喂,你们还要亲热多久?那个姓杜的女人说啊,她的女儿快死了!”姓杜的女人?夏寒山忽然像被蜜蜂刺了一下似的,他微微一跳,笑容从他的唇边隐去。他站起身来,披上晨褛,打开了房门,他在女儿那锐利而调侃的注视下,走出了房间。初蕾笑吟吟的望着他,眼珠骨溜溜的打着转。
“对不起,爸。”初蕾笑得调皮。“不是我要打断你们,是那个姓杜的女人!”姓杜的女人!不知怎的,夏寒山心中一凛,脸色就莫名其妙的变色了。他迅速的走下楼梯,几乎想逃避初蕾的眼光。他走到茶几边,拿起听筒。
初蕾的心在欢唱,撞见父母亲的亲热镜头使她开心,尤其在这个早晨,在她胸怀中充满闪耀的光点的这个时候,父母的恩爱似乎也是光点中的一点;大大的一点。她嘴中轻哼着歌,绕到夏寒山的背后,她注视着父亲的背影。四十五岁的夏寒山仍然维持着挺拔的身材,他没发胖,腰杆挺得很直,背脊的弧线相当“标准”,他真帅!初蕾想着,他看起来永远只像三十岁,他没有年轻人的轻浮,也没有中年人的老成。他风趣,幽默,而善解人意。她欢唱的心里充塞着那么多的热情,使她忘形的从背后抱住父亲的腰,把面颊贴在夏寒山那宽阔的背脊上。夏寒山正对着听筒说话:
“又晕倒了?……嗯,受了刺激的原因。你不要太严重……好,我懂了。你把我上次开的药先给她吃……不,我恐怕不能赶来……我认为……好,好,我想实在没必要小题大作……好吧,我等下来看看……”
初蕾听着父亲的声音,那声音从胸腔深处发出来,像空谷中的回音在震响。终于,夏寒山挂断了电话,拍了拍初蕾紧抱在自己腰上的手。“初蕾,”夏寒山的声音里洋溢着宠爱:“你今年已经二十岁了吧?”“嗯,”初蕾打鼻子里哼着:“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该再像小娃娃一样黏着你了。”“原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夏寒山失笑的说。
初蕾仍然紧抱着寒山的腰,身子打了个转,从父亲背后绕到了他的前面,她个子不矮,只因为寒山太高,她就显得怪娇小的,她仰着脸儿,笑吟吟的望着他,彷佛在欣赏一件有趣的艺术品。“爸,你违背了诺言。”
“什么诺言?”“你答应过我和妈妈,你在家的时间是我们的,不可以有病人来找你,现在,居然有病人找上门来了。这要是开了例,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所以,你告诉那个什么杜太太,以后不许了!”“嗬!”寒山用手捏住初蕾的下巴。“听听你这口气,你不像我女儿,倒像我娘!”初蕾笑了,把脸往父亲肩窝里埋进去,笑着揉了揉。再抬起头来,她那年轻的脸庞上绽放着光彩。
“爸。”她忽然收住笑,皱紧眉头,正色说:“我发现我的心理有点问题。”“怎么了?”寒山吓了一跳,望着初蕾那张年轻的,一本正经的脸。“为什么?”“爸,你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吗?”
“张爱玲?”寒山怔怔的看着女儿。“或者看过,我不记得了。”“你连张爱玲都不知道,你真没有文化!”初蕾大大不满,嘟起了嘴。“好吧,”寒山忍耐的问:“张爱玲与你的心理有什么关系?”“她有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心经’,你知道不知道?”
“我根本没文化,怎么知道什么‘心筋’?其实,心脏没有筋,人身上的筋络都有固定位置,脚上就有筋……”“爸爸!”初蕾喊,打断了父亲:“你故意跟我胡扯!你用贫嘴来掩饰你的无知,你的孤陋寡闻……”
“嗯哼!”寒山警告的哼了一声,望着女儿。“别顺着嘴说得太高兴,那有女儿骂爸爸无知的?真不像话!”他捉住了初蕾的手臂,微笑又浮上了他的嘴角。“初蕾,你不是心经里的女主角,如果我猜得不错,那女主角爱上了她的父亲!”
“哈!爸爸,原来你看过!”初蕾愕然的瞪大眼睛。
“你呢?你才不爱你的老爸哩,”寒山继续说,笑容在他唇边扩大。“你的问题,是出在梁家两兄弟身上,哥哥也好,弟弟也不错,你不知道该选择谁,又不能两者得兼……”
“噢!”初蕾大叫了一声,放开怀抱父亲的手,转身就往楼上冲去,一面冲,一面涨红了脸叫:“我不跟你乱扯了!你毫无根据,只会瞎猜!”寒山靠在沙发上,抬头望着飞奔而去的女儿,那苗条纤巧的身子像只彩色的蝴蝶,翩翩然的隐没在楼梯深处。他站在那儿,继续望着楼梯,心里有一阵恍惚,好一会儿,他陷入一种深思的状态中,情绪有片刻的迷乱。直到一阵父的衣服声惊动了他,他才发现,不知何时,念苹已从楼梯上拾级而下,停在他的面前了。
“怎样?跟女儿谈出问题来了?”念苹问。
“哦?”他惊觉了过来。“是的,”他喃喃的说:“这孩子长大了。”“你今天才发现?”念苹微笑的问。
“不,我早就发现了。”
念苹去到餐厅里,打开冰箱,取出牛奶、牛油、和面包,平平静静的说:“别担心初蕾,她活得充实而快乐。你……”她咽住了要说的话,偷眼看他,他正半倚在沙发上,仍然是一股若有所思的样子。早晨的阳光已从窗口斜射进来,在他面前投下一道金色的、闪亮的光带。她拿出烤面包机,烤着面包,不经心似的说:“你该去梳洗了吧?我给你弄早餐,既然答应去人家家里给孩子看病,就早些去吧!免得那母亲担心!”
寒山吃惊似的抬起头来,望着念苹。她那一肩如云般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背上,薄纱般的睡衣,拦腰系着带子,她依然纤细修长,依然美丽动人。他不自禁的走过去,烤面包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却盖不住她发际衣襟上的幽香。他仔细的、深深的凝视她,她迎接着他的目光,也一瞬不瞬的注视着他。他再一次觉得心中掠过一阵痛楚,不由自主的,他伸出手去,把她揽入怀中,他的头轻俯在她的耳边。
“念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什么?”她吃惊的推开他,大睁着眼睛“你发疯了?怎么忽发奇想?初蕾都二十岁了,我也老了,怎么再生孩子?何况,你现在要孩子干嘛?”
“我一直喜欢孩子,”寒山微微叹了口气。“初蕾大了,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或者,添一个孩子,会使我们生活中多一些乐趣……”“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吗?”她问,语气里带着抹淡淡的悲哀。“不是枯燥乏味!”他急忙说。“而是刻板。很久以来,我们的生活像一个电钟,每天准确固定的行走,不快不慢的,有条不紊的行走……”“只要电钟不停摆,你不该再不满足,”她幽幽的打断他,垂下眼睛。她语气中的悲哀加重了。“或者,我们缺少的,不是孩子。二十年的婚姻是条好长好长的路,你是不是走累了?你疲倦了?或者,是厌倦了?我老了……”
“胡说!”他粗声轻叱:“你明知道你还是漂亮!”
“却不再吸引你了!再也没有新鲜感了……”
“别说!”他阻止的低喊,用手压住她的头,下意识的抚摸着她的头发。一时间,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只是静静的站着,悄悄的依偎着,室内好安静好安静,阳光洒了一屋子的光点。初蕾从卧室里跑出来了,她已换了一身简单而清爽的服装,红格子的衬衫,黑灯心绒的长裤,挽着裤管,穿了双半统的靴子。今天要郊游,今天要去海边吃烤肉,她拎着一个旅行用的牛仔布口袋,跳跳蹦蹦的跑下楼梯。
蓦然间,她收住脚步,手中的口袋掉到地下,骨碌碌的、砰砰碰碰的滚到楼梯下去了。这声音惊动了寒山夫妇,慌忙彼此分开,抬起头来,初蕾正呆楞楞的站在楼梯上,嘴巴微张着,像看到什么妖怪似的。半晌,她才伸手拍着自己的额,惊天动地般喊了起来:“天啊,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情人节呢?还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念苹的脸居然涨红了。走到餐桌边,她掩饰似的又拿起两片面包,顾左右而言他:
“初蕾,要吃面包吗?”“要!当然要!”初蕾笑嘻嘻的跑了过来,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年轻的脸庞上绽放着光彩,她本身就像一股春风,带着醉人的、春天的韵味。她直奔到母亲旁边,抓起了一片刚烤好的面包。“我马上走,不打扰你们!”她说,对母亲淘气的笑着。“你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她咬了一口面包,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满足的、快活的轻叹了口气。
“幸福原来是这样的!”她口齿不清的叽咕着,走过去捡起自己的手提袋,望着窗子外面。
窗外是一片灿烂的、金色的阳光。
2
这不是游海的季节,夏天还没开始,春意正浓。海边,风吹在人身上,是寒恻恻而凉飕飕的。夏初蕾却完全不畏寒冷,脱掉了靴子,沿着海边的碎浪,她赤脚而行。浪花忽起忽落,扑打着她的脚背和小腿,溅湿了裤管,也溅湿了衣裳。她的袖子卷得高高的,因为,不时,她会弯腰从海浪里捡起一粒小贝壳,再把它扔得远远的。她的动作,自然而然的带着种舞蹈般的韵律,使她身边的梁致文,不能不用欣赏的眼光注视着她那毫不矫情,却优美轻盈的举动。
“我不喜欢文学家,他们都是酸溜溜的。”初蕾说,又从水里捡起一粒贝壳,仔细的审视着。
“你认识几个文学家?”梁致文问。
“一个也不认识!”“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酸溜溜的?”
“我猜想!”初蕾扬了扬眉毛。“而且,自古以来,文学家都是穷光蛋!那个杜老头子,住在茅草篷里,居然连屋顶上的茅草都保不住,给风刮走了,他还追,追不到,他还哭哩!真‘糗’!”“有这种事?”梁致文皱拢了眉毛,思索着,终于忍不住问:“杜老头子是谁呀?”“鼎鼎大名的杜甫,你都不知道吗?”初蕾大惊小怪的。“亏你还学文学!”“噢!”梁致文微笑了。“搞了半天,你在谈古人啊!你是说那首‘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是吗?”
“是呀,三重茅草卷走就卷走了吧,他还追个什么劲?茅草被顽童抱走了,他还说什么‘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舌燥呼不得,……’真糗!真糗!这个杜老头啊,又窝囊,又小器!又没风度!许多人都说杜甫的诗好,我就不喜欢。小孩子抱了他的茅草,他就骂人家是盗贼,真糗!真糗!我每次念到这首诗就生气!你瞧人家李老头,作诗多有气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念起来就舒服。‘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够味!豪放极了!‘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棒透了!我喜欢李老头,讨厌杜老头!”
梁致文侧过头来看着她,落日的余晖正照射在她身上脸上,把她浑身都涂上了一抹金黄。她浓眉大眼,满头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头发,面颊红红的,嘴唇轻快的蠕动着,那一大段话像倒水般倾了出来,流畅得像瀑布的宣泄。他看呆了。
夏初蕾扔掉了手里的贝壳,弯腰再拾了一枚。站直身子,她接触到他的眼光,他的眼睛深邃而闪亮。每当她接触到他的眼光,她就不由自主的心跳。她总觉得梁致文五官中最特殊的就是这对眼睛。它们像两口深幽的井,你永远不知道井底藏着什么,却本能的体会到那里面除了生命的源泉外,还有更丰富更丰富的宝藏。从认识梁家兄妹以来,初蕾就被这对眼睛所迷惑,所吸引。现在,她又感受到那种令她心跳的力量。“你盯着我干嘛?”她瞪着眼睛问。为了掩饰她内心深处的波动,她的语气里带着种挑衅的味道。“我明白,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你们学文的,都推崇杜甫!你心里准在骂我什么都不懂,还在这儿大发谬论!”
“不。”梁致文紧盯着她,眉尖眼底,布满了某种诚挚的、深沉的温存。这温存又使她心跳。“我在想,你是个很奇怪的女孩。”“为什么?”“你整天嘻嘻哈哈的,跳跳蹦蹦的,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可是,你能把李白和杜甫的诗倒背如流。”
“哈!”初蕾的脸蓦然涨红了。“这有什么稀奇!你忘了我妈是学中国文学的,我还没学认字,就先跟着我妈背唐诗三百首,爸的事业越发达,我的诗就背得越多。”
“怎么呢?”“爸爸总不在家,妈妈用教我背诗作为消遣呀!”
“即使如此,你还是不简单!”梁致文的眼光更温存了,更深邃了,温存得像那轻涌上来,拥抱着她的脚踝的海浪。“初蕾……”他低沉的说:“你知道?你是我认识的女孩子里,最有深度……”“哇!”初蕾大叫,慌忙用双手遮住耳朵,脸红得像天边如火的夕阳。她忙不迭的,语无伦次的喊:“你千万别说我有深度,我听了浑身的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你别受我骗,我最会胡吹乱盖,今天跟你谈李老头杜老头,明天跟你谈汉老头哈老头……”“汉老头哈老头又是什么?”梁致文稀奇的问。
“汉明威和哈代!”初蕾叫着说:“知道几个中外文学家的名字也够不上谈深度,我最讨厌附庸风雅卖弄学问的那种人,你千万别把我归于那一类,那会把我羞死气死!我是想到那儿说到那儿,我的深度只有一张纸那么厚!我爸说得对,我永远是个疯丫头,怎么训练都当不成淑女……”
“谁要当淑女?”一个浑厚的声音,鲁莽的插了进来。在初蕾还没弄清楚说话的是谁时,梁致中已一阵风般从她身边卷过去,直奔向前面沙滩上一块凸出的岩石。初蕾站定了,另一个高大的影子又从她身边掠过去,直追向梁致中,是那个傻小子赵震亚!这一追一跑的影子吸引了初蕾的注意力,她大叫着说:“比赛谁先爬到岩石顶上!”梁致中头也不回的喊。
初蕾的兴趣大发,卷了卷裤脚,她喊着:
“我也要参加!”“女孩子不许参加!”梁致中嚷:“摔了跤没人扶你!”
“谁会摔跤?谁要你扶?”初蕾气呼呼的:“我说要参加就是要参加!而且要赢你们!”
放开了脚步,她也对那岩石直奔而去。
梁致文呆立在那儿,楞楞的看着初蕾那奔跑着的身影。她的腿匀称而修长,轻快的踏着海水狂奔。她的衬衫早已从长裤里面拉了出来,对风鼓动得像旗子。她那短短的头发在海风中飞扬,身子灵活得像一只羚羊。
初蕾已快追上了赵震亚,她在后面大叫:“赵震亚!”“干什么?”赵震亚一边跑,一边喘吁吁的问。他那大头大身子,使他奔跑的动作极为笨拙。
“致秀在叫你!”初蕾嚷着。
“叫我做什么?”赵震亚的脚步缓了下来。
“她有话要对你说!”“什么话?”赵震亚的脚步更慢了。
“谁知道她有什么知心话要对你说!”初蕾追上了他,大声的嚷着:“你再不去,当心她生气!”
“是!”那傻小子停住了脚步,慌忙转过身子往回头就跑。
初蕾笑弯了腰,边笑边喘,她继续向梁致中追去。致中可不像赵震亚那样好追,他结实粗壮而灵活,长长的腿,每跨一步就有她三步的距离,她眼看追不上,又依样葫芦,如法炮制,大叫着:“梁致中!”梁致中已跑到岩石下面,对初蕾的呼唤,他竟充耳不闻,手脚并用,他像猿猴般在那岩石上攀爬。初蕾急了,放开喉咙再喊:“致中!梁致中!等我一下!”
“鬼才会等你!”致中嚷了回来。
“不等就不等!”初蕾咬牙喊:“你看看我追得上你追不上!”“哈!”致中大笑。“你要追我吗?我梁致中别的运气不好,就是桃花运最好,走到那儿都有女孩子追!”
“梁致中,你在胡说些什么?”初蕾恨恨的喊。
“我胡说吗?是你亲口说要追我呀!”“贫嘴!你臭美!”“我不臭美,是你不害臊!”
“要死!”初蕾冒火的叫,身子继续往前冲,猛不防,她的脚碰到了一块水边的浮木,身子顿时站不稳,她发出一声尖叫:“哎哟!糟糕!”刚喊完,她整个身子就摔倒在沙滩上了。沙滩边一阵混乱。初蕾躺在地上,一时间,竟站不起来,只是咬着牙哼哼。梁致文、梁致秀,和赵震亚都向她奔过去,围在她的身边。梁致秀蹲下身子,用手抱住她的头,急切的问:
“怎么了?初蕾?摔伤了那儿?”
初蕾往上看,赵震亚傻傻的瞪着她,一脸大祸临头的样子。梁致文微蹙着眉头,眼睛里盛满了关切与怜惜。梁致秀是又焦灼又关心,不住口的问着:
“到底怎样?伤了那儿?”
“致秀,”致文蹲下身子,“你检查她的头,我检查她的腿。”
初蕾慌忙把腿往上缩了缩,嘴里大声的呻吟,要命,那该死的梁致中居然不过来!她悄悄的对致秀眨了眨眼睛,嘴里的呻吟声就更夸张了:“致秀,哎哟……我猜我的腿断了!哎哟……我想我要晕倒了。哎哟……哎哟……”
致秀的眼珠转了转,猛然间醒悟过来了。原来这鬼丫头在装假,想用诱兵之计!她想笑,圆圆的脸蛋上就涌上了两个小酒涡。她偷眼看她的大哥梁致文,他的脸色因关切而发白了。她再偷眼去看她的二哥梁致中;天哪!那家伙竟然已经高踞在岩石的顶端,坐在那儿,正从裤子口袋里取出口琴,毫不动心的吹奏起口琴来了。
初蕾的“哎哟”声还没完,就听到致中的口琴声了,她怔了怔,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抬头一看,梁致中正高高的坐在那儿,笑嘻嘻的望着他们,好整以暇的吹奏着“散塔露琪亚”。她这一怒非同小可,跺了一下脚,她咬牙切齿的骂了一句:“混蛋!”就拔腿又对岩石的方向跑去。她这一跑,赵震亚可傻了眼了,他直着眼睛说:“她不是腿断了吗?”“她的腿才没断,”致秀笑着瞪了赵震亚一眼:“是你太驴了!”致文低下头去,无意识的用脚踢着沙子,他发现了那绊倒初蕾的浮木,是一个老树根。他弯腰拾起了那个树根,树根上缠绕着海草和绿苔,他慢腾腾的用手剥着那些海草,似乎想把它弄干净。致秀悄悄的看了他一眼,低声自言自语的说:“看样子,她没吓着要吓的人,却吓着了别人!”
“你在说什么?”赵震亚傻呵呵的问。
“没说什么!”致秀很快的说,笑着。“你们两个,赶快去帮我生火,我们烤肉吃!”
在岩石上,致中的“散塔露琪亚”只吹了一半,初蕾已爬上岩石,站在他的面前了。他抬眼看看她,动也没动,仍然自顾自的吹着口琴。初蕾鼓着腮帮子,满脸怒气,大眼睛冒火的,狠狠的瞪着他。他迎视着她的目光,那被太阳晒成微褐的脸庞上,有对闪烁发光的眼睛和满不在乎的神情。她眼底的怒气逐渐消除,被一种近乎悲哀的神色所取代了。她在他面前坐了下来,用双手抱住膝,一瞬也不瞬的看着他。
他把一支曲子吹完了,放下了口琴。
“你的嘴巴很大。”她忽然说。“丑极了。”
“嗯。”他哼了哼。“适合接吻。”
“不要脸。你怎么不说适合吹口琴?”
他耸耸肩。“我接吻的技术比吹口琴好,要不要试一试!”
“你做梦!”他再耸耸肩。“你的眉毛太浓了,眼睛也不够大,”她继续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没有致文漂亮?”
他又耸肩。“是吗?”他问,满不在乎。拿起口琴,他放到唇边去,刚吹了两个音,初蕾劈手就把口琴夺了过去,恨恨的嚷着说:
“不许吹口琴!”“你管我!”他捉住了她的胳膊,命令的说:“还给我!拿来!”“不!”她固执的,大大的眼睛在他的眼前闪亮。他们对峙着,他抓紧了她的胳膊,两人的脸相距不到一尺,彼此的呼吸热热的吹在对方的脸上。夕阳最后的一线光芒,在她的鼻梁和下颔镶上了一道金边。她的眼珠定定的停在他脸上,他锁着眉,眼光锐利,有些狞恶,有些野气。她轻嘘一声,低低的问:“你怎么知道我摔跤是假的?”
“谁说我知道?”他答得狡狯。
“噢!”她凝视他,似乎想看进他内心深处去。“你这个人是铁打的吗?是泥巴雕的吗?你一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吗?”
“你不是香,也不是玉。”他微笑了起来。
“说得好听一点不行吗?”她打鼻子里哼着。也微笑起来。
“我这人说话从来就不好听,跟我的长相一样,丑极了。你如果要听好听的,应该去和致文谈话。”
她的眼睛伫立刻闪过了一抹光芒,眉毛不自禁的就往上挑了挑。“噢!好酸!”她笑着说:“我几乎以为你在和致文吃醋!”
他放开抓住她的手,斜睨着她。
“你希望我吃醋吗?你又错了!”他笑得邪门。“你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你——”她为之气结,伸出手去,她对着他的胸口就重重一推。“哎呀!”他大叫,那岩石上凹凸不平,他又站在一块棱角上,被这么用力一推,他就从棱角上滑下来,身子直栽到岩石上去。背脊在另一块凸出的石头上一撞,他就倒在石块上,一动也不动了。“致中!”初蕾尖叫,吓得脸都白了,她扑过去,伏在他身边,颤声喊:“致中!致中!致中!你怎样?你怎样?我不是安心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她咬紧嘴唇,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他打地上一跃而起,弯腰大笑。
“哈哈!我摔跤显然比你摔跤有分量……”
“你……你……你……”初蕾这一下真的气坏了,她的脸孔雪白,眼珠乌黑,嘴唇发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瞪了他几秒钟,然后一摔头,回身就走,走了两步,才想起手中的口琴,她重重的把琴往石头上砸去,就三步两步的跳下了岩石,大踏步的走开了。
太阳早已沉进了海底。致秀他们已生起了营火,在火上架着铁架,一串串的肉挂在铁架上,肉香弥漫在整个的海边。
初蕾慢腾腾的走了过来,慢腾腾的在火边坐下,慢腾腾的弓起膝,用手托着腮帮子,对着那营火发怔。
致文仍然在剥着那大树根上的青苔和海藻,他脸上有某种深思的、专注的神情,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问题。
“你知道,杜老头那首‘八月秋高风怒号’的诗,主题只在后面那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后人推崇杜甫,除了他的诗功力深厚之外,他还有悲天悯人的心!”初蕾怔了怔,歪过头去看致文,她眼底闪烁着一抹惊异的光芒。她的神思还在致中和他的口琴上面,蓦然间被拉回到杜甫的诗上,使她在一时间有些错愕。她瞪着致文,心神不宁。致文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淡淡的笑了笑,就又低头去弄那树根,那树根是个球状的多结的圆形,沉甸甸而厚笃笃的。“我想,”他从容的说:“你已经忘记我们刚刚谈的题目了。”“哦,”初蕾回过神来。“没有,只是……杜老头离我们已经太远了。”她望向海,海面波潮起伏,暮色中闪烁着点点粼光。沙滩是绵亘无垠的,海风里带着浓浓的凉意,暮色里带着深幽的苍茫。致中正踏着暮色,大踏步的走来。初蕾把下巴放在膝上,虚眯着眼睛无意识的望着那走来的致中。
致文不经心的抬了抬头。
“无论你的梦有多么圆,”他忽然说:“周围是黑暗而没有边。”她立即回头望着致文,眼睛闪亮。
“谁的句子?”她问。“不太远的人,徐志摩。”他微笑着。
她挑起眉毛,毫不掩饰她的惊叹和折服。
“你知不知道,致文?你太博学,常常让人觉得自己在你面前很渺小。”他的脸涨红了。“你知不知道,初蕾?”他学着她的语气:“你太坦率,常常让人觉得在你面前很尴尬!”
她笑了。“为什么?”“好像我有意在卖弄。”
她盯着他,眼光深挚而锐利。
“你是吗?”她问。“是什么?”他不解的。
“卖弄。”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抹狼狈。
“是的。”他坦白的说:“有一些。”
她微笑起来,眼光又深沉又温柔,带着种醉人的温馨。她喃喃的念着:“无论你的梦有多么圆,周围是黑暗而没有边。”她深思,摇摇头。“不好,我不喜欢,太消极了。对我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怎么说?”“无论你的梦多么不圆,周围都灿烂的镶上了金边。”她朗声说。“这才是我的梦。”
她的眼睛闪亮,脸发着光。
“说得好!”他由衷的赞叹着:“初蕾,”他叹口气。“你实在才思敏捷!”“哇!”她怪叫,笑着:“你又来了!你瞧,你把我的鸡皮疙瘩又撩起来了!”她真的伸着胳膊给他看。
他也笑了,用手握了握她伸过来的手。
“你是冷了!”他简单明了的说:“你的手都冻得冰冰凉了。”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的肩上,那外衣带着他的体温,把她温软的包围住了。她有种奇异的松懈与懒散,觉得自己像浸在一池温暖的水中,沐浴在月光及星空之下,周围的一切,都神奇而灿烂的“镶上了金边”。
致中早已走过来好一刻了,他冷冷的看着这一切。看着他们两个有问有答,又看着致秀和赵震亚手忙脚乱的忙着烤肉、穿肉、洒作料……他重重的就在火边坐下,带着点捣蛋性质,伸手去抓火上的肉串,嘴里大嚷大叫着:
“哈!好香,我饿得可以吃下一条牛!”
“还不能吃!”致秀喊:“肉还没烤熟呢!”她夺下致中手里的肉串,挂回到架子上。
致中往后一仰,四仰八叉的躺在沙滩上,拿着口琴,送到嘴边去试音。那口琴已摔坏了,吹不成曲调,只发出“嗡嗡”的声响,致中喃喃的诅咒:
“他妈的!”赵震亚听了半天,发出一句评语:
“你吹得很难听!”致中抛下口琴,对赵震亚翻了翻白眼:
“人丑,说话不会说,连口琴都吹得难听,这就是我,懂了吗?”致秀看看二哥,再回头看看大哥。初蕾小巧的身子,懒洋洋的靠在致文身上,脸上有个甜得醉人的微笑,致文的一只手,随随便便的揽着初蕾的腰。他身子前面,放着那个他好不容易弄干净了的圆形大树根。
“这是什么?”初蕾问,用手摸索那树根,仰脸看致文,她的发丝拂在他的面颊上。对于致中的吼叫,她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致中拿起树根,举给初蕾看:
“像不像一个女人头?”他问。“像不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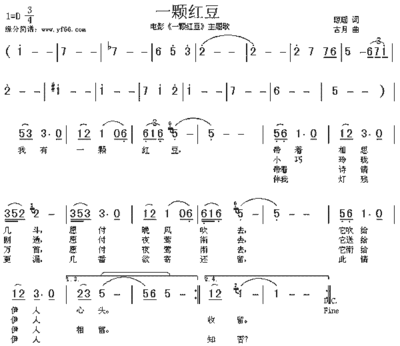
初蕾愕然,她仔细的看那树根。
“是的,像个人头,不过………”她小心翼翼的说:“我不会这么丑吧?”
致文失声大笑了。很少听到致文大笑的致秀,禁不住楞了楞。致中回头看了那木根一眼,轻哼了一声,眼睛望着天空,自言自语的说:“木头比人好看!它不会东倒西歪!”
初蕾吃惊似的回眼去看致中,挑起了眉毛,她似乎要发作,她的眼睛瞪圆了,脸色变了,致秀慌忙拍了拍手,大叫:
“肉熟了!肉熟了!要吃烤肉的统统过来!”
初蕾的注意力被肉串吸引住了,顿时间,只感到饥肠辘辘。她咽着口水,贪馋的对肉串望着,大家都对营火围了过去,火光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
夜色来了。
3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杜慕裳坐在女儿的床沿上,愀然的,怜惜的,心疼的望着那平躺在床上的雨婷。那么瘦,那么苍白,那么恹恹然了无生气,又那么可怜兮兮的。她躺在那儿,大睁着一对无助的眼睛静静的瞅着慕裳。这眼光把慕裳的五脏六腑都撕碎了。她伸手摸着女儿的下巴,那下巴又小又尖,脆弱得像水晶玻璃的制品。是的,雨婷从小就像个水晶玻璃塑成的艺术品,玲珑剔透,光洁美丽,却经不起丝毫的碰撞,随时随地,她似乎都可以裂成碎片。这想法绞痛了她的心脏,她轻抽了一口冷气,抬头望着床对面的夏寒山。
夏寒山正拿着一管好粗好粗的针药,在给雨婷做静脉注射。雨婷的袖管掳到肩头,她那又细又瘦的胳膊似乎并不比针管粗多少,白皙的手臂上,青筋脉络都清晰可见。寒山找着了血管,把针尖直刺进去,杜慕裳慌忙调开视线,紧蹙起眉头。她的眼光和女儿的相遇了,雨婷眉尖轻耸了一下,强忍下了那针刺的痛楚,她竟对母亲挤出一个虚弱而歉然的微笑。“妈妈,”她委婉而温柔的喊,伸手抚摸母亲的手。“对不起,我让你操了太多心。”
“怎么这样说呢?”杜慕裳慌忙说,觉得有股热浪直往眼眶里冲。“生病是不得已的事呀!”
“唉,”雨婷幽然长叹。“妈,你别太疼我,我真怕有一天……”“雨婷!”慕裳轻喊,迅速的把手盖在雨婷的唇上,眼眶立即湿了。她努力不让泪水涌出来,努力想说一点安慰女儿的话。可是,迎视着雨婷那悲哀而柔顺的眼光,她却觉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用牙齿咬紧了嘴唇,来遏止心中的那种恐惧和惨痛。寒山注射完了,抽出了针头,他用药棉在雨婷手腕上揉着,一面揉,他一面审视着雨婷的气色,对雨婷鼓励的笑了笑,说:“你会慢慢好起来,雨婷。但是,首先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雨婷望着寒山,她的眼光谦和而顺从,轻叹了一声,她像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夏大夫。我真谢谢你,这样一次又一次麻烦您来我家,我实在抱歉极了。”
“你不要对每个人抱歉吧,雨婷。”杜慕裳说,拉起棉被,盖在她下颔下面。“这又不是你的错。”
“总之——是为了我。”雨婷低语。
寒山收拾好他的医药箱,站起身来。
“好了,”他说:“按时吃药,保持快乐的心情,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希望过两天,你已经又能弹琴唱歌了。好吗?”“好!”雨婷点头,对寒山微笑,那微笑又虚弱,又纯挚,又充满了楚楚可怜的韵味。“您放心,夏大夫,我一定会‘努力’好起来。”寒山点点头,往卧室外面走去。杜慕裳跟了两步,雨婷在床上用祈求的眼光看她,低唤了一声:
“妈!”慕裳身不由己的站住了,对寒山说:
“你先在客厅坐一下,我马上就来!”
“好!”寒山退出了卧室。慕裳又折回到床边,望着女儿。雨婷静静的看着她,那玲珑剔透的眸子似乎在清楚的诉说着:别骗我!妈!我活不了多久了。蓦然间,她心头大痛,坐在床旁,雨婷一下子就跳起来,用双手紧紧的搂住了母亲的脖子,她那细弱的胳臂把慕裳紧箍着,她的面颊依偎着她,在慕裳耳边悲切的低语:“妈,我不要离开你,我不要!如果我走了,谁再能陪伴你,谁唱歌给你听?”“噢!”慕裳悲呼,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了。“雨婷,不要这样说,不会的,决不会的!夏大夫已经答应了我们,他会治好你!”雨婷躺回到床上,她的眼光清亮如水。
“妈妈,”她柔声说:“你和我都知道,夏大夫是个好医生,可是,他并不是上帝。”“不!”慕裳用手遮住了眼睛,无助的低语:“不!他会治好你,他答应过的,他会,他答应过的!”
雨婷把头转向了一边,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可怜的妈妈!”她耳语般的说了句。
成串的泪珠从慕裳眼里滚了出来,可怜的妈妈!那孩子心中从没有自己,每次生病,她咬住牙忍住疼痛,只是用歉然的眼光看她。可怜的妈妈!她那善良的、柔顺的心中,只有她那可怜的妈妈!她不可怜自己,她不感怀自伤,在被病魔一连串折磨的岁月里,她那纯洁的心灵中,只有她的母亲!她用手背拭去泪痕,再看雨婷,她阖着眼睛,长睫毛细细的垂着,似乎睡着了。她在床边再默立了片刻,听着雨婷那并不均匀的呼吸声,她觉得那孩子几乎连呼吸都不胜负荷,这感觉更深更尖锐的刺痛了她。俯下头去,她在雨婷额上,轻轻的印下一吻,那孩子微微的翻了个身,嘴里在喃喃呓语:
“妈,我陪你………你不要哭,我陪你………”
慕裳闭了闭眼睛,牙齿紧咬着下嘴唇。片刻,她才能平定自己的情绪,轻轻的站起身来,轻轻的走到窗前,她轻轻的关上窗子,又轻轻的放下窗帘,再轻轻的走到门边。对雨婷再投去一个依恋的注视,她终于轻轻的走出了房间。
夏寒山正在客厅中踱来踱去,手里燃着一支烟,他微锁着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喷着烟雾,似乎被某个难题深深的困扰着。杜慕裳走近了他。他站定了,他的眼光锐利的注视着她,这对眼睛是严厉的,是洞烛一切的。“你哭过了。”他说。她用哀愁的眼光看他,想着雨婷的话:妈妈,你和我都知道,夏大夫是个好医生,但是,他并不是上帝。她眨动眼帘,深深的凝视他,挺了挺背脊,她坚强的昂起下巴,哑声说:“告诉我实话,她还能活多久?”
他在身边的烟灰缸里熄灭了烟蒂,凝视着她。她并不比念苹年轻,也不见得比念苹美丽,他模糊的想着。可是,她那挺直的背脊,那微微上昂的下巴,那哀愁而动人的眼睛,以及那种把命运放在他手中似的依赖,和努力想维持自己坚强的那种神气……在在都构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强大的引力,把他给牢牢的吸住了。一个受难的母亲,一个孤独的女人,一个可怜的灵魂,一个勇敢的生命……他想得出神了。
他的沉默使她心惊肉跳,不祥的预感从头到脚的包围住了她。她的声音簌簌发抖:
“那么,我猜想的是真的了?”她问:“你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骗我了?事实上,她是活不久了,是吗?”她咬紧牙关,从齿缝中说:“告诉我实话,我一生,什么打击都受过了,我挺得住!可是,你必须告诉我实话!”
他紧盯着她。“你不信任我?”他终于开了口:“我说过,我会治好她!”
她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他说得多坚决,多有份量,多有把握!上帝的声音,也不过是如此了。她眼中又浮起了泪痕,透过泪雾,他那坚定的面庞似乎是个发光体,上帝的脸,也不过是如此了。她几乎想屈膝跪下去,想谦卑的跪下去………他忽然捉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上帝的手,也不过是如此了。“过来!”他命令的说,把她拉到沙发前面。“坐下!”他简短的说。她被动的坐在沙发里,被动的望着他。
他把自己的医药箱拿了过来,放在咖啡桌上,他打开医药箱,从里面取出一大叠X光的照片,又取出了一大叠的病历资料和检验报告。他把这些东西摊开在桌面上,回头望着她,清晰的、稳定的、强而有力的说:
“让我明白的告诉你,我已经把雨婷历年来的病历都调出来了,检查报告也调出来了,从台大医院到中心诊所,她一共看过十二家医院,从六岁病到现在,也整整病了十二年。平均起来,刚好一年一家医院!”
“哎!”慕裳轻吁了一声。“我从没有统计过,这孩子,她从小就和医院结了不解之缘。”
“她的病名,从各医院的诊断看来,是形形色色,统计起来,大致有贫血、消化不良、轻微的心脏衰弱,一度患过肝炎,肝功能略差,以及严重的营养不良症。”
“我……我什么补药都买给她吃,每天鸡汤猪肝汤就没断过,我真不知道她怎么会营养不良。”慕裳无助的说:“以前的周大夫,说她基本体质就有问题,说她无法吸收。无法吸收,是很严重的,对吗?”
夏寒山定定的看着她。
“如果不吃,是怎样都无法吸收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不吃?”慕裳惊愕的抬起眼睑:“你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没有做给她吃吗?”“你做了,她不一定吃了!”
慕裳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不懂。”她困惑的说。
“让我们从头回忆一下,好不好?”他的眼光停在她的面庞上。“她第一次发病是六岁那年,病情和现在就差不多,突发性的休克,换言之,是突然晕倒。晕倒那天,你们母女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眼珠转了转,然后,就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上了她的面颊。“是的,”她低声说:“那是她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想到再嫁。有位同事,和我一起在大使馆中当翻译,追求我追求得很厉害……”她咽住了,用手托着头,陷入某种回忆中,她的眼睛浮起一层朦朦胧胧的雾气,唇角有一丝细腻的温柔。不知怎的,这神情竟微微的刺痛了他。他轻咳了一声,提醒的说:“显然,这婚事因为雨婷的生病而中止了?”
“是的。”她回过神来。“那年她病得很凶,住院就住了好几次,我每天陪她去医院,几乎连上班都不能上,那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那同事去了美国,现在已经儿女成群了。”“好,从那次以后,她就开始生病,三天两头晕倒,而医院却查不出正确的病名。”
“是的。”夏寒山不再说话,只是镇静的看着她。于是,她有些明白了,她迎视着他的目光,思索着,回忆着,分析着。终于,她慢慢的摇头。“你在暗示……她的病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她说了出来。“我没有暗示,”夏寒山稳定的说:“我在明示!”
“不!不可能!”她猛烈的摇头:“心理病不会让她一天比一天衰弱,你难道没看出来吗?她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轻得连风都可以把她吹走,而且,她那么苍白,那么憔悴,这些都不是装出来的……”
“我没有说她是装出来的!”夏寒山沉着的说:“她确实苍白,确实憔悴,因为她又贫血又营养不良!她在下意识的慢性自杀,怎么会不憔悴不苍白!”
“慢性自杀?”她惊呆了,睁大了眼睛。她不信任自己的听觉:“你说什么?慢性自杀?她为什么要慢性自杀?她三岁失去父亲,我们母女就相依为命,我又爱她又宠她,她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事……”“并不是不满足,而是独占性!”寒山打断了她:“她从六岁起就在剥夺你交男朋友的自由!她在利用你的爱心,达到她独占你的目的,她知道你的弱点,她就利用这项弱点,只要她一天接一天的生病,你就一天接一天的没有自由……”
她的脸色变白了,她的眼神阴暗。
“你……你……”她开始有些激动。“你根本没弄清楚!这样说是冷酷的!你不了解雨婷!她从小就没有自我,她一心一意要我快乐,每次生病,她都对我说:对不起,妈妈。我好抱歉,妈妈……”“我知道!我亲耳听过几百次了!”他又打断了她,沉声的,稳定的,几乎是冷酷的说了下去:“她越这样说,你越心痛,只要你越心痛,你就越离不开她!我曾经有个女病人,也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她的丈夫,只要丈夫回家晚三分钟,她就害病晕倒。我告诉你,你必须面对现实,雨婷最严重的病,不在身体上,而在心理上。她在折磨你,甚至于,在享受你的痛苦,享受你的眼泪,记住,她做这一切是出于不自觉的,她并不是故意去做,而是不知不觉的去做……”
“不是!”她叫了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眼睛里涌满了泪水:“你这样说太残忍,太冷酷,太无情!你在指责她是个自私自利而阴险的坏孩子!但是,她不是!她又乖巧又听话,她一切都为别人想,她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善良得像一只小白兔!她没有心机,没有城府,她是个又孝顺又听话又善解人意的女孩!你这样说,只因为你查不出她的病源,你无能,你不是好医生,你们医生都一样,当你查不出病源的时候,你们就说她是精神病!”
夏寒山站在那儿,他静静的望着她,静静的听着她激动的、带泪的责备。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为自己解释,当慕裳说他“无能”的时候,他只轻微的悸动了一下。然后,他慢慢的走到咖啡桌边,把摊在桌上的病情资料,和X光照片收进医药箱里去。慕裳喊完了,自己也被自己激烈的语气吓住了,她呆坐在那儿,呆望着他收拾东西,眼看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收进箱子里,眼看他把医药箱合了起来,眼看他拎起箱子,眼看他走向门口……她爆发的大叫了一声:
“你要到那里去?”
他站住了,回过头来,他的眼神温柔而同情,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火气,却充塞着一种深切的关怀与怜恤,他低沉的说:“放心,我会治好她!”
她陡然间崩溃了。她奔向了他,站在他面前,大大的眼睛里,盛满了悲凉与无助,盛满了祈求与歉意,她蠕动着嘴唇,呻吟般的低语:“我昏了,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他注视着那茫然失措的脸,忧患、寂寞、孤独、无助、祈谅、哀恳……都明写在那张脸上。他又感到那种强烈吸引他的力量,不可抗拒般的力量。然后,他不知不觉的放下了医药箱,不知不觉的伸出手去,不知不觉的把她拉进了怀里,不知不觉的拥住了她,又不知不觉的把嘴唇盖在她的唇上。
片刻,他抬起头来,她的眼睛水汪汪的闪着光。她显然有些迷惑,有些惊悸,像冬眠的昆虫突然被春风吹醒,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来迎接这新的世界。可是,崭新的,春的气息,已窜入到她生命的底层,掀攘起一阵无法平息的涟漪。她喘息的,惶惑的凝视着他,低问了一句:
“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他答得坦率,似乎和她同样惶惑。“很久以来,就想这样做。”“为什么?”她固执的问。
“你像被冰冻着的春天。”他低语。
冰冻着的春天,骤然间,这句相当抽象的话却一直打入她的心灵深处,这才醒悟自己虚掷了多少岁月!她扬着睫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面前这个男人,不,这个医生,他不止在医治病患,他也想挽住春天?忽然间,她有种朝圣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到圣庙前的感觉;只想倒下来,倒下来什么都不顾。因为,圣庙在那儿,她的神狄苍谀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