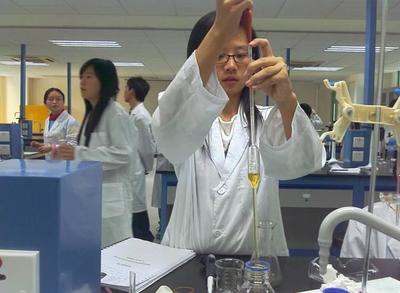人类的十字路口——伊朗高原
伊朗高原是亚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帶。伊朗高原由小亚細亚和高加索開始,一直向東延伸,包括現今阿富汗的絕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伊朗高原面積約250萬平方公里,其東部邊界是兴都庫什山脉,它將伊朗與印度分開;其西部邊界是扎格羅斯山脉,它將伊朗高原與底格里斯河谷分開;其南部邊界是印度洋和波斯灣;其北部邊界是阿拉斯河、里海、科彼特山鏈、阿姆河以南的帕羅帕米蘇斯山。伊朗高原周圍被雄偉的高山所包圍,高原中央是遼濶的內陸盆地,沒有河流通往大海。從伊朗高原各山脉內坡流出的河流,全都消失在這個干燥貧瘠的盆地之中。伊朗農業條件最好的地區,是毗鄰兩河流域的胡澤斯坦地區,還有北部、西北部山鏈的山麓與河谷地區,特別是里海、高加索山脉的斜坡地區。按照自然地理環境,伊朗高原可以劃分為五個特征明顯的自然地區:一,扎格羅斯地區;二,內陸茺漠盆地或中央茺漠盆地;三,里海沿岸地區;四,古代的帕提亚地區;五,東伊朗地區。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但不管哪种假说,都说明中亚地区对于研究人类及其语言的多样性极其重要。这是笔者近十年来基于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成果而获得的一点认识。在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学者外,还先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王士元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院士、金锋博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李辉博士,上海癌症研究所吕宝忠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等的指教。国表中所列雅弗的诸国创10:2-5中,已肯定辨识出来的是雅完(希腊);玛各,米设,与土巴(俄罗斯);歌篾(德国),提拉(色雷斯,埃特鲁斯坎)玛代(玛代),亚实基拿(德国),陀迦玛(亚美尼亚),与多单(Dardanians)。他们大多数都似乎移居欧洲,一般说来,成了所谓高加索人与亚利安人种的祖先。『当然,之后,他们再散布到美洲,南非,及许多海岛上去。闪的后裔,创10:21-31特别包括希伯(希伯来人),以拦(波斯)亚述(亚述)及后来藉以实马利,以扫,及亚伯拉罕其它的后裔(并摩押,亚们,及罗得的后裔)的阿拉伯国家。
一些含的后裔创10:6-20,都相当清楚的辨认出来,尤其是麦西(埃及),古实(埃塞俄比亚)迦南(迦南人,腓立基人,赫人)及弗(利比亚)。虽然谱系不容易追溯,很可能黑人的各民族也是含的后裔,因为,似乎只有含的后裔才迁到非洲去。最先的巴比伦人、苏美人,也是含的族系,属于宁录的一支。
蒙古人的祖先较难找出来。但是,一些考虑似乎也显明这些民族也是含的后裔。第一,藉筛减法,因为闪及雅弗族系已经清楚找出来,其它的就该假设都属乎含族。第二,西尼人创10:17被列为迦南的后裔,可能这个名字,与中国有字源上的关联。第三,中国的古名为Cathay,有证据显明,这个名字出自Khetae, Khetae又可能出自赫人,赫则是迦南的儿子。第四,在身体特征及语言方面,蒙古人更像含族,与已知的闪族及雅弗族,则较少相似。这些理由当然贫弱,诚然还有极大的空间可以研究这些人及他种早期人来源,而获得丰硕的成果。若是人种学家用创世记第十章与十一章作研究指南,以代替大多数现代古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的进化论的猜想,他们无疑的能够澄清许多不能确定的地方。一位在这方面写作甚丰立论精辟的古人类学家是库斯坦司博士(Dr.Arthur Custance) Khazanov划定的中东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相当于ThomasJ.Barfield划定的“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的游牧文化区。在现代民族志材料中,这里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根据地势依海拔高度迁徙,畜群种类颇有差异,包括绵羊、山羊、马、双峰驼和驴,牧民在农庄里饲养对牧埸和水源要求更高的牛,用畜肉和毛、奶、皮革制品与农民交易谷物和其它制品,谷物在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牧民用黑山羊毛织物制作的帐篷设立营地。以下是Khazanov对中东地区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评述。
畜牧甚至半游牧人群出现在伊朗山地和亚美尼亚高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年代非常旱,但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游牧民。古提安人(Cutians)和加喜特人(Kassites)似非真正的游牧民,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公元前第一千纪和公元第一千纪前半叶的流动畜牧者,这与中世纪的景象迥然有别。在古典期的小亚细亚,虽然畜牧人群随季节变化将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却不是真正游牧民;在古典期的伊朗,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的六个部落中有四个是游牧民。史料中的畜牧者虽然普遍,真正的游牧民却较少,法尔斯地区(Fars)有骆驼饲养者。其后第一批出现的游牧民是山地居民,他们给各种政治集团特别是希腊人带来冲击,被称为“流浪者”和“抢劫者”。马地亚人(Mardeans)、卡都西亚人(Cadusians)、科萨亚人(Cossaeans)、攸克西亚人(Uxians)、埃拉米亚人(Elameans)、帕瑞塔卡人(Paraetaceni)与后来的库尔德(Kurds)人和鲁尔人(Lurs)相似,与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也有些相似,均存在辅助性的定居和农业。在畜种构成方面,这些山地部落的小牲畜与大牲畜同样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乘畜,几乎没有马匹,更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原始印欧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可以认为在东欧、南俄、西亚和中亚这些区域之间。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欧人为何,至今也无定论,因为当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印欧部落姗姗进入历史舞台之时,在三大洲交接处早已兴盛多时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达罗毗图人等。安纳托里亚地区赫梯人的重新发现将印欧人的历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显太晚;直至近世对丝绸之路上重新发现的吐火罗语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学者们才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语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欧人。
现在的欧洲固然是印欧语的天下,然而远古并非如此,至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远古居民不是说印欧语的,例如西欧的巴斯克人就是古代欧洲非印欧语人的遗裔,而南部的伊比利亚和亚平宁乃至巴尔干地区在凯尔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迁入之前也都生活着说非印欧语的居民。这充分表明,原始印欧人绝不是欧洲的土著,而是本来位于欧洲东部或东方,后来才向西迁徙的。因此,最早的印欧人是生活在比后来更靠东的地方,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文明,从而激励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吐火罗语的原始性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为了在文献记载上找到最早出现吐火罗人的踪迹,学者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W.B.Henn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库提人”(Guti/Kuti)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亨宁从语言学上进行论证,将一些库提语专有名词与吐火罗语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邻的东方有一个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Tukri),这正是“吐火罗”、“敦煌”等名称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库提”则可以对应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等名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则和伊凡诺夫由亨宁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了这样的推断: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纪,原吐火罗语便已经分化为两大互有差异的方言,这两大方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库提语和图克里语。将公元前三千~二千纪近东的古代民族库提人(包括Kuti和Tukri)跟后代的吐火罗人(他们留传下晚至公元一千纪后期的用两种方言写成的文献材料)等同起来的观点,与吐火罗语比许多其它印欧语言更具古老性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分离出来的年代应该定在印欧语尚未扩散出其起源地之前和安纳托里亚语分化之后,也就是说,吐火罗语独立的时间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纪初,甚至更早。分成两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联系的群体的吐火罗诸部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他们经历许多国家,来到中央亚细亚,一路上留下了属于公元五~八世纪的吐火罗语文献。在这样的推断下,吐火罗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从近东、伊朗西部(在这里他们以“库提人”而为人所知)到中央亚细亚(他们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亚的广阔区域内——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古代伊朗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正可以发现,在伊朗和中国之间远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一条商路,而这条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长期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欧人——吐火罗人。
二、吐火罗与大夏
“吐火罗”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罗的译音。“大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个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说成立,那么此时出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从近东迁来的兄弟部族“库提”和“图克里”。
由于吐火罗人到达中央亚细亚的时间远早于另一支印欧人——雅利安人,因此,原始印欧人同原始汉藏人的接触最早主要是通过吐火罗人与华夏人的交流来实现的。根据以蒲立本为代表的一些汉学家对上古汉语与上古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汉语中有若干词汇系来源于印欧语(主要是吐火罗语),如“蜜、犬、剑、昆仑/祁连”以及“乾坤”的“乾”等等。将这些词汇带入汉语的,正是活动于上古东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曾远征大夏),稍后西迁;禺知则发展为强大的月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中亚到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
“大夏”后来再次出现在中国史籍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被张骞称为“大夏”的那个区域在西方文献中叫做“巴克特里亚”,到了贵霜、嚈哒及突厥人入侵之时,便通称为“吐火罗斯坦”了。
三、雅利安与伊朗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欧人中发生了著名的雅利安人大迁徙,这次迁徙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夏末商初。雅利安人与吐火罗人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两者属于印欧语中不同的两大语组(Satem与Centum),吐火罗人虽然后来的地理位置在雅利安人的东边,但由于它远早于后者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因此吐火罗人的语言反倒更接近西部的印欧人如拉丁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雅利安人在语言上大致对应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雅利安”(Aryan)是其自称,意为“高贵的”,盖因雅利安人迁入之地本为达罗毗图人所有,雅利安人在征服他们之后,便以“高贵者”自居。
此次迁徙主要分两个大方向,向南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达罗毗图人,是为印度-雅利安人;向西南的一支进入伊朗高原,征服了亚述人和埃兰人,是为伊朗-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并带去了他们的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后来发展为印度教;伊朗-雅利安人则分为两支,西支为米底人和波斯人,分别进入伊朗高原西北部和西南部,东支通称为东伊朗人,主要进入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后来成为波斯国教的祆教最先即是由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创立于东伊朗。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米底人首先崛起,推翻了亚述人的霸权;不久波斯代兴,居鲁士二世于前六世纪后期统一了整个伊朗高原,建立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强大的波斯帝国;与之相对,东伊朗人则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更喜欢城邦自治的形式,像花拉子模(火寻)、索格底亚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等都是很古老的城邦国。后来出现的“伊朗”(Iran)这个名称,便是由“雅利安”演变而来,因此最初只是雅利安人一个部落名称的“波斯”远没有“伊朗”的涵盖面广,此外,“伊朗”将东伊朗人也包含在内,尽管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很早便已分离;不过,这层含义在现代只局限在语言学中(东伊朗语支),而在其他方面,“伊朗”人显然是不能将中亚的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等等)包含在内的。
虽然同为印欧人,但雅利安人同吐火罗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区别在语言上的明显性也暗示出其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雅利安人是比较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吐火罗人则因东迁较早而混入不少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和汉藏人的血液,白种特征已不甚明显;雅利安人较早进入定居生活,如印度、波斯等,都建立了较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吐火罗人则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商业,充当着东西交流的媒介。
四、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势必会对早已到达中央亚细亚的吐火罗人造成影响,在两者交界的区域,部落人民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与重组是相当自然的。本节拟从西方史料的记载出发,结合东方文献,简要分析古代中亚地区与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有关的游牧部落。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南迁后,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后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马萨革泰人因受东方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关于伊塞顿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处只需大致指出,这是一个吐火罗-雅利安混合部落;而对于阿里玛斯普人,则因资料缺乏,很难作具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阿里玛斯普”是斯基泰语的名称,意为“一目”,联系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记载有一个“一目国”,因此这个民族的存在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黄时鉴认为,该族可能是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语部落,对应于前匈奴人,西方则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中国古史中的猃狁;但无论是“前匈奴”还是“猃狁”,他们都同蒙古高原直至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关。分析一下此时的东方,我们发现,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关于这方面将在后文详析,此处不赘述)。周人和犬戎的关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后,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后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后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前述将阿里玛斯普人比定为猃狁的假说,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力向西移动。此后,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人史》中,将“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等同起来,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但从地域上来看,两者差别太大,中间还相隔有不少别的部落。不过,从名称上分析,“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的确存在某种关系:“Massa-”是雅利安方言“大”的意思,“Getae”则可以对应“月氏”。如果我们联系到亨宁的假说,那么此处的“Getae”和“月氏”就都可以看成是“古提”(Guti)的对音,即他们与更早的古提/库提人可能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马萨革泰人中存在着吐火罗成分。但是从地域上看,由于夹在属于雅利安人的斯基泰人和吐火罗-雅利安混合的伊塞顿人之间,马萨革泰人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吐火罗人,而又与邻近的斯基泰人习俗相近,因此他们很可能也是雅利安-吐火罗混合部落。
五、月氏、乌孙与塞种
汉文史籍中的“月氏”,更早的形式为“禺知、禺氏”等,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活跃于中国西北的民族。根据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月氏语很可能是吐火罗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将月氏视为亨宁假说中的古提人东迁到中央亚细亚的后裔之一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推测。月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天山中部一直延伸到贺兰山甚至黄土高原,但它的核心则在河西地区。林梅村提出,月氏的故乡应当在天山北麓东段的巴里坤草原,从游牧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月氏同许多吐火罗人部落一样,也不仅仅是游牧民族,而是过着一种筑城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生活。很可能,河西一带本来是一些小的吐火罗城邦,月氏人向东扩张征服了他们,于是月氏人的中心也移到了河西。月氏人在河西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中有很多都能用吐火罗语去解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实月氏人原先是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昭武城是月氏在河西的故都,“昭武”其实就是“张掖”的异译,两者都是吐火罗语“王都、京城”之意。“姑臧”是武威/凉州的旧称,也出自吐火罗语,它与同属吐火罗人城邦的“高昌”可能是同源词,高昌的主人姑师/车师的得名也可能与此有关。“敦煌”,在更早的史籍如《山海经》中写作“敦薨”,正是“大夏”/“吐火罗”的异译。“祁连/昆仑”,经林梅村考证,原来也是吐火罗语,意为“天”,它的原型与同属Centum语组的拉丁语的“天”Caelum非常相似。
说到月氏,就不得不提及乌孙。乌孙本来与月氏一道,都在“敦煌、祁连间”游牧,但乌孙的势力似乎不及月氏大,并且原来可能还附属于月氏。据蒲立本的看法,乌孙语可能也是一种吐火罗语,因此乌孙人原先也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乌孙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西戎中的“允姓之戎”,秦穆公所灭西戎八国中的“乌氏”可能也与之有关,联系到西戎中的吐火罗成分,蒲立本的看法显然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西戎中有斯基泰成分或者说操雅利安语的部落——在当时雅利安人的最东端大概也就在天山中部一线,因此将月氏和乌孙归入伊朗语部落似乎不大合情理,不过乌孙的居地更偏西,可能已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相邻,故而其杂有雅利安血统也并非没有可能,史载乌孙于西域诸族中欧罗巴人种特征最明显,也可作一旁证。
匈奴兴起后,击败月氏,月氏西逃,仓卒间将乌孙击破,乌孙在匈奴扶植下恢复后,发动复仇之战,彻底击破月氏,月氏西迁,引发了原居天山北麓西段至哈萨克草原的塞种部落的大迁徙;这个塞种部落,实则正可以大致对应西方史料中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由四个较大的部落组成,以阿息(Asii)部落为首(伯恩斯坦认为“阿息”就是“乌孙”,伊塞顿实乃以乌孙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他为加兹亚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i)和萨卡劳利(Sacarauli),阿息和加兹亚尼分别与乌孙和月氏同源,都属吐火罗部落,而Tochari则更是毫无疑义的吐火罗人,因此,伊塞顿部落联盟中实际上只有萨卡劳利可能是属于斯基泰即操伊朗语的部落,其他则都是吐火罗部落。不过,塞种部落虽然由吐火罗部落占统治地位,但其组成中可能更大多数是操雅利安即伊朗语的萨迦(斯基泰)人部落(如萨卡劳利部落),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曾经大部是塞种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和田、疏勒一带发现的“塞语”多被认为属伊朗语。
六、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各种假说,仅就与吐火罗有关的一些材料稍作探究。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后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后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后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后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后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后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后,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后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后,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后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后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后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后,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后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后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后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后来匈奴的主要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的吸收定然不少。例如,“祁连”本为吐火罗语的“天”,月氏被匈奴击败后,其故地的“祁连山”落入匈奴之手,久之竟成为匈奴的要地,后来汉夺其地,匈奴人无不叹息,每每哀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生息”,殊不知那本是吐火罗人之地。而匈奴人称“天”为“祁连/撑犁”也极可能是从吐火罗人那里继承,这一称呼也传给了后世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等民族,至今蒙古人仍称“天”为“腾格里”。
七、马、鹿、龙、羊、狼之族
古代的民族曾普遍经历游牧时期,而游牧民族多以某种动物来标志其族。如突厥人以狼为贵,自称“狼种”,华夏人则自命为“龙种”。
吐火罗人作为最早游牧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民族,他们的标志最有可能与马有关。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中的斯基泰人是最早的骑马民族,马具及骑射之术也出自他们。但是,从时间上来看,雅利安人进入中央亚细亚要晚于吐火罗人,而驯马的起源更可能是在那里;再则,斯基泰地域的更明显的标志是所谓的“鹿石文化”,从其可知,斯基泰人对鹿更为尊崇。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马方”有可能即与吐火罗人有关——其时殷人尚不可能与斯基泰人接触。
大概吐火罗人很早即以对马匹的善牧和品种的改良而闻名,因此位居犬戎前沿的秦、赵之祖在其影响之下,也练得一手高超的养马与御马的本领。赵人的祖先造父即以异常出色地为周穆王驾御马车而发迹,受封于山西的赵城,同族的秦人也一并受惠,后来非子也因善牧被封于秦,其嫡支则在犬丘,与犬戎关系更为密切;非子之后为周击犬戎,立下大功,渐渐取得关中之地,因此秦人所受吐火罗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赵氏后来成为晋国大卿,分晋之后,因北与戎狄相接,遂对其大加挞伐,而赵氏本就善牧,地域的影响使其习俗也渐染胡化——赵襄子在灭知伯后,曾漆其头为饮器,此俗不见华夏,却见于斯基泰、月氏、匈奴,据此可以推测,当时赵国已与鄂尔多斯一带的月氏人有所接触,甚至有可能也接受了斯基泰人的一些风俗:由墓葬可知,斯基泰人存在将马带上角装扮成鹿的风俗,这也可折射出其对鹿的崇奉;另一方面,赵氏之后的赵高在秦二世统治期间,曾有“指鹿为马”之举(日语中仍有“马鹿”一词,意为胡说),疑此即与斯基泰人扮马为鹿的习俗有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除受到赵国北方民族的影响外,赵氏自身的戎狄因素也是很值得考虑的。继犬戎之后最强大的西戎部落为义渠,“义渠”之名可能与吐火罗语“马”有关,似也可表明义渠以马著称;而后来作为人质的冒顿逃回匈奴,也正是靠盗取月氏的宝马;凡此种种,说明吐火罗人的确与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月氏人尤其以盛产宝马出名。林梅村认为,汉藏语的“龙”与“马”可能有某种同源关系,尤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月氏人将宝马称作“龙”,正是月氏人的西迁,带走了宝马的品种,也带走了月氏人牧养、驯服宝马的专利技术——“豢龙术”,中原人从此与良马绝缘,只在传说中依稀保留着“龙”的故事。直到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才重新得知大宛的宝马,但此时他们已然忘记,这些“天马”就是他们从前传说中的“龙”。在吐火罗语中,“马”和“龙”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有些吐火罗方言的“神、帝”一词,也与“龙”有关;据此,吐火罗人与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汗地区出土的一处大型贵霜王室墓葬表明,其中有不少与龙有关的饰物,而它们并非从中原输入。华夏人的圣物也是龙,但华夏人与吐火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似乎只能在黄帝部落东来以前,两者各自的龙究竟有何关系已很难推断了。“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象,其起源也各异,东方的“龙”可能与鳄鱼有关,西方的“龙”可能与巨蛇有关,吐火罗人的“龙”则可能与对“马”的崇拜有关。后来属于吐火罗人一支的焉耆人即以“龙部落”为名,焉耆人的首领也被称为“龙王”。
史载,羌人主牧羊,本为“西戎中之卑贱者”,然则西戎之中当有尊贵者,联系当时情景,犬戎最有可能为其尊者。然而犬戎以犬为贵,似乎与吐火罗人的马崇拜不合。案犬、狗、狼实为一体,本来都是游牧民族羊群的保护者(至今牧人仍有牧羊犬之种),后世的高车、突厥、回鹘等都以狼为尊,似乎可以推测阿尔泰人中突厥语民族早期的崇拜物也是犬、狼;因此,犬戎有可能是吐火罗人与前突厥人的混合民族。周穆王曾伐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可证其确与狼崇拜有关,此处的白鹿则有可能与染入犬戎中的斯基泰因子的鹿崇拜有关;又,蒙古的始祖传说为苍狼与白鹿,可知蒙古核心部落的祖先也与突厥有关,而此处之白鹿则与斯基泰无关,而系出自东胡——兴安岭地区自古即有对鹿之崇拜。
八、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月氏西迁,先居于伊犁、楚河流域一带,后在匈奴老上单于时,复为乌孙所破,于是继续南迁,进入锡尔河流域。当以吐火罗人为首的塞人部落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月氏在索格底亚纳地区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土著本为东伊朗人,被月氏征服后,王族也易为月氏人,而被统治的广大臣民则是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稍后,月氏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吐火罗人的大夏国,旋又分为五大翕侯长期割据混战,最终,约在公元一世纪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崛起时,西边波斯故地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已经衰落,贵霜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又侵占了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约在二世纪中,贵霜内乱,一部分不愿屈服于南面渐染印度传统的王朝的贵霜移民遂向东方故地迁徙,他们取道楼兰、敦煌,进入河西,少数并一直到达洛阳。这些贵霜人由于离开故地河西已逾三百年,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中亚物品来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便活跃于中亚与河西之间的商路上,为贵霜及中原人作贸易交流,这在敦煌、楼兰的出土文书中都有证明。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叶,史载灵帝喜好胡物,洛阳一时胡风大盛,此即与贵霜移民的到来颇有关系。在董卓从西凉带去的部队中,除羌胡外,也有不少支胡,即月氏胡,这些月氏人可能是小月氏或卢水胡部落,也可能与贵霜移民有关。例如董卓的女婿牛辅即有手下名支胡赤儿,而出身武威的张绣也有部将名胡车儿(即《三国演义》中盗取典韦双戟、致其战死之人),他们很可能都是月氏人。另有若干支姓高僧在洛阳传播佛教,更有一部分人后来南迁到东晋加入清谈玄佛的行列,这些则肯定是来自中亚贵霜的大月氏人。
贵霜在四世纪时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嚈哒的族源,似乎与东胡有关,蒲立本将其视为西迁的乌桓部落,余太山则将其与西部鲜卑中的乞伏、乙弗联系起来。嚈哒一度役属于柔然,后征服索格底亚纳,并于五世纪时南下击破贵霜,进而西向与萨珊波斯争雄,后于六世纪中叶被突厥与波斯联手灭掉。嚈哒馀部继续存留于吐火罗斯坦,并在后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创建的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后改名杜兰尼),而“阿布达里”(Abdelai)正是古代的“嚈哒”(Hephthalitai)。
自贵霜兴起以来,索格底亚纳一直是由月氏王统治下的粟特诸城邦并立着,在嚈哒入侵期间,诸王不得不暂时屈服,连姓氏也改易为“温”;后当嚈哒人的统治被推翻后,诸王又恢复其姓为“昭武”,意在重提其月氏传统——昭武为月氏在河西故地的都城。中国史籍将其统称为“昭武九姓”,但这只是一种泛指,各书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也未必只有九个邦国,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唐书》)是:康、安、曹、石、米、何、戊地、火寻、史,共计九姓。其中,康国位于今撒马尔汗,是诸国之首领,安国位于布哈拉,石国位于塔什干,火寻则是花拉子模的异译;此外,尚有穆、毕等国。大约迫于嚈哒入侵的压力,昭武九姓国人曾在四、五世纪时大量东移至河西,有许多粟特人聚居于北凉的首都姑臧,北凉的统治者沮渠氏出自卢水胡,双方的接近似乎也可以通过与月氏的亲缘关系来加以解释。北凉国灭于北魏后,姑臧有大量的粟特人被俘,为此粟特王还派特使来觐见太武帝,请求予以归遣。
九、九姓胡、突厥与安史之乱
昭武九姓的粟特诸城邦是祆教的主要信奉地区,而粟特的商人和武士——统称“九姓胡”则更是闻名于天下。当突厥兴起占据中亚两河流域之后,九姓胡纷纷进入突厥上层,对突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厥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但在建立汗国后不久,开始信仰祆教,史载“突厥事火”,虽然这有可能是突厥本身的固有习俗(突厥实行火葬暗示其有较强的印欧背景),但对拜火之祆教的信仰则是受之于九姓胡。突厥建国初期,尚无文字,此时即通用九姓胡之粟特文,后来后突厥人创立的突厥文字,据研究也是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发明的。在突厥统治中亚期间,九姓胡在突厥国中的地位颇高,由此也因与突厥通婚而产生了大量“杂胡”。唐破突厥后,将其部落人民徙居鄂尔多斯一带,而其中的“六胡州”则主要是九姓胡的聚居区。至八世纪,虽然相隔遥远,中国北方的九姓胡仍然与中亚故地的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随着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而加剧。史载九姓胡诸国曾数次向中国请求派兵协助抵抗大食,然而此时的大唐已是有心无力,于是有不少落难的粟特移民东逃,以躲避阿拉伯人的统治——其时大唐的北部本已充满了归降的突厥、契丹、高丽等各类胡人,这对于西来托附的九姓胡来说无疑是一处绝佳的避难之地。
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之下爆发的安史之乱在唐王朝宫廷政治斗争之外又表现出文化与种族这一巨大冲突的复杂性。应当说,蕃将与内相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激化乃是动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满布胡人的北方地区早已潜在进行着的胡化进程却是这次动乱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动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杂胡:安禄山本为康国人,其母为突厥阿史德人,其义父为安国人,故禄山改姓安;史思明则是母为九姓胡,父为突厥(阿史那之“史”,也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国之“史”)。这种杂胡的出身使他们精通多种胡语,有利于多方联络各种胡人势力,从而更加壮大其反叛事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就曾多次利用九姓胡的商会来培植、拓展他的势力,提高他在胡人中的声望,近似的文化与种族使得北方胡人内部的认同感在其首领的努力之下更为增强,以至于安史之乱平定半个多世纪后,处于藩镇割据状态的河北幽燕地区仍尊安、史为“二圣”。
安史之乱同西晋的刘石之乱有不少相同之处(安禄山和刘渊都曾在中央朝廷进行过深入的活动,嗣后再返回胡人地区兴兵举事)。它们其实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叛乱,而是种族与文化上聚集起来的巨大差异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后者开启了“五胡乱华”,形成东晋十六国甚至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前者则开启了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所不同的是,刘石之乱导致汉族政权在中国北方无法再立足,因此他们及其他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后来都得到了史家的承认,而安史之乱虽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唐廷后又收复了长安,将叛军局限在河北,因此在名义上唐朝得以在中原再延续下去,实则河北诸镇仍然各自为政,内部也继续承认安、史的正统地位,因其地胡人居于强势。唐朝的中央朝廷也屡次想兴兵讨伐,打破这种分裂局面,但无一成功,一则朝廷被宦官把持,皇权不稳,二则河北自身的向心力也不大——汉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九世纪的黄巢之乱使这一平衡崩溃,党项、沙陀等都借平乱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源出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唐宋之间中国的走向。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后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后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馀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后唐和后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后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馀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十、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石姓的王朝,一个是十六国时由石勒建立的后赵,一个则是五代时由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前者为羯族,出自匈奴别部;后者自托沙陀,出自突厥别部。这两个“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不为人注意,其实,两者都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有关。
羯人的来源,至今仍不明朗,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羯、赭石”等与中亚石国(塔什干)有关。据《晋书》的记载,入塞的南匈奴有十九种,其中的羌渠、力羯当与羯人有关,“羌渠”可能即是“康居”的异译,而康居正是月氏西迁的初居地,昭武九姓与康居等一样可能原本就是月氏人内部的部落名。据此,羯人有可能是月氏中的一部,在匈奴征服月氏后,羯人归降,成为匈奴别部。羯人以“高鼻深目多须”著称,这是很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想月氏人的外表应当与此相类,但由于匈奴的兴起,汉人极少同月氏人直接接触,因此在汉文史料中看不到对西迁前月氏人容貌的描述,而其对匈奴人的容貌则未有显著的议论,以此推知匈奴本部的种族当非白种,而与中原人相差不大。可以参证的是与月氏人近似的乌孙人,汉人对它感觉到的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似乎说明西迁之前的月氏人也当与之相近,同属欧罗巴人种。石勒的继承者石虎字季龙,按照北朝胡人常将其本名(胡名)作为汉名的字的惯例,石氏羯人似乎与“龙”关系密切,而如前所述,月氏人也是崇“龙”的民族。羯人与月氏的关系还可以从宗教上发现证据。史载,当冉闵欲专国政之前,石虎的旧部曾计划刺杀冉闵,他们率领三千甲士“伏于胡天”,此处的“胡天”,正是火祆教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因此,羯人的宗教本为火祆教,而火祆教此前从未传入过中原,也不见于匈奴,故其只能是羯人在归降匈奴之前的固有宗教。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宗教信仰,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但从大月氏西迁中亚后很快便接受火祆教这一现象来看,原先月氏人中很可能已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羯人即其中之一。又,长期研究中亚七河流域塞人遗存的苏联学者伯恩斯坦提出,七河流域很可能是原始火祆教的起源地之一,那么从地域上看,月氏、乌孙等吐火罗部落中亦存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史家多将后唐、后晋、后汉皆称为沙陀人的王朝,其实,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并非沙陀人,而是随沙陀本部东迁的中亚九姓胡,从其姓氏来看,当同石勒一样,亦出自石国(塔什干),岑仲勉早就指出此点(《隋唐史》),惜至今未引起重视。不过虽然统治者为九姓胡的石国人,后晋在整个国家特点上确实与前后两个沙陀人的王朝没有多少不同,都是沙陀与九姓胡人相结合的政权,汉人的势力虽也不小,但毕竟不占统治地位,不过,汉化的趋势却是与日俱增,汉人将领的权力也逐渐加大,到后汉末,出身沙陀军人的汉人郭威逐渐得势,掌握了政权,建立后周,汉人才又夺回对中原的统治权,然而,燕云十六州却已经被石敬瑭割给契丹人,华北的门户从此大大洞开了。到了辽宋对峙的时代,昭武九姓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不过,“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北宋的毕昇,似乎竟然是一个来自昭武九姓中的毕国胡人,而导致这一发明产生的直接动因,则很可能与摩尼教的传播有关,不过,cinason的这一猜想过于武断,目前尚无坚实之证据,其证实或证伪只有等待更新的发现了(参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
圣经与万国——圣经人种学
人种学(ethnology--出自希腊文字根ethnos),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包括世界各国各民及各种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它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学问,如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人口统计学等科学。为了了解原始世界的文化,及古代的各族历史,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历史学家所用的工具与方法,都必须使用。研究的领域显然如此广阔,如此重要,即使只论及其与圣经的关系及意义,也不可能只用一章的篇幅就能办到。
当然,本书中心主题,旨在论及圣经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就是与物理科学及生命科学的关系。但又因为人种学正位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边界,目前只在这方面概略论述已足,有兴趣之学子,可作进一步之钻研。不幸的是,所有讲到人类社会关乎种族方面的文献中,到处充满了进化论人文主义的文字。这使得难于从进化论对真实资料的推测中,过滤出真实的资料来。因为在社会科学中这种进化论的偏见,在追溯这些古代的发展上,圣经的启示就没有依所应该有的情形被重视。因此,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概括叙述圣经中对世界民族,文化,国家的记录,再以广阔的人种学的资料,证明其为真。
虽然世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但所有的人都是人类。以生物学的观念看,他们仍然是同一种。“祂从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只要有机会,人仍然自由交配,尤其是当那新的语言障碍逐渐被商业,教育打破之后,在历史中充满了许多这种混合,所属民族改变的情形。人种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及研究文化的人类学者,可以在研究古时与现代各个人群时,找出这些变动至相当程度。
列国的起源
创世记第十章中的列国表,提供了列国起源的最重要资料。上述各种科学家在从事他们的研究时最好用它作为指南,不用那错误的进化论哲学。虽然一些人讥笑那个列国表,但那些曾经研究过它的真正有资格的科学家,却对其有关古代历史的看法的精确性感到惊异。比如,那位普世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考古学家阿尔布来德博士(Dr.William F.Albright)曾作过这样的评估:“它在古文学中,完全孤立,....即使在希腊文学中,也找不着些微的平行的记载。....这列国表,保持了惊人的精确的文献。....它显明了对现代世界复杂的种族语言,具有『现代』的了解,学者们对作者关乎这题目所有的知识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注一
从创世记这些记录之中所得到的最明白的事实是,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在亚拉腊山(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及巴比伦(现今的伊拉克)附近。巴别塔之后列国的分散,可以相当程度的追溯到创世记第十章所记挪亚的后裔。这些原始的国家试着在图三十二的地图中加以辨识。一般说来,雅弗的各族都迁往欧洲西北。含的各族主要的迁徙到南方及西方进入非洲,及地中海东部地区;虽然,其中的一族——赫人,在西亚及土耳其建成了一个大帝国,其它的人可能去到远东。闪族则多少集中在中东。
列国表中所列雅弗的诸国创10:2-5中,已肯定辨识出来的是雅完(希腊);玛各,米设,与土巴(俄罗斯);歌篾(德国),提拉(色雷斯,埃特鲁斯坎)玛代(玛代),亚实基拿(德国),陀迦玛(亚美尼亚),与多单(Dardanians)。他们大多数都似乎移居欧洲,一般说来,成了所谓高加索人与亚利安人种的祖先。当然,之后,他们再散布到美洲、南非,及许多海岛上去。闪的后裔,创10:21-31特别包括希伯(希伯来人),以拦(波斯)亚述(亚述)及后来藉以实马利、以扫,及亚伯拉罕其它的后裔(并摩押、亚们,及罗得的后裔)的阿拉伯国家。
一些含的后裔创10:6-20,都相当清楚的辨认出来,尤其是麦西(埃及)、古实(埃塞俄比亚)、迦南(迦南人、腓立基人、赫人)及弗(利比亚)。虽然谱系不容易追溯,很可能黑人的各民族也是含的后裔,因为,似乎只有含的后裔才迁到非洲去。最先的巴比伦人、苏美人,也是含的族系,属于宁录的一支。
蒙古人的祖先较难找出来。但是,一些考虑似乎也显明这些民族也是含的后裔。第一,藉筛减法,因为闪及雅弗族系已经清楚找出来,其它的就该假设都属乎含族。第二,西尼人创10:17被列为迦南的后裔,可能这个名字,与中国有字源上的关联。第三,中国的古名为Cathay,有证据显明,这个名字出自Khetae,Khetae又可能出自赫人,赫则是迦南的儿子。第四,在身体特征及语言方面,蒙古人更像含族,与已知的闪族及雅弗族,则较少相似。这些理由当然贫弱,诚然还有极大的空间可以研究这些人及他种早期人来源,而获得丰硕的成果。若是人种学家用创世记第十章与十一章作研究指南,以代替大多数现代古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的进化论的猜想,他们无疑的能够澄清许多不能确定的地方。一位在这方面写作甚丰立论精辟的古人类学家是库斯坦司博士(Dr.Arthur Custance)注二
那著名的挪亚的预言创9:25-27在这方面,是十分引人的。挪亚因知道洪水之后新世界中的万国都会是他三个儿子的后裔,就在上帝的领导之下,预言他们在未来团体生活上所将有的主要的贡献。
这项预言或者部分基于他对三个儿子品格的观察,知道他们的子孙由于遗传,及父母的教训,就会表现出一些父亲特别的性格来。人有三一性——灵、智、体——并且,在每个人里面,这三者之一会得势。以挪亚的儿子说,显然含的兴趣主要的在于体,雅弗的兴趣则在于智,闪则追求虔诚。因此,从遗传及环境说,都可合理的说,那从他们所出的各国,这些性质也会得势。
或者由于闪深切的灵性及对他的关心,挪亚就论到闪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无疑的藉此预言闪系将是保存及传扬真神上帝知识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祅教,与基督教伟大的一神教,诚然都是闪系的人所宣扬的(其它世界宗教则都是泛神的或多神的)。同样重要的是,依人的遗传说,基督是由闪系而出。依照挪亚的预言,“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这项扩张主要指智的方面。雅弗的后裔要在文化、哲学、科学各方面,影响全世界。当然,这项智力的影响,当然,必须也先由政治扩张所支持。
但是,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经过长时期,这项预言才开始应验。含系的苏美人、埃及人建立的国家,在已知的世界中得势了许多世纪;以后是闪系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得势,但是,最后,希腊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下,征服了波斯。自此之后,雅弗系的国家在世上称霸。
古希腊人承认“Iapetos”(Japheth雅弗)为他们的祖先。他们似乎建立了古式雅弗文化。现在都承认,西方文化是希腊哲学及科学的继承。那造成希腊扩张的,是她的科学--纯科学及应用科学--而非她的人力。以后的罗马、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及美国也是一样。
而且,雅弗要“住在闪的帐棚里”。这种说法,其唯一的意义是,以某种意义说,雅弗系要成为闪系的一部分。但是,这项联合不可能意指实际组织上的吞并。其意显然是雅弗虽然对人类主要的贡献是学术,但他要分享闪的属灵生活。这在雅弗系国家接受亚伯拉罕的上帝及以色列的弥赛亚上,得到充分的应验。
若是闪与雅弗的品德与贡献主要的是分别在灵性与学问上,含的贡献则主要的在于体。但这并不指没有价值的小事,或作仆役。含的贡献曾是最使人印象深刻的。在他的后裔之中,我们相信有:苏美人、埃及人、腓尼基人、赫人、达罗毗荼地域人种。中国人、日本人、埃塞俄比亚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马雅人,以及现代的黑人、美国印第安人、阿斯基摩人,及太平洋岛屿的各部落。这些人为人所知不是因为他们在属灵及学术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科技上、文化的生活舒适面有过许多进展。比如,他们在离开巴别塔,到偏远地区探险,是最先的先锋。发现美洲的不是艾利生或哥伦布,而是印第安人。很可能许多印第安人在洪水之后的冰河期渡过白令海峡,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愈来愈多的证据显明,其它的人由海路而来,可能从腓利基或埃及来。不管情形如何,他们都多半是含的后裔。
同样的,在含的族系中,有最先的航海者、最先的造城者、最先使用印刷术的,并多半是最先发展农业,蓄牧业、金属工业,及许多其它科技上的贡献。文字的发明,无论其为苏美人的蝌蚪文、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腓利基的字母,似乎也是含的族系的贡献。至少在从巴别塔之后的新文字的情形是如此(闪族自己被认为参与巴别对宁录的背叛,多半继续使用所已经熟习的洪水前的文字)。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用的指南针也是。总之,有关人类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的供给--探险、食物、住处、衣服、交通、通讯、金属工业,与其它,都多半似乎是出于含的族系。
文明的起源
进化理论系统,其范围,在传统上,包括人的身体,也包括人的社会。他们认为,人从类猿的祖先获得生物上的进化之后,就跟着有社会与文化上的进化,从原始猎食及采集食物的人群,经过各种阶段进化到文明的都市生活。
实际说来,那可靠的证据都反对这种进化的看法,圣经如此,真科学也如此。何处寻得可靠人类社会的证据,在那里就可寻到在十分早期的历史中就有高度学术与科技的证据。
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曾企图将早期人类历史分为几个时期,就像地质学家对人类出现之前的进化历史所行的一样,认为可藉这些时期的工具及艺术品而得辨识。所使用的多多少少平行的名称如下:
1、旧石器时代----蛮荒时代 = 食物收集阶段 2、中石器时代----野蛮时代 = 开始耕种 3、新石器时代----文明时期 = 村庄制度
石器时代之后,人被认为已学会怎样使用金属。接着就有铜器时代,以后是铁器时代。这些名词清楚显明了这些学者进化论的思想架构。这种人工分法,当用为年代的次序时,就会显出有住在蛮荒时代猎食文化的人在今天各处地方居住。今天的情形若是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各时期也多半是如此。而且,许多证据指明,这些“原始部落”已经从过去更复杂的现在只保存在他们传说中的文明退化了。因此,这样的进化区分,当其以时间为基础去解释时,就毫无意义了。人可以借着供给适当的训练及机会,将一个石器时代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大学毕业生,与进化阶段毫无关系。无论情形如何,那人类学者藉以辨别文明景况的进化论标准,是值得我们简单研究一下的。他们称这种状态中的发展为“新石器革命”。那粗糙的石制工具为磨光的石斧及精密形状的箭头所取代;陶器被使用,农业发展,动物家畜化。还有,不久就发展出金属工具,此时才真正被认为是文明。城 市化不久就伴随着这些发展出现。
这样,对文明起源的讨论,必须主要的论到这五种文明装备:(1)陶器,(2)农业,(3)蓄牧,(4)金属工业,(5)城市。这五样将在下面作简略讨论。对所提出的年代则不可太认真,因为这些年代主要是基于某些关键性放射性碳及树的年轮测定,再加以修改而来。这些年代问题将简略讨论,同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文明的性质,在近东,正如圣经所说,约在同时出现。
比如,试考虑陶器的发明及经过烧窑的砖用于建筑,并雕刻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施密斯博士(Dr. Cyril S.Smith)说:“在中东,主前九千年就烧成了小装饰品了。....当陶罐不仅发现有用,并且悦目之时,当陶匠发现,用更高的温度,加上各种矿物质能产生富丽的颜色与细致的质料,增加他们产品的美丽及用处时,陶器正顺利的要成为火的科技艺术品中最高贵的。....即使今天,我们对陶器制造,也只是原则上知道一点其所使用的物理与化学性质及其之间的关系。”注三
显然,这些“原始人”在十分早期就对那十分复杂的陶瓷及材料科学,所知甚多。陶器已经成为考古学家的宝藏,其整个年代系统建造在他所挖出的陶器破片上。实用的农学与蓄牧的成就,对有组织的人类社会乃是必要的。人必须学到生产比他仅仅为家人需要去收藏或猎取的更多的食物,他才能在求生存之外,作一点别的事。因此,蓄牧及耕种,尤其是种植小麦,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因此,考古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因此,从今日的分布研究,我们可以作结论说,古老世界农业的摇篮是从扎格罗斯山西部山脚(伊拉克,伊朗),托罗斯山脉(土耳其南部),及加利利高地(巴勒斯坦北部)所构成的弧形地带。”注四
至于农业及蓄牧业开始年代,现代顶尖的考古学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布来伍德(RobertBraidwood)及伊斯坦堡大学的康贝尔(HaletCambel)说:“十分粗略的估计是,现在所有的证据显明,在近东,在主前九千年,农业,蓄牧业,及大量食物收藏,已经开始。”注五
请注意同时代同样地点同时有的现象,不仅最先的农业与蓄牧业,甚至也有陶业,也有所谓的大量食物收藏,但以先却认为属于较早的进化阶段。“我们认为村庄就代表农夫的旧观念,已经丢弃。”注六
宾州大学的戴生(RobertDyson)证实了家庭农业,蓄牧业的同时及复杂的起源。“但是,现在的研究已清楚显明,问题比这个简单的问题所提出的更加复杂。可能实际上农业并不比蓄牧早。它们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中分开成为家庭的正业。现在也不再有农业与蓄牧业的先后问题。每一种动物与植物为人的家庭所培养,其本身不视为问题。”注七
换句话说,近东与中东许多不同的社区,约在同时达到了文明地位。为了文明社会的安定,蓄牧与农耕几乎同等重要。打猎需要狗,制作衣服需要牛羊,交通需要马与骆驼。一件有意义的与圣经意思相同的是,显然,人最早蓄养的动物是羊。“根据沙尼达尔洞穴及其附近的发现统计资料看,绵羊似乎在主前九千年就已经为人所蓄养,远在最早的狗与公山羊的证据之前。”注八
我们该记得,亚当的儿子亚伯是牧羊的,因此,无疑的,那带进方舟的羊是家中蓄养的羊。并且,至少挪亚自己的一些儿女也为了祭物,食物,与衣服而牧羊过。但是,不仅羊,也有牛,狗,及其它的动物,显然,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近东与中东,为人所眷养。艾赛克(EricEsaac)写道:“考古学的证据支持家畜为人眷养是在西亚。”注九。狄生(Dyson)告诉我们说:“驴是在埃及为人饲养,在主前三千年,再向东方传播到美索布达米亚。”注十
关于狗、山羊、骆驼、马、猪,并大多数其它的家畜,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金属的使用,也如同圣经所说,在人类历史十分早期发生。施密斯博士说:“所知最早人工打造的金属物品,是在伊拉克北部发现的一些紫铜珠,年代在主前九千年。”注十一,
同样的,古代金属物品,已在土耳其发现,显明了金属手艺技术不弱。“事实是,在主前七千年前,住在特皮西(CayonuTepesi)的人不仅熟识金属,并用天然的紫铜磨成及锤成各种形状的物品。”注十二。虽然,紫铜是最先使用的金属,其它的金属几乎在同样早的时候就为人所知。“这些金属的发现显明了,到了主前五千年,紫铜、铅、银,与金,在中东一带,已为人所知。”注十三
所谓铁器时代的来临,也在十分早期。甚至钢的使用,也可追溯至远古之时。“在时间的某一点,--尚不能确定,但多半在主前五千年之后不久,在那构成肥沃新月地带北疆的山中,人发现,将某种绿色的矿物在适当的火中加热,就能制造出金属,换句话说,一些东西已经发现。”注十四
“人造的铁的箭头出现在主前三千年。在主前1500年,在赫人的国家里,铁已不是稀有的东西。....好钢已被路易斯坦(伊朗西部山中)的铁匠,在主前一千年左右(上下不出两百年)打造出来。”注十五
因此,虽然,铁器的发现不如铜器及其它金属那样早,但它们的年代已在摩西时代之前(约在主前1400年)。看起来有些奇怪,铜为人所知所用,竟会在铁七千年之前。可能是,早期已经使用铁器,但未经挖掘出来,或者,那较古的考古遗址年代,因为过于相信放射性碳的年代测定,而被夸张。在下一段将会更多讨论年代测定技术。
另一个人类文明的一面是城市化。有组织的社会发展无疑的受到上述其它文明的作为所刺激,但是,其为因或为果,则不甚清楚,因为城市似乎是与其它的东西同时兴起。因此,一些城镇十分古老。但在另一方面,一些科技较发达的文明,却似乎并无城市而存在。那最出名的是瓜地马拉及尤卡坦的马雅人文化。他们有华丽的庙宇,及艺术,甚至有复杂的象形文字,但显然并无城市。
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城市化十分重要。这项发展再一次最先发生在圣经所记述的地方,并约在同一年代出现,如同上述的文明其它方面一样。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的亚当斯博士(Dr.RobertAdams)在检讨这个题目时说:“在大多数文明中,城市化开始早。无疑的,那最古的文明及最早的城市--古美索布达米亚的文明与城市--的情形,正是如此。”注十六
这拥有最早城市的最古的文明,当然是苏美人的,就是那最先住在巴比伦的。现代研究这些人最伟大的权威是克雷摩(Samuel N.Kramer)。他的著作(注十七) 清楚描述了他们的文化。阿尔布来德在讨论克氏的著作时说:“苏美人,....在主前四千年时,创造了最古的城市文明,有着进步的较高的文化。”注十八。至于较小,较单纯的社会,农庄与猎庄的起源是一回事,农耕及蓄牧同时开始。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也是在近东,其年代约在主前九千年。“我们现在知道,在主前七千五百年前,在近东一些地方的人,不仅是收集动物性及植物性食物,及居住于农村为特征,其文明已达到以生产为特征的程度了。注十九
这些村庄有卵石铺的街道,高大的石才建筑,有犁,有带轮的车,并有各种泥制及石制的装饰品及工具。他们的科技与直到现代世界各处许多类似的农村相比,显然也并不太逊色。
城市出现后不久,就看到毫无问题的书写的文字。最早发现的苏美人蝌蚪文字是在主前四千年。“在这之后,最先的文字记录在主前四千年中原始文字时期出现。”注二十
因此,我们作结论说,那以农耕,蓄牧,陶器,金属工,城市化,永久性的建筑,及文字为界说的人类文明,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许久之前,在圣经所说各地约在同时开始。
人类年代问题
正如圣经所说,人类文明就这样在近东开始。但是,通常对这些发展所讲的年代(其范围约在主前9000年至主前4000年),诚然与圣经有明显的矛盾。乌社尔年代表指出,洪水约发生在主前2350年,而一切有关的考古资料必然是洪水后的文化遗迹。
当然,还有所谓旧石器时代,被认为其年代更早,包括了人只是猎人及食物收集者,使用粗糙的石头工具及武器的全部时期。人,以现代身体的形式说,进化论者所定的年龄是一百万年至三百万年。
多数这些人类的遗体与遗物,已经从地质学的观点看,归在更新世或近代的各时期里,而这些,我们相信必定是洪水之后的。洪水本身的沉积与化石相当于古生代,与中世代。并大多数属于第三纪。是否有甚么办法能将人类洪水之后几百万年,甚至11000年的历史,与乌社尔年代表中洪水年代为2350年的情形相调和呢?我们相信,圣经年代学,虽然不够详尽,但比起进化论的年代更与实际情形相近。
旧石器时代及其之前的年代,多半基于钾氩测定法,而新石器时代年代的测定,主要的是放射性碳。但这些测定法,经严格审视时,可以看出测出之主前两千年前的年代有严重的错误。放射性碳测定法对主前两千年之后的事,可能测定的结果还相当不错,但更早的年代,因为在一些放射年代计算错误的假设,其测定的结果是无效的。请参考第九章中这方面的讨论。注二十一
树轮年代学近年来也变得愈来愈重要。目前仍然活着最古老的树是美国西南部的一种叫bristlecone的松树,尤其是生长在加州白山上的。其中一棵在内华达蛇山发现的,由它的年轮估算,其树龄已达4900岁。几个其它的人的估算是超过4000年。借着将活树与死树的年轮相比较,一棵这样的松树在阿里桑那大学推算出的年代是8200年。若这项年代正确,乌社尔年代表所列洪水后至今的年代只有4300年的年代就显然错误。
但是,人不必太急于废除乌社尔年代表。虽然计算年轮似乎十分简单,几乎是个推算过去年代不会错的方法,但其中仍然牵涉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第一,一棵树一年产生两个以上的年轮是十分可能的,尤其是那些生在低地,或纬度较南的树。这方面的顶尖研究者费佳生(CharlesFerguson)说:“某些松柏科的树,尤其是那生长在低地及纬度较南的,一个季节的生长可能包括两次以上迸发性的生长。每一次这样的生长,可能酷肖一个年轮。”注二二。费佳生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用在这种松树身上,因为它生长的地方高,天气干燥。即使他所说的在近代的境况下是对的,但在洪水之后的前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时,则并不真实。现在已清楚知道,如今内华达干燥区,及大盆地,从前雨量甚丰,湖泊有比现在更高的水平面(比如labontan湖及Bonneville湖)。那时的气候可能十分不稳定,十分可能使那几百年中树木每年生出两个以上的年轮。这样,一棵四千九百年的树,不一定实际上会有四千年的树龄,实际年龄或更少。
那将死树与活树的年轮比较而使年代增加的作法,更是有问题,尤其是那些靠近洪水时代长出的年轮。而且,这种比较,必然十分主观,甚至以统计方式用计算机去分析也是如此。每棵死树剖面所含年轮在计算年代时计入的数目,只是从50至最多两三百个。对将之实际与从前所已经建立的序列配合,也总是产生问题。在那些我们所提最古的松树,年轮特别薄,每个年轮平均只有一公厘的百分之几、因此,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相似的形式十分难于辨认。其之所以需要用统计方式及用计算机分析,并且最后的关系系数甚低,就足以证明,这种比较十分含糊。不知甚么缘故,树龄较大的树,在开始建立这项年代测定法时,未曾使用。所使用的树只是树龄在1200年以下的活树。在这个基础上,再用二十种不同的死树予以延伸,最后可算得过去8200年。或者是如此,但是人会想,既然这些研究的互相关联性是低的,每棵树又只用了其少数的年轮,是否可能可以配合的“主年代”剖面不止一个呢?还有其它的问题。“bristleconepine-sequoia时间表的有效性为了一些理由一直受人质疑。对我们说,我们最关心的是,那在三千年之前的年代,它的根据只是一种在非典型条件下--就是在为10000至11000英呎高度--生长,或曾经生长的树。”注二三
年轮年代测定法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可靠,可在下面的话中显明:“对那些既非放射性碳的科学家,也非年轮年代测定法专家的人说,必须知道所有的树在年轮测定年代上,其价值并不相等。安全的说法是,对大多数的树说,其价值甚微,或完全没有价值。”注二四。许多人,像费佳生一样,认为bristlecone树是适用于年轮测定年代法最好的树。但是即使这种树,也是问题重重。
“在松树中,pinus aristata(就是bristlecone pine), 甚至比杜松更不可靠。....我们在SantaBabara植物园有许多从内华达东边加州白山一万公尺高度,雨量少,并不规律的地区移植过来的这种松树。也有一些从犹他州西南高地及在阿里桑那旧金山山峰移植来的同样的树。比较所测出的年轮图,看不出甚么相似性。”注二五 这样,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与年轮年代测定,都是十分不规则,不可靠的。但是,它们是目前发展出测定人类史前年代最好的方法。一旦我们超越了有实际记录开始的时间,就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正确的测定年代。因此,根本没有真实的理由去弃绝,甚或去质问传统的乌社尔圣经年代表。到是进化论者显出有一种非常的热望,要尽其所能将过去的年代推到最远,简直显出他们是有意在设法使人不相信圣经。“也有许多地方,其用放射性碳14测出的年代太近,不正确。这些虚假的数目少的年代,常未发表,但是每一个考古学家都知道一些这样的例子。那些发表的又常得不到该有的注意。这些无法解释的近期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也常是十分稳妥,在测定过程中找不到任何瑕疵。”注二六
那科学家自夸的客观性,是一个他们喜欢投射给别人的美好形像,但是实际情形却常将之破坏无余。“考古学的证实更加困难。每个地区人最先居住的年代测定十分重要,但是,这项工作常被许多工人喜欢他们发现的年代比任何人都古而成为头条新闻,受到蒙蔽。”注二七
写上面这段话的人,是指北美洲最早有人居住年代测定的问题,但是,这种想将任何年代测定推得更远的欲望,显然在进化论的地质年代学家中间十分普遍。使之显得越古,似乎圣经就显得愈不可靠,上帝也就推得与祂所创造的世界更没有有意义的关联了。
不管情形如何,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这种显得怀疑史前圣经事件年代的任何证据。在年轮年代测定中,当从两个或更多年轮中拣选一个时,那被拣选的很可能是算出的年代最久远的。这各种“配合”,最好的互相关联性也低,因此,那一个被选,完全是武断。
实际说来,年轮学家常使用木头放射性碳的测定,先决定在死木标本中那一些年轮可以配合,再在那个区域中寻找可能的互相关联性。费佳生说:“偶然,还没有用年轮测定年代的样品,先作放射性碳分析。所获得的年代,显明了那-标本的一般年龄,而这就供给线索,指出应该观察主年代图中的那一部分,这样年轮年代测定就更容易。”注二八
但是这种对放射性碳的依赖,必然造成误导。当对不平衡的情况较正之时,那是放射性碳方程式所必需的,其所计算出的年代,比所有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所用一般放射性碳平衡模式所算出的要少许多,少了几千年。
因此,十分令人怀疑,年轮年代测定,真能废除洪水的主前2350年代。但是放射性碳测定本身的情况如何呢?在考古学使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之前,考古学家相信新石器时代的乡村生活,是相当新近进化的。但放射性碳测定大大增加了这项时间距离。“不仅算出了所盼望的主前4000或4500年的年代,近东最早的村庄的年代,已证明远至主前八千年。”注二九
但是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乃是假设在时间与空间中,放射性碳与天然碳的比例呈稳定状态。这种情形曾经用埃及有记录的历史中的年代核算而显为相当正确,但这只回溯到埃及的第一王朝。“向来人人都知道,主前3000年前,就是埃及历史开始之前的时期,所有的年代都只不过是臆测罢了。”注三十
但是那较近的年代,稳态的假设变得十分重要。库克(MelvinCook)博士已经指出。注三一,现今实际的放射性碳比率更适合不平衡的模式,胜于标准的平衡模式。他并指出,因为这项改变,公式所算出此项过程开始(被认为约在洪水之时)的时间就会在主前7000年至主前12000年。在洪水之前,同温层上面有一个广大的水汽罩盖被认为防止了大量放射性碳的形成。因此,只当这些水汽凝结,在洪水时落在地上时放射性碳系统才真正开始。 因此,所有放射性碳计算出在主前1000年的年代(那时平衡模式改变成不平衡模式)应该重新计算,以适合更正确的不平衡模式。比如平衡模式下放射性碳算出来的年代为主前8000年,就会修正为主前3000年,如此类推。即使使用这项修正,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算出的一些年代,仍然超过了4300年。但是,那不平衡模式的问题,只是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中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另一个问题是磁场的改变。若在洪水后不久期间磁场的强度比原先大许多,即使水汽顶盖已经消散,也会抑制放射性碳的形成。这项效应会更进一步修正放射性碳的方程式,使之不仅可以容许地上放射性碳衰变总量与时逐渐增多,也容许大气中放射性碳形成的总量与时逐渐增加。
前面已经讨论过,巴恩斯博士已经证明注三二,地球磁场呈指数型衰变,其半衰期为1400年。这样,在乌社尔年代表中洪水时期,(约主前2350年)地球磁场比现今的强八倍。虽然据我们所知,那精确的效应尚未计算出,但毫无问题的,更多的宇宙射线被折射,因此,形成的放射性碳数量就会比现在少得多。整体的效应是,放射性碳测得的年代,还要更进一步的缩短。
我们预测,一旦所有的计算完成,洪水之后放射性碳开始形成的年代,将不会早于主前4000年,并十分可能早到主前2350年。
记录历史不正确
那仍然留下的问题是,实际记录下来的历史是否与乌社尔年代表相冲突。鉴于在所有实际测定年代方法中许多无法证实的假设,对人开始记录年代之前的任何年代,就永远不会有确实的把握。并且,由于人喜爱夸张,就是这些记录,也并不都可靠。
一般说来,最古老的两个文明,埃及及苏美人的文明,是我们已接受年代的根源。“当然,史前的发现,因其性质,未伴随任何写下的记录。唯一可能有的资源是从已知找出未知。设法从有历史记录的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历史文化向没有记载的周边探索。比如,那以古代记录为基础的埃及历史年代,可以没有甚么问题的延伸到主前1900年,因为,记录中有天文的事件。因此,埃及的‘帝王表’,虽然不是那么样使人完全放心,还可以用为建造成另一个再向前推十一个世纪,至主前3000年的年代表。”注三三这个年代,主前3000年,离乌社尔所算出的洪水年代不远。埃及第一个王美尼斯的年代,很可能与挪亚的孙子麦西时期相当。他可能是埃及国的创建者。(麦西这个名字在圣经中与埃及同义,曾十几次如此使用过)。
但是埃及的开始,及其它国家的开始,其年代必须从巴别塔人分散之后开始计算,依照圣经的说法,那是在洪水之后100年。麦西,他的父亲含,可能在人分散之后,仍然活了一段长时期,因此,许多人用了相当长时间迁移到尼罗河,在那里奠定了立国的根基。埃及在圣经中也称为“含地”诗106:21-22
埃及长久分为两个帝国,上埃及与下埃及。上埃及称为巴忒罗,显然得名于创10:14节,麦西的子孙帕斯鲁细。下埃及则继续与麦西本人相联。上面所提到的帝王表,尤其是曼内托的年代表(Maneto-约在主前290年)提供了埃及年代表主要的基础。而埃及年代表又成为发展其它古代国家年代表的基础。但是,有些迹象显出,他的年代表中包含了两个帝国同时代的王朝,而将它们的年代错误的加在一起。而且,曼内托历史所根据的数字,很可能得自早期帝王及文士们的夸张说法。因此,埃及第一王朝的主前3000年,应该大为减少。
同样的问题,可以放在苏美人的帝王表及年代记录上。在巴比伦、吾珥、基什、埃卜拉及这个区域其它城邑的最早的王朝,显然是在埃及第一王朝开始之时同时开始。一些学者相信,如像埃及的情形一样,可能类似的力量也在作用,使其扩张了几百年。
无论情形如何,实际年代记录的开始,不超过主前三千年。并且这些年代都可能是夸张的年代。寇飞利(DonovanCourville)注三四与费里可夫斯基注三五以及一些其它的学者,曾提出使人信服的理论说,这些古时的年代,都应该至少减少八百年。这样,认为乌社尔年代表中洪水年代为主前2300年左右,是十分容易辩护的。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基要派圣经考古学家辩称说,洪水的年代是主前是3500至4000年。这不仅是因为如帝王表,放射性碳及年轮测定等原因,也因为通常所定主前2000年亚伯拉罕时代人所居住复杂世界的缘故。许多保守派圣经学者提倡说,在创世记第十一章的族谱表中,可能有一两个间隙。比如在路3:35-36节与创世记十一章平行的族谱之中,该南的名字插在亚法撒与沙拉中间。那最可能存在着大间隙的地方是在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创10:25十一章中所列出法勒之前三个人的寿命是438、433、464岁,法勒及他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则是239、241、230岁。因此,在寿命减少了一半的法勒与希伯之间,可能有一个长的间隙。
在法勒与希伯之间是否有,比如说,1500年的间隙呢?在这种情形下,创11:16节,就可能译为:“希伯活了430年,生了法勒(的祖先)。”在那个时代,这个间隙代表四五代人的寿命。这个长时期沉默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巴别塔语言混乱使记录中断所造成。这样,当法勒不知名的父亲过了一千年之后再继续记录(在法勒的祖先希伯的儿子诞生之后四百年闪去世之时记录中断)之时,他为他的儿子起名法勒,以记念巴别塔悲惨的背叛及其后果。
这种说法是否合理,读者可以自己去衡量。是否要效法寇飞利与费里可夫斯基重新解释历史及考古学资料,以符合乌社尔年代表,也仍然是个争论中问题。无论如何,根据这些解释,使圣经年代及历史文化考古学年代彼此符合,诚然是可能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可以解决那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问题。
文明之前
这样,圣经的人类早期历史,已充分得到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的考古学实际资料的支持。但是,对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呢?那些旧石器时代的人,尼安德塔人,直立猿人,克罗麦格兰人呢?那些美国印第安人,南海岛民,爱斯基摩人,非洲的矮人,并其它被认为是原始民族的人呢?他们如何去到海岛,森林,北极及深山中的呢?
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常说,在较低之处找到了石器时代的文明,甚至在较高之处发现较进步文化的文明同一地点发现。对他们说,这是讲说人类的进化。但是,对这些资料,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充分与发现的资料及圣经相吻合。洪水是普世性的,并造成极大的灾难。彼得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后3:6所有洪水前的人及他们的文明,都被水淹没,毁灭,摧毁,世上没有任何地方留下一个城市及村庄。因此,若有任何人的骨头或人的制品被保存下来,它们就几乎必然在流动的沉积中深深地,任意地被埋葬,使其以后不容易发现。人常问,若是洪水毁灭了洪水前的世界,为何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人类化石?实际说来,因为在洪水前,各大陆与诸海洋的地理情况与洪水前的完全不同,许多洪水前的人类尸体可能现在深深埋在海底的沉积之中。另外的一些可能深深埋在地壳的岩层里。但是,由于人的机动性,大多数洪水前的人,或者完全未被埋葬,是最后被水淹死,在地面干了之后,尸体分解了。
但是,为了辩论,我们可以假设,有十亿人被埋,在洪水的沉积中变成化石。地球的表面面积约为5x10的15次方。平均的沉积至少是一英哩厚。(5280英呎)因此,平均埋葬一个人的沉积容积为:
因此,人必须平均挖掘260亿立方英呎的沉积岩(或相当于地球表面面积一平方英哩深度947英呎的岩石)才能发现一个洪水前的人化石。因此,除了碰巧,人难于盼望找到洪水前的人化石。
因此,世界上数以百计的考古遗址,都不能代表洪水前的文明。它们没有一个例外,都是洪水后的移居与定居。这项结论也与其普遍所测定在更新世及鲜新世后期的年代相吻合。这更新世及鲜新世以圣经的地质学看,就是意指洪水之后。
虽然洪水前文明也是高等层次文明(创1-11章讲到城市,金属,农事,乐器,珠宝,蓄牧,及其它有组织文明的事),但都在洪水中毁灭了。只有那些能储存在方舟中的东西,惟有挪亚与他的三个儿子能储存在他们脑中的技艺,能在洪水后用以建造一个新文明。
洪水后的世界起初是荒凉,崎岖,常有暴风雨,与他们从前所居住的美丽的普世暖房环境大不相同,不适于人居住。经过许多年,或者几个世纪,为了生存,就耗用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
仅仅为了先要寻找开发的矿源才能开矿炼铁,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探勘,挪亚与他的家人,起先就无法使用铜器与铁器。他们的工具必然是石器与木器,在加上陶器,因为这些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材料。他们所需要的食物起先必须藉打猎及收集获得,尤其是当他们出去探险,移民到新的地方居住之时。直到他们有时间自己种植庄稼,蓄养牛群及羊群的时候。
这样,考古学家在某一个地方,在一联串增高的层次中,似乎发现了证据,显明先有碎石文明,以后是磨石农村文明,然后是铜器与铁器文明时,并不代表自然的进化过程。它们只是显明了洪水后小群的人在困难的环境中,除了他们自己的聪明智能之外,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去努力建立一个有生机的社会时所遭遇的困难。这种情况与鲁宾生飘流记的情况相近,在孤立的荒原中必须藉他们的聪明与双手生存。这些早期的人,不但不该贬低,视他们为“原始、野蛮”,反而为了他们惊人的成就,该受到尊重与崇敬,不仅是为了生存与繁殖,也因为他们在如此早期,就建立了,并如此迅速在古代世界的伟大民族及科技中,累积了丰富的文化基本要素,那些人坚决不肯依照上帝的吩咐分开,迁到新的地区去居住,而宁肯大家留在一处在亚拉腊特山附近在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士拿地区,在两河之间。所能找到最肥沃与舒适的地方。他们叫这两条河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以记念那两条从伊甸流出来的美丽的河流。
他们抗命的结果,就是上帝在巴别塔的惩罚,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得不分散。此后的历史考古学家们正在逐渐找出来(虽然他们大多数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挖掘出这些人所居住过的山洞,所建造的村庄,以及他们在全球移居及定居的证据。
当人口增加,争取最好地方的竞争也随之增加。那最强的,最有科技头脑的家族(最先是一些含的后裔)就在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及在尼罗河谷获得及开发了一些最好的地方。迦南人在地中海东岸及东北岸定居下来。雅弗族的人迁到较不适于居住的北区与西区,尤其是进入欧洲。闪族人则留在亚拉腊山近处,但是逐渐散布到东方及南方,进入阿拉伯,亚述,波斯等处。
进一步的人口增长及竞争引起战争,及其后战败一方移居到更远的地区去。一般说来,当每一个战败的民族被迫继续迁移,那些存活的人,就必须再一次有石器时代,铜器及铁器时代,建城等文化经历,
战败的民族永不能再回来,将那已经建立,安定下来的文明社会夺回。他们只能继续向前,到一些新的地区去,再一次过猎人,食物收集者的生活,直到他们在一个地区安居下来的时间够久,能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及资源。“一般说来,规则是,若猎人扩张他们的地区,实质上只是进入空的领土,也不会使从前安居下来的居民受损。这项规则明显例子是像美洲新大陆的最初占领。那必然是个单一事件,而非一连串的移民波。”注三六
怪不得对最早期的所谓原始人的研究(如尼安德塔人,克罗麦格兰人,以及直立猿人)都集中在西欧,东亚,及南非。这些地区都远离巴比伦,是人类在巴别塔分散之后早期居住的最外围。住在那里的人被强迫离开比他们更成功的亲戚,为了生存,必须住在洞中,深山里或森林中,以求生存。在大多数情形下,虽然是近亲生殖,食物不足,(比如尼安德塔人有佝髅病)并有一般性的退化,他们身体外表多少有些变形,甚至最终可能绝种。
但是,大多数的情形,他们迁到资源丰富的新地区中居住,渐渐某种形成安定有效的社会。这一切事情,可能都发生在冰河时期。同时尼安德塔人正在欧洲近冰帽之处,努力求生存。在亚洲的西伯利亚族,埃及,苏美,及其它古代伟大的文明,则正在较低的纬度,没有冰的地方,但有更丰富的雨量,气候更怡人的地方发展
我们相信,所有真实的人类学及考古学资料,都与上列事情的顺序相一致。比如在西伯利亚,那些移居的民族曾在那北边所有的地方,在河流村庄的岩石上,留下了图画,作为他们文化的记录。“这些发现,是古代岩石画,在大陆北边从斯堪的纳维亚直到西伯利亚极东的阿穆尔河床都有发现。”注三七
在这些地方发现的古人的遗物,都依从通常先是石器,以后金属器皿的模式。它们也反映出环境情况的改变:冰河时期逐渐过去。在非洲也发现同样的现象。在埃及,王朝时期之前先有在尼罗河谷安居下来的民族在科技上的迅速发展。“现在知道,这些尼罗河流域文化保存及稀少的假设,大错特错。....而且,有使人信服的凭据显明,这些地方所居住的人,其石器技术,印刷术与世界其它地方同样复杂与进步。”注三八
在更南边的非洲,就如同在西伯利亚一样,借着岩石画,能最清楚地追溯移民与定居的景况。“非洲独特地在岩石表面上有成千上万幅图画与雕刻。....有这些图画的地方从北边撒哈拉边缘,到好望角都有。....它们的年代从可能主前8000年到近代,并表现出从大陆这一端到另一端连续的艺术风格。”注三九
看见人如何从巴别塔分散到欧洲,非洲与亚洲,相当容易。但是人如何进入南北美洲,及太平洋的岛屿的呢?答案是,他们是从陆地及海洋两方面去的。在冰河时期,海平面多半较低,有陆桥跨过白令海峡,马来群岛,进入新几内亚及印尼。“从丰富的证据,已清楚认定,威斯康辛冰河在40000年前最大,使海平面低了460呎。....在450呎时,从一边的大陆海滩到另一边的海下平原整个宽度必然暴露出来,提供了一个1300英哩宽的走廊,使不再分开的大陆之间的生物可以流通。”注四十
无疑的,许多美国印第安人,及大多数美国品种的生物,是从西伯利亚经过这陆桥到达的。但在另一方面,也十分可能,一些中美与南美的居民,先乘船到达。而且,造船技术必然是经过洪水而存活的人所拥有的。有许多证据显明,古代的腓利基人并其它的人,都擅于航海,他们航海从南边绕过非洲,并航行到全球。
各海岛无疑的起先也是由乘船来到的人定居下来。有意义的是,这些地方是人最后居住的地区,如同近东地区是人最先居住的地区一样。计算机分析目前的陆地指出,地球真正的地理中心是在土耳其的安卡拉附近,其“中心对点”(anticenter——离所有陆地最远的一点),位于南太平洋,约位于纽西兰及南美洲的中间注四一。方舟着陆点位于地球的中心点,藉此加速人与动物的地上繁殖,乃是上帝的安排。
十分晚近,人才进入南太平洋诸岛
人进住玻里尼西亚群岛东端的马克萨斯的年代已确定为主前122年。其西端的萨摩亚(Samoa)则在主后9年。其邻近的裴济岛推定的日期稍早,为主前46年。似乎在裴济岛也至少有理由可以盼望同样年代的证据。在北方的远处,在夏威夷,一个测定中可能的年代是主后124年,显示这个玻里尼西亚群岛的前哨,约在基督教世纪开始时才有人定居。南边,在纽西兰,在那里他们采到了三十八种放射性碳的标本,人最早在那里居住的年代,到目前所获得的证据是在主后1000年左右。注四二
以上的年代所依据的是放射性碳,但是这种测定法,似乎只对这种晚近的年代才有效。这岛上的居民似乎来自大陆各个地方,从亚洲,也从南美洲。这项比较简略的叙述可以作更详尽的发挥。每一个考古人类学的新发现,似乎都说明,及支持了圣经所说人类起源及早期历史的记载。人不是经过几百万年慢慢从动物祖先进化而成,他一直就是人,十分聪明,有本领,能到全世界探险并定居,并能够在所到的任何地方发展出复杂的文化来。
—————————————————————
注一:W. F. Albright, Recent Discoveries inBible Lands(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55), p.70.
注二:Arthur Custance, Noah's Three Sons(Grand Rapiods: Zondervan,1975) 368 pp; Genesis And Early Man(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331 pp.
注三:Cyril Stanley Smith, "Materi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Civiliazation and Science," Science, 148 (May 14, 1965): 908
注四:HANS HELBACK, "Domestication of Food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Science 130(Aug 14, 1959): 365
注五、六:Halet Cambel and Robert J. Braidwood,"An Early Farming Villagein Turkey," Scientific American 222 (Mar. 1970)
注七、八:Robert H. Dyson, Jr., "On the Origin of the NeolithicRevolution, "Science 144(May 8, 1964): 673—674
注九:Erich Isaac,"On the Domestication of Cattle," Science 137 (July20, 1962): 196.
注十:Dyson,"On the Origin", p.675.
注十一:Smith, "Materials, "p. 910
注十二:Cambel and Braidwood, "Early Farming Village," p.56.
注十三:Theodore A. Wortime, "Man's First Encounters with Metallurgy,"Science 146(Dec 4, 1964): 1259.
注十四:Smith,"Materials," p.910.
注十五:同上,p. 913.
注十六:Robert M. Adams,"The Origin of Cities" Scientific American 203(sep 1960): 154.
注十七:Samuel N. Kramer, The Sumeria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3) 355 pp.
注十八:William F. Albright,"Sumerian Civilization, " Science 141 (aug 16, 1963),: 623.
注十九:Cambel and Braidwood, "Early Farming Village, " p. 51.
注二十:Robert M. Adams, "Origin of Cities, " p.160.
注二一:亦参见Henry M. Morris , ed. Scientific Creartionism(San Diego:Creation-life, 1974), pp. 161-67.
注二二:C. W. Ferguson, "Bristlecone Pine, Science and esthetics, "Science 159(Feb, 23, 1968): 840.年轮所算出的年代广为人接受,并曾用以向上修正成已为人接受的放射性碳的年代,大部分是CharlesFerguson一个人在亚里桑那大学年轮研究实验室中的工作。
注二三:Elizabeth K. Ralph and Henry M, Michael,"Twenty-five Years ofRadiocarbon Dating." American Scientist 62(Sept-Oct, 1974):556.
注二四、二五:Harold S. Gladwin, "Dendrochoronology, Radiocarbon andBristlecones, "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f Canada 14, no. 4(1976):4—5
注二六、二七:Grover S. Krantz, "The Populating of Western North America,"Society for California Archaeology OccasionalPapers in Method andTheory in California Archaeology 1(Dec 1977): 7.
注二八:Charles W. Ferguson, "Bristlecone Pine," p.845.
注二九、三十:Colin Renfrew, "Carbon 14 and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Scientific American 225(Oct, 1971): 67.
注三一:Melvin A. Cook, Prehistory and EarthModels(London: Max Parish, 1966) pp.1-10.
注三二:Thomas G. Barnes, Origin and Destiny of the Earth's MagneticFeild, 2nd ed. (San Diego: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1983).
注三三:Colin Renfrew, " Carbon 14 and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Scientific American 225 (Oct, 1971): 63 . Also see Renfrew's book,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1974), pp. 25-28.
注三四:Donovan Courville, The Exodus Problem, Volumes I ahd II(LomaLinda, Calif.:Challenge, 1971).
注三五:Immanuel Velikovsky, Age in Chaos(New York: Doubleday, 1952),350 pp.
注三六:Grover S. Krantz, "The Populaitng of Western North America,"Society for California Archaeology Occasional Papers in Method andTheory in California 1(Dec. 1977):5.
注三七:A. P. Okladnikov, "The Petroglyphs of Siberia," ScientificAmerican 221 (Aug, 1969): 75.
注三八:Fred Wendorf, Rushdi Said, and RomualdSchild,"Egyptian Prehistory: Some New Concepts" Science 169(Sept.18, 1970): 1161
注三九:Carleton S. Coon, "the Rock Art of Africa, " Science 142(Dec.,27, 1963):1642.
注四十:William G. Haag, "The Bering Strait LandBridge," Scientific American 206(Jan 1962):120.
注四一:Andrew J. Woodsand Henry M. Morris, The Center of the Earth(San Diego: Institutefor Creation Research, 1973)p. 6.
注四二:Edwin N.Ferdon, Jr. "Polynesian Origins, "Science 141(Aug 9, 1963):500.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
【译后记】有句歌词说:“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句话如果用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的概念来解读,那就是:星星对现代人来说,不再是一种“神显”,也就是说,星星不再被认为体现了宇宙的神圣性;人们可能对星星怀有一些浪漫的想象甚至航天征服的理想,但却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换言之,现代人对日月星辰难以产生一种宗教性体验,也因此,我们不容易感受到永恒。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明,整个空间和时间都被“去神圣化”了。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都市这样的人工环境下,对自然的感受是疏离和淡漠的,虽然人们亲近自然时仍感到喜悦,但却很少会引发一种敬畏和神圣的心灵冲动。这也是人们难以理解那些远古神话和风俗的根本原因。它们虽然仍会时不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比如中国探月航天工程仍以嫦娥奔月的传说命名),但却只是一些有趣而零碎的片段。因此,要想清楚地知道古人为何要创造那样的神话,其背后到底蕴含了什么深意和象征,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重新感受宇宙——也就是说,像古人一样将宇宙设想为无限、永恒、神圣性的唯一根源。
在《神圣的存在》中,伊利亚德不厌其烦、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天、太阳、月亮、水、石、大地、植物、农业丰产、圣地、神圣时间等十大类“神圣的存在”。简言之,原始人的宇宙与现代的相反,它是一个“圣化的宇宙”,人人都分享着宇宙的神圣性,万事万物都可能成为显示神性的征兆和表象。就像南方壮族传说中蛙是大神和图腾,在怀有这样观念的人眼里,蛙就不再是普通的蛙,而是雷神和雨水的象征,它可以主宰着人们的农业生产收成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在人力无法主宰和控制自然力的时代,人们通过对神圣征兆的认定和祈祷来消除心情的紧张焦虑,以此在心理上获得一个绝对的支撑点。
古代地球表面有着许许多多彼此隔绝的人类文明,因此也就有无数个宇宙,因为每一个文明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支撑点,他们在这个自己构筑的小宇宙中象征性地庆祝整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人们还迫切地希望那个神显能够周期性地重复自身,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确认自己的幸福存在。伊利亚德将这种愿望称为“天堂的乡愁”:古代人普遍存在这种渴望,即回归到那个远古的黄金时代,重新获得一种神圣状态——在基督教神学中,那是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则是尧舜时代的三代之治。
原始人的这种基本冲动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现象。例如无论在西藏,还是秘鲁的印第安人遗址马丘比丘,人们经常将宗教场所修建在山顶上,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在这样的地方生活,食物饮水等基本需求都极为不便,很难想象当初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地点。但对一个具有宗教体验的人来说,高山是最接近天空的,具有一种天然的神圣性,是神的居所,因此世界各地神话中主要神灵一般都居住在高山之上,如希腊神话中十二大神都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顶。高山也常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点和支撑点,是大地和天空相遇的地方,在此最有可能接近神灵。
中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宗教影响力最为弱化的一个例外,高度发达的史学和文字传统在两三千年前就已侵蚀了远古神话,因此中国的神话传说大抵都支离破碎。正因此,中国人要想理解祖先对宇宙的感受,才格外需要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否则仅靠一些孤立的证据,想要完整地复原上古中国人的神话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中国神话,但他丰富的例证和谨慎可信的结论却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举例来说,古代传说和两汉画像砖均表明中国人始祖之一的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从中国古籍中找不到可以说明为何他俩下半身是蛇形的证据,这一形象就成了一个神秘符号。但比较神话学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许多神话中证实:蛇在原始人心目中普遍被视为长生不死的象征(因为蛇每年蜕皮,犹如复活),常常和雨水、大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等城邦的祖先的形象也同样是人首蛇身。又如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中国人常将之理解为一个造福百姓的医学英雄,而伊利亚德告诉我们:“有时,植物就是神。”采集草药也是一种仪式,它绝非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充满神圣的实体、缩小的生命树、包治百病的资源”。
阅读这本书无疑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体验。不仅是因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洞察力,也因为古人对宇宙神圣性的丰富想像力本身就足以使人赞叹。和他们比起来,现代的传奇故事看起来并没有脱离他们几千年前就划定的圈圈。尼斯湖怪兽的传说和金?凯瑞的《变相怪杰》虽然沾上了现代色彩,但实际上却与上古神话有着高度的精神一致:即认为水具有巫术力量,水中生物或盛巫术力量的器具都沉在海底或湖底。更不用那些述说年轻人付出许多努力后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最终夺取宝物的故事——这是许多武侠小说和动画中的经典情节,例如《圣斗士星矢》——而这一构想的根本来源正是出自“鬼怪守卫的不死符号”这一神话母题。
这种包含变化的延续性非常重要,虽然伊利亚德研究的范围只是宗教学和神话学,但他阐述的许多结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某些现象。按他的洞察,每个神话,都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从前的事件,由此提供了一个先例和范型,此后人们的仪式和行为都是在重复那个神话的原型。任何神圣形式或崇拜不管如何变化多端,都具有这样向某个原型的回归。其实现代政治的运作何尝不是如此?在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上台后每年都要隆重纪念最初发迹的“啤酒馆暴动”,将它理解和渲染为一个神圣事件,其目的则是为了预示下一个同样的神圣事件,因为它不断地强调德国青年要像当年的啤酒馆烈士一样无条件服从和绝对信任领袖。由此,这个原本普通的啤酒馆和事件就成了一种“神显”,被赋予了远远超过它本身的意义。这一切,难道也仅仅是神话吗?
第1章 初论:神圣的结构和形态
1.“神圣”和“世俗”
迄今为止对宗教现象所下的全部定义有一个共同之处:每个定义都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表明神圣的、宗教的生活就是世俗和现世的生活的对立面。但是,一旦着手规定神圣这个概念的范围就会遭遇到各种困难——既有理论的困难,也有实践的困难。因为,在尝试给宗教现象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从什么地方寻找证据,而且首先必须寻找到那些能够在“纯粹状态”下看到的各种宗教的表现——亦即那些尽可能“素朴的”、尽可能接近其源头的表现。不幸的是,这类证据是根本找不到的;在任何我们已知其历史的社会里,在任何“原始人”及当今未开化的民族中间都找不到。我们在任何地方所看到的宗教现象几乎都是一个复合体,表明其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
因此,就是将某个宗教的材料加以收集整理,也会遭遇相当严重的操作上的困难。甚至一个人仅仅研究种宗教,终其一生也不足以完成此项研究,若想做比较宗教的研究,则好几辈子也不足以达到目的。然而我们想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研究,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神圣不断变化的形态及其历史发展。所以在着手这项研究之际,我们必须从历史学或者人种学已经发现的诸多宗教中撷取若干种,然后仅仅去研究它们的某些方面和某些阶段。
这种选择,即使仅限于某些主要的神圣的显现,也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对神圣作出一些限定和规定,我们必得拥有足敷操作的一定数量的宗教表达以供使用。如此的话开端已属不易,那么,这些宗教表达之纷繁复杂则将令我们愈加气馁。我们会面对各种仪式、神话、神圣形式、神圣和敬拜的对象、象征、宇宙观、关于神的话语、被祝圣的人、动物和植物、圣地,不一而足。每一个范畴都各有其自身的形态(morphology)——各有衍生的、繁复的内涵。我们不得不处理一大批杂乱无章的材料,美拉尼西亚的宇宙起源神话或者婆罗门的献祭,以及圣特雷莎(St.Teresa)或者日莲宗僧人的神秘著作、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原始民族的入会礼(initiation)、“婆罗浮屠”(Borobudur)、西伯利亚萨满举行仪式的服饰和舞蹈、许多地方发现的圣石、大女神的神话和仪式、古代国王的登基以及附丽于宝石之上的诸种迷信,都值得我们关注。每种现象都必须被视为一个神显,因为它通过某种方式表达了神圣在历史上的某个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模态,也就是说人类已有的诸多神圣经验中的某一种。
每一个现象皆因其告诉我仃丁两件事情而具有意义:其一,它是一个神显,所以它揭示了神圣的某种模态;其二,它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就揭示了当时人类对于神圣的态度。例如,以下的《吠陀》文本是送给一位死者的:“爬回到你的母亲,大地那里去吧。愿她将你从虚无中拯救出来!”这份文献表明了大地崇拜的特点;大地被视为母亲,大地母亲(TellusMater);但是它也表明了印度宗教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当时大地母亲——至少在某个团体里面——被当作抗拒虚无的女保护神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在《奥义书》的改革和佛陀的教训中这种意义就被清除出去了。
我们且回到开始之处,如果我们想要对宗教现象有所理解,则每一种类型的证据(神话、仪式、诸神、迷信,等等)在我们看来实际上都是同等重要的。对宗教现象的理解总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神显也是一个历史事实。神圣的每一种显现都发生在某种历史情境里面。甚至最个人化和最超越的神秘经验也受到它们所处时代的影响。犹太先知得益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证明了他们的正义,证实了他们的真实;他们也得益于以色列的宗教史,以色列的宗教史使他们能够解释所经验到的一切。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不过不是作为一种个人经验——某些大乘佛教神秘家的虚无主义和本体论若是没有《奥义书》的沉思、梵语的发展以及其他事物便是绝无可能的。我并不是说每一种神显和每一种宗教经验都是在神性活动中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偶然事件。最伟大的经验不仅在内容上有所相似,而且在表达上也经常是相似的。鲁道夫·奥托(RudolfOtto)在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Eckhardt)和商羯罗(Sankara)的语汇和术语中就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
一个神显总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说,总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发生),这个事实并不削弱其普遍性。某些神显仅仅在当地才有意义;而其他的神显则拥有或者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意义。例如,印度人称某树为菩提树(agvattha);在这棵特定的植物中显现的神圣仅对他们而言具有意义,那是因为仅对他们而言菩提树不仅仅是一棵树。因而那个神显不仅具有时间的特定性(每一个神显均无例外),而且具有区域的特定性。尽管如此,印度人还有宇宙树(大地之轴EAxisMundi])的象征,而这个神话一象征的神显是普遍的,因为我们在诸古代文明中都能找到宇宙树。但是请注意,菩提树之所以受到敬拜,在于它具体体现了在生命的不断更新中的宇宙的神圣意义;事实上,它之所以受到敬拜,是因为它体现了各种神话中宇宙树所代表的那个宇宙(参见§99),或者说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或者象征着这个宇宙。然而,虽然我们可以用在宇宙树拥有的同样象征来解释菩提树,但是,将一种特定的植物形式转变为一棵神树的神显,只是在特定的印度社会中才有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此例子中,一个神显被相关民族的现实历史所遗弃:闪米特人曾经在历史上崇拜过飓风和生殖之神巴力(Ba'al)和丰产女神(尤其是大地的丰产)贝利特(Belit)所组成的一对神界夫妻。犹太先知称这些崇拜是渎神的。闪米特人认为——也就是由于摩西改革后那些获得了一个比较纯粹、比较完全的上帝观念的闪米特人的观点——这样一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古老的闪米特人对巴力和贝利特的崇拜也是一种神显:它表明(尽管具有不健康的、魔鬼般的形式)有机生命、血液的基本力量、性和丰产的宗教价值。这个启示的重要性即使没有延续数千年,至少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作为一个神显,它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被另外一个神显所取代,而这种新神显——在精英宗教的经验中臻于完满——证明其自身令人更加满意,达到了更完满的程度。耶和华的“神圣形式”胜过了巴力的“神圣形式”;它显示出一种更加完满的神圣性,它赋予生命以神圣,却不会任集中在巴力崇拜中的那些基本力量的肆意放纵,它揭示了一种灵性的经济学,人的生命和命运可以从中获得一个全新的价值;与此同时,通过它可以获得一种更为丰富的宗教经验,一种比较纯洁、比较完善的与神交流的形式。耶和华的神显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神圣的普遍的模态,它所具有的本性就是要向其他文化开放;它通过基督教而变成全世界的宗教价值。因此可以看到,某些神显拥有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而变得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神显依旧是地方性的和阶段性的——它们不对其他文化开放,而最终甚至在它们由之产生的社会中也消失了。
2.方法的困难
但是,我们暂且回到前面提到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上来:那就是材料的极端多样性。更为严重的是,每当我们将这些成千上万的零碎证据收罗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材料所涉及的范围似乎是无限多样的。首先(正如所有历史材料一样),我们必须处理的材料多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留存至今的(文献如此,纪念建筑、碑铭、口头传说和习俗亦概莫能外)。此外,那些偶然留存下来的材料来源各不相同。例如,如果我们想要拼接出早期希腊宗教的历史,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相互迥异的纪念建筑以及某些还愿品;在日耳曼和斯拉夫宗教那里,我们只有利用一些简单的民间传说,在处理和解释这些传说的过程中必然是险境重重。一份鲁尼文碑铭、一个在不知其意且历经数世纪之后方才记载下来的神话、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绘画、一些史前纪念建筑、大量的仪式以及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民问传奇一一日耳曼和斯拉夫宗教的历史学家手头就只有这些材料。如果人们只研究一种宗教,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还好说,但是当人们试图进行比较宗教的研究或者试图把握大量不同的神圣模态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完全如同一位批评家手头只有一些拉辛(Racine)的手稿、一份拉布鲁耶(LaBruyere)的西班牙文翻译、一些外国批评家曾经引用的文本、一些游客和外交家的文字回忆、一份外省图书馆的书目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文献,就不得不去写作一本法国文学史一样。一个宗教史学家能够得到的全部材料大抵如此:大量残缺不全的祭司口传知识(这是一个阶层独有的产物)、旅行家的笔记摘录、外国传教士收集的资料、世俗文献中反映的内容、一些纪念建筑、一些碑铭以及依旧保存在当地传统中的记忆。当然,历史学就是要将这类零碎的偶然的证据串连起来。但是宗教史家面对一个比历史学家更为重大的任务,历史学家只是将保留在他那里的一些证据组合成为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宗教史家不仅必须追溯一个特定神显的历史,而且必须首先理解并且解释该神显所揭示的神圣模态。而在任何情况下,要解释一个神显的意义就已经够困难了,而所得到的证据的歧义性和偶然性会加大这一工作的难度。想象一个佛教徒试图凭着一些福音书的残篇断简、一本天主教的每日祈祷书、式各样的装饰物(拜占庭的图像、巴洛克的圣徒雕像,也许还有一件东正教的圣袍)来理解基督教,但是另一方面他能够研究欧洲某个村庄的宗教生活。
毫无疑问,我们这位佛教徒观察家将会注意到,在农民的宗教生活方式以及乡村教士的神学的、道德的以及神秘主义的观念之间的明显区别。然而,虽然他能够把握到这种区别固然没错,但是如果他仅仅因为那位教士只是一个个体——如果他坚持认为,只有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村庄所表达的经验才是真实可靠的——而拒绝根据这位教士所保存下来的传统来判断基督教,那么他就是错误的。基督教所揭示的神圣模态实际上更加真实地保存在教士表达的传统(尽管具有很强的历史的和神学的色彩)而不是村民的信仰里面。这个观察家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瞬间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基督教本身。在整个村庄里面只有一个人可能拥有关于基督教的仪式、教义和神秘主义的正确知识,而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得到的相关知识是错误的,他们的宗教生活沾染了迷信成分(也就是被抛弃了的神显的残余),这个事实对于他的研究而言或许无足轻重。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人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即使不是原创的基督教经验,至少也是其最基本的因素,以及其神秘的、神学的和仪式的价值。
我们在人种学研究中常常发现这个方法上的错误。由于传教士古兴德(Gusinde)在其研究中仅仅局限于一个人,保罗.拉丁(PaulRadin)就认为应当拒绝他所得出的结论。这种立场只有在严格局限于社会学研究对象时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研究在一个特定时期火地岛(Fuegian)共同体的宗教生活,不妨采取这样的立场;但是当我们要发现火地岛民有多少宗教经验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立场就完全不同了。原始人认识不同模态的神显的能力是宗教历史上最为重大的难题。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正如在最近数十年中所作做到的那样),最原始的民族的宗教生活实际是极其复杂的,它们不能被化约为“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或者甚至是祖先崇拜,它们包含各种拥有一个造物主一上帝的一切全能的至上神的想象,那么,那些否认原始人能够接近“高级的神显”的进化论假设就是无效的。
3.神显的差异性
当然,我为了说明宗教史家所掌握的证据之稀少而进行的比较乃是一些虚构的事例,并且必须这样看待它们。我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考虑到我们的证据的歧异和稀少,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谈论不同的“神圣的模态”呢?这些模态之存在,乃由一个事实所证明,亦即一定的神显可以被一个共同体中的宗教精英和其余成员以极其不同方式所共享和解释。对每年秋天大批涌入加尔各答的迦梨戈特(Kalighat)神庙的信徒而言,杜尔迦(Durga)只不过是一个恐怖女神,耍向她献祭山羊;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受礼的虔敬者(gaktas)而言,杜尔迦展现了宇宙生命持续不断的、剧烈的更新。很可能在那些供奉湿婆林伽(1ingam)的人中间,许多人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生殖器官;但是也有人将其视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代表着宇宙节律性的成住坏灭——宇宙通过各种形式显示自身,并且周期性地回到自己初始的、先于任何形式的统一体,然后再复生。杜尔迦和湿婆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受礼之人的解读还是大量信众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将试图证明两肴具有同等意义;大众所赋予的意义与受礼者的解释一样,都是代表着杜尔迦和湿婆的神圣的真实模态。我能够证明这两种神显是一致的一它们所显示的神圣的模态绝非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是一个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确保我赋予大众经验的记载与仅仅反映精英的记载以同样的重要性质。这两类范畴都是必不可少的——使我们不仅能够追溯神显的历史,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确立神显显示自己的神圣模态。
这些想法——本书还会予以充分的证明——可以运用于我前面谈论到的大量不同的神显中。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证据不仅在来源上均衡的(有的来自祭司和受礼者,有的还来自大众,有的仅仅是片言只语、残经和语录,而有的却是完整的经文),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不均衡的。
苏拉米.莫莱《破译的圣经》
| 第一章 上帝与你同在 | 第二章 在神话的背后 | 第三章 寻找人类的父母 |
| 第四章 撩起恐怖的面纱 | 第五章 最后的审判 | ` |
| 第六章 通往天堂的道路 | 第七章 上帝的天国 | 第八章 寿终正寝的千年预言 |
| 第九章 众神的葬礼 | ||
《科学与圣经》目录
前言导言
第一部 自然科学
1 科学之后——圣经与神
2 基督与宇宙——圣经的宇宙论
3神迹与自然律——圣经中的超自然现象
4 误称的假科学——圣经进化论
第二部 物理科学
5世界的创造——圣经宇宙发生学
6 天上的万象——圣经天文学
7 热能——圣经的热力学
8地上的尘土——圣经化学与物理学
第三部 地球科学
9世界的根基——圣经地球物理学
10水与上帝的圣言——圣经水文学与气象学
11 被水淹没——圣经地质学
12化石与洪水——圣经古生物学
第四部 生命科学
13 肉体的生命——圣经生物学
14照上帝的形像——圣经人类学
15巴别塔与世界人——圣经人口统计学与语言学
16 上帝与万国——圣经人种学
| 前言 | 导言 |
| 第一部 自然科学 | |
| 第一章 科学之后——圣经与神 | 第二章 基督与宇宙——圣经的宇宙论 |
| 第三章 神迹与自然律——圣经中的超自然现象 | 第四章 误称的假科学——圣经进化论 |
| 第二部 物理科学 | |
| 第五章 世界的创造——圣经宇宙发生学 | 第六章 天上的万象——圣经天文学 |
| 第七章 热能——圣经的热力学 | 第八章 地上的尘土——圣经化学与物理学 |
| 第三部 地球科学 | |
| 第九章 世界的根基——圣经地球物理学 | 第十章 水与上帝的圣言——圣经水文学与气象学 |
| 第十一章 被水淹没——圣经地质学 | 第十二章 化石与洪水——圣经古生物学 |
| 第四部 生命科学 | |
| 第十三章 肉体的生命——圣经生物学 | 第十四章 照上帝的形像——圣经人类学 |
| 第十五章 巴别塔与世界人——圣经人口统计学与语言学 | 第十六章 上帝与万国——圣经人种学 |
亚特兰蒂斯(1)
亚特兰蒂斯(2)
亚特兰蒂斯(3)
亚特兰蒂斯(4)
《圣经》考古新发现(一)
《圣经》考古新发现(二)
《圣经》考古新发现(三)
《圣经》考古新发现(四)
眭澔平探险世界(搜狐)
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一)
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二)
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三)
精品区>亚特兰蒂斯密码
与科学家一起论说创世记
【宇宙昆仑文明】:星际来客
海底大西洋城的秘密:亚特兰蒂斯
【地球人类文明的渊源】:文明的冲突
地球人类文明的渊源(八):雷姆利亚文明
地球人类文明的渊源(九):亚特兰蒂斯文明
地球远古地下长廊之谜 地球内部的世外桃源
亚特兰蒂斯——精典博维 //起点中文网
眭澔平探险世界神秘古文明探险记
神话新解《神话是真实的历史》
美国作家唐纳里著的《海底大西洋城的秘密》
秉诚(里程):《游子吟--永恒在召唤》
宋文淼:读圣经,学科学、(3) 圣经和语言
读圣经,学科学(1)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读圣经,学科学(10)信仰与历史 (六)以色列的民族的发展历史
读圣经,学科学(11) 信仰与历史 (七)民族、国家与人类的历
(12)读圣经,学科学: 信仰与历史 (八)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中编
伊格内修斯·唐纳里:《海底大西洋城的秘密:亚特兰蒂斯》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美)麦克斯缪勒 -天主教在线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套装共3册)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马丁·海德格尔)
宗教学导论(英)麦克斯·缪勒
西方建筑:从远古到现代
宗教学导论的笔记(12)
神圣的存在_百度百科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破译圣经》读书笔记(下)
《破译圣经》读书笔记(上)
科学与圣经、信仰与科学
基督教与科学、面对进化论
圣经中人物名字意义
进化?退化?神化?
圣经--超越时空的神言
与科学家一起论说创世记
科学之思—科学家的人文反省
幽涧寒松:惊天大秘闻:窃世大盗-《圣经》原为抄袭
沙龙葬礼安排:哀悼持续一个月 至亲“头七”不做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