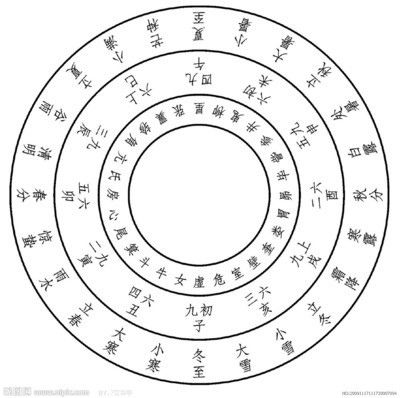“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的来龙去脉
——谈新版《王明传》的一个重要变化
戴茂林
2009年04月27日13:55来源:《北京日报》
《王明传》,戴茂林、曹仲彬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王明传》,是我与曹仲彬教授在1991年5月出版的《王明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部人物传记在17年后再次出版,自然要做较大调整。我们在后记中已经写明:“这本《王明传》较之1991年版,作了较大改动。结构上,以王明人生的几大阶段为依据,将原来的十章改为九篇;观点上,诸如'右倾投降主义’等原有的提法按照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作了调整;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间等史实根据新发现的史料重新做了考证;还增写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等一些新的内容。”
其中增写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是新版《王明传》的最大变化,也是在此之前几个版本的《王明传》、《王明评传》中都没有涉及的内容。
不涉及,并非不重要。很多人都知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经是王明教条宗派的代名词。但重要的问题未必能够轻易地搞清。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经过查阅文献,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认真研究思索,我们在这部《王明传》中首次公布了如下研究成果: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出现的两种提法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这些人的说法又可分为四类,这几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
“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讽刺性称谓的提法是比较可信的
真正搞清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由来,必须联系“十天大会”召开的背景来看,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
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也借用了中国“二十八宿”的传说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信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是有一定道理的。
已无必要继续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虽然并非是后人的虚构,而是在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但是,存在过的未必就要沿用。所以,我们在《王明传》中采纳了杨尚昆同志的意见:“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实事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作者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杨华1962 于 2012/3/22 0:09: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 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 稼祥等。汪云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 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当事人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 仍属少数。
早在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心眼多多,向时任副校长的米夫献计,趁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对反对这两派的“第 三势力”加以利用。这为米夫当校长铺平了道路,王明也成了米夫的心腹。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像“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二十八个半”。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群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因为 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意即“绝对正确”)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
有史以来像苏共、中共这样将党内斗争看得如此严重而绝对,斗得如此执着而残酷者,数不出几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本来就带来国内的矛盾分歧,山头 林立,“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语),而校方和共产国际又将苏共党内的路线、宗派之争掺合进来,更搅得你死我活。善良的人往 往不解:同在镰刀斧头红旗下,怎么自己人斗得这么狠?原因并不复杂:为了在敌我斗争中取胜,本来就无所不用其极,专制君主是谁有父王授命谁上台,民主领袖 是谁有民意拥戴谁上台,而当时中共拼的是路线——谁能证明自己路线“正确”谁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为此,就得将论敌打成“内奸”“叛徒”“反革命”和 “托派”。
1929年夏天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0年底,米夫来华。他此行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控制中共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 徐以新。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提出中央委员补选和政治局改组名单,要求中共“按照组织纪律”必须通过。翻脸大吵一番之 后,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就成了中共掌舵人——不过,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 个半”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笔者见到的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 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王明重新赴苏联,就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在一家小酒馆“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八 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权柄。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这里姑且不提;他们残杀自己人不眨眼,让人毛骨悚然。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 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 “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杀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 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 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夏曦同张国焘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去给张当助手的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沈泽民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从理论和行动上 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堪称帮凶。仅1931年秋天两个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十分之一,达2500多人。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内一 次就逮捕3900人,当即杀掉2500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3年6月以后,张国焘、陈昌浩又在新开辟的 川陕根据地大屠杀,杀了红四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另一领导人曾中生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他们不敢公开杀,是长征途中在张国焘住房里被用绳子勒死的……
“二十八个半”后来分道扬镳。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转而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在遵义会议上他与张闻天站在毛这一边;毛泽东在“七大”时专门讲:“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却没熬过“文革”,在受冲击和批判中去世。
博古与德国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作战一败涂地,不得不承担责任,交出了权力。后因飞机失事而亡。“二十八个半”在战争年代牺牲、病故或因意外而死的还有:沈泽民、夏曦、殷鉴、陈原道、何子述。
李竹声(上海中央局书记)、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组织部长)、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汪盛荻、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人被捕后叛党;杜作祥(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被捕后下落不明。
凯丰(中宣部副部长)、陈昌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盛荣、杨尚昆、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张琴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人,有幸活到建国以后,还 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也程度不同受到许多冲击。其中陈昌浩在“文革”中自杀。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走运的。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 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66年,他因对毛泽东录音窃听事件被打倒,关了12年。“文革”后平反进入权力中枢,当了国 家主席。
王明、孟庆树夫妇对于造成的灾难未曾悔改。党的“七大”召开时,王明患病,开幕式时被抬进了会场,历时15分钟。毛泽东劝服代表仍将 之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2月他去苏联治疗定居,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寓所抱病写完《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文版)的第四 天病死,享年70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中共党史上交织血与火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他们,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论其初衷多么 不同——从最高尚到最卑劣——他们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写下了一出大悲剧,包括他们个人的悲剧(而其中像夏曦,不论当权者将他供 奉在什么样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对于后人来讲,或许更重要的是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轻人,怎么才能避免落入阴谋和残忍的万劫不覆的梦魇。
> > > 正文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一对叛徒夫妇
2010年07月30日 08:37 《同舟共进》
核心提示: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出版说明”和“译后记”,盛忠亮于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叛变,且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调查部当了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作者:散木,原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一对叛徒》
曾几何时,每个被接纳进党组织的新共产党员,都曾心潮澎湃地在党旗前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这其中,“永不叛党”四个字分量最重,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然而,中国革命既曾涌现过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
以下就是一个当年从革命队伍中悄然隐身的女子的故事。
莫斯科与一对革命佳偶
秦曼云(1908-2001),曾用名秦影云、秦缦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她生逢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结识了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批早期女共产党人,并在她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济南的“非基督教大同盟”等革命团体。1925年,秦还与王辩等人发起成立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并参与山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之后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她转为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了省立女中党支部书记)。
秦曼云活跃在大革命的舞台上。“五卅”运动中,她带领省立女中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又参与济南团地委组织领导的全市性反帝运动。8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开始疯狂镇压山东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秦曼云则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改变斗争策略,转入地下活动。这期间,她曾担任共青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学委书记、宣传部部长,1926年7月,当选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青年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说“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的)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了。“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
关向应是中国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一个是大道,一个是歧途。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
1928年6月至7月,秦曼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洗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守候在门口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以及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和交通员周惠年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和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一说后经保释出狱,从此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不时发生,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以及党建问题的特别重要。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与黄文杰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这里必须说说盛忠亮。此人后来易名盛岳,字伐樵,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不久成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劳卓著”的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随即折节叛变。
李竹声和盛忠亮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也都是王明宗派主义小团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人物。盛忠亮是学生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书卷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学习成绩优异,外语能力出类拔萃,又自视颇高,曾于学习期间被安排在工人预备班教授政治常识——与他一同给工人授课的,还有洛甫(张闻天)。围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政权力之争,新任校长米夫与王明等一班人马声气相投,拉帮结派,最终形成一个宗派阵营。王明等人为了争取盛忠亮,不惜采取卑劣做法,即:“最可耻的是,竟用李竹声的老婆方俊如施美人计把盛忠亮拉过去。”(李一凡《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盛忠亮入伙后果然了得,他被米夫等重用为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兼任支部局秘书,全盘负责文字和会议的翻译工作,所谓参与机密,炙手可热。据说盛后来还是苏联进行“大清洗”时“别格乌”(即“契卡”的前身)的助手,曾参与对中国被捕同学的逼供。
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出版说明”和“译后记”,盛忠亮于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叛变,且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调查部当了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那么,秦曼云呢?继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她又奉命出庭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随即又被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过,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同志却终止了这一时期党内“被捕即叛变”的恶性循环,他们在狱中大义凛然,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风范。如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空如(即陈焯)是朱镜我的同乡和亲戚,他写信要“保释”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信后轻轻地说了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加理睬。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留学时的同窗,他也来劝说朱镜我“自新”,遭到朱镜我的驳斥。(两人在会见室用日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朱说自己革命无罪,根本不需要“自新”。)朱镜我夫人的叔父赵次胜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他出面要保释朱镜我,但朱不为所动,赵次胜只得感叹地称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1943年,盛忠亮在民族抗争的热潮中天良发现,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中国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其间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达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盛忠亮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任欧洲司司长,曾出任驻乌拉圭和伊拉克的大使。解放前夕,盛、秦夫妇转赴台湾,后定居美国。
重说“二十八个半”
盛忠亮也是著名的“黑皮书”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作者。
此书最早在1971年由美国纽约派拉贡书局出版(英文版)。中国大陆于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相应的党史研究逐渐开放,后又逐渐引进一些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比较可靠的“内部书籍”,并渐渐成为热门的党史参考研究资料——《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正是其中之一。
此书的最大亮点,是由亲历者讲述了中共党史上那个被人猜测过无数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路线错误——王明左倾路线,其发生和渊源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莫斯科;最初的雏形,就是这个众说纷纭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盛忠亮专门讲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等内容。盛忠亮的讲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在场者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是他真实而又不乏见解的忏悔录。
盛忠亮写道:“在中共六大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形成”,“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原来,在当时苏共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围绕“教务派”和“支部派”,中国学生也展开了同样激烈的斗争,王明等人和校长米夫站在了一起,他们打压“教务派”和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等),又炮制了“江浙同乡会”等冤案,“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盛忠亮说:“这一同盟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共本身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盛忠亮回忆:当时,“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普遍地不得人心。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同他们打成一片,他只和一小撮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这些人后来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著称”,“这些人”中,就有盛忠亮。他还说:“尽管米夫不受中山大学许多学生的欢迎,可是他却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随着1925年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形势对共产国际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米夫担任的中山大学校长的职位也就随之成了为人所共羡的美差。再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给了他进一步改善其地位的机会。”
正是“由于他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尽管在当时的俄国比他能干的人多的是,却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国学生的争论中,“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胜利的姿态问世”,并且“为他们后来夺取整个中共的领导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于是,当这些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优秀学生回国后,这批“斗争干部”先是反对李立三的路线,接着反对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错误”,又反对何孟雄、罗章龙等的争夺,最终米夫跟着来到中国,“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言之,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以及“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的持续动乱和国势颓败。对此,盛忠亮在书中客观地指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他们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哪些人,有过种种的无稽之谈。算我走运也是我倒霉,在出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我正好在中山大学上学,而且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盛忠亮接着点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具体名单:
陈绍禹(王明)、孟庆树(王明之妻)、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杜作祥(陈的妻子)、沈泽民、张琴秋(沈的妻子)、陈原道、殷鉴、朱阿根、何克全(凯丰)、夏曦、李竹声、盛忠亮、孙济民、王保礼、汪盛荻、王云程、袁家镛、王盛荣、朱子纯(女,即朱自舜)、何子述、李元杰、宋潘民、肖特甫。(至于那个“半”,当是徐以新,即徐一新,后为外交部驻外大使。)
盛忠亮分析这份名单:其中的成员都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党员或团员(湖北最多),有4位女性(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出身工人的有5个,“其余全是知识分子”,“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中共要员。这些人后来的命运,4人去世,3人为烈士(陈原道、何子述等),还有11人“被国民党抓捕后脱离了共产党,其中三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被捕和处决”——这最后的一群人之中,当然就有盛忠亮自己了。
“二十八个半”的名单,当年有各种版本。盛忠亮提供的这个版本,由于他是亲历者,自然有可信的价值。至于“二十八个半”的产生,一般来说,是由于1929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十天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一说其尚未成年),于是遂有“二十八个半”之称。另据李一凡的回忆,之所以称为“二十八个半”,是“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二十九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据说是徐一新——作者注),所以余笃三同志嘲笑他们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二十八个半!’之后,'个半’就成笑柄而传开了”。也有人(如陈修良)认为并无所谓“半”,就是“二十八个”。
事实上,“二十八个半”的来历并不重要,究其本意,应该是后来的人们借助这一称号,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不过,“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随着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成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比如个中的人物,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就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等,杨尚昆更是第二代领导人中职任共和国主席的人物,其他许多人也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然而,在“文革”中,“二十八个半”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打狗棒”,如康生就曾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使一些无辜者遭到严酷的审查和关押,乃至受迫害而亡(如张琴秋等)。鉴于这种情况以及这一名称常被人误解,杨尚昆生前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出:“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如此说来,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称的不精确和容易误解,不如代之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他称号为宜,如“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小团体”等。当然,如果去除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歪曲的褒贬色彩,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典故,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称也不妨存在。
却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除盛忠亮外,还有李竹声(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袁家镛(又名袁孟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与李竹声一起被捕叛变,后在“中统”工作,改名严英)、王云程(化名张汉卿,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书记、中央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叛变,与李竹声同流合污,导致罗登贤和廖承志等被捕)、孙济民(即孙际明,化名黄守素,团中央组织部长,后与王云程一起被捕叛变。孙解放后被逮捕法办)。此外还有一些未能查明的人,如朱阿根(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后来一说退党,一说叛变)、汪盛荻(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说退党,一说叛变,解放后在湖南被处决)、李元杰(一说回国后淡出政治舞台,一说叛变)、王保礼(即王宝礼,曾“荣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之位,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也有一些人后来退出革命,如朱自舜、杜作祥、肖特甫(下落不明)。
除了“二十八个半”中的叛徒,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堕落为中国革命叛徒的,还有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其叛变经历极其传奇)、蒋先启(叛变后曾任国民党36师政训处长,参与对瞿秋白的审讯和监刑,后更堕落为汉奸,为汪伪“中国青年模范团”训导长、“青年暑期集训营”训练处长)、费侠(女,后与国民党中统首领徐恩曾姘居、结婚,专事收买留苏叛徒,国民党立法委员,姚文元的“干妈”)、费克勤(女,后为中统职业特工)等人。
正所谓“大浪淘沙”。“沧海横流”中,也会“显出宵小的本色”。
突然回国的海外“阔太太”
有人曾问:“盛岳、秦曼云这一对叛徒夫妻,后来为何没有遭到中共'特科’的'清算’,最后也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排挤和抛弃,反而结局挺好?”
可惜盛岳和秦曼云都没有留下相应的回忆,而我们的党史著作和回忆也没有留下相应的信息。笔者分析,也许是由于他们叛变后隐蔽得较深,中共“特科”后来也受到重大挫折,无力“迅速出击”,使他们得以苟活;而且,他们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张扬,当然也没有像张和顾那样的“资格”来让国民党特务“较劲”。所谓叛徒,聪明者,会选择低调以苟且偷生,时间一长,也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了。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忠亮全然不谈自己和秦曼云叛变后的经历和生活,不说是难以启齿,也实在是“乏善可言”吧。不过,应该说,这对夫妇的晚年并不是一点作为也没有。
盛忠亮,当年可谓中共中央机关的青年才俊,才思敏捷,又通晓俄、英、法几国语言。他用英文写完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在序中说:写这本书,他特别“要感谢中山大学同学和我的妻子秦曼云给了我以全力支援。我并不是单单感谢她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但她有这样好使的脑子却是我的莫大幸运,她随时帮我回忆往事,这既可以勾起我的回想,又可帮我校正。她对关于中共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尤为可贵,因为只有她比任何别人更有资格来提供六大的情况”。的确,当时在世的人当中,由于秦曼云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去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中国学生之一,又以其职责所在,是有充分回忆的余地的,所以,书中引述了许多秦的口述,因其历史价值颇高,现在被许多史著所征引。
盛忠亮晚年身居海外,仍关心祖国状况,并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他在故乡湖南石门设立了一项“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的贫困女子完成学业(每年资助10名小学女生从小学三年级读到高中三年级),大致至2006年止,已累计资助了70名女生完成高中学业、10名完成大学学业,先后投入资金约50万元。他还派长子盛孝威博士偕夫人回故乡颁发这笔资金。至于秦曼云,更多次回国观光,还作为“爱国华侨”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1986年秋,秦曼云回国探亲时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的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此时此地,不知她作何感想?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在一篇《我与干爸爸王鹤寿》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件事,实际上说的就是秦曼云。她说: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秦曼云如何为自己当年的行径“开脱”,可惜这里没有记录。也许,当年她是别有“苦衷”吧。其实,当年盛、秦夫妇的叛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上述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的连续被破坏,以及黄文杰等的被捕,都可以有人证实的。当年在上海“文委”秘密活动的夏衍也曾回忆说: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租界当局,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突击行动”,“不仅逮捕对象和机关都相当准确,而且使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文委、左联、印刷厂等,同时受到了打击。事实很清楚,没有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王明死党的告密,2月19日的大破坏是不会那样严重的。”(夏衍《懒寻旧梦录》)
秦曼云返国观光,已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一些特别的人物陆续得以回国,在他们中,除了秦曼云,还有龚楚等。
2001年,秦曼云去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