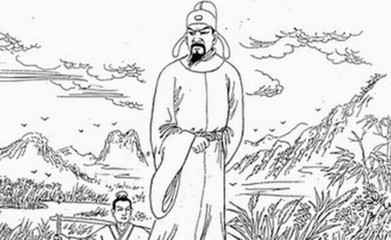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第一,近代之君主政体,如古代之用专制至极点者亦甚少。除俄国、支那、土耳其数国外,大抵皆以宪法为主……所以如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在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今日之世界,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立宪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立宪已胜,故专制之后,必成立宪也无疑矣。[93]
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不仅明确将中国政体定性,并进一步以世界大势为据,指出这一政体必将为立宪所取代,提出了变革的方向。这种论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启发与帮助。
受以上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约自1901年起,“专制”说逐渐为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所了解,并迅速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94]1901年5月10日《国民报》第1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说:
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故夫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并没有使用“专制”一词,不过其具体描述与后来“专制”说所概括得并无区别。作者显然了解“专制政体”,他在后面叙述欧洲历史时多次提到“专制”问题,如“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于是列国乘之缔结维也纳大同盟,主张君主专制之政体,将以全欧国力,压抑民权之说”等等。[95]一个月以后,即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刊登的《说国民》一文引述流行观点则直接将中国自秦以来的政体归为“专制”。文云:“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嬴秦以后无国民。”[96]此文发表上距《万法精理》中译本问世只有半年。
此后,各种批判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不断见诸在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各种报纸。
梁启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号《新民丛报》及1904年6月第49号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1902年11月第21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后文中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对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观概括,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并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均归结为专制之祸,说:
中国数千年君统,所以屡经衰乱灭绝者,其厉阶有十,而外夷抅衅、流贼揭竿两者不与焉。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木+巳)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于是者也。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97]
以下,梁启超历数各代衰亡的原由,最终无不落实在专制政体上,所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之也。”“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98]此文痛快淋漓,可以说是声讨中国二千年专制政体的一篇战斗檄文,其思路与观点对时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此文对于中国的专制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此后,知识分子则更多是直接接受这一论断,基于“专制”说展开论述。
1903年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接受了中国“专制”说,此前他多次谈到或写到政体与朝廷情况,他只是称为“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没有提到“专制”。[99]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说:
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100]
这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专制”。数月后他在檀香山发表演说,亦云: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01]
此时“专制”已是与“共和”相对的制度,不过,孙中山尚没有明确将中国数千年帝王统治归为“专制”。到了1906年,他也如梁启超,开始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02]。此后,专制成为他所常用的概念。
这种论断出现不久就迅速开始在国内传播,传播的桥头堡应是上海。1900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8卷本,增加了《自强论》一篇,其中指出:“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蒙谓”当是指孟德斯鸠,看来他亦是从孟氏思想论著中接受的“专制”论。此前,作者心目中的政体概念还是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14卷本《议院上》),此时作者尽管已经接受了“专制政治”这个概念,却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治,或是有所忌惮,或是抱有幻想。[103]
1902年甘韩编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入了前引《国民报》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之中国》、《说国民》等文,包含了抨击秦以来二千年专制的内容,此外,《君民权平议》与《尊民权》亦从不同角度批判专制,伸张民权。其中所收《孟德斯鸠学说》更是详细介绍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孟氏三大政体说。[104]1903年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其一开篇就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后面回顾历史指出“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他思想来源是:“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理论基础是:“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05],其上述思想亦应是源于孟德斯鸠等的著作甚明。
1903年发表于上海《国民日报》,并收入次年的《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的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亦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106],亦是出于反对专制提出要改用黄帝纪年。时人的思考已经从抽象的“专制政体”发展到对其具体表现的改造,可见“专制政体”说已成为思考的一个支点,表明该说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发表于该报,后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的《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说:“环地球而国者以百数,而专制之国,独以亚洲为多;环亚洲而国者以十数,而专制之国,又以中国为最……及秦有天下,变封建而为统一,地方分权之制变为中央集权之制,君民共主之世变为君权专制之世……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以下则述历代限制君权的思想以及怂恿发展君权的思想,以证明“专制之祸”“溯其原因,皆起于中国人民之思想”。[107]亦是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作者的分析将政体的不同落实在空间上,特别是将“专制之国”与亚洲联系起来,有明显的“自我矮化”的味道。
此后,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虽已不多,正如熊范与1907年所说:“今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108],许多文章都是以此为立论的一个前提。如1905年2月孟晋在《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一文中指出:“然观我政府,自数千年专制以来,积习相沿,已若牢不可破。”[109]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第1号发刊词中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110]1906年1月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称:“夫专制流毒之浸淫于中国者,二千有余载矣。”[111]同年4月署名扑满的《革命横议发难篇》一文亦说:“中国自秦以来,专制之术,日益进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无虑皆钤制束缚之策也。”[112]1907年5月署名与之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认为:“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113]
除了批判“专制政体”,亦有人提出应利用“专制”以实现“立宪”,显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1905年5月刊发的榖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一文亦指出:“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不过,作者不赞成“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主张,提出“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具体做法是“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通过专制的力量发展教育,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刬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并批评说“世人不察,徒诟厉专制之政教,欲举一切蹂躏之,盖亦炫于立宪之美名,而不知所处耳”[114],其说认识到立宪无法一蹴而就,需利用专制力量,较之简单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在当时也显得另类。1906年1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说录》亦云:“我个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幺可贵……(但)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115],亦是超越了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观。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主流。
其实,同在1905年,最早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并加以批判的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目睹其民主制度的弊端与旅美华人的状况后,思想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在该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指出中国民智不开,施政机关未整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尚不具备,转而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希望通过一强大而开明的朝廷来行使国家主权,抗衡西方。[116]此说看似倒退,实际反映了梁启超更深的观察与思考。不过,衬托在当时主张立宪与革命的两派的高亢旋律下,这类声音颇为微弱。其实,孙中山后来所说的“训政”的含义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并无原则性的差别,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途径不同:孙是在推翻清朝后实行,而梁则寄希望于清廷。
20世纪初,上海的报刊与日本的中文报刊内外呼应,一道成为传播“专制”说的阵地。
经过几年的宣传,尽管在如何对待“专制”上意见并未统一,但视中国过去二千年为专制上并无异词。此说影响之大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主此说,就是如康有为、黄遵宪与杨度这样反对革命,倡导保皇改良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说低头。
早在1902年9月发表的《辨革命书》中,康有为就称:“又历朝皆少失德,无有汉桓、灵,唐高、玄,宋徽、光,明武、憙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117]强调专制并非满族所创设,而是沿袭汉代以来的旧制,潜台词并不否认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政治专制”。次年1月13日黄遵宪在《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说:“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非生于今日,地球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中国)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118]所说不无道理。杨度在1907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报》“叙”中说:“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119]此三位均反对革命,却同样不否认中国历来专制政体之存在,可见此说影响之深广。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为专制政体说出现10年后,甚至连清廷的大臣、官员也屈从于这一论断。武昌起义爆发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革命风潮浸及东省,东省人士非不知脱离专制,尊重自由。无如默观时局,知非君主政体不足以自立”云云。一个多月后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其中亦称:“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因此认为不能急于实行共和[120]。尽管这些人反对共和,但他们却已在使用与“共和”密切相联的“专制政体”一词来概括历代政体,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屈服于新思潮。“专制政体”说开始成为清廷部分官员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为其覆灭提供了思想基础。宣统宣布退位后两天,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齐耀琳致电袁世凯等亦称:“此次中华改革国体,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阅时不过四月,潮流迅急,亘古所无”。[121]此人视清廷为“专制”显非始于清帝退位之时。从这一角度看,“专制”说并不只是一种流行世间的论断,它亦参与到历史实践中,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维新派、革命派、保皇派,还是清政府,均接受了“中国专制”说,确如佐藤慎一所指出的:“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122]
3.“专制说”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与学界的不同见解
“专制政体”之说不仅很快见诸国内的书籍、报端,国内新出现的百科辞书中不久也开始出现“君主专制”的条目。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就设有此条,解释做“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123]。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虽未见“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的专条,但亦有一些条目内容涉及“专制政体”或“专制国”。[124]1915年首版的《辞源》也有“专制”一条,释义二做“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曰专制,参看专制政体条”。同时设“专制政体”一条,云:“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为立宪政治之对。”[125]表明来自西方、表示政体的“专制”,作为一个新词已在汉语日常词汇中占据了合法的位置,预示它将逐步成为中国人认识历代政体,乃至历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扩大“专制”说社会影响的另一重要渠道的是20世纪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初起,一些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绘成“专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绘成“专制”王朝。目前所见,1904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节体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再版,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该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的第五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上”云: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促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126]
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云:
文帝好黄老家言,其为政也,已慈俭为宗旨,二十余年,兵革不兴,天下富实,为汉太宗。其专制君主之典型哉。[127]
第二十节“汉外戚之祸一”云:
推其(指母后临朝之制——引者)原理,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128]
第六十五节“文学源流”云:
(以文辞取士)与中国相始终,推其原意,皆立谈之变相耳。此专制政体之不得不然也。[129]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均以“专制政体”来解释,无论现象与专制政体间是否存在联系,“专制政体”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药。
此外,1914年出版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治”指出:
始皇为专制之大枭桀,故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下略)。
此书1914年8月发行,至1920年已印行16版[130],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可想而知。又如1924年出版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云:
明太君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这为什幺呢?其实只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罢了。[131]
再如1932年出版的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三编“中古史——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中说:
从此以后政权遂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而确定二千余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基石。
次年出版的下册中称:
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中于君主一身,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明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恶劣,远甚于前代。
君主专制的局势,到明代而达于极点,但这样的政制,便于英主而不利于庸君。[132]
再如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说:
汉代盛时的政治中心,实在是在皇帝一人手里。所有那时的政治,实在可说是君主专制政治,和上古的贵族专制不同了。[133]
应该指出,1949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颁布的各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均没有将秦以来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的条目与要求,只是个别标准提到欧洲“中古教会之专制”、“十八世纪世界专制政治及其所引起之反动”[134]或“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政治”[135]。明确将秦以后的政体与专制联系起来的是1956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36]上述教科书中的论述均是出自编者本人的观点,这些作者,除了钟毓龙生平待考外,余下的大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礼,在教科书中做如此判断并不奇怪。
私塾蒙书退场后,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广大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中国专制”说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到开始进入中学教科书,前后不过几年时间,其间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消化与鉴别。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一种舶来的新词汇、新论断就被视为当然的结论采入中学教科书,传授给青年,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急心态。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专制”说不过是民国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年以后学术界的共识之一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为“专制政体”。1929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治,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后世之政体,虽若一君专制之外,更无他途可出”。[137]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138]这一表述对1949年以后的大陆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其实除了“封建国家”说之外,接受的均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观点。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资生亦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政体。[139]杨熙时在讨论中国历代政制的时代划分时指出:“第二,有秦一代,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交替时代。第三,秦代以来专制一尊,成了政治的常轨,所谓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中唐的藩镇,元清的种族专制等,都在这个自秦以来的专制一尊的政治环境里盘桓。”[140]王亚南在1947-1948年曾概括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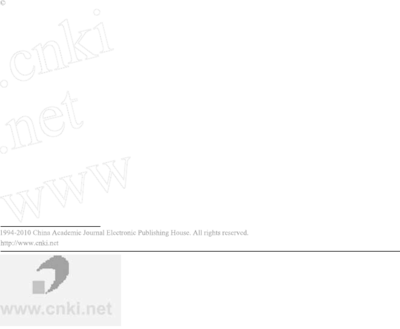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141]
确如王亚南所说,在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无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赞同共产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各派见解不同。就连更早的“国粹派”也频繁使用“专制”来描述中国传统政体。[142]
民国时期,大概惟有钱穆明确反对将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归入专制之列。1941年10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强烈不满,关于政体,则指出,“西人论中国政制,每目之曰专制,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自鄙”,认为自称中国专制是“自鄙”。对于中国为何不是专制,他也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有很大区别,其结论是“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143]几年后,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指出:“西方学者言政体,率分三类:一、君主专制。二、贵族政体。三、民主政体。中国自秦、汉以下,严格言之,早无贵族,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此不待论矣。中国虽有君主,然固非君主专制,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也。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144]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存在过“专制”,同是在1945年发表的《论元首制度》中,他说:
细按中国历代政制,惟满清君主,始为彻底之专制,其所以得尔者,盖为满洲王室有其部族武力之拥护。其专制之淫威,虽甚惨毒,而亦尚不至于黑暗之甚,则因中国传统政制,虽此君权相权衡平调节之妙用已为破弃,而此外尚多沿袭,故最高政令虽常出之满洲皇帝一人之专断,而其下犹得弥缝匡救,使不致流为大害也。[145]
以上是钱穆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前出版的《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与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钱穆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146]尽管如此,此说一出,犹激起了萧公权与张君劢等人的批评,可见主张中国古代为专制政体者之固执。仔细分析,钱穆的论断尽管反对专制论,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与专制论者均接受了亚里斯多德三大政体说的基本框架,同样是以西方的政体说作为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政体,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说。这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更多的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钱穆立说依然没能挣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
三、中国接受“专制说”的背景与后果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 “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显然不可能对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安心从事研究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接受的,并随即应用到实践中。从学术的角度看,是犯了结论先行,以论代史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这一并无多少事实根据,且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论断?
从中国本土方面考虑,最直接的是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到的空前挫折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历史,意识到自己的政体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前人的研究已多[147],不拟赘述。这里仅就政治局势背后隐藏的深层“心态”做些分析。
进一步观察,支持这种认识的是中国人看待“过去”时长期存在的“成王败寇”逻辑。这种逻辑集中体现在史书中,中国历史上“正史”编撰的基本方式是本朝只修起居注与实录,由后代为前朝修史,更强化了这种逻辑。权力斗争中取胜的一方(新王朝)拥有最终的叙述前代王朝历史的权力,失败的一方(覆灭的王朝)只能被表述,不能自己去陈述自己的“过去”。在这种格局下,历史的叙述,特别是涉及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时自然多呈现出“曲笔”与“回护”,将历史进程描述为向新王朝迈进的“线性的历史”,贬低前朝的政绩与功绩。史家往往成为枪手,负责执行“曲笔”任务。[148]同时,还应注意到,所有的士人,即知识分子,都是在不断阅读这些呈现出“线性历史”的史书中步入士林,进入官场的,难以逃脱浸透在“史书”中的这种史观的潜移默化影响。即便到清末,当他们走出国门,这种逻辑也会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在清末巨大冲击中所遭遇到的是亘古未有的变局,取胜的不再是某个从中国内部产生的新王朝,或某个周边的外族,而是远道而来,挟坚船利炮的“夷人”,落败的不仅是清王朝,而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专制说”等等对自身历史的批判与重新论述,再次充当了执行“曲笔”的枪手,只不过这次目的发生了变化,目的是拯救中国,而不仅仅是证明某个中国王朝的无能与失败。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分析中国史学的正统问题时就曾指出:“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149]不幸的是,他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却依然重蹈覆辙。
这种逻辑也同样应用到打败清朝的“洋人”身上,因为自1840年以来洋人多次打败清军,显示了船坚炮利的力量,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西洋人、西洋学说由漠视到佩服与羡慕,从而出现了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自我否定历史的潮流。20世纪以后出现“全盘西化”说不过是这种潮流的极端而已。这种逻辑说穿了是一种“以今度古”的“非”历史的态度,类似于对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50]。更深一层讲,体现了权力对“历史”叙述的操纵。如果说近代西方逻辑是“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权力就是(历史)知识”,拥有权力也就获得了解释历史知识的权力。
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如学者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欧美东方学的理解与方法在中国自我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对过去的理解中成为一个可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儒教、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家族主义还是特别的种族特性,都可以溯源至欧美东方学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的共同之处在于使用出自西方观念的形象、概念与标准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传播这种西方意识的不仅是西方的传教士,还包括海外的中国人[151],实际上还包括作为重要桥梁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这几股力量共同作用将西方对东方的表述,如中国专制之类,译成中文,引入中文世界,并变成自己的表述加以传播,进而重新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记忆。[152]
其结果是中文世界中出现的中国史,表面看来由中国人自己做出的论述,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实际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语言,而是经过翻译、引进与创造的“近代汉语”语汇,骨子里则是欧美东方学对中国漫画式认识的重复、再现与拓展,中国“历史”因此丧失了依据自身的脉络表达自己的机会与能力,从而实现了在物质层面之外的“文化与表述层面上”对西方的依附。
同时,这种舶来的论断又直接卷入清末的实践活动,为推翻清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中国人在对自己历史的描述中用“专制政体”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年政治时,就等于在替西方人宣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正是由于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己如此表述,也才会更具有欺骗性与“说服力”,才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接受这一论断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走向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即按照西方人的观念重新塑造对中国自身历史认识的过程。其结果是我们在空间上是生活在西方以外的东方,但是,从商品、品味、感觉到表述,实际都难以挣脱西方制造的牢笼。
“中国专制”说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历程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背景下国人思想上经历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中国在现实中仅仅是半殖民化,但在思想观念上受到的殖民却更加严重。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得的),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和“中国专制”说一样,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加以西方“东方主义”的歪曲,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不可等闲视之。这种歪曲的中国观通过各种渠道流行于世,所以,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当代学者也并非直接、透明地面对史料,而是透过包含着近代以来,乃至早到传教士时代以来所形成积累的“中国观”在内的观念来认识过去,因此,近代历史对于研究古代的学者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清末救亡图存的斗争年代,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的武器无可厚非,随后未经认真充分的研究,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则遗害不浅。这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忽略并遮蔽了许多历史现象,妨碍对帝国体制的把握,也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无意间为西方的“东方学”做了不少添砖加瓦之事。即便是似乎远离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实际也难以摆脱其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对以“专制”说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观的彻底清理,具体研究很可能会在不自觉中为这些歪曲之说推波助澜。
如果以上分析不误,现在亟需摘掉这类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153]在缺乏对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以及君臣关系全面清理的情况下,贸然以“专制”论作解,可能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54]。这一重新探索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间也许充满艰辛与曲折,但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却是值得的。
本文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本所黄正建先生、马一虹女士及本院近代史所崔志海先生的惠助,在近代史所吕文浩先生的安排下曾于2005年6月在该所青年沙龙上宣读过此文初稿;后曾将此文提交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6月,上海)、北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北京),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会议(2007年12月,香港),得到与会学者,特别是葛兆光、罗志田、王东杰、于庚哲、张建华、章清与孙宏云等先生的指教;关于日本思想界的一节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杨宁一先生的指点,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93]《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第24-25页。
[94]关于《译书汇编》的影响,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2页有扼要的分析。
[95]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70页。
[96]《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6页。
[9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0页。
[9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3、95页。
[99]如《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年初)、《中国的现在与将来》(1897年3月1日)、《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下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87-106、172-173页。
[10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
[101]《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102]《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103]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第173页指出,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就多次提到君主“专制”,不确。引文出自郑观应著,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及第112页注释①。
[104]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8“民政”,第3页下-8页上、第14页下-16页上,卷4“法律”,第13页上-19页下,商绛雪斋书局1902年刻本。收入卷4的《孟德斯鸠学说》一文作者不详,似非梁启超。
[105]《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652-653、654页。
[106]《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影印本,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5.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276页。
[107]《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第342-343、349页。
[108]《国会与地方自治》,1907年5月《中国新报》第5期“论说四”,第87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09]《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社说”,商务印书馆1905年2月,第1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10]《民报》第1号,影印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111]《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社说”,1906年1月,第246页。
[112]《民报》第3号,影印本,第7-8页。
[113]《新民丛报》第4年第20号(原第92期),1907年5月,第30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14]《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第80-81页。
[115]《民报》第6号,影印本,第11-12页。
[116]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七,第77-83页;参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73-177页;董萍平:《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37-42页。
[117]《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第63-64页。
[118]《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9页。
[119]《中国新报》第1卷第1号,第1页。
[12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8页。
[1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90页。
[122]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123]转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124]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立宪政体”条(5.1009)、“法治国”条(8.268),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分见丙集第91页,辰集第27页。
[125]《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2年第17版,寅集,第94页。
[126]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12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3页。
[128]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7页。
[12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355页。
[130]钟毓龙:《新编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1920年第16版,引文见第57页。
[131]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1-62页。
[132]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60页;下册,1933年版,第116、118页。
[133]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134]徐则陵起草的《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第46课与第90课,收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135]《1929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四)“近世史”,收入《历史卷》,第40页。
[136]《1956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说明,初中一年级“完成了统一全国事业的秦始皇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收入《历史卷》,第137页。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秦、明与清代亦有类似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98、207、208、209、212页;此后《1963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1986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均有类似的内容与要求,收入《历史卷》,第275、277、278、342、393、400、401、402、403、455、463、464等页。
[137]此书原为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后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1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8页。
[139]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影印本,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1、35页。
[140]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影印本,第14页。
[14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1948年初版,1981年再版。
[142]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页。
[143]收入《政学私言》下卷,《钱宾四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3、133-135页。
[144]1945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第2页,后收入《政学私言》上卷,《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5-6页。
[145] 1945年5月《东方杂志》第41卷第10期,第2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42页。
[146]见《国史大纲》“引论”八,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6页。《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此外,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晚年则在《国史新论》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关于他的这一观点近来亦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见万昌华:《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117-118、119-120页。
[147]彭明、程啸:《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84页;佐藤慎一指出了四点原因,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1-242页,可参。
[148]关于正史的曲笔,清人赵翼等已做过不少分析。这里不妨以前人很少提起的《汉书》为例,再做一具体说明。班固为了维护汉朝的正统,不惜在记述王莽与新朝时加以“曲笔”。不仅将对王莽的记载归入“传”,且安排在全书的最后;就是具体的记述中也通过特定“笔法”加以贬斥,如对王莽所下诏书,《汉书·王莽传》书做“下书”而非“下诏”,见《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28、4130、4131、4154、4158、4159、4161、4174、4175、4178页等,只有两处用了“下诏”,见第4152、4164页,恐是没有改尽。据该传载群公奏言“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第4134页),田况上言云“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云云(第4172页),可知当时仍用“诏书”,说“下诏”。班固写作“下书”是为了将王莽贬入“闰位”,不承认其为皇帝,这自然是一种歪曲。此外,为了证明王莽无计可施,云“(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并举出若干事例,最后说“如此属不可胜记”(第4186页)。根据《论衡》以及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我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汉代人“好时日小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对此,班固并没有正面记述,而在这里却格外专门举出王莽好时日小数,一无一有,似乎衬托出王莽到了穷途末路,实际上,汉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了“时日小数”,并非走投无路才如此。班固如此记述是为了证明历史在向汉朝发展而有意安排的,也是一种曲笔。
[149]《新史学·论正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24页。
[150] H.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arlesScribner’s Sons. 1951). pp. 1-7,107.梁启超
[151]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 No.4. (Dec.1996), pp.106-107.
[152]关于这一问题,参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93、195页;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4、17-19页。两位强调的是19世纪末以来的变化,实际还应追溯到明清传教士时代。
[153]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第348页亦提到这一点。
[15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入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