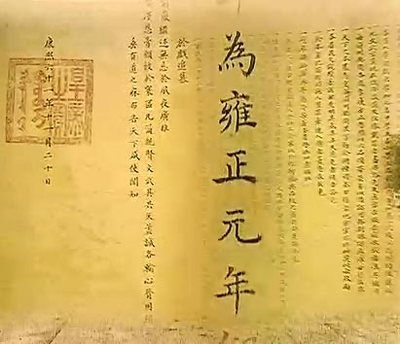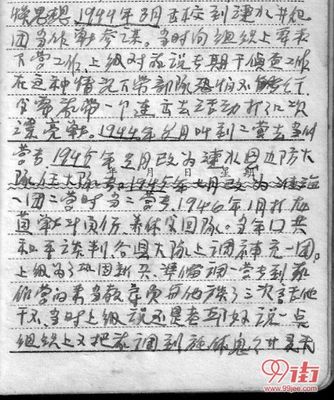<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1)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我的家乡在陕西省神木县乔岔滩乡桃柳沟村。乔岔滩乡建国前属于佳县,佳县也叫葭县。解放后,划归神木县。神木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东北端,黄河河套之南的长城脚下,北与内蒙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相望,是晋、陕、内蒙三省交界之要塞。据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棵,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松。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家乡人说,神木就是由神松的传说而来。自古以来,神木地区就是塞上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秦王过此点军;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路过神木,北宋范仲淹到这里巡边;杨家将镇守边关,在神木一带抗击契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从神木打出陕北……黄河、黄土养育出陕北人的粗犷和豪情,高亢悠扬的陕北民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家乡情。一神木家事我的祖籍原是在临近黄河边的葭县贝干村,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生活很困难。先祖张念功十几岁时,只身来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的桃柳沟村。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张氏子孙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氏家谱按:“念进应汝守天继振仁有世步如鸿贤良访正开元龙品阁高……”排列,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我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父亲的长子。在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皆因生活困苦从小夭折。这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7月18日),正是天气炎热的季节,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生下我,我全身沾满了泥土。村上老辈人说,这孩子沾了“地气”,命硬,长大必是个硬汉子。为了好养活,父母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地落”,学名按家谱排序叫张鸿毓。我的父亲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这些豪绅丈量到我家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佳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佳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佳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生了13个孩子,只活了五个。母亲勤劳善良,在别人有难处时,总是热心帮助。乡亲们都很亲近和敬重她。1936年,我回神府工作时,回家看望母亲,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当说到父亲时,她哭成了泪人。乡亲们讲述了父亲被“左”倾肃反杀害的情况,有的说,把那几个人抓来偿命,有的说杀了报仇。母亲停止了哭泣,对我说:你在外面,可不能像他们那样乱杀人啊!我对父亲的被杀很悲伤,但听了母亲的这番话,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对她说:我不会那样做的。这时,我发现母亲瘦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可是她那和善的面孔一点没有改变。1939年,我在绥德特委工作,后来到延安中央党校。生活安定后,我将母亲接到身边。她总是惦念着家乡的亲戚们,常常和我说:“你出来了,要想着那些受苦的孩子。你大伯家的老二被错杀了,他媳妇改嫁,带上了老二的女子,孩子在人家受苦,快接回来吧。”我和程帆结婚有了家庭后,先后将我的弟弟、大伯家堂兄的四个孩子都接到延安上学。母亲看着一个个孩子念书有出息,满心欢喜。因为人多,分了两处住,母亲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常常为战士们洗洗补补。以后母亲随我到东北,生活好了,程帆常给她做几件衣服。她舍不得穿,都给了老家来的亲戚。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却总是为别人的事情操心。他们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2)二求学革命高家堡小学父亲很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有本事的人,决意让我上学念书。1919年,我八岁时,在村里私塾念了两年的冬学。1922年2月,父亲让我和堂兄张鸿恩一起到离家三十多里的高家堡小学读书。高家堡是一座古城,城里住着很多有钱人。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只有我和鸿恩是乡下人。由于路远,我们在学校住宿,从家里带来粮食和咸菜,自己做饭。每到寒暑假,我们都回家,和大人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在高家堡小学读了三年书。1925年春,我转到佳县高级小学上学。校长叫张镜川,他很喜欢我这个农村孩子,给我起了个字“秀山”,取自“秀甲天下,光耀山川”中的两个字。1930年以后我就改名叫张秀山了。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佳县高级小学。这时,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到我们学校宣传革命,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我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如: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纪念会等,并开始阅读一些宣传革命的书报,课余时间还读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初步懂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道理。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县党部里多是由共产党员在做组织工作。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1927年春天,我和同学们集体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4月,同学们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乡下去做宣传工作。我们走了300多里路,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农民开会,宣传革命。1927年下半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局发生逆转,县党部里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工会、农会、学生会全被解散了,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到处抓人,一片恐怖气氛。我年少气盛,和一些胆子大的同学跑到街上,愤怒声讨蒋介石反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后来在学校无法呆了,就回到家中。这时我感到非常压抑和苦闷。榆林中学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榆林中学相承于明代的榆阳书院,已有几百年历史。1918年,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杜斌丞先生接任榆林中学校长。他倡导科学民主,提倡教育救国,在学校推行以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新式教育,反对旧文化和封建传统教育。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杜斌丞先后聘请了新文化运动干将、共产党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李子洲(陕西省委代理书记)、魏野畴等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气氛。榆林中学由此一改旧貌,成了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新式学校。在之后的岁月里,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革命战士,成为陕北革命进步文化的摇篮。在榆林中学,我感受到了这种新的气息,也产生出一种新的激情和力量。榆林中学的学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热情很高。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罪行,长时间激荡着社会各界,我们在县里多次开大会声讨蒋介石。后来,反动当局进行镇压,党组织因白色恐怖加剧转入地下活动。即使这样,1928年到1929年,榆林中学的党团组织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党在学生中仍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我在这个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我入校不久,学校几位党员教师向我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问题》等。这些书籍对我有着重大的启蒙作用,使我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对工人、市民、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城市里大批失业人员涌满街头,农民破产逃荒逃难。尤其令人憎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屠杀进步青年学生,更加激起我们的极大愤怒。1928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和几名同学一起去了太原,想报考北方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用枪杆子铲除黑暗。到了太原,北方军校的考试日期已过,没有办法,我们就报考了美术专科学校,等待时机再报考军校。我们在太原学习了半年,看到很多陕北来的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抓了起来,太原城里失业的人更多,连许多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工人、城市贫民家里吃不上饭,大人叫孩子哭的悲惨情景。而军阀、官僚,有钱人,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如此黑暗,不打倒这个社会,穷苦人民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冬天,我回到家,父亲知道我去太原的事,但他没有责怪我。加入共产党1929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榆林中学,插班继续学习。由于我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积极靠近党团组织,因此学校的党团员也主动地接近我。一到星期天,我常和党团员到城外,向农民宣传革命。这年的3月底,黄培中、李彦希两人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是在榆林城南门外金刚寺里举行的,和我一起入团的还有曹华山。党组织对我们考查得很严,主要是考查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入团仪式上,我向团组织表示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奋斗终身的决心。入团以后,我的革命热情更高了,革命决心更坚定了。不久我就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干事。1929年下半年,党组织开始组织学习党的六大决议文件。通过学习,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一些重大问题。1929年的秋天,经过党组织批准,我由共青团转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榆林中学,是党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半是由党员担任。我们在同学中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并带动许多同学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问题》等革命书籍。针对各县来的学生,我们在学校还分别组织了“同乡会”,党员利用“同乡会”宣传马列主义。我们组织的“佳县同乡会”还出了会刊。我在会刊上写文章,揭露贪官污吏和佳县的北霸天、大土豪贺德广。我把他的名字写成“货都光”,其意是说他压迫农民得来的钱财将来都要光。我们党在榆林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晚上,我常常和一些同学到街上贴传单,白天也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巧妙地放入米店仓子内的小米里,以此来宣传革命,扩大党的影响。同学们都很关心南方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室里,我们把《大公报》或其他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红军的消息,都用红笔框起来,以引起同学们阅读时注意。在学校里,党团员积极给校内的工友做宣传工作;星期天,组织学生去城里的工厂、作坊,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运动;到城外农村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农民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社会上开办平民学校,组织党团员给贫苦人家的孩子讲课,利用讲课传播革命道理。党组织还要求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我就在井岳秀的炮兵营里介绍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位叫张怀树的,1932年被敌人发现,杀害了;另一个是佳县籍的士兵屈子荣,后来参加了红军。党团员对组织分配的工作都很积极,每天或隔一天就要向小组长汇报工作。到了傍晚,在学校的操场上能经常看到两个人边走边谈,那实际上是党团员在向组织汇报工作。《我的八十五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青少年学生时代(3)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总是假惺惺地要人们在大会小会上必须诵读《总理遗嘱》,这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反感。我们党组织就根据群众情绪,把国民党党歌中所写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尊,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冠冕堂皇的话,改写成:“杀民主义,狗党所尊,以卖国民,以坏大同,军阀官僚,残害人民,矢勤矢勇,屠杀工农。工农联合,狗命送终……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恭读遗嘱,阿弥陀佛”,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他们的罪恶行径。传单散发出去后,教师和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引起大家的共鸣,产生很大影响。榆林中学一位数学教员叫谢子恒,平时从不关心国事,看到传单后,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说:“恭读遗嘱、阿弥陀佛”这句,我实在赞成。这时,榆林的整个政治斗争形势对我党很有利,在社会上已初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就连党外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开始同情我们党。1929年春,杜斌丞先生从外地返回榆林。他不住在井岳秀的公馆里,而住在榆林中学事务处办公室的小炕上。办公室的人在办公,他也不厌烦,他对榆林中学充满了感情。他给同学们作讲演,讲到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时,批判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荒谬说法。他说:“党外无党,实际上是党外有党。比如共产党就是一个。党内无派,实际上是派系很多。蒋、冯、阎、李各成派系,而且蒋系内还有很多派系。”杜斌丞先生的讲演,对教育青年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他的讲演也说明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遭反动当局通缉1929年11月7日,榆林中学的党组织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活动中,组织了五个飞行队,每队四人。我们这个队最果敢,趁着夜色,我们把革命标语贴满榆林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震动了整个榆林城,并很快传到了乡村,鼓舞了劳苦民众,使反动派坐立不安。反动派认定我是共产分子,以我在学校“佳县同学会”的会刊上,写出揭露佳县大地主、大土豪贺德广和其他贪官污吏罪行的文章为借口,佳县县长陈琯下令通缉我,堂兄张鸿恩、佳县同学崔继浩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1930年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正放寒假,我在家中帮助父母碾米。突然,三个衙役(警察)闯到院子里。他们什么也不说,先用铁链把我捆绑起来。然后,他们拿出县长陈琯通缉我的“红谕”,上面写到:“共产分子、张如德之子张鸿毓(我的原名)……”我怒斥衙役说:“走!现在就进城,去见你们县长,我犯了什么法!”衙役们都是些大烟鬼,走了两天路,来了当然要吃要喝,还要鞋脚钱。其中一个叫高喜的衙役说:“你们家请个人来,先把你保起来,我们明天再走。”我父亲就去请来村长张鸿元做保人。衙役把我身上的铁链解开,进屋吃喝去了。晚上,父亲对我说:“你犯的是共产党的案子,是大案子,可不得了,就是不死,一辈子也出不来。就是死,也得先死老子,哪有先死儿子的道理。你赶快逃跑吧,明天由我替你顶官司。”我不同意,说:“哪能让父亲受牵连,我自己顶着。”但是拗不过父亲。到了鸡叫头遍,父亲把我叫醒,硬是推着我从窑洞间的梯子爬到窑上,顺着后山的小路匆匆逃离了敌人魔爪。天亮后,衙役抓不到我,就把父亲和保人张鸿元抓往县里。父亲对衙役说,保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又给了衙役一些钱,保人便被放了。县长把我父亲关押了很长时间,老人受尽折磨,后经村人担保,花了很多银子,才放了回来。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很难过,这也是父亲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否则我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更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别。我逃出来后,又回到榆林中学。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