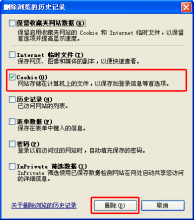杨友德在哨楼上演示自制土炮
(《山花》2010年第八期》)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为了反对强制拆迁,武汉东西湖农民杨友德自学“阿凡达”,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了个“炮楼”,用自制的火炮两次打退了拆迁队的“进攻”。
56岁的杨友德承包了25亩地,2029年到期。在这片田地里,杨友德开展多种经营——养鱼、养牛还种植棉花和瓜果。去年杨友德听说自己的25亩地被征用了,但是由于补偿没有谈妥,他拒绝搬出。后来拆迁方就多次放话出来,说要对他动手。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今年年初,杨友德将一辆手推翻斗车的前部铁皮拆掉,在翻斗里面放置了一箱礼花弹,准备对抗拆迁队。今年2月6日,30多人的拆迁队伍来到地头准备强征。杨友德就点燃了礼花弹,拆迁队员因躲在铲车后面,毫发无损,等礼炮放完后,他们冲出来把杨友德打了一顿。为了汲取教训,杨在亲友的帮助下做了一座“炮楼”,并改装了“武器”。5月25日下午,又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拆迁队,戴着钢盔拿着盾牌,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掩护下,再次来到杨友德的承包地里。杨发现后立即爬上炮楼,朝拆迁队放了几炮,他们便被吓住了,没敢继续向前推进。
杨友德的住所
杨友德此举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关注,有人认为杨“炮击”拆迁队是一种合法的维权行为,与那些以自焚或自杀抵制强制拆迁的“消极抵抗”相比,属于“积极抵抗”。也有人认为杨自制土炮,武力抗“法”,已经超出了“合法抗议”的范畴,是一种不择不扣的“暴民”行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
以笔者之见,杨友德的“炮击事件”,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拆迁队所倚仗的地方规章制度或曰“土政策”是否代表了国家法律?如果“土政策”同国家法律乃至宪法相冲突时,作为公民的个人是否有权反抗“土政策”,从而在捍卫个体权利的同时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性?二是如果承认这种反抗的正当性,那么,公民的“抵抗权”是否因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美国电影《哈利之战》。
哈里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国民。电影的开篇,是哈里折叠弃之墙角的一面国旗。这说明哈里是一个认同美利坚民族的爱国的公民。当税务局不合理地向爱好收藏军品的姑妈征税甚至征讨房子的时候,哈里则站起来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从法律角度讲,税务局,作为地方职能机构,它的规章制度,并不具有法律效能。但是,在权力的操纵下,税务部门却将老太太给逼死了。哈里这个时候向税务局表达其抵抗,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影片中,哈里开着装甲车(老太太的收藏品)找税务局讨公道,还闯进电视大楼里发表了演讲,随后哈里就被军警围在老太太的仓库里。哈里于是开着装甲车奋起反击。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在媒体的介入之下,哈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哈利之战》剧照
这部讲述“一个人对国家的战争”的电影,在中国观众看来也许有些荒诞不经,但它揭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即相对于国家权威,公民抵抗权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它彰显的与其说是美国的“宪政精神”,还不如说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民主权利。在现代国家,或许只有宪法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其他所有法律法规制度,都必须站在公民权利的目光中,接受合不合法的审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并不总是合理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允许公民对权威说“不”(当然是在维护公民权利的意义上)。如果一个法律不允许人说“不”,而只强调服从服从再服从,那这个法律只能是“恶法”——毕竟,法,也是人制定出来的——为此,美国作家和思想家梭罗写出了他的政治学名篇《论公民的不服从》,来论证公民的“抵抗权”。
梭罗说——
“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愿意服从的权威──因爲我乐于服从那些比我渊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我甚至乐于服从那些不是那麽渊博,也不是那麽能干的人──这种权威也还是不纯正的权威: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産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民主,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就是政府进步的尽头了吗?不可能进一步承认和组织人的权利了吗?除非国家承认个人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于个人的权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乐于想象国家的最终形武,它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一样。如果有人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职责,但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不爲其所容纳的话,它就寝食不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并且听其尽快果熟蒂落的话,那麽它就爲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国家铺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国家。”
梭罗以诗意而充满哲理的文字,阐述了国家权威和个人权利互相依存的关系以及公民“服从”和“不服从”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梭罗还身体力行,为了反抗州政府的不合理税赋,跑到远离大城市的瓦尔登湖隐居了五年,以此表明他关于“不服从”的政治主张。当然,跟中国公民杨友德和美国公民哈里相比,梭罗的行为是一种“消极反抗”。这与梭罗遵从的非暴力主义理念有关。所谓“非暴力主义”,源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这并不能成为取消“暴力不服从”的生成基础。再以美国为例,在任何国家,国旗都是最重要的民族象征,而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燃烧美国国旗不能被宣布为非法:因为它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公民表达抵抗权的形式。抵抗权,也不只是简单概念上的反抗和暴力。它有多种抵抗的形式,从服从,到不服从,一直到暴力革命;迁徙、不执行、抵抗,都是抵抗权的表达方式。而暴力革命乃是公民对国家抵抗的最高形式。当一个国家堕落为黑社会的扩大版时,它对社会成员的掠夺与压迫就总有被暴力革命所反抗的那一天。
就此而言,杨友德以自制土炮抵抗强制拆迁案的“不服从”行为,传达出的是国家法律被“土政策”僭越和践踏之后,社会成员试图通过与“暴力拆迁”对等的“武力抵抗”,寻求国家权威和宪法支持的无奈之举。正如杨友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在他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都能全文背下来。这无疑表明,杨友德具有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知识素养,其行为显然可以看做是他自觉维护公民权利的理智之举。所以,当记者问他怕不怕有人说他是“暴民”时,才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同意。一个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产生的环境。我不是强买强卖,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就“拆迁”问题有过一段著名的话:“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很显然,毛泽东是赞成农民对不合理的“土政策”采取抵抗行动的。而对于今日之“杨友德事件”,人们与其在他是不是“暴民”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倒不如思考一下:现行法律工具为何对那些肆无忌惮地侵犯和剥夺公民权利的“土政策”表现得如此软弱乃至于熟视无睹?当违法以“官权”的面目出现时,很少受到追究,而当个人为了“维权”触动某些“土政策”时,“官权”则可以冠冕堂皇地声讨和采取一切手段去“平息”。这种官权与民权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与现代民主和法理精神相悖,而且是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理念的侵害。
杨友德曾反复表示,他相信法律,相信国家,“瞎搞”的只是“下面的人”。所谓“下面”,其实就是那些代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部门。用梭罗的话说,就是“政府是人民选择来行使他们意志的形式,在人民还来不及通过它来运作之前,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滥用或误用”。
面对这种国家权力被“滥用或误用”的现象,明智的办法不是给用土炮“武力维权”的杨友德戴上一顶“暴民”帽子了事,而是应该加快建设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疏通管道,并通过重建宪法的权威,遏制官权和资本的无休止蔓延,以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和西方宪政框架下的“公民权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兼容共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走上一条消除历史积怨,充满和谐与和解精神,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光明大道。
这,或许就是“杨友德事件”带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2010年6月9日草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