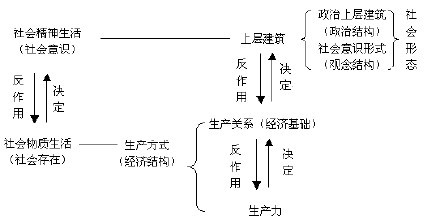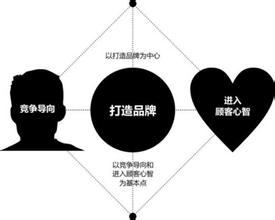论小说与电影的改编
一
1895年,在法国巴黎迦夫埃昏暗的地下室,卢米艾尔兄弟摄制并公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十年之后中国上演了自己摄制的无声影片《定军山》。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获得了飞速发展,在建国前已经比较成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电影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电影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综合艺术从来没有和文学分开,电影的拍摄必须要有文学剧本作为底本,电影文学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也只有在声、光、色、电的影像中才能全方位地实现其艺术价值。
茂莱通过对近二十个西方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个案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位小说家一旦成名,他能从电影买卖中获得的钱数简直是无限的。今天的小说家所享受的合同待遇会使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斯坦贝克和海明威歆羡不已的。我们很难举出哪一个稍有才能的当代作家没有向电影界卖过作品或没有写过电影剧本的。”[1]写电影文学剧本的剧作家有些是专门的剧作家,有些是优秀的作家,写电影文学剧本是20世纪作家文学创作的又一种重要方式。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发展历程中,洪深、欧阳予倩、田汉、夏衍、阳翰笙、郑伯奇、阿英、沈西芬、袁牧之、许幸之、于伶、宋之的、柯灵、凌鹤、应云卫、张骏祥、司徒慧敏、叶以群、陈大悲、陈白尘、陈残云、吴祖光、姚雪垠、张爱玲、周纲鸣、黄谷柳、端木蕻良、曹禺等知名作家都参与过电影文学的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或者是作家直接创作,或者是由一些小说作品改编而来,改编是电影文学剧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方式。
L·西格尔认为:“改编是影视业的命根子”,“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影片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改编的”,“在任何一年里,最受注意的电影都是改编的”。[2]电影和小说都是叙事艺术,小说的叙事性决定了在诸多文学样式中它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美国电影研究家乔治·布鲁斯东在1957年就说过:“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是最有希望获得金像奖”、“在盈利最多的十部影片中,竟有五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3]这五部影片是《乱世佳人》、《走向永生》、《太阳浴血记》、《长袍》、《你往何处去》。其中《乱世佳人》被认为是最佳有声片和最佳“永不过时的影片”。据资料统计,自电影问世以来,70%以上的电影都是改编自文学原著,其中主要是改编自小说。欧美每年平均拍摄一千部电影,一千部电影的故事来源主要是古典小说,经典小说,以及一些有创造性的通俗小说,小说实际上是电影的题库。古典小说如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此情可问天》,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剑客》、玛格丽特的《情人》、杰克·伦敦的《海狼》。通俗小说拍成电影并走销的有:《与狼共舞》、《侏罗纪公园》、《绝命追杀令》、《阿甘正传》、《生死时速》、《亡命天涯》、《麦迪逊郡桥》,都创造了空前的票房记录。从五十年代开始,仅仅从契诃夫作品中改编的影片就有—百多部,这位古典作家的小说、戏剧乃至散文,都被搬上了银幕。雨果的《悲惨世界》被世界各国改编多达十几次。

好莱坞作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代表,在一个多世纪中从文学中选取电影素材的例子不胜枚举,差不多每一部电影精品都是以文学作为先导的:如《乱世佳人》、《绿野仙踪》、《呼啸山庄》、《洛丽塔》、《欲望号街车》、《恋爱中的女人》、《印度之行》、《普通人》、《猎录人》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评论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也都曾涉足电影创作或电影评论。一些文学经典名著也陆续被改编成电影,80年代将名著搬上银幕的有老舍的《骆驼祥子》(主演:张丰毅、斯琴高娃)、曹禺的《雷雨》(主演:孙道临、秦怡、马晓伟、张瑜)、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导演:吴贻弓;主演:张丰毅)、鲁迅的《阿Q正传》(导演:岑范;主演:严顺开)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祝福》是第一个将文学名著改编成功的范例。《祝福》之后,名作改编成电影的有:《茶馆》、《伤逝》、《药》、《寒夜》、《边城》、《青春之歌》、《万水干山》、《红旗谱》、《早春二月》、《林海雪原》、《暴风骤雨》、《李双双》、《洪湖赤卫队》、《子夜》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的三部影片,竟然都是改编的作品。
新时期电影中的优秀之作相当一部分是由小说改编成的。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红衣少女》、《神圣的使命》、《内当家》、《枫》、《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十六号病房》、《飘逝的花头巾》、《青春祭》、《女大学生宿舍》、《青春万岁》、《野山》、《老井》、《祸起萧墙》、《花园街五号》、《神鞭》、《哦,香雪》、《找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轮回》、《炮打双灯》、《红粉》……等等。
电影大师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谢飞的《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花影》,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都是得益于小说创作,对此张艺谋说得很明白:“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要否定电影编剧们的功劳,电影编剧们自己创作的剧本拍出好电影的也不少,但那成就不算太高。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4]
当代作家中,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的知名作家有:莫言(《红高粱》、《白棉花》、《幸福时光》)、王朔(《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撒把》、《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大鸿米店》),池莉(《家事》)、铁凝(《红衣少女》,《村路带我回家》《童年故事》)王蒙(《青春万岁》)、刘恒(《菊豆》、《没事偷着乐》)等。这些改编大多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一个时段的热门话题。《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改编造就了一代大导演张艺谋。
二
宝琳·凯尔说:“从乔伊斯开始,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受过电影的影响……”[5]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但在我们通常的文学研究中,往往不缺乏对一些影片的独立评论,也不乏对一些小说的研究文字,问题是,电影叙事和小说叙事毕竟是不同的媒介叙事方式,在由小说向电影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那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研究小说史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小说在传播途径中发生的变异,变异背后的文化导向是什么,电影对小说的介入有没有影响小说写作,是怎样影响的?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在题材选取、审美情趣、叙述视角等方面都深受电影艺术的影响。李今在《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6]一文中对此做过精彩的论述。实际上不仅新感觉派,就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在不同层面上受到电影的影响。相对来说人们更习惯将电影看作是一种通俗文化来理解,往往忽视了其中的现代性和文学性因素。在20世纪文学史上,电影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几乎是一片空白。
电影和小说一样属于面向大众的一种文学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小说不是正统文学,小说从说唱文学中脱胎而出,它的通俗性、娱乐性、叙事性与电影是极为相似的。小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门主要的文学样式,但自20世纪以来小说开始受到影像传媒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诗歌历来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但现代社会已经很少有人写格律诗,“五四”以来的新诗文化运动也丢掉了古典诗歌的语言系统和结构规范,当代诗歌在朦胧诗之后一直处于尴尬徘徊的境地。当代人可能不读诗,但可能不会不读小说;可能不读小说,但可能不会不看电影、电视。电影和小说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屏,影视对小说的改编成了小说传播的又一种形式。对于当代小说来说,影视对小说的改编是有选择性的,中国大陆21世纪初每年的电影产量是100部左右,其中有一些是根据独立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的,每年的长篇小说总数是一千多部,只有部分作家部分小说才有被电影导演“青睐”的可能。其中描写情爱生活的小说是电影改编的一个重要部分。电影杰作《乱世佳人》的成功就是一个明证。1938年12月15日,《乱世佳人》在亚特兰大市上映时,全市政府机关和学校放假一天。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上,《乱世佳人》共获得八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彩色片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乱世佳人》的改编为本来畅销的小说创造了更大的观众群,带来了巨额的票房收入,成为20世纪最卖座的电影。1977—1997年中国类型电影中产量最高的是刑侦破案(包括缉毒、公安)的影片,它已达到229部,平均每年10多部;其次是与刑侦类型相接近的动作片、然后是爱情片和武侠片,它们的总产量都在150部左右。20世纪末,有两部耗资巨大的影片,将爱情故事和灾乱相结合,也赢得了巨额的票房,这就是《珍珠港》和《泰坦尼克号》。就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影片来看,也大多是与“情事”相关的。新时期从小说改编的情爱电影更是不可胜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野山》、《桃花满天红》、《阳光灿烂的日子》、《妻妾成群》、《红高粱》、《菊豆》、《米》、《炮打双灯》、《美穴地》、《与往事干杯》、《有话好好说》、《生活秀》、《周渔的火车》、《天上的恋人》。一些网络爱情小说也被改编成电影,如《我的野蛮女友》、《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也都有很好的票房。
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媒体,这两种媒体对观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西格尔认为:“一本畅销书的读者可达百万,如果是最畅销的书,则可达四、五百万。一出成功的百老汇舞台剧可有一百至八百万观众,但一部电影如果只有五百万观众,则被视为失败之作。如果一部电视系列剧只有一千万观众,它就要被停播。电影和电视剧必须赢得巨量观众才能赢利。小说的读者和舞台剧的观众档次较高,所以它们可以面向比较高雅的市场。它们可以重在主题思想,可以写小圈子里的问题或采用抽象的风格。但是如要改编成电影,其内容必须符合大众的口味。”[7]比之小说电影更时尚、更通俗、更大众化,电影更要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接受能力。电影对情爱的叙述也更多地表现出时代的大众心理色彩,触及到当代人情感困惑的敏感神经。因此,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必然也会遵循这样一些法则:只有能引起观众强烈反应,契合当代人情爱追求,表达当代人情爱心理,探索当代人的情感困惑,能引起人们对情爱重新认识,让人玩味爱情的乐趣,领悟爱情的真谛,给人以想象和快乐,总之,对情爱的叙事既有探索性、趣味性又能满足大众的情爱心理期待的小说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
三
电影和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想象与诗意的文字符号系统,电影是直观的声像符号,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相互翻译必然会碰上一系列的问题。电影的叙事传统严格来说只在二战之后才开始形成。毫无疑问,电影也是一门艺术,电影借助声、光、色、影、形的手段比小说更富有形象感,在表现场面的真切,人物行动的逼真,甚至对人物心理的探索、人物情绪的渲染,电影都是有其独到之处。在一个具体的情爱故事中,电影的讲述为了在一定的时间内(电影的时间限制比较大)将一个故事讲完(也有不讲故事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一个整体的“意义”),必然会对改编的小说作出较大的改动,除了这种形式上的要求和媒介的不同之外,大众的社会接受心理,改编者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内容的变化。
杰·瓦格纳在《小说与电影》一书中,论及美国电影改编的三种流行方式:“第一种是‘移植式’,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的改动”。第二种是“注释式”,“影片对原作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并加以重新结构”,它“对作品某些方面有所变动”,甚至转移作品重点。第三种是“近似式”:“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8]在实际地分析一部作品的改编时,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改编呢?在小说被电影改编的时候,电影表达出了小说中的那些原味和真义吗?其中过滤掉的又是什么,突出放大的又是什么?有时是不同的编剧对小说进行改编,有时是小说的作者亲自操刀充当编剧,在小说纷纷被影视化的时候,作家的写作是否受到影像化的冲击呢?
很明显,一部同名的电影和一部小说,在文学的意义上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幅历史画和它所描绘的历史事件相比,是一件不同的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电影也是一件不同的东西。说某部影片比某本小说好或者坏,这就等于说瑞特的约翰生腊厂大楼比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好或者坏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归根到底各自都是独立的,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本性。”[9]《教父》、《乱世佳人》的原著在文学史上地位都不那么高,而他们在电影方面的地位就很高。而《战争与和平》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拍成电影却不是一流的电影。电影的巨大观众群体带来的是巨额的经济回报,小说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知名度和影响力都会发生变化,电影的改编还会直接推动小说发行量的上升。根据乔治·布鲁斯东的分析:“《大卫·科柏菲尔》在克利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公共图书馆不得不添购了132册;《大地》的首映使小说销数突然提高到每周3000册;《呼啸山庄》拍成电影后,小说销数超过了它出版以来92年内的销数。杰里·华德用更精确的数字证实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呼啸山庄》公映后,小说的普及本售出了70万册;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达到33万余册;《桃源艳迹》售出了140万册。1956年,在映出《莫比·狄克》和《战争与和平》的同时配合出售原著,也是这种趋势的继续。”[10]“查尔斯·韦布的《毕业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影片问世之前,它只售出精装本500册和平装本不到20万册;改编影片大获成功后,平装本的销售量突破了150万册。当1962年拍摄的影片《杀死知更鸟》于1968年在电视上播出时,平装本的出版商立即又印制15万册以满足进一步的需要。”[11]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由于著名演员巩俐加盟《周渔的火车》,作家出版社将以《周渔的火车》的书名合集出版了北村不同时期的8部优秀中短篇小说,首印3万册就被一抢而空,而其前身《周渔的喊叫》当年连保底的3千册都没卖掉。北京电影学院苏牧教授认为我国娱乐已经进入视听时代,影视成为推广小说等文学艺术的媒介。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对于作家是名利双收的事。对于当代的知名作家来说,“触电”几乎成了普遍现象。
但当代作家大多对影视保持一种冷峻的高蹈姿态。在文学圈内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小说是高雅的艺术,而电影是俗的娱乐快餐。“电影诞生之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低下的娱乐形式。直到1925年,洪深要参加搞电影,人们还劝他‘不要自堕人格’;有人甚至说他‘拿他的艺术卖淫了’。”[12]刘恒说:“写电影剧本在文体上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让我放弃的话,别的都可以,最后只剩下小说。”[13]苏童说:“在中国,靠写小说当百万富翁,一般来说是比较可笑的。真要逼急了,也没办法,只好触电。《妻妾成群》拍成电影时,版权费只给了5000元。后来《红粉》多一些了,《米》就更多了。目前我的生活状态,养活自己还可以。”“我一般不写剧本。影视剧这玩艺儿,也就是客串客串,写多了会把手写坏。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在文学圈内的知名度和他的社会知名度不同。身为作家,还是要坚守纯文学阵地,准确看待自己,看准这种成名的成分的复杂性。”[14]相对来说,像王朔那样对影视有好感的作家并不多,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个东西需要改变,就是传达思想和情感不只是写字的方式、文字的形式,还有别的形式也很有效,比如视听的形式。好的电影并不比好的小说差,而坏的小说可能比坏的电影更没法看。在这里,好与不好是重要的,形式是什么并不要紧。我觉得,用发展的眼光看,文字的作用恐怕会越来越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影视就是目前时代的最强音,对于这个‘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去掌握?”[15]
这些作家对电影的鄙夷姿态的出发点就是将影视看作是通俗的大众的“低级”艺术,而将小说看作是高雅的、探索性的“高级”艺术。这种偏见和文学史上诗歌和小说之间地位的关系有些类似,自19世纪末梁启超大力提倡小说以抬高其文学地位以来,小说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体形式。在以“五四”的现代性诉求为内驱力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小说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品格。小说成了文学百花园中的主流,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小说在20世纪是分层的,电影也是分层的。“要有原创的、真切的生活体验,有对人生、文化艺术独特的真知灼见,有艺术家独特的个性,这是文化艺术电影的要求。‘主旋律’电影不一定要求这个,商业片更不要求这个。商业片应该表现社会公认的主题,如爱情、正义压倒邪恶、大团圆,才会赢得最大的市场。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要加入你个人独特的超前的见解,那么这个商业片肯定是不会成功的。”[16]这种分层与当代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大众文学(民间话语)、精英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主流文学(国家权力话语)是相似的,作家们对电影的偏见和文学史上对通俗作家的看法是相似的,这里的盲视和偏见影响了我们对影视文学的研究,导致了一个重要领域的忽视。很多作家将影视看作是时尚的流行文化,而把小说看作是艺术品,忽视了电影也有商业片和艺术片、主旋律之分。在爱情片中,电影也有层次的差别。电影中的爱情叙事有时可能成为流行时尚的注解,有时也会探讨爱情的深层问题。《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安巴》等“新浪潮”电影,在“心理银幕化”美学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使电影走上了现代艺术之路。电影艺术的哲理化审美倾向在60年代形成高潮,尤其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写实和写意都是电影哲理化的表现方式。谢晋说一部影片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这就是说电影仍然有灵魂的,是像小说一样写人类情爱的困惑,可以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厚度。但这不等于说小说能做到的电影都可以做到,电影无论怎么复杂,也不可能超过小说,无论在写意、写心理上借助声音和视觉形象都不可能有语言直入人心的酣畅明了。由于电影的时间限制,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用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必然要过滤删减小说的旁根错节和枝枝蔓蔓,在复杂性、散漫性、模糊性、语言质感上电影肯定比不过小说。小说的读者可以断断续续地读,长篇小说必须断断续续地读,还可以反反复复地回视回味,但电影一般会一气看完,容不得回视,虽然现在的家庭影院可以让影碟回放,但毕竟电影在单位时间内必须完成故事的叙述,叙事必须简洁明了,人物的关系不能过于复杂,心理刻画不能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花数千字来描写一个人某个时刻的心情,也不可能像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对日常生活的琐事絮絮叨叨。捷克作家昆德拉刻意要创作一部不能改编的小说,存在主义作家安德尔·加谬的《局外人》、《堕落》、《瘟疫》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很难搬上银幕。如同上文所言,在电影的改编中必然要失掉小说的一些丰富性,但也不等于说电影就比小说要逊色。
(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美]茂莱(Murray·E):《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2][美]L·西格尔:《影视艺术改编教程》,苏汶译,《世界文学》1996年第1期。
[3][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4]李尔葳:《张艺谋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美]茂莱(Murray·E):《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6]李今:《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7][美]L·西格尔:《影视艺术改编教程》,苏汶译,《世界文学》1996年第1期。
[8][美]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式》,见《电影改编理论问题》,陈犀禾选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9][美]乔治·布鲁斯东:《小说的界限和电影的界限》,见《电影改编理论问题》,陈犀禾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10][美]乔治·布鲁斯东:《小说的界限和电影的界限》,见《电影改编理论问题》,陈犀禾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
[11][美]茂莱(Murray·E):《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12]钟大丰:《论影戏》,《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3]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见《文学的力量》,张英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4]张宗刚、苏童:《苏童:从天马行空到朴实无华》,《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12日。
[15]白烨、王朔:《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
[16]谢飞:《对年轻导演们的三点看法》,《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