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22:47:25分享人:和我恋爱吧来源:互联网6
|
|
| 华北地区素来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华北在东北沦陷后,立时成了中国国防第一线,亦成了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必经之地。华北一旦失守,内地将失去屏障,日军就可随意进出。同时,华北地区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战略价值。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一方面压迫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平津和河北,削弱国民党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华北五省广大地区制造一种特殊的政权,这个政权表面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实际上中央政府在这个政权内既无权力,也无实力,而完全受制于日本。其实质是,日本企图通过不断挑起事端,“分离”中国,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实际控制了华北,为下一步扩大侵略打下基础,又避免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这次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必然性。它实际上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继续“实践”,也是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在实际中推行所造成的恶果。这次事变的发生不仅是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害。它成为一种重要的外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内部政局的演变。统治阶级从以“攘外必先安内”、“忍辱求全”为政策主导、地方实力派割据分裂的状况,发展为首次表明对日强硬态度,欲整合全国抗日之意志和力量,以挽民族危局,并开始打压或惩处亲日派。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索基础上,以及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与张学良等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接触中,逐渐清晰了自己的抗日政策主张,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力量从华北的逐渐退出,积极承担起发动和领导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华北是抗日斗争的前线,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进步力量的重要基地。再者,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兴盛起来,爱国民主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促进南京国民政府进入宪政时期和合作性政党政治形态的重要推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全民族抗战作了重要的准备。
一、日本以“亲善”为名,威逼利诱,拉拢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分化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力量。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67届议会发表演说,希望中国能早日“觉醒”,与日本“亲善”,跟日本的外交走。2月20日,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作中日关系的报告,称:“读了这次广田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是大致吻合。……我现在坦白的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的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妨害之言论行动等,一天一天地消除,庶几……中日提携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与此同时,派出王宠惠跑到东京去与日当局交换“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见书。5月中旬,将日本公使升格为大使,以表示“调整邦交”的诚意。但是,汪精卫等人如此热情地与日“亲善”,并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
1935年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中国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冀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塘沽协定》,并以天津日租界《振声报》社会白逾桓和《国权报》社会胡恩溥两个汉奸被暗杀为理由,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并扬言,若不接受这些要求,日军将越过长城,进入平津地区及非武装地带。面对日军挑衅,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形成了何应钦、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议,即习惯上所谓的《何梅协定》。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6月5日,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张北地方挑起事端,要挟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随即关东军电令在北平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主持与中国交涉。由于宋哲元不久被免去察省主席一职,由秦德纯代理。故土肥原贤二的交涉改与秦德纯进行。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与土肥原贤二签订协定,史称《秦土协定》。日本侵略者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平、津、冀,开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达真正控制华北的目的。
1935年9月24日,日本新任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天津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全面实现“华北自治”要求。10月4日,日本内阁召开三相会议,通过了外、海、陆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和《鼓励华北自主案》。在《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中,制定了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广田三原则”,迫使中国承认并实行。《鼓励华北自主案》则主张策动华北自主运动。这两项议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10月中旬,土肥原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之命,潜入平津,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同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
土肥原对华北五省军政实权人物商震、韩复榘、宋哲元等软硬兼施,鼓动他们脱离南京政府,建立华北联合“自治”政权。11月6日,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建立所谓“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并拟出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日本为迫使宋哲元就范,限令宋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行使武力。同时,日军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派海军舰只开往大沽、青岛,关东军飞机连日在平津上空盘旋。

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之下,一方面致电南京,以此试探蒋介石对华北“自治”的态度。另一方面对日本的要求搪塞敷衍,以拖延应付。蒋介石于11月20日复电宋哲元,指出宋哲元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同日,蒋介石在于日本大使有吉明会谈时,特别表示,反对日本在华北的分裂活动。日本未能迫使宋哲元在11月20日宣布“自治”。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放弃其分裂计划,除继续对宋哲元施加压力外,日本于11月25日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宣布冀东22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宋哲元急电南京请示对策。26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六项决议:1.撤销北平军分会;2. 华北政务收归中央军事委员会处理;3.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4.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5.将“独立”区专员公署撤销;6.明令通缉汉奸殷汝耕。日本方面对于南京的决议极为反感。日本内阁训令广田外相对华交涉,逼迫南京承认华北伪政权,反对何应钦北上。日本浪人在天津闹事,要求保护殷汝耕。加之在北平、天津迅速兴起的抗日救亡浪潮,使得宋哲元无法应付。12月2日,何应钦到达北平,宋哲元向何应钦汇报了华北局势并明确表示:绝对听命于中央,不向日本人屈服,并说明他与日本人之间并无任何秘密协定。但对南京政府削弱其权力的做法极为不满。对于何应钦坐镇华北,日本大使有吉明在会见南京政府新任外长张群时,明确指出:日方认为何应钦北上是中日关系之“倒退”,而非“进步”,并暗示,如果何应钦不离去,华北问题很难解决,只有非蒋嫡系的宋哲元才是日方愿意合作的对象。为挽回华北危局,南京政府批准于12月11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负责华北政务,辖区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后由于“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又推迟到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中有王克敏、王揖唐等亲日派人物,适应了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是一个既同南京政府有名义上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是日本与蒋介石、宋哲元三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在日本看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二、华北事变促使南京国民政府转变政策,进一步整合了统治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士气。
华北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略野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偌大的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亲日派在日本“亲善”政策的诱骗下,秉承“忍辱求全”的外交策略,断送的却是中国越来越多的领土治权。华北事变导致了中国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在抗日还是妥协、内战等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已引起极大矛盾和分化。因而,是选择团结抗日,还是仍旧追随蒋介石继续进行剿共内战,南京国民政府各地方实力派,包括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亦必须要作出自己的决择。救亡运动的冲击,使得张学良、杨虎城更进一步认识到,此时再不抗日将会失去一切:“日本人步步进入,自己已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张)。”“抗日,国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杨)。”因而他们选择的结果就是停内战抗日本,他们检讨自己原有的主张和行动的结果就是抛弃追随蒋介石从事内战剿共的“安内攘外”政策而联合红军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当蒋介石仍旧逼迫他们剿共内战时,他们当然就要有所表示,“促使他反省”。所以,华北事变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牵动世界至为重大”,也是“近种西安事变之因”。在华北事变和以华北事变为动因所引发的西安事变的促动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从其先前“攘外必先安内”、重在对内“剿共”的主导政策,转变为整合全国抗日之意志和力量,逐渐对日态度强硬,并重新分化和整合统治力量,打压或惩处亲日派,以挽救民族危局。
华北事变中,蒋介石逐渐意识到,“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销军分会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于是,蒋介石为使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整合全国力量以抗日救国的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蒋介石亲自邀请日本想拉拢作为“反政府势力”的冯玉祥、阎锡山参加会议,“尤使大会精神粹厉奋发”,“显示国内趋于团结”。1935年10月23日,蒋介石还亲自飞抵太原,邀请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大会,阎锡山“面允入京,参加大会,并表示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举为稳定华北局势的重要前提。
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案》、《对于党务报告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等。于右任在致会议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全会“中央执监各委员除远在海外及少数直接指挥剿匪之官长外,几乎是全体到会参加,可算是第四届中央的第一次盛会”,充分表现了“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异常圆满”。他强调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进一步增强团结,“集中国力和充实民力”,“来挽救环境的艰难”。冯玉祥也认为“六中全会……一切办法均改为少长有序,整齐严肃了,不似以前之乱七八糟”。此次全会中,国民党第一次表明了对日本侵略比较强硬的态度,标志着国民党已从一贯妥协退让的立场,开始向抗日方面的转变。
继四届六中全会后,在“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集中全党意志”,“发扬革命精神”等口号号召下,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人数最多的一届。“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安慰;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中国共产党的巴黎《救国时报》的评论也指出:“国民党各派的首领纷集南京,差不多为蒋介石当权以后少见的现象。”“久若国民党各派割据内讧祸国殃民政策的全国人民,也多少为之耳目一新。”
国民党五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有利于抗战的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检查过去之工作,深觉吾人此日若不舍弃个人之一切,贡献所有之能力,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则革命大业将有中断之危,而民族前途有不可想象之惧。”为此,提出了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10条措施。尽管五全大会在有的决议中仍诬称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要求继续肃清陕北红军,但由于华北局势日益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国民党内部反日倾向的增长,以及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手,共产党和红军已不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已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博古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但是,也指出:“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
在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危急关头,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平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奔腾向前,席卷全国。
在整合全国抗日救国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亲日派卖国行径的挞伐。1935年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指责汪派对日所持“忍辱求全”的外交政策,实则妥协无度,“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于右任大骂汪精卫汉奸卖国贼,孙科更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被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6人媚日卖国行径提出弹劾,矛头仍然指向汪精卫。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礼成后,中委齐集阶前合影后转身退上后阶。正在此时,晨光通讯社青年记者孙凤鸣因痛恨汪精卫亲日倾向,挤入人群朝他连开三枪。汪立即倒地,后经抢救才脱险。
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这次事变的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同时,也表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得人心。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华北事变后,日本又积极实施其侵占绥远图谋。日军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7月至 12月,傅作义领导晋绥军队在绥远省(今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抗击日伪军进攻的战役,收复了百灵庙等战略要点,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绥远抗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36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向傅作义发贺电称:“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盛赞傅作义发起的绥远抗战时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索基础上,以及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与张学良等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接触中,逐渐清晰了自己的抗日政策主张。
在国际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的形式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935年8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比“八一宣言”更进一步,对华北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发展、阶级关系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问题都作了分析和阐述。11月28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1934年12月27日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的致国民党公开信,8月25日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决议”指出:“自阿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斗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从组织上的最后完成。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中共政策的转变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促就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救亡抗日运动和之前的救亡运动具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它的最大特点是参加运动的阶层广泛,斗争深入,并逐步走向有组织的斗争阶段。具有这样一些明显特点的运动高潮,使得“抗日情绪之鼓荡,此为最遍。”运动还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已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不但在外交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整个国策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要求国民党“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动员全部的力量去对付敌人。”放弃对日妥协政策,“速即抗拒日本”,“否则理应引退(指蒋汪),以谢国人。”因而,这场运动必然对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产生极大的震动。它产生的客观结果就是要求各阶级各阶层在这场浪潮的汹涌中,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亡国巨祸中,必须要检讨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同时也必须要进一步去认识其它派别的主张和行动,抗日者救中国得民心,妥协者、内战者亡中国失民心。应该说这场运动是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也是对“安内攘外”政策的一次反运动。
四、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整合了中国各种抗日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建立,成为促进南京国民政府进入宪政时期和合作性政党政治形态的重要推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全民族抗战作了重要的准备。
政党政治有三种:一是竞争性的,二是独裁性的,三是合作性的。民国初年首先选择和实验的是类于两党制、多党制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而独裁性的政党政治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党政治,始于大革命后期蒋介石的背叛,将国民党逐步演化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了一党专政即独裁性的政党政治。在“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体制下,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方针,并密令取缔一切进步的群众团体,还特别加强特务统治、保甲制度、党化教育、新闻检查等,禁锢自由和民主。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由追随蒋介石转为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持中立态度,并且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独裁大为不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关内的扩张和国民党继续妥协所造成的新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的反蒋斗争逐步走向公开化,先后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民权保障同盟和上海其他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收复失地、保障民众权利等。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70余人,选举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会。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地抗日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由于国内外民主潮流的影响和推动,加之共产党人的直接支持和巨大帮助,中国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民主党派。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或中间性党派相比,它们具有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坚持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两大显著特点。基于这些特点,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积极引导,逐步与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基础上进行了合作。
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萌芽了以统一战线为表现形式的合作性政党政治。合作性政党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关系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雏形,成为促进南京国民政府进入宪政时期和合作性政党政治形态的重要推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全民族抗战作了重要的准备。 |
|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3/181611.html
更多阅读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TPP与中国主导的RCEP之争?作者:@北方乔峰【@北方思想库 140522#华山论剑#】《日本经济新闻》5月18日载文《TPP在中国打响前哨战》,在17日开幕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有12个与会成员同时也参与了TPP谈判。而对TPP阵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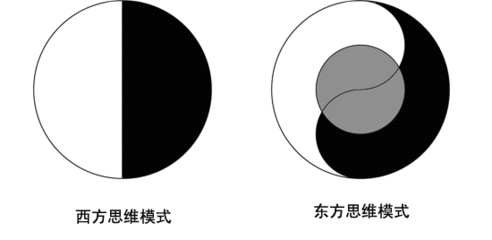
易经与中国文化(演讲稿)郭顺红2010年10月29日在本单位参加了一场《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下面是讲稿内容,愿与大家分享。易经与中国文化《易经》为中华文化的精粹,乃五经之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易经》的发展横贯数千年,至今仍深深影响

《蓝漠的花》在《中国卡通》杂志发表之后,引起通心粉们的狂热追捧!原来只是一篇准备发(上)(下)两画的短篇,现在与漫画家百无商量之后,决定将其延长,最早将于2013年3期重新登录《中国卡通》故事版,绝对值得期待!2013

惊曝!日本为与中国冲突中“先发制人”做好准备2009_7_13_16057_9616057.jpg(37.44 KB)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http://bbs.huanqiu.c

“九一八”事变里,日军在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司令部上升旗。1931年9月18日,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拉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东北三省短短数月沦丧敌手。81年后的今天,中国非当年之中国,世界亦非当年之世界。鸣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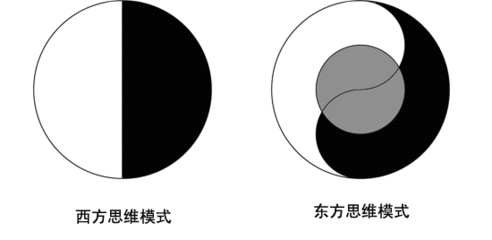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