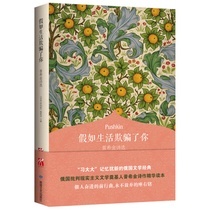茨冈普希金
瞿秋白 译
大群热闹的茨冈
沿着柏萨腊比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好些车轮中间,
一半盖着地毡,
点上了灯,一家人
围着就预备晚饭。
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地上放着,
篷帐后面一只熊开了锁链躺着。
旷场中间,一切
都是活泼地:
小孩子叫着,
娘儿们唱着,
还有车上的
行军灶响着。
这些人家,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们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荡的营帐扎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来了。
静悄悄的旷场,听得见的
也就只有马嘶跟狗咬了。
那儿也再看不见火光,
什么都安静,只有月亮
高高的独个儿在天上
照着那静悄悄的营帐。
一个蓬帐里面
老头儿还没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点儿火气烤着,
看着那远远的田地
罩满了夜里的雾气。
他有个年轻女儿,
到荒田里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儿,
就这么游荡惯了;
她来是要来的,
可也已经太晚了,
月亮送着云儿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儿,真妃儿呢怎么还不来,
老头儿这顿穷饭也要冷完了。
啊,她来了。跟着她后面走的
那个人,年纪很轻哪,——
老头儿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姑娘说:“我的父亲哪,
我同得个客人:我在坟场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来到咱们的营帐,
让他这儿过夜罢。
他说,他要做茨冈,
跟我们一样,
衙门里要捉他,我可要保护他。
他名字叫阿乐哥,
愿意到处跟着我。
老头儿:
我很高兴。
就在咱们篷帐
里面的草堆上
过夜也行,
要是你真愿意
留在我们这里
一块儿来挨这个苦命,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准有你的面包,
准有地方睡觉,
你就做了我们的人,
只要惯了就成,
虽然说是穷困,
倒也自由得很。
咱们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块儿赶着车动身;
随便你找个什么事做做:
锤铁呢,阿乐哥?
还是你会唱歌
带只熊到村庄上去走走?
阿乐哥:
我留着不走了。
莫妃儿:
他是我的——
谁也不会来把他赶走的!
啊呀,已经是太晚了……
弯弯的月儿落山了,
田地都已经给雾盖住了。
梦魔来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头儿轻轻的
绕着那个没声音的
篷帐走着。“起来罢,
真妃儿,太阳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罢!
孩子们,好梦别太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热闹,
篷帐拆了,车子准备好,
这么一大群的人
大家一块儿动身,
那好空旷的平原上,
后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还有小孩子,骑着驴:
驴背上两大筐
一边一个的挂着,
孩子在里面耍着。
叫唤着,闹着,
熊也在叫着,
它的锁链响着;
花花绿绿的是破烂的衣服,
小孩子老头儿还光着脊背;
狗的叫声,咬声,人说话的声音,
还有咿咿呀呀的车子的声音。
这是多么烦杂,多么野腔调,
可是,一切都活泼地安静不了,
没有我们那种死沉沉的情调,
没有那样的安闲生活的单调,
——只有奴隶的歌谣
才会单调得无聊。
尽看着空旷的芒地
那年轻人是在烦闷,
优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问一问。
现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儿同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年轻人的心可还在跳动,
他担心着什么这样心痛?
你看罢,看那上帝的鸟儿,
它不用劳动也不用担心,
夜长呢,树枝上睡个觉儿,
那儿为着做窠儿去操心。
太阳出来了,
拍拍翅膀就要飞的
鸟儿唱开了,
好噪子是上帝给的。
春天景致是最好,
等到热过了一个夏天,
晚秋就又要雾又烟,
人要苦闷要烦躁,
鸟儿可远远的飞去了,
飞过苍茫的大海,
飞到暖和的天边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来。
他也像只无忧无虑的鸟,
给人赶出来了,到处漂流,
靠得住的窠儿,向来没有,
无论什么,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儿都是他的路,
到处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来,听到上帝的调度,
一天到晚就这么吊儿朗当。
要过活固然
总要用些心机,
可是他的懒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时候
意外的降临,他要有
这样的偶然的运气,
就过得堂皇富丽。
孤零零的他,
头上也不止打过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吗?
他总是马马虎虎倒头就睡。
就这么过活,
管不了许多,
看那瞎了眼了运命
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然而他的情爱,
耍过他的心神,
那是多么难挨,
满腔都在沸腾!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静了是不是能长久?
那情爱是总又要醒的:
等着罢,不给你放心的。
真妃儿:
好朋友,你讲罢,
你扔掉了那些,
有点儿可惜罢?
阿乐哥:
我扔掉的那些……?
真妃儿: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乡的人,
还有故乡的
城市。
阿乐哥:
要可惜人?
可惜什么?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么!
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四面围着了堡垒,
朝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钱,
还带一根锁链。
我丢了什么?是卖朋友的干活,
是那些发疯似的要钱的家伙,
是荒谬绝伦的判决词,
还是耀武扬威的羞耻?
真妃儿:
然而那儿有高大的宫殿,
有的是那花花绿绿的地毯,
热闹的玩意儿,还有酒宴,
姑娘们的打扮是那么好看!
阿乐哥:
城里面的热闹那又有什么快乐?
那儿没有爱情,那儿就没有快乐;
姑娘们呢……你没有他们的
珠宝跟首饰,没有他们的
你不要变心,我的亲爱的!
我……就只有一个心愿——
要给你爱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心甘情愿。
老头儿:
孩子,你倒还爱我们,
虽然出身是个富人;
可是,谁要是享惯了福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咱们这里好久就有一个传说:
皇帝把一个人赶了出来,
叫他来到这里过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
虽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贵姓大名)
他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可是他的好心,却又活泼又年轻;
他的噪子可来得稀奇,
像流水的声音那样潇洒,
真有点儿唱歌儿的天才。
大家都爱上了他,
他就在那敦奈河边儿住下,
谁也不肯得罪,他
只爱讲故事,真叫人舍不下。
他是什么也不想,
又胆心又没力量,
真像个小孩子
只等着吃奶子,
打措捉鱼,都是别人替他干,
河里冻了冰,那可是真可难;
冬天的大风雪,呼啦呼啦的吹着,
一层层蓬蓬松松的雪花儿盖着,——
盖着这神圣的老头;
可是,他仍旧不能够
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穷苦,
东飘西荡,他脸是那么干枯。
他说这是上帝的震怒,
罚他的罪过,叫他受苦。
他尽在等着饶恕,
可怜呵,总是愁苦;
就这么沿着敦奈河流荡,
多少痛苦的眼泪流得那么冤,
还在那里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离得那么远……
他死的时候,
悲伤的朋友
还听见了他的遗嘱:
请他们把他的尸骨
一定要送到南边去安葬,——
死都记得这是他的外乡。
阿乐哥:
O,罗马,O,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你子孙的命穷!
爱情的,天神的歌曲家,
请你说罢:什么是光荣?
是坟墓上的呼号,
“歌功颂德“的热闹,
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声名?
还是在草堆里借着树阴,
支起烟雾沉沉的篷帐,
听说故事的野蛮茨冈?
过了两年。这此和平的茨冈
仍旧是那样成群的流浪,
照旧是到处欢迎,
到处有的是安静。
阿乐哥抛弃了那锁链似的文明,
自由自在,和他们一样,
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
就这么一天天的流荡。
仍旧是那么样的他,
仍旧是那样的一家;
以前的事情,
甚至于忘完了;
茨冈的生活,
他已经过惯了。
他爱他们的过夜的草堆,
爱那永久的懒惰的沉醉,
爱他们讲话的腔调,
又响亮又那么单调。
那个毛茸茸的熊,
丢掉了自己的洞,
也住在他的篷帐,
倒象个客人的模样。
沿着荒郊野地的道路,
靠近莫尔多人的院子,
它就在村庄上去跳舞,
一群人围了一个圈子,
人家小心珍重的,
它可臃臃肿肿的,
又那么哼哼的叫着,
把陈旧的锁链咬着,
老头儿撑着旅行的手仗,
懒懒的敲着鼓儿;
阿乐哥唱着歌儿,
牵着那个熊儿;讨点儿赏——
丢一个圈子,可要难为真妃
去收大家的钱,谁愿意就给……
晚上来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儿
煮着人家没有收割的小麦;
老头儿睡着了——什么都安静了……
篷帐里静悄悄的,那么鸟黑。
老头儿的血已经快要冻了,
晌一晌那青春的太阳
暖和一下罢;女儿可唱动了,
她靠着摇篮就那么唱,
她唱她的爱情,
叫阿乐哥寒心,
阿乐哥的脸
苍白的可怜。
真妃儿唱: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就斫我,你就烧我,
我不怕马,我不怕火,
我的心肠铁硬,
看见你就要恨;
我爱了另外一个他,
就是死,我也爱着他。“
阿乐哥:
别吱声。唱歌真叫我厌烦,
这样的野腔调,我不喜欢。
真妃儿:
你不喜欢?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唱我的歌儿,我唱给我自己。
“你就斫我,你就烧我,
我可是什么也不说。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不会知道他,
你别想知道他!
他比春天还新鲜,他比夏天还热烈;
他是多么爱我!多么勇敢,多么年轻!
那天悄悄的晚上,我和他多么亲呢!
说起你的花白头发,我还笑得要命。
阿乐哥:
别吱声,真妃儿,我满意……
真妃儿:
你的歌儿,你懂了没有?
阿乐哥:
真妃儿……
真妃儿:
我唱的就是你,
你要生气,有你的自由。
(她走开,唱着“我的老丈夫”等等。)
老头儿:
对了,对了,我记得了;这一首歌儿
还是在我们的时候唱起的头儿,
就这么唱着好玩,
大家都已经听惯。
从前在卡古尔的荒野,
流浪着的冬天的长夜,
我的马理乌拉对着火儿,
摇着女儿唱着这首歌儿。
过去的那些年代,
一天天的消磨,
暗淡得记不起来,
独有这一首歌,
简直和生了根一样,
深深的记住在心上。
安静得什么也……
南方,南方的夜……
那碧青天上
挂着一个月亮。
真妃把老头儿叫醒:
“阿乐哥多可怕,0!父亲!
他做着恶梦,你听听:
他是在哭着,又在哼。”
老头儿:
别动他,别吱声;
俄国有个传说:
现在半夜三更,
宅神总是压着
睡着了觉的人,
呼吸就很难过;
天快亮了,宅神
自己就会走脱。

你,现在别做声,
来跟我一块坐。
真妃儿:
父亲,他在悄悄的叫“真妃儿”!
老头儿:
他在找你呢,虽然做着梦!
可见得这是他看着真妃儿
比整个儿的世界还贵重。
真妃儿:
我对他的爱情要已经冰冷,
我的心要自由,我实在气闷,
我已经……可是,静些,你有没有听?
他又叫了另外一个人的姓名。
老头儿:
是谁的?
真妃儿:
你也没听清?
他哑着声音的哼,
咬着牙齿的发狠,
多么可怕!我去叫他醒。
老头儿:
何必呢;不要把夜神赶走,
他自己会走的。
真妃儿:
他在翻身了……
他醒了……起来了……他在叫我……
我去看他。再见,你也好困了。
阿乐哥:
你那儿去了来的?
真妃儿:
跟父亲
一块儿坐了一坐。你好难过!
什么鬼压住了你,你的心
在梦里苦够了。真吓着了我:
你在梦里咬牙切齿的叫我。
阿乐哥:
我梦见了你。仿佛是你和我……
唉,我看见了可怕的幻想。
真妃儿:
你,别信那梦里的怪现象。
阿乐哥:
我吗?唉,我什么也不信:
梦也不信,甜言蜜语也不信;
就是你的心,我也不信。
老头儿:
你干什么时时刻刻的操心,
干什么要叹气,唉声,
我的发疯的青年人?
这里的人是自由的,
天是青的,老婆有的
光荣就是美丽。不要哭;
烦闷死了,你自己吃苦。
阿乐哥:
父亲,她不爱我。
老头儿:
朋友,你别难过,
她是个小孩;
你的发愁真没有道理
你那们的爱,
又难又苦,女人的心理
可来得个随便;
你看那个天边,
远远的月亮
自由的在逛;
它的光辉顺便的
平等的照着整个天下,
它就那么随便的
射着一片云,那云底下
可真是灿烂的光芒,
但是,你看它已经又
移到了别一片云上,
仍旧又不会有多久。
谁能够指示天上一个地方,
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谁又能够对着青年的姑娘
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
你宽心些罢!
阿乐哥:
她以前多么爱我!
多么亲热的待我,
就说晚上罢,
在空旷的寂静里面
总和我一块儿谈天!
她充满着孩子气的快乐,
还有那可爱的嘁嘁昔昔,
或是温柔的拥抱,
会把我的愁闷
一下子就都赶掉!
现在怎么样呢?
真妃儿对我要欺瞒了!
我的真妃儿竟冷淡了!
老头儿:
你听着,我给你讲我自己的故事。
要知道,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莫斯科人还没有恐吓敦奈河——
(你瞧,我记起了旧的悲哀,阿乐哥)
那时候,我们害怕着苏丹,
归帕萨蒲扎孔谟总督管,
他那高高的堡垒在亚克尔曼,
那时候呢我还年轻,我的心肝
正在沸腾着狂热的快乐,
我的头发没有灰白一根。
年轻美人之中,一个……
我真当她太阳似的赏识,
后来呢,她终究成了我的。
唉,青年时代是容易过的,
真只象流星那么样一闪,
我的爱情可比这个还短:
她,呀,我的那马理乌拉,
只爱了我一年。有一天,
我们在卡古尔的水边
碰到另外一帮茨冈儿;
他们在我们的附近
山脚底下,搭了篷帐,
一块儿歇了两晚上。
第三天他们就动身,
马理乌拉,丢下了小女儿,
就这么跟着他们走了。
我安安稳稳的睡着觉儿,
天刚亮,我醒过来,没有了!
没有了我的爱人。找着叫着,
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真妃儿也哭了,尽在吵闹着,
我也哭了!……从那时候
世界上的姑娘们,
我从来也不过问,
寂寞得我一个人,
再也没有找爱人。
阿乐哥:
你怎么没有立刻赶出去,
追着那个,忘恩负义的,
和那个野兽,怎么没有去
一刀刺进那刁货的心理呢?
老头儿:
干吗?青年比鸟还自由,
谁能够拦得住爱情呢?
快乐也让大家去轮流,
过去的,是回不来得呢。
阿乐哥:
我可是不能够那么样。不行:
我也不争论,可是我不能够放弃
我的权利,
至少,也要痛快的报仇,才行。
要是无底的海岸边,找到了
睡着的仇敌,
吓!我赌咒,我的
脚尖也不肯饶他:
我哪,就是他不会抵抗,
我也要把他推进海洋,
我颜色也不变。我要凶狠的笑他,
笑他那突然惊醒的恐惧,
听着他扑隆通的掉下去,
这声音够我长久的好笑,
也可算得甜蜜的音调。
年轻的茨冈:
再,再亲一个嘴!
真妃儿:
快些!
我丈夫又凶又爱吃醋。
茨冈:
再亲一个……要长久些。
为着分别。
真妃儿:
分别罢,趁他没有到来以前!
茨冈:
说罢,什么时候又再见面?
真妃儿:
今儿;当着月亮落山,
在那儿,在冢后墓上。
茨冈:
骗人!她不会来的。
真妃儿:
跑罢——他来啦。我亲爱的,
我要来的。
阿乐哥睡着。他心里
浮动着恍惚的幻影;
他,暗黑里边叫边醒,
醋意地伸开手臂;
手在担心
抓到被窝冷冰冰——
他的伴儿离开很远……
他颤抖地抬起身来瞧瞧……
什么都安静:恐惧把他拥抱,
浑身又冷又发烧;
他起来,从篷帐往外走,
阴惨的,绕着车子漫游;
一切恬寂寂;旷野静悄悄;
黑〓〓;月亮躲在云雾里,只有稀微的星光闪耀,
那露水上勉强可辨的足迹
通到远远的冢丘:
他焦急的顺着
不祥的足迹走去。
坟墓在他的前头
远远地在路旁发着白光,
他怀着预感的苦恼,
拖着无力的双脚,
嘴唇打颤,膝盖发抖,
向着那儿走……
突然间……这也许是梦?
突然在那被污渎的墓上,
他看到亲昵的双影,
又听到亲切的细语。
第一人声音:
是时候了——
第二人声音:
别忙罢!
第一人声音:
我亲爱的,是时候了。
第二人声音:
不,不,别忙,
等到天亮罢。
第一人声音:
已经不早了。
第二人声音:
你爱得好胆怯呵。
再等一分钟!
第一人声音:
你会害我。
第二人声音:
再等一分钟!
第一人声音:
如果丈夫醒来
我不在……
阿乐哥:
我醒来了。
你们那儿去呵?
你俩都别忙罢;
对你们,这儿坟边也好。
真妃儿:
我的朋友,逃呀,逃!
阿乐哥:
别忙!
年轻漂亮的人儿,去那儿?
躺下去吧!(用刀刺他)
真妃儿:阿乐哥!
茨冈:
我要死了!
真妃儿:你在杀他!阿乐哥!
瞧:你溅了一身血!
0, 你干了什么?
阿乐哥:
没有什么。
现在你呼吸他的爱情去罢。
真妃儿:
不,我不怕你,够了,
佻的威吓我鄙视,
你的杀人行为我祖咒。
阿乐哥:
你也死去罢!(刺她)
真妃儿:
我死也爱他。
曙光照耀的东方发亮了。
冢丘后,阿乐哥
血淋淋,手握着刀,
在墓碑上坐着。
他面前躺着尸首两个;
凶手有面孔可怕,
一群受惊的茨冈
胆怯地围住了他;
墓穴就在一旁挖,
挨个过来了悲伤的妻子们
把死者的眼睛吻了一下。
老头儿爹爹独个儿坐着,
在沉默发呆的悲哀里
朝那死去的女儿望着。
他们举起尸首,抬着,
把年轻的一对儿放到
冰冷的土地的怀抱。
这一切,阿乐哥远远的看到。
当他们被最后一撮土盖好,
他默默地,缓缓地欠身向前,
从墓碑上向草地跌倒。
这时候,老头儿走近来,说道:
“离开我们罢,骄横的人!
我们是粗野的人,
我们没有法律,
我们不磨难也不处死人,
我们不要血也不要呻吟;
可是跟杀人犯一起过活却不甘心。
你生来不是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
我们怕你的声音:
我们胆子小,却有善良的灵魂,
你呢,又凶又横;——对不起呵,
离开我们罢!祝你安宁!”
话说完了,游荡的茨冈人
闹哄哄的一大群动了身,
离开那可怕的过夜的山峪,
很快的全都消失在草原的远处。
只有一辆车子,
盖着一条破毡子,
在命定的旷野上留住,
就宛如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
在雾气弥漫的早晨,
从旷野飞起了一群迟飞的野鹤,
叫着飞向那远远的南方,
有一只被致命的子弹打中,
它垂着受伤的翅膀,
悲惨地留下来了。
夜来了;
在漆黑的车子里
没有谁把火生起,
在搭着的幕顶下面
直到早晨没有谁安眠。
结 语
歌儿的魅力
在我的朦胧记忆里
就这样复活起
那忽而光明,
忽而悲惨的日子的幻影。
在那可怕的战鼓声音
长久没有平息的国家里,
在那俄罗斯人给斯坦部尔
划定疆界的国家里,
在我们的老双头鹰
还被喧嚷着过去的光荣的国家里,
我在草原上的古代营垒中间,
碰见了和平的茨冈的车辆,
和他们孩子气的柔和的自由自在。
跟随着一群懒洋洋的茨冈
我常常在旷野上游荡,
吃的是他们简单的食物,
躺在他们的火堆前睡眠。
在缓缓的行进中,我喜欢
他们那一片快活的歌声——
可爱的马理乌拉的温柔的名字
我长久地念着,一次又一次。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儿子!
在破烂的篷帐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在荒野中也逃不了不幸,
到处有命定的情欲,
那就抵抗不了命运。
In the shadows of the forest, among the beechtrees,
something moves and rustles and whispers all at once.
Flames are flickering, their glow dances
Around colorful figures, around leaves and rocks:
It is the roaming band of gypsies
With flashing eyes and waving hair,
weaned on the holy waters of the Nile,
tanned by Spain's scorching sun.
Around the fire in the swelling green forest
Wild and bold men are resting,
women squat to prepare the meal,
and busily fill ancient goblets.
And tales and songs resound all around,
telling how the gardens in Spain are so full
of bloom, so full of color;
and words of magic to ward off need and danger
the wise old woman recites for the listening crowd.
Dark-eyed girls begin their dance
While torches flicker inredish glow;
The guitar casts its lure and the cymbal sounds;
The dance grows wild and wilder.
Then they rest, weary from the night of dance,
and the beeches rustle them to sleep.
And, banned as they are from their blissful homeland,
they see it in their dreams, that happy land.
But now, when the morning awakes in the east,
so vanish the beautiful visions of the night;
at daybreak the mules paw the ground,
the figures move away-who knows where?
茨冈
[俄]普希金
1
拇指与食指中指的配合
拈出一片黄昏,拈出
篝火纵横交错的历史
自印度沿经阿富汗、波斯、土耳其
混成歌声,跳跃舞蹈
这就是你?就是
丢弃占卜买来的路径
拈出扑克暗示的苍穹
一路流浪到欧洲的你?
2
遍布西亚东欧,细腰悬挂红色
一群一群的小辣椒,环佩叮当
风过的时候骗满天的云彩
雨塌陷了蓬车骗路过的河流
麻袋一样老的老人腿上布满伤疤
兀自拨着吉他伴年轻人欢歌
这就是你?就是
苍老并不能阻止愉悦
青春闪现的笑容夹杂着调皮
用流浪做追击的姿态
掩杀将来?
3
额际深陷月光
车辙嘹亮历史
内心的桀骜不驯只承认自由
与天与地与一路的狂风
格格不入的,还有
穿越时空的岁月
这就是你?就是
砍伐目光所能达及的富裕
摧毁收容赐予的平安
将手鼓翻作舞步,快速中旋转升腾
将歌唱永远高亢于原野
并在四野尘埃落定死一样的寂静后
从不哭泣?
4
即使无所求,即使逃亡
也没有逃出纳粹
死亡像苍蝇那样跟着飞舞
薅草一样倒下的并不包括
弗拉明戈舞,萨拉萨蒂,圣桑
拉威尔的崇拜和炫技
不包括你的蔑笑以及狂放
也不包括沿途的树木,星光
这就是你?就是
杀戮并不能左右你的思想
并不能在辽阔江山的背影里
阻止你宽达几万公顷的脚步
并且不返回印度返回始祖
并且不停止歌唱
继续流浪?
5
这就是你?
还是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