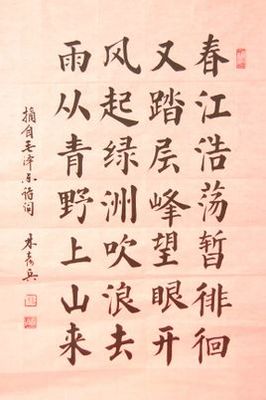我一家三口都供职于山东大学,因此对山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迎着朝阳的儿子比步入夕阳的我对学校的大事小情更为关注敏感。前几日他说:张金光老师去世了,王学典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你们认识张金光老师吗?
听着另两位家庭成员的一句句问答,张金光是谁我仍然一脸的茫然,最后经提示:“就是摆饭摊的那个老师啊!”我眼前立即出现了那位黑黄瘦弱的满脸病容的、总是穿着那件沾满油渍的衣服、总是留着油乎乎的头发、总是在家属院斜对面粮店前那片空地上收拾碗筷和啤酒杯、总是被不少人投去鄙夷目光的那位老师……
自1987年我家从校园筒子楼搬入南院宿舍至2006年搬出,与张金光老师同住一个大院,我住东部,他居西部,除了他的贫窘“落魄”开饭摊和他儿子的逝去,其他我都没印象……当我看完王学典老师充满真情正义的文章,在感慨和震撼中,我不仅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马路边摆饭摊的张老师增加了真正的了解,也增添了对张老师从没有过的深深敬意,同时也为自己曾经对张老师流露出的目光和自己与张老师毗邻而居长达19年却只记住了他开饭摊而对他的学问一无所知而愧疚……
听我家人回忆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那十多年间,忙碌的张金光老师有空时常在我们称之为街心花园的空地找个地方蹲着,这并非是他喜爱闲逛,而是因家里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太多,有限的空间太挤太乱,他“没”地方呆,所以爱在这里找个安静。我家人那时还年轻,觉得张老师虽其貌寒窘,但肚里富有,所以常常爱去和张老师聊天,听他讲自己过去的故事:张老师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好,病泱泱,在南开大学没完成学业就被迫休学回家务农,后来几次想回校复学都历经坎坷,这段求学路他一直耿耿于怀……在村里,壮劳力挣满一个工分也吃不饱饭,何况他的病体只能挣半个工分,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自己竟然没有饿死,这使他感到万幸……就这样,张老师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学问的思考,1978年他考上山大历史系研究生,求学期间还要兼顾务农……张老师自己多子并无多福反而遭罪受累,开个饭摊,采买做卖,因老伴身体不好,主要都是由他一手操持,他感叹自己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到了一天到晚为生计的操劳上。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与生活的重重负累让张老师常常发出几声无奈的叹息……2000年至2006年学校许多教工陆续迁入新宅,张老师无力搬入新建的宿舍只能搬进别人腾出的29号楼一层三室旧居,但他在几代同堂热闹无比的家里仍知足而乐地继续他的史学研究……文人不幸文章幸,正是由于张金光老师在国困家贫的岁月里长期在社会最下层煎熬,才使他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才能有他的《秦制研究》,这宝贵的人生体验仅在象牙塔和书斋里是绝然获取不到的……
“举目纷纷笑我穷,我穷不与别人同”,张老师今年77岁,在如今“健康老龄化”社会中他的年纪实在不能算老,于家、于史学界他都还能发挥巨大的余热,然而他却赫然辞世,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惜……今特转贴王学典老师的文章,以追思这位身贫道富的知识分子对学问的痴醉、执着与赤诚!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痛悼张金光先生
王学典
“张金光老师今早病故了!”当我2013年9月2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时,正伏案赶写一个东西,但放下电话后,却再也一个字写不下去了,张老师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容,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第二天,我和老同事陈尚胜教授偕赵凯球先生往张府吊唁。在那张效果很不好、几乎失容的遗像前,我们鞠躬和张老师永别。贫寒的家境,悲伤的亲属,使我站在遗像前的那一刻感到极度的压抑和悲怆。那一刻,多么想放声一哭,为上苍和命运对作为史学天才的张老师的不公而哭!
张老师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以学问为生命、以学问为信仰的人。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他对学问的痴迷和虔诚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上苍和命运的不公在于:没给他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来张府吊唁我才知道,他生前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这可能在山东大学文科教师中是不多见的。“不图腰缠十万贯,但求坐拥五车书”,是自古以来多少书生的梦想!他到去世也没实现这个梦想!他有五个孩子,现住在南院家属区一个三居室的套房里,家里一度连摆双人床都睡不下,哪里还会有他自己的书房!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房,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的那些名留学术史的论著都是在饭桌上写成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书架!其实他根本用不着书架,因为他甚至没有自己治学的专用书籍!他买不起书。他1956年入读南开大学历史系,本来是学明清史的,之所以后来改治秦汉史,就是因为秦汉史的资料到处都有,不需要自己再掏钱买书。他实在太穷了!
他至去世都没能完全逃脱贫穷的魔爪,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已有很大改善。他像当年马克思所自况的那样:贫穷如同魔鬼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角,无论怎么用力都甩不掉。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事实是:张老师在学校出名,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的贫穷,特别是因为他上个世纪90年代竟然在校园门口开过饭馆!
我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不知多少个私下场合,对作为一个有造诣的历史学家的张老师,把餐馆开在自己任教的大学门口,表达过一种看法:这不是张老师的耻辱,这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张老师有什么办法:妻子带着五个孩子从乡下进城谋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下,这怎么能养活得了?你给他那么点工资,又不让他开饭店,你想让这七口人喝西北风么?“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对张老师来说,只有开饭店,才能立马挣钱,才能立马糊口!其他的任何自救举措都远水不解近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是个什么年代?知识分子最寒酸的时代,而人文学者尤甚。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民谣一时流行,高校教师经商下海,就集中出现在此一时期。这样一种总体状况,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困境,迫使他走上边治学边开餐馆的谋生之路,这怨得了他么?而且就是在他开餐馆期间,他的一个在餐馆帮忙的爱子还触电身亡。才高八斗,一贫如洗,一至于此,竟还有人指责他损害了学校的声誉,情何以堪!理何以堪!
张老师走了,也许他只有走才能彻底摆脱贫穷带给他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压迫感和挣扎感。七十七年的生涯,已让他尝尽生活的艰辛。
张老师走了,秦汉史学界从此少了一根支撑自己的栋梁,这个领域从此少了一个引领者,少了一个最辛勤的劳作者。中国史学界从此少了一个已臻最高治史境界的杰出历史学家。
在生活中他是个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短于生计的农民,但一入秦汉史领域,他则成为一员纵横驰骋、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的猛将,最后则赢得了此一领域几乎所有学者的敬重。
出手不凡,大气磅礴,是张老师在科研上最重要的特点。他的成果,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几乎件件都是一等选题,件件都搅动了秦汉史研究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所汲汲以求者便是一个‘新’字”,“无新见誓不为文”!198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他,几乎同时在《中国史研究》和《文史哲》上推出了《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和《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两篇长文,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了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的乃是“普遍的真正的土地国有制”的见解。此一见解,堪称石破天惊,翻了一个历史巨案。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中国土地私有制之先河。而且这一看法从董仲舒以来就流行。而张老师现在则提出: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是“按户计口授田制”。一石激起千层浪,先秦秦汉土地制度史从此被改写。
为张老师所改写的何止仅仅秦的土地制度史?秦的户籍制度、爵赏制度、学吏制度、乡官制度、家庭制度、刑徒制度、田地规划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和居资赎债制度等,均为张老师的“详尽研究”所改写。而且,不仅是改写的问题,其中若干制度,要么为张老师所发现并首先命名,例如,秦的“为田制度”即田地规划方案,就是“一个从未被认知的问题”,秦的“官社经济体制”,“一向为学术界之所未知”,秦的官作“居资赎债”制度,“由于文献阙文,过去一无所知”,这些端有赖他的努力而被发现并彰明于世;要么有的制度虽为人们所知,但并不清楚,例如,“秦的阡陌封疆制度”早已是“千古之谜”,虽“历来说者蜂起”,然“终无破解”,秦所确立的系统的乡官组织及乡政运作,后世也“不甚了了”,秦的“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千古以来也“鲜为人说”,特别是对秦的“户籍制度”,后世“尤其无知,向为学术界一大空白”,这些也端赖张老师的洞察力而大白于世。
以上述发现和发掘为基础的《秦制研究》一书,其巨大的学术史意义便不容轻忽了。论者咸认为,这部煌煌近百万言的巨著,将不仅成为“秦制”研究的经典,也将会是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因为“秦制”开此后中国历史之先河,“汉承秦制”,历代又承汉制,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两千多年来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制”格局就这样延续下来。然而,有关“秦制”,特别是“秦制”形成过程的文献存世极少,连离秦灭不远的司马迁,也慨叹“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样,作为中国制度源头的“秦制”,特别是其中的“食货志”,在此后两千多年间,就长期处在“无闻”的状态。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从根本上结束了这一状态,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秦制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张老师常年处在“蜗居”状态,但屋墙的四壁似乎并未限制住他高远的学术视野。他是一个有巨大学术雄心、学术抱负的人,虽然身居“外省”,但他未必不想在学术上称王,也许研究秦制使得他想当学术上的秦始皇。即使当不上秦始皇,他也肯定想做一个永远不被兼并的学术诸侯,“五霸”或“七雄”,大概是他最低的学术期待。他是一个想创造学派也创造了学派的人,他是一个想提出自己的方法论也提出了方法论的人。
深厚的实证功力与卓越的概念化能力同臻至境,是张老师治学的杰出之处,他在这两方面同时获得了同行的激赏和钦服,这很不容易。秦汉史研究名家黄留珠先生,对张老师的材料疏通考辨功夫就再三致意、称道不已。他认为张金光先生关于秦简《法律答问》“部佐匿诸民田”应作“部佐未将诸民田上报”的考证,关于龙岗秦简“行田”为国家授田制的考证,“畴企”为田中畎亩规划形貌的考证,关于“制辕田”即“为田开阡陌封疆”的考证,关于青川秦木牍文“畛”的考证,关于孟子井田说非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国家份地授田形式”的考证,关于“君子”、“野人”对立即官民对立的考证,关于“提封田”制的商榷等等,均“堪称史料疏考功夫之典型”。其中,张先生关于《商君书•境内》之“校徒操出”应为“技徒操掘”的考订,尤为“精妙”,“令人叫绝”。这一考证,既纠正了章太炎的老师俞樾的疏解,也超越了高亨先生在《商君书注解》中的相关训诂,“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张老师的实证功力无疑是一流的,但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愿意做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说:“实证不过是我的第一步功夫,还要进一步出于实证而进到分析研究的理论层次,亦即史、论结合的层次。”所以,我认为他已进入到一个大历史学家的行列:他不仅把自己的研究推进到较高的学术层面,而且他追求的,还是学术的世界设准。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并非仅为了描述历史”,而是要发现历史本身的逻辑,“并从中提炼和建构普遍性理论分析系统概念”,他说:“吾致力于此道之研究凡三十余年,其目的在于另辟蹊径,以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免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笼罩之困境,回归中国历史境遇,建构一符合中国历史实践逻辑的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张老师已经实现了他治学的初衷:初步建构起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粗具规模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框架和一套属于自己的、独创的概念范畴,而这一点是并世的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所没有做到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大致可分为下面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而用来反映这一历史描述框架的核心概念有:“官社经济体制”、“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等等。在构筑这个历史框架和概念系统时,张老师也作出了一些宏观历史判断:周秦以降三千年,“不是民间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权力塑造整个社会”,“国家权力是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等等。这些基本判断和概括的理论意义是不容低估的:由此出发,将改写整个中国历史。
张老师也是中国史学界少数具有方法论自觉的学者,事实上,他一直一面在治学,一面在进行升华和反思,遂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点的治学方法和历史理念。关于前者,他说他的原则是:“断代问题,通史做法;具体问题,一般做法;个别问题,普遍做法。”也就是说,不管大小问题,总是先做通体研究,打通一条线,旁及一大片,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把握具体和个别问题。譬如,他研究“秦制”,“其时限却不仅囿于秦十四年的历史,其空间界域亦非仅囿于秦之旧部,而是上挂下连,左右旁通,亦即追究前后通时变,旁及六国考异同,上考其源,中究其制,下指其归。一言以蔽之曰:于秦制中通古今之变,于通变中深考秦制”。
至于张老师的历史观念,尤深具启发意义。他说他的历史观念:是由传统的二维关系调整为三维关系,由平面关系调整为立体关系,由左右关系调整为上下关系,横向关系调整为纵向关系,进一步的说,把民间关系调整为官民关系;把社会间关系调整为国家对社会间关系。总之,他认为,“官民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传统中国,远比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重要,更具本质的意义。在他看来,传统的“阶级论”的方法,“恰恰略去了国家权力这个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维度”,而官民关系,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更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剥削关系。这堪称张老师的典型的中国历史观了。如同前面所说,他的历史观如得到贯彻和实践,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将呈现另外的面貌。
近六十年来,有两个“主义”对史学界危害巨大:前三十年是“教条主义”,后三十年是“实证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形成了共识,但“实证主义”的危害,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由于披上了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受到鼓励和放纵。当前中国正在急剧崛起和转型,但处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历史学却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何去何从,这就是实证主义泛滥所种下的恶果。实证主义对史学界的危害不亚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只相信“归纳”的作用,完全排斥“演绎”,排斥抽象概括、排斥理论工具、排斥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题意识”的作用,从而把史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如同现在中国的工厂企业大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中国的史学界现在也处在世界学术产业链的末端:中国的学者们如同世界学术分工中的小工,每每像蚂蚁一样到处收集整理材料、清理事实,然后外国学者利用这些材料和事实加工成概念和模型,中国学者再引进这些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历史。如果这些概念和模型与中国社会历史基本相合也就罢了,问题就在于它们并不相合。一方面学术界对概念和理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引进的“洋奶粉”与中国的肠胃不合,而中国的学术奶企又不生产这些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学界只好陈陈相因而找不到出路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张金光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概括容或可商,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亦不乏可挑剔之处,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他在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方面已尽了一个开辟的责任。他的努力,代表着未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健康的方向!
张老师走了,山东大学从此失去了一个能为自己创造巨大声誉的人,《文史哲》杂志从此失去了一位杰出作者。作为秦汉史专家的张金光先生是从《文史哲》起步的,他的秦汉史研究的处女作《论曹操》,就发表在1977年第4期《文史哲》上,在此后三十多年间,他在《文史哲》上共刊出11篇文章,这些文章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大都能在学术史上留名则是肯定的。他在《文史哲》(2010年第5期)上的绝笔之作是《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一文,正是在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他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史哲》杂志这个平台,张老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张老师的交往实际上比水还淡。在他生前,我从未去过他的府上。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他孩子多,住处之窘迫可想而知,他又很要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去他府上无异于让他难堪!我们所有的见面都是在路上或是在系里开会的时候。尽管见面很少,尽管年辈有悬殊,但他始终把我看作他的学术知音,见面就聊学术,全是最近学术上的所思所想,我不记得聊过学术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也没给我们正式开过课,我们读本科期间,他在上研究生。唯一的例外,是他作为研究生实习,给我们开过一次讲座,但对这次讲座我已全无印象。但他却是我来山大读书后结识最早的人。“七九级”是1979年9月初开学的,记得就在当月,历史系在文史楼201教室召开“历史发展动力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学前我就关注这场历史学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以,当时还是新生的我挤进会场旁听了这场讨论,老师们之间的这场唇枪舌剑,让我大开眼界。张老师作为研究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发言,依稀记得是说农民起义没起什么好作用之类的,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因此,直到现在,连他当年开讨论会时坐在201教室的哪个位置,我都记得十分清晰。在我留校作教师后,他还做过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记得是“小平南巡”、新一轮改革启动之后,教育界受冲击很大,许多人感到传统学科已发生生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为应对这一局面,当时有人动议历史系改名为“旅游系”或“旅游文化系”,对此,许多人私下有保留,但也没人公开反对,但张老师却在教师大会上站起来发言,主张以不改为好。这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此动议遂被搁置。张老师的坦率、冒失和学者风骨,于此可见一斑。
我和张老师之间唯一一次比较“大”的交往,已被他记录在案。在2003年10月28日写的《秦制研究》一书的“后记”中,张老师在叙述了此书出版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挫折后,说:“《秦制研究》书稿几经周折,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先生鼎力相助,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经十余载坎坷路,终赖王学典先生给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吾不胜感激之至,没齿不忘。”张老师实在言重了!
《秦制研究》一书堪称他一生心血之所寄,是他的“藏之名山”之作,他对此书的看重不亚于司马迁对《史记》的珍视。他在此书“后记”的第一句话是:“这部《秦制研究》书稿,是我二十余年来含辛茹苦之作,它凝聚着我的心血与良知。”他在自述中说:当他1981年开始有志做“秦制”研究时,曾拟订了一百多个题目,其中做成了12个题目,1987年,应一家出版社之约,他把这12篇论文整合成《秦制研究》一书,当时,正是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时刻。《秦制研究》至少先后经历了三家出版社,均未付梓。前面说了,我和张老师见面很少,大概是1997年的一天,在文史楼下碰到他了,看到他右手几个手指均缠着白纱布,脸色蜡黄,问他怎么了,他说:台湾联经要他的《秦制研究》,但必须用繁体字交稿,张老师实在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出版机会,遂夜以继日,将这部近百万字的书稿重抄了一遍,中指、食指、大拇指,为此全部磨出了血泡,没办法,他就用纱布缠上继续抄。听完之后,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之余,他的《秦制研究》书稿就这样刻在我脑子里了。2002年底,当新生的文史哲研究院筹划出版自己的“专刊”时,我想到了这部历经磨难的书稿,并推荐给了我的同事们,于是被列入首批专刊计划,并于2004年面世。此书一面世,好评如潮,震动了整个秦汉史领域,为此套“专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应该感谢张老师,因为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在继续给“专刊”创造声誉:2011年,山东大学的老校友,誉满全球的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所表扬的当世学人的唯一一部相关著作,就是《秦制研究》。
张老师走了。早在2012年初,他其实就透出了即将离世的悲音:他把学生对他的一篇访谈稿刊发在《史学月刊》上,竟题为《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等于告诉世人:孤独的、郁愤的、寂寞的他即将驾鹤远行……
张老师,您走好!天堂里也许没有人世间的“风刀雪剑”。在那里,您也可以多招点研究生——在人世间据说您只带过两个硕士生;在那里,您也可以评上博士生导师,为自己找几个学术传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在人世间是在退休之年才评上教授的,当然无缘博导,尽管谁都知道您很有学问。可谁叫您开过饭店呢,谁叫您那么耿介呢,谁叫您生不逢时呢?“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句诗是对您一生的概括吗?
2013年9月29日
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报》2013年10月9日第25期(总1909期)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张金光教授访谈
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SXYK201207002.html
逝者张金光老师简介
张金光,男,1936年12月18日出生,山东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张街村人,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取山东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秦汉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9月2日7时,因病去世。张金光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秦汉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学术研究,另辟蹊径,走创新之路。积三十余年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研究之功,力求构建一个具有独创系列范畴概念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张金光新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实践历史学”等原创性核心范畴、概念。张金光在《历史研究》、《汉学研究》(台湾)、《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三等奖多次。著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秦制研究》。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
作者王学典老师简介: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后跟随葛懋春先生攻读硕士,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2012年1月担任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