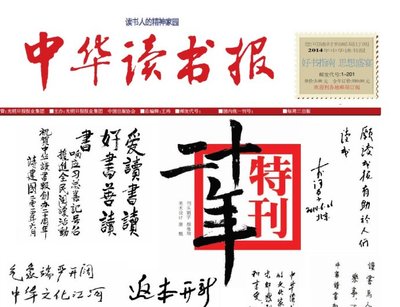
载2014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
我与《中华读书报》的文字缘
江晓原
我查阅了自己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非学术文本的不完全记录,发现我最早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文章,居然是一篇新书《我看鸳鸯蝴蝶派》的推介,发表于1997年8月27日,那时《中华读书报》创报刚刚三年。转眼又过去了17年之久,这些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写过两个专栏,接受过《中华读书报》许多次的专访和访谈,和这家报纸结下了深厚的文字缘。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写过的两个专栏,都和王洪波——他已经是《中华读书报》的资深报人了——有直接关系。
“重写科学史”专栏是一个很有追求的栏目,最初的想法,是将科学史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大众阅读文本介绍给读者。这个栏目并非我的个人专栏,栏目文章中也有别的作者。当然,因为科学史这样的学科,它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大众感兴趣的,而它的研究者却和别的学科的学者们一样忙碌,所以这个专栏很快就无疾而终。我为这个专栏写过4篇文章。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另一个专栏“幻影2004”持续了四年半,这是我的个人专栏,从2004年6月23日开始,到2008年11月26日结束,前后正好40篇文章。从专栏名称上不难推测,这是一个科幻电影的影评专栏。
这个专栏的开设,有一点小小八卦,反映了编辑王洪波和我的深厚交情。当时我正在《中国图书商报》(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上写着一个名叫“准风月谈”的影评专栏,而且已经逐渐将评论的电影集中到科幻影片上来。有一天王洪波邀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开影评专栏,我就告诉他:已经写着一个呢。由于我从1993年开始专栏写作时,就给自己订了一个纪律:不接受频度大于每月一次的专栏邀约——主要是献身精神不够,担心自己负担太重,毕竟我还有学术的“正业”要打理。即使执行这个纪律,由于我一直同时写着几个专栏,事实上有时也会达到每周一篇的频度,这已经是我自己规定的极限了。
王洪波知道我这个纪律后,却轻描淡写地说:那就把专栏移过来吧?这让我稍稍有些惊奇,他为什么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提出这种建议呢?当然是因为他有把握,知 道我会接受他的建议。于是这个《中华读书报》上的“幻影2004”专栏一写就是四年多。写到第二年时,报社曾征求我的意见,说要不要“与时俱进”地将专栏名称改为“幻影2005”?我说不要,我要一直用“幻影2004”。后来有朋友问我这个专栏名称因何而来,我告诉他,其实是从法国当年的一款战斗机“幻影2000”而来。后来这个专栏的责任编辑又换成了丁杨,我们同样合作愉快。
随着观影成为知识分子圈中的时髦之一,许多与书业有关的报刊都开设了影评栏目,其他报刊的读书版面上也出现了影评栏目。我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写“准风月谈”影评专栏时,自己刚成影迷,尚属菜鸟。我之所以逐渐将评论目标集中到科幻电影上,是因为我所见到的科幻影评,是最少让我满意的。电影评论的“专业人士”通常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所以他们通常总是像评论一般影片那样去评论科幻电影,经常不能理解或根本没有注意到科幻影片的思想性,特别是当这种思想性涉及科学史、科学哲学、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等等学科和思潮时,他们会比菜鸟还要菜鸟。所以我很快决定将自己的影评目标集中在科幻影片上。
从时间上说,“幻影2004”专栏正好伴随着我对电影“道行”的成长——在你学习一个事物时,有一个你的个人专栏和你的学习过程相伴而行,实在是一件既很有风险又大有收益的事情。收益是很容易理解的:为了要写专栏文章,你对电影就不能看过算数,仅仅满足于观影过程中的愉悦和享受,你还要思考并写作,还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风险当然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这些文字很可能有幼稚之处甚至硬伤。最近我重温了当年“幻影2004”专栏的文章,很庆幸的,倒没有发现什么硬伤。
由于《中华读书报》是一份主要面向国内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对于学者们的思想成果,一直相当重视。
2002年,以北大、清华、上海交通大学为主的一小群学者,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并在是年12月2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署名“柯文慧”的《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在社会上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一个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或“反科学文化人”的群体开始活跃登场。在后来的学术文本中,上面这篇《学术宣言》已被一些学者视为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同样署名“柯文慧”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五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备忘录》的摘要版,也以“多元科学观的浮现及其他”为题,在2007年4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
还有一件有点引人注目的事,是《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2日刊登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200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试题”。由于该试题难度甚大,当年实施的结果,成绩最高者仅得40多分(满分100),引发了《中华读书报》上持续多次的争论,有的读者投书斥之为“思想早泄”,有的读者则投书力挺。
作为一张书业报纸,《中华读书报》报的“主业”当然是书籍的推介和评论。这些年我在书评写作上堪称“勤奋”,每年都要评论数十种新旧书籍,在《中华读书报》上当然也写了许多书评。2006年我还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及全国27家相关媒体(其中包括《中华读书报》)评为全国四位“优秀书评作者”之一。
我最近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长篇书评,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我和《中华读书报》在书评方面的合作风格——力求为读者提供真实的图书评论。
有一家少儿出版设出版了一套《中国科幻名家获奖佳作丛书》,创意很好,入选的名家之作也都很好,出版社给我寄了全套的书,请我写一篇书评。可是我因为一直主张中国科幻应该“远离科普,告别低端”,不赞成由少儿出版社来出版科幻作品——这会极大地妨碍成年人阅读这些本来非常适宜于他们阅读的作品,所以我迟迟没有写这篇书评。后来禁不住出版社方面一再催促,我终于不得不写了这篇书评,但是我将上面的真实想法写了进去。当我将这篇书评给《中华读书报》时,还是顾虑重重。王洪波安慰我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接着《中华读书报》就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书评(“让科幻承担起更重大的使命吧——由“中国科幻名家获奖佳作丛书”想到的”,2014年4月19日)。出版社的编辑虽然深感遗憾,对我说“好像我们做了错事一样”,但还是表示能够谅解。
这就是我和《中华读书报》的文字缘,君子之交,淡淡如水,但静水深流,长久不绝。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