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封(George-Lou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作家,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和宣传者,原名乔治·路易·勒克来克,因继承关系改姓德·布封,1707年9月7日出生于蒙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从小接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1728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后,又学了两年医学,1730年结识一位年轻的英国公爵,一起游历了法国南方、瑞士和意大利,在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刻苦研究博物学,1733年进法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曾发表过有关森林学的报告,还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植物学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1739年当上了副研究员,并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1740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53年6月23日补已故院士桑思总主教兰格·碍·热尔日的遗缺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以后又先后被选为德国和俄国科学院院士;布封毕生从事博物学研究,1749-1788用了40年时间陆续完成36卷极具文学价值的百科全书式巨著《自然史》,其中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1749年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书中描绘了宇宙、太阳系、地球的演化,认为地球是由炽热的气体凝聚而成的,地球的诞生比《圣经》创世纪所说的公元前4004年要早得多,主张物种的可变,提倡生物转变论,提出“生物的变异基于环境影响”的原理以及“缓慢起因”论,成为进化思想的先驱,并创立了新地质年代学;1777年法国政府在御花园里给他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自然史》全书共44卷,1788年4月16日布封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编写出版了后9卷。达尔文盛赞布封“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自然演化问题的第一人”。
1753年8月25日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式上的演说——论风格:
诸位先生:
蒙你们召唤我到你们的行列里来,真使我荣幸万分;但是,只有在接受光荣的人能实副其名的条件下,光荣才是宝贵的,而我那几篇论文,写得既没有艺术,除大自然本身的藻饰之外又没有其他藻饰,我不敢相信,它们竟能使我有足够的资格,敢侧身于艺术大师之林。诸位都是在这里代表着法兰西文学光辉的卓越人物,诸位的名字现在被各国人民赞扬着,将来还要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底口里获得轰轰烈烈的流传。诸位这次属意于我,还有些别的动机:多年以来我就荣幸地属于另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了,诸位此次推选我,也就是为了对于这个学术机构作一个新的崇敬表示;我虽然对双方面都应该感激,但并不因之减低了我感激的热诚。今天,我的感激心情迫使我有所贡献,但是我怎样去尽我这个责任呢?诸位先生,我所能贡献给诸位的,不过是诸位自己所已有的一些东西罢了:我对于文章风格的一点见解,是从你们的著作中汲取来的;我是在拜读你们的著作和欣赏你们的著作之余,心里才产生了这些见解;也只有在你们的明鉴之下,我把这些见解提出来,才能获得些许成就。
历来都有一些人,善于用言辞的力量指挥别的人们。但究竟只有在明达的世纪里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真正的雄辩需要锻炼天赋的才能,具备学识修养。它与口才大不相同,口才不过是一种才干,一种天赋,凡是感情强烈、口齿伶俐、想象敏捷的人都能具有。这种人感觉得快,感受得也快,并能把所感所受的东西有力地表达出来;他们以纯粹机械的印象把自己的兴奋与感受传递给别的人们。这是单纯的官能与官能之间的语言;一切动作,一切姿态,都奔向共同目标,起着同样作用。为了感动群众,号召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一般的人来说,为了动摇他们,说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手势,一些爽利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少数神智坚定、鉴别精审、感觉细腻的人,他们和诸位一样,不重视腔调、手势和空洞的词句,那么,就需要言之有物了,就需要有思想,有意义了;就需要善于把这些物、这些思想和意义陈述出来,辨别出来,序列起来了:专门耸人视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作用,针对他的智慧说话以感动他的内心。
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串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词句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是如何漂亮,风格却是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
但是,在寻找表达思想的那个层次之前,还需要先拟定另一个较概括而又较固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只应该包含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把这些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安排到这初步草案上来,题材的界限才能明确,题材的幅度也才能认清;作者不断地记起这最初的轮廓,就能够在主要概念之间确定出适当的间隔,而用于填充间隔的那些附带的、承转的意思也就产生出来了。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跟前;凭着辨别力的高度精审,作者就能区别空洞的思想和丰富的概念;凭着长期写作习惯养成的慧眼,作者就能预先感觉到他这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只要题目稍微广阔一点或者复杂一点,则一眼就能看到全题,或者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渗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愈能借冥想之力赋予思想以实质和力量,则用文词来表现思想也就愈为容易。
这种草案还不能算是风格,但它却是风格的基础;它支持风格,导引风格,调整风格的层次而使之合乎规律;不如此,则最好的作家也会迷失路途,他的笔就会像无缰之马任意驰骋,东划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西涂一些不调和的形象。不管他用的色彩是多么鲜明,不管他在细节里散播些什么美妙的词句,由于全文不协调,或者没有足够的感动力,这种作品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结构;人们佩服作者的智慧,却很可以怀疑他缺乏天才。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写文章和说话一样,虽然话说得很好而文章却写得很差;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凭着想象力的灵机一动,起调很高,后面却接不下去;唯其如此,所以又有些人生怕一些孤立的、稍纵即逝的思想散失无存,便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许多零篇断什,然后勉强地、生硬地把这些零篇断什连缀起来;总之,唯其如此,所以七拼八凑的作品才这样多,一气呵成的作品才这样少。
然而,任何主题都有其统一性;不管主题是多么广阔,都可以用一篇文章包括净尽。间断,停息,割裂,似乎应该只在处理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或者在要写的事物太广泛、太棘手、太庞杂,才思底运行被重重障碍所间断、被环境的需要所限制的时候,才用得着。否则,割裂太多,不仅不能使作品坚实,反而破坏整体;这样写成的书,乍一看似乎很清楚,但是作者的用意却始终是隐晦的;作者的用意要想印入读者的头脑,甚至仅仅想叫读者感觉得到,都只能凭线索的连贯,意思的和谐配合,只能凭逐步发挥、循序而进、层次匀整;然而这一切,一间断就没有了,或者就软弱无力了。
为什么大自然的作品是这样地完善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先以单一的动作草创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活动,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这种成品当然使人惊奇;但是真正应该使我们震惊的却是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的迹印。人类精神绝不能凭空创造什么;它只能在从经验与冥想那里受了精之后才能有所孕育。它的知识就是他的产品的萌芽;但是,如果它能在大自然的远行中、工作中去摹仿大自然,如果它能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如果它能把这些最高真理集合起来,连贯起来,用思维方法把它们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了。
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得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意思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它们的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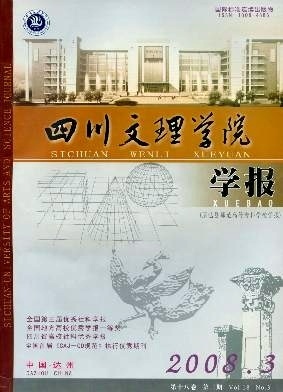
但是,只要他能先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题材所有主要的意思都集拢起来,分别主从先后排列,他就很容易看出何时应该动笔,他就能感觉到他的腹稿的成熟,急于要使它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地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热力就从这种愉快里产生,到处传播,给每一个辞语灌注生气;一切都愈来愈活泼;笔调提高了,所写的事物也就有了色彩;情感结合着光明,便更增加这光明,使它愈照愈远,由已写的照耀到未写的,于是风格就能引人入胜而且显得明朗。
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布到全文,而那些警语就像许多火星子,只是硬让许多字眼互相撞击出来的,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那都是一些仅仅凭着正反对立来显露身手的思想:作者只呈现出事物的一面,而将其余的各面一概藏到阴影里;通常,他所选择的这一面,只是一个点、一个角,作者可以在上面卖弄才情,这一点、一角离事物的广大面愈远,则卖弄才情愈为容易,而人类常情之考察事物却正是要从事物的广大面着眼的。
还有些人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这种巧思妙想就和金箔一样,只有在失去坚固性时才能获得光芒,没有比这种巧思妙想的追求更违反真正雄辩的了。因此,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得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除非这种才调本身就是主题内容,作者本意只在谐滤,没有其他目标:这样说来,谈论小事物的艺术也许比谈论大事物的更困难了。
又有些人,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比这个更违反自然美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读者不仅不赞赏他,反而要可怜他:他竟花了这样多的工夫锤炼字句的新的音调,其目的无非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个毛病是那些富于学识修养然而精神贫瘠的人的毛病;这种人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他们在字面上做工夫,他们排比了词句就自以为是组织了意思,他们歪曲了字义,因而败坏了语言,却自以为是纯化了语言。这种作家毫无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风格的幻影。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而他们只晓得涂抹空言。
所以,为了写得好,必须充分地掌握题材;必须对题材加以充分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连贯体,一根绵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他的动作。风格的谨严在此,构成风格一致性的、调节风格徐疾速度的也在此;同时,这一点,也只要这一点,就够使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了。这是天才所制定的第一条规律,如果在遵守这一条规律之外,作者更能鉴别精微,审美正确,征词选字不惜推敲,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词语来称呼事物,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如果作者再能不对他灵机初动的结果轻易信从,对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赫概予鄙弃,对模棱语、谐渡语经常加以嫌恶,那么,他的风格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最后,如果作者能怎样想就怎样写,如果他要说服人家的,他自己先深信不疑,则这种不自欺的真诚,就构成对别人的正确态度,就构成风格的真实性,这就能使文章产生它的全部效果了;不过,这也还需要不把内心深信的事物用过度的兴奋表示出来,还需要处处显得纯朴多于自信,理智多于热情。
上述各点,诸位先生,我读着你们的作品,仿佛你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这样教导我的。我的心灵,它如饥如渴地吸取着你们这些至理名言,很想飞腾起来,达到你们的高度。然而,枉然!你们又告许我,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风格必须有全部智力机能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只要耳朵灵敏一点就能避免字音的失调,只要多读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耳朵有了训练,精于审音,就会机械地趋向于摹仿诗的节奏和演说的语调。然而,摹仿从来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所以这种字句的和谐不能构成风格的内容,也不能构成风格的笔调,有些言之无物的作品,字句倒往往是铿锵动听的哩。
笔调不过是风格对题材性质的切合,一点也勉强不得;它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要看作者能否使他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作者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而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则笔调也就仿佛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并且,如果天才能一面把笔调维持在这高度上,一面又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每一对象以强烈的光彩,如果作者能在素描的刚健上再加上色彩的绚丽,总之,如果作者能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则笔调不仅是高超的,甚且是壮丽的。
说到这里,诸位先生,讲规则也许不如讲实际应用那样易于使人明了,举出实例来也许比空讲箴言更易使人获益;但是,我读着你们的著作时常使我眉飞色舞的那些壮丽的篇章,现在既不容许我——征引,我只好限于说出一些感想。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有用,而且也许是更为宝贵。
壮丽之美只有在伟大的题材里才能有。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哲学讲述并描写自然;诗则绘画自然,并且加以美化:它也画人,加以放大,加以夸张,它创造出许多英雄和神祇。历史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因此,历史家只有在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的时候,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他的一切场合,他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哲学家每逢讲自然规律、泛论万物的时候,述说空间、物质、运动与时间的时候,讲心灵、人类精神、情感、热情的时候,他的笔调是可以变得壮丽的。在其他场合,他的笔调但求能典雅、高超就够了。但是演说家与诗人,只要题材是伟大的,笔调就应该经常是壮丽的,因为他们是大师,他们能结合着题材的伟大性,恣意地加上许多色彩、许多波澜、许多幻象;并且也因为他们既然要经常渲染对象,放大对象,他们也就应该处处使用天才的全部力量,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
布封《自然史》作品欣赏
《松鼠》
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乖巧,驯良,很讨人喜欢。它们虽然有时也捕捉鸟雀,却不是肉食动物,常吃的是杏仁、榛子、榉实和橡栗。它们面容清秀,眼睛闪闪发光,身体矫健,四肢轻快,非常敏捷,非常机警。玲珑的小面孔,衬上一条帽缨形的美丽尾巴,显得格外漂亮。尾巴老是翘起来,一直翘到头上,自己就躲在尾巴底下歇凉。它们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爪往嘴里送东西吃。可以说,松鼠最不像四足兽了。
松鼠不躲藏在地底下,经常在高处活动,像飞鸟一样住在树顶上,满树林里跑,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它们在树上做窝,摘果实,喝露水,只有树被风刮得太厉害了,才到地上来。在平原地区是很少看到松鼠的。它们不接近人的住宅,也不待在小树丛里,只喜欢住在高大的老树上。在晴朗的夏夜,可以听到松鼠在树上跳着叫着,互相追逐。它们好像很怕强烈的阳光,白天躲在窝里歇凉,晚上出来奔跑,玩耍,吃东西。
松鼠不爱下水。有人说,松鼠横渡溪流的时候,用一块树皮当作船,用自己的尾巴当作帆和舵。松鼠不像山鼠那样,一到冬天就蛰伏不动。它们是十分警觉的,只要有人触动一下松鼠所在的大树,它们就从树上的窝里跑出来躲到树枝底下,或者逃到别的树上去。松鼠在秋天拾榛子,塞到老树空心的缝隙里,塞的满满的,留到冬天吃。在冬天,它们也常用爪子把雪扒开,在雪下面找榛子。松鼠轻快极了,总是小跳着前进,有时也连蹦带跑。它们的爪子是那样锐利,动作是那样敏捷,一棵很光滑的高树,一忽儿就爬上去了。松鼠的叫声很响亮,比黄鼠狼的叫声还要尖些。要是被惹恼了,还会发出一种很不高兴的恨恨声。
松鼠的窝通常搭在树枝分杈的地方,又干净又暖和。它们搭窝的时候,先搬些小木片,错杂着放在一起,再用一些干苔藓编扎起来,然后把苔藓挤紧,踏平,使那建筑足够宽敞,足够坚实。这样,它们可以带着儿女住在里面,既舒适又安全。窝口朝上,端端正正,很狭窄,勉强可以进出。窝口有一个圆锥形的盖,把整个窝遮盖起来,下雨时雨水向四周流去,不会落在窝里。
《马》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它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它驯良不亚于勇毅,它一点儿不逞自己的烈性,它知道克制它的动作:它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它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步,它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它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它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旨,人家希望它感觉到多少它就能感觉到多少,它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它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它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它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它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
以上所述,是一匹所有才能都已获得发展的马,是天然品质被人工改进过的马,是从小就被人养育、后来又经过训练、专为供人驱使而培养出来的马。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对这种动物的奴役或驯养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它们时,很少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它们在劳动中经常是披着鞍辔的;人家从来不解除它们的羁绊,纵然是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人家偶尔让它们在牧场上自由地行走,它们也总是带着奴役的标志,并且还时常带着劳动与痛苦所给予的残酷痕迹:嘴巴被衔铁勒得变了形,腹侧留下一道道的疮痍或被马刺刮出一条条的伤疤,蹄子也都被铁钉洞穿了。它们浑身的姿态都显得不自然,这是惯受羁绊而留下的迹象:现在即使把它们的羁绊解脱掉也是枉然,它们再也不会因此而显得自由活泼些了。就是那些奴役状况最和婉的马,那些只为着摆阔绰、壮观瞻而喂养着、供奉着的马,那些不是为着装饰它们本身,却是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黄金链条的马,它们额上覆着妍丽的一撮毛,项鬣编成了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
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们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既不受拘束,又没有节制;它们因不受羁勒而感觉自豪,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料;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得强壮、轻捷和 遒劲。它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质,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妍媚而已。
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犷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的,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它们一无所畏,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它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作它们的食粮,由于它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它们的食欲,又由于它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它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它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它们无需互相妒忌。
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型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如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相。相反地,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轻捷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地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并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鬣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着、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大不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的,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于它很适合。由于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天鹅》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禽兽的或人类的社会,从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鹫,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它是水禽界里爱好和平的君王,却又敢与空中的霸主对抗;它等待着鹰来袭击,不招惹它,却也不惧怕它。它的强劲的翅膀就是它的盾牌,它依靠羽毛的坚韧、翅膀的频繁扑击对付着鹰的嘴爪,打退鹰的进攻,它奋力的结果常常是获得胜利。而且,它也只有这一个骄傲的敌人,其他善战的禽类没一个不尊敬它,它与整个的自然界都是和平共处的;在那些种类繁多的水禽中,它与其说是以君主的身份监临着,毋宁说是以朋友的身份照看着,而那些水禽仿佛个个都服服帖帖地归顺它;它只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领袖,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首席居民,它赋予别人多少,也就只向别人要求多少,它只要求宁静与自由,对这样的一个元首,全国公民自然是无可畏惧的了。
天鹅的面目优雅、形状妍美,与它那种天性的温和正好相称;它叫谁看了都顺眼;凡是它所到之处,它都成了这地方的点缀品,使这地方美化;人人喜悦它,人人欢迎它,人人欣赏它。任何禽类都不配这样地受人怜爱:原来大自然对于任何禽类都没有赋予这样多的高贵而柔和的优美,使我们意识到它创造物类竟能达到这样妍丽的程度。俊秀的身段,圆润的形貌,优美的线条,皎洁的白色,婉转的、传神的动作,忽而兴致勃发,忽而悠然忘形的姿态,总之,天鹅身上的一切都散布着我们欣赏优雅与妍美时所感到的那种舒畅、那种陶醉,一切都使人觉得它不同凡俗,一切都画出它是爱情之鸟;古代神话把这个媚人的鸟说成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父亲,一切都证明这个富有才情与风趣的神话是很有理由的。
我们看见它那种雍容自在的样子,看见它在水上活动得那么轻便、那么自由,就不能不承认它不但是羽族里第一名善航者,并且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航行术的最美的模范。可不是么,它的颈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圆圆的,就仿佛是船头,冲开着波浪;它的宽广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为了便于疾驶,向前倾着,渐渐向后就渐渐高,最后翘起来就像船舳;尾巴真正是舵;脚就是宽掌桡;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轻轻地鼓起来,这就是帆,帆推着这艘活的船舶,自己漂行,自己操纵。
天鹅知道自己高贵,所以很自豪,知道自己很美丽,所以自好。它仿佛故意摆出它的全部优点:它那样儿就像是要听到人家的赞美,引得人家注目;而事实上它也真是令人百看不厌的,不管是我们从远处看它们成群地在浩荡的波涛中,和有翅的船队一般,自由自在地游着,或者是它应着召唤的信号,独自离开船队,游近岸旁,以种种柔和、宛转、妍媚的动作,显出它的美色,展开它的娇态,供人们仔细欣赏。
天鹅既有天生的美质,又有自由的美德;它不在我们所强制或关闭的那些奴隶之列。它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我们的池沼里,如果它不能享受到足够的独立,使它无奴役俘囚之感,它就不会停留在那里,不会在那里安顿下去;它要任意地在水上遍处游,或到岸旁着陆,或离岸游到水中央,或者沿着水边,来到岸脚下躲荫凉,藏到灯芯草里,钻进最偏僻的湾汊里,然后又离开它的幽居,回到有人的地方,享受着与人相处的乐趣,——它似乎是很欢喜接近人的,只要它在我们这方面发现的是它的居所和朋友,而不是它的主子和暴君。
天鹅在一切方面都高于家鹅一家,家鹅只以野草和籽粒为生,天鹅却会找到一种较精美的、不平凡的食料;它不断地用妙计捕捉鱼类;它做出无数的不同姿态以求捕捉的成功,并尽量利用它的灵巧与气力;它会避开或抵抗它的敌人:一只老天鹅在水里,连一匹最强大的狗它也不怕;它用翅膀一击,连人腿都能打断,其迅疾、猛烈可想而知。总之,天鹅似乎是不怕任何暗算、任何攻击的,因为它的勇敢程度不亚于它的灵巧与气力。
驯天鹅的惯常叫声与其说是响亮的,毋宁说是浑浊的:那是一种哮喘声,十分像俗语所谓的“猫咒天”,古罗马人用一个谐音字“独楞散”表示出来。听着那种音调,就觉得它仿佛是在恫吓,或是在愤怒;古人之能描写出那些和鸣铿锵的天鹅,使它们那么受人赞美,显然不是拿一些像我们驯养的这种几乎暗哑的天鹅做蓝本的。我们觉得野天鹅曾较好地保持着它的天赋美质,它有充分自由的感觉,同时也有充分自由的音调。可不是么,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宁可说在它的嘹唳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
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它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作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它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朝暾初上,风浪既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在自然史上没有一个杜撰的故事、在古代社会里没有一则寓言比这个传说更被人赞美、更被人重述、更被人相信的了;它控制了古希腊人的活泼而敏感的想像力:诗人也好,演说家也好乃至哲学家,都接受着这个传说,认为这事实实在太美了,根本不愿意怀疑它。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杜撰这种寓言;这些寓言真是可爱,也真是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实之上;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这都是些慰藉的比喻。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作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成语:“这是天鹅之歌!”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