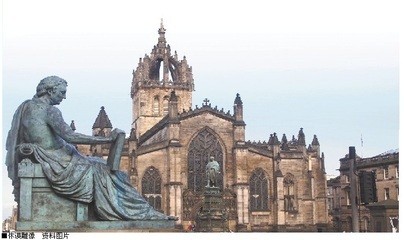1.鲧治水与共工一样是为自己部族而非为天下说
《尚书·尧典》说:“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哉!方命圮族。’”按照《尧典》的说法,鲧是在尧时发生了大洪水而被四岳推荐去治理天下洪水的。但是按照《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来看,鲧与共工氏具有同样的祸心,治水方法也相同,是危害天下人民的,并未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周语下》说:“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以此看,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鲧也是“播其淫心”,显然这不是为了天下人民,而只是为了安宁淫逸。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共工兴起了滔天洪水,危害天下人民。鲧也是效法于后,“称遂共工之过”,结果共工“以害天下”——也就是说危害了天下的人民,下场也有相似之处,共工因此灭亡了,鲧也因此被尧流放到了羽山。按照《逸周书·史记》篇的记述,共工氏是被“唐氏”消灭的[注:《逸周书·史记》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这里所说共工是因“久空重位者”而灭亡的,与上面所引《国语·周语下》所说因为治水而引起天怒人怨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治水不当引起天下其他部族方国的不满而导致了战争;而国内又是长期高官重位空缺,内忧外患,便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知道“唐氏”是尧的国族之号,这也就是说共工氏大约也是在尧时期因洪水问题而被灭亡的。而按照《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似乎共工因筑堤防而振兴的滔滔洪水是在舜的时代。如果我们笼统地说,共工造成的洪水也是在尧舜时代,只不过时代稍微早于鲧罢了。
如果说鲧和共工氏一样,都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法,而且都“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播其淫心”,“以害天下”,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鲧的治水是奉命为天下而行事的。因为,首先,若鲧是为天下治水,治水不成功也不至于被流放到羽山去。其次说鲧治水时“播其淫心”,“淫心”是指邪恶之心,治水过程中如同战争,大敌当前会有什么样的邪恶之心呢?从《周语下》说鲧“称遂共工之过”就可以知道,鲧也是“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用筑建河流堤坝的方式危害了天下人。而这里所说的“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也只能是为自己的部族方国,并非是为了天下之人。所以鲧和共工一样也被唐尧赶走到了羽山。因此笔者认为《国语·周语下》记载鲧治水有过错的情况,比《尚书·尧典》等文献说得更合理,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共工还是鲧,他们都是在洪水到来之时,为了自己的部族国家,筑建大堤来堵截洪水,以免大水冲毁自己的家园田宅。但是这样做的同时,大洪水便有了集聚的条件,以更大的更集中的流量和更凶猛的水势向下游冲去,势必给下游人们带来更大的危害。于是在天下部落联盟首领的领导下,不但灭了共工氏,紧随其后的鲧也遭到了被流放的命运。
如果说一般的部族能严守洪水来临时“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那么共工、鲧为什么不能遵守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与这两个部族的地理位置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2.共工、鲧两部族的地理位置考
共工部族的地理位置有两说,一说在东汉时的弘农。另一说在今河南辉县。前说见之于《国语·鲁语上》韦昭注云:“共工氏,伯者,名戏,弘农之间有城。”依韦昭之说,共工在东汉弘农之境,应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一带。而徐旭生先生认为共工在今天的河南辉县:“《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这就是《庄子·让王》篇内的共首、《荀子·儒效》篇内的共头,为今河南的辉县。”笔者认为,后者徐先生的说法是对的。
鲧的部族在何地呢?鲧之国名为“崇”,此名一直延续到禹承舜为天下共主称名为“夏”之前。《国语·周语上》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云“鲧,禹父。崇,鲧国。”《逸周书·世俘》篇云:“乙卯,人奏《崇禹生开(启)》三钟终,王定。”近人刘师培说:“案‘崇禹’即夏禹,犹鲧称‘崇伯’也。‘开’即夏启。”[25]鲧和其子禹建夏之前的崇国在何地呢?我们知道,“崇”实际上就是嵩山之“嵩”的异体字,其字还可作“崧”,“崇”、“崧”,是形声字,而今天所习用的“嵩”是会意字,音义全同而形体结构不同罢了。
崇(嵩、崧)国其实就是以嵩山为名命名的部族方国。其地域范围也应在今天嵩山周围一带,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嵩山之南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岗城址[26],2002年、2004年在王城岗又发现了大城遗址[27],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其年代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属于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城址[注:参见: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第3期;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文物》,1984年第2期;方酉生《田野考古学与夏代史研究》,《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笔者基本赞成这些看法,但同时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小城与大城,应分别是鲧与禹早期的都城。《礼记·祭法》孔疏引古《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说:“禹居阳城。”王城岗城址为这些古文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新证据。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后来在成为天下共主并成立夏朝之时,应迁徙到今禹州市的新砦文化遗址区域之中,也就是过去所说的“禹居阳翟”。这一点此不细说,详见他文。
虽然鲧、禹所都为阳城,但其国称之为“崇国”,就是以崇山——也就是嵩山南北一带区域范围活动,夏太康之前在嵩山以南为政治中心区,太康之后以嵩山之北作为政治中心区,但其实都是围绕着嵩山活动。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十分明显而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国语·周语下》说崇伯鲧会“称遂共工之过”?为什么后来共工之后四岳又是辅佐禹治理洪水而获得成功?原来鲧、禹所居之国与共工及其后嗣四岳之国正好处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共工、四岳之国的共国在黄河之北,鲧、禹之国崇国在黄河之南,两国夹河而立,也正好相互学习,相互协作。
3.共工、四岳和鲧、禹皆为农业部族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们也必须了解,这就是鲧、禹的崇国,还是共工氏、四岳之共国都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部族国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说明在夏代以前,人们尊奉的谷神后稷一直是姜姓的烈山氏后裔柱。共工,《山海经·海内经》谓之属姜姓为炎帝之后,《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引贾逵之说亦为共工为炎帝之后。以此可见,共工氏、四岳本来就是炎帝姜姓之后,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而著称。
而历史上的禹也是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著名的。《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明确说禹和后稷一样是因为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使自己或后人获有天下的。《诗经·鲁颂·宫》:“宫有亻血,实实枚枚。赫赫姜女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禾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禾巨。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宫》说从事农业生产的能手后稷弃是继承了夏禹的事业而成功的。
其实,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是相依为命,密不可分的。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肯定擅长于平治水土。炎姜部落被称之为“神农氏”,是说此部落集团特擅长于农业生产;而到其后共工氏子孙已经因为擅长于平治水土而被天下之民奉为土神——“后土”,就说明了从事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鲧、禹也是善于耕稼的部族,是从事农业的能手,要从事农业生产自然离不开平整土地,治理水土,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于是,在尧舜大洪水来临之际,就先有鲧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土地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而“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却“以害天下”——大大地伤害了黄河下游地区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于是,众多的部族方国在酋邦联盟首领尧舜的率领下,一举把崇国首领鲧赶跑到了东方羽山一带,意思是让他好好品尝品尝处于黄河、淮水下游屡遭洪水灾难的日子吧!流放了鲧,但面临大洪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酋邦联盟首领舜又请鲧的儿子及共工氏的后裔四岳来治理这场大洪水。有幸的是,禹已经处在洪水后期,大洪水已经平息,只剩下了疏通河道江湖,排除淤泥积水,让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他成功了,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他找到了一条比他父亲更好的治水方法才成功的。其实,是因为洪水平息后的善后工作尽管辛苦,但还是容易成功的。
不过这当中自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饱尝大洪水泛滥之苦的普天下之民看来,共工、鲧是人民的公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田地庄稼和家园,“壅防百川”,把大量的洪水排到黄河下游才使下游的部族方国饱受其害的。现在居然仍然要把鲧的儿子禹和共工的后裔四岳推举出来去治理洪水,于情于理合适吗?古人常举此事作为“举贤不避仇”来解释[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似乎是古人的一种美德。笔者并不认为此说完全合理。我认为这还要从当时的职业习惯来分析。常常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崇禹国和四岳国,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平治水土的经验,而且也应该具有比其他部族先进的农业工具,所以在大洪水肆虐之后,也只有依靠禹、四岳率领天下之民去平治水土。这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并非其他原因。
4.共工、鲧治水用壅土筑堤方式的原因
《国语·周语下》太子晋在谏其父周灵王想筑堤防保卫周都洛邑时,曾举“古训”说“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说法,但这条“古训”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也应是酋邦联盟以至后来方国联盟时期的“习惯法”,在史前尧舜时期尤其应该如此。但为什么共工和鲧这样的部族首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他们公然“壅防百川”,违反这一“习惯法”呢?笔者的回答是,这也是情势使然,迫不得已。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鲧、禹的崇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共工及后裔四岳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国家是完全需要定居的生活方式,常常迁徙就无法正常地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史前许多部族是半农半牧或半农半渔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与像共工、鲧、禹这样以农业为主要特色的农业部族就大不相同,他们可以更为频繁地迁徙,商代开国君主成汤时就有“前八后五”的迁徙之说。因此,共工和鲧面临大洪水的来临,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有“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尽管可能也知道“壅防百川”,就会使大洪水更为积聚,河道水位也急剧升高,就意味着向河道下游排放大量的洪水,对河道下游周围部族方国的危害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田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城市,不得不筑建堤坝去防止洪水来破坏住宅,破坏庄稼田地。《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淮南子·本经训》未言共工如何“振滔洪水”的,但结合前面所引用的《国语·周语下》在黄河等大河旁边用土建筑起了大坝大堤,这样黄河水流就不能自由流动,只有沿着河道飞速冲向下游,便兴起了滔天洪水,使黄河下游、淮河下游成为汪洋一片,人们爬上了丘陵高山,爬上了高树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礼记·祭法》疏引《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我们今天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城墙不大可能是从鲧的时代才开始产生的。但是可以说从鲧的时代,不仅有内城,而且修建了外城“郭”。根据战国时期《孟子·公孙丑下》所谓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可知“城”是保护城内居民和房屋住宅的,而“郭”则是保护城外郭内田地农作物的。《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就说明鲧不仅已经修筑了城墙来保护城内居民,还修筑了“郭”来保护郊区的庄稼,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特色的体现。
本文来源:中国读史网http://www.cndsw.cn/a/xianqinlishiziliao/20111019/2909.html
王青:鲧禹治水神话新探
现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事实[1]。也就是说,对于洪水神话,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osism)应该是部分适用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
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同是《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此事的: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於!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其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以看出,同是《尚书》,对此事的记载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而根据《尧典》,鲧治洪水是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尧帝曾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批准了鲧去治水。第一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很明显已经带有后世国家制度的痕迹,应该是较为后起的说法。
自从上个世纪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我们对洪水的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98年时“人不给水以出路,水就不给人以生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则著名的洪水神话,无疑会有全新的理解。
我对鲧禹治水神话的新解释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历史学的假设:我想象、理解中的鲧禹时代,黄河流域尚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是由许多部落画地而居,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是松散的联盟。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应该属于常识。第二个是音韵学上的假设,我认为鲧与共工是同名异记,鲧在上古音中属于见母文部,共属见母,工属东部,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两者的读音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这虽然是一个新观点,但我自信也并不牵强。因为并不仅仅是由于“鲧”与“共工”在读音上相近,更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事迹惊人的一致,在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证。
首先,在历史记载中,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国语·周语下》记载:“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徐旭生说,有关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和水有关[2],此说极是。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淮南子·天文篇》中的记载:“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照样是对水流东南的神话性解释。
第二,鲧是为祝融所杀的,上引《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战争且不胜。《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当然,文献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共工与颛顼的争斗,如《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篇》又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但这与和祝融战并不矛盾,因为祝融本是颛顼之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之都在今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又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颛顼号为高阳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而祝融的后裔,己姓之昆吾,彭姓之豕韦,都在或曾在濮阳住过。据此,与共工作战的主力应该是处于濮阳的昆吾与豕韦部落,他们声称自己是颛顼之后也没有错。
第三,他们的结局相同。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已是为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也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淮南子·原道》篇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第四,两人都有一个平治九州的儿子。禹是鲧的儿子是大家所熟知的,《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这里的九有、九土都是九州的意思。虽然名字与大禹不一样,但其事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同一时代有两个人都平治了九州。显然,他俩实际上是一个人。
综上所述,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的分化。洪水神话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中传播,当地民众对主人公有不同的态度。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事实我都同意徐旭生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徐旭生先生对这次洪水的研究只差一步就已经直指历史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最后一步工作。
二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下面我试图来解开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也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低的地方垫高,主要的方式是“堙庳”。这在各种记载中均无异义。堙塞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加高河道的堤防,照徐旭生的说法是类似于筑土围子一样的方法。所以,在历史传说中,鲧还是城郭的创作者。《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礼记·祭法》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说:“鲧作城。”[3]这里的城,我的理解就是护卫部落聚居地的高堤,目的是抵御洪水。
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淮南子·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为什么用“堙“的方法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呢?我们来看看鲧(共工)部落所在的地域。
共工部落的聚居地当在共地。上古称为共的地名和国名共有五处。即:1、《路史后记·共工氏传》云共工氏建国在莘、姺之间,在今河南陕县境内;2、《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2、《中山经》说:“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水经注》卷四《河水下》引此文,并说:“今诊蓼水,川流所趋,与共水相扶”,是以蓼水为共水,在今山西西南隅,芮城县境内。3、《中山经》次六说:“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水经注·洛水下》曾引此文。地在河南新安县境内。4、《诗·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个共可能在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5、《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其地为今河南省辉县[4]。
徐旭生的看法是共地在今辉县境内,此地有入河的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黄河在此处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后来共水竟成为一公名——洪水[5]。这个说法有很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历代水患全是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缺点是:除了《汉书》这一后起的材料之外,共工居辉县,没有其他的材料作为佐证。
如果将鲧与共工视为一人,那么,我们的材料会更多一些,线索也会更多一些。鲧的封地在崇,这是古代文献中较为一致的记载,只不过这个崇倒底在什么地方,却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这个“崇”是崇山,今名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第二种是崇侯虎之崇国,在今陕西鄠县东,此崇为商之属国,与鲧并无关系,已是定论,可置不论。第三是赵穿所侵之崇。《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此地虽说不能确指,但王夫之《稗疏》云:“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这种说法是非常可信的。渭北之晋地为什么会有“崇“这一地名,大概是鲧部落的的迁居有关。虽说鲧是禹的父亲有些可疑,但鲧与夏族必然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大夏故墟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所以,一般认为在鲧与禹之时,夏人有过一次迁徙,从河南的伊洛地区迁居到了山西的西南部。
据此,我觉得鲧部落之聚居地以与芮城境内之共水为是。“赵穿侵崇”之崇地应该不出芮城之范围。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之一东下冯遗址离芮城甚近。芮县北部的永济、运城、侯马、闻喜、新绛、襄汾、绛县、临汾,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6]。鲧在芮城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
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三个河段,即河口镇至龙门间(简称河龙间);龙门至三门峡间(简称龙三间);三门峡至花园口间(简称三花间)。这三个区间产生的洪水是构成下游洪水的主体。上述三个不同来源区的洪水,组成花园口站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一是以三门峡以上的河龙间和龙三间来水为主形成的大洪水(称为上大洪水)。如1933年洪水,陕县站实测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1843年大洪水,据调查估算陕县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这类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对下游防洪威胁严重。二是三门峡以下三花间来水为主(称为下大洪水)。如1958年花园口站实测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和调查的1761年花园口站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这类洪水的特点是涨势猛、洪峰高、含沙量小、预见期短,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三是以三门峡以上的龙三间和三门峡以下的三花间共同来水组成(称为上下较大洪水)。如1957年及1964年洪水,花园口站流量分别为13000立方米每秒和9430立方米每秒。其特点是洪峰较低,但历时较长,对下游堤防威胁也相当严重[7]。因此,如果在这一区段内堵塞支流不让其泄洪的话,对下流的危害可想而知。
那么,祝融部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他的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所居住的地域散布很广,大致上包括今之河南许昌县、濮阳县、温县、范县、山东定陶县(祝融部落董姓之鬷夷族所居)、邹县,莒县、江苏徐州(彭姓氏族)等地,最远达到湖北。古代的黄河在下游地区分为东西二渠从豫北向东北方向流入海。东渠在濮阳以北的内黄县。今县内有黄河故渎,这条故渎虽然不一定是夏商时期的河道,但夏商河道当距此不远。所以,祝融八姓基本上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8]。
据传说,共工堙堵洪水之后,受害最大的是空桑,空桑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载有空桑,其云: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陀。
《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曰:“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揄冈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郝懿行说还有一个空桑在赵、代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地方称为空桑。1、在莘、陕之间。2、在陈留。3、在兖州。4、在赵、代之间。我认为以陈留说为是,亦就是莘地,在今定陶附近。此地的西北是温县、北面是濮阳、范县,西南是许昌,东北为定陶、邹县,东南为彭城,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祝融八姓诸部落的中心地区。洪水振薄空桑,受害最大的无疑是祝融部落。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起兵攻打处于上游之鲧(共工)部落,最后将其流放。
鲧所流之地为羽山。羽山何在?《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计其道里不相应,似非也。”吴任城注:“《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十道志》:‘羽谭一名羽池,东有羽山’。《郡国志》云:‘钟离泳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饮。’刘会孟曰:‘淮安赣榆县有羽山。’《经》所记,未详是非。”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居住在最东面的祝融八姓所控制的区域,似以郯城县为是。
综上所述,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融氏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3](P61-66)。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尧舜时大洪水及其涉及范围考辨
从先秦古文献来看,尧舜时发生了一场历史千年难遇的大洪水。从《诗经》、《尚书》到战国秦汉文献,有不少史籍就追溯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3]《诗经·商颂·长发》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3]《尚书·尧典》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氵巳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4]《孟子·滕文公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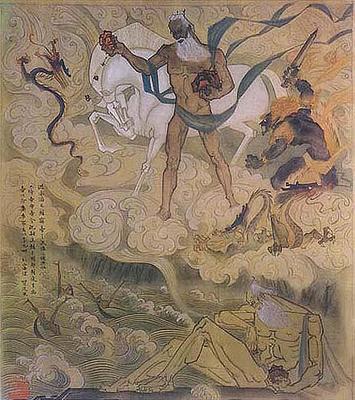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4]《孟子·滕文公下》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5]《庄子·天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6]《山海经·海内经》
洪泉极深, 何以填之?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7]《楚辞·天问》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8]《吕氏春秋·爱类》
(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邱陵、赴树木。[9]《淮南子·本经训》
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9]《淮南子.览冥训》
《墨子·七患》引《夏书》云“禹七年水”,另外《书序》、《庄子·天下》、《吕氏春秋·古乐》、《论语·泰伯》、《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皆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新近发现的燹公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有关事迹,其铭云:“天令禹敷土,堕山氵睿川,乃差地设征”。这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致相近,也与《书序》、《尚书·益稷》、《诗经·商颂·长发》等篇的说法相似。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也记述了这场历史上的大洪水及其大禹治水的过程:
……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居,水潦不氵皆,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第24简)……面干腊[注:上两字原整理者未释读。“干”字本从“”、“旱”声,应是旗杆之“杆”的本字,此可读为“干”;“腊”本从“鱼”、“昔”声,此可读为“腊”,“腊”本为干肉,此句“面干腊”是指面部干燥皱裂。],胫[注:“胫”原整理者未释。此字从“”从“”声,可读为“胫”。]不生之毛,□□氵皆流,禹亲执木分(畚)耜,以陂明(孟)诸之泽,决九河(第25简)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居。禹通淮、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居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第26简)海,于是乎(?)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伊、洛,并里[廛]()、干(涧),东(第27简)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居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居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第28简)汉以北为名谷五百。[10]
可见尧舜时代的大洪水,从西周时代的文献《诗经》、《尚书》开始,到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都有大致相似的说法。不过20世纪前半世纪徐旭生在仔细考察这场大洪水时,作结论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境内。余州无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11]187对此说笔者是不赞同的。
首先此说与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的记述是不相符的。《尚书·禹贡》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都提到了“九州”,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是九个不同的州。有的学者结合考古发现所见龙山时期的文化区系,以为《禹贡》所说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12]。其实在后代不同地域不同方国的人们都承认禹治理洪水的情况。《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是西周时殷后裔宋国人的作品[13],说明商遗民承认禹治水并扩大疆土的情况;齐叔夷钟铭云:“()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14]《殷周金文集成》272-278春秋时居于东方的叔夷也称自己的先祖成汤统一天下,也居住在禹平水土之上;春秋时秦公簋铭云:“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宅禹责(迹)。”[15]《殷周金文集成》4315春秋时居于西陲陕甘一带的秦人自称自己“受天命”的先祖居住在“禹迹”;《诗·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梁山”盖即今陕西韩城市西北黄龙山,可见西周时韩国承认禹治水已到达梁山一带;《诗·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此地今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诗·小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依朱熹集所说“终南山也”,说明西周时居住在关中终南山一带的周人也相信禹治水已到了这一带。《国语·鲁语下》述孔子之语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会稽山在今天浙江北部,说明禹的活动踪迹已到达浙北一带。上述古文献材料都是比较早的,可见西周春秋时的人们都相信禹治水的故事,其地域分布相当广泛,已基本接近《禹贡》与《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所说的“九州”地域。
其次,这场大洪水不仅我国古文献记载是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注:《圣经·创世纪》第7章也有这样的记述:“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大地上。”挪亚和他的妻子乘坐方舟,在大洪水中漂流40天以后,搁浅在高山上。为探知大洪水是否退去,挪亚连续放了三次鸽子,等第三次鸽子衔回橄榄枝后,说明洪水已经退去。也说明挪亚时的大洪水也是一样凶猛(《新旧约全书》,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第6页)。],可见这应该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从新近考古发掘所见的新石器晚期洪水遗迹情况来看,这些传说确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不管是在中原地区还是黄河上游下游,抑或是在长江下游,近来的考古发现都可为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
在相当于尧舜时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遭受到大洪水袭击的有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王城岗有东西排列的两座城,其西城被来自西北部王尖岭下来的山洪冲毁,城内冲沟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东城则是被五渡河河水暴涨冲毁的[16]。
同样,地处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也是在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期之前遭到明显的被毁的迹象。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龙山城内的低凹地开始出现比较厚的淤积层,城墙的坍塌与兴建与造成这些淤泥层的洪水有关。(1)孟庄龙山城址的城垣东西北三面都经过重新发掘,估计当时的城墙高度当在4米左右,但该墙在二里头时期东墙内侧保存的高度仅为1米左右,在西墙内侧仅有0.5米高,因为在这两墙内侧都发现有二里头夯土修补的痕迹,同时北墙外侧也有修补的夯土,这是二里头文化筑城之前受洪水或大量雨水冲刷的结果。(2)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3米左右。东、北、西三面墙发掘10余个探方、探沟的资料表明,内侧壕沟中淤积厚1.5米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陶片的淤土。此外,南、北面护城河的发掘表明,护城河与之同样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雨水造成的。(3)孟庄龙山城被毁于洪水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时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经探出部分有15米宽,从已经发掘的Τ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走,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的陶片。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这说明该缺口是在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而且孟庄遗址的低洼处都是洪水淤积层,城垣坍塌,西墙中北部被洪水冲开一个15米以上的大缺口[17]。
处于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发生的重大灾变现场,经地学考察,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和沉淀物,且遗址内还找到多次地震遗迹。地层关系表明遗址内先遭地震,后有洪水,洪水形成的地层叠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上[18]。这为尧舜时大洪水的猛烈性、突然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其范围是相当广泛,不仅发生于黄河下游,连上游的青海地区也遭受其害。
良渚文化晚期的居民曾因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有些学者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1米以上。在芙蓉湖、氵鬲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湖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19]。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特别是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在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2—3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10—15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T25(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20]。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遭受到了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正如俞伟超先生所分析的:“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经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21]
从上面所列举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确有一个气候异常的大洪水时期。这也与今天气象学研究成果一致,距今5 000-40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降雨量最多的时期[22]。这场大洪水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和古文献所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及其禹治理洪水所涉及的区域几乎差不多。可见过去徐旭生先生所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的说法是不对的。
本文来源:中国读史网:http://www.cndsw.cn/a/xianqinlishiziliao/20111019/2910.html
周克庸:月神原型为玄冥说
在华夏远古神话中,月神的形象主要有三种。《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王逸在注文中训“顾菟”为“顾望之兔”,此乃月神为兔形之所本。《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无“托身于月”以下12 字),此乃月神为女子形、为蟾蜍形之所本。
兔、姮娥、蟾蜍,表面看殊难联系,然究其源,则可发现,此三者统统是华夏神话系统中更为远古的月神原型——龟蛇一体的玄冥意象之讹裂。
一、在上古音韵中,顾菟、恒(俗字作“姮”)娥、蟾蜍等字,与龟、鼋、它(蛇)等字之间,存在着读音—假借方面的联系。
“顾菟”与“龟它”音近(顾/龟:鱼之旁转,见母双声;菟/它:鱼歌通转,透母双声),故可通假。自王逸肇始,诸家咸以“兔”训“菟”,而对“顾” 字的说解,则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要皆以未解“顾”即“龟”字之假借 ,“菟” 即“它”字之假借也。
“恒娥”与“龟鼋”音近(恒/龟:蒸之对转,匣见旁纽;娥/鼋:歌元对转,疑母双声),故可通假。汉时避文帝刘恒讳,将恒娥改为常(俗字作“嫦”。恒、常二字音义相近)娥。又据纬书,嫦娥小字纯狐,而“纯狐”二字,在读音上亦与“它龟”相近(纯/它:文歌旁对转,禅透准双声;狐/ 龟:鱼之旁转,匣见旁纽)。
“蟾、蜍”二字及其切音,皆与“它”音近(蟾/它:谈歌通转,禅透准旁纽;蜍/它:鱼歌通转,禅透准旁纽;蟾蜍二字切音/它:鱼歌通转,禅透准旁纽),故可通假。闻一多《天问释天》云:“盖蟾蜍与兔音易混,蟾蜍变为蟾兔,于是一名析为二物,而两设蟾蜍与兔之说生焉。”从音韵联系上考虑问题,是闻先生高明处。惜乎,闻先生未能进一步看出,蟾、蜍、兔,皆为“它”字读音的讹变,故其对“顾菟”的说解,终归难以令人折服:蟾蜍与兔,前者为源后者为流的纵向发展关系,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支持,此其一;其二,即使此说对“菟”字的说解能讲通,其“顾”字作何解释,仍毫无着落。
二、顾菟、恒娥、蟾蜍与龟蛇存在着若干文化意象方面的曲折联系。
先说顾菟与龟蛇的意象联系。夏人“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篇》)。早有学者指出,夏祖鲧的氏族图腾为三足鳖。我赞同此说,并据有关考证认为,鲧的儿子大禹,为了便于同工共氏的后人大岳联手,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一则平治水患,一则积蓄与舜相对抗的力量以最终取而代之),采用了龟蛇一体的“玄冥”形象为两大集团的联合图腾。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龟蛇崇拜成为夏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夏有顾国,而顾国以“巳”为姓(“顾、龟”二字音近,“巳”字则是蛇的象形),——是国名与姓,恰恰是一龟一蛇。由此可以窥见,该国与“玄冥”在文化意象上的曲折联系,亦可证明,训“顾”为“龟”并非向壁虚构。
训“菟”为“它” ,佐证其夥。仅举数例: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虫状如菟。”——不称“兽”而称“虫”(《说文》:“它,虫也。”“虫”即“它”的古称),可见,此“菟”不是“兔”而是“它”。
《吕氏春秋·离俗》:“飞兔……,古之骏马也。”《宋书·符瑞志》:“飞菟者,神马之名也,日行三千里,禹治水,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应其德而至。”——禹非游牧部落首领,有关禹的较为原始的治水神话中,亦未见有天降神马的内容,倒是有龟蛇辅佐大禹治水的记载(晋玉嘉《拾遗记》卷二:“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所以,此“飞菟”者,实即“飞它”, 亦即“螣蛇”(《山海经·中山经》云,柴桑之山多“飞蛇”, 郭璞注:“即螣蛇,乘雾而飞者”)。
《淮南子·说山》:“千年之松,下有获苓,上有兔丝。”——兔丝又作“菟丝”,即女萝,一年生缠绕寄生草本植物。其叶退化,其茎虬曲蟠绕与蛇形相近,而与兔形无干。故“菟丝”即“它丝”亦即如蛇之丝也。
《搜神记》卷六:“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之象也。”——视龟兔变异为“兵甲将兴之象”,实源于“旐”旗的文化意象。“旐”是一种绘有龟蛇图案的旗帜(《周礼·春官·司常》:“龟蛇为旐”),从《诗经》描写的情形看,这种旗帜常常被用于率军出征、出猎及凯旋之类的场合(如《小雅》中的《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旌矣”,“出车彭彭,旂旐央央”,《采芑》:“其车三千,旂旐央央”,《车攻》:“建旐设旄,搏兽于敖”;《大雅》中的《桑柔》:“四牡骙骙,旟旐有翩”等),故“兔生角”之“兔”,当是“它”字在口口相传中的讹变。
另外,虎有“於菟”之古称,在晚近隐语中,也仍有称虎为“白额菟”者(见《绮谈市语》)。——虎与兔向无攀扯,而虎与蛇却有着共同的名称:蛇,一称“虫”,至今蛇仍被唤作“长虫 ”, 而虎则有“大虫”、“班(斑)虫” 之名。由此亦可看出“菟”乃“它”之讹变。
次说恒娥与龟蛇的意象联系。汉代大量以“奔月”为素材的画像石刻,其恒娥形象多有呈“蛇躯”者,这应当是恒娥为蛇属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之一。
《楚辞·天问》:“帝降夷弈,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羿既受帝命降抚夏民,却恃强凌弱,竟用箭射夏人崇仰的河伯(夏祖玄冥为水神,河伯亦水神),且霸占雒嫔,是大不道也。但强扭的瓜不甜,被羿强娶为妻的雒嫔,必然要与羿离心离德(恒娥窃不死之药弃羿奔月的神话,当由此衍生。雒嫔奔月而称恒娥,盖因“恒”乃是上弦月这一月相的名称)。据王逸的注文,雒嫔为“水神,谓宓妃也”,即后世名声大著的洛神。——从雒嫔的神格特征看,其原型应为龟鳖之属。其证有三:其一,“宓”与“鳖”音近(质月旁转,明帮旁纽 ); 其二,宓妃为水神,而夏人的水神为鳖,为龟蛇一体的玄冥;其三,宓妃为洛水之神,而传说中的那部神秘的《洛书》,恰恰是由洛水中的“神龟负文而出”(见《洪范》伪孔传),洛水还因此得了个“龟津”的别号(《全唐诗》卷四十六《宋楚客》残句:“采旗临凤阙,翠幙绕龟津”)。
玄冥为水神,而恒娥(作为育龄妇女)则有“信水”。以科学眼光看,此水固非彼水,但在以联想律为特征的原始思维中,这毕竟为将二者相比附提供了某种依据。综上,可以证明将姮娥的原型定为玄冥,不是无根之谈。
最后说蟾蜍与龟蛇的意象联系。汉代“奔月”画像石刻中,既有蟾蜍,亦有似蟾蜍而实非蟾蜍者(其状体圆而具四足,前有首后有尾,俨然鳖鼋之形)。由于鳖鼋与蟾蜍在初民心目中归为一类(统称之“黾”)且二者之形相似易混(甲文中“鼋”、“黾”二字殊不易别,可为佐证),故在原始艺术中,鳖鼋、蟾蜍常常相混同。后于奔月图画中,竟蟾蜍之形兴而鳖鼋之形替矣。
《通俗编》:“俗言虾蟆惟月中者三脚,因有‘三脚虾蟆无处寻’之谚”。《述异记》卷上:“古谓蟾三足,窟月而居,为仙虫。”——此“三脚虾蟆”、三足蟾的形象,实由夏人祖先鲧的图腾“能”即“三足鳖”化来。《国语·晋语》记叙鲧的传说曰:“昔有鲧违帝命,殛之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所谓“黄能”者,即鲧的氏族图腾“三足鳖”是也(《尔雅·释鱼》:“鳖三足,能”)。
三、月亮与龟蛇之间,亦存在着许多可用以比附的联系。
其一,“月、鼋”二字古音相近(月元对转,疑母双声 )。又,神话中的御月之神,名曰“望舒”, 此二字与“黾它”古音相近(望/黾:阳部叠韵,明母双声;舒/它:鱼歌通转,审透准旁纽)。
其二,上弦趋圆之月相曰“恒”(《诗经·小雅 ·天保》:“如月之恒”,其笺曰:“月上弦而就盈”),而恒、龟二字古音相近(蒸之对转,匣见旁纽)。又,每月初一、十五之月相称朔、望 ,此二字分别与蛇、黾二字古音相近(朔 /蛇:铎歌通转,山床旁纽;望/黾:阳部叠韵,明母双声) 。
其三,月亮圆缺盈亏相循,若死而复生,故屈原曾在《天问》中称月有“死则又育”之德;而龟蛇或永寿或蜕皮或冬眠,亦有“长生不老”、“死而复生”之象,所以在初民眼中二者有相通之处(此种观念不独存在于华夏上古文化之中,人类文化研究巨著《金枝》一书的作者詹·乔·弗雷泽曾指出,在许多民族的原始神话中,都有以月亮与蛇、蟹关系为情节的,有关长生不老或死而复生的传说,其“根据”亦源自月亮的圆缺相循与蛇、蟹的蜕皮相比附。——参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一书,第一章第二节)。
其四,《淮南子·天文训》:“方诸见月,津而为水”,其注曰:“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盈时以向月下,则水生。”《吕氏春秋·精通》:“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盛;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可用来从月中取水的器具“方诸”以“大蛤”为之;蚌蛤之实虚盛亏随着月相之变化而变化。这足以证明,在古人心目中,蚌蛤与月亮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上古神话系统中,具有“百介之灵”和“月神”双重身份的玄冥,在蚌蛤与月亮之间充当了中介环节:一方面,龟既是“百介之灵”,蚌蛤之类便理应对其最高统帅亦步亦趋。也正因为此,充当阴燧的大蛤,才被命名为读音与“鳖它”相近的“方诸”(方/鳖:阳月通转,帮母双声;诸/它:鱼歌通转,照透准旁纽);另一方面,玄冥为月神,月相变化由玄冥所操纵,因此,蚌蛤等百介之属,随着月亮的圆缺变化而虚实盛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四、在性征方面(包括客观性征及其由神话所折射的、在原始思维中所呈现出的性征),玄冥与月亮存在着大量的“相似点”。
概括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资料,龟蛇一体的玄冥,乃主寒、色黑,位在北方之水神。玄冥的这些神格性征,皆可从月亮的性征中找到“相似点”。
玄冥为水神,而月亮则与水颇多关涉。丁晏注《天问》引王充《论衡》曰:“夫月,水也。”《书钞》一四九引傅玄《拟天问》曰:“月为阴水。”此种认识,当源于先民对月相与气象特定联系的长期观察,由此取得的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经验,经原始思维之升华,便定格在了月亮“掌管水旱”的神秘力量之中。《开元占经》引诸书云:“月初生小而形广大者,月有水灾”(引《荆州占》);“月先行离于毕,则雨”(引《春秋纬》);“月晕辰星,在春大旱,……在秋大水”《引《海内占),是其证也。
又,《周礼·秋官》列有“司烜氏”之职,专司“以鑑取明水于月”。古人认为“明水”(实为夜间生成的露水)生于月,“司烜氏”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以鑑从月中取明水来供祭祀时使用。所谓“鑑”,即前文提到的“方诸”, 因常与聚焦日光以取火的凹面铜镜“阳燧”对举故又被称为“阴燧”,是专门用来“取水于月”的器具(《淮南子·览冥训》曰 :“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王充《论衡·乱龙》曰:“铸阳燧取飞火于日,作方诸取水于月”)。可见,在古代文化中 ,“月” 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玄冥位在北方,而月亮与“北”这一方位也有着多重间接联系。在古代比附式思维的分类系统中,日为“阳”、为“火”、为“君”;月为“阴”、为“水”、为“臣”。而在古华夏文化的奇特构架中,“阴”、“水”、“臣”又皆与“北”这一方位相对应。如《汉书·天文志》集注引孟康云:“北为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曰:“北方者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北极,雨府也”;《后汉书·班彪传》注云:“北面,谓臣也”,——既已知月之征象为阴、为水、为臣,又已知阴、水、臣皆与北方相应,则月亮与北方的底层关系也便昭然了。
玄冥主寒,月亦属寒地。在古代诗文中,月亮向有“冰鑑、冰镜、冰轮、寒兔、冰蟾、霜蟾”等雅号,此当源于日行于昼而热,月运于夜而冷的常识,自不待多言。这一常识在神话中的反映,则是将月亮归于寒地。《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东方朔《十洲记》,称月亮按时节在广寒宫内韬养其光(“冬至后,月养魄于广寒宫”);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则以“广寒”为月中宫阙之名(“明皇游月宫,见榜曰‘广寒清虚之府'”)。此二说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将月亮与“寒” 联系在了一起。
玄冥色主黑,月与“黑”的关系则是明摆着的,所以,月又被称为“夜光”(《博雅》:“夜光谓之月”)。另外,在月亮“死则又育”的神话传说中,月亮正是在黑暗达到极致时,才摆脱死亡而重获新生的,所以,《释名·释天》对月相“朔”字的解释,是“苏也,月死复苏生也”。
五、通过对相似相关点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玄冥不仅与月亮相符度最高,而且恒娥、蟾蜍、顾菟,也都是通过玄冥这一中介,才与月亮发生联系的。
比较月亮、玄冥、恒娥、蟾蜍、顾菟的相似相关点,可以列出一张附表(参见下面的“附表”)。
通过比较下表所列的各项性征,我们可以发现:(1)玄冥与月亮的相符度最高,而恒娥、蟾蜍、顾菟与月亮的相似、相关点,未有一项能超出玄冥与月亮相似、相关的范围。这一事实表明,月神的原型正是玄冥。(2)恒娥、蟾蜍、顾菟与玄冥的相符度,都超过了它们各自与月亮的相符度,就是说,此三者除了具有某些既与玄冥相符、又与月亮相符的相似、相关点之外,还各自具有某些与月亮无关而仅仅与玄冥相符的相似、相关点。而这一事实,则一方面表明恒娥、蟾蜍、顾菟是较玄冥晚出的月神,一方面表明,此三者正是借助玄冥这一“中介”,才与月亮搭上关系的。
综上,笔者认为,华夏古神话中的月神,其原型,乃是鼎盛于夏代其后逐渐渗透于中原底层文化中的、以龟蛇合体为形式的玄冥意象,而如顾菟者、恒娥者、蟾蜍者,皆为玄冥意象之讹裂;至于玉兔、嫦娥及伐桂吴刚之类后出的月神形象,则更为讹裂后的诸意象之流裔耳。附表:
月亮 | 玄冥 | 恒娥 | 蟾蜍 | 顾菟 |
阴 | 阴 | 阴 | ||
死则又育 | 长生永寿 | 窃不死药 | ||
与水有关 | 水神 | 信水(月经) | 水陆栖 | |
与北方相应 | 北方之神 | |||
冰鑑、广寒宫 | 主寒之神 | |||
运行于夜 | 主黑之神 | |||
主蚌蛤实虚盛亏 | 百介之灵 | |||
月水以方诸收取 | 方诸鳖它音近 | |||
月相:恒 | 龟恒音近 | 名称:恒娥 | ||
月相:望朔 | 望朔黾蛇音近 | |||
御月之神:望舒 | 望舒黾它音近 | |||
名称:月 | 月鼋音近 | |||
龟它 | 纯狐它龟近 | 顾菟龟它音近 | ||
龟,三足鳖 | 娥鼋音近,宓妃龟鳖属 | 三足虾蟆 | ||
它,蛇冬眠 | 蛇 躯 | 蟾蜍它音近 冬眠 | ||
王八、乌龟: 性侮辱隐语 | 兔崽子:性侮辱隐语 |
行文至此,又检得二证:其一,《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王逸注曰:“呼太阴神使承卫也。”——玄武即玄冥,太阴即月亮。是王逸早已明言,玄武即月神。其二,《开元占经》卷十八:“巫咸曰:‘……日为朱鸟,月为玄武。’”——是在较晚近的传说中,也还一直保留了玄武为月神的说法。有此二证,则以玄冥为月神的观念,在华夏神话中,可谓源远流长矣 !
六、附论:龟蛇意象的产生决非始自汉代,其渊源可上溯到鲧禹时期。
关于龟蛇意象产生的时代,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是“西汉说”,如许道龄认为:“玄武又为灵龟的别名,故西汉中叶以前,世人都以灵龟为他的象征,后来因为民间相信龟蛇为雌雄二物,故以‘龟蛇合体'代替之”(《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载前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五期);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写道:“所谓‘玄武',自汉代起人们一般认为是龟蛇合体的一种灵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9页);《中国神仙传》亦称:“西汉中叶以前,人们都以灵龟为玄武象征 ,……到了西汉末年,又加上一条蛇”(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5页),等等。但也有学者认为,龟蛇意象产生的年代要久远得多,如孙作云在《敦煌画中的神怪画》一文中考证,鲧为鳖氏族酋长,死后化为三足鳖,其妻为蛇,龟蛇一体即玄武图上的龟蛇交尾之象(参阅《考古》1960 年第 6 期)。另外,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也持此观点(其后,何氏又在其《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认为,玄武乃是受有如蛇头龟身的幼鳄形象激发,由“汉代人的想象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怪物”)。
我们认为,龟蛇意象的产生决非始自汉代,其渊源可上溯到鲧禹时期。当然,要论证这一点,非本文篇幅所能胜任,这里,我们仅举出若干较为显豁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论点。
1、《诗经》中的有关诗句表明,诗经时代,绘有龟蛇图形的“旐”旗,不仅仍经常被用于出征、出猎等场合(例句见本文第二节),而且甚至还被用于占梦:“牧入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小雅·无羊》)。——大意是说,牧人梦见蝗虫变成了鱼,旐旗变成了旟旗(“旟”为绘有鸟隼图形的旗帜)。“大人”为他占梦说:蝗虫变鱼意味着丰年,旐旗变成旟旗则意味着子孙众多。——连牧人都以旐旗入梦,可知此物为当时世人所熟见,亦可知龟蛇意象决非始自汉代。
2、《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焉有虬龙,负熊以游?”。此二问皆与鲧的传说及龟蛇意象有关。“鸱龟”二字,旧训多不得要领。“鸱”不应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某种禽类,它不过是对口耳相传的某个词的读音的记录罢了。鸱、它古读相近( 脂歌旁转,穿透准双声),故“鸱龟”即“它龟”;因它、弟二字古音亦相近(歌脂旁转,透定旁纽),所以这一形象又称“弟龟”(见金文徽号文字“弟龟”,——其蛇、龟二形一目了然);因弟、吊二字古音相近且字形易混,故“弟龟”又演化为“吉吊”。“吊” 即“弟” 即“它”,“吉” 读作“介”( 质月旁转,见母双声 )即“甲”,所谓“吉吊”也就是生有甲壳的蛇(李时珍《本草纲目》引裴渊《广州记》及《太平御览》:“吊,蛇头龟身”)。所以,鸱龟、弟龟、吉吊,都是龟蛇意象的变形而已。虬龙负熊,与鲧的化生传说(一说鲧死化龙,一说鲧死化能)有关。“虬龙”是蛇的美化,“熊”是“能”(三足鳖)的讹变。龙负熊即蛇负龟,——仍是龟蛇意象的变形。
《楚辞·招魂》状幽都主司“土伯”之形,既称其“九约”,又称其“敦脄”(《章句》:“敦,厚也;脄,背也”),更称“其身如牛”。王逸训解说,土伯“其身九屈”,“广肩厚背”,“身又肥大,状如牛也”。王说殊不可信:既有弯弯曲曲的躯干,又何来“广肩厚背”之肥牛形?其实,土伯之形乃由龟蛇意象化出:“九约”状其蛇之头尾,“敦脄”状其龟背;而所谓的“牛”,也不过是“能”字的读音讹变罢了(牛/能:之部叠韵,疑泥邻纽)。
3、据鲧的化生神话,鲧死后化为龟鳖(《国语·晋语》:“昔鲸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化为龙蛇(《山海经》郭璞注引《开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化为禹(《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表层结构,却曲折地反映出了龟鳖、龙蛇和禹的三位一体:一方面,三者共同体现着鲧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三者又是治水事业的整体符号,龟鳖象征治水中的“堙”法(“玄龟负青泥于后”,青泥即“息壤”),龙蛇象征治水中的“导”法(“黄龙曳尾于前”),而禹则是运用堙、导诸方法平治水患的人格化代表,——就是说,龟蛇即禹,禹即龟蛇。这一关系,从禹的名字中亦可看出:“禹”字从虫,虫即蛇。从金文看,“禹”字正像有足、有膨起之腹部的蛇形。如将“禹”字同像蝎子之形的“万”字作比较,这点会看得更其清楚。因此仅训禹为“虫”还不够准确,只有把禹训为龟形“虫”,才算把握到了关键处。与字形相表里,禹字的古读音也恰与鼋、龟相近(禹/鼋:鱼元通转,匣疑旁纽;禹/龟:鱼之旁转,匣见旁纽)。这一切概由“巧合”来解择,是难以说通的。
4、《山海经·海外北经》:“蛇巫之山,……一曰龟山”。众所周知,地名有极其稳定的承传性,在远古时期尤其如此。因此,蛇巫之山又称龟山的记载表明,龟蛇并提及龟蛇一体意识的产生,必远远早于《山海经》成书的时代。
另外,《山海经》一书,所载龟蛇意象的“变体”,尤为多见。仅举二例如下:
1)《大荒南经》云:“有蜮民之国,……射蜮是食。有人方扞弓射黄蛇。”“蜮”为水物(即后世传说善“含沙射影”者),古音与龟相近(职之对转,匣见旁纽),当是“龟”的讹变。经文既称有蜮民“射蜮”, 又称其“射黄蛇”, 可见,“蜮”即“黄蛇”,——此处“黄”非指颜色,而是龟或鼋的通假字(黄/龟:阳之旁对转,匣见旁纽;黄/鼋:阳元通转,匣疑旁纽),所以,“黄蛇”应读作“龟蛇”或“鼋蛇” 。有趣的是,清光绪二十一年立雪斋印本《山海经存》的“蜮人”插图中,“蜮”的形象恰恰作鼋蛇合体状。
2)《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东经》:“雨师妾,……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禺彊即玄冥,玄冥即鲧即三足鳖,故禺彊珥蛇、践蛇的传说,亦为龟蛇意象之变体。雨师也是指玄冥,“雨师妾”即“玄冥妾”,玄冥之妾操蛇、践蛇,自是龟蛇意象之变体。至于雨师妾“操蛇”和“操龟”的不同说法,则更透露了在最古老的原型中雨师妾龟蛇一体的消息。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蒙文通定为从西周前期至春秋战国之交;袁珂认为,该书除《海内经》四篇外,皆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并指出《山海经》所载内容与成书时间不应等同视之,该书记录的许多神话片断,性质上更接近于原始,其大部分内容当是原始时代的产物,只不过一直到《山海经》成书时期,这些自古以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才被用文字正式记录下来罢了(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神话论文集》)。我们非常同意袁珂先生的看法,并据此认为,龟蛇意象变体在《山海经》中的大量存在,恰为这一意象产生年代之久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周克庸)
周克庸:华夏水神的原型及其讹变
华夏最早的且具有普遍认同性的水神为玄冥,其神格脱胎于共工氏、鲧和大禹的治水,其龟蛇一体的形象,则源于鲧的儿子大禹和共工的从孙大岳共同治水时的联合图腾。
尧舜时代,出自“治水世家”的共工氏和鲧先后出任水官,其治水实践虽相继以失败而告终,但共工和鲧与“水”的关系,却被人们牢牢地刻在了记忆中;正因为如此,共工及其图腾—蛇,鲧及其图腾—龟鳖,便具有了水神的义涵。
共工氏—蛇:据典籍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注),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竹书纪年》),因其治水中“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国语·周语》),以邻为壑,伤及住在地势较低处的其它部落的利益,故传说中,共工又被指为制造水患的祸首:“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共工与“水患”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其获得了水神的神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即讲到,当时民间春旱乞雨时,要用八条活鱼祭祀共工。共工既为水神,其图腾物——蛇,自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神格。
我们说共工的图腾为蛇,根据如下:
《山海经·海内经》称:“祝融降于江水,生共工。”依此,共工出自祝融。“融”字从“虫”,而“虫”字乃是蛇的象形,故有前贤曾据此猜测,“融”的“本义当是一种蛇的名字”(闻一多说);祝融之为物,就是《山海经·东山经》所载“其状如黄蛇,鱼翼”的“” (郭沫若说)。假如这些说法可信,那么,出自祝融的共工,当然也就是“蛇”了。另外,我们还发现,共工氏后裔中亦有以蛇为姓氏者,如《路史》云,太岳(即与鲧同时代的“共工”之从孙,亦即与大禹联手平治水患的“四岳”)后有“苴人氏”、“锡我氏”。“苴”、“蛇”二字古读音近(苴/蛇:鱼歌通转,床母双声),而“锡我”二字的切音,也恰恰与“蛇”的读音相近(“锡我”二字的切音/蛇:歌部叠韵,心床准旁纽),故“苴人氏”、“锡我氏”即“蛇人氏”、“蛇氏”。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并云:共工“人面蛇身”;《路史》注引《归藏·启筮》云:“共工人面蛇身朱发”;《神异经·西北荒经》亦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传说中共工的奇诡形象,亦可为“共工以蛇为图腾”的结论提供佐证。
共工与水关系密切,而在古人心目中,蛇与水亦存在着神秘的关系。《左传·庄公十四年》注引服虔曰:“蛇,北方水物”;《尔雅·释鱼》郭璞注称:螣蛇“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据《管子·兵法》记载,古代军旅以“九章”(绘有九种图案的旗章)指挥行军,当使用绘有蛇形的旗帜时,则意味着命令队伍“行泽”;《淮南子·齐俗训》注高诱注云:“黑蜧,神蛇也,潜于神渊,能兴云雨”;《文选·江赋》注引《说文》:“蜦,蛇属也,黑色,潜于神泉之中,能兴云致雨”。龟鳖与水的关系十分显豁,而在古人心目中,蛇是可以化为龟鳖的:“雨水暴下,虫蛇变化,化为鱼鳖”(《论衡·无形篇》);《尔雅·释鱼》郭璞注引《国语·晋语》“鼋鼍鱼鳖,莫不能化”韦昭注曰:“化,谓蛇成鳖鼋”。——将蛇与水联系起来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以蛇为图腾且“为水师而水名”的共工氏的水神神格,则是将蛇与水紧密联结起来的纽带之一。
共工氏所辖族民的形象、共工氏的宗教活动等,亦可表明其图腾为蛇。《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又云:“共工之臣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相柳、相繇“九首蛇身”的形象,应是对共工氏集团蛇图腾的一种折射。《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所谓“共工台”,当与共工氏集团从事宗教活动的设施有关。此台朝向四方,每个角各有一蛇。——这表明,蛇乃是共工氏集团的共同保护神。
鲧—龟:共工治水失败后,鲧出任尧舜部落联盟的水官负责平治水患,虽亦历久无功,被殛于羽山,但如共工一样,其治水的经历也使他和他的图腾物——龟鳖获得了水神的神格(鲧父颛顼乃主水的北方大神,其配神为水神玄冥。这个玄冥应当就是鲧,其说详后)。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孙作云便曾指出,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原诸部落中,“鮌族以鳖为图腾”;“鳖氏族的酋长,在古文献中可考见的,有‘鮌’。”[1]孙氏虽未对此结论做详细考据,但其结论却是可信的。
《史纪·夏本纪》云:“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据此,鲧乃颛顼之子、黄帝之重孙。曾有学者指出,“轩辕”乃“天鼋”二字之假借(杨向奎说)。——此说可从。在上古读音中,黃帝的“黄”与“鼋”字读音相近(黃/鼋:阳元通转,匣疑旁纽);旧题汉郭宪《洞冥记》云:“影娥池中有鼊龟,望其群出岸上,如连壁弄于沙岸也。故语曰:夜未央,待龟黄。”可见“黄”有龟鳖义。黄帝又号“有熊”,而“熊”、“龟”二字古读音相近(熊/龟:蒸之对转,匣见旁纽),亦可通假。黃帝之孙、鲧之父颛顼,与龟鼋间的联系更则为明显。作为星座,颛顼在天上的位置是“虚”。“虚”的另一称呼为“玄枵”(《尔雅·释天》:“玄枵,虚也”),而“玄枵”作为十二星次之一的名称,恰恰是“天鼋”(见《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注)。《路史》曰:“邹屠氏有女,履龟不践,帝(颛顼)内之,是生禹祖”。邹屠氏之所以“履龟不践”,当出于对“龟”图腾的禁忌。帝颛顼与邹屠氏之女将其子命名为“鲧”,亦与龟图腾有关(恩格斯指出:“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那一个氏族。”[2]):“鲧”与“龟”古读音相近(鲧/龟:文之通转,见母双声),故二字本可通假。
考鲧的“事迹”,也多与龟鳖有密切关联。试分述之如次:
窃息壤治水。《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息壤(即能够生息成长的土壤)这一意象与“龟”之间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据莫尔根介绍,崴安多特部落中有个海龟氏氏族,就又被称作“美丽的土地”[3];世界各原始民族神话中,龟鳖由洪水中拯救大地、大地由龟鳖负载等传说俯拾皆是。据屈原透露的信息,出谋划策、撺掇鲧“窃帝之息壤”者,正是所谓的“鸱龟”(《楚辞·天问》:“鸱龟曳銜,鲧何听焉?”)。
化生为“能”或“青要之山”。《国语·晋语》:“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羽、龟二字古读音相近(羽/龟:鱼之旁转,匣见旁纽),鲧以龟鳖为图腾,故其被殛之山称龟山,其所入之渊称龟渊。《山海经·南山经》载:“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蚖也”。蚖也就是鼋。黄、鼋二字音近,前已述;能乃鳖属(《尔雅·释鱼》:“鳖三足,能”),故所谓“黄能”,即“鼋鳖”。鲧被殛于羽山事还见载于《左传·昭公七年》,其文将“能”字改为“熊”。黄熊非水族,何能“入于羽渊”?注疏者为此颇费了些周折,甚至生造了个“能”字下面加三点的字,称此字才是本字,“能”字“下三点为三足也”,“熊”乃是写了错字,并引束皙《发蒙记》云,该字的意思为“鳖三足”(见《史记·夏本纪》正义)。其实,要解释“黄熊”,根本沒必要另外造出个字来,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按照古读音,“黄熊”可径读作“鼋龟”。晋王嘉《拾遗记》讲得直截了当:“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见者谓为河精”。鲧字本作“鮌”,“鮌”即为“玄鱼”二字之拼合,鱼、冥二字古音相近(鱼/冥:鱼阳对转,疑明邻纽),所以“鮌”即“玄鱼”也就是“玄冥”(“鲧”字的古读音与“玄冥”二字的切音亦十分相近:二者文真旁转,见匣旁纽),而“玄鱼”、“玄冥”恰恰是鳖的讳名。《山海经·中山经》记载了另外一种关于鲧的化生传说:青要之山为“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神武罗司之”。“禹父”就是鲧;“仆累、蒲卢”是螺蛳、蜗牛之类(至今北方某些方言中还将螺蛳、蜗牛称为“勃拉子”、“勃拉牛儿”);“武罗”当读作“黾螺”(武/黾:鱼阳对转,明母双声;罗/螺:微歌旁转,来母双声),即一种水生的大螺。在中国“四灵”神话系统中,龙为“百鳞之灵”、凤为“百鸟之灵”、虎为“百兽之灵”,龟为“百介之灵”(《大戴礼记》:“介虫之精曰龟”。“介虫”,即生有甲壳的生物如蜃蚌等)。知此,则青要之山“多仆累、蒲卢,神武罗司之”这一表层结构携带的信息,也就不难破译了。——作为介虫的总司令,鲧亦即“三足鳖”化生的山上遍生介虫并以大螺为神,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青要”这一山名中的“要”字,与“龟”字的古读音相近(要/龟:宵之旁转,影之邻纽),故“青要”之山,其实就是“青龟”之山。
做城。在传说中,鲧是城墙的发明者(《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水经注》引《世本》也都有此说法)。以“治水”名世的鲧之所以“作城”,最初大约只是在以“堙”法堵水过程中筑堤为防,其后渐渐演变成了环绕居住地的“土围子”。鲧如何“作城”这里没必要深究,值得关注的是在后起的神话中,常有灵龟助人筑城的传说,如《太平御览》卷166引《九州志》云:“益州城,初累筑不应。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又166卷引《成都记》云:成都号龟城,是因秦灭蜀后张仪在此筑城屡倾,“忽有大龟周行,随其所蹑而筑,功果就焉”。鲧身为“作城”的祖师爷,故后人筑城受阻时,他自当显灵相助。——这一传说的表层结构下隐含的信息,仍是鲧以龟鳖为图腾。
此外,从鲧的儿子大禹身上,亦可析出鲧以龟鳖为图腾的信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今本无):“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此处的“熊”字,如前已述,当被解读为“能”——三足鳖,或径直将其读作“龟”。事实上,“禹”字古音,也恰恰与鼋、龟相近(禹/鼋:鱼元通转,匣疑旁纽:禹/龟:鱼之旁转,匣见旁纽)。
大禹与大岳—龟蛇:共工和鲧治水相继失败,随之又被作为“四凶”遭到尧舜制裁后,蛇、龟作为水神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幸有鲧的儿子大禹再次出任联盟的水官,与共工之从孙大岳联合治水,遂以龟蛇合体的形象为“联合图腾”(Associatedtotem)。经长期艰苦奋斗,禹不仅在平治水患方面大获全胜,而且在治水过程中积蓄起足以与舜相对抗的实力和威望,最终夺得了联盟最高首领的位置,建立了夏王朝,从而使龟蛇一体的水神形象得到了确立和广泛的认同。
以龟蛇一体的徽号为水神形象,至少隐括了这样一组义涵:a.肯定鲧的不屈精神。《山海经》郭璞注引《开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国语·晋语》云:“昔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山海经·海内经》则云:“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鲧所化黄龙、黄能(“三足鳖”)和禹,三位一体,共同体现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b.揭橥正确的治水方法。共工、鲧治水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仅使用“堙”法,而禹靠了疏、堙二法并举才成功地平治了水患。晋王嘉《拾遗记》卷二云:“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显然,龙蛇象征着疏导法,而龟鳖则为湮堵法的象征符号。c.指出成功平治水患乃是由以龟鳖和蛇为图腾的两大部落采取联合行动的结果。因为这一徽号从多种角度折射着“平治水患”的信息,又有夏王朝的大力推崇,所以蛇蛇意象就成了华夏水神的形象,而“玄冥”一词也就成了水神或水官的名称(《左传·昭公十八年》曰:“水正曰玄冥。”又:“禳火于玄冥”注云:“玄冥,水神”) 。因冥、武二字读音相近(武/冥:鱼耕旁对转,明母双声),玄冥后来又被改称作“玄武”。
除了玄冥,古代神话中还有不少其它的水神形象。究其源,则这些形象大多为龟蛇意象之讹变。
应龙:蛇的变体。《洪范·五行传》郑玄注曰:“蛇,龙之属也。龙无角者曰蛇”。《楚辞·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后世最具认同性的水神形象——龙王,当由此衍化而来。
禺强:龟的变体。古音中,“禺强”二字的切音与“龟”相近 (禺强二字的切音/龟:侯之旁转,群见旁纽),故“禺强”不过是“龟”在口耳相传过程中的讹变罢了。《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北方禺彊,……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庄周曰:‘禺彊立于北极,一曰禺京。’”郝懿行疏:“禺京,玄冥,声相近。《越绝书》云:‘玄冥治北方,……使王水。’《尚书大传》云:‘北方之极……,帝颛顼神,玄冥司之。’《吕氏春秋·孟冬纪》云:‘其神玄冥’,高诱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为玄冥师,死祀为水神。’是玄冥即禺京,禺京即禺彊”。
冰夷:龟蛇变体。冰夷,河伯之名,又作“冯夷”、“无夷”。《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陆德明音义引《清泠传》云:冯夷“华阴潼乡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服石成仙”云云,表明此说只能是魏晋后才会有的比附。《楚辞·九歌·河伯》洪兴祖补注引《抱朴子·释鬼》云:“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亦出比附。《山海经·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仭,维冰夷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曰:“冰夷,冯夷也。《淮南子》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其实,“冰夷”与“黾它”二字音近(冯/黾:蒸阳对转;帮明旁纽;夷/它:脂歌旁转,喻透准旁纽),冰夷即“黾它”,——龟鳖为“黾”属,而“它”则是蛇的古称。又据《楚辞·天问》王逸注,河伯之妻雒嫔为“水神,谓宓妃也”。宓当读作“鳖”(宓/鳖:质月旁转,明帮旁纽),“鳖”嫁给“黾它”为妻,自可谓门当户对得其所哉。
龙马:蛇龟变体。《宋书·符瑞志》云:龙马为“河水之精”。《山海经·中山经》云:“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太平广记》卷四三五引《洽闻记》称,唐高祖武德元年,景谷有龙马出,其状“龙身马首”。《山海经·北山经》称:“求如之山,滑水岀焉,……其中多水马”,郭璞注:汉武帝时“敦煌渥洼水出马以为灵瑞者,即此类也”;郭氏又作《水马赞》云:“马实龙精,爰出水类。渥洼之骏,是灵是瑞。昔在夏后,亦有河泗”。其实,马、龟乃一物之讹裂。《山海经·海内经》称:“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段简略的文字看上颇有些怪诞不经;但倘换一角度,从音韵关系上去考察,就会发现,“白马”二字其实就是“鳖黾”二字的讹变(白/鳖:铎月通转,并帮旁纽;马/黾:鱼阳对转,明母双声),而“骆明”则是“龙黾” 二字的讹变(骆/龙:铎冬旁对转,来母双声;明/黾:阳蒸通转,明母双声),故“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可径读为“龙黾生鳖黾,鳖黾是为鲧”。《尚书·顾命》:“伏牺王天下,龙马出河”;《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孔颖达注:“是龙马负图而出”。众所周知,“河图”是由神龟负之而岀的(《尚书·洪范》孔安国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之而岀”;《洛阳记》云:“禹时,有神龟于洛水负文于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所以,“龙马”不过是“骆明”亦即“龙黾”的变体罢了。
奇相:龟蛇变体。《广雅·释天》:“江神谓之奇相”。《蜀典》卷二“奇相”条引《蜀梼杌》曰:“古史云,震蒙氏之女窃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为奇相,即今江渎神是也。……《一统志》引《山海经》(今本无)云:‘神生汶川,马首龙身,禹道江,神实佐之。’”如前已述,辅佐大禹治水者,一黄龙一灵龟而已;又知“马”可读作“黾”,所以不难推见,“马首龙身”,其实就是龟首蛇身。
夔:龟的变体。《说文》云:“夔,母猴。似人”。“母猴”即休猴亦即猕猴。《张衡·东京赋》薛综注云:夔“如龙,有角”。《国语·鲁语》韦昭注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缲,人面猴身能言”。《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则必风雨。……其名曰夔”。夔的形象有“猴”、“龙”、“牛”及“一足”之说,要皆龟蛇意象之讹裂:夔古音与“龟”字相近(夔/龟:微之通转,群见旁纽);“龙”形由蛇化来;而“一足”则是“鳖三足”的讹变。猴、牛二形,则因猴字古音与龟字相近(猴/龟:侯之旁转,匣见旁纽),牛字古音与“能”——即“三足鳖”——字相近(牛/能:之部叠韵,疑泥邻纽)。
猴:龟的变体。清袁枚《子不语》卷十六《西江水怪》云:“有咒取鱼鳖者,……一日偶至大泽,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猕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势欲相攫。其人急以裩蒙首走,物奔来跃上肩,抓其额,人即仆地,流血晕绝。物见众至,作声如鸦鸣,跃高丈许遁去。……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鱼鳖为子孙。吾食其子孙,故来复仇耳”。前文已述,猴、龟、夔古音相近,故猴形乃为龟、夔之讹变。此外,猴、禺二字古音亦相近(猴/禺:侯部叠韵,匣疑旁纽),所以猴形或又由禺彊讹变而来。《山海经·南山经》云:招摇之山有兽,“其状如禺”,郭璞注:“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说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图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郝懿行疏:“《说文》云:蝯善援,禺属。又云:禺,猴属,兽之愚者也”。《山海经·南山经》云:“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注意:“长右”二字,可读作“它龟”(长/它:阳歌通转,定透旁纽;右/龟:之部叠韵,匣见旁纽)。——是猴形由龟蛇意象之化出,其源亦远矣。
无支祈:龟的变体。《山海经·大荒东经》吴任臣广注引《岳渎经》云:“尧九年,巫支祈为孽,应龙驱之淮阳龟山足下”;《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引《戎幕闲谈》云,禹理水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形若猿猴。经一番较量,禹终于将其“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龟山足下”。《唐国史补》“淮水无支奇”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使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面,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引者案:“军”读作“龟”)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这些晚出的神话,当属民间对由龟、夔、禺等意象讹裂出的猴形水神之演义。
河童:龟的变体。河童(见下图。转自《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为日本的水神。据吉野裕子介绍:河童“往往作为童话和俳画题材中的‘水的妖怪’或‘河神’出现”。“在日本,全国到处存在着有关河童的传说,尤其是河流多的地方。其中有名的是远野地区的河童,人们在河岸边修建了河童之祠”。“河童这一形象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至今还不知道。有些地方把河童叫‘猿猴’,它有很大的身体,确实很像‘猿’。不过,从它那嘴及侧脸来看,颇像‘老鼠’,而背负的那层厚厚的甲壳又恰似乌龟的样子。”[4] ——该形象显然是由龟及其变形猴组合而成的。
牛:龟的变形。牛形水神产生甚早,西汉时已有“潜牛”之说(见张衡《西京赋》),《山海经》中亦有其“状如牛”的水神夔的记载。《水经注·叶榆河》云:勾漏“县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明陈仁锡《潜确类书》云:“陝川有铁牛庙,头在河南,尾在河北,禹以镇河患”。《异苑》云:“晋康帝建元中,有渔父垂钓,得一金锁。引锁尽,见金牛。急挽出,牛断,犹得锁长二尺”。所前所述,牛、能二字古读音相近,所以,牛亦为龟鳖之讹变。
周克庸:鲧何以被殛——兼论尧舜诛“四凶”的原因
鲧被尧舜殛于羽山之事,典籍中颇有记载,如《尚书·洪范》曰:“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鲧则殛死”;《国语·晋语》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国语·周语》云:“其在后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山海经·海内经》称:“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之遭殛不是孤立的事,而是尧舜诛“四凶”行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与鲧一起受到尧舜严惩的,还有共工、驩兜和三苗(《尚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左传·文公十八年》亦载:舜“流放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这里所谓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即分别指驩兜、共工、鲧和三苗)。因此,要弄清鲧何以被殛,就须与其它“三凶”遭受尧舜严惩的原因联系起来考察。
鲧被殛的表层原因,似乎有两点:第一点,是鲧与其它“三凶”一样道德品质低劣。此点尽管于典籍中也能找到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但这大都属于胜利者罗织罪名加诸失败者的一面之词,不足为凭。第二点,是鲧未接受共工治水失败的教训,仍沿袭“堙”法治水,久而无功大失人心,且导致了集团内部氏族、部落间冲突迭起,“祸乱并兴”。——考诸典籍,这一点确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鲧之前负责治水并以失败告终的是共工。鲧和共工生活在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管子·揆度》);当共工、鯀被授权平治水患时,水灾为害相当严重:“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可以想见,平治水患,是当时尧舜联盟各部落、各氏族所共同面对的最为严峻、最急待解决问题之一。共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凭借其丰富的治水经验,才被众部落首领推举出来负责理水的,但共工有负众望,其治水竟以失败而告终。继共工之后,鲧出任了联盟的治水负责人,历时多年,其治水实践仍步共工之后尘,也同样失败了。共工和鲧不仅未能平治水患,消弥“天灾”,而且还制造了一系列的“人祸”,导致了许多氏族和部落的不满。
共工和鲧治水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使用了共同的治水方法——“堙”法。所谓“堙”法,就是“堵”法,也就是“水来土挡”的方法。以此种方法治水,在水势不大的情况下应当是可以取得一定成效的(从共工和鲧先后出任联盟理水工程负责人这点上可以看出,他们以往因堙法治水取得的功迹,确曾使他们在尧舜部落联盟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是,在水势过大、水患常年不止的情况下,再单靠“堙”法平治水患,就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平添出许多氏族、部落间的利益冲突来了。
《国语·周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与洛水相激,将毁王宫。灵王打算壅塞谷水,使水由北出以解困。但太子却认为此法断不可行。他在申明自己的理由时说:据我所闻,古时爱护下民的君长,“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接着,他又从反面举例来证明“壅塞谷水”之法不可行:“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后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堕高堙庳”怎么就与“以害天下”挂上钩了呢?原来,那个时期各氏族、部落在联盟中都有属于自己活动范围的“领地”,为了缓解不同组织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较为邻近的氏族、部落会逐步形成一些诸如互不侵扰之类的惯例。所谓“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等等,大约就属于此类习惯法的内容。由于各群体居住之外的地势高低各不相同,洪水泛滥时,居住于高地的群体比居住于低处的群体,在损失上肯定会小些。对此,受灾的群体也只能自认倒霉。而采取“堕高堙庳”的“堙”法治水,就势必要改变自然格局,从而使水患染上“人祸”的色彩;“堙”法只堵不疏,洪水从彼处找不到出路就会灌向此处。那些因此而遭受水患的氏族和部落,自然不仅不肯听命于共工调度,而且势必会对共工的这种治水方略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在“庶民弗助”的情况下,再加上“皇天弗福”,洪水势头只增不减,各氏族、部落在生存空间、生态环境等方面原本就已存在的矛盾持续激化,不断升级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集团内部“祸乱并兴”,共工的治水难以进行下去,当然只有是以失败而告终。在后世传说中,治水的共工竟秛描绘成制造水患的祸首(《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足以表明,共工在以“堙”法治水的过程中,是很伤了一批氏族、部落的感情的。
继共工之后出任联盟治水工程负责人的鲧,似乎并未从前车之鉴中汲取教训,他不仅仍然使用“堙”法(《尚书·洪范》载“鲧堙洪水”,《礼记·祭法》云:“鲧障鸿水”,《山海经·海内经》则称:“鲧窃帝息壤以湮洪水”),而且更进一步,大兴土石,修堤筑防,以他发明的“土围子”战术,去壅堵洪水(传说中,鲧是城墙的发明者。《吕氏春秋·君守》、《淮南子·原道训》、《水经注》引《世本》并有“夏鲧作城”的说法。所谓“作城”,大约最初只是在鲧以“堙”法堵水的过程中,筑堤为防,其后渐渐演变成了环绕居住地而建的“土围子”)。鲧的这种被认为是“称遂共工之过”的做法,势有必至地遭到了许多氏族、部落的对抗。“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众叛亲离之势既成,治水也就只能步共工之后尘,重蹈失败的覆辙了。
鲧治水失败大失人心,固然是其被殛的重要原因(共工和鲧治水旷日持久功用不成且引发了“祸乱并兴”,出于收拾人心、强化联盟凝骤力、确保自身权威的考虑,尧舜将共工和鲧踢出来做替罪羊,本属不难理解的谋略手段),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是能够冠冕堂皇地讲出口来的原因。实际上,鲧之所以被殛,更深刻的原因,乃是在围绕联盟“公权力”而进行的争斗中,以鲧为首的“小集团”竟敢与盟主尧舜展开激烈的争夺。为确保自身的盟主地位,尧舜利用鲧治水失误不得人心这一天赐良机,果断地实现了一次成功的“门户清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以一段言简义赅的文字记叙了这一史实:“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在与尧舜抢夺大盟主位置的斗争中,鲧表现得最为强悍,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讲:“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付之以吴刀。”——看来,觊觎部落联盟大盟主之位,不惜分庭抗礼,公然分裂,“以患帝舜”,这才是鲧最终被殛的根本原因。至于“四凶”中的其它三“凶”遭受严厉制裁的根本原因,也不过是因为他们都属于以鲧为首的“小集团”组织中的骨干成员罢了。
作为与尧舜相对抗的“小集团”成员,共工、鲧和驩兜的实力皆不容低估。《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放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先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从这段话中看,“帝鸿氏”之子、“少皞氏”之子、“颛顼”之子的名头,表明共工、鲧和驩兜皆为“帝”之贵冑,氏族声名显赫;“世济其凶,增其恶名”,表明由他们组成的“小集团”拥有不少来自基层的依附力量,——被“天下之民以比三凶”的三苗,即属于基层支持“三凶”的中坚力量之一;而“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的说法,则表明了该“小集团”实力之强大,的确非比等闲。
尧舜与“四凶”的暗中争斗由来已久,尧舜之所以未能及早断然收拾“四凶”,一是因为“四凶”在部落联盟中的势力甚强、威望甚高,二是因为尧舜还没有找到翦除“四凶”的合适理由,三是因为尧舜与“四凶”的斗争尚未公开化。
在共工治水失败、鲧出任理水工程负责人之前,由尧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联盟首长会议。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叙,这次联盟首脑会议共讨论了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将来由什么人来接替尧的联盟元首位置:“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讙兜的这句话,在《尚书·尧典》中被记作“都!共工方鸠僝功”,其疏云:“呜呼,叹有人之大贤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于所在之方,能立事业,聚见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当放齐推荐尧之嗣子继位的建议遭到尧的否定后,作为“四岳”之一的讙兜(即驩兜),立即挺身而出举荐共工,并为共工大唱赞歌。由此可见,即使是治水失败后,共工在部落联盟首领中仍然是很有些势力和威望的。对这一举荐,尧虽以“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为词予以否定,但还是答应“试之工师”,给了共工一个类似于后世“大匠卿”的位置,表示要对共工做进一步的考察。
这次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当前的大水患应该由谁负责去治理。讨论中“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类似记载又见之于《史记·夏本纪》:“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史记·五帝本纪》在另一处也提到此事:“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一致推举鲧出任理水官,即使在遭到尧的明确否定后,仍以“经比较未见有贤于鲧者”为由,“强请试之”。由此可见,鲧在联盟集团上层首领中,也是很有势力和威望的。唯其如此,尧才不得不顾及众议,违心地同意了“用鲧治水”。
为了弄清作为“反对党”存在的这个“小集团”的夺权野心及其各自的实力,根据已收罗到和梳理过的零星材料,我们想对“四凶族”的代表人物再作些粗略的概述和分析:
共工:古代典籍所載共工事,上及远古,下至虞夏。由此可知,“共工”乃氏族名;该氏族不同时期的首领,亦被称为“共工”。所以,“共工”非特定的某一个人的专名。作为氏族,“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注),因此该氏族一向声名显赫:“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以为社”(《国语·鲁语》)。“九有”即九域,共工氏曾“伯九有”,可见其历史地位之崇高。《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共工氏竟能够“与颛顼争为帝”,亦可见其势力早就十分强大。作为“四凶”之一的这个共工,即受尧命平治水患最终失败的这个共工,在部落联盟中自然是颇有势力和威望的,否则尧也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权柄轻易授予此人。治水失败后的共工,其威望和影响力已大大下降,但即使这样,联盟内仍有推举其于尧后继任大盟主的呼声;共工一向自视甚高(《周书·史记篇》称:“共工自贤,自以无臣”),颇不甘受尧舜辖制。这一切表明,共工是个有可能动摇尧舜盟主地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治水失败后,共工收敛起与尧舜争斗的气焰,以韬光隐晦。在此情况下,他主动靠拢同为“治水世家”出身并坚持以“堙”法治水的鲧,与鲧互通声气、相互支持,继续与尧舜暗中抗衡,则是情理之中的一种选择了。
鲧:鲧是“禹父”的专名,此人与尧舜时代的那个共工有很多相似处,比如a、与共工氏一样,鲧的氏族也有显赫的历史,《史纪·夏本纪》云:“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据此,鲧乃颛顼之子,黄帝之重孙。b、鲧与共工都出身于治水世家,都在尧舜部落联盟中拥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威望,并都曾出任尧舜联盟集团的水官,总调度联盟治水诸事宜。c、鲧与共工都以“堙”法治水,都历久无功,也都因治水而与许多氏族、部落结下怨恨,并因此降低了自身威信;d、鲧与共工都对部落联盟大盟主的位置有所觊觎,都或明或暗地与尧舜作对;e、鲧与共工最终都被作为“四凶”之一而受到严厉制裁。因二者如此相像,以至于童书业、姜亮夫等人均认为共工与鲧是一人之分化。《神话与中国社会》一书亦称:“共工与鲧本是一个,因传说纷纭渐分为二,为中国神话史上一大公案”[1]。其实,共工与鲧分属两个不容混同的氏族。共工治水在先,其治水失败后鲧才由四岳推荐出任水官。《竹书纪年》云: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又云:帝尧“六一年,命崇伯鲧治河”。这些纪年固然不足为信,但共工和鲧出任联盟的水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却是无可怀疑的。
因共工采取韬晦之计,鲧继任水官后遂被推到了与尧舜相抗衡的“小集团”主帅的位置上。从性格上来看,较之于共工,鲧显得更为梗直(《楚辞·离骚》:“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更不屑于掩饰自己夺取大盟主位置的野心,更敢于公然表示对尧舜权威的蔑视,更敢于与尧舜进行公开对抗。
驩兜:在由“四凶”组成的“小集团”中,驩兜是一个很重要却又显得颇有些神秘的角色。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驩兜乃“帝鸿氏”之子,——即黄帝的后代。从驩兜能以“四岳”之一的身份参加部落联盟鼎级决策会议这点来看,他在联盟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在推荐尧之后盟主预备人选的会议上,当放齐推荐尧之嗣子丹朱继位的建议遭尧否决后,驩兜立即举荐共工,为共工造势,可见他与共工的关系非同寻常。驩兜与鲧的关系似乎也很不一般,《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即“驩兜”,这点早已是学界共识。准此,则驩兜与鲧两个氏族间似乎还存在着血缘或姻亲关系。驩兜与三苗之间同样存在着某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瓜葛,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颛顼生欢兜,欢兜生苗民”的记载,欢兜亦即驩兜竟成了苗民之祖!还有,尧舜对驩兜实行制裁的方式也很有些值得琢磨之处。《孟子·万章》称尧“放驩兜于崇山”;《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并载舜“放驩兜于崇山”;而《荀子·议兵》和《战国策·秦策》则并云:“尧伐驩兜”。制裁者一说为尧一说舜,这并不奇怪,因为诛“四凶”本来就是尧舜的联手行动,倘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当时尧已“令舜摄行天子之政”,那么发号施令者以尧的名义或舜的名义就都无所谓了。值得推敲的,倒是“尧伐驩兜”这句话中的“伐”字。尧舜之所以需要诉诸武力,那肯定是因为驩兜不服制裁,并组织了武装抗争,所以,尧舜才不得不靠“伐”去解决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不无道理的大胆推测,即:驩兜很可能就是被尧剥夺了盟主继承权的尧之长子——丹朱。邹汉勋在《读书偶识》2中说:“驩兜(《舜典》、《孟子》)、驩头、驩朱(《山海经》)、吺(《尚书大传》)、丹朱(《益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从音韵学角度看,邹氏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字还有作“讙兜”、“欢兜”者)。《太平御览》卷63引《尚书逸篇》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汉学堂丛书》辑《六韬》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此处所说的丹水,恰恰是丹朱被流放之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史记·五帝本纪》),对此心怀怨恨的丹朱,被舜流放丹水之后,很可能是出于共同的敌忾,与三苗结为联盟,甚至成为该联盟的大盟主(这恰好是对“欢兜生苗民”说法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因此,丹朱即欢兜亦即驩兜才有了与尧舜武装对抗的资本;也因此,尧舜才不惜动用武力对威胁自身权力的丹朱即欢兜亦即驩兜大加讨伐。这场讨伐与反讨伐的争斗,大约是以丹朱即欢兜亦即驩兜的被杀(《庄子·盗跖》称:“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大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吕氏春秋·当务》曰:“尧不慈”;《楚辞·九辩》云:“尧舜……被以不慈之伪名”,——这些闪烁其词的传说,已透露了丹朱被尧所杀的消息)、驩兜三苗联盟被逐而告结束的。
三苗:三苗是与驩兜站在同一立场上,与尧舜相对抗的一支力量。三苗国所在地“赤水”,即丹朱被流放之地“丹水”。《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看来,“三苗”被诛的直接原因,也是反对“尧以天下让舜”,而间接原因则是其一向不听尧舜号令,“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为了去掉这块心病,舜大约曾经多次“亲征”,组织军事行动对三苗实行武力围剿,以至于有传说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
诛“四凶”是舜的主意:“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诛“四凶”是舜“归而言于帝”并主动“请”求采取行动的结果,其目的是保住自己大盟主继承人的地位。这一目的,当时看上去似乎是达到了;但历史的进程是阻挡不住的,在国家诞生前夕,在公权力私有化的进程中,“天下咸服”是假象,是暂时的,而围绕等级特权展开的争夺,却必然会愈演愈烈起来。
社会组织形式由“部落联盟”进化到“国家”,其间有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塞维斯等人类学家将这个过渡阶段称之为“酋邦时代”[2]。早在颛顼时期,便已有共工与之“争帝”的事情发生;逮及尧舜禹,社会进化已发展到了“酋邦时代”的晚期。此时,部落联盟组织中已出现居于特殊地位拥有特殊权力的“最高首领”,而不再像早先的部落联盟那样,所有加盟部落首领在地位和权利方面人人平等;管理部落联盟事务的最终决断权,也已越来越归之于“最高首领”,而不再像早先的部落联盟那样,实行所有加盟部落首领一致通过的议事规则。因此,在尧舜禹时代,所有有实力的加盟部落首领,觊觎“最高首领”位置的野心早已膨胀开来,“最高首领”权力的转移也早已沾染上了浓厚的血腥味,“禅让制”早已名存实亡。尧舜间通过“禅让”实现权力过渡的说法,不过是后世儒家为了美化先贤想像出来的昏话。即使尧舜确曾表演过一场“禅让”的滑稽剧,那也只不过是由已将实权稳稳操控在手的舜充任导演的一场作“秀”罢了。——其实,这在当时恐怕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比如,《韩非子·说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舜逼尧,……人臣弒其君者也”;《史记集解》引《括地志》亦称:“《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广弘明集》卷11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史通·疑古篇》也讲:“舜放尧于平阳”;就连《孟子·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舜之得掌权柄,乃“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的说法。
正因为国家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公权力的争夺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日后鲧的儿子大禹与共氏的从孙大岳联手治水终获成功,大禹乘势从舜手中夺得权力,坐上了该部落联盟最后一位大盟主的交椅,并最终将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夏王朝,也就应当被视作顺应潮流之举了。
少昊金天氏身首异处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2)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3)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4)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5)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6)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7)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8)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9)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0)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1)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2)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3)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4)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5)
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张敬国
《淮南子》九州与禹贡治九州迥异
五千年前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黑人部落
水神的盛宴——《西游记》神话与鲧禹父子治水传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