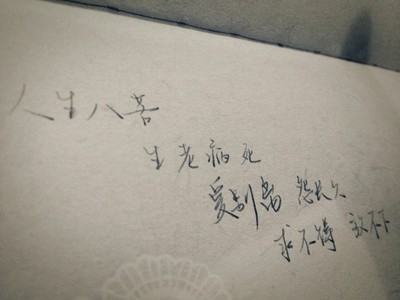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题记
1931年春,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听说挚友胡适将乘船由上海赴北平,就邀请他顺道来青岛演讲。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适给杨振声发电报,仅“宛在水中央”五字。杨振声则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前者化用《诗经》,后者直引古乐府,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还被人记为逸事,发表在《大公报》上。
那些名士风流,就这般跃然纸上,令人怀想。
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
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群星璀璨,俨然是当时的“文化根据地”。这短暂的光辉,与国立青岛大学息息相关。梁实秋、沈从文、洪深、老舍、冯沅君、闻一多、游国恩、宋春舫……这些载入文化史的人物与教育家黄敬思、数学家黄际遇、化学家汤腾汉、生物学家曾省之等人一起,组成了当时国内大学中难得一见的“豪华学者群”。
那时,青岛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也正因为他们,青岛产生了独有的“客居文化”。小说、诗歌、戏剧、译著、论著……客居者们的众多代表作在这里诞生,当然,还少不了海洋学和气象学的种种辉煌。
这一切,又与杨振声分不开——他是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用自己的魅力为国立青岛大学广纳贤才,他以新月派诗人、作家的身份投身教育界,摇身一变成为继承蔡元培衣钵的教育家。
杨振声的一生,以五四为界。此前,是青春激昂,此后,是春风化雨。
他的青年时光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十分激进,并以新潮社干将、五四风头人物的身份留名于史。那时,他是北大国文系学生,与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家伦等是同学,1918年夏天,受《新青年》杂志的感召,壮怀激烈的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开始筹备大名鼎鼎的《新潮》杂志,并任编辑部书记,当年年底,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组织“新潮社”——这一串日后大放异彩的名字,彼时都是激扬少年。
《新潮》的英文刊名为“The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介绍西方思潮和文学,也刊登学生自己的论文、小说和诗歌,不乏革命意气之作,第一期就抢尽眼球,尽管是学生刊物,却能连印三版,销售三万多册,而且这三万多册并不代表读者仅三万多人,据说,青年学子们互相传阅,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校长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字,学校还每月给予资助,额度还不小——大洋400元。
那时的北大,着实兼容并包。
杨振声既是《新潮》的编辑部书记,也是重要作者,他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以及一些新诗均发表于此。
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是发起人之一,曾组织千人大会,也曾在《新潮》办公室中,与同学通宵“苦战”,写下三千多条标语,火烧赵家楼事件中,他亦是参与者,结果成了当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后经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而与战友们不同的是,他还曾二次入狱,5月25日,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的《五七周刊》,却遭当局拒绝,并被扣押,在监狱中呆了一个月才被释放。
但与很多五四闯将一样,后来的杨振声,也在肯定五四重大意义的同时进行反思——以现代史观而论,反思的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结合当时外交举措的实质,反思五四运动中隐约可见的暴力成分和操之过急,二是结合1949年前后的政治形势,从无产阶级史观的角度去检讨五四,杨振声选择的是后一种。比如1949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杨振声发表《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他还发表了《“五四”与新文学》,认为“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以当下眼光来看杨振声的这些说法,依稀可以嗅到左倾的味道,颇令人感慨,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应景之作,1950年,杨振声又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此文从观点上来说更烈,可谓全面反思“五四”在文化层面上的一些弊端,但抛开左倾思维的影响,部分观点颇有理有据,比如他认为“五四”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便一语中的,事实上,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曾在晚年重拾中国传统文化,检讨当年极端崇拜西方文化的盲目性,比如胡适,又如在遗言中感慨中国文化之精深的殷海光。正如杨振声所说,“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
杨振声的反思,其实从五四运动后就逐渐开始了。那年年底,他通过考试获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一起赴美。在美国,他攻读的是教育,也是他此后半生的研究方向,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后又赴哈佛读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4年回国的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众多国内一流大学留下足迹,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则专门邀请北大同窗杨振声、冯友兰相助,打造班底,任命杨振声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如今看来,这些都是积累,让他缓缓靠近一生教育成就的顶点——1929年,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筹备委员会,以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1930年6月,正式任命杨振声为校长,这一年,他40岁。
独当一面的杨振声,魄力与魅力并举。据载,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一年经费仅40余万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同级院校的1/3甚至1/4,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杨振声却偏偏办到了。他曾有名言,“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根据这一原则,他在行政编制上极尽缩减,省下来的钱均投入购书与设备,他说“我们惟有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我们经常费能多省一文,即设备上能增加一点,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基石”,图书馆和实验室均是其眼中的重中之重,竭力打造。
作为校长,他亦以身作则,力行节流,比如校长公务配车,他选旧车不选新车,公家的东西他从不私用,哪怕是信封和信纸,但每周的校务会,他都会带着自家香烟、咖啡和茶叶赴会给大家享用。
而办学一事,更重要的是人才。杨振声是蔡元培的弟子,自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准则,他又是五四干将,在教育界和文坛均有名气,且一向以为人坦荡豪爽诚挚豁达著称,故知交满天下,大打个人魅力这张牌,竟延揽大量人才,把一间新学校变为了文化重镇。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是大教育家黄敬思,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是大数学家黄际遇,化学系主任是汤腾汉,生物系主任是曾省……
闻一多和梁实秋二人的到来很有意思,堪称逸事。当时,杨振声专程前往上海游说二人,梁实秋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载:“今甫(杨振声字)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青岛风物,确实迷人,梁实秋晚年思念大陆,最念念不忘的地方便是青岛,那些国立青岛大学的同僚们,也都把青岛视为一生中极难忘怀的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因为杨振声的个人魅力和青岛的宜人环境,使得教师待遇虽比某些大学略低,大家也甘愿俯就。
为了节省办学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教师,自掏腰包租下青岛黄县路7号,与教务长赵太侔(后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校医邓初等几家合住。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应为黄县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如今的黄县路,其实依旧是悠然清静的。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虽也有车经过,却终究比普通马路上的车少了许多。这条路地势起伏,呈微微的漏斗状,德国人修路总是留有余地,所以百年前的老路也挺宽阔。院子两旁都是独立的院子,院内有各色树木,少不了的是阔大的梧桐、嫩绿的冬青、清幽的紫藤,还有人种了竹子,不多的几棵,稍稍高出院墙,倚在院落一角。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黄县路,乃至以小鱼山为轴心的十数条德式老街,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教育强国之梦。
而杨振声所居住的黄县路7号,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德式民居,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如今加了窗子,成为了住宅的一部分。我年少时常在那一带流连,老舍故居也在左近,门牌是黄县路12号。
那时,这里时常高朋满座,国立青岛大学的学者们喜欢来这里谈诗,有人回忆说,杨振声“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好玩的是,杨振声虽秉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但招聘人才,总要讲究你情我愿,少不得共同语言,所以,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和外文这两系几乎成了新月派的天下。
——杨振声自己,就是新月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而梁实秋、闻一多、孙大雨和方令孺等人,也都属新月一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立青大还有“酒中八仙”一说,阵容颇为显赫,校长杨振声亲自带头,还有教务长赵太侔、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会计主任刘本钊、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秘书长陈季超和任教于文学院的女诗人方令孺。杨振声还拟了一副名联,叫做“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之所以有这“酒中八仙”,一是因为文人好酒,二是因为青岛虽然景致迷人,商业也繁华,但终究开埠未久,不若老城市有人文气息,文化人长居于此,难免觉得单调,杨振声邀请大家外出聚会,也算用心良苦。
梁实秋晚年文字,对这段时光提及甚多,仅手头可查文字,便有《饮酒》、《酒中八仙》、《胡适先生二三事》、《忆闻一多》、《忆杨今甫》和《方令孺其人》等多篇。据他回忆,他们聚会的馆子,一个叫顺兴楼,一个叫厚德福,有时甚至远赴济南、南京等地,“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他还在《酒中八仙》里回忆杨振声,“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一派名士风范,跃然纸上。说到名士气,还有一桩逸事,据载,当时,学校的通知布告多是固定格式和死板套语,杨振声却独出心裁,经常把布告填成诗词发布出来。据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回忆:“在文艺方面,‘青大’称得起当代文苑的一角。校长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他为人民主,风度翩翩。在布告里时常看到他用俊秀的草书亲笔写的布告。用的是四六句,很有风趣,至今还记得他幽默地批评男同学:‘破坏风纪,月旦女生’。”
好玩的是,他们酒中八仙的彪悍酒风吓怕了著名“妻管严”胡适。胡适和杨振声本是挚友,除了前文提到的著名电报之外,二人在北大任教时便过从甚密,到了1931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胡适就举荐了仍在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结果此事未成,最后是胡适自己接任。1937年初,二人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抗战胜利后,又一起承担北大的复校工作,可谓半生知己。而在青岛期间,杨振声也多次邀请胡适前来,有一回胡适真来了,一看这群老友划拳斗酒,赶紧出动私家武器——戴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让大家围观,要求不参战。更好玩的在后头,回到北京后,胡适还写信给梁实秋,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这不是明摆着挖老友的墙角嘛。
如今,在原国立青岛大学所在的鱼山路与其旧居所在的黄县路之间,修起了一座矮矮的立交,以减轻因道路过窄带来的交通压力,桥两边的老博物馆和冯沅君、童第周等人的故居,似乎都因此矮了一截。这看起来有些煞风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座立交已经在尽量迁就两侧的建筑了。

而在七十多年前,每日经过这里的杨振声想必是悠然的——因为没有遮挡的缘故,不远处的海浪声总会不时传入耳内,黄县路的石板路也会与他的手杖发出清脆的触碰声。
也许就是在这海浪声中,杨振声起了开拓海洋生物学、海洋学和气象学的念头。在他看来,“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因此首创海洋科学学科,此后,从国立青岛大学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第一,1949年后,山东大学搬至济南,但却在其原有基础上创办了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就此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还有一创举,就是于1932年将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此举得到教育部称许,蔡元培亦对此赞不绝口。合并的用意,是让文科生必修理科的某些课程,理科生也必修一些文科课程,杨振声认为“大家常把文学院与理学院看为截然不同,大概把科学放在理学院,非科学放在文学院,是错误的……文、理两学院不但不能此疆彼界,而严格地说起来,更是相得益彰。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是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文学院中的人,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理学院中的人,做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
这等见识,直到今天仍不落伍——这些年来,谈及中国教育,文理的绝对分科一直遭受诟病,学生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断然割裂文理,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文科生缺了逻辑思维,理科生则往往墨守成规和人文气质。而多年前的杨振声,早已预见这一点。
他也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认为培养学生即是为了服务社会,所以必须联系实际,比如当时的农学院,就针对山东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如莱阳梨的病虫害防治、山东棉花的改良等。
彼时的大教育家们,思路其实都差不多,蔡元培、张伯苓等尽皆如此。
可惜的是,杨振声在青岛的时光太短,1932年5月,他便因故离开青岛。据载,那时的他极为矛盾,他的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前往南京游行示威,引起当局不满,杨振声一方面顶住当局压力,坚持教育独立,保护学生安全,另一方面却也希望学生克制,专注于学业。作为当年的五四干将,他的隐忍令很多人意外,但实际上,这是许多经历过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他们清晰看到激进固然会影响时局,但若要强国,学生最重要的还是读书,用一代人的心理强壮去改变这个国家。
但杨振声的选择,无疑两头不讨好,当局怪他包庇学生,学生怪他支持太少。他的离去,多少有些无奈,梁实秋也曾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
离开青岛后,他与家人回到北平定居。此后的他,除了参与一些公职外,开始将视野转向儿童教育,以图救国。他曾亲手编写《抗日救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子杨起曾回忆,“为了使所选编的教材真正适应少年儿童,父亲陆续带着编成的教材,每星期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试教。同时,他也经常把小学生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给他们吃点心,讲故事,以增进对孩子们的了解”。直到抗战爆发,杨振声前往西南联大任教时,仍在潜心编写《中学国文课本》。
胡适也曾回忆,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武大方面安排他们与小学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为孩子们讲故事。尽管诸位都是文坛大家,教育界的大腕,可据胡适说,讲起故事来都不算成功,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今甫,也作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掌文化一脉,杨振声参与筹备并前往任教。1937年8月,他以教育部代表身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和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对杨振声都多有提及,一是建校出了大力,二是治学教学的严谨。当时,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外,还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
著名现代文学学者,后来曾长期执掌中大中文系的吴宏聪当时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本就景仰杨振声,待得上课后,更是敬佩,他曾回忆杨振声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课,说“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而他极为景仰的另一位老师沈从文,也是这样对待学生习作。
大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也曾写过《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不过他谈的并非西南联大时代,而是1929年的燕京大学时代,那时杨振声主讲现代文学,“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据载,当时的众多年轻作家都曾得杨振声提携、帮助,其中还包括了沈从文。
可惜的是,一生旷达的杨振声,却晚景凄凉。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要求杨振声离开北平,还准备了南下的机票,但杨振声拒绝了,选择迎接新中国。可他先是在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学阀”,到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他又被分配至东北人民大学,此举形同发配,也有人曾记载,说德高望重的杨振声离开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的一些领导“出力不小”,只是时过境迁,真相已经不得而知。杨振声人本豁达,毅然前往,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患上胃病,抗战后回北大任教时又做了切除手术,本需长期疗养,当时东北是抗美援朝的前线,生活艰苦又无人照料,尤其是硬高粱米对他的胃影响极大,两年之后就患上肠梗阻。加上医院处置不当,致病情恶化,1956年病逝。其子杨起先生曾回忆,父亲病重时曾想喝点酸奶,他跑遍北京城都找不到,听来让人凄怆。
杨振声之所以处境惨淡,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与胡适有交情,二是与鲁迅没交情。
前文已经提及杨振声与胡适交情莫逆,这两位从五四时代就已是朋友,数十年间见面、书信往来无数,在文坛上大有交集,在教育界也并肩作战。当时大肆批判胡适,杨振声难免受牵连,而且他一向仁厚,尽管身边许多人为了自保,把彼岸的胡适骂得狗血淋头,他却只写一点不痛不痒的应景文字,交差了事。而远在美国的胡适,曾把批判他的数十万字看了个遍,对众多老友的批评嗤之以鼻,看透了这些“老友”的嘴脸,可唯独未批驳杨振声,可谓尽在不言中。
而与鲁迅没交情,是指他曾被鲁迅“点名”。1924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玉君》,据说是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胡适、陈西滢等人对此小说推崇备至,陈源将其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实际列了十一部)中,并赠誉“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偏偏胡适和陈西滢这两位老兄都是鲁迅的死对头,杨振声与他们过从甚密,尽管他本人向来没有拉帮结派的念头,却已让鲁迅看不顺眼,将他归入“语丝派”(也称“现代评论派”),现在看到对《玉君》的评价,觉得自己前不久发表的《阿Q正传》未受重视,立马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写道“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一派讽刺之意。
到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之际,因为杨振声延揽的文学院教授多是新月派人物,新月派又是鲁迅的论敌,所以鲁迅仍对杨振声全无好感,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写道:“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后来,鲁迅编撰《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入了杨振声当年在《新潮》上发表的处女作《渔家》,将其列为“新潮派”的代表作,给予了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的评价,却依然对《玉君》无视。不过其他文坛众人都对《玉君》评价极高,梁实秋就曾写道:“《玉君》清丽脱俗,惜(杨振声)从此搁笔,不再有所著作。”
1949年后,鲁迅登上神坛,曾被其批评者后来均遭批判,杨振声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据杨起先生回忆,“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里沈先生生怕父亲‘牵连’到他。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自己写了一篇‘代序’。”
这也怪不得沈从文,因为1949年历次政治运动均极残酷,人人都被吓怕了,彼时影响未消,有顾虑实属正常。
作为大教育家,杨振声的家庭教育也值得称道。前文提到的杨起先生是他的次子,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而长子杨文衡是著名农学家,尤其是在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上极具造诣,真可谓满门书香。
那些名士风采,总在人们的神往中若隐若现。其实,记忆之所以封存,只是因为它足够珍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