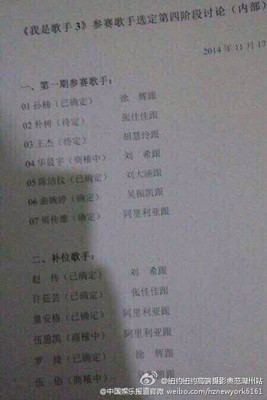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诗曰:
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世事到头终有尽,浮花过眼总非真。
贫穷富贵天之命,事业功名隙里尘。得便宜处休欢喜,远在儿孙近在身。
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这两个为头接将来,智深也却好去粪窖边,看见这夥人都不走动,只立在窖边,齐道:“俺特来与和尚作庆。”智深道:“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都来廨宇里坐地。”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夥人不三不四,不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攧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众人面前来。那张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们特来参拜师父。”口里说,便向前去。一个来抢左脚,一个来抢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腾的把李四踢下粪窖里去。张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两个泼皮都踢在粪窖里挣侧。后头那二三十个破落户,惊的目瞪痴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个走的,一个下去,两个走的,两个下去。”众泼皮户都不敢动旦。只见那张三、李四在粪窖里探起头来。原来那座粪窖没底似深,两个一身臭屎,头发上蛆虫盘满,立在粪窖里叫道:“师父饶恕我们。”智深喝道:“你那众泼皮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打一救,搀到葫芦架边,臭秽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两个泼皮洗了一回,众人脱件衣服与他两个穿了。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夥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俺这里戏弄洒家?”那张三、李四并众火伴一齐跪下说道:“小人祖居在这里,都只靠赌博讨钱为生。这片菜园是俺们衣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师父却是那里来的长老?恁的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有师父。今日我等愿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为杀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五台山来到这里。洒家俗姓鲁,法名智深。休说你这三二十个人直什么,便是千军万马队中,俺敢直杀的入去出来。”众泼皮喏喏连声,拜谢了去。智深自来廨宇里房内收拾,整顿歇卧。次日,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买了十瓶酒,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都在廨宇内安排了,请鲁智深居中坐了。两边一带,坐定那二三十泼皮饮酒。智深道:“什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众人道:“我们有福,今日得师父在这里,与我等众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里,也有唱的,也有说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哄,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的叫。众人有扣齿的,齐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们做什么鸟乱?”众人道:“老鸦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这话!”那种地道人笑道:“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只聒到晚。”众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几个道:“我们便去。”智深也乘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众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净。”李四便道:“我与你盘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只叫:“师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罗汉身体!无千万斤气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鸟紧。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众泼皮当晚各自散了。从明日为始,这二三十个破落户,见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将酒肉来请智深,看他演武使拳。过了数日,智深寻思道:“每日吃他们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还席。”叫道人去城中买了几般果子,沽了两三担酒,杀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时正是三月尽,天气正热。智深道:“天色热,”叫道人绿槐树下铺了芦席,请那许多泼皮团团坐定,大碗斟酒,大块切肉。叫众人吃得饱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浓。众泼皮道:“这几日见师父演力,不曾见师父家生器械。怎得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说的是。”便去房内取出浑铁禅杖,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众人看了,尽皆吃惊,都道:“两臂膊没水牛大小气力,怎使得动。”智深接过来,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众人看了,一齐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听得,收住了手,看时,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个官人。怎生打扮?但见:古
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爪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摺叠纸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众泼皮道:“这位教师喝采,必然是好。”智深问道:“那军官是谁?”众人道:“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名唤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请来厮见。”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两个就槐树下相见了,一同坐地。林教头便问道:“师兄何处人氏?法讳唤做什么?”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林冲大喜,就当结义智深为兄。智深道:“教头今日缘何到此?林冲答道:“恰才与拙荆一同来间壁岳庙里还香愿。林冲听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锦儿自和荆妇去庙里烧香。林冲就只此间相等。不想得遇师兄。”智深道:“洒家初到这里,正没相识。得这几个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头不弃,结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来相待。
恰才饮得三杯,只见女使锦儿,慌慌急急,红了脸在墙缺边叫道:“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林冲连忙问道:“在那里?”锦儿道:“正在五岳楼下来,撞见个诈奸不及的,把娘子拦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来望师兄,休怪,休怪!”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和锦儿迳奔岳庙里来。抢到五岳楼看时,见了数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干边胡梯上。一个年小的后生,独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拦着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林冲娘子红了脸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因此高太尉爱惜他。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主
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高衙内说道:“林冲,干你什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认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认的时,他没这场事。见林冲不动手,他发这话。众多闲汉见闹,一齐拢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林冲将引妻小并使女锦儿,也转出廊下来。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林冲见了,叫道:“师兄那里去?”智深道:“我来帮你厮打。”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林冲见智深醉了,便道:“师兄说得是。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了。权且饶他。”智深道:“但有事时,便来唤洒家,与你去。”众泼皮见智深醉了,扶着道:“师父,俺们且去,明日再得相会。”智深提着禅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阿哥,明日再得相会。”智深相别,自和泼皮去了。林冲领了娘子并锦儿,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郁郁不乐。
且说这高衙内引了一班儿闲汉,自见了林冲娘子,又被他冲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乐。回到府中纳闷。过了三两日,众多闲汉都来伺候。见衙内自焦,没撩没乱。众人散了。数内有一个帮闲的,唤做干鸟头富安,理会得高衙内意思,独自一个到府中伺候。见衙内在书房中闲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内近日面色清减,心中少乐,必然有件不悦之事。”高衙内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内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乐?”富安道:“衙内是思想那双木的。这猜如何?”衙内笑道:“你猜得是。只没个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难哉!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这个无伤。他见在帐下听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小闲寻思有一计,使衙内能勾得他。”高衙内听的,便道:“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心中着迷,郁郁不乐。你有甚见识,能勾他时,我自重重的赏你。”富安道:“门下知心腹的陆虞候陆谦,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内躲在陆虞候楼上深阁,摆下些酒食,却叫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教他直去樊楼上深阁里吃酒。小闲便去他家对林冲娘子说道:‘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一时重气,闷倒在楼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赚得他来到楼上。妇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再着些甜话儿调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闲这一计如何?”高衙内喝采道:“好条计!就今晚着人去唤陆虞候来分付了。”原来陆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内。次日,商量了计策。陆虞候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小衙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且说林冲连日闷闷不已,懒上街去。已牌时,听得门首有人叫道:“教头在家么?”林冲出来看时,却是陆虞候。慌忙道:“陆兄何来?”陆谦道:“特来探望。兄何故连日街前不见?”林冲道:“心里闷,不曾出去。”陆谦道:“我同兄长去吃三杯解闷。”林冲道:“少坐拜茶。”两个吃了茶起身。陆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长到家去吃三杯。”林冲娘子赶到布帘下叫道:“大哥,少饮早归。”
林冲与陆谦出得门来,街上闲走了一回。陆虞候道:“兄长,我们休家去,只就樊楼内吃两杯。”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两个叙说闲话。林冲叹了一口气。陆虞候道:“兄长何故叹气?”林冲道:“贤弟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陆虞候道:“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谁人及得兄长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谁的气?”林冲把前日高衙内的事告诉陆虞候一遍。陆虞候道:“衙内必不认的嫂子,如此也不打紧。兄长不必忍气,只顾饮酒。”林冲吃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遗,起身道:“我去净手了来。”林冲下得楼来,出酒店门,投东小巷内去净了手。回身转出巷口,只见女使锦儿叫道:“官人,寻得我苦!却在这里!”林冲慌忙问道:“做什么?”锦儿道:“官人和陆虞候出来,没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慌慌急急奔来家里,对娘子说道:‘我是陆虞候家邻舍。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只见教头一口气不来,便重倒了。只叫娘子且快来看视。’娘子听得,连忙央间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汉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内一家人家。上至楼上,只见桌子上摆着些酒食,不见官人。恰待下楼,只见前日在岳庙里罗唣娘子的那后生出来道:‘娘子少坐,你丈夫来也。’锦儿慌慌下的楼时,只听得娘子在楼上叫杀人。因此我一地里寻官人,不见,正撞着卖药的张先生道:‘我在樊楼前过,见教头和一个人入去吃酒。’因此特奔到这里。官人快去!”
林冲 见说,吃了一惊。也不顾女使锦儿,三步做一步,跑到陆虞候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只听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怜见救俺!便是铁石人,也告的回转。”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开门!”那妇人听的是丈夫声音,只顾来开门。高衙内吃了一惊,斡开了楼窗,跳墙走了。林冲上的楼上,寻不见高衙内,问娘子道:“不曾被这厮点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门。女使锦儿接着,三个人一处归家去了。
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迳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林冲自归。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娘子苦劝,那里肯放他出门。陆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内,亦不敢回家。林冲一连等了三日,并不见面。府前人见林冲面色不好,谁敢问他。第四日饭时候,鲁智深迳寻到林冲家相探,问道:“教头如何连日不见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师兄。既蒙到我寒舍,本当草酌三杯,争奈一时不能周备。且和师兄一同上街闲玩一遭,市沽两盏如何?”智深道:“最好。”两个同上街来,吃了一日酒。又约明日相会。自此,每日与智深上街吃酒,把这件事都放慢了。且说高衙内自从那日在陆虞候家楼上吃了那惊,跳墙脱走,不敢对太尉说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陆虞候和富安两个来府里望衙内。见他容颜不好,精神憔悴。陆谦道:“衙同何故如此精神少乐?”衙内道:“实不瞒你们说,我为林冲老婆,两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惊,这病越添得重了。眼见的半年三个月,性命难保。”二人道:“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妇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正说间,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症。只见:
不痒不疼,浑身上或寒或热。没撩没乱,满腹中又饱又饥。白昼忘餐,黄昏废寝。对爷娘怎诉心中恨,见相识难遮脸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门关上去。三魂荡荡,安排横死案中来。
那陆虞候和富安见老都管来问病,两个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来,两个邀老都管僻净处说道:“若耍衙内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内在一处,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内性命。”老都管道:“这个容易。老汉今晚便禀太尉得知。”两个道:“我们已有了计,只等你回话。”老都管至晚,来见太尉,说道:“衙内不害别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几时见了他的浑家?”都管禀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庙里见来。今经一月有余。”又把陆虞候设的计,备细说了。高俅道:“如此因为他浑家,怎地害他。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陆虞候和富安有计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唤二人来商议。”老都管随即唤陆谦、富安,入到堂里,唱了喏。高俅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陆虞候向前禀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见说了,喝采道:“好计!你两个明日便与我行。”不在话下。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语说道:“好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林冲也不理会,只顾和智深说着话走。那汉又跟在背后道:“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林冲只顾和智深走着,说得入港。那汉又在背后说道:“偌大一个东京,没一个识的军器的。”林冲听的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但见:
清光夺目,冷气侵人。远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琼台瑞雪。花纹密布,鬼神见后心惊。气象纵横,奸党遇时胆裂。太阿巨阙应难比,干将莫邪亦等闲。
当时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那汉叹口气道:“金子做生铁卖了。罢,罢!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来家中取钱还你。”回身却与智深道:“师兄且在茶房里少待,小弟便来。”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见。”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到家去取钱与他。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就问那汉道:“你这口刀那里得来?”那汉道:“小人祖上留下。因为家道消乏,没奈何将出来卖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谁?”那汉道:“若说时,辱末杀人。”林冲再也不问。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已牌时分,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听得说道:“又是什么多口的报知了。”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裳,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认的你。”两个人说道:“小人新近参随。”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见太尉。林冲又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说道:“教头,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禀太尉。”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两个人自入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林冲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不是礼。”急待回身,只听的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什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说犹未了,傍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恰似皂雕追紫燕,浑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诗曰:
头上青天只恁欺,害人性命霸人妻。须知奸恶千般计,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义萦心由秉赋,贪嗔转念是慈悲。林冲合是灾星退,却笑高俅枉作为。
话说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拿下林冲要斩。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来节堂有何事务?见今手里拿着利刃,如何不是来杀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唤,如何敢见。有两个承局望堂里去了,故赚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说!我府中那有承局?这厮不服断遣!”喝叫左右,“解去开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就把宝刀封了去。”左右领了钧旨,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见:
绯罗缴壁,紫绶桌围。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提辖官能掌机密,客帐司专管牌单。吏兵沉重,节级严威。执藤条祗候立阶前,持大杖离班分左右。庞眉狱卒掣沉枷,显耀狰狞。竖目押牢提铁锁,施逞猛勇。户婚词讼,断时有似玉衡明。斗殴相争,判断恰如金镜照。虽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从冰上立,尽教人向镜中行。说不尽许多威仪,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干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阶下。府干将太尉言语对滕府尹说了。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衔冤。小人虽是粗卤的军汉,颇识些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与妻到岳庙还香愿,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把妻子调戏,被小人喝散了。次后又使陆虞候赚小人吃酒,却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候家楼上调戏,亦被小人赶去,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皆有人证。次日,林冲自买这口刀。今日太尉差两个承局,来家呼唤林冲,叫将刀来府里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下。两个承局进堂里去了,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听了林冲口词,且叫与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B241来枷了,推入牢里监下。林冲家里自来送饭。一面使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告下,使用财帛。正值有个当案孔目,姓孙名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道这件事。转转宛宛,在府上说知就里,禀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道:“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孙定道:“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知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牢城。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两个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只见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两个公人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林冲道:“多得孙孔目维持,这棒不毒,因此走得动旦。”张教头叫酒保安排案酒果子,管待两个公人。酒至数杯,只见张教头将出银两,赍发他两个防送公人已了。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张教头道:“林冲,什么言语!你是天年不齐,遭了横事,又不是你作将出来的。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过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锦儿,不拣怎得,三年五载养赡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内便要见,也不能勾。休要忧心。都在老汉身上。你在沧州牢城,我自频频寄书并衣服与你。休得要胡思乱想,只顾放心去。”林冲道:“感谢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两相耽误。泰山可怜见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张教头那里肯应承。众邻舍亦说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时,林冲便挣侧得回来,誓不与娘子相聚。”张教头道:“既然如此行时,权且由你写下。我只不把女儿嫁人便了。”当时叫酒保寻个写文书的人来,买了一张纸来。那人写,林冲说。道是: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正在阁里写了,欲付与泰山收时,只见林冲的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女使锦儿,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寻到酒店里。林冲见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那妇人听罢,哭将起来,说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张教头便道:“我儿放心!虽是林冲恁的主张,我终不成下得将你来再嫁人。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来时,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费。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妇人听得说,心中哽咽,又见了这封书,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动。但见:
荆山玉损,可惜数十年结发成亲。宝鉴花残,枉费九十日东君匹配。花容倒卧,有如西苑芍药倚朱阑;檀口无言,一似南海观音来入定。小园昨夜春风恶,吹折江梅就地横。
林冲与泰山张教头救得起来,半晌方才苏醒,也自哭不住。林冲把休书与教头收了。众邻舍亦有妇人来劝林冲娘子,搀扶回去。张教头嘱付林冲道:“你顾前程去,挣紥回来厮见。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养在家里。待你回来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万频频寄些书信来。”林冲起身谢了,拜辞泰山并众邻舍,背了包裹,随着公人去了。张教头同邻舍取路回家,不在话下。且说两个防送公人,把林冲带来使臣房里寄了监。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说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见巷口酒店里酒保来说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请说话。”董超道:“是谁?”酒保道:“小人不认的。只叫请端公便来。”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当时董超便和酒保迳到店中阁儿内看时,见坐着一个人,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下面皂靴净袜。见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请坐。”董超道:“小人自来不曾拜识尊颜,不知呼唤有何使令?”那人道:“请坐,少间便知。”董超坐在对席。酒保一面铺下酒盏,菜蔬果品案酒,都搬来摆了一桌。那人问道:“薛端公在何处住?”董超道:“只在前边巷内。”那人唤酒保问了底脚,“与我去请将来。”酒保去了一盏茶时,只见请得腹薛霸到阁儿里。董超道:“这位官人请俺说话。”薛霸道:“不敢动问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请饮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筛酒。酒至数杯,那人去袖子里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说道:“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烦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认得尊官,何故与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沧州去?”董超道:“小人两个,奉本府差遣,监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烦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陆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连声,说道:“小人何等样人,敢共对席?”陆谦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着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处讨纸回状回来便了。若开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行分付,并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结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纪又不高大,如何作的这缘故。倘有些兜答,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当下薛霸收了金子,说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两程,便有分晓。”陆谦大喜道:“还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时,是必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陆谦再包办二位十两金子相谢。专等好音,切不可相误。”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三个人又吃了一会酒。陆虞候算了酒钱,三人出酒肆来,各自分手。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时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监押囚人来歇,不要房钱。当下董、薛二人,带林冲到客店里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三两日间,天道盛热,棒疮却发。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董超道:“他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里有余的路,你这样般走,几时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里折了些便宜。前日方才吃棒,棒疮举发。这般炎热,上下只得担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慢的走,休听咭咕。”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里埋冤叫苦,说道:“却是老爷们晦气,撞着你这个魔头。”看看天色又晚,但见:
红轮低坠,玉镜将明。遥观樵子归来,近睹柴门半掩。僧投古寺,疏林穰穰鸦飞。客奔孤村,断岸嗷嗷犬吠。佳人秉烛归房,渔父收纶罢钓。唧唧乱蛩鸣腐草,纷纷宿鹭下莎汀。
当晚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到得房内,两个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来解了。不等公人开口,去包裹取些碎银两,央店小二买些酒肉,氽些米来,安排盘馔,请两个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来,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边。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提将来,倾在脚盆内,叫道:“林教头,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挣的起来,被枷碍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计较的许多。”林冲不知是计,只顾伸下脚来。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滚汤里。林冲叫一声:“哎也!”急缩得起时,泡得脚面红肿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见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颠倒嫌冷嫌热!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话。自去倒在一边。他两个泼了这水,自换些水,去外边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林冲起来晕了,吃不得,又走不动。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动身。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耳朵并索儿却是麻编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时,脚上满面都是潦浆泡。只得寻觅旧草鞋穿,那里去讨。没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算过酒钱,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气。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唤不止。薛霸骂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将起来。”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岂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搀着林冲,又行不动,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
层层如雨脚,郁郁似云头。杈牙如鸾凤之巢,屈曲似龙蛇之势。根盘地角,弯环有似蟒盘旋;影拂烟霄,高耸直教禽打捉。直饶胆硬心刚汉,也作魂飞魄散人。
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今日这两个公人带林冲奔入这林子里来。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沧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里歇一歇。”三个人奔到里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树根头。林冲叫声“呵也!”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只见董超说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来。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树边。略略闭得眼,从地下叫将起来。林冲道:“上下做什么?”董超、薛霸道:“俺两个正要睡一睡,这里又无关锁,只怕你走了。我们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稳。林冲答道:“小人是个好汉,官事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说。要我们心稳,须得缚一缚。”林冲道:“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的绑在树上。两个跳将起来,转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道:“不是俺要结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候传着高太尉钧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话。便多走的几日,也是死数。只今日就这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须精细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话。”林冲见说,泪如雨下,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等闲来赴鬼门关,惜哉英雄,到此翻为槐国梦!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