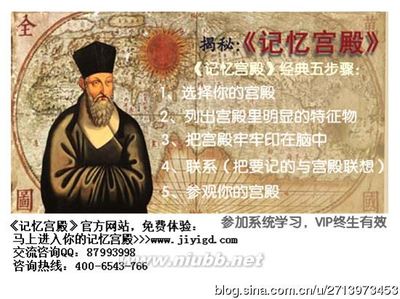巴陵戏名班岳舞台百年的风风雨雨
陈湘源
岳舞台是近现代巴陵戏的主要班社之一,从1914年建班,到1952年与新岳舞台合并成立“岳阳岳舞湘剧团”,活动时间长达38年。其间,历经曲折,饱受摧残,幸亏艺人们百折不挠,团结奋斗,才使巴陵戏得以火尽薪传,并不断发扬光大。
一、周吟鹤负气组班社
许升云受聘访名伶
民国初年,岳阳的戏剧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城内除不售票的县城隍庙、府城隍庙、南岳庙、火神庙、天王庙、李公庙(长沙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等8座庙台,时有乡班酬神还愿演出外,还是售票经营的咏霓、怡和、怡园、和平等4个剧院,经常挂牌演出。一时名优竞技,争雄斗胜,京锣汉鼓,热闹非凡。
1914年春节后不久,咏霓戏园老板陈汉溪请来京剧名宿路凌云所率京班,开场露演《群英会》、《三气周瑜》等剧。该班阵营齐整,文武兼备,一举轰动岳阳。一日,岳阳商会会长周吟鹤等11人,买了10张票,大摇大摆地前往咏霓戏园看戏。当时虽由戏园验票,但还有戏班监票。监票的艺人发现少了一张票,便求他们补票。周吟鹤坚持不补,艺人们据理力争。周会长恼羞成怒,将手中的票一把撕碎,率众愤愤回到商会。周吟鹤受此冷遇,决意自办剧院,并组织本名优进城,与外江班抗衡。他把这个想法对商会同仁说后,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只是担心本地班社行头破旧,恐难声威奇人。周吟鹤想:自办剧院自组戏班,既可附庸风雅,笼络人心;又可盘踞一方,开辟财源;还可借此抵制外来班社,出出这碰壁的闷气。于是断然决定以商会的名义兴建剧院、组建班社,并具体议定了三条行动方案:第一,将座落在玉清观的天王庙改建成剧院,定名“岳阳商办岳舞台”;第二,延请在岳阳城郊演出的清和班名小生许升云组建班底,薪俸从优;第三,以周吟鹤为首结股40人,每股出银元50块,派人赶赴外地购置行头。决议一经拍板,行动十分迅速。商会调集城内的能工巧匠,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天王庙改建成功。由于周吟鹤在这项工程中玩弄手段,虐待工人,以致在大革命中促成了他的死罪,这是后话。再说买行头的人到了上海,很快打听到顺清王的干女筱兰花,因顺清王正法,抑郁成疾,一病身亡。为料理丧事,其家人将筱兰花生前购置的一堂崭新的行头押在当铺;后因无钱赎取,当票被转到了汉口,价值正好是两千块银元。商会得知这个消息,星夜派人赶赴汉口买回行头。此时,周吟鹤志踌躇满志,只等艺人一到,即可挂牌开锣了。
许升云接到商会的聘请,当晚便与异父同胞兄弟丁国贤、丁爱田和师父钟和清商议。师徒们都感到,巴湘戏(岳阳地方大戏定名“巴陵戏”是1953年)自清末“巴湘十三块牌”、“巴湘十八班”的鼎盛时期后,历经刧难,此时虽有十二三个班社提锣钻乡,但技艺大不如前。如能通过商会汇集名伶,组建新班,无论从提高技艺,振兴巴湘戏剧,还是从保障艺人生活等方面考虑,都是大有裨益的。经过一番议论,大家决定让许升云应聘,丁爱田、钟和清全力相助。钟和清是清代名班小春和科班第一科的高足,出科不久,便在第三科任教。现在又是清和班的班主,在巴湘戏班中享有盛名,人脉甚广。经师徒合计,决定将清和班一干事务交与丁国贤料理,余则分赴四乡邀集名伶,组建班底去了。
二、岳舞台名噪巴陵郡
京汉楚销声岳州城
清末民初,湘北断续或长期活动的巴湘戏乡班有永和、天泰、春和、天胜、清和、文华、潇湘、十成、宝华、春林、老三胜、新舞台、少人和等十三个。由于战乱饥馑,名伶几乎凋敝殆尽。仅存的少数名伶,均为各乡班台柱,要将他们抽出来,难处实在太大。幸亏许升云能说会道,又兼钟和清素负盛名,终于说服了各班班主,将诸班大部分名角请到了岳阳。
当时,剧院和戏班都共用“岳阳商办岳舞台”这一名称。剧院行头精良,戏班名伶荟萃。生、旦、净三大行中12个主要行当都配双角,像三生、老生、小生、大花脸等,多有配至四五人的。全班共有90多人,比一般的江湖班多出一倍。著名艺人有:三生蔡碧林、何春茂、巢玉春、郑永林、陈太清;老生钟和清、马元泰、吴禄常、丁爱田、皮汉林;靠把李多文、苏升碧、苏升瑞;小生许升云、杨和风、彭和远;老旦易尧和、李春仲;正旦吴升华;闺门张普凤、万玉昆;蹻子周普美、周光钱;大花脸袁集喜、谭元明、凃训生;二净李福玉、雷元金、;二目头雷小春、郑同庆;三花缪纳春、胡永发、吴普忠、黄升福等。剧院首演亦是《群英会》打炮。演出中,鞭炮雷动,喝彩声不绝。艺人们劲头倍增,精、气、神俱备,真是异军突起,名噪古城,连演数月,座无虚席,就是当时的京剧名宿路凌云,对岳舞台也极为佩服,特别是对小生四块牌的天牌杨和凤,更是格外敬重。每逢杨演出,他总是缀演定票观摩。平日还常请杨聚餐,举杯论艺,推心置腹。岳舞台开张后,京、汉、楚各班营业开始衰落,只得先后收拾行囊,转赴他乡。
面对这一现实,咏霓剧院老板陈汉溪甚为不服。他以长沙会馆的名义,往长沙联络族人,以重金请得一湘剧班来岳,意欲与岳舞台见个高低。湘班经过一番筹划,于1916年来岳,但演出未逾一月,因观众太少,只得离岳他往。这主要是岳阳人对湘剧高腔不甚习惯,又兼当时人们的地方观念甚浓,加之周吟鹤等巧言利舌,四方活动,至使不明真相的湘班牵连受累;咏霓剧院从此也一蹶不振。1917年岳阳大火,咏霓被焚,至此,周吟鹤的心腹之患得以根除。不久,“讨袁”战争和南北战争接踵而至,周吟鹤因做了北兵内应,事务繁杂,慢慢对岳舞台很少过问,1919年干脆将行头租与许升云,他只坐收盈利,岳舞台戏院也改名岳阳大戏院。此时,岳舞台正式成为巴湘戏班的专一名称。
三、逢战乱岳舞台离乡井
遇灾荒六合公闯湘西
军阀混战,给岳阳还个千古兵家必争之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加之甲子(1924)水患,乙丑(1925)大旱,岳阳一带灾情惨重。饥寒交迫的灾民糊口尚且艰难,谁还有雅兴闲情来观赏这升平歌舞,盛世元音?岳舞台在本地无以为生,只得背井离乡,向华容、南县一带流徙,度日艰难。
许升云率班进入南县不久,却有常德文华班派专人来接岳舞台赴常德演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戏地域性极强,有如诸侯割据,各占一方,谁要想进入对方的领地,虽说不是难于上青天,确也要煞费周折。为什么文华班竟来邀请岳舞台去常德呢?这里有段前因。1918年,文华班与岳舞台同在安乡县演出,当时,文华班因天灾人祸,囊空财尽,无法还乡。许升云闻知此讯,立即向班友募化,得银元20块,奉送文华班,资助他们租船返回故里。如今听说岳舞台难以维持,文华班怎不全力相助?岳舞台在危难中盼到一线生机,个个欢喜雀跃,翌日即将行箱上船,扬帆逆沅水而上,直奔常德。
船到鼎州,但见江岸手臂招摇,人头攒动,原来是文华班的班友齐集码头,迎候故友。岳舞台的行箱搬进文华班的基本剧场──鼎盛戏园后,当晚两班即同台合演。文华班演出《沙陀搬兵》,岳舞台演出《黄鹤楼》。演毕,文华班又设盛宴款待。为了保证岳舞台的收入,文华班在与岳舞台分演日夜场十数天后,主动让出剧场,自己下乡演出去了。由于岳舞台班底实力雄厚,上演剧目丰富,又兼艺人善采众长,变易乡音,迎合当地观众口味,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业务一直很好。为了不使文华班长期在外演出,岳舞台便撤出常德,往桃源、汉寿、益阳等地游锣钻乡。
1929年冬,岳舞台进入益阳县城关,适逢国庆科班在此演出。巴陵戏国庆科班于1927年在湘阴县大湾杨太平庵起班,因班主杨美高不擅经营,起科虽有两年多时间,但学徒技艺提高缓慢,能演戏者寥寥无几。为摆脱困境,杨便借机提出将科班卖给许升云。岳舞台历经15度春秋,名老艺人多已谢世,有的年近耄耋,难以日夜登台,正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时。许升云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果断买下国庆科班,并将其更名岳字科,指派专人执教,重新习艺四年。许升云本是科班出身,加之管理得体,授艺有方,使巴陵戏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科班起死回生,面貌大变。此时跟班学徒中苏来保、胡仙霞等也崭露头角,与岳舞台的一批中年艺人交相辉映,又出现了人才济济的鼎盛局面。由于人手增多,又兼许升云处事苛刻,引起了部分艺人的不满。1931年,以苏来保、任金印、邓永启、易桂红、胡仙霞、李安生六人为首从岳舞台分出,另组成“六合公”岳舞台,公推苏来保为起师,领班从常德出发,经桃源、沅陵、辰溪,直达洪江、会同、靖县等地,一路颇为顺利。苏来保本欲领班进入贵州,但因班友思家心切,不愿作此长行,只得从靖县取道黔阳、怀化、芷江一带,转益阳、沅江返岳。抗日战争期间,又往沙市、湘西一带演出。
四、落陷阱坤伶受凌辱
遭颠沛名优丧异乡
岳舞台自分班之后,许升云自往常德经营纱厂去了,班里事务交与其子许明昆照料。许明昆即领班返岳,依旧演出于岳阳大戏院。时或出城钻乡,时或往湘、鄂、赣交界县城演出。
巴陵戏近代没有女艺人。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周光钱之妻田翠容学戏几出,间或演唱,开创了男女艺人同台合演的局面。但她学戏不多,影响不大。1933年,女艺人丁艳香随父丁爱田学戏,两年后露演于岳阳大戏院,即以其绰约风姿和精湛技艺一新时人耳目。其后,她又自制行头,学演新剧,影响日益扩大,终成巴陵戏坤伶一代名宿。
在旧社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俗云“世间只有三般丑,王八戏子吹鼓手”!而女艺人的命运就更为悲惨。抗日战争期间,当岳舞台再次逃难至常德剪家溪时,国民党九战区某连连长,传帖叫丁艳香前去陪客清唱,意在趁机侮辱。因班主坚决不应允,终于惹来大祸。这个连长假借商量演出筹款抗日为由,在“来来茶楼”备茶洽谈。艺人代表应邀前往,一上茶楼就遭到了对方伏兵的袭击。虽说去的艺人中朱岳寿、周岳狮等都练了几手拳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遍体鳞伤,跳下茶楼,混入围观的群众中逃走。周岳狮边走边吐血,待跑回班里,人已昏迷。伪连长还不罢休,扬言要提锣封箱,烧毁行头,硬将立足未稳、生计艰难的岳舞台赶出了剪家溪。
坤伶的厄运并未就此终结。1941年,岳舞台从慈利进入大庸,丁艳香又被当地土匪头子罗环九看中。罗环九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有时请唱堂会陪酒调戏,有时派土匪在戏院鸣枪骚扰,弄得岳舞台不得安宁。在罗环九用尽威逼利诱等毒辣手段后,终使温纯善良的丁艳香落入陷阱。这时,与丁艳香结婚不久的李筱凤欲与罗环九以死相拼,但考虑到全班老小的生计,又只得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罗环九得手后还不放过李筱凤。一天罗环九摆酒请客,以堂会的形式点李筱凤与丁艳香合演《秋胡试妻》。戏开场后,李筱凤排除了万感交集的思绪,慢慢进入角色。戏愈演愈真,罗越看越怒。忽然“啪”一声,罗环九拉开了枪栓,把枪口对准李筱凤,丁艳香见状,急忙用身体挡住枪口,周围的艺人也帮着苦苦哀告。罗环九见众人求情,便借机限令李筱凤即日离开大庸,并对天鸣枪,以示警告。这时的李筱凤,已是岳舞台老生行当的主要接班人,但面对残酷的现实,班友们只得匆匆筹资雇船,送别身穿破袄的李筱凤出了大庸城。是日寒风凛冽,乌云盖天,班友们目送孤帆远逝,无不酒下心酸痛楚的泪水。
坤伶被霸占,新角遭驱赶,名优更堪悲。仅以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为例,六合公岳舞台就先后有五个主要演员相继去世。他们是名冠湘西北的三鼎甲跷子胡应鹏、花脸李安生,老生“马大王”马元泰,老旦李春仲,三生新秀李岳云。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使六合公岳舞台掌班苏来保痛感独木难支,只得于1941年进入大庸,与岳舞台合班。不久,名重一时的文武三生邓忠林又染病身亡,班里日食维艰,无力掩埋,只得由其师任一新沿街化板。谁知讨来的一个木匣子又太短太小,大家含悲忍泪,勉强将他的尸体塞了进去,草草安葬。
岳舞台合班之后,由苏来保主事,继续在湘西活动。
五、抗日救亡群情激奋
劳军义演众志成城
在日寇占我大片国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满怀爱国热情的岳舞台全体艺人,没有采取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的态度,而是全力以赴,为唤起民众投身抗日奔走呼号。
1938年,由许升云之子许明昆主事的岳舞台离别沦陷的家乡,从南县进入汉寿。同年秋末,在汉寿成立了“岳舞台抗敌化装游击宣传团”。后删去“游击”二字,隶属国民党常德专员公署管辖。由许升云任团长,许明昆任干事。在此期间,艺人们编演《亡国恨》、《仙桃镇》、《桃花江》等戏剧和大量的曲艺节目,宣传抗日。
同年,六合公岳舞台亦在沙市成立了“六合公岳舞台抗敌宣传队”,又称“演剧一队”,隶属沙市市政府管理。由苏来保任队长,编演了《雨花台》等节目,坚持每周一次劳军义演,主要活动于鄂西南、湘西北一带。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艺人们不畏艰辛,常常是上午步行转点,下午演出,晚间排练。在班里收入太少、艺人无米下锅的时候,大家便将身边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来维持日常生活。红净冯福强,竟将多年积攒下来准备为独生女儿治疗眼疾的钱也献了出来。为使抗日宣传与营业演出并行不悖,丁爱田日以继夜地操劳,将他十年前改编的《岳飞传》认真加工润色,将科介、调度、锣鼓点子写得清清楚楚。排练中他苦心研究,每出新意。如《岳母刺字》,他以猪尿泡作假皮,用明矾水书字其上。演出时,“精忠报国”四字边刺边现,极为真实感人。由于他刻苦钻研,既缩短了排练时间,保证了演出质量,增加了经济收入,又达到了宣传目的。
在配合抗日救亡宣传中,至今仍令人怀念的要数文笑十。文笑十,湖北汉口人,话剧演员出身。抗日战争暴发后,与杨笑天等人流落湘西,搭班岳舞台直至病逝。其为人爽朗幽默,机敏聪慧,班友敬称他为“文先生”。他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慘状,又深恶痛绝一些国民党官兵不思抗日报国,反而干起以抓赌为名,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一次,他在借住的楼房里,摆开牌桌,打起牌来。路过的警察听见楼上口音错杂,热闹非常,如获至宝,连忙上楼抓赌。谁知上楼一看,唯有文笑十一人笑坐桌边。警察以为其他的人躲起来了,便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结果一无所获,弄得啼笑皆非,怏怏而去。原来是文笑十一人操着四省口音,故意捉弄这些发国难财的“抓钱手”。这些军警宪特及豪绅恶霸,抗日救国无能,敲诈百姓有方,且特别贪生怕死。每当日机来袭,警报一响,就争先恐后往防空洞里钻,只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听到鞭炮声也以为是机枪声,吓得跳进茅坑躲避。文先生将这些见闻,编成幽默风趣的曲艺节目,在每场演出前说唱,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教益。1942年春,他在创作宣传抗日的剧目《亡国恨》时,不幸身染伤寒,由于无钱医治,病情日见严重,有时高烧数日不退。为了不使班友受累,他只身跳入澧水河中浸泡,待体温稍减,又蜷缩在拼凑的书桌上奋笔疾书。《亡国恨》刚刚脱稿,他即含恨而死,年仅38岁!
为了犒劳抗日官兵,国民党常德专员公署和沙市市政府,曾以“中华民国戏剧总会”的名义,多次举行劳军义演和募捐义演。每逢这些活动,艺人们总是争先恐后,积极参与。当时只有16岁的刘立炎,尽管只学了几出丑角戏,也主动报名,唯恐后人。年逾古稀的马元泰,是六合公岳舞台进沙市接去打码头的。他看到班里抗日热情高涨,也不顾年迈多病,常常抱病参加义演。由于贫病交加和过度劳累,1941年病逝荆州。弥留之际还一再叮嘱班友:“抗战不胜利,不要把我的尸体送回老家。”充分展示了一个热心抗日宣传、至死不改其志的老艺人的高尚情操。
六、艺海浮沉休戚与共
世道维艰患难相扶
生活的道路本来坎坷不平,何况在那战乱频仍、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的动乱岁月?岳舞台由于长期流落异乡,处境自然更加艰难。但是,由于艺人们同舟共济,患难相扶,终于度过了重重难关。
为了不使年逾八旬的孤老艺人熊集凤在战乱饥荒岁月中冻馁而死,许升云派人将他接到班里,随班养老,班友们把他看成嫡亲长辈。熊老感慨万千,在随岳舞台辛苦奔波的最后十年中,每日起早贪黑,传艺授徒,记录整理传统剧本300多个,交给班里,以丰富上演剧目。可惜这些珍贵资料大多毁于兵燹,仅存的110个剧本,又毁于十年浩劫!熊老逝世不久,司鼓王庆生一家四口,突然三人染上瘟疫,未及两日全都死亡。为了筹资办理丧事,班友们个个解囊相助,苏来保将自己唯一值钱的皮袄也典当了。黄德明是岳舞台收留的流浪儿,随班学艺时,丁爱田视若亲生,不幸刚有所成就被日本飞机炸死,又是丁爱田筹钱掩埋。巴陵戏剧团有不少异姓兄弟姊妹的家庭,都是在那患难与共的年代组成。如李安生逝世后,留下孤儿寡母,无人抚养,王庆生便主动承担了抚孤肓寡的担子,至今李安生的女儿李玉仙与王庆生的女儿王菊仙及其后人,仍如亲姊妹一样往来。苏来保病逝不久,任一新即将其遗孤苏金仙带在身边,悉心照顾。任一新终身无子女,苏金仙承欢膝下,直至将二老安葬归山。像这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家庭,在岳舞台不胜枚举。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岳舞台在万万恶的旧社会之所以能延续30多年,除了扎紧把子,自强自立外,还得力于兄弟剧种一些戏班的大力支持。其中资助最多的当首推常德武陵戏班。前面提到的文华班救助岳舞台于危难之际便是典型例子。后来常德小天华班的雷华禄、黄华全、傅华亮、龙华云等,又在岳舞台人手短缺之时,主动搭班岳舞台一年多,为巴陵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巴陵戏与湘剧,俗称上、下路班子,传统友谊十分深厚。清代中、末叶,两个剧种常同演庙戏,各演半天,相执如宾。光绪年间,湘剧福字科班艺徒黄升福、方福秀未出科即到巴陵戏永升平科班学艺,黄升福后来成为巴陵戏名丑。二人还带来了高腔《锄豆》等剧,丰富了巴陵戏的上演剧目。1916年,湘剧班在岳阳咏霓戏园演出时,该班名净罗元德与岳舞台名净胡永发一见倾服,结为知己。二人常促膝论艺,互相学戏交流。特别是1938年,岳舞台在沅江草尾镇演出,恰遇从长沙逃难而来的湘剧福喜坤班。该班几乎全是青年女艺人,行动十分困难。岳舞台对此深表同情,主动承担起监护人的义务,两班合演近半年之久。文笑十曾撰联云:“湘班子,汉班子,班子合班子,多情的戏子;新难民,老难民,难民救难民,仗义的难民”,横披“同病相怜”。真乃两个剧种艺人休戚与共的真实写照。1942年,岳舞台艺人朱岳寿、熊正芳、杨岳红、钱岳才、罗岳英、朱花生等在逃难中失散,无处安生,多亏湘剧五云班主动收留,并长期留该班串演武戏,直至找到岳舞台为止。
巴陵戏与湖北汉剧是同源异流的兄弟剧种,其交往早在初有二黄之际。1771年,自幼在岳阳楚玉部学戏,且“名噪湖之南数年”的李翠官去武汉,带去拿手戏《贵妃醉酒》、《陈姑赶潘》、《玉堂春》,名动汉口20多年。道光二年出版的《汉口丛谈》,还为他立了传。嘉庆年间,岳阳人和班高秀芝在武汉演出,又受嘉誉。诗人叶调元颂扬当时戏艺的18首《汉皋竹枝词》中,就有两首是赞许他的。光绪年间岳阳人和班名老生贺四在沙市演出,收余洪元为徒,悉心授艺,使余成为了清末民初在武汉把水口的汉剧“老生泰斗”。沙市老郎庙碑曾载此事,惜今庙碑已毁,但《汉剧志》作了记述。岳舞台成立后,两个剧种的传统友谊日渐加深。《岳阳民报》1934年9月12日载:岳舞台参加“县救灾委员会”举行的游艺筹赈时,于外埠加聘坤伶多人同台合演。搭班的湖北汉剧艺人有鲁春艳、孔艳秋、冯小楼、小滑稽等。同台演出的剧目有《辕门斩子》、《陈姑赶潘》、《打花鼓》、《上天台》、济公拿妖》等。抗日战争期间,又有吴艳霞在六合公岳舞台演出《兴隆庵》中饰武曌,《三搜索府》中饰杜氏,《双下山》中饰小尼姑。继而冯春辉等十余人,又在岳舞台搭班演出半年之久。他们的搭班演出,大大的丰富了巴陵戏的表演艺术。
除上述剧种、剧团外,还有京剧、话剧等艺人,也为岳舞台的生存发展贡献了力量。如1935年,京剧艺人潘活猴就曾在岳舞台教徒传艺,将京剧的武打套式和高难度的翻扑技巧无私地传给巴陵戏艺人,对巴陵戏武戏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班友的团结,兄弟剧种的扶持,使岳舞台在垂危的生死线上不断获得了生机。
七、百卉竞芳奇花吐艳
两班合并枯木逢 春
岳舞台从建班以来,荟集了清末至建国初期近百年中巴陵戏的几代名宿,真可谓群芳争妍,馨香远播,现仅就前三辈人中影响较大者,撮要列传于下,略见其班底之雄厚。
熊集凤(1837-1927),汨罗长乐街人,12岁进集庆科班学戏,工闺门旦。他擅长唱功,讲究咬字发音,注重神情韵味,对巴陵戏旦行唱腔影响深远,曾先后执教永升平、春台等科班,桃李盈庭,各有所成。他好学饱记,行行皆能,一人可以教一个科班。80高龄到岳舞台随班养老,还传徒授艺,并记录整理了300多个传统剧目。
钟和清(1864-1916),汨罗营田人。小春和第二科学生,出科不久,即任教三科,人称“少先生”。他终身事艺,勤学不倦,生旦净丑无一不精,吹打弹唱无所不通,乃至经史书画,武术拳棍,都有一定造诣。他的内外八功也很深,如演《云台山刳莽》的王莽,手带刑具出马门,一个“梭扑虎”,飞身串过舞台,起身又是一个人多高的“仰壳子”,惊人心魄。演《莫成替死》的莫成,当唱到“那一厢急坏了徐大人”时,罗帽、胡须、手指与悬脚鸳鸯交错甩弄,上下三盘,情真技绝。
杨和凤(1862-1921),汨罗大湾杨人,11岁入小春和二科学戏,是清末“小生四块牌”中的“天牌”。他文武兼备,特别是颈上功夫老到,无论舞翎耍翅甩水发,全凭颈部暗劲,演来灵活多变。他演《三气周瑜》,为表现周瑜战败后,寻找丁奉、徐盛的仓皇狼狈的情境时,将水发甩起呈烟炬状,冲过舞台,不散不倒,至今尚无人步其后尘。
何春茂(1870-1922),汨罗归义街人,出身小春和第三科,工老生。他身材魁梧,嗓音清越。晚年对唱腔精心琢磨,并从京、汉剧名家的唱法中汲取养料,改革旧腔,锐意求新。他以孔明戏饮誉湘北。其《收姜维》中一段108句的唱皮,他运用花腔、子腔、反复叠唱等技法,使人百听不厌,至今脍炙人口。
马元泰(1867-1941),岳阳县龙湾人,三元科班出身。工老生。他敬业重艺,谁要在舞台上演出不认真,便当场斥责,人们敬称“马大王”。善用鼻音,注重神韵,年轻时即负盛名。尤擅长三国戏,有“活孔明”之誉。
老一辈的艺人们对开拓岳舞台的事业起了先驱作用。创业难,守业更难,继承而又发展了巴陵戏事业的要数岳舞台的中年一辈。他们大多年少进班,几乎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岳舞台。最突出的是:
许升云(1887-1962),汨罗归义街人,12岁入永升平科班学戏,工小生,坐科六年。1919年接手岳舞台起师,掌管该班直至1952年合班。他自幼刻苦好学,在科班即为师父的助教。为塑造好人物,他自学文化,修改剧本,使传统戏锦上添花。如《黄鹤楼》原周瑜出场只有四句简单的唱词,不能很好地表现人物。他便根据剧情串写了长达20句的长段唱词,运用北路的成套板式,揉入顿音、重音、花腔和险板承腔等技巧,既简略地介绍了“三讨荆州”的由来,又将周瑜年轻气盛、高傲自负的性格,酣畅淋漓、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人称“活周瑜”。他翎子功的水波浪花、太极图花,帽翅功的单闪、双闪、单转、双转;《赶斋泼粥》的抛鞋接鞋等均为绝技。1952年,他以《打严嵩》邹应龙出神入化的表演,获得省汇演专家的一致好评,被选为湖南省文联委员,并赴中南区汇演。
胡永发(1882-1966),岳阳县马家店人,11岁入永和班习艺,即以聪颖刻苦著称,为岳舞台、人和班挂牌红角。他功底深厚,善于创新,所演大花及丑角戏,皆称绝一时。其中,武大郎的矮桩表演,和尚戏中各种步法,转肩挪臀,伸颈舞佛珠,都能按特定人物和典型环境巧妙使用,丝丝入扣。1955年湖南省戏曲汇演时,他将《九子鞭》中的奸诈凶狠的刘谨刻画得惟妙惟肖,荣获一等演员奖,并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苏来保(1904-1950),艺名筱来保,岳阳县黄沙街人,从小入岳舞台,本工三花,后从丁爱田学老生,生旦净丑都能串演。他勤学苦练,转益多师,唱做俱佳,文武不挡,刻画人物,细腻深刻,名列岳舞台新秀“三鼎甲”之首。1977年,我们去武汉汉剧院采访汉剧名丑李罗克。进入李老家时,他躺在睡椅上问:“你们是哪里的?”对曰:“岳阳岳舞台的。”李老坐起来了:“岳舞台的,那苏来保老师还健旺吧?”对曰:“1950年就过世了!”李老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们说:“么事!他老人家过世了?他那叫仙戏啊!我一闭上眼睛,他老人家演的一个个鲜活人物就在我的脑海里转,转了几十年啊!”
丁爱田(1885-1946),汨罗归义街人,自幼随兄进清和班学艺,1914年受聘岳舞台,直至终老。他戏路极宽,常演的300多本戏,无论生旦净丑都谙熟于怀,打鼓操琴,亦见功力。其醉戏《禁马门》,醉笑能达两分钟之久,使人如闻满台酒香。《黄鹤楼》中刘备的“阴阳脸”──双目眼珠向两侧微斜,一边佯笑以应付周瑜,一边脸带忧含愁以寻觅赵云,摹态毕肖,独步艺坛。其它的蟒靠戏、剑衣戏、员外戏,皆演得惟妙惟肖,扣人心弦。
至于岳舞台的青年一辈,建国后大都成了巴陵戏剧团的台柱,如李筱凤、周扬声、丁艳龙、李玉仙、许云姣等等,老戏迷们今天还能数上一群。
1942年,岳舞台在大庸(今张家界市)合班后,继续在湘西北一带活动,直至1948年才返回岳阳。但演出不久,因遭遇国民党伤兵闹事,不得不再度往华容、南县等地钻乡。1949年6月,刚从华容返岳不久,7月20日,岳阳解放。岳舞台艺人欣闻喜讯,连忙组成秧歌队,迎接解放军进城,并在翰林街忠义祠义演三日劳军,以迎正义之师。1950年,岳舞台成立工会,由工会主席张义怀主持班内工作。1951年,岳舞台以“岳阳岳舞湘剧团的名义进入长沙市演出,获得省会观众一致好评。1950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通过在湘潭和岳阳的学习整顿,于10月与1945年杨岳红组班的新岳舞台合并,由李筱凤任工会主席,主持全面工作。1953年,曾称巴湘戏、岳州班的岳阳地方大戏,正式定名“巴陵戏”。至此,岳舞台走完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巴陵戏剧团却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这正是:历经坎坷卅八春,岳舞台上几浮沉,一曲皮黄变迁史,留待后人仔细评。
原载1986年7月《岳阳文史》第二辑。2014年3月2日重录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