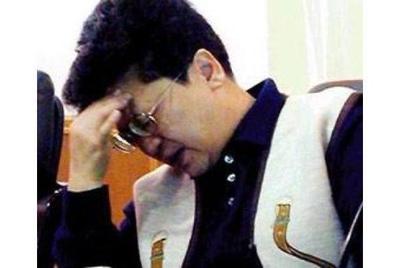重庆市第三届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二等奖2011.11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CSSCI),2011.6月出版
(本文已公开发表,转载须告知作者和注明出处。)
内容摘要:
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铜梁龙舞,在国际与国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它不仅是重庆铜梁的地方名片,更是中国乃至华人的民族徽号,是民族情感的集体凝结。“铜梁龙”以其龙体造型美、龙舞舞法活为艺术特点,是其他龙舞不能比拟的,以它的大气磅礴之美体现着当代中国人的自信与进取。本文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研读和对民间老艺人的采访,以及亲身参与到龙舞的活动中而作,梳理出龙舞(铜梁龙舞)的历史发展源流,及其艺术特色,着重力量放在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当代铜梁龙舞发展的决定症结,从本源入手,摸藤察蔓,在历史的解读中找出价值,以解今人之忧。
关键词:铜梁龙舞 龙崇拜历史价值 传承与发展 非遗保护

一、中华龙舞的发展概述
数千年来,龙就是华夏民族崇敬的对象,是民族的崇拜物,后人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以示敬意。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四灵之一,我国人民对龙的崇拜,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民间信仰之一,而且“龙崇拜”作为一种行为也较早地进入民间习俗的行列,早在三代时期,那尊神示鬼的殷商就已出现龙舞的活动,龙舞作为通神、求雨祈福乃至娱神的姿态逐渐成形,进入了龙舞的“滥觞期”。当今舞蹈史学家王克芬通过对史学的考究得出,“把十五个人与龙连在一起,排成一条长龙的形象”(“十人又五~~龙~田,又雨。”《殷契佚存》)力证商时的龙舞活动,他们迈着雄健的步伐用粗犷豪放的动作在天地中跳起祭龙求雨的舞蹈,而且用龙舞来祭祀求雨的场面已颇有规模和气势。这在那个巫术盛行、图腾崇拜的早期文明中出现是合乎情理的,是人类精神的文明产物,因此,龙舞在“祭祀”的摇篮中出世,在不经意之中创造了与天对话,与神对话的祭龙求雨舞,从此开始传承为风习,积淀为文化,绵延至今。
龙舞发展到汉代,进入了“飞升期”。这时的龙舞也在舞蹈的自身发展规律中得以解脱,不再是单独的祭祀活动,而是从祭祀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了一种独立的表演艺术,与当时的杂技、幻术、假形舞蹈(龙舞、凤舞、鱼舞)、歌舞戏等共同并入“百戏之中”,成为汉代艺术之代表,更有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作为引证,讲述着当时的舞蹈画面,“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这就是大规模、大场面的“鱼龙曼衍”舞蹈;除此,龙舞在民间被扎成黄、青、白、赤、黑五色,承担者求雨祭祀的作用,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五行”,在五行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创造了五色龙,并且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色神龙,它们在祈雨祭祀中分别为青龙(苍龙)居东方主木,春舞;赤龙居南方主火,黄龙居中央,夏舞;白龙居西方主金,秋舞;黑龙居北方主水,东舞;它们在各季节中穿着各色彩衣,舞起长达数丈的各色大龙,场面十分壮观。
隋唐时期,龙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龙舞不只是舞蹈的艺术,在其自身的造型没上得到了极限的发展,在龙体内装有蜡烛和油灯,至此“龙灯”的概念和形式也就产生。“龙灯”的点亮,翻开了龙舞辉煌的一页,这种新的龙舞样式得到了唐王朝的倡导。据福建福州地区《三山志﹒土俗》记载:“燃灯驰门禁止,自唐光天始,本州批准假三日,诸大刹皆挂灯球……又为纸偶人作缘竿覆索飞龙戏狮之象,纵士民观赏。”文中所谓“飞龙”既是指的舞龙灯活动,龙灯的出现,使龙舞艺术更加绚烂,并以它的光彩夺目而成为我国古代舞蹈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因此,唐代不仅仅是诗歌,乐舞艺术及其它文化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也是龙舞艺术值得骄傲的时代。
进入了宋代,龙舞完全渗入民间,加之宋代的社火形式,与勾栏瓦舍的出现,龙舞得到了极大的普及,每逢正月初一与十五,大街小巷都搭设有许多乐棚或影戏棚以及最精彩的灯山,观灯和耍龙灯可谓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宋代高度自我总结的艺术发展中,龙舞也历经了自我的重塑。而进入了明清,龙舞已经发展到有专门的组织来承担,他们不仅遗承了之前的祈福求雨,还会在宫廷中取悦统治者及达官贵人,因此,舞龙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门类而大大发展,除各种风习和程式,龙舞的艺术形式也得到了总结,舞龙者除了热情以外还要具备几种技能:一要掌握圆场功,以保证在跑圆场时身体平稳;二是要臂力,以保证在跑龙时龙身不因为分节而有断裂感;三是摆字时要保证速度与准确的路线,避免龙节因步伐和路线的差错而缠绕在一起;四是每个舞者都必须学会相同的数量的字形,以保证因表演对象不同时摆出不同应景字形的需要,可见这种训练有素,专业水准的舞队在明清时已成为主流,也悄然形成了雇佣关系,为龙舞的普及与商业化进程迈进了一步,进入了近代,龙舞的发展起起伏伏,龙舞的分支也在自我的发展改变中,其中铜梁的龙舞是最为耀眼的一致,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二、铜梁龙舞的历史渊源与独特魅力
铜梁龙灯,从广义上讲包括节日舞龙、民间祭祀等相关的一切艺术活动,是以龙灯为道具,集合舞蹈、音乐、美术为一体的民间综合艺术样式,其发展历程既离不开中国龙文化的演变发展,又离不开各纵向艺术门类的前进,有史记载早在三代时期就有“龙舞”的早期活动,至汉代而广为流传,宋元以后大兴,乃至到清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历史的姿态清晰的讲述着它的发展历程与荣耀,乃至近代的几十年,才让“铜梁龙”被人所熟知,走上高台,走出国门。那些淹埋于历史的资讯未能及时的跃然纸上,所以要想给铜梁龙的现代激活必须从系统的“艺术考古”开始,展开那一段鲜活的历史画面。
铜梁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重庆市西北部,地处川东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交接地带,介于东经105°46’22”至106°16’40”,北纬29°31’10”至30°5’55”之间。铜梁,历史悠久,山川锦绣,地灵人杰、物产富庶,唐代长安四年(公元704)建县至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河,波翻浪涌、大浪淘沙。县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重庆市西北部,地处川中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交接地带;南接永川县,西南靠大足县,西北毗邻潼南县,东北连合川县,东南与璧山县为邻。在1976年的“铜梁文化”遗址考古中发现,距今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战国时,先为巴国的垫江(今合川)属地,后属秦,历汉代至唐为合川的石镜县辖地。唐武周长安四年(704)始建县,以境内有“小铜梁山”,名铜梁县。至明清,先后又与巴川县、大足县、遂宁县、安居县分分合合,直至近代才得以“独立”地位。1983年铜梁划分重庆市辖县,截止至今,建县已历1307年的历史,其文化属性中既有中华民族的集体审美,又有独具巴渝特色的山地文明,其间“龙”的发展也是潜潜的准备着。
数百年来,随着龙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铜梁人民与龙灯、龙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年新春期间都要耍龙灯,端午赛龙舟祭江,遇天旱玩黄荆龙求雨,年终舞大龙、火龙、稻草龙庆丰收。古往今来,由笃信演化为娱乐,相沿成习,形成了铜梁民间传统的龙灯盛会。孕育、滋生了铜梁龙舞这一巴渝民间艺术之花。特别是清代,铜梁龙灯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据清道光本《铜梁县志﹒风俗篇》记载的盛况为:“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闹街市,有月逐入,尘随马之观。”且民间有“大足(县)朝佛,铜梁观灯、合川(县)看春”的民间俚语。但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时,铜梁龙灯这一民间艺术却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厄运,它被视为彰显帝威的代表,被扫地出门,视为封建糟粕销声匿迹。直到1980年,全国进行文化普及,才从北京吹来了抢救民间文化的暖风。铜梁龙从蛰伏中惊醒过来,重新显示了它的威风,1983年当铜梁龙在解放碑震动山城,1984年铜梁扎制的35节大龙首次在北京国庆三十五周年盛典上亮相,1988年9月铜梁舞龙队参加在北京市举办的全国龙舞大赛一举多得桂冠后,铜梁龙便开始腾飞五洲,享誉海内外,1999年被国家体育局宣布铜梁龙为“国家舞龙队”,2004年4月8日国家文化部公布铜梁龙为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2006年1月,国务院公布铜梁龙舞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殊荣种种,都代表着铜梁龙舞的当今取得的成绩,从古代的风行到近代的艺术高度都凝结在它那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之中。
三、铜梁龙舞的艺术特色
铜梁龙舞原是民间传承下来的一种广场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之所以备受各级文化部门的青睐,并在各种龙舞大赛中多次争金夺银,屡创辉煌,这与它突出的民族性,广泛的民俗性和鲜的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以下阐述其艺术特色。
(一)气势宏大,气氛热烈
在中国龙舞中,道具造型,构图变幻和动作套路是三个最基本的条件。而铜梁龙舞的主要特色是以大龙具、大场面、大套路、大变化来营造他的大气势。
首先从造型来看,铜梁龙的龙身较长(一般由24节组成,全场54米,超大可达100米以上),龙胸粗大壮实,全身丰满浑圆,立体感极强,价值龙出场时前有排灯引导,旁有云牌、黄烟衬托,且摆出一副皇帝出巡,大将出征的架势,所以,只要龙一出场,就会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风八面的视觉感受,其代表为“大蠕龙”,可达百米。
其次,从铜梁龙舞的套路和技法来看。由于套路较多(现有50多个套路),技法熟练、变化较大,所以,玩舞时龙的鲜活感极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199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见过50周年庆典,当重庆铜梁舞龙队以9条50米长的大龙、两只15米长的大凤和由160多牡丹花组成的牡丹方阵进入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时,不仅观礼台上和台下十万之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给予表演很高的评价。
(二)刚柔相济,表现力强。
中国龙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但从构图和动作韵律来看仍有一些共同特征,这就是梁力生在《中国龙舞》一书中所概括的“圆曲”、“翻滚”、“绞缠”、“穿插”、“窜跃”,其中“圆曲”是龙舞艺术的核心,“翻滚”是龙舞的基本动态,“绞缠”是龙舞动作形象化的诀窍,“穿插”是龙舞构图的基本路径,而“窜跃”则是保持龙体圆曲鲜活的的重要因素。
铜梁龙之所以誉满全国、享誉中外,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的还是龙体美、玩的活。龙体美是铜梁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而玩的活则是现代铜梁人集体智慧和审美情趣的结晶。如果玩舞时没有腾、跃、翻滚、盘、绞、缠、绕等技法的运用,就很难使一条人工扎制的彩龙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快慢结合、前后呼应、刚柔相济的动作组合就难以表现龙的威猛轻健和神力无边的雄姿,铜梁龙之所以给以人美的享受,龙体美、玩的活是其关键所在。
(三)灯火阑珊,别具一格。
铜梁龙舞自古与烟火相伴,有彩灯配合、龙舞玩的好否,也往往与施放烟火爆竹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烟花质量高施放数量多,玩舞的人尽头就越大,群众的热情就越高,节日的气氛也会烘托的更浓。
古时的龙灯在龙体内用油纸来照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操作方便改用电灯泡(干电池)代替,玩舞时龙体金光闪耀,四周各有灯笼和烟花配合。加上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的烘托,使铜梁龙舞更是风格独具、魅力无穷,并给人无以言表的兴奋之情。
(四)音乐艺术。
铜梁龙舞的音乐为巴蜀民间打击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要锣鼓有大锣、大鼓、大钵、二鼓、小号及唢呐等,其曲牌多用“长锤”、“和牌”、“赶眼”、“陕锣”、“水龙吟”、“朝天子”、“霸王鞭”、“伴灯鼓”、“双竹马”、“将军令”等等,由于铜梁龙舞注重形声结合,现场套打,并且根据情节或急或徐、或扬或抑,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优美抒情,所以,不但对渲染现场气氛十分有利,而且协调了动作,统一了节奏,当大蠕龙出场时,有雷鸣电闪般的前奏锣鼓先声夺人,首先给人一种震撼,接着龙舞队才在惊涛拍岸中亮相,当舞至灯舞“天花”时,打击乐用“扮灯鼓”加唢呐“朝天子”伴奏,使大蠕龙有天子排朝坐殿的神韵;当表演完“宝塔叠翠”时,锣鼓奏“尾煞”曲牌,凭听觉就能判断大蠕龙将在波涛声中返回龙宫。
铜梁龙舞除上述特点以外,简洁明快、风味古朴,酌加花边的对襟服装也给它增添了不少的民间风采。
四、铜梁龙舞的现状与忧思
从今天的铜梁龙发展来看,铜梁龙似乎进入了一个顶峰。处于顶点的铜梁龙该怎样来继续上升是我们该思考的,因为在龙舞的发展中有着更多的兄弟门类也在自我改革谋求发展,铜梁龙舞的不进就是一种固步自封,再加上铜梁当地的诸多对发展不利的因素,导致今天的铜梁龙舞的形式很不乐观,客观的讲,铜梁龙舞文化在一片辉煌的背后难以掩盖诸多隐忧。
忧思之一:铜梁龙舞艺术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铜梁龙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再次崛起,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各种国际国内的舞龙大赛,铜梁龙屡屡夺魁,其舞蹈艺术一直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但在2004年的江西第五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上海、湖南等舞龙队的表演艺术表现极高的造诣,并在服装、道具、音乐、套路以及演员整体素质等方面超越了他们,铜梁龙陡然有一种危机感。比如舞龙队的整体素质,他们的队员年轻化,平均年龄20岁左右,经过专业训练,其舞蹈记忆高超,身体灵活性强,大多具备专业体操和舞蹈的基础,表现出专业化很强的技艺水平,逐渐的脱离民间的“自娱气质”,而走向“专业气质”;而铜梁的队员,平均年龄超过了35岁,仅从面容上看就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在技巧和灵活上自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其次,在龙舞表演的套路上,上海和湖南已经有了大胆的创新,许多套路和动作令人耳目一新;而我们的套路总体上比较传统,新鲜的东西不多。第三,上海、湖南等队在服装道具上更胜一筹,道具龙的形态和色彩有不少翻新,不同的比赛项目选用不同的道具,再搭配合适的演出服饰,“龙”与人显得十分和谐,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我们的服装和道具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容易给观众造成视觉上的疲劳。
其次,就全国范围而言,许多地方的龙也是有着自身极强的特色和价值,比如湛江人龙舞、汕尾滚地龙、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泸州雨坛彩龙等都具备很强的挖掘价值,它们同铜梁龙一起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在做着积极而又努力的发展。
忧思之二:铜梁龙舞艺术传承形势严峻。从品种上看,为铜梁、为重庆、为祖国争得无数荣誉的只有“大蠕龙”、“火龙”、“竞技龙”等极少数的品种,而原生态的“黄荆龙”、“稻草龙”、“扁担龙”、“草把龙”、“鱼龙”以及“正龙”、“板凳龙”、“竹梆龙”、“高台舞狮”、“开山虎”、“南瓜棚”、“雁塔题名”等舞蹈却罕见其身影。即使是“大蠕龙”和“火龙”,它们原生态的元素也在不断弱化甚至淡出,没有很好的保存。
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传承人匮乏,铜梁龙的传授方式是口传身授的师传或是家传的模式,不论彩扎艺术还是玩舞艺术均没有图文记载,更谈不上音频记录,随着老艺人的不断减少,铜梁龙的许多样式和套路都已失传,其品种和传统元素也在不断减少。到20世纪50年代后,铜梁龙彩扎业有“三大传人”,既太平镇的周均安、安居镇的傅全泰和二坪镇的蒋玉霖,三人各有所长,尚能演绎铜梁龙彩扎艺术的精髓。但周均安早于1993年就已去世,蒋玉霖从1998年开始因病缠身而停止授徒,于2005年郁郁而终,如今健在的傅全泰,已70多岁的高龄,因颈部患肿瘤致使身体状况堪忧,作品极少,铜梁龙舞蹈的艺术传承给人们敲响了警钟,20世纪40年代以前,上有魏承模、赵贵云罗夕之等一批艺人活跃在民间;50年代后有影响的黄廷炎、尹登榜等艺人在重庆市群艺馆舞蹈辅导干部胡静的带领下挖掘、整理、创编并教习舞龙艺术,使得铜梁龙在20世纪后期达到顶峰;到今天,因多数时间应付舞龙的商业演出,铜梁龙舞已少有含金量的创编和传承活动了。
忧思之三:现有的铜梁龙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不理想。铜梁龙灯产品在整个文化产品市场中的占有率却微不足道,这就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最大支持。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全年,铜梁县龙灯文化产品销售总额仅为500万元,演出收入仅2500万元,不足整个文化产业收入的20%;而龙灯产业要作为铜梁文化的支柱产业,收入比例应不低于整个文化产业的80%,且应当不低于全县GDP的2%。
铜梁龙灯彩扎业基本上仍提留在较分散分散、较原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手工制作,费时费力,成本较高,没有形成高中低各种需要的制作模式,手工的高端技术可以保留和发展,在手工技艺上精益求精,在中低端机器化大生产的保障下用于各种文娱活动或者宣传。除此,在龙舞的宣传模式上应该放开放大,不仅仅只停留在简单的“文化状态”中,怎样才可以跨越此界限,让文化走向市场,龙的衍生产品,龙的媒体宣传都是眼下必须要做的。对于工艺品,怎样才可以吸引大众,在造型的设计上应该尽可能满足各种年龄的人群,以适应铜梁龙文化产品的大繁荣,衍生产品发展的好,也会给铜梁龙的专业发展和学术发展带来很多保障,再加上行业的提升,铜梁龙自然会有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再看龙文化的演出、教习、培训、营销市场,由于铜梁龙灯文化市场发展刚刚起步,很不成熟,政府还没来得及制定相应的规范办法,加上相应的行业协会没有建立,无法发挥其自律作用,因此,基本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不规范的广告,不规范的价格,不规范的经纪人,导致胡乱杀价,竞相拆台,错制滥造,使得铜梁龙灯艺术品对外输出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这既是影响到静音这的经济相依,也直接影响到铜梁龙灯品牌的声誉。
忧思之四:铜梁龙文化宣传的系统性不够。客观的讲,政府在铜梁龙文化的宣传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举办龙灯艺术节,实施“五个一”工程,央视播放专题纪录片,四次晋京参加盛典,多次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如此种种的大手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铜梁龙灯的知名度,也提升了铜梁的整体形象。但就目前来看,宣传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宣传内容上看,目前局限在大大小小的龙舞活动方面,对龙舞艺术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魅力宣传不够,对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情感的纽带以及龙舞艺术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很少阐释,对铜梁龙彩扎艺术则基本未提及,从宣传的形式上看,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媒体互联网,利用得很不够,几家龙舞艺术团体借助一些网站的服务器对自己的企业走了宣传,但宣传内容呆板,缺少更 新。而由政府主导的专题性的、动态的、内容全面的宣传网站则没有建立,缺少主流声音的铜梁龙灯给外界的印象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
忧思之五:铜梁龙灯文化艺术研究力量薄弱。目前,铜梁县从事龙灯文化研究的力量一场薄弱,能坐下来搞研究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像有一定成就的王万明、戴明、杨建国、李明忠等老同志,他们从事研究工作也基本出于自发的状态,没有谁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任务,也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铜梁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其实,研究成果对龙为文化品牌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国各地打龙文化牌的地区不少,许多城市都自诩为“龙乡”、“龙都”甚至“中华第一龙”,且拿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河南安阳就因出土文物距今7000多年而自诩“第一龙”,铜梁县对龙文化的研究仍提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这些年没有新的突破,因此在对外交流中显得十分被动,巩固“中华第一龙”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自信。研究成果对发展龙文化产业同样至关重要,同来那个龙灯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需要什么载体,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创新理念作支撑,这些年,铜梁龙文化产业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而处于自然发展状态,错过了很多发展壮大的机会。
铜梁龙舞的发展承受着巨大的压了和挑战,但是也有着很多的机遇。比如现在国家越发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和扶植,铜梁文化部门也在积极应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未来的五年计划,也延伸到了2020年的总体目标,我们相信铜梁龙舞会在它积极的发展中重新站在中华龙舞的高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强。
参考书目:
《重庆通史》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
《中国龙舞》梁力生 葛树蓉 著重庆出版社
《龙舞》周艳林主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舞龙》张琳钟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汉代百戏报告》王海涛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
《龙乡铜梁》“龙乡铜梁”编委会编重庆出版社
《铜梁县志》铜梁县志编修委员会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铜梁龙灯》铜梁县党史县志办公室铜梁县文广新局编
《舞蹈知识手册》 隆荫培 徐尔充 欧建平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 袁禾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舞龙舞狮——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罗斌 宋梅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