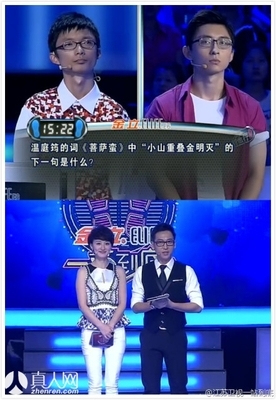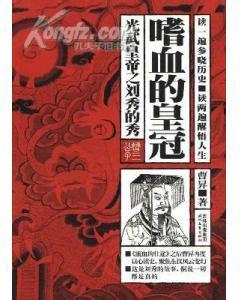不拘言笑的刘庆邦
作家刘庆邦这个名字,已经伴随我生活了许多年,早已“硬邦邦”地刻在我的心壁上。说实在话,平日忙于琐事不善于独坐室中静心读书的我,对刘老师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走窑汉》和改编为电影《盲井》的中篇小说《神木》。在我的印象里,刘老师是当代作家写“煤矿题材”小说的第一人。
那天,坐在教室里,我看见一个个头不高、衣着朴素,谈不上风度翩翩的人迈步走上讲台,坐了下来,再看面容,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你可以把他黝黑、略显油光的面容和农民、矿工联系在一起,但你肯定不会想到他就是享誉全国的“短篇王”,因为在他的外表里,你实在寻觅不到一点书卷的气息。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
刘老师,穿一件并不展挂的蓝西装,里面一件素淡的羊毛衫,黑黑的头发稍有些凌乱。一看就是个平日里不拘小节,不在意穿戴的人。在他的眉宇间,凝结着一团团散不开的忧虑。从表情上看,他当农民、矿工和十几年记者的经历,已经把他打磨成一个不拘言笑、遇事冷静坦然的硬汉子,实质上,我已感觉到他内心涌动的儿女情长和善良柔润。特别是,他讲到对母亲逝去时的感受时,两眼含着朵朵欲开的泪花,惹得我也陷入了想娘的悲伤。
在讲课中,刘老师不紧不慢、语调舒缓,他从作品的“虚”与“实”娓娓道来,引经据典,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历程,给学员们上了生动、熨贴的一课。给我最大启发的是他讲到关于《神木》的创作构思:犯罪分子结群,诱骗另一名农民工加入,然后下煤矿打工,再把被骗农民工打死,制造矿难假象,再冒充死去矿工的亲人,骗取矿住的赔偿金。这个案例许多人在新闻报道里都看过。如何写这个题材?刘老师采取了农民工儿子高中毕业寻找失踪父亲,又被两个犯罪分子在火车站寻找“猎物”,诱骗去煤矿打工这样的角度展开来写,是作品马上立了起来。
这告诫我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不要拿起笔来就“直捅捅”的写,要先思而下笔,要学会换个角度去讲述。
刘老师一直没有展开自己的笑容,就连和文友们照相时,都是极其平静的。他说自己是个十分“心重”的人。是的,我在生活里也是个“心重”的人,所以,我才会在刘老师不拘言笑的外表里,我分明感受到了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依然流动着满腔善良、温暖、慈爱的血液。
2011年12月24日下午在太原讲课,晚上回北京。25日就是刘老师60周岁的生日,又恰逢圣诞节,全世界的人都在为刘老师过生日。
刘老师,真是个幸运之人啊!一定会继续创作丰收、健康长寿的。
刘老师讲课笔录精华
1、关于文学创作,有人认为可以传授,有人认为不可传授。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可以传授的。创作是有技术的,也是有规律可偱的。关于举办作家班,王安忆曾经说过,就是要“引导和提高作家对写作的兴趣,要发现天才,要使天才克服懒惰,变得勤奋。把琐碎的才华整合成一体”。
2、作家要讲究细节之美,要锤炼语言,要提高审美自觉。
3、我对母亲的感情,在她逝去后,久久不能释怀,不能从悲伤中返回来。我不是不明白,但就是不能返回来。
4、每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都是一个心重的人。心的重量决定了作品的分量,因为任何作品都是生命派生出来的。好多人不远承认自己心重,认为心重是“小心眼”、偏执。其实,心重的人敏感、善良,是对责任心的一种承担。
5、心重,“九九归心”,生命的分量,是作家的分量。一个心重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分量的生命。
6、有什么样的生命,写什么样的作品。生命的质量、分量、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分量。任何好的作品,都是生命之弧、之光,都是作家的另一种精神形式。
7、作品的质量,是作家独立思考世界的能力;作品的分量,主要是一个作家的阅历、经历,长年的累积,这是后天的。
8、沈从文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出《史记》,有这样的文学态度,最主要的原因与司马迁一生各方面所得到的教育有关这些不仅仅是积学能完成的。”有分量的生命,都是有痛苦和忧患意识的生命。
9、古埃及,人死后,把心取出来,称重。超重就不能成为神,来世也不能再成为人。就会把超重的心,丢给犬,把心吃掉。我宁可不成为神,下辈子不变成人,我还是让我的心继续“重”下去。
10、大量的小说写的过于实,和现实拉不开距离,和新闻拉不开距离,多是对生活的一切照相。看不出新鲜的东西,雷同,非常写实。有的刊物设“非虚构”,我不赞成。这会给作家造成误导,引导作家越来越实。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种虚构。虚构不是虚幻、虚无,是审美层面的飘逸、空灵、诗意化。
11、汉字是最好的。每一个汉字都是实体,局限于实体之中。西方与拉丁字母是表意的。
12、小说有三个层面:1、从实到虚;2、从虚到实;3、从实再到虚。也就是从入世到出世,出世再入世,入世再到出世、超世、超越。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都是雾,看水变成一片云。
13、实是虚的基础,虚是实升华出来的。机场的跑道决定了飞机的起飞。
14、经历和生活十分重要,凭空想像。是想像不出什么东西的。细节是从回忆中得来的,离不开自己的经历。
15、凡是使人上瘾的东西,第一次都不是很好的。比如喝酒、吸毒······
16、女人失身第一次伤感,男人失身第一次也很伤感。《神木》改编成《盲井》,得了20多个奖,也挖掘出了王保强这个具有天赋的“本色演员”。
17、写小说都要找到自己。从广义上来说,写自己,找到自己的心。写自己的心,只有找到自己,抓住自己的心。
18、一个人一旦有了生命意识,就显得很迫切。到了一定的岁数,死亡意识就会逐渐强烈起来。死了,就和世界没有什么关系,进入了虚无、未知。一个人的弱点是克服不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有种紧迫感。
人往往急于抓到的是物质的东西:男人急于抓到女人,女人急于抓到大款。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抓不住,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好了歌”里说的太清楚了。
虽然物质的东西抓不住,但可以抓住自己的心,抓住心和世界的联系,同时再造一个世界。我之所以选择写作,热爱写作,就是要抓住自己的心。
曹雪芹抓住自己的心,再造了一个《红楼梦》的世界。越来月散发出艺术的光辉。是从“虚”再到“实”的典范。
19、好作品,可以激发你的想像,达到诗意化的境界。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契柯夫的《草原。、沈从文的《边城》。一夜就能看完的小说,不是好小说。好小说要一段一段的看,舍不得一下子看完。
20、写“虚”的作品,情节极其简单,但细节丰富,刻画人物与大自然贴的比较近。从大自然里“借”了许多东西,描写大自然多。道发自然,归到老子的自然大道。
21、现实大致是相同的,因作家主观的区别才不同。作家思想水平的高低,显出作品的高低。对世界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歌颂金钱和权力。作家是一个不和谐的“动物”
22、小说不是讲道理的,但一篇小说里的思想非常重要。每一篇都饱含在里面。思想在引导,完成从此岸到彼岸。思想上不去,作品就上不去。
23、王小波的独立性,对文革生活有自己的创作。遗憾英年早逝,如果坚持到今天,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张爱玲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出来的。她作品的思想性,和鲁迅、沈从文不能同日而语。
圣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输入。
一个人大悲才有大慈。有了悲痛感,就会有悲悯情怀,提前看到了生命的尽头,看开了,就会慈祥、慈悲。好的作家都有悲痛感。
(以上段落没有经刘庆邦老师过目审阅,如有不妥之处,请博友见谅指出)
作家刘庆邦简介
刘庆邦,著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1967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矿务局宣传部干事,《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主要作品:《断层》、《高高的河堤》、《落英》、《走窑汉》、《心疼初恋》、《刘庆邦自选集》 《梅妞放羊》、《不定嫁给谁》、《在深处》、《家道》、《胡辣汤》、《屠妇老塘》、《鞋》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
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千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下井最有趣的“发现”,他认为,凡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
对于矿工特有的性格,刘庆邦喜欢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幽默”来浓缩。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最让刘庆邦难忘的是这样一个细节:矿工上井喜欢喝酒,上街看女人喂眼———这是矿工们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上街看漂亮女人。矿区永远是缺少女人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渴望。除了女人,矿工们另一个消遣是喝酒,有时候空着肚子不喝酒,也能划拳。
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这实际上是极具风险的,但令人钦佩,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做煤矿报道记者这个职业,让刘庆邦开阔了眼界,让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很多矿工被困井下,那天漫天大雪,刘庆邦去报道矿难,他看到很多矿工亲人日夜都在苦守,他们希望亲人能够生还。这其中有抱着孙子的老人,他表情惶恐,但强忍着,不敢掉泪,怕的是不吉利。还有个老矿工站在雪地里,人拉他,他不肯进屋。“在这种情景下,作为记者你不用问任何问题,你只能用心体察,用心体会。”刘庆邦回忆说:那一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发现刘庆邦像是记者,就问他是不是来采访。刘回答说是,年轻人继续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劝他别悲观,他摇摇头,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叫刘庆邦大吃一惊,小伙子问:“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话当时就令刘庆邦心如刀绞。“这孩子要参加工作,必须要以父亲的死亡为代价……这里面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你却无法写进报道。”后来,这个在他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被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小说《雪花那个飘》。
世界上,有矿区生活经历的作家并不少,当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要坚持时,他说,“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我曾经看过一份矿工与矿主签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若出现意外,一只指头赔偿50元”。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著名作家刘庆邦工作照片
“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 ,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
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著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全国著名诗人,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山西文学院副院长潞潞老师主持刘老师讲座
刘老师的话语, 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进我的心里
诗人,自有诗人的气质和观察世界的睿智和冷峻
听刘老师的课,对我的创作意识有了一次转化,我受益匪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