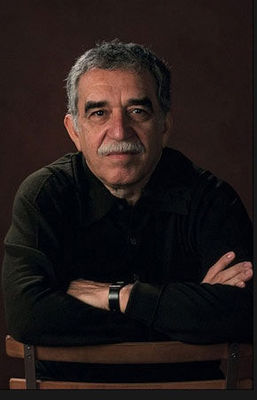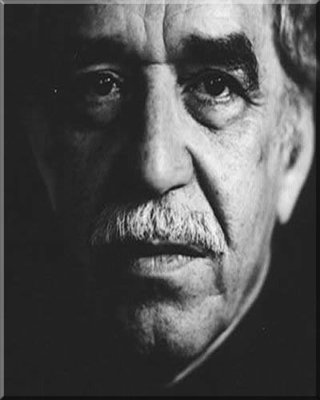文字整理: Flora Death2010年2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Universal Edition
中文翻译:杨松斯特别观察行动组
“当我第一次听马勒时,我仿佛就身处在天堂。”
1.您还记得第一次听马勒的音乐是在什么时候吗?杨松斯:我恐怕记不清楚确切的年份,我已经不是那么年轻能够记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笑]。我认为大约是在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初,大概是在那段时期,我那时16到18岁左右。我很难精确的说出,因为我成长在音乐世家,从小听过很多音乐,和我的父亲一起去听音乐会、看歌剧。这就让我很难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听过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
2.当您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去更多了解这位作曲家(马勒)时,当时的经历、体会是什么?杨松斯:我记得第一次听到马勒的音乐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仿佛就身处天堂之中。尽管当时我很年轻——我当时大概在上音乐学校或者已经在音乐学院深造,我记得不太准确——但是他的音乐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绝对就身处于天堂之中。他就是那样的天才,那样的伟大的作曲家,我认为当你年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总会认为,那(马勒)就是“我的作曲家”。这种感觉(马勒是“我的作曲家”)在我接触马勒之初就立刻产生了。我迅速地就对马勒的音乐产生了极大的热爱,并且这种感情从未消失过。
3.在当时的苏联,马勒的音乐接受程度如何?杨松斯:当然人们对他了解的不多,也很少听他的音乐。我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当时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老师拉宾诺维奇教授(NikolaiRabinovich)是最早介绍马勒音乐的指挥之一。他指挥学生管弦乐团演出马勒的作品,甚至是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当然还有另一位十分欣赏马勒的顶级指挥家基里尔·康德拉欣(KirilKondrashin),他指挥马勒的作品并使得马勒在苏联变得更加受欢迎,可以说在苏联是他“发明”了马勒的音乐,你也许会说那不是“发明”,但是他指挥马勒的作品非常棒。总之他是一位杰出的指挥,非常严肃,在我的记忆中他指挥的每部作品真的都非常精彩,包括他的马勒。另外,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我第一次听马勒的作品是他的第三交响曲,也就是我现在正要演出的(采访时,杨松斯正在与RCO排练马勒第三交响曲)。

4.我们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十分欣赏马勒……杨松斯:是的,他(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过:《大地之歌》仿佛将他带到了天堂。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斯拉瓦(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Rostropovich)曾经告诉我的。我经常自问:如果你只能带一部作品或CD去荒岛,那么你将会选择什么?这确实是个相当难的问题,我总是说:“我不能抉择,真的不能。”但是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大地之歌》。斯拉瓦(指罗斯特罗波维奇)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亲密的朋友,而我与斯拉瓦关系很好,因此他给我讲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些话。
5.肖斯塔科维奇是如何这么了解马勒的作品的?马勒的作品一直能演出吗?甚至在斯大林时代?杨松斯:是的,当然。马勒的作品并不是禁演的,他也许只是不那么被人所熟知。当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也在苏联演出,我记得当时公众的反响,他(肖斯塔科维奇)十分受欢迎,民众的勇气也因他而增强。我不喜欢用“理解(understanding)”来表达,因为在我看来理解音乐声响的想法是很有趣的。你可以理解语言,但是我不确定你也一定能理解音乐——也许它(指understanding)在这种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我想也许通过讨论人们对音乐的感受和人们与音乐的关系,是描述它比较好的方式,但是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还记得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关系如何,人们喜欢他的音乐的程度,以及他如何不断受大众欢迎的。当然也不一直是这样,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的人们都真正喜欢他。我记得有人说,他们对此(肖的音乐)并不确定,当然他们是在说无法“理解”他的音乐。因此肖斯塔科维奇是不断被大众欢迎,并且最终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勒。尽管我当时不在西方生活,但是也适用于西方国家,甚至是在著名的维也纳。马勒的受欢迎程度也是一步一步加深的,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嗯...或者不是说正常,而是一种事实。
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马勒如此受欢迎?”我也自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如此受欢迎,每个人都热爱他,每个人都在谈论他?有一些人会说“马勒对我来说太复杂了”,但是同样我认为那些说“我的世界属于布鲁克纳”的人,也许也并不多。马勒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受爱戴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音乐包含了全部世界、所有事物:宇宙、自然、人类、悲剧、讽刺、爱恨、争斗等等,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在他的音乐中。因此,在我看来每个个体都会形成一座通往马勒音乐的桥,也许是这个、也许是那个、也许多一些、也许少一点。就像一面镜子,你看着看着,会突然发现有一些与你很接近和共通的东西。我并不虚伪地认为我说的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以上我说的,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受爱戴,为什么每当你听到马勒的音乐都会觉得是极为重大事件的原因。
6.您认为马勒的音乐与他的人生(他经历种种斗争,要应对反犹太主义)有什么联系?两者之间有关联吗?杨松斯:[笑]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勒的人生,他的所说、所写、所想与他的音乐没有任何关系,音乐就是音乐。我们知道马勒经常在完成作品之后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说自己并不想这样,等等。但是对于我作为指挥来说,了解马勒的人生、所说、所写,以及他的情感,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对于马勒而言,这是我的方式或程序,我一直是这样准备每一部作品(演出),不论是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还是巴托克,都是如此。我需要时间去走进作者的世界,沉浸其中。作为一名专业指挥我可以在技术上很快地完成准备工作,你甚至会说我已经指挥了几乎所有的作品,只要再重复一遍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想真正完成一次我称其为“宇宙性的(cosmic)”演出,这样做是毫无意义而失败的。这种方式(指机械演出)意味着你已经不在地球上,而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中,一个渐强、渐弱、重音、速度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的维度中。
事实上,你在一个充满内容的世界中,你就在“音符的后面”,因为这些音符就是标志,你可以通过这些标志做出很好的效果:可以让它们渐慢或渐强,可以营造出有详尽诠释的过渡部分和完整的旋律线,甚至还可以营造出美妙的音响效果。但是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我很难解释那些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把它们描述成某种宇宙的维度。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指挥真正的天赋?在我教学工作的经历中,我能够解释什么是“指挥”,但是诚然,指挥真正的天赋是一个谜,这确实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对于我个 人而言,把自己沉浸在作者的经历中或作品的氛围中是尤为重要的。比如,当我在准备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时,我看了贝多芬在写第二交响曲时写下的《海里根施塔特遗嘱(HeiligenstadtTestament)》后,我痛哭不已,与此同时我还在思考,这位伟人在如此令人担忧的处境中却写下了第二交响曲,实在是难以置信。之后当他写第三交响曲时,他又是在何种精神状态下呢?我想这些都会给我(处理作品的)灵感。有些人会说“这都与音乐无关”,好的,也许是这样,但这是非常个人的问题。因此我还是要重申,我喜欢去了解作者对作品的解释,所思所想,甚至一些与音乐毫无关系的有趣之事。
当马勒为第三交响曲起名字时,他用了潘神(Pan)的形象,这里有一很有意思的故事:当他正在写标题时收到了Annavon Mildenburg的信,他在信封上写下了P.A.N(Post AmtNummer,邮局号码),之后他认为这是一种信号。也许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这给了我不少灵感,我无法解释,但是他给了我一些很特别的...也许是想象空间,我不是很确定。
7.当您在维也纳学习时,是否听了很多马勒的作品?杨松斯:是的,不仅仅是马勒,我几乎听了维也纳所有的音乐会,生活在维也纳就仿佛是我人生中神圣时刻。当然我在圣彼得堡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我不得不说那(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指挥学校。我们有极好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西方国家并不很多:有专业的管弦乐团让我们来练习,在专业的歌剧院里排练、演出芭蕾和歌剧。因此我在很早的阶段就开始指挥歌剧和芭蕾。这十分重要,因为作为指挥这些就是你的“乐器”。在列宁格勒这样一个更加西方化的城市,我有很多极好的老师,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楷模。首先必须要说到的是穆拉文斯基,他十分欣赏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在这个层面上他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苏联指挥。当然还有出生、成长在拉脱维亚的父亲,以及我的老师拉宾诺维奇Rabinovich,他对布鲁克纳、马勒、莫扎特等等都有极大的兴趣。
我能来到维也纳,这个音乐世界的中心,这真是一份天赐礼物,难以置信。我在音乐学院跟Swarovsky和KarlOsterreicher学习,还有跟其他所有的教授学习实在是太棒了。我学习了很多古乐方面的知识。JosefMertin教授是著名的音乐学专家,他非常有趣,但经常会忘记人名。他有时对我说:“嗯...列宁格勒先生,请过来一下。”(‘Ah,Herr Leningrad, kommen Sie bitte’)[笑]我非常幸运能看到这里所有伟大指挥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我不得不说,我每天都要去歌剧院或者金色大厅或者音乐厅。即使在周日,我也总是会去看三场演出:早晨、下午、晚上。所有的售票员都认识我:我们经常能从音乐学院得到极其便宜的票,有时我忘记了带音乐会票,而没有时间回去再拿,不管我去哪里看演出,他们(售票员)总是会放我进去。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在天堂,我在维也纳学到了很多,从那时起维也纳成了我最喜爱的城市。它就在我的心中,我每次去维也纳总能感到一些特别的,一种十分积极、健康的力量,我在维也纳感受到的一切和这种关系真是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但是这种感觉至今存在。我经常去维也纳指挥我的乐团或者维也纳爱乐乐团,对于我来说那总是一个神圣的时刻(HeiligeMoment)。
8.您是否认为维也纳乐团的音色影响了作为作曲家的马勒?杨松斯:我不确定。众所周知,门格尔贝格与马勒之间的关系。很遗憾门格尔贝格的录音不是很多,但是仅有的录音中,你可以听到门格尔贝格的马勒作品风格中,有很多滑奏和在音符上的慢慢推进。我不确定马勒本意真是如此,因为你也许会说如果马勒想滑奏他会写在谱子上。你可以对此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我可以找到很多证据证明为什么他写在这里,而不是那里,这是有逻辑的。你有时会在音乐中找到一些,你会说:是的,我能够理解它因为如此如此。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比如,他在一个地方写着“collegno(用弓杆击弦)”,在另一个地方写着“mit dem Bogengeschlagen(用弓背击弦)”,这确实不很清楚他到底是否要“col legno”或者“mit dem Bogengeschlagen”,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你在这里演奏时collegno(用弓杆击弦),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举个例子,在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最后部分,最后两页中,你可以听得到一点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声音,但是我认为第一小提琴的声音就不能够同时被听到,只有当你做出一些特殊的处理和人工改变才能所改善。但是我认为这样处理马勒的音乐不很合适,因为他在思考阶段所想的音响效果是这样的,而当他写下时却在强弱法(dynamics)上改变了。因此,当你问我这是否影响到他的音乐...是的,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不确定,但是每个作曲家都多少会受到所生活城市的环境影响,并且马勒还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理所当然会经常听到乐团的演出,乐团的音色也会一直在他脑海中。这就像是乐团的“声音模型”,帮助他依此来创作他想要的作品效果,而且马勒有极其敏锐的听觉。因此这些也许影响了他。
9.您是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您也指挥过维也纳爱乐乐团很多次,这两个乐团都是最传统的马勒乐团。杨松斯:是的。
10.如果让您比较一下两个乐团的独特音色,您如何描述呢?杨松斯:这两个乐团正如您所说在某些地方,十分接近。他们都有非常美妙的、平衡的、透明的音色。当然两者也有区别,感谢上帝,我认为所有伟大的乐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优秀乐团,乐团的水平都非常高,但是也面临着个性特点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伟大的乐团才能保持住他们的个性之处,在这方面维也纳爱乐和阿姆斯特丹都有着极其突出的个性。但是也有一些乐团在向其他方向发展,比如我的另一个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乐团,还有柏林爱乐乐团这个伟大的乐团,这两个乐团却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把维也纳爱乐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归在了一类。
11.柏林爱乐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有什么特别之处?杨松斯:两者都是真正的德国乐团,有着非常饱满和深厚的音色,是自然的乐团。当然维也纳爱乐也非常自然,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非常高贵和深厚的。他们演奏起来并不疯狂,但却是发自内心的。
12.您是否受过其他马勒指挥的影响?杨松斯:是的,有很多指挥家指挥马勒,录制了很多录音。在某种程度上,在你年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你,这很正常,因为你还年轻刚开始听音乐、思考音乐,特别是指挥家将会有很大的影响。我的老师影响了我,他给了我方向,但是渐渐地,我在努力寻找我自己的方式。我不是说我与众不同,我是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得到某种理解是因为它本应此,我愿意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之前有人做过了而影响到了我。
当然我认为最初我们都受到了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很深的影响,这是正常的。他是一位伟大的,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有极好的性格,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指挥马勒总是有极大热情和感情,我们受到很大影响。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是说我不喜欢那样或是评价他,而是我发现与最初相比,我的理解和处理的方向有所改变。
13.您是否同意您(对马勒作品)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夸大的或者过分激情的?杨松斯: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应用到所有音乐中,在音乐中过分夸大一些东西并不是很好。马勒的音乐十分复杂和情感化,它驱使着你,如果夸大一些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举另外一个例子,也许你会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比如在处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过分夸大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作曲家是在如此的感情中,运用了突慢等等。如果你夸大,那么就破坏了音乐,你必须用传统的方式处理。我的父亲总是说这样一句话,我铭记在心,他说:“永远不要把糖加进蜂蜜里,那样太甜腻了。”[笑]
音乐驱使着你去过分的夸张,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当我教我的学生时,有人说那样(指不夸张)很无聊,不能表达出所有的情感。如果年轻指挥想要过分夸大,我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虽然你压抑这种夸张而又恰当的表达出来,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时一些年轻人比较害羞,那么你需要激发他们表达出其情感。但是通常就像是这样,我总是举这个例子:如果你的裤子很长你可以剪短,但是如果裤子太短,你就没有办法了。[笑]我说这些是从老师的角度出发的,年轻人如何去处理音乐,如果他们有天赋,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指夸张的)表达音乐,你可以在之后再削减它。
(未完待续)
友情提示:由于涉及多方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附视频(节选):当代指挥谈马勒系列(Universal Edition)——杨松斯谈古斯塔夫·马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