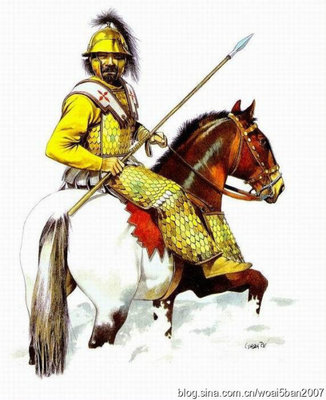香港《明报月刊》今年八月号上刊登的《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演说词,乃是顾彬应香港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之邀而发表的讲演录音稿,本来不是正式学术论文,发表的场所也非学术刊物。不想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刘再复等人相继撰文驳斥。刘文尤其声势浩大,盛气凌人,不禁找来顾彬文章看看,以明就里。
顾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发生在长篇小说上,盖因语言啰嗦,难以达到令其欣赏的水准,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如此,美德也概莫能外。二是谈到高行健,认为高算不上流亡作家,他八七年离开中国,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基于他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一九八四年,顾彬与德国文艺交流中心合作,帮助他们邀请中国作家来柏林创作,高行健成为第一位获邀对象,在柏林呆了半年,八五年夏高行健再次来到柏林,却没有潜心创作戏剧,而是投身绘画,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画作销路颇旺,他在弗莱堡找到一家画廊展出自己画作,大获成功,遂于一九八七年接受巴黎展览画作的邀请,从佛莱堡前往巴黎,从此没有回北京,因此他后来的宣布流亡,不过是自我推销的一种手法;他认为高行健离开中国,是中国戏剧界的巨大损失,至今他的地位仍无人能够取代,尤其是在戏剧理论方面,但他的戏剧理论要远胜于他的戏剧创作。顾彬和学生先在德国翻译高行健的话剧《车站》,得到西方的一些注意,并在维也纳、汉堡等地公演,但很难找到出版社出版,最后还是顾彬自掏腰包八百马克找了一家出版社替他出版。他组织学生将《灵山》的一部分翻译成德文发表后,也无人问津。一九九二年他在维也纳看了《对话与反诘》后,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实在太差,因此决定以后不再和他合作。三是谈到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作品中“女性的问题”,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五四已降的男作家所写的女性有灵魂,让读者同情,而八九年以后的男作家写女性,则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四是谈到诺贝尔文学与翻译的问题。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此外葛浩文不遗余力为莫言鼓与呼,如果葛浩文翻译的是王安忆,宣传的是王安忆,那么去年的诺奖得主很可能就是王安忆了。五是谈到莫言,他认为莫言长篇小说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创造出现代性的长篇小说。现代长篇小说创造于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多德勒尔和钱钟书,他们语言精练、思想深刻、并能创造出一种新形式。莫言虽能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但无法再现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莫言也创造诸多不同形象来描写中国历史,但这些形象实在无足观,多一个少一个区别不大。莫言的写作是为了治疗心中的伤痕,但作家应该超越自身的悲伤,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提出了时间与记忆的问题,钱钟书的《围城》探讨了现代婚姻的问题。《围城》充满了幽默,而四九年以后的作家则缺少幽默感,他们喜欢关注诸如祖国、民族、人类等大题目,所以幽默不起来。莫言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爱”,到处充斥着叙述者连接到主人公的“恨”。
顾彬向来以特立独行、敢说敢做闻名于当代中国,他这篇演说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高行健的流亡作家身份,窃以为即使他八七年去巴黎并非流亡,但后来的种种言行,造成“等是有家归不得”,其生存状况、心理状态、写作志趣,都不能排除其流亡作家的身份;如他认为八九年以后中国作家所写的女性缺乏灵魂,失之过泛;说莫言获奖葛浩文有功固然不错,但说葛浩文翻译王安忆则王安忆得奖就有点颠倒主次、喧宾夺主了;他对莫言的成就过于贬低,这些都是他的演说有让人不能同意的地方。
嗣后《明报月刊》九月份特辑一连刊登四篇文章,驳斥顾彬观点。其中尤为浓墨重彩的是刘再复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态度,撰写七千余字长文《驳顾彬》,对其大肆鞑伐,攻击谩骂。老实说像我这样读鲁迅文章长大的人,对文人骂架本来特别好奇,也并不陌生。但马齿徒增以后,年少的不平之气渐灰,尤其读了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文章再去读鲁迅,就觉得了无趣味。觉得文人骂架,恰如妇人斗嘴,无论骂得多漂亮,终究是件无意义的事情,没什么建设作用。看刘再复的标题,上来就是什么给欧洲愤青一个回应,什么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搬用低级的“妇姑勃谿”斗法,什么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精神变态,什么值得研究的精神浮肿病案例,扣帽子贴标签,一条条上纲上线,让人不寒而栗。刘再复批评顾彬有文革作风,然而我读完顾彬的演说词并不觉刺目,即便批评高行健莫言有我不同意的地方,也不能令我怒发冲冠,反而刘文的语气和措词,却不由令人遥想那个可怕的年代。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饱受质疑,发展迄今,出现高行健和莫言这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确属难能,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中国当然作家的能力。但既然中国作家进入世界视野,全世界人对其进行批评研究,出现不同观点和声音,甚至批评挖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人对高行健和莫言曲意回护,也可以理解。但对批评这两位作者的人施行人身攻击,就显得太幼稚。顾彬上述五条观点俱在,一一驳斥即可,不知刘再复这样级别的大腕,怎么会沦落到姑嫂骂架的水平?我觉得主要是他太愤怒了,愤怒让他失去理智,才会一气呵成这样一篇有点怪味道的文章。
附:刘再复全文:
驳顾彬
刘再复
(一)给“欧洲愤青”一个必要的回应
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我本来对顾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如2010年许子东先生把我和顾彬一起请到岭南大学中文系时,和他一起吃饭、开会,我只和他“和平共处”,但不赠书,也不走访,那时我就知道他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理极不平衡(他推荐的人没能得此奖),便退避三舍,让他三分。一起吃饭时,只是沉默,避免争论。今天我所以对顾彬要“顾一顾”,乃是因为他此次得寸进尺,在香港太横行,一副让人难以忍受的殖民者姿态与腔调,甚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比在大陆所摆的“洋教师爷”架势更咄咄逼人,完全越过做人治学的道德底线。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
我出国已二十四年。出国后我守持《道德经》所示的“不争之德”,对于强加给我的一切歪曲、侮辱、诬蔑、诽谤、中伤,包括《求是》、《人民日报》、《文艺报》诸报刊以及海外民主激进派的攻击,我都退避三舍,不予理睬,严守价值中立与容忍态度。所以沉默,仅仅是为了心灵的平静,以保持读书研究的沉浸状态。但是,今天我决定打破二十四年的沉默,给德国人顾彬一个必要的回应。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因工作关系开始与德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有所联系,那时我和许觉民(文学所前任所长)联系的是马汉茂教授,并不知道有“顾彬”。马汉茂教授朴实,谦虚,厚道,身为社科院副院长(管外事)的钱钟书先生让我和他“合作”(特为此事写信给我)。后来马汉茂教授不幸英年早逝,我为此非常悲伤,特写了“马汉茂和他的中国情结”一文(发表于《明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此时马汉茂的名字仍在我心中闪光。而知道“顾彬”这个名字,则是前几年偶尔在网上看到消息,说有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很像“愤青”,(有人干脆称他为“欧洲愤青”)在中国当代文坛里混迹了几年,作了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因为这“垃圾论”,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垃圾论”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暴得大名”之功。面对“垃圾论”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但在《明月》第八期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子东先生却为“垃圾论”辩护,说“大陆媒体只记得顾彬的垃圾论,那真是一叶障目”。“只记得”,说得好轻巧!难道“垃圾”的侮辱可以忘却可以不在乎吗?我还要提问:既然顾彬已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的头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呻吟一下,申辩一下,抗议一下?!被侮辱了,还替侮辱者“张目”,还怪同胞们“障目”,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咄咄怪事。子东兄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
读了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推出骇人听闻的“垃圾论”:因为只凭一部只有复制性而没有艺术感觉的文学史书,很难在偌大的中国引起“轰动”,唯一的办法是制造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论,即写一书不如骂一通,编一“史”不如踩一脚。我要问:有这么一本唱老调子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就可以信口雌黄侮辱中国当代文学与高行健吗?

(二)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
我到过德国两次,第一次是1992应马汉茂教授之请,到鲁尔大学作讲演;另一次是2011年到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欧洲经济如此困难,德国虽好一些,但还是拨款举办这样规模的会议(除了德国学者外,还邀请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七位学者),真不简单。会下进餐时听到与会者多次缅怀马汉茂教授,却没有人提到“顾彬”二字,可以肯定,顾彬在德国远不如在中国出名,可见他的“垃圾论”还是在中国凑效了。谁能起哄,谁就能在中国的浅薄文化圈里得逞,顾彬真不愧是“中国通”。
对于德国的学者,无论是马汉茂教授还是爱尔兰根大学的朗宓榭教授,我都非常敬重。在美国,我对西方学者也非常尊重,并悄悄向他们学习。总结二十四年的所见所学,我觉得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关于第一点,中国本来也不差,曾国藩的治家八本,就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但近数十年来,此“本”却被上上下下的国人大打折扣。没想到顾彬也丧失此“本”,进而践踏这两项基本的学术品格,通篇讲话都是妄说妄评妄言妄语(下文我再举例说明),更谈不上进入学术问题。谈论高行健与莫言,本可以引发许多学术问题。就说莫言吧,我说莫言的作品呈现了“酒神精神”,但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精神,就大可讨论。莫言获奖前,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就认为中国没有“酒神精神”,而他的学生刘东博士则说“有”,而且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另外,李欧梵说当今欧美小说缺少“现实幅度”与“想象视野”,而莫言恰恰具备这两项,我还补充说,莫言是现实幅度、想象视野和审美形式的“三通”。但有朋友提出质疑,认为如此界说欧美小说有些不公平。还有,莫言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来自本土蒲松龄的“狐幻现实主义”?这也可以讨论。至于高行健,可以进入的问题就更多。例如,“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小说写法,在世界小说史上是否有过先例?其戏剧所创造的非人物的人物形象(如“生死界”、“对话与反诘”中的形象)是生命存在、心理存在还是哲学存在?高行健笔下“你、我、他”内在主体三坐标与弗洛依特的“本我、自我、超我”有何区别?《山海经传》中的“原始人荒诞”与二十世纪西方戏剧中的“现代人荒诞”有何异同?《周末四重奏》中的两对主人公经历的是最苍白的生活瞬间,文学在书写没有诗意的瞬间时如何呈现审美的诗意?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三)搬用低级的“妇姑勃谿”斗法
大陆曾有一个时期,学术文章与学术书籍也往往不进入问题。即使学术会议,也看不到“进入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倒是充满问题之外的“政治是否正确”、“立场是否符合主义”以及人格抹黑和人身雌黄等等,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不知在新世纪中是否还有遗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顾彬所以还能在大陆与香港文坛横行无阻,说明人们感兴趣的还是诗外功夫、学术问题外的“妇姑勃谿”。
鲁迅最讨厌把“妇姑勃谿”的婆媳吵架态度与方法搬入文坛学界。《鲁迅全集》三次(分别在第一卷、第三卷、第十一卷)嘲讽这种低级的战法斗法。“勃谿”原出自《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唐代成玄英注疏说:“勃谿,争斗也,室屋不空,则不容受,故姑妇争处,无复尊卑。”庄子和成氏的意思是说,被家中的利害和个人的情绪所支配的婆婆与媳妇争吵,最不讲理(以情绪取代理性),一味只顾抹黑对手,压倒对方。鲁迅先生所以竭力反对把这种低级的“妇姑勃谿”搬入文坛学界,乃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文学批评也如“妇姑勃谿”,整个学界将乌烟瘴气,斯文扫地,脏水横流,也将使江湖骗子趁机而入,文化扒手借乱取利。中国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文学批评者就像婆婆,倘若沿袭中国的婆媳斗法,就会苛刻苛求而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把看不上眼的作家吃掉、灭掉,至少得咬他们身上的几块肉。钱钟书先生早就对那--些妄谈他作品的人说:“我是一块臭肉”。言下之意是:唯苍蝇才扑上我身。高行健太“傻”,他完全不知世道人心的险恶。他早该做点钱先生似的声明。鲁迅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深知人性的黑暗,嫉妒心的阴冷与恶毒,所以他努力保护作家,捍卫天才,不能容忍只有口水没有墨水或只有牙齿而没有学问的各种婆婆们。我所以要在此多讲几句“妇姑勃谿”,是因为目睹当下大陆与香港学术风气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史无前例的“勃谿”之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许多不学多术的语狂、夸大狂、自恋狂,甚至是泼皮、骗子、伪君子。
(四)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精神变态
顾彬除了不知进入学术问题而热衷于“妇姑勃谿”的低级斗法之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绝症,就是不尊重事实,以妄言代替分析,以泄愤代替论证(和曾国藩所说的“以不妄言为本”正相反)。
顾彬在发言中,讲了许多“事”,但都不“实”。就我亲身经历的相关之事而言,就明白顾彬全是信口开河,肆意歪曲甚至造谣诽谤,说话极不负责任。现举四个例子。
(1)断言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说高行健“离开中国并非政治因素所致”,而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金钱收入的考量”本是顾彬的生命密码,他居然移植强加给高行健,十分可笑。而说“非政治因素”,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高行健是个典型的流亡作家,他的人生经历过多次流亡(大约有五次之多,其流亡史可写成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本是众所周知的鉄铸事实。未出国时,他就经历了一次著名的从首都到边陲的大逃亡。一九八三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当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幸而,得知这一信息的剧作家苏叔阳,连夜告知高行健。在此政治压力下,高行健只好匆惶逃出北京,到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流亡,北至大雪山,南至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也因为有此次流亡,才产生了被马悦然教授称赞不已并译成瑞典文的《灵山》。高行健早就说:“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人,总在流亡”(《没有主义》第154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所以他总是高举流亡的旗帜。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他因宣布退党、并发表声明,又导致被开除党籍、公职和更久远的流亡。至今国内仍严禁他的作品,扼杀他的名字,封锁他的消息,连我的《高行健论》也无法出版。与顾彬横行无阻的宾客待遇完全不同。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德国人顾彬却闭着眼睛硬说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这种不顾基本事实的无聊歪曲与挑衅,不仅毫无根据,也毫无意义。我在这里加以驳斥,实在是浪费口舌。
(2)顾彬说德国《法兰克福报》批评《八月雪》的演出是一堆木偶戏。这也是瞎说。二〇〇五年马赛演出《八月雪》时,我正在附近的普罗旺斯大学参加高行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就近去看戏。这是台湾戏剧精英和法国马赛歌剧院的联合演出。我亲自看到法国观众一再起立,热烈鼓掌欢呼,演员谢幕达八次之多。那天晚上,我真为慧能、为高行健、为中国艺术而激动不已,彻夜不眠,并写下了一段文字。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中国文化年”,排斥高行健,所以此剧未能在巴黎上演。因为有此经历,所以我不相信遥远的德国《法兰克福报》会特意攻击马赛的《八月雪》演出,于是,便打电话问高行健。行健说,这就叫做“天方夜谭”。
(3)我知道高行健在德国有许多译者朋友和激赏他的学者,如鲁迪格·哥奈,他是德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是真学者、真思想者。他已出版过二十多部德国文学的论著。还有贝诺德·赖劳师德,她是德国著名的路德维克美术馆馆长和艺术评论家。他们俩人都写过高度评价高行健的文章。在爱尔兰根大学的高行健讨论会上,我又结识了深受中国学人尊敬的朗宓榭教授等真才实学的德国汉学家。高行健在德国出版了许多德文译本,完全不必借助顾彬的翻译。顾彬编造出因不翻译而交恶的离奇故事,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吹嘘自我叫卖的猎取功名的生存小技巧。
(4)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这更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胡说八道。关于葛浩文教授热爱莫言、翻译《酒国》、《丰乳肥臀》的功勋,我在回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已作了高度评价,此处不再赘述。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亲眼看到葛浩文的辛苦耕耘,包括为了照顾读者的承受力,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但顾彬却把“删除个别章节”蓄意夸张为葛浩文为莫言“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请注意,顾彬在这里挖空心思使用了四个大概念(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每个概念所指涉的内涵全是捏造,与事实全然不符。这种“蓄意捏造”的机谋,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顾彬因为作了点“翻译”,便把“翻译”的功能无限夸大。表面上在说葛浩文,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夸自己。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编造与胡夸真是令人目瞪口呆。顾彬还把葛浩文夸大为“第二个作者”,这种夸张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弯弯绕的是什么。我批评过当代文人的“精神浮肿病”,没想到,今天又见到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例。李锐曾写过一篇散文,说诗人顾城可作为一种病例分析,那是“小顾”。我今天则发现“大顾”,觉得顾彬也可作为精神浮肿病的典型案例解剖一番。如此狂妄,如此自吹自擂,如此大胆而巧妙地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这种现象实属稀罕。很值得研究。
我曾把文学评论者分为若干类,第一类靠脑子生活;第二类靠心灵生活;第三类靠鼻子生存;第四类靠牙齿生活。靠鼻子嗅,能赢得名声,靠牙齿咬人也可以赢得名声,这便构成批评界的荒诞。二十世纪西方的荒诞小说家与戏剧家,他们用“荒诞”一词来描述世界,实在太精彩。今天我们张开眼睛看看文坛学界,难道不处处可以看到荒诞戏剧吗?
(五)值得研究的“精神浮肿病”案例
我说顾彬可以作为“精神浮肿病”的典型案例进行解剖研究,绝非戏言。因为顾彬现象包括四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1)德国出现过让中国人深深敬佩的大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等,此外,德国学者的严谨诚实态度也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德国人顾彬,为什么反而离诚实离严谨这么远,离学术这么远,好像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学术规范”。更为奇怪的是,他怎么会这么善于讲大话,怎么会这样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胡言乱语,比当下的“中国愤青”还甚(中国愤青只是幼稚,顾彬则狂而阴,阴而痞。),这种“精神浮肿病”是怎么发生的?他属于德国当代文化的特例还是常例?他的胡夸胡说是受中国污染还是他在污染中国?(2)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被查禁(戏剧也被禁演)、被封杀,而顾彬侮辱高行健和当代文学的言论却在中国畅通无阻(一年被大陆邀请了七次),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也普遍发生精神浮肿病和黑白颠倒而对此症熟视无睹?甚至听了他的胡夸与诽谤还会产生共鸣与快感。(3)无论是德国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反对人身攻击,但还是常常可以看到攻击现象。而像顾彬这种对基本事实肆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却极为罕见。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倒是失去诚实,到处可见假话、谎话、大话和洋八股、土八股,不知现在是不是仍然如此。在中国的语境中,顾彬如此好讲大话、假话,是否与文化大革命有些关联?即是否与“红卫兵”作风和造反派恶习相似,这也值得研究。(4)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歌德关于人格的定义曾积极地影响中国的学人。他的人格定义不同于中国的先贤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强调的是:高尚人格一定要尊重有学问、有才华、有贡献的人。如果让我们引伸一下,便是懂得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高尚,不知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卑劣。在当下的中国,高行健、莫言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行健被剥夺了前半生,但后半生却不屈不饶,竟然在小说、戏剧、绘画、理论、诗文诸多方面取得惊人成就,其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各种语言的译本已达三百多种。其水墨画在十几个国家作过七十多次展览。其思想又是如此清醒、透彻,正是他,提供了当代世界最清醒的文学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对这种贡献卓著的文学艺术家,不知敬重反而处处污辱、诬蔑、毁谤、攻击、中伤,这不是人格卑下是什么呢?还有莫言,这么一个从贫瘠的黄土地站立起来的穷孩子,最后自己长成参天大树,写出十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三十多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其艺术感觉,其“想象”才华,其良心意蕴,其批判力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而顾彬在会上却说他是“媚俗”,是“葛浩文所制造”。而在会下又多次对着媒体侮辱、戏弄莫言。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顾彬竟在此次讲演中用下流的语言对高、莫二人作出如此妄断:“我们应当注意到高行健和莫言的小说中,都有一个秘密的主人公,那就是女人的胸部”。顾彬对高、莫的作品,看来是大部分都没有读,所以才会杜撰出主人公是“女人的胸部”。女人的胸部,恐怕正是顾彬“犀利”的关键词,也是他本人眼睛的聚焦点。这我们不管,但他用这种色迷迷脏兮兮的语言抹黑高、莫,如此不尊重这两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则是人格污浊的铁证。歌德真伟大,一语就击中“人格”的要点。此明镜一确立,顾彬的人格病态就一目了然了。
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