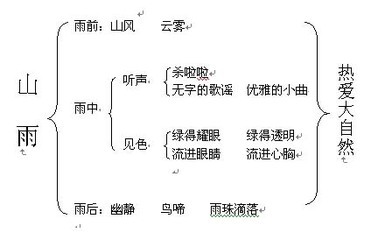选文本分析课的同学请有兴趣可阅读我上节课的讲稿,前二节发到公共邮箱,这篇讲稿贴在博客里。随后的讲稿有些可贴在这里。看起来方便。因原来以为新浪博客只能贴一万字以内的文章,现在看来升级很快,可以贴二三万字。刚才高兴得太早,还是贴不进这么长篇幅,分做二篇。
第三讲 “吃”的唯物论与“棋”的文化解构
——解读《棋王》的“非寻根”意义
陈晓明
1985年的春天,阿城风尘仆仆来到上海,怀着急切的心情召集王安忆几位朋友小聚。多年后,王安忆回忆道:“这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带一个菜,组合成一顿杂七杂八的晚宴。因没有餐桌和足够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处,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则正襟危坐于床沿,无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1]阿城对“寻根”如此热心,当不难理解。1984年底,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一批青年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主题就是“文化寻根”。而在此之前,阿城的《棋王》在上海发表,轰动一时。在写《棋王》之前,阿城这个名人之后并不如意[2]。70年代末,阿城就从云南边陲回到北京,但因家庭政治问题错过高考机会,他在社会上很艰难地寻找自己位置。苦于没有文凭,他辗转于几个杂志社的编辑部,但都是干些杂活,“以工代干”自然难以在文艺圈子里有长久立足之地。通过范曾,他结识了袁运生。那时袁在首都机场画壁画,正是颇受社会瞩目的艺术举动,阿城能充当助手干些粗活,已经是他最风光的时刻了。据说袁运生很看重他,认为阿城悟性颇高。袁运生还和范曾一起联名推荐他报考中央美院,但未能被录取。他后来依然试图进入一些编辑部和机构,都未能如愿。搞过一些画展,也并不十分成功。甚至和朋友办公司也以落败告终。后来结识李陀转向文学,他才开始上路。那时他经常在李陀家吃涮羊肉,以凶狠狼狈的吃相与精彩动人的讲述惊异四座,李陀总是鼓动他把讲述的故事写下来。1984年,阿城时来运转发表《棋王》;1985年,阿城要抓住机遇,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事件“寻根”中,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后来事实证明,阿城的敏感是对的,“寻根”成就了并不充分的他;正如他给并不充足的“寻找”提供一份证言一样。
《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一直是与“寻根文学”互相诠释,《棋王》的意义依赖“寻根”的历史语境;而“寻根”的意义也通过《棋王》之类的作品得以建构。“寻根”既放大了《棋王》的意义,也遮蔽了《棋王》更为原本的内涵。《棋王》如何被定位为“寻根”,它包含的大量的文化蕴含来自文本中哪些标志,这一直是令我怀疑的地方。当然,不想去探讨关于《棋王》如何被指认为“寻根”代表作的那样一个知识谱系——那肯定是另一篇有意思的文章的目标。在这里,我更想去分析《棋王》文本,看看它实际更有可能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如何与“文化”南辕北辙,它更有可能反感于文化(那些精神活动、思想谱系、乃至于思想斗争),它要寻求的是极为朴素的唯物论的生活态度,一种最为朴实无华的生活之道。
当然,历史既在文本中,文本也在历史中重建意义[3]。到底是一些作家或作品文本酿就了时代的潮流,还是时代潮流重新建构甚至定义了文本,有时还真难以说得清。在我看来,还是时代潮流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寻根文学”及其《棋王》就是最突出的事例。那些“寻根”的代表作品大都是后来指认的结果,按说,这更能说明是先有一大批作品而后才有潮流,这样的潮流难道不是更有真实性吗?事实上,潮流总是概念化的和整体化的,而作品是另一种事物,另一种无数的个性化的他者事物,如何被指认为一种同一性的潮流?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协调的文学行动。但事件、潮流构成的整体性和概念化,都是历史(也是文学史)所必需的,没有事件、潮流,我们就没有历史,历史就没有力量,历史就没有宏大性和普遍性。我们都生长在一种文化中,生长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所有个别行动都会表达出整体性和普遍性,这就是历史意识可以疯狂生长的的缘由。《棋王》所代表的“寻根文学”,既是对现代意识的追踪,又是对它的躲避。追踪与躲避的悖论就最有效地建构起“寻根”的内在矛盾和复杂的神话意义。
本文并不是去怀疑或否认《棋王》的艺术价值或美学意义,恰恰相反,即使离开了寻根,它依然具有自身作为文本的那种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依然要找到文本顽强地自我存在的那种品格和力量,没有这种素质,文本就没有自己真正介入历史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相信有一种文本自主性的思想,文本总是在历史语境中被解释,文学性并不是牢固而确定地存在于文本内的,它与字词有关,但并不是字词使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全部的文学性价值。文本总是以它的方式激发了历史建构的想象,这种想象反过来形成了文本的审美光环。在这里,我们不仅注重读解《棋王》的作为个别独立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也同时去看待文学性如何与时代潮流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何被历史语境建构的那种想象关系。
一、时代精神的早期瓦解:“吃”与“下棋”的唯物论特性
《棋王》在当时发表给人以最鲜明的艺术震撼之处莫过于它对王一生下棋的痴迷的描写。在陈思和主编的那本影响卓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写道:“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谜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从小就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4] 文中还写道,王一生看似阴柔孱弱,但在无所作为中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他就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的能量。很显然,这一“下棋”行为被投射了深厚的民族精神意义,这种意义是那个时期所需要的时代意识形态。1984年,《棋王》发表后,王蒙撰文《且说〈棋王〉》[5] 王蒙高度赞赏了这篇小说,指出小说对王一生的下棋的描写相当成功,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王蒙虽然是在当时的“人性论”的框架内来讨论问题,但他关注到小说对“下棋”这个行为的描写所具有决定性意义。王蒙按他一贯的文学观念,还是觉得“下棋”格局太小,题材有局限性,算不上“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存在,总是被那种语境赋予历史意义。曾镇南则认为,《棋王》的意义也正在于它对“棋王”性格开掘中“写出了扑不灭、压不住的民族的智慧、生机和意志……”[6]。时代的宏大意义诉求压抑住了文本最初被给人的艺术感觉,这种感觉迅速被过度阐释。这种阐释后来被进一步放大为“文化寻根”也就顺理成章了。事过境迁,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试图从《棋王》中捕捉时代精神已经显出捉膝见肘。《棋王》最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可能就是他以最为淡漠的态度,写出了那个时期离开时代精神的唯物论的生存态度。这种态度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色彩,但整体上来说,是不具有宏大化和抽象化的生存态度。如今,意识形态的时效性褪去后,我们可以更单纯地面对文本,不是去看“下棋”反射的时代意义,而是看看“下棋”在文本构成中所起作用。
尽管我们可以剥离当时语境赋予的时代精神的或文化的意义,但王一生“下棋”在小说叙事中还是具有基本的象征化冲动,那就是意味着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下棋”无疑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智力活动,“下棋”的竞赛性会被提升为一种精神境界。《棋王》之所以后来被当作“文化寻根”的代表作,被赋予了那么多的精神性意义,也不冤枉。但阿城在小说叙事中,“下棋”的意义始终存在着矛盾:那就是精神性/去精神性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在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或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加以梳理的是:王一生“下棋”所反射出来的那种“无所作为”到“有所作为”的变化,并不是人物性格的必然显现,人物性格是否真的有这种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是值得怀疑的。在流行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阐释中,王一生的“下棋”总是被当作性格内敛的一种表征,在关键的时刻,那种原本存在于性格中的潜能就会暴发出来。我更乐于去理解的是,小说叙事是如何在情节的意义转向、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转化方面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下棋”在王一生的行为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本质规定的积极潜能,到时就能暴发出来,实际上,“下棋”在王一生的身上要体现的更有可能是一种逃避和自我隔绝。
当我们说《棋王》是在表达一种庄老之道时,主要是通过“下棋”这个动作表达出来的。所谓庄老之道是崇尚自然,去圣却智,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智主义,是“去精神化”的一种哲学。庄老之道的哲学是悖论式的,一方面要超出事物的功利性去达成一种虚无的精神境界;但另一方面这种“虚无”的精神境界本身成为一种存在性,存在一种自我肯定的的可能意义。否则“虚无”也无法存在和确认[7]。“下棋”要摆脱的是对世事的过度关切,暂时忘却眼下利益和前途命运。但“下棋”在王一生最初始的心理学意义可能是一种逃避。就从小说叙事而言,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王一生下棋,在火车上乱哄哄的现场,王一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摆上棋盘与“我”对弈起来。王一生倒是很坦然,“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8] 如此杂乱却能安下心来下棋,那确实就是棋痴了。不要人送,或没有人送,王一生的心境真是那么坦然么?小说写道:
我实在没有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9]
这“忽然“一词,且”身子软下去”,还是道出了王一生内心的虚弱。王一生“下棋”似乎是自觉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证明,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典范。事实上,在这种痴迷于棋局中的是对家庭的一种逃避,对父亲亡故/缺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的一种逃避。在王一生后来与“我”以及与“脚卵”交往的日子里,王一生实际很敏感“我”和脚卵的家庭。依然是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我对王一生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说话儿。王一生却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随后一路下去,我与王一生开始有了互相的信任和同情。王一生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但王一生还是要在他和“我”之间作出区别,王一生认为,我家道尙好时不过是想“好上加上好”,王一生当然不相信“我”可以轻易理解他的苦衷。他说道:

“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惟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作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惟有象棋。”[10]
看来“下棋”是解脱的惟一方式。这里的我们“这种人”当然是指家庭出身,王一生的母亲当过窑姐儿,从良做小,生父是谁都不知道,王一生是遗腹子,母亲再嫁,跟养父长大。没想到母亲也死了。养父是卖力气活的,解放后,养父年纪大了,干活挣钱就少了,要养活他们一家四口,力不从心。王一生母亲死后,养父整天喝酒。可想而知,王一生处于这种家庭境遇,他的日子如何难过。就是打小时候起,他的家庭生活就过得艰苦。很小跟母亲去印刷厂叠书页子,看到象棋书,从那开始迷上了象棋。王一生的母亲死于贫病,死前把王一生叫到床前,拿出一副牙刷磨就的无字棋。王一生说,家里多困难,他都没有哭过,可是看着这副没字儿的棋,他就绷不住了。“下棋”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是逃避、摆脱,也是精神世界的延展。在阿城的叙述中,王一生关于“下棋”有双重态度,王一生说,他常常烦闷的是:“为什么就那么想看随便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11] 这就是说,下棋还有一种关于活着的精价值神追求,这就是主动性的精神提升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消极与积极的统一,被动与主动的结合。
实际上,在王一生那里,下棋所具有的积极和主动的精神意向相当有限,阿城并不想给予王一生在“下棋”的行为中太多的意义,那实际上是与“有饭吃”平行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精神活动方式,恰恰是去除太多的精神抱负,太多的现实革命热情。要知道,在那样的时代,知青中的政治激进人物多如牛毛,“扎根派”和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比比皆是。就在每一个火车站知青上山下乡送行场面,都是激昂的革命现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阔天地炼红心”,是那个时期青春激情燃烧岁月的基本精神面貌。至于寻找一切机会推荐上大学,招工、招干,在知青生活中也充满了竞争和荣辱。王一生的生活态度,显然是表达了无助的平民子弟的无奈。没有背景没有门路,他除了下棋来找到自我安慰外,再也别无他法可完成自我确认。对于王一生来说,有饭吃,有棋下,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应该知足了。这种人生观,在当时知青激烈的倾轧争斗中,实在是无奈之举。下棋不过是回到个人的志趣,极为有限的自我肯定,而不是时代的抱负。对于阿城来说,写作“下棋”也不过是写作个人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最平实本分的个人行为,这与他这个人一直不得不采取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显然更加合拍。
小说另一被推崇之处在于描写了王一生的“吃”,把“吃”写得如此津津有味,《棋王》也因此被认为精彩绝伦。小说有几处关于吃的浓墨重彩,首先开篇在火车上,坐定下来要下棋,王一生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12] 这里整整长达一页描写王一生的吃相,还有二页讨论吃的问题,涉及到杰克·伦敦《热爱生命》和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等,古今中外,平民百姓,家长里短,总之,关于“吃”,阿城是下足功夫渲染一番。另一处大费笔墨的是王一生到知青点吃蛇肉,在这个吃的现场王一生并无多大表现,主要是脚卵表现他在吃上的丰富经验,关于吃螃蟹、下棋、品酒、做诗,以及关于吃燕窝的记忆,脚卵家庭的高雅生活,让王一生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对于一直秉持“有饭吃、有棋下”的人生观的王一生来说,无疑有一点小小的触动,但也不可能对王一生构成更严重的冲击。
这里关于吃的描写有一种多元性,既有王一生贫苦人家的穷酸吃相,又有知青点对吃的津津乐道和馋相,也有脚卵叙述的富足文人家庭高雅的吃。阿城如此不厌其烦对吃津津乐道,明显是在表达一种唯物论的生活观。人的生物性(物质性)最基本的特征就反映在饮食男女上,当“男女”受到严格的限制时,“饮食”就成为生物性存在的人的全部内容。尽管“吃”在中国还是一种文化,并且是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在阿城这里,在知青生活中的吃,实在是在表达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欲求。脚卵说的那么高雅奢侈的“吃”,对于王一生们来说有多少意义呢?充其量只是表明还有如此富贵的生活,那不是他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生活。眼下的生活就是“有饭吃”就行。小说中不断地谈到王一生对饥饿的记忆和叙述。王一生第一次听“我”说起父母双亡,没有饭吃的饥饿经历,非常投入且一再追问计较细节,如干烧馒头、油饼之类充饥的作用,王一生显然在这样的时刻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吃”在《棋王》中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问题,“吃”被当作生活的第一要义,吃的贫困是生存最根本的困窘。由此,就不难理解,在阿城的叙事中,王一生的生存事相关注于“吃”的问题,“吃”一直是个严重问题,王一生甚至极端到对“我”所描述的困境不以为然,认为,“我”总是有过家境好的时候,只不过是想吃得“更好”罢了。而他则是在饥饿线上挣扎,一直为满足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困扰。如果小说是以王一生的生存态度为基准的话,那么,“吃”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意味,吃如此牢固顽强地与饥饿感联系在一起,与王一生的生存绝境联系在一起,如此贫穷困苦中的吃,能有多少文化的含量?小说叙事中借脚卵之口说出的那些关于“吃”的文化品味,与王一生相去甚远,实际上也是作为一个逝去的年代的经验来回忆,他不是作为现实追求的目标,只是作为现实不可能性的一种对照。
1984年底,《中篇小说选刊》第6期在转载《棋王》的同时,登载了阿城写的《一些话》。阿城表示自己的写作只是为了抽烟,为了伏天的时候“能让妻子出去玩一次”,“让儿子吃一点凉东西……”,说得可怜巴巴,文学全然没有多么远大的“文化寻根”。但说他没有现实的针对性也不对,他关注的恰恰是更为平实的物质生活,他写道:“我不知道大家意识不意识到这个问题(吃饭的问题)在中国还没有解决得极好,反正政府是下了决心,也许我见闻有限,总之这一二年讨饭的少了,近一年来竟极其稀罕,足见问题解决得很实在。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们是不会答应的。”[13] 8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领域的左右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改革开放,还是保守倒退,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关切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阿城肯定不能例外。“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这句话显然包含着十分尖锐的斗争意味。应该说,阿城是站在改革派一边,以此推断,阿城当然是从改革开放后百姓有饭吃这一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知青下到西南贫困地区,阿城一定目睹过农民饥饿的状况。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却要挨饿,这无论如何是巨大的历史失败。阿城通过王一生表达的“有饭吃,有棋下”就好,这也是对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还在论争的姓社姓资问题的回应。人民的生活有着极其朴素的唯物论的立场,与那些政治制度、主义、道路、方向、社会性质……无关。唯物论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但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唯物论则只是一种政治象征,并不具有日常生活的实践性意义。在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社会意识都是要求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物质,日常生活实践是彻底反唯物论的“精神辩证法”(因而也是精神胜利法)。只有到了80年代,唯物论才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实践联系在一起,社会的经济发展,物质生产的丰富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因而,在整个80年代,人们对物质性的追求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它既是物质主义的,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但唯物论始终有它的朴素性,那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人民首先要吃饱饭,民以食为天,如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主义”有什么用呢?另一方面,8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开始给予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生活多样化的可能性,对人性也不再那么压制。不管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无法抑制人们对身体自由和物质欲望的向往。尽管非常有限,但欲望的闸门初次打开,里面涌动的力量无法遏止。邓丽君、龙飘飘和走私的录音机对沿海开放城市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洗礼,舞厅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在大学的校园里怂恿着年轻的人群激情荡漾。长头发和喇叭裤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对思想自由解放的追寻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相混淆,排队买彩电的盛况与热情奔放的文学讲座交相辉映,构成了那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激动人心的现场。只要想想那个时期居然有一个如此广泛的美学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个费解的定理居然构成了时代审美的心声,就不难理解人们对自我意识的追求构成了时代精神强有力的内核。在理论界,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讨论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脱离社会实践。普通民众开始理直气壮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把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世界看得比自己居家过日子还更重要。最要命的是,自从1984年以来,物价正在飞涨,人们一方面憧憬“生活比蜜甜”;另一方面却也忧心忡忡,担心高涨的物价会让人们重回艰难的日子里去[14]。显然,作为一种时代心理,强调物质生活、强调饮食居家过日子,也是那个时期刚刚滋生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这一意义上,《棋王》的“吃”是一种朴素单纯的“唯物论”,他要回应的是当时现实,一方面是人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美好明天”;另一方面对昨天的物质匮乏的记忆犹在眼前。不管是阿城本人的声称,还是《棋王》中王一生实际的表现,都表明它对特质性生活的关注,对物质性书写的刻骨真实。王一生身上的文化冲动既不明显也不深沉,除了把他的平淡泰若与庄老之道联系起来外,也难以确定其他的文化意味。但平淡朴实本真何以就是庄老之道呢?回到特质性就是一种素朴的“唯物论”,就是一种吃的“唯物论”,别无其他的深意何尝不可?王一生不要文化人的那么多的忧患,也不羡慕脚卵父辈的高雅,他时刻记忆的是母亲给他的无字棋,他时刻要保持的也是贫困中的人们更加本分朴实的生存之道。“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就是一种人生信条和训诫了。1984年,在反传统的潮流中,说阿城那时就笃信庄老之道或儒道释的文化蕴含,那无异于痴人说梦。1984年,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的那种西方科学主义理性思维;文学上声势浩大的现代派;美学上的信条是来自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尽管说阿城有可能偏离时代潮流,在潮流之外领悟他个人的思想天地。但在1984年,在“寻根”命名之前,以文化上的自觉或哲学思想的自觉去回到庄老之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如果说文化的记忆也可以是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种自然平淡的表达中达成了“复古的共同记忆”,但那也需要历史提供一种平静的反思性语境。在80年代激动且乱哄哄的历史现场,阿城写作《棋王》已经尽到最大可能性去削减时代精神的投影,那就是回归平淡素朴的日常生活。小说的结尾如此写道: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掮着柴禾在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人,那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15]
这是本真性的生活真理本身,它不再要承载更多的理念或历史意向。它不是主动的承担与召唤;而是退却和平息,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然而,关于小说结尾还有一段公案。据说小说原来的结尾是:“‘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据李陀所言,小说故事原来是这么结束的。李陀对《上海文学》要求阿城改动了结尾很不满意,他认为原来的结尾更好。现在看来,原来的结尾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与现在的结尾相比,各有特色。但如果说阿城的小说在那时的原来意义,是表达唯物论者的生活态度的话,那原来的结尾就真正点出了题意。现在的结尾则包含着形而上的冲动,但唯物论的色彩就很不鲜明了。根本是落在吃上,吃饱了是福,这就足够了,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据说,阿城当年讲述的《棋王》的故事就是在李陀家中吃涮羊肉神聊的故事,李陀一再鼓励他写出来,当时故事可能已经很成形,甚至结尾都与李陀说过了。而这样结尾正是应了其“有饭吃”唯上,这不过是“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的更直接朴素的表达罢了。在80年代中期,其现实指向也恰恰是与意识形态翻云覆雨的斗争表达不满和厌倦。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运作终于离开现实而自成一格,并不是什么二元对立之类的胜利,而是现实的唯物主义占了全部上风,人们已经完全厌倦意识形态的种种运作。《棋王》正是回到最朴素的唯物主义这点上,把“有饭吃”推到最要紧的地位,甚至可以替代“有棋下”这一精神活动。只是后来《上海文学》编辑要求的修改,使作者原来的意思发生微妙的变化,而给“寻根”提供了捕风捉影的文化蕴含。
二、知青记忆与文化寻根的替换(集体记忆的瓦解:无父之子的个人怨恨)
“寻根”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只持续了如此短暂的时间,以至于与它在文学史上占据如此重要地位显得很不相称。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属于自发的事件少得可怜,“寻根”就不得不以其独特的“文化意味”引人入胜。“寻根”显然是一次追认的运动,作为一种文学史的事件,追认也未尝不可,但追认总是要建立这一行动(1)有基本的潜在意向,(2)也有可以归纳的更明确的历史目标,(3)以及被追认之后形成更加强大的形势。但“寻根”在这三方面都不充足。当然,这仅仅是针对“寻根”作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史事件的充分性的质疑,至于这个时期有这么一批作品,形成一个时期的文学高潮,其积极意义无庸置疑。对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的确认来说,无所谓“寻根”不“寻根”。也许事过境迁,我们试图褪去其“寻根”的文化外衣,可以看到更加独特的文学性魅力。当然,“褪去文化外衣”的做法也是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的行为,它不可能避免也是对文本进行文学史的探究。我们也可以这种方式看看一个文本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如果说《棋王》在阿城那里原来并没有明确的主观意愿进行“文化寻根”或表达特定的文化意味,那么这篇小说更为本真的意义何在呢?当然,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能全然决定作品文本的意义,以“作者死了”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作者的声明对理解文本并没有优先性。在“寻根”成为一个事件之前,阿城关于《棋王》的创作谈论与“文化寻根”无关,从当时的文学客观语境与写作主体的可能意愿来看,《棋王》都是一篇标准的知青小说。事实上,绝大部分后来被归结为“寻根”的小说,大都是知青小说的变种。
《棋王》写的是知青生活,其主题在三个层面上是典型的知青共同记忆,本章前面已经有所讨论,这里加以归纳:其一,关于“吃”的记忆。这篇小说对“吃”的描写令人惊异的细致和充沛,“吃”所表征的饥饿感是知青生活最重要的记忆。其二,关于“棋”或与世无争的记忆。“下棋”的态度并非与“吃”构成简单的二元关系,“吃”是物质性的,或“下棋”是精神性的,或者二者都被给予文化蕴含的提升。“吃”与“下棋”都可做庄老之道的阐释。在《棋王》中,要表达的是与世无争的一种态度,“有棋下”正如“有饭吃”一样,这就是人生的知足的素朴的人生观,并不要那么强大的关于“献身”、“扎根”和“出人头地”的抱负。“吃饱是福”,做个朴素平常的回到生活的基本层面的普通人。相当多的知青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因为家庭出身处于竞争的劣势,却又无可奈何,转而寻求自我安慰。但这种人生态度,在当时只能压抑在内心深处,无法被公开表达。现在阿城对知青生活的抒写,发掘了这种在当时应该是相当广泛的知青记忆。其三,关于家庭出身的记忆。《棋王》花费大量的笔墨在讲述和描写王一生、“我”和脚卵的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出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是一个在政治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年代,一方面是严重的政治歧视;另一方面则是无可置疑的政治特权。
王一生与脚卵的家庭背景构成明显的对比关系。王一生母亲临终嘱托有一副棋无字棋,那里面凝聚的是普通平民家庭的辛酸与无奈的希冀;而脚卵下乡,他的父亲给他一副祖传的乌木象棋,脚卵用于与文教书记做交换。脚卵的调动有了着落,王一生也可以比赛了。但王一生却对此并不买帐,他不想参加比赛,并且对脚卵的交易颇有微辞。小说是这样的叙述的:
躺下许久,我发觉王一生还没有睡着,就说:“睡吧,明天要参加比赛呢!”王一生在黑暗里说:“我不赛了,没意思。倪斌是好心,可我不想赛了。”我说:咳,管他!你能赛棋,脚卵能调上来,一副棋算什么?”王一生说:“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我妈留给我的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我说:“脚卵家里有钱,一副棋算什么呢?他家里知道儿子活得好一些了,棋是舍得的。”王一生说:“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做了交易,倒像是我占了便宜。我下得赢下不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16]
从字面上来看,王一生是个有骨气的人,他不想靠脚卵倪斌获得参赛的资格。但他对脚卵用父亲的乌木棋去做交换不满,他提到母亲给他的无字棋。这里隐隐包含的是对脚卵不珍惜祖传“信物”的批评,但更深的心理怨恨则可能是人与人的平等,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王一生一无所有,他连参赛的资格都要靠别人帮助才能获得;这里的自尊还包含着一些赌气,赌气中又透示出一些对不平等的怨恨。同为知青,同为人,何以出身家庭不同命运如此不同?王一生因为母亲出身卑微,显然要承受着物质生活贫困和走向社会的艰难。
在表达这一家庭不平等的状况时,阿城超出了伤痕文学的经典叙事,那就是老干部倒霉,连累了“狗崽子”,主人公总是落难公子或公主,而老子总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大干部。另一种模式或者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里控诉的是极左路线。阿城这里讲述的脚卵的父亲却是一位文人,其政治身份也不清晰,阿城是有意避免直接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还是从更平淡和更普遍的知青的生活记忆出发来描写家庭背景的不平等。阿城关注的只是知青记忆中的事实性,而不是事后所要做的批判性,这就是阿城超出伤痕反思文学的地方。
事实上,寻根群体基本上都是知青群体这一事实,决定了寻根小说本来就是知青小说的再命名。“知青群体”的写作,在个人记忆的经验范围内,它表达了个人青春失落的痛苦经历。“知青群体”本身也不是一个整合体,并不具有同一性。这样的“集体”在历史中是被政治化的,正是在对父亲的批判和反思性上,阿城改变了伤痕文学,他写出了伤痕更为内在的政治身份的区隔。在那些偏远的山乡留下的记忆,不同的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失落感,在个人记忆的意义上,最底层的知青到底是些什么人?这是《棋王》开启的后知青小说最为尖锐的提问。
也就是说,《棋王》对知青经验的书写之深刻,并不在于所谓的文化意味,而是隐藏在文化表象之下的一代人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之所以铭刻在心灵上,在于它是个人的最切身的感受。文革时期对青春期的知青最大的压迫感或焦虑感,当然是被政治认可和接纳,成为政治上的红人。但成为政治上的红人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家庭出身,政治成份是知青那一代人的生命,所谓政治生命。如果出身不好,那就意味着前途暗淡渺茫,预先就被宣判了绝境。如果出身好,特别是有一个政治上红彤彤的父亲,如果再加上有权有势,那就是又红又专,前程似锦。对父亲的认同的焦虑感,是隐含在知青文化中最内在的焦虑,也许阿城个人有此经历,也许阿城对知青的创伤经验的深刻体认。因为触及到这内在创伤,小说中的王一生的心理刻划才有那么多曲折、微妙,那么深挚的困惑和无望。阿城才可能不断地书写王一生在绝境中挣脱的那些努力。
因此,《棋王》中的知青记忆,最本质的东西就不会是“文化记忆”,而是一个关于无父的创痛。这是一代人的最内在的焦虑在王一生心灵里的积聚。这种心理表达出来则又具有弗洛伊德式的“反俄狄浦斯情结”——这就是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娶母”改变为一个“寻父”的故事。如此说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但小说叙事对家庭的不平等的表现是如此深刻就令人深思。对于王一生来说,家庭经验是如此深重的内心创伤,他会如此关切别人的家庭的“光景”,“家道尙好”时总是“有过好日子”,“不过是想好上再好”。王一生作为遗腹子,母亲早亡,继父又窝囊,在那样的年代,对他人父亲的敏感理所当然。脚卵的出现,对王一生内心的刺激无疑非常有力。王一生无父的创伤与脚卵对文人世家的炫耀,使王一生有可能产生寻父的潜在愿望。王一生之所以要以平静淡漠的态度处世,乃是内心深重创伤的一种掩饰和自我化解。小说叙述的故事最后出现一个老者与王一生对弈,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这是混合弒父与寻父双重矛盾的一种叙事,下棋就是一种搏杀,也如小说所渲染的王一生与老者对弈场面的紧张和壮烈,不亚于剑拔弩张的拚杀,或者说乃是武林高手较量的另一种象征形式。老者最后出现,提出与王一生和棋,还请王一生到家里歇了,“养息两天”,谈谈棋道,但王一生还是谢绝了。小说以王一生战胜老者结束,也不妨看成一种象征意义。王一生家道贫困,沉迷于象棋,少年时遇一老者,替他撕大字报,得以老者传授棋道。下棋无疑是他自我证明的根本方式,在遍访高手,经历无数次的棋盘上的搏杀,他成长为一个坚定而能平静淡泊的棋手。这个无父/寻父的心理在小说叙事中虽然不是作者阿城明确要表达的内涵,但小说叙事以无意识的方式给出了这种隐喻。
在80年代初期的那些反思“文革”的岁月里,这些“个人记忆”被放大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加以历史理性的思考,这是时代打下的烙印。而在寻根的旗帜下,“个人记忆”中的生活经验也再次被时代遮蔽,不再向着“个人经验”或“自我意识”方面深化,却以偏远山乡的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为基础,刻意呈现原始粗陋或异域风情的文化特征。显然,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去处都是偏僻的山村,那些贫困的生活和异域风情不过是“个人记忆”中保留的生活经历。既然回忆过去,寻找失落的青春年华,当然要写出那种生活经验和情调。它们本来无所谓“文化性”,更谈不上“根”之类的东西。而“寻根”的文学姿态夸大了“个人记忆”:原来处于附加地位的经验表象,而转变为写作和批评关注的中心。《棋王》,本来最内在的经验在于家庭经验在个人心灵上留下的创痛,或者另一层面上描写知青生活贫困去显示出另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完全可以在一般的人生态度意义上加以阐释的。而在“寻根”的姿态摆出之后,王一生的生存态度却在儒、道、释中讨生活,并且被进一步放大为“东方民族”特有的精神状态。大家的思路开始琢磨这种“精神”在现代文明中,在中国步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永久性价值。至于韩少功、李杭育和郑万隆等人讲述的那些异域风情的故事,在1985年以前是作为知青生活经历的回顾,1985年以后,“个人记忆”的痕迹被抹去,那些原本是作为个人生活环境的风土人情上升为故事的主体部分,因为它们显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价值,它们被置放到中国步人现代化的历史转折点上来观看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不光是因为自觉对城市生活的审美把握还有点吃力和幼稚,更重要的是觉得中国乃农业大国,对很多历史现象都可以在乡土深处寻出源端。”这样,知青经验的消沉迷惘现在改变为自觉的文学追求。自我意识的内在化和情绪化,被历史临时选择替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