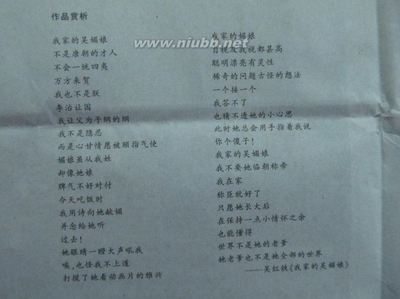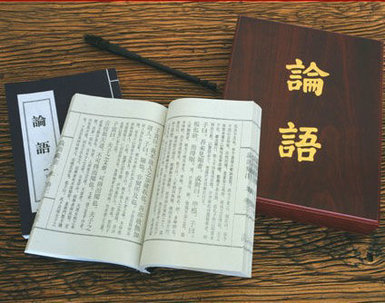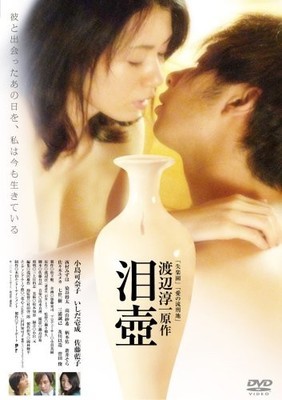性、梦幻与感觉的密码
——《褐色鸟群》的“叙述迷宫”与都市想象
蔡志诚
《褐色鸟群》是代表格非先锋时期实验风格的标志性作品。它在形式实验上的苦心孤诣,对叙述迷宫的精构巧制,以及结构空缺所带来的意义消解,如梦似幻而又暗含一种柔和的理性的仿梦叙述,优雅机智而又迷惘感伤的青春冥想式叙述语调——这些似乎难以调和的小说叙事因子在格非笔下有机地融为一体,恍如一幅织进各种奇幻图案又带有梦想体温的波斯地毯,更准确地说,《褐色鸟群》像是罗兰·巴特《恋人絮语》式的“可写文本”。这部代表形式实验极致的“可写文本”,自发表以来就一直被批评界征引为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代表文本,频频出入于论及先锋小说的种种论文或专著里。《褐色鸟群》的晦涩享有盛名,连批评家也难窥其堂奥,季红真认为它“过于抽象而失去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1]陈晓明甚至称之为“中国当代小说中最玄奥的作品”。[2]
相比于格非《追忆乌攸先生》的“历史寓言”,《迷舟》的个人史“宿命传奇”,《褐色鸟群》确实是一个难以归类的实验文本。先锋小说以形式探索崛起于当代文坛,晦涩多义是其美学风格的一部分,新奇的形式,惊鸿一瞥的陌生化体验,往往令读者与评论家在文本阅读障碍中领悟其有别于传统叙事的独到之处,晦涩含蓄几乎是先锋文学唯美追求的一种标尺。但晦涩加玄奥,也许就是一种叙述极端化的尝试,玄奥之思总是指向存在的哲学意蕴,从形式的锤炼到存在的省思,格非的《褐色鸟群》在探寻叙述的极限的同时,也在探寻季红真所谓的“形式的哲学”,但与其说是“过于抽象而失去了叙事的本性”,不如说是“追踪叙述的本性而过于玄奥”。追踪叙述的本性而抵达形式的哲学,这是格非对先锋小说叙事历险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奇妙的是,这一形而上的思索却是在另一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个播撒性、梦幻与感觉的踪迹的青春冥想故事。从叙事话语来看,它一点也不抽象,那种带有梦的质感的叙述语句不断在文本层面优雅地滑翔而过,但循着一个个抒情喻像化的语句前行时,不断延异的文本踪迹悄然绘出一幅整体结构上的叙述迷宫:前后自我否定的叙述指涉,悬而未决的叙事空缺,故事套故事的重复叙述中的差异性改写,细节上的真实感觉与整体上的玄思奥想,在场的梦幻叙述与不在场潜隐于叙事结构之外的形而上思索,这种种叙述悖论使《褐色鸟群》的玄奥成为一个待解的文本之谜。在我看来,格非这部玄奥的“可写文本”,不妨将其读作一部关于叙述的叙述,一部关于虚构的寓言,一部有关先锋小说叙事历险的隐喻文本。
《褐色鸟群》的开篇就有一种元叙述的意味:
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象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
叙述者以一位孤独的精神漫游者的语调开始叙述,搁浅的季节大船,朝夕更嬗的迟缓,“我”蛰居在“水边”像一个投入写作历险的时间不感症者,逝者如斯的“水边”与书写一部施洗约翰的预言之书。这段影影绰绰的叙述语句里,叙述者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它不仅是小说主人公“我”的自述,也可视作叙述者等同于作者的一番关于书写的自白,正是这一重叠的叙述者映像使小说文本像一把开翕自如的绣花扇一样呈展开来:“主人公”、“叙述者”、“作者”时而三位一体,时而“花开三朵,移位换影”,它们之间的交错互动使小说文本看起来颇似一部立体三维的开放性文本。在西方现代叙事理论里,叙述者或叙述人“指的是语言的主体,一种功能,而不是在构成本文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的个人”,[3]第一人称叙述的“我”作为讲述者的叙述主体,一个可见的、虚构的“我“,这个语言主体的“我”尽其所愿地介入叙述之中,甚至作为一个角色——小说中的主人公参与到行动中。这里,作为叙述功能的“我”与作为人物行为者的主人公“我”显然有别,前者是虚构的语言主体,后者则是文本中的人物行为者,它们有时重叠有时又平行分离。在《褐色鸟群》里,与人物行为者重叠相连的叙述者“我”的叙述修辞可以转述为下列形式:
[“作者”叙述:(叙述者“我”自传式地陈述:)]我(作为人物行为者的主人公)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
通过这一三维叙述层面的细化回放,文本中主人公“我”既与叙述的语言主体重叠交互,又与“作者”的写作经历相切交合——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这部预言之书的书写历程与小说的叙述进程共时性地交错展开,形成一种互文指涉的文本效果:“我的书写得很慢。因为我总担心那些褐色鸟群有一天会不再出现,我想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我的忧虑和潜心谛听常常使我的写作分心,甚至剥夺了我在静心写作时所能得到的快乐。后来,我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我耳畔常常回荡着一种空旷而模糊的声响,我想它不会是侯鸟渐近时悠长的哨子般的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它象是来自一个拥挤的车站,或者一座肃穆的墓地。这声音听上去象是落雪,又象是落沙。”这段叙述里,“我的书写得很慢”有或此或彼的两重指涉——文本内部的预言之书与正在叙述的《褐色鸟群》,“我”的叙述者身份不时交叉换位,在叙述者恍恍忽忽的幻觉叠影中,“我”的叙述声音也产生分裂性的自我“复调”。当不速之客“棋”指出:“好哇。格非——李朴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认识你连李劼也不认识嘛?”叙述者与作者在文本叙述过程中又叠印在一起。
《褐色鸟群》在一个三维叙述空间里展开了故事套故事的叙述迷宫,小说文本叙述了四个“我”的故事:一、以“眼下”的叙述现在时,叙述“我”在水边的白色公寓里巧遇似曾相识的“棋”,她似乎是在“我”写作预言之书的幻觉里摇曳而至,夜里“我”向棋讲述多年之前在企鹅饭店邂逅并跟踪一个穿栗树色鞋子女人的奇幻经历;二、多年以后,1992年春天“我”与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在歌谣湖畔的村子里重逢,但她表示并不认识“我”,也不承认曾经到过城里,她说自己已10多年没进城了;三、相逢后的一天深夜,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跑来告诉“我”,她的丈夫去世了,“我”与这个女人结为夫妻,但她在结婚的当日就突发脑溢血死了:四、“棋”听完“我”的讲述就告辞了,“我”仍然继续写那部预言之书,但天天期待着棋的出现——直至数年之后,“我”又在水边公寓遇到“棋”,但“棋”表示并不认识“我”,甚至说她的名字也不叫做“棋”。在这四个不同时间单元的“我”的故事里,叙述者的身份并不确定,显然有多个“我”参与叙述:一个是《褐色鸟群》的叙述者“我”,一个是讲述预言之书的“我”,还有一个预言之书里的人物行为者“我”,最后还有一个带有“作者”的符号标识的隐隐约约的“我”,这四个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叙述者“我”身兼多职,“我”不仅是两个互文文本的叙述者,而且又是两个交叉文本的人物行为者——“主人公”,再加上隐约浮现的暗示性“作者”印记,正是这多重交叠的叙述者身份,使小说文本像一个多棱旋转的语言魔方,不同叙述身份的“我”变幻出参差错落的悖论性叙事景像,事实上只要辨析出“我”的多种差异性叙述者身份,《褐色鸟群》的玄奥之谜还是可以得到破解的。
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和“棋”先后表示不认识“我”,并否认她们曾经出现在“我”的追忆叙述里,两个女人变成四个似有若无的幻影,表面上看这是以后面的叙述否定前面的叙述,使关键的真相呈现出“叙事空缺”,实际上从更深层的叙述追踪来看,这是叙述人移位换形的“似真错觉”引起的: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作为预言之书里的女主人公,她认识的只是同样是人物行为者的“我”,对讲述故事的叙述者“我”(相当预言之书的作者)不认识,就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不认识福楼拜一样,尽管叙述者“我”以自传式陈述直接参与叙事,但它只是一种语言主体的叙事功能,并不等同于人物行为者。由于作者有意隐去叙事功能上的差异性而代之于貌似同一性的“我”,就容易造成阅读文本时的“误认”,但这种“叙述分身术”并非作家故弄玄虚的炫技,相反,格非似乎将叙述焦点投向有关虚构的形而上思索。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编码里,叙述前三个不同的“我”可以清晰地再现还原为:叙述者“我”在写一部预言之书,它讲述一个奇幻悱恻的爱情故事,他和她在一次不期而遇后历经曲折成眷属,但结婚的当天她就去世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巧遇“棋”,她好像知晓这个爱情故事的隐秘曲折,当我讲述出预言之书的结局时,“棋”就不辞而别了。这一还原简化的叙事编码虽然有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但它们各自双向推进最终交汇于一个聚合点上——“我”讲述的结局与“棋”知晓的正好相吻合,它的结构就类似于双线拱门式结构,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鲁迅的《药》,双主线的叙事推进最终聚合在情节高潮的拱门之上。但格非似乎有意将形式实验推向极致,马原诡异的“叙事圈套”在叙述者与作者的交叉互动上已经掀起叙事革新的狂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不时以叙述者、主人公兼作者的多重叙事身份出现在小说里,[4]但格非在《褐色鸟群》里设置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叙事圈套,他将思考的场域扩展至:作者、叙述者、主人公、读者甚至批评家如何参与虚构,他们之间多元互动的复杂关系如何得以呈现?虚构与时间——那些会把时间带走的褐色鸟群——的竞争关系,性、梦幻与感觉的密码又如何既作为虚构的叙事元素又成为虚构的叙事动力?甚至,虚构是虚幻的现实预构,还是“现实”本身也是虚构的?
“棋”的叙事配置,更显出格非棋高一招的叙述智力。在写作幻觉中翩然而至的“棋”,作为一个符号性的对弈隐喻——叙事与下棋都是一种智力游戏,“棋”具有多重的指涉功能。她在两部互文的叙述文本里交替出现,在作者正在叙述的《褐色鸟群》里,“棋”以一位梦幻佳人的形象突然降临“我”的寓所:“我的寓所从未有过任何来访者。她见到我并未遵循两个陌生人相遇应有的程序,而是表现出妻子般的温馨与亲昵”。“棋”的出场披着神秘的面纱,读者往往会被字面上的性诱惑所吸引,将注意力投向暧昧不明的情色遐想,但如果对“棋”天真而老练的目光有所警觉,再想到叙述者“我”讲述预言之书时“棋”的冷静挑剔的反应,不妨将“棋”视作是在文本间性中浮现出来一个隐喻性的读者形象。这里相应的也有三个层面:一是与文本中主人公“我”对应的“棋”,她是一个实体性的人物角色,深夜来访主客问答类似于苏轼《前赤壁赋》中的那位对话的“客者”,但充满性诱惑意味的“棋”又可看作《聊斋志异》里常见的夜半书生逢狐媚的奇幻他者,她的魅影出没于故事情节层面,使文本表层染上一层梦幻传奇色彩:二是与叙述者“我”对应的“棋”,她作为一个隐喻性的读者(也喻指批评家)提前参与到预言之书的写作过程中,不断追问“后来呢”以及对叙述者“我”的讲述提出质疑,这时的“棋”显然由人物行为者转换为叙述的参与者,这类似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常用的在叙述文本中插入有关叙述策略的再叙述;三是与作者元叙述对应的“棋”,她既可视作是写作历险的一种隐喻,叙事本身也是一种文字的对弈,“棋”不过是作者信手拈来投在纸上一个符号性“棋子”——一种功能化的叙事装置,但由于在“我”与棋的对话中,“格非”成为似曾相识的某种辨认标识,在“作者”写作幻觉里浮现的“棋”又可视作一种深层心理召唤的欲望幻象,“她”在作者创作心理层面投下悠长而又绰约的无意识魅影——性、梦幻与感觉的寻踪。这三个相对应的层面,使叙述者“我”与“棋”形成复杂交错的结构性关系,在这个由参与虚构叙事的各方组成的话语场中,叙述者“我”、“棋”、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与其说是具体的人物形象,毋宁说是某种抽象的叙事功能的隐喻: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叙述主体与隐含读者,甚至批评主体与文本阐释,这些功能性角色成为虚构寓言的象征性结构要素。这一意义上,《褐色鸟群》是一部关于虚构的寓言,它展示了格非小说创作的操作流程与————叙述的隐秘。
《褐色鸟群》的叙述话语隐含着一种绮思冥想的梦幻质地,有论者称之为“仿梦叙述”,这种细腻柔和带有梦想体温的叙述语调,与小说整体结构的叙述迷宫,形成格非的某种叙事风格:局部细致的肌理与整体虚幻的氛围。小说中的叙事细节主要是由性、梦幻和感觉的寻踪组成的一系列视听画面,如果单从故事层面的主题分析来看,小说很容易被当作一则“性意识”的心理浮世绘。“棋”和穿栗树色鞋子的女人,在“我”的细腻敏锐的视听感觉中充满了性魅惑的意味。“棋”就是以一副被凝视的性特写画面出现在叙述者的目光中:
她站在寓所的门前和我说话,胸脯上像是坠着两个暖袋,里面像是盛满了水或柠檬汁之类的液体,这两个隔着橙红(棕红)色毛衣的椭圆形的袋子让我感觉到温暖。
这副性魅惑画面,并非是“棋”有意识发出的身体信息,它纯粹是由叙述者的感觉冥想触发的,“我”的视觉遐想穿透了红色毛衣,感觉到“暖袋”、“柠檬汁”的温暖,这是一种梦想的体温。作为被看的他者,“棋”天真而老练的目光,在视觉对峙中并不处于下风,“我”与“棋”之间的深夜对话,她“充当了一个倾听诉说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当然,这只是故事层面上的“倾听者”,而“我”似乎是为了隐而未发的性遐想,才努力把另一个故事讲得曲折生动。在“我”的讲述过程中,“棋”的角色虽发生转换,她由故事层面的“倾听者”转换成叙述层面的隐含读者,“我”讲述跟踪一位漂亮女人的故事与其说是对情殇往事的追忆,不如说是试图挽留“棋”的话语追踪。棋用“审判一样的目光”紧盯着“我”,还不断地对“我”正在讲述的故事作出批评,老练苛刻的棋总能预知“我”下一步的讲述,“根据爱情公式”她就能提前知道“我”讲述的“后来”,而“我”为了避免被棋识破叙述的进程,只好强调“它完全依赖于我的叙述法则”,并有意识地改变叙述的路线。
当我讲完“雪夜跟踪”的奇幻经历,“棋”评价说“这是一个庸俗的结尾”,为了躲避和回答棋的责难,“我”只得不断延异对漂亮女人的话语追踪,随之而来的“相逢、丧夫、结婚、突亡”等故事情节,毋宁说是为了吸引和得到“棋”的赞赏而进行的叙述转向。叙述者“我”和棋似乎在展开一场旗鼓相当的叙事博弈,这时的“棋”俨然一位熟稔叙述路数的批评家,她敏锐地指出:“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可以永远讲下去。”从小说中的主人公到读者再到批评家,“棋”的身份转换正好预示着叙述者“我”的叙事转换,“我”不断变换叙述技巧以引起作为“批评家”的棋的赞赏,这不正是先锋小说与先锋批评话语的隐喻性关系的象征?黄子平曾以一句妙喻——“被创新的狗追得气喘吁吁”,来形容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追新逐奇的小说实验潮流,而用“审判一样的目光”盯着“我”的棋不正是批评家的化身?当棋听到“我”讲述自己与漂亮女人结婚当天她就患脑溢血死去时,棋做出冷静的批评家才有的反应,她觉得“我的故事再也没有任何延伸的余地”就告辞了,而且她还说要去参加一群年轻艺术家主持的未来派雕塑的揭幕形式。作为批评家化身的“棋”显然对我讲述的悲情故事并不满意,比起未来派画家来已不够新潮。由此观来,棋刚出现时所背的画夹和结尾时出示的镜子,并非仅仅是细节上的某种装饰,而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隐喻。如果联想到前面棋让“我”看画时,说“我”一点都不懂画,那么棋刚来时背的画夹就是一种类似未来派的艺术新潮的象征,它几乎隐喻着批评家“棋”的一种期待视野,希望“我”的叙述能像未来派一样前卫。然而,“我”讲述的爱情追踪故事却有负其期待,所以作为批评家隐喻的“棋”告别后一直没有出现,最后偶尔路过的时候她还表示不认识“我”,实际上可理解成批评家不认同“我”的叙述方式,而棋结尾时出示的“镜子”,这时也获得了隐喻性的象征意义,它不妨视作是“镜子式”现实主义再现论的一种象征。写作预言之书的叙述者“我”与批评家“棋”的叙事博弈,某种程度上几乎浓缩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潜在关系,这一意义上,《褐色鸟群》甚至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先锋小说叙事历险的隐喻性文本。从表面上看,叙述者“我”在对弈中是落败了,但是,对另一位更高位阶的叙述者——《褐色鸟群》的作者来说,即使“棋”的身份由隐喻性读者转换为冷峻苛刻的批评家,她最终也还是作者笔下的虚构人物,像“棋子”一样被布设在叙事棋盘上。因此,玄奥的《褐色鸟群》其实是格非叙述智力的一种极致演绎。批评家“棋”手里握着的未来派画夹与现实主义式的“镜子”,不妨读作是格非对擅长贴标签戴帽子的批评家的一种揶揄式的反讽。格非对自己叙述智力的自信,还体现在叙述话语中运用性、梦幻与感觉的追踪所营造出来的文本愉悦效果:
她迎面走来的姿势跟我刚才在她背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她的魅惑力像泉水一样从她浅黄色、深棕色、栗树色的衣饰的折褶中流淌出来。我等待着她走近,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她双腿轻盈地朝前迈动,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她是静止的,而我正朝她走近。
她的栗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
这两段文字是“我”追踪穿栗树色鞋子的漂亮女人的视觉画面,它们就像一匹在清风徐来中铺展开来的绸绢彩缎,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丝绸般细腻柔和的咝咝声响。罗兰·巴特曾以“文本的欢愉”(文之悦)命名这种奇妙的感觉,他指出:“在阅读一部小说时,使我们燃烧的热情不是‘视觉’的热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是感觉的热情,也就是说,一种高级关系上的热情,这种高级关系也有自己的感情、希望、威胁和胜利。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5]事实上,《褐色鸟群》从叙述形式来看是“虚构寓言”或“形式哲学”的隐喻性文本,但另一方面,它的叙述话语又总是将读者带进一个奇妙的感觉领域,那种由性、梦幻和燃烧的感觉交汇而成的文本的愉悦。
陈晓明在解读这部玄奥的叙事作品时,一方面以“空缺”与“重复”来阐释叙述迷宫的玄妙,另一方面又以叙述追踪性意识的“怪圈”去印证存在的困扰。[6]这种解读无疑使《褐色鸟群》玄而又玄,迷宫、怪圈、存在还是不在,这些带有玄秘气息的批评语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小说文本的神秘氛围,但是以玄秘来解玄奥,反而使批评解读笼罩在一片氤氲迷雾之中。对叙述形式与主题层面的神秘化解读,其实隐含小说文本的内在冲突,如果只强调小说叙述形式上的迷宫结构,那《褐色鸟群》就带有某种故弄玄虚以显示叙述智力的炫技表演,如果强调其主题层面的性意识梦幻,将它归类为具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心理小说,又显然有悖于小说浓厚的形式意味。在前面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部关于虚构的寓言,一部关于先锋小说叙事历险的隐喻性文本。然而,另一个问题迎面而来,如何看待小说这些带有梦幻般性意识的细节描写?
如果从主题层面切入,它也许会被看作是一部充满精神分析色彩的心理小说。“我”和棋的深夜彻谈的确像是一场性意识的漫游记,而且小说文本那种细腻而忧郁的叙述话语与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有几分相似,尤其是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当然两者还是有些差别,《梅雨之夕》的叙述结构较为简单,它只是一段浮想联翩的性意识跟踪经历,较贴近30年代都市中年人那种落寞而又有所期盼的心境,是一篇典型的精神分析性的心理小说,[7]而《褐色鸟群》则具有多维叙述层面,结构复杂近似形式迷宫,性意识的心理漫游只是其中的一个维面,它抒写的是80年代末期都市年轻人曲径幽魅的青春冥想,性遐想与孤独的行吟、梦幻的感觉交织出一种颓废而又浪漫的情调,这实际上是90年代弥漫开来的都市小资情调的想象性预支,只不过它在80年代末还只能栖居在心理意识层面,但已经透露出那种潜滋暗长的都市新感性的感觉密码。格非在先锋早期作品中的“都市场景”系列中对这种新感性有过细致的描绘,《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和《蚌壳》等作品都涉及到这一主题。然而,若单从《褐色鸟群》来看,它的形式意味还是超过主题意蕴上的都市新感性,性意识的心理维面并没有强化到足以掩盖作为虚构的寓言的形式隐喻,性、梦幻与感觉的密码与其说是主题层面的表述意图,毋宁说是虚构寓言的叙事元素,它们更像是格非也包括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在内的先锋作家进行写作历险时经常使用的叙事元件,他们通过对这些叙事元件的不同组合,以各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形式,创造出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兼容的想象时空。这实际上正是先锋小说作为文化前卫的价值所在,而《褐色鸟群》则对这一文化历险进程做了寓言性的概括。“那些褐色鸟群会不会把时间一同带走”,对虚构与时间的竞争关系的某种忧虑,其实正是由现代性想象性预支所引发的焦虑,当这种现代性焦虑在90年代成为现实境遇时,先锋小说所放飞的“褐色鸟群”——一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可能性进行预支想象的精灵——已掠过历史的天际,想象性的虚构演变成现实之后,先锋小说也似乎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自90年代中期以后它只能在历史的凭吊中成为回望的记忆神话。
[注释]
[1]季红真.《格非:质询主体》,《众神的肖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9.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5.
[3][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20.
[4]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340-352
[5][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原载《外国文学报道》1984(4),编入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史》(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04-505.
[6]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桂林:广西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117页,第165页。
[7]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9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