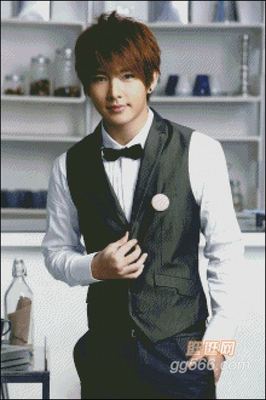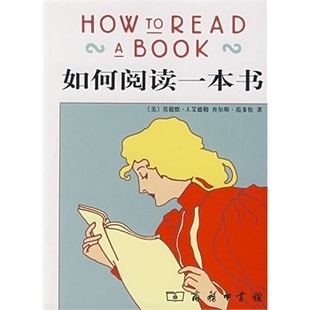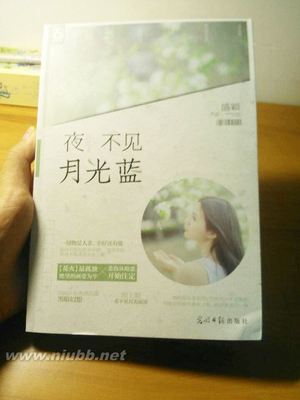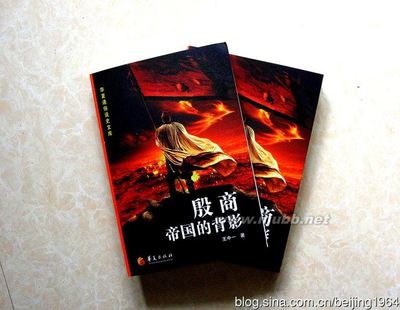《中国命理学史论》出版
很高兴向各位报告,我的朋友、同行陆致极先生的著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此,先将致极先生这本著作的目录及陆先生自己写的序言刊登如下,供朋友们先睹为快。
内容简介
本书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寻和叙述传统命理学的发展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通过传统命理学的历史研究,加深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认识。
作者简介
陆致极,1949年生于上海。1981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1991年美国伊利诺大学语言学系博士。出版的著作有《计算语言学导论》、《计算语言学》、《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八字命理新论》、《八字与中国智慧》(《八字命理新论》增订版)等,并在中外学术杂志发表语言学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序言
各章提要
第一章 传统命理学的现代诠释
第二章 命的观念和传统命理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第三章 阴阳五行学说和自然生态模式
第四章 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分期
第五章 孕育时期:神煞、四时和刑冲会合
第六章 古法时期:古典模型
第七章 今法时期(一):标准模型
第八章 今法时期(二):论性情和论疾病
第九章 今法时期(三):六亲网络和财官网络
第十章 今法时期(四):格局系统
第十一章深化时期(一):《神峰通考》和《命理约言》
第十二章深化时期(二):《子平真诠》
第十三章深化时期(三):《滴天髓》
第十四章深化时期(四):《穷通宝鉴》及《命学玄通》
第十五章转型时期(一):从近代到现代
第十六章转型时期(二):开拓和挑战
第十七章传统命理学和传统思维
第十八章传统命理学的再认识
附录中国命理学史古代文献资料简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以上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网页www.spph.com.cn/people/index.asp)
陆致极著:《中国命理学史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人文专著丛书,637页,2008年8月第1版
序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去年暮春,我辞去工作,一个人关在芝加哥西郊的小楼里,专门来从事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当时,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陆老师,你真的不要‘饭碗’,来搞这迷信?”
我看着他疑惑的目光,回答说:“不要‘饭碗’,是事实;搞迷信却不是,恰恰相反,——是破除迷信!”
在我看来,神秘和无知,是培植迷信的土壤。要破除迷信,揭示真相,最好从历史的研究做起。因此,当我最初拿起笔来的时候,我为自己确立了三个目标:
第一,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去探寻和叙述传统命理学——这里主要指八字命理学——的发展历史。
传统命理学在民俗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影响,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地叙述它形成和发展历史的专著。
古代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七十年前方重审曾说:“盖古代士大夫阶级,目医卜星相为九流之学,多耻此道;而发明诸大师,又故为惝恍迷离之辞,以待后人探索。间有一二贤者,有所发明,亦秘莫如深。既恐泄天地之秘,复恐讥为旁门左道,始终不肯公开研究,成立一有系统详明之书籍,贻之后世。故居今日而研究此种学术,实一大困难之事。”这里道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命理学属于“九流之学”,进不了封建时代正统的学术殿堂;二是研究者即使“有所发明,亦秘莫如深”,使之带上了“惝恍迷离”的神秘色彩。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和文化思想,曾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模式骨架的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被人们所抛弃。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认为,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理解世界的框架,在中古时代尚算可以,到近代就太落伍了。诚如何丽野所指出:“这种观点几乎是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得到一致公认的观点。张岱年先生讲,阴阳五行之气的概念,‘五四时期许多人已不理解’,如陈独秀即认为它是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实不是不理解,而是不屑于去理解,因为它已经被认为是毫无价值。”那么,在民俗文化中生存的、根植于阴阳五行说的传统命理学,自然是命途多蹇。尤其是解放后,它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更是无人问津了。
然而,作为一种民俗现象,自有它发生、发展以及衰亡的理由。何况明清两代,八字算命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曾有过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若不加以研究,将来更趋困难。仅从文献上来讲,比如,明代《三命通会》中所摘录的当时流行的命理书籍,今天基本上都已经绝迹。因此,就填补学术上的这个空白而言,我觉得也值得下功夫,对已有的资料作一番整理和研究。用现代观念和语言开掘并梳理出一些基本线索,记录下它曾经有过的漫长的发展历程。这是我们炎黄子孙对自己古国文化应负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谢天蔚教授。他曾邀请我到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作过两次有关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和八字命理的学术报告。报告之后,中外教师和学生一再提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记得当时天蔚对我说:“致极,你应当写一本有关八字命学史的专著。你是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同时对命理有长期的兴趣和心得,——你是写这本专题书的最佳人选!”挚友的话,的确震动了我的心灵,使我下了决心,专门来写本书。虽然深知自己才思钝拙,但我的确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来完成它的。
事实上,对于一门学术的透彻了解,是离不开对其发展历史的认识的。命理学尤其如此。因为它是在民俗文化中生存和发展的,鲜少“权威”。现存的材料,大多“头绪繁杂,文义俚拙”;或兼收并蓄,或各说各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是不同的探索视角、甚至不同的分析模型,长期共存,各自挺进。作为第一本命理学史,我着力在挖掘和整理它的发展脉络,重点揭示和剖析一些代表性著作的主要立论和方法、以及对整个学术发展的贡献,从而勾勒出传统命理学千年进程的概貌来。
第二,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
本书首先是一本命理学史,但同时又是一本史论。这就是说,它试图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命理学?它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八字命理学作为一种通过个人的出生时间去描写和预测其命运的学问,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智者隐士冥想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是可以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找到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的。
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成熟的命理学产生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并论证先秦时期出现的个体主体性意识,对现实生命存在(世俗生活)的肯定态度,以及秦汉大一统所奠定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和“家国同构”的封建秩序,为传统命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土壤(见第二章)。同时,在追溯阴阳五行说的历史源流和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气一元论的论说,蕴涵了阴阳五行信息的干支符号模型的形成以及它所映射的古老中华自然生态模式,为传统命理学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分析工具,并由此推断传统命理学发端于东汉后期(见第三章)。
从历史看,传统命理学的基础,是寻求和建立个人出生时间跟其生命潜质、人生历程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里并没有迷信的色彩。然而,传统命理学之所以能越出术数的藩篱、跨入学术的境域,是因为它在这样的对应关系基础上,构建起了描写和预测的“理论模型”。本书正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描写和概括八字命理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比如,在叙述宋明时期的徐子平论命模型(这个模型一直沿用至今)时,作者深入地讨论了作为这个模型核心内容的六亲网络和财官网络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后的时代内涵(见第九章)。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就会有它形成、发展、成熟、直到消亡的历史过程。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也将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不可避免地丧失它的描写和预测的能力。本书在讨论现代命理探索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指出传统命理学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它的陈腐和局限,正日益暴露。如果命理研究无法出现“突破”的话,那么,死亡——将成为这位走过千年历史征程的老人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见第十五、十六章)。
第三,通过传统命理学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既然传统命理学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自然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认识。可是,由于它长期存身于民俗文化之中,到了现代,又被贴上了迷信的标签,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充分理解,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了。事实上,它是蕴含了我们先人智慧的一个宝藏。正因为如此,作者下了很大的工夫,来解剖这只目前还一息尚存的麻雀,并用了本书最后两章的篇幅(第十七、十八章),全面地探讨了传统命理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智慧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目前尚未得到学术界充分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多视角的探索方法;一是“以小见大”(或“以微见著”)的智慧形态。多视角的探索,这是跟传统智慧着重于从(黑箱的)“功能”下手的探求思路有关;而以小见大则是一种东方中国独有的智慧形态。它不同于西方或现代科学的探求角度,这是中国古代实用-经验理性在认识世界方面的突出表现。事实上,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我国传统学术(甚至技术、技能)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并不等于“全”,而目前一些现代学者(因为不了解传统智慧的这些特点——希望不是“不屑于去理解”),大多是从“全”的方面来责难中国传统学术的。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贤者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毕竟做出来了。”事实上,认真挖掘和考察传统命理学里所洋溢出来的这些“中国的智慧”,是不难解答爱因斯坦的惊奇的。
本书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来撰写的。但为了使行文通畅,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有较大的可读性,作者把相关的引用资料、比较繁琐的历史考证、以及历史上各家有关的认识和评论,尽可能地放进注释中。若对相关论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留意注释的内容。同时,作者还摘编了与传统命理学发展历史相关的一些古代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附录,供读者参考。至于本书是否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写作目标,书中的观点和论说是否合宜,则有待于读者和专家们的不吝指教和批评。
今夜是农历八月十五。搁下笔,从小楼之窗遥望静謐的夜空。刚下过雨,依然厚云密布,见不到婵娟的清辉。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时,我的心已经飞越了重洋,回到了万里之外的故乡!
(2007年9月25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