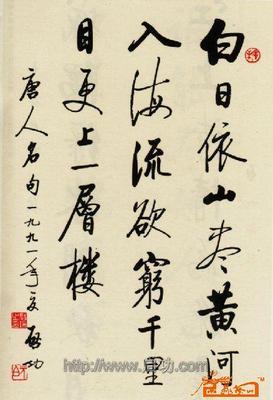以下内容翻译自这本书《Baby Division》
卡尔-海因茨·德克尔(Karl-Heinz Decker)
党卫军第25装甲掷弹兵团
卡尔-海因茨·德克尔
我10岁的时候(1935年)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在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阅读军用地图,还有大量的体育活动,徒步旅行以及唱歌。我打算加入某个党卫军骑兵师。在报名处,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师?我同意了。我加入党卫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精锐部队。在进入部队前,我就在学校接受过8到9个月的预备役以及士官培训,虽然这段时间很辛苦,但后来这一切都在战场上得到了回报。此外,由于相同原因,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师之初就成为了一个小头头。
我被分配到了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2营8连,库尔特·迈尔是我们的团长。我远远的见过他几次,他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知道如何善待自己的手下。到了前线后,我们总是在夜间才能行军,我根本不记得我们路过了哪些法国村庄。幸好我(们)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后勤人员,他总能在夜里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候,我们甚至还能吃上一些法国难民留下的鸭子、鸡肉等。法国人总体上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善和礼貌的。诺曼底初期的几场战斗结束后,我跟随一个小战斗群负责坚守法莱斯地区的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坚固的墙壁替我们抵挡了不少加拿大人的炮弹。我们待在一座可以俯瞰道路的大屋子里,屋子周围是一片果园……。最终,我们的阵地还是被敌人突破了,只能丢下伤员向后退去……
敌人的轰炸总是永不停息,规模也是我军比都没法比的。以德累斯顿为例,官方说总共被炸死了30,000人,其实根本不止这个数。在任何部队都有好人和坏人,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屠杀战俘事件总是频频发生。有许多士兵被随意枪决仅仅是因为他们身穿党卫军制服或者手臂上有党卫军部队特有的刺青。而这些屠杀过我们同志的盟军士兵事后都没有受到任何审判或追究,被枪决或吊死的只有德国人。所谓的纽伦堡大审判不过是一场无耻的作秀。
1944年8月18日,我在法莱斯包围圈之战中被俘。我先被押送到了英国,接着又被运送到了美国。一开始,我被关押在阿肯色州,后又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在这两处我们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只是经常挨饿。到了1946年,我们又成为英国人的战俘并被关押在比利时的战俘营里(编号2228)。在战俘营里,我们的食物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我们10天才需要去一次厕所。
数周后,许多党卫军战俘又被押送回了英国。按照日内瓦公约,艾森豪威尔应该为1945年到1947年间,因为饥饿而死亡的德军战俘负全责。
被俘后,我被报告为失踪。我有一个姑母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兰辛。她设法找到了正在东普鲁士避难的我家。1948年圣诞节,我终于获释回家。我的父亲也在同一时间从一座英国战俘营里获释并返回家里。说起我父亲,战争开始时,他就一直在海军部队服役。
党卫军的老兵们互相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为我曾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战后,美国人对德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洗脑教育。美国人告诉所有德国人,从1933年到1945年,德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他们成功了,现在所有德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德语中现在充斥了大量的美国单词。在朋友面前,我现在管德国就叫“小美利坚”。我极其反感那些把美国人塑造成英雄的各种言论、报纸和电影。
然而,我们这些老兵在德国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1983年和1985年两次举行的党卫军老兵聚会,都遭到了反对者的骚扰,他们向我们投掷石块并且破坏了我们下榻的酒店。我们不得不将聚会地点改至奥地利。我从来没见过人们如此讨厌我们(这要归功于美国人灌输的思想),现在的德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剩下了。我现在定居在威尔士北部并且接受了这里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
1985年,在内瑟尔旺(Nesselwang),反纳粹人士正聚集在克罗内(Krone)酒店的门口抗议党卫军老兵聚会,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维持现场秩序。
洛塔尔·艾丁(Lothar Eiding)
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
洛塔尔·艾丁
在希特勒青年团里,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我们天天都唱各种民歌和爱国歌曲,还要参加各种田径比赛以及足球、手球等运动。到了夏天,我们还可以到乡间野营。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化学家,但是这个梦想很快因为战争的到来而破灭了。
1942年,我加入了党卫军。我相信这是一场为了祖国而战的正义战争。因为我的父亲也在一战中服役了整整四年,而且我绝不接受《凡尔赛合约》强加在祖国头上的种种一切。作为一名机修人员,我属于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我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是还能接受,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战场上隐蔽自己,学习如何使用步枪、手枪、MG34机枪、MG42重机枪、如何投掷手榴弹,埋设反坦克雷以及熟悉党卫军的种种条条框框,比如荣誉条例,结婚条例等。基础训练接受后,我们在波美拉尼亚的劳恩堡(Lauenberg)的一所学校里接受士官培训。我由于能力突出被选派到了刚刚成立的希特勒青年团师担任士官。
我很后悔没有直接返回老部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这个师(希特勒青年团师)严重缺乏士官,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士兵大多仅仅完成基础训练或者只是适龄人员。跟我一起在连里担任士官的还有几名同样来自劳恩堡的学员,以及9名来自东线的老兵担任着班、排级的指挥官。让这些在俄国前线战斗过的老兵接受我们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新人根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我们连的士兵都是1926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都是志愿加入党卫军的。这些人在体检时,就被询问想加入装甲兵、炮兵还是步兵等等,他们甚至可以进行士官资格的报名。
1944年4月底的一天,我们连奉命接受上级的检阅。与平时一样,列队完毕后,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高赫(Gauch)向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布本策(Bubenzer)汇报准备完毕。在布本策身边是一名瘦瘦高高,身上挂满了勋章的军人,他的名字叫彼得森(Petersen)。连长告诉我们,彼得森教授将从我们中挑选出几个人,上一堂特殊的教学课。彼得森教授沿着队伍来回走了两次并不时的与我们中的一些人说上两句,最终他挑出了3个人。这时候,他突然注意到我是士官中唯一一个身上没有任何勋章的人,因此他把我也挑了出来……。开始上课后,他铺开一副巨大的地图,然后掏出红色铅笔开始勾勾划划起来。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布本策,他在组建希特勒青年团师初期负责培训士官的工作。
他在地图上勾划的同时,还不时的抬头问我们多大了,老家在哪里,接着问我们为什么加入党卫军。我那时才刚刚18岁入伍也仅仅一年,但是当他问到我时,我回答说,我从少年时就想加入党卫军了。我从父母那知道了战争爆发的消息,我知道元首是不想发动战争的,我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包括与波兰、法国、挪威等国的战争都是为了自卫,后来我才知道一切并不如我所想。
在父亲的桌上有一份报纸,《黑色军团报》(DasSchwarzeKorps)。从这份报纸上,我第一次知道特别机动部队以及党卫军。后来我又读到了“闪电迈尔”,就是后来的“装甲迈尔”。当我读到侦察部队总是冲在战斗最前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也是我加入党卫军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一定要成为摩托车兵,像“装甲迈尔”一样永远冲在最前方。当我开始学习党卫军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时,我才真正感到党卫军是一个有着特殊精神的战斗组织,这些都在我们的誓言和歌曲里一一体现。
1944年6月6日,我在“装甲迈尔”的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下担任一名班长。我奉命前往卡昂附近的卡尔皮凯机场侦察那里是否被敌军占领。6月8日深夜2点整,我们对布雷特维尔-洛格约斯发动了一次夜袭。在战斗中,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腹部,我被立刻送到了野战医院。我们的红十字急救所已经被敌军的飞机炸毁了,敌人在战斗中不断的犯下各种战争罪行……。我在雷恩(Rennes)的战地医院里花了整整十天才养好伤。由于我扣扳机的手指也受伤了,所以手仍裹着纱布。
不久后,我坐上了一列从巴黎开往林堡(比利时东部一省)的红十字列车。火车的每一节车厢都被漆成了白色,并画了醒目的红十字标志。这下我感觉应该能够安全的离开法国了,但是当凌晨3点列车开始全速运行时,我们再次遭到了敌军的空袭。我们的列车在猛烈的空袭下很快就脱轨了,许多伤员都被甩出了病床。剧烈的爆炸过后,我发现我自己躺在车厢的地板上并且开始胃出血,包扎手伤的纱布也成了一根根小碎条。我记不清我是昏迷了还是他们抢救伤员的速度飞快,反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劳恩堡的医院里。医生告诉我,我的右手已经不需要再包扎了,因为马上要做截指手术。我央求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再后来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切掉我的手指。经过休养,我的手指只是活动起来有些不灵便。到了9月,我终于可以伤愈归队了。没过多久,我被送到位于布拉格的容克学校里继续学习深造。1945年3月,我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并得到了一个“B”。我很快被调到了SS第2“帝国”装甲师。这个师正在布尔诺(Brunn,今捷克境内)激战。1945年5月8日,我们奉命向西撤退,我们一直退到了维也纳的西北方。5月9日,在遇到第一批美军后,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了。
我和另外两名战友决定无论如何我们都待在一起。我的手表、钢笔等一切东西都被战俘营的看守们搜刮一空。我和战友设法逃了出来,但是很快又被美国人抓住,扔进了位于瓦勒姆(Wallern)的战俘营。我再次从这个战俘营逃了出来,仅仅4天后,这个战俘营就被俄国人接管了。在我回家的漫长旅途中,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座森林里发现了3名战友的尸体,我根本没有力气掩埋他们,只能简单的用松树叶盖住他们。我走了整整1800公里才到家,战争也结束了同时我也快满20岁了。即使是到了1945年5月8日后,战争对党卫军来说并没有结束,成千的党卫军士兵被无故的枪杀或者吊死。迄今为止,还有不少组织在追捕党卫军成员,就因为纽伦堡审判中认定我们为犯罪组织。这些被黑手党控制的媒体(指美国为首的盟国组织)直至六十年后仍在散布这些错误的信息(认定党卫军为犯罪组织),这一切对我打击很大。我现在仍与在诺曼底战役开始时就在一起的两名战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历史上,战败者的历史总是被胜利者任意书写的。最新的例子就是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所谓的联邦德国总是在扮演一种惟命是从的龙套角色,而德国新出生的一代人则是完完全的傻子。
乌尔里希·费尔登(UlrichFleden)
乌尔里希·费尔登(右数第2)。1943年,突击队员(候补军士)费尔登在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下属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7连服役时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我出生和长大在一个原来属于德国,但现在已经成了波兰一部分的地方,这块地方700年前是属于德意志的。我小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军人。14岁时,我自然也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隶属西里西亚的克吕茨贝格(Kreuzbg)第51青年营。我加入党卫军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精锐部队。1941年10月4日起,我在里希特菲尔德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军营里接受各种训练。在那里我一直待到了12月30日。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格言指导下,我们进行着刻苦的训练。
俄国步兵的战斗素质很低,但是他们的大炮和坦克确实厉害。俄国军官在战斗时,从来不关心自身的伤亡。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师担任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1945年3月28日时,我正躺在一所匈牙利医院里养伤,这座医院里住满了德国和匈牙利的伤兵。邻床的一名突击队员跟我是一个部队的。第二天,俄国人来了,我很快就听见了叫喊声还有枪声。他们杀死了医院里所有的德国人,因为我们的衣服就放在床边上,因此那些俄国人很容易就知道哪些是匈牙利人,哪些是我们德国人。这时候,一名勇敢的匈牙利护士飞快的将我和那名士兵的衣服藏在了她的护士袍下,然后她镇静的走过俄国人身边一直到楼下,并将衣服扔出了病房的窗户。俄国人冲进了房间,用手枪指着挨个指着伤员的脑袋问,“是不是德国人?”我闭上眼睛装作昏睡过去,同屋的匈牙利士兵则不停的跟俄国人说着话,其中一名俄国士兵抢走了我的手表。最终有32名德国人被俄国人打死或枪杀。我和那名突击队员是仅有的两名幸存者……
1945年1月,俄国人就占领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都被他们杀害了,我再也没见到过我的家,我的父母。从战争时期一直到现在,美国人都在我们(党卫军)的问题上谎话连篇,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组织或狂热的纳粹分子。我们不过是一些为了祖国而战的普通士兵而已。
现在德国的年轻人都是被人操纵的,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历史。他们既不了解祖国真正的含义也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特奥·弗兰德卡(Theo Flanderka)
特奥•弗兰德卡在党卫军第3“德意志”团服役的照片
我加入党卫军是因为他们吸引人的海报以及严苛的规则,能够加入其中的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分子。我被分到了“德意志”团并在慕尼黑训练了整整8个周,然后又在布拉格训练了8周。当希特勒青年团师建立时,我就加入其中直到战争结束。
在盟军登陆后的第二天,我们赶到了诺曼底。一路上总是遭到盟军不停的轰炸,我们的掷弹兵一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战斗。在整个大战中我总共负伤7次,4次在东线,1次在诺曼底,在匈牙利又负伤一次。
1945年至1948年我一直待在战俘营里,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一直为我所在的部队和战友间的深厚情谊而感到骄傲。
特奥·弗兰德卡获得银质战伤章时拍摄的照片
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显示了1943年秋季,正在训练希特勒青年团师新兵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特奥•弗兰德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