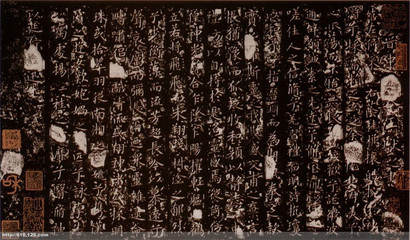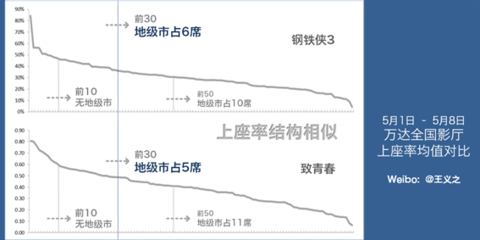按:同学们好。讨论六朝的艺术,我们多次谈到了顾恺之的绘画。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洛神赋图》的文章,发表在《艺术探索》。现在转发在这里,仅供大家参考。
树·空间·图式
——对《洛神赋图》个案研究的一种尝试
内容提要
《洛神赋图》在绘画史中有重要地位,然而对其误读却常有发生。本文试图从作品画面分析入手,以其树造型为出发点,逐步发现《洛神赋图》独特的造型语言和空间表现的观念,力图在秦汉以来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观念背景下理解六朝绘画,从而矫正后世用山水画或文人画观念解读《洛神赋图》的视域。
关键词
人大于山水不容泛 洛神赋图树比兴空间人神对峙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六朝绘画时说:“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我们不知道张彦远是否看到过顾恺之的原作,但就《洛神赋图》来看,画面中山水、人物、树木的造型基本上符合张的描述。尤其树木,看上去画家似乎还未掌握树丛密林的表现技法,树木都是棵棵独立,伸出的枝干和树叶仿佛人的手臂一样有趣。“人大于水,水不容泛”说的是其比例大小不符合自然规律,似乎山水只是人的背景或陪衬,整个画面因而似乎是一种平面的、二维的、没有空间感(缺乏大小、远近、透视感)的构成。
《洛神赋图》真的可作如是理解吗?后世论画者多喜欢把《洛神赋图》作为中国绘画童稚期的作品,喜欢用张彦远的话作为一种事实性的陈述却很少对其画面的构造意匠做具体的缜密分析[1]。这是值得反思的。其实,有多种理由可使我们相信《洛神赋图》远不简单。其一,如前所述,六朝虽然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在艺术和文化上却非常繁荣,甚至被学者类比与欧洲的文艺复兴[2]。其次,六朝艺术观念和实践十分活跃[3],虽然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传世画论和有限的作品中亦可一窥其复杂性和水准。比如读一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就会发现他对绘画的造型和经营远不简单。文章一开始就提到“山有面则背向有阴”,很强的立体造型的观念。后面提到“山别详其远近”,“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详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耳”,也能看出他对比例、远近的重视。通篇还详尽描述了画面各段人物、山石、峰峦的布局、赋彩方法、及其严密而有趣的关系,等等。鉴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洛神赋图》必须从作品特定的时代语境、创作者的视角和艺术语言的选择予以具体分析和解读。本文就是试图以树木造型为切入点对作品的创作条件、背景、手法、意义进行解读的尝试。
一、独特的树造型
图1 蘑菇树 |
图2 点叶树 |
首先来看点叶树。
有一个疑问是“这种树是否象一些学者所说的就是柳树”[5]?这是值得怀疑的。持此观点其实就是相信画家把它作为柳树来描绘,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表现。当然《洛神赋图》有很强的目的性,画者不厌其烦地以如此大的体量和密度表现点叶树肯定不是偶然随意的行为,但这是否与柳树相关则是另一回事。依据绘画创作的经验不难理解,作者应该在下列条件的制约下表现了点叶树:其一,我们可以假想作者有可能遵循了古已有之的某种画树的习惯或法式,这使得他不期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画法。其二,该图是对曹子建《洛神赋》的图像表现,故对点叶树的描绘很有可能是为了图解诗文。其三,画者也许对这种树素有偏爱,或生活环境中经常见到,这种偏爱或经验影响到了他的绘画。无疑,这三种因素都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查阅汉魏以来的画像传统却很难见到这种所谓的“柳树”的形态和画法,即使在风格与此图十分接近并有复杂树木形象的北魏洛阳《宁懋石室画像》和《孝子画像》石棺中,也看不到这种点叶树。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尽管也是为了图解文学作品,但画者似乎对树木的表现毫无兴趣。这说明,把柳树看做那个时候画者的意图、喜好或习惯是很牵强的。
有证据表明,《洛神赋图》很大程度上是对曹子建原赋的“转译”。下表列出了《洛神赋》与《洛神赋图》在形象塑造和情节表现上相对应的地方:
表一:
类别 | 《洛神赋》与《洛神赋图 》相对应的描写或描述 |
景物 | 惊鸿 游龙 秋菊 春松轻云 蔽月 太阳 朝霞芙蕖 绿波 幽兰玄芝 云车 水禽文鱼 静波 六龙玉鸾 |
人物 | 曹植主仆 丽人 众灵冯夷 女娲 南湘二妃游女 |
动作 | 车怠马烦 俯察 仰观睹丽人 以邀以嬉采玄芝通辞 解玉佩以邀之众灵杂遝 戏清流 翔神渚采明珠 拾翠羽 鸣鼓清歌 腾文鱼鸣玉鸾 背下陵高足往神留 遗情想象顾怀忘愁 就驾归乎东路 |
表一说明,画家在表现形象的时候绝非空穴来风,其主要的依据就是原赋。那么,如果如此重要的点叶树就是柳树的话,那么原赋中想必会有关于柳树的描述。并且我们还可推想,假如作品系顾恺之所为,画家在其他讨论风景画的文章中也很可能会留下蛛丝马迹。表二就列出了在原赋和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所有涉及到的植物:
表二:
诗文 | 该作品中所有涉及到的植物 |
洛神赋 | 秋菊 春松芙蓉幽兰玄芝椒蘅匏瓜芙蕖 幽兰 |
画云台山记 | 涧中桃桃树 孤松 |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柳树的线索。那么,《洛神赋》中有没有关于曹植身处环境的描述呢?原赋的一开始就说:
“余从京师,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轅,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怠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
此处蘅皋、芝田均与柳树无关。而阳林,据李善注:“一作杨林,地名,多生杨,因名之[6]”。可知,如果认可画家据文作画,此处的点叶树与其说是柳树倒不如说是杨树了。总而言之,把这种点叶树认作柳树只是凭视觉经验而已,除此之外并无依据,且毫无情理。这说明了什么?在这样一幅与原文高度契合的画作中,画家不厌其烦地描绘如此多的点叶树,岂不正说明在画家的意图中这种树必然别有深意吗?也许画家受到了生活中柳树的启发,但前述分析使我们相信,画家并不是想要表现柳树,而是要用一种特定的点叶树的精微形态传达另外一种含义。为此,需要对这种树作进一步的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放到点叶树的分布与其它物象的关系上。这次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点叶树的分布特点与其它树截然不同。在整幅画卷(以故宫本为例)中,点叶树的出现似乎与曹植及其从仆的出现密切相关:凡是有树遮盖曹植等主仆,一定是点叶树,而在神灵出现的环境中,点叶树则十分罕见。实际上,曹植主仆在画面中总共出现了六次,其中除了有两次例外(一次乘船追赶洛神,一次乘车马离去)之外,其余四次均以点叶树覆盖其上[7](图3、4、5、6)。这种对点叶树如此明确而集中的使用,显然是画家有意为之,其意义这里暂不作分析。

图6曹植与点叶树图7辽宁本中松树图8 故宫本中红叶树 图 9 蘑菇树形状图 10“伸臂布指” |
那么,与点叶树有所不同的蘑菇树又是怎样的一种树?其使用方式又有何特点呢?下面来看蘑菇树。
“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多存古法,其树木皆如孔雀扇形,分断画赋意[8]。
孔雀扇形是学者们喜欢的用来描述此树的一个比喻。除此之外,也有人用“薄荷把”、“芝而(灵芝)形”等作喻[9],但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树直到现代才有学者加以判定。比如称之为“梧桐树”或“银杏树”[10],也有人根据原赋有春松的描述而推测之为松树。这都是不妥的。其实,在辽宁本中有一段专门描绘了两组七棵松树,用以呼应原赋“华茂春松”的诗句(图7)。在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树的针叶形成球状,松针的感觉十分强烈,而且松树还有以淡墨渲染过的痕迹。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有关于松的画法的叙述:
“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醲也”。
图 11、12、13 蘑菇树与山的组合十分密切 图 16 大小蘑菇树的组合 图 17、18 小蘑菇树分布于河边和远处山脚 |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依照画家的原意这种蘑菇树肯定不是松树,当然也不会是梧桐等其他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相信,画家之所以大量地描绘并使用这种树恐怕也别有他意。依照在分析点叶树中获得的经验,不妨从这种树的分布及与其它物象的关系中发现它的特点。这样,当我们把注意力重新回到画卷上的时候,会发现蘑菇树的分布有另外的特点。
图 17、18 小蘑菇树分布于河边和远处山脚 |
图 14、15 蘑菇树与神灵的组合 |
首先,只要在山丘起伏的地方几乎必有蘑菇树,把山丘与蘑菇树结合在一起很明显是画家有意构思的结果。统观画卷,《洛神赋图》中描绘山林的场景有五个,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与山组合的树主要是蘑菇树(如图11、12、13)[11]。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凡是在起伏较高的山顶上出现树,一定是蘑菇树而不是点叶树。其次,还需注意之点是蘑菇树与神灵的关系。前面已知点叶树与曹植主仆人物密切相关,这里我们发现,蘑菇树与神灵也有内在关系。一方面,在神灵旁边常常会伴随一些蘑菇树(图14、15),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密切,因为神灵并不被树遮挡或靠近,而是稍有距离地并置。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神灵常常处于周围有蘑菇树的环境里。其三,蘑菇树的复杂性在于其大小和分布的不同。蘑菇树有大有小,大树与小树常常会交错在一起(如图16),比如在一棵高高的蘑菇树根部,会有几棵小小的蘑菇树。而小蘑菇树分布十分自由,在河边的石溪,在远处的山脚,在点叶树的旁边,在人物的周围,(图17、18)等等。看上去,大小蘑菇树虽然都采用了类似“孔雀扇形”的画法,但它们的用法不同,似乎在努力代表不同的东西,因而采用了如此多变、甚至矛盾的用法。
下面,我们可以把两种树的分布特征加以总结,然后就可以揭示其内在的意义了。
表三:
树 | 体量 | 形态 | 数量 组织 | 与其它物象关系 | 其它特征 |
点叶树 | 较大 | 统一 | 不太多,分布集中 | 凡有树遮盖曹植主仆,必是点叶树 | 神灵旁边罕见此树。近处偶有点叶树 |
蘑菇树 | 大小不一 总体较小 | 多变 | 多 分布较广 | 在神灵周围环境,并置。 与山丘关系密切。凡山顶或陡峭山谷有树,必是蘑菇树 | 不可覆盖人物 近处若有蘑菇树,体积较小 远山处蘑菇树较小 |
由此可见,当画家使用两种树的时候,是有选择的,也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设想,画家之所以设计了这两种树,并把它们在特定的位置使用,一定希望达到某个目的。问题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二、树造型的意义及空间表现
研究树造型是为了对《洛神赋图》有更内在的解读,这意味着需要了解此作品的原创者特定的创作情境,即画家因何而画,主旨何在,难点何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对《洛神赋图》的创作权及创作时间学界多有疑议。比如有学者认为此图并非顾恺之作品,还有的把它的创作年代定为南朝[12]。然而,此类考证对本文的讨论影响不大,这基于学界对《洛神赋图》的一个基本判断:此图原作必为六朝名家之作品,其造型特征和审美倾向与六朝艺术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理解树造型及其意义的话,原作作者是顾恺之,陆探微,抑或史道硕,就都不重要了。
1、画家的难题
其实,《洛神赋图》本身就承担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追求曹植诗作《洛神赋》所表现的意境。当我们读《洛神赋》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那充满瑰丽神奇的浪漫色彩的人与神相遇、相视、相交融的境界。曹植是现实中的人,洛水也是现实中的景,而洛神则属于诗人所向往的神灵世界。近年来对曹植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曹植所描述的“人神对话”的观念绝非偶然现象,它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恒久主题,而且在盛行神仙崇拜的六朝社会中更具有典型意义[13]。《洛神赋图》的创作者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此时代审美取向的深刻影响。在思考该作品的审美特质时,苏涵发现作者以曹植与洛神“眼神对视”来经营位置的审美构思[14],这是揭示其“人神关系”的初步尝试。不过在本文看来,“对视”只是“人与神”各自的地位及其属性确立之后的发展,因此,对于此画来说,当画家面对一片空白的画帛构思之际,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一个有形画面的二维空间如何表现“现实与神灵并置”这样一个难题。其难点在于,现实空间是切近的、真实可触的、有远近大小空间的,神灵世界是无所谓远近的、超越了三维空间的、不确定的,并且这两种空间还要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因为画面人和神两种人物有邂逅,有交流。当然还不能忘记,作为一幅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人物画,叙事性和人物描绘是画家的基本任务。因此,画家面对的是双重的挑战:
a,画面要有均匀的、连贯的、并且处于活动和交流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和组织;
b,要为每个人物赋予一种空间,或者是真实空间,或者是神灵空间。
图 19 神的衣服凌空飘动 |
针对上面两个任务,我们可以从画面中再一次寻找答案。首先对于第一个任务,可以理解为对处于时间中的叙事性的表达。苏利文认为这种类似连环画的技巧和佛教的传入有关[15]。更准确的说法是,《洛神赋图》的叙事手法应该受到了当时在中国已经广泛流行的佛教壁画手法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印度佛教的图式系统最典型的是“佛像图式”而不是叙事性,正如傅抱石所说的,中国佛教绘画更多的是模仿印度的图像造型、晕染的方法、背景的运用[16]。而叙事性的壁画,用景物作不同场景的分界线,乃是中国汉画传统与宗教主题相结合的产物[17]。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树木对画面的分割作用显而易见。然而,《洛神赋图》与其很不相同,景物对画面的分割是十分含蓄、不着痕迹的,而且有理由相信,山水树木的描绘和布置已经成为《洛神赋图》主题描绘的组成部分。对此可以提出几种证据:其一,点叶树与画面分割毫无关系,它与人物结合为画面主体表现的成分;其二,山水树木造型复杂,在画面中占据空间很大,与其说山水分割画面,倒不如说人物在山水中游;其三,水流、丘陵、石矶、林木延绵不断,使得画面形成富有律动的节奏,是赋予画卷完整性的重要线索。由此可见,《洛神赋图》景物造型远远超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以及其他六朝绘画的意义涵指。因此,对于创作的第一个任务,画家的表现游刃有余,似乎并不构成创作的真正难题和挑战。
图 21、22 人与神着地点的比较 |
图 20 人的衣服静态下垂
|
但是,仅仅靠人物塑造还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似乎只有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寻找办法。什么样的环境呢?土石?道路?河流?树木?考虑到画面之内布满如此多的树木,而且造型如此奇特且有规律,我们不能不想到,树木在上述空间表现中一定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
2、树:来自生活体验的空间象征
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树木的秘密似乎可以破解开了。用一句话概括之,《洛神赋图》中的树木是一种源自真实生活体验的图像,画家在作品中转而以之象征某种特定的空间观念和意象。下面试具体阐述之。
其一:点叶树和真实空间
图 29 西方画家笔下的蘑菇树形象 |
其二:蘑菇树的两种含义:“远”和“小”
人为地取用某一种树的形象象征神灵空间是危险的。顾恺之并不采用简单的对立法为洛神设计专门的象征符号,而是试图从真实空间的丰富表现逐渐扩展到神灵世界。为此,一种与“近”和“大”的点叶树相对的另外一种树:蘑菇树出现了。
蘑菇树何以能能象征“远”和“小”?首先,远就会小,小就显得远,二者是统一的。其次,凭我们的生活经验,当树木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时,繁密的枝叶消失了,树的外轮廓显现了,越来越像一个伞或蘑菇的冠状,以至于我们习惯用“树冠”称呼树木整体的印象。图25和27是笔者拍摄的真实树木。可以发现,树冠的形象和树距离观者的远近有关,与树木的种类也有关。但是依照我们经验总的来看,树越小,离观者越远,越容易呈现为蘑菇树的形态。这一规律不是顾恺之的独特发现,其实,西方艺术家画的远树也有这种特点。图29是荷兰17世纪画家MeindertHobema的作品,这些道旁树呈现为清晰的蘑菇状。
另外,处于近处的,然而体积较小的草丛或灌木,从视觉效果上看,它们也类似远处的树丛,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体验到的。顾恺之看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用同样的手法表现近处的本来就小的植物和远处的看上去变的小的树木。可是,这一本来源自真实观察的表现手法,在作品的阅读中常常会发生障碍。人们觉得,同一种蘑菇树在靠画幅较上和较下的两个空间同样出现,似乎画家并没有真实空间的概念,树木的表现和安置一定是随心所欲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前面的分析使我们相信,在顾恺之的作品中,蘑菇树的使用要么是表现一种较远的空间,和较为不真实的空间,它们因而常常伴随在神灵人物左右,要么表现较小的一种植物,它们偶尔出现在画面最下面的某个角落,甚至和世人靠近的地方。并且,这种双重语义的使用有一个好处,使得在真实空间和神灵空间之间有一个过渡和交流,这和画面所追求的宗旨是一致的。
其三:大小蘑菇树的并置:两层含义
有时候,画家会在一个较大的蘑菇树下并置几棵小的蘑菇树(图16)。根据笔者的理解,它就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高的树长在短的草丛或其他小植物中,这种情景在自然中是常见的。第二种是,下面的小蘑菇树是远处的树,这样考虑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极强的空间感。至于采用那种解释,需要看大树和小树树根落点之间的关系,水平并置是前者,而小树树根较高时,则属后者,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经验,也符合视觉透视的原则。
其四:点叶树和蘑菇树的并置:复杂的自然景观
无疑,在真实的自然场景中,远近高低都是同时并存的。既然画家试图用不同的树形和大小表达空间,必然会出现各种树并置的情况。在“洛神赋图”中段敲鼓的仙人背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点叶树、大蘑菇树,小鸡冠树并列在高低起伏的山丘间(图30、31)。中间还偶有红色花叶小树,当为桃树,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曾提到“宜涧中桃傍生石间”,还描写了人与桃的穿插呼应[18]。当我们试图以新的语义观看这种混杂的图像时,就会发现原来这里是一片如此复杂、悠远的自然意境。
其五:树丛的表现
画家似乎并不想真实地表现复杂的浓密树林,他需要的画面应该是六朝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简淡悠远。因此,如何以少胜多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有理由相信,当画家在同一个区域水平并置三棵或三棵以上的同类树木,尤其是小的蘑菇树的时候,那应当是一片树林。“三”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多的含义[19],何况,如果没有这种象征性的考虑,三株以上小树的平行并置似乎并无必要。
3、树与人的组合:在地上还是空中?
《洛神赋图》的主题是人与神之间的邂逅和交流,而人与神的区别,不仅表现于形象不同,并且处于不同的空间中:人必须在真实的地面上行动,而神则不受此限制,可以自由地在空中、水中、云中,在不可琢磨的空间中存在。通过画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顾恺之用了许多办法体现这种差别。比如,如前所述,画家对于世俗人物和神灵两种形象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衣服、着地点、车马、云水等等,用不同的方式区别两种不同的空间。除此之外,树对这两种人物所处的空间表现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分别看一下。
首先看点叶树。点叶树主要被用于表现曹植主仆的真实空间关系。比如第一段中,主仆八人站立在枝叶婆娑的点叶树下,树叶在离开头顶不远的高处飘动,与红色的华盖相呼应,这种真实感有了极生动的表现(图3)。而在这一段中,从回首凝望的女神一直到水中嬉戏的两个女神,中间没有一棵点叶树。直到这一段末尾靠近下一段曹植再度出现,又开始有点叶树,甚至有一位女神与点叶树靠在一起。不过奇怪的是,虽然该点叶树着地点明显在女神之前,但女神的衣服仿佛挡住了树叶,这种在空间上的暧昧和矛盾恰恰说明女神处于极不真实的空间中(图32)。在第二段中,又出现一位敲鼓奏乐的神灵被点叶树挡住,是符合真实的(图33)。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由于鼓的造型十分大而真实,需要一个确定的着地点,另一方面,神灵奏乐表现的是人与神已经获得沟通,这种交流应当在一种真实的空间中展开,亦即神走入了人的世界。于是点叶树可以象征性地表达这种空间关系的微妙转变。
图 33 冯夷鸣鼓与点叶树关系 |
三、《洛神赋图》树的表现根源
前述分析说明,《洛神赋图》中树的表现方式和画家试图传达的原赋中人神有殊的空间意境有关。尽管树的造型受到了画家生活经验的影响,但以形象表达抽象的空间观念和审美情境,足可以象征名之。其实,象征与写实本身并不矛盾,二者兼而有之的状况说明了六朝时期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画家开始从以人物为主逐渐扩张审美的视域,自然界景物开始成为玄览的对象,对人的品评和对自然的品评并行发展,而且相互渗透影响。这一时代审美特征在《洛神赋图》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因此,从六朝审美观念的背景考察《洛神赋图》中树的表现,可使我们对其造型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1,比兴:人的表现的延展
图 34汉画表现生活中的树:附属在山的轮廓内 图 35 汉画人神关系图式 图 36、37 战国人神关系图式 图 38 《洛神赋图》及南北朝绘画中人神关系图式 |
固然,庄学游心于太极坐忘于心斋的追求与山水精神颇多契合,但笔者更倾向于强调六朝对自然的发现与对人自身关注的密切关系。比如,《洛神赋图》的树造型中可以发现,这里的树,与其说来自对自然的静观,倒不如说是对人自身的“比兴”式的描绘。首先,此图中的树造型皆棵棵独立,从来不形成森林密布的形态,这和人们对自然界的真实感受是很不相同的。顾恺之曾记述其游会稽山水后的感受: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22]
可见六朝人对自然风光蒙笼葱郁、云霞掩映之整体性的视觉感受和现代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洛神赋图》绝不把山川树木作为视觉的整体予以表现,其独立孑行,姿态万千的蘑菇树显然不可以单纯用自然形态加以解释,和人的形态反倒颇有神合之处。其二,张彦远称六朝山水“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其中所谓“伸臂布指”是人才有的动作和情态,后人往往把这话视为张彦远的一个比喻,但无论其原意若何,这个词确实十分生动准确地表达出六朝绘画树木表现的真谛:树非树,也许此时的画家就是把树当成人物来描绘的。其三,以人画树的方法还体现画卷中树与人一一对应的关系上。《洛神赋图》中点叶树与曹植等人对应,神灵旁边则以蘑菇树与之呼应。《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树与人物一一对应的关系更明确。在此图中,假如树只是作为画面分割线,那么它就没必要给予如此生动详尽的描写。相反,在摇曳多姿、风流潇洒的枝叶形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在画它们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无他,正是其旁边所依傍的人物。其四,还可以从六朝后期绘画“传神”的观念理解树的表现,“传神”也是促进对树木表现拟人化的原因之一。“传神”及其引申出来的“气韵生动”[23]是六朝绘画最高的审美标准。然而,在六朝人眼里,只有“人”才存在“传神”的问题[24],比如顾恺之所言:“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25]。可见,其传神本来就是在人物画中提出来的。再如,其《论画》起首句: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
这就道出了为什么人难画的原因,这是由“传神”的标准加以评判的。树木,介于人的生命体和无生命的台榭之间,无法以“传神”衡量之。我们可以假想六朝人如果打算把树木画到传神的高度,其可能性的选择似乎只有把树木“拟人化”这一条道路了。
其实,在从魏晋前溯的中国文学中,对自然植物的描写比比皆是,这种描写大多可视为人与自然的“比兴”关系,也就是说,人并非真地对自然发生审美的兴趣,徐复观认为:
“比是以某一自然景物,有意的与自己的境遇、实际是由境遇所引起的感情引发出来……自然对人生所发生的比兴作用,是片段的、偶然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占有很明显的地位,所以也只赋予自然以人格化,很少将自己加以自然化”[26]。
所谓“自然人格化”,不就是用表现人的方式表现自然吗?“比兴”一词虽然来自古文学范畴,但用于解释《洛神赋图》的树造型也是有意义的。其树的造型特征体现了对人的比拟,而由独特醒目的树木形象开始,把人的视觉引向特定的人物中去,亦可理解为“兴”的手法。同时,“比兴”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洛神赋图》乃至南北朝时期其他作品中的树木造型之所以有别于后世山水画、有别于视觉真实形象的原因所在。
2,人神对峙:早期绘画传统的发展
《洛神赋图》两种树的造型及其意义,是由原作“人与神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造就的。如前所述,此主题是画家面临的时空表现中的难题,同时又赋予该作品一个突出的特质。不过,本文不认为这是《洛神赋图》的作者的独创,而认为它延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艺术表现的命题,也就是说,人神对峙是中国早期绘画传统的发展,了解这一发展脉络则有助于理解南北朝绘画中树木的意义和价值。
和六朝相比,汉代艺术对人神关系有更确定的观念,甚至学者认为汉画中存在一个确定的天人宇宙结构图式[27],在《马王堆帛画》、《金雀山帛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上下分层的图式结构(图35)。其特点是,第一,上下并置,层次清晰。由上而下分别为天上世界、仙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四个部分,这是对汉代天人宇宙观念的完整表达。当然,在具体的作品中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层次[28],但上帝、鬼神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人与神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就必然会采用上下对峙的方式以体现其高低层次,并且之间往往有明确的分割线,二者绝少沟通。比如,汉画中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山造型,一种采用鸟瞰式构图,有整齐的山峰,气象生机勃勃,用以表达理想化的真实风景。而另一种山,采用蘑菇型的昆仑山,辅之以与仙道有关的祥瑞图像,用以表达天堂观念[29]。虽然这两种形象也许不在同一个画面中,但在汉人的心目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并峙是十分清楚的。其二,汉画结构体现出来的人神并峙是对完全不同的空间观念的表达:人的空间、处于昆仑山的仙人空间、上帝的空间以及幽都的空间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主体形象遵循不同的生存方式、行为准则,人神之间极难沟通。在汉人看来,只有人在死去的时候才具有进入仙界或冥府的契机,并且需要诸多条件,足可看出人神交流之难。其三,汉画中对于人界与神界的表达,多是以抽象的符号表示的。比如在《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用仙鹤、有金乌的太阳、扶桑、有蟾蜍与玉兔的新月等象征天上世界,这些都是画者想象的形象。
汉代的人神观念来自先秦时代早已有之的上帝、鬼神的观念。尤其在周王朝建立之后,“承袭了商奴隶主祭天祀祖、敬事鬼神和政权神授的宗教迷信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30]”。“国人尊礼尚德,事鬼敬神而远之”[31],对当时人来说,鬼神是必须敬奉而不可及的对象,这其实正是汉画人神关系的最初表达。不过,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王权倾颓,到了战国时代人对鬼神的态度已经有明显改变。如出土于长沙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图36)人站在神力巨大的巨龙背上,以缰牵引,乘风劲驰,二者交锋直率刚烈,不需要其他符号、形象的意义象征或说明,生动体现了当时人“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宇宙观[32]。图37大致表示了此图的人神关系模式,其中的虚线表示人与神之间不像汉画那样截然分离的,而是存在着相互交流,显然,这里的交流乃是人对神的凌驾和控制。在战国的人神关系中,人驾驭了象征神灵的巨龙,这种态度在历史上虽然短暂,且随着秦汉一统而散失,但它与六朝另一种“人神关系”遥相呼应,体现了古人宇宙观念内在变化的线索。
图 38 《洛神赋图》及南北朝绘画中人神关系图式 |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树木在这种转变中的人神关系中的作用。根据本文的分析,《洛神赋图》中的点叶树与蘑菇树的对峙,加强了人与神关系这一主题,而两种树所象征的空间关系的微妙转换也暗示了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和互融。在古人眼里,树总是从属于山水,而山水林泉则与神灵之境相关。《释名·释长幼》曰:“仙,迁也,迁入山也”。可见,汉人把昆仑山视为神仙常驻之所[36],而后来的人则把“人与山林”的关系视为古人升仙求道的隐喻。这样,在《洛神赋图》中被树木覆盖的山峦,就包含了些许仙界的含义,它既是诸神居留的场所,又是曹植以及画者所向往的境界。
结语
六朝后期尤其是南北朝时代,艺术依然注重人物表现,山水画则在初创期,因而与人关系密切的树木得到详尽的表现和利用。相比之下,山的比例小,造型也十分简单。但这种自发的造型样式不能抑制画家对艺术意境和复杂空间表现的愿望。为此,他必须寻求合适的语汇,这种语汇首先要来自对真实自然的观察和体验,其次才能使之转化为具有一定象征意味的图形组织绘画空间。所以,阅读《洛神赋图》必须理解这种语汇,同时又要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解答。
附录:北京故宫本《洛神赋图》全图
(本图由北京大学李松老师拍摄提供)
[1]此类评论散见于当代学者论著中。如李祥林《顾恺之:中国书画名家话语图解》93页:“人物与背景之间比例失调,近景和远景拉不开距离,高山仿佛土丘,大河如同小溪。至于树木,竟只能勾画一个个扇形轮廓,绘画技巧尤其稚拙。中国绘画史上,这种状况在顾恺之时代相当普遍,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后,才真正得到改观。另见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2~6页,承载《历代名画记全译》79页,等等。
[2]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美学散步》209页。
[3]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判史纲》70页,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文中提到:六朝美术创作成就引人注目,“画坛第一批令后人景仰的百代宗师出现于此。人们津津乐道的画坛四祖,此期居三。”“成为当今文化景观并誉满世界的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响堂山、栖霞寺等国内各主要石窟均开创在这一时代”,此时期“仅见于史籍的画家就有一百六十五人之多”。
[4]李若晴《竹林七贤与荣起期画像砖渊源考》36页,见《美术史与观念史IV》,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长虹《中国古代美术史纲》69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林树中《六朝艺术》119页,南京出版社,2004年;等等。
[5]林树中:“所画杨柳与梧桐树……”见《六朝艺术》119页;袁有根:“所画柳树则刷脉镂叶,如伸臂布指”,见袁有根、苏涵、李晓庵《顾恺之研究》100页,民族出版社,2005;周宗亚以柳树讨论此树,见博士论文《故宫藏洛神赋图之图像研究》69页,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
[6] 袁有根、苏涵、李晓庵《顾恺之研究》79页,民族出版社,2005。
[7]在辽宁本中,仅有一次曹植与洛神对晤的一个场面未画点叶树,此场景表现曹植解下玉佩赠给洛神,以表现原赋“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邀之”。此表现方式原因待考。
[8] 清端方撰《壬寅消夏録》3页。
[9]清顾復:“衣褶如篿菜条,树木若薄荷把,水石奇古,设色精研”,《平生壮观》102页;清震钩:“图中树皆作芝而形,舟车皆古制”,《天咫偶闻》卷一102页。
[10]见注6;另见韦正《从考古材料看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年代》,自《艺术史研究》第7辑2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等等。
[11]此六个图在画面中与人物依次间隔出现,起到间隔画面的作用。其中只有一个图间杂有两棵点叶树。其含义在后文将做分析。
[12]韦正《从考古材料看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年代》,自《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袁有根《洛神赋图卷的创作权问题》自《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13]熊伟业《魏晋时期的人神观念与曹植洛神赋的创作动机》,自《电影文学》2007年18期77页。
[14]袁有根、苏涵、李晓庵《顾恺之研究》79页,民族出版社,2005。
[15](英)苏利文:“《洛神赋图》运用了连环画技巧,同一个人物在情节需要的情况下可能会多次出现,这种设计应当是随着佛教从印度的传入而出现的,因为在汉代艺术中几乎看不到连环画的渊源”。《艺术中国》86页。
[16]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自汉以来,中国绘画已趋于线条变化的追求……我以为六朝画风,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常常可以看到印度来的作品,仿着描绘,从中颖悟了晕染的方法,背景的应用。当时造像壁画风起云涌。”转引自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易存国:“佛教思想与中华文化有合拍之处,其图绘于壁的方式与中华艺术若合符契……佛教故事画,其早期依据佛经内容严谨绘制,由于佛经卷帙浩繁,其中有成百累千的故事题材,绘图于壁的故事亦随之丰富多彩”。《敦煌艺术美学》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红叶树:辽宁本本中没有这种树,故宫本中有。此树当为宋人临摹中修改而成。桃树在汉画中就作为一种祥瑞图形常有使用,顾恺之记述中的桃树恐与道教有关。本文称此为桃树,只是猜测而已,聊作一说。
[19]汉代以三峰象征山、群山或仙山的图像可为一证。见巫鸿《礼仪中的美术》2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0]如汉代画像中的常青树、灵芝、柏、桃梗、蓂荚等等植物,均为祥瑞图像。参见周保平等《汉画吉祥图像的图像学解析》自《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341页,2006年;王明丽《南阳汉画像中的祥瑞图像》自《寻根》2008年02期;李晨《论汉画像石祥瑞图像的艺术特征》,自《艺苑》26页2009年第一期,等等。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73-27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
[22] 见《世说新语:言语》。
[23]“传神”与“气韵生动”的互释:“气韵生动”乃是顾恺之的所谓“传神”的更明确的叙述。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1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24]一直到唐代,传神(气韵)只用于评人禽鬼神,从不用于山水;山水景物的传神直到五代荆浩《笔法记》才提出来。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137页。
[25] 见《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
[26]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169页。
[27]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60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28]实际上,汉画内容和结构不拘一格,十分自由,有很多对现实生活或想象中世界的单纯描写。但上下四层分布式结构具有典型性,体现了汉代人神关系的本质特点。
[29]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245页,自《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2005年。
[30] 《中国哲学史》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7月第一版。
[31] 《礼记·表记》
[32]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33]萧统《文选·洛神赋》李善注:“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
[34] 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硕士研究生论文。
[35] 姚义斌《六朝画像砖研究》66页,南京艺术学院2004年博士论文。
[36] (东汉)刘熙《释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