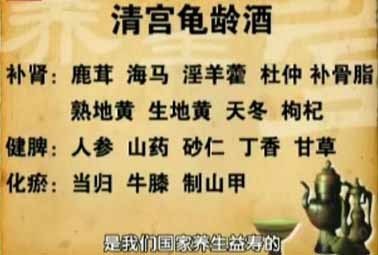一我和莫怀戚是川大中文系82届同学,四载同窗,毕业后又常聚会,对他颇有了解。岁月如水,淘去了无数旧事,但关于他的一些龙门阵,我却没有忘掉。莫怀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以敬业为本,以淡泊自守,注重言传身教。受到这种熏陶,他自幼就喜欢读书学习,期望能以所学贡献社会,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早年当过知青,做过电影院的送片员,也担任过川剧团的伴奏。这些经历似乎都与文学绝缘,实际上却相当有益,因为它们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使他接近和了解复杂的社会。他最初写的不是小说,迷上的是剧本。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小说创作还未复苏,热闹的是电影和戏剧。他来自剧团,总想写几个好剧本出来。就这样,莫怀戚闯进了戏剧领域,每天都去图书馆借好几本有关的杂志来钻研借鉴。中文系的学生都想出成果,他只不过更痴迷。创作欲望像鬼魂一样缠着他,他常常为此熬更守夜,憔悴不堪,后来听说瘦人长寿的居多,他心里才坦然一些。
在那个学年里,只要条件允许,只要一有空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写剧本。
莫怀戚创作的时候,是不欢迎别人上门的。下课回到宿舍,他立即在桌上竖起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自学时间,请勿打扰。”然后,他鸵鸟似的将脑壳藏在文件夹后面,或奋笔疾书,或冥思苦想,绝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大家知道他的秉性,也都不去纠缠他。
他采用的是速记法,写作效率极高,手稿上大片大片均为符号和线条,别人看不懂,就他心中有数。
成圣成狂,往往在于一念之差。莫怀戚搞创作,有那么一股韧劲儿,坚定不移。像吃饭一样,他大约也给自己规定了每日的“定量”,倘若完不成,他便不允许自己上床去休息。
他熬夜就各自熬吧,偏偏又不安分守己,偶尔觅到几句得意的台词,半夜三更也忍不住要放声朗诵,且是高八度。久而久之,他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公愤,同寝室的人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我至少听到两个同学在私下说过:“真想把他龟儿子卡死!”还有同学开玩笑,说要集资雇请杀手将其灭掉。
莫怀戚在学生宿舍成了众矢之的,呆不住,只好独自躲到校园里去念他的台词。有天早上我见他鼻青脸肿的,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他昨晚被巡夜的工宣队师傅当作小偷,他也以为对方是歹徒,双方在黑暗中发生互殴,打得头破血流。
直到元旦节后,莫怀戚才得以“平反”——他的剧本先被系上选中,接着又被推荐到学校礼堂公演,出足了风头。他还被选为文体委员,当了宣传队长,可以任意挑选男女同学为他配戏,可谓扬眉吐气。
不久,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刮起旋风,川大同学自发组织起“锦江文学社”,莫怀戚这才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小说创作。文学的枝叶,在他心田里抽条、竞长,不知付出了多少劳瘁,耗费了多少心血,莫怀戚方才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他在《锦江》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问世之初即获好评,显示出他已度过了最困惑的探索期,开始走向成熟。二
人的快乐与否,性格的重要不亚于命运。
有一年夏天,同学们相约去游新都宝光寺,进了山门,或赏莳花,或观长联,怡然自得。不料经堂那边一阵喧哗,间杂以莫怀戚的争辩声——原来这位老兄又闯了祸。他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在庄严神圣的经堂内拉起了心爱的小提琴,要为菩萨献上一首独奏曲,那些虔诚万分的佛教徒们,其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围着莫怀戚指指点点开批判会。幸亏大学生人多势众,掩护着他突出重围。大家既然接受了莫怀戚,便都愿意与之交朋友,还将他在川医读书的小兄弟莫党生戏称为“莫怀八”,带着一道去玩耍。其实莫怀戚不仅豪爽,亦极细腻,不单敏感,更为坚强。他的幽默带有机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来自清贫,生活节俭,衣着不求时髦,但求经久耐用。遇上宿舍停电,他就用煤油炉照明坚持写作,不过为了省油,他特意用两只大铁夹子夹住其它油芯,只留两束燃烧。那几年,你要是在川大校园里看见一位常年穿运动衫、蓄长发、骑老式28圈加重车的家伙,准保是他老兄。
他的咀嚼肌发达,饭量大,因而能保持充沛的精力,睡眠少。他平日里喜欢小酌两杯,也不在乎菜肴的好坏,有点花生米、豆腐干、猪头肉之类的,他便心满意足。同学间打平伙搞野餐,他担心伙食费超支,总要提醒说:“不要搞得太复杂,主要是吃个气氛就行了。”
那时国民经济尚未全面好转,烟、糖、酒都得凭票供应。故尔每到月初,他就要去打女生的主意,不是满口甜言蜜语,就是装得可怜兮兮,反正要将她们的号票哄到几张才会罢手。
有天深夜,我被连续的敲门声惊醒,一听是邻室那厮的声音,心内便有几分不悦,躺在床上气乎乎地问:“有啥事还不歇着?这么晚了。”
莫怀戚在门外陪着小心说:“杨老弟,我今天光顾着写东西忘了买酒,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二两,明天一定还。”
“我可没有这么多存货。”“这样吧,只借一两。”夜游神赖着不走,并且降低了要求。他见我仍不开门,发起急来,接着又说:“干脆,只借五钱,我抿一口,不然我实在睡不着。”我终于明白,今夜要想清静,除非尽快打发他走,于是很不耐烦起身开门,倾其所有。他接过酒去,眼内放出光来,称我为“大恩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莫怀戚爱喝酒,但善于自制,从未喝醉丢丑或借酒闹事,酒德甚好。唯一的事故,是我们同游百工堰时他喝了点酒,回程骑车带人,将外校一位女生的脚擦出血来,引起一场虚惊。
周期性的,有时他不爱凑热闹,一人骑车外出,抒发独游的雅兴。他越阡陌,步泥径,到城外拉拉琴,去河边摘几枝杨柳,甚至钻进茅草丛睡个午觉,都极有兴味。回到学校,他会大肆吹嘘自己又“逃了学”。
实际上莫怀戚上课极其认真,把学问当作上帝和宗教一样崇拜。每学期他按所开的课程,准备了相同数量的小本本,把老师讲的要点、阐述、引伸、举例全记上,有闻必录。临到考试前,他还要找其他同学核对笔记,生怕有所遗漏。不消说,他每期考试都名列前茅。
对于选修课他也颇为讲究,不选可学可不学的课,不干可有可无的事。戏剧、电影、文艺批评、美学,他是必选的,并且视同正课对待。他中学啃的是俄语,大学还是选这门外语,高了兴嘴里就要冒几句出来,多为卷舌音,极不中听。
他有个长处是不懂绝不装懂,遇上疑问,他一定要举手请老师解答,下课后他还会缠住老师问东问西,非要打听个水落石出。因而他做学问浑厚而又通融,毕业论文没费多少事就获得了通过。
莫怀戚知道珍惜感情,尊重朋友。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偌大世界,真能相知相悦的又有几个?记得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其中包括财院、川音、烹调学校的几位女生,时常外出郊游,相处极好。此情无关风月,却长久铭刻在心。
毕业之际,同学互相题词为念,我给莫怀戚所题的,无非是祝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老兄给我题的是:“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三大学盛宴既罢,莫怀戚又步入社会,先后在两所高等院校任教,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当他踏上讲台的刹那间,他的心便被一种神圣感所占据,知道这里就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愉快地放下了满是书籍的行囊。
他从前在中文系求学,如今在中文系开课,翻开熟悉的教科书,他如鱼得水,应付裕如。他给学生上课,典故讲得巧,例子用得活,大受学生的欢迎,连不少外系的同学也跑来旁听他的课。莫怀戚说:“也许我走出学校就会胡言乱语,但是对学生,我从不说瞎话。我是抱有责任感的。此心昭昭,天日可鉴。”
在莫怀戚看来,教书是培养后人,是发育自身,也是造福社会。有了这样的基调,他就能身处陋室而恬然,面对尘世而不受侵扰。
不过,他虽然成了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住房也解决了,却依然展不开紧皱的眉头。原因很简单:他的文学梦未圆。
老同学之间常来往,大家谈及生活种种,谈及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社会氛围,谈及各自的处境和浮躁,都生出不少感慨。这种对话,大多是涉世者的坎坷经历与曲折的心声,自然也就含有“人生”的味道,细细琢磨,便能品出几分酸涩和辛辣。
感慨系之,莫怀戚不禁文思涌动,又拿起笔来,潜心构筑他的小说。他的特点是坦率,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信奉的是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回到事物本身。”
《都有一片绿茵》发表在《红岩》杂志上,内容是写不正常年代的婚姻,到了正常年代出现了裂痕。
时为80年代初期,离婚远未成为时髦,提出诉讼的男方,照例被说成是“陈世美”,而有关部门从未对这类婚姻的基础作任何定量分析。莫怀戚的作品闯入了这个“禁区”,命运的无情与个体的弱小,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现,每个场景都重重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争论,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大家都肯定,莫怀戚这家伙能写东西。
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好几个短篇,以头条位置刊载于《花溪》等纯文学期刊上。他此期着重写作技巧的实验,对于多种外国流派进行借鉴和模仿,觉得尤其对口味的是海明威和三毛,时常反复揣摩,获益匪浅。
除了给期刊供稿,莫怀戚同时也给报纸投稿,多为千字篇幅的人物速写,主人公或为市民,或为农夫,或为商贩,或为屠户,总之是些平常的市井人物。说来也怪,这些司空见惯的人物,一入莫怀戚笔下,就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们的朴实憨厚、狡黠固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相当可爱,令人忍俊不禁。《重庆晚报》为他特辟“市井”专栏,足见器重。
莫怀戚说:“我是喜欢跟老百姓打堆的。”在乡村集镇,在茶馆酒楼,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那爽朗的声音。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四面伸出触角,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为人不拘小节,热情大方,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很容易与朋友打成一片,大家也乐于同他交谈。有些人不清楚他的姓名,混熟了就给他取了一大堆绰号,诸如“络耳胡”、“运动员”、“体育老师”、“骑自行车的那个人”。其中最别出心裁的,莫过于称他为“开糊”,原因是他但凡去哪家冷清的小酒馆一坐,从此那家小店的生意就会红火,相当于打麻将开了糊。
四民众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民众关切的热点,在他的作品中会得到迅速的反映。他有敏锐的正义感,时刻把握着不站出来就会后悔终身的时机,嫉恶如仇。他的不少千字短文,针砭时弊,嘻笑怒骂,读者看了都抚掌称快。
有人因此评论说,莫怀戚的文章幽默调侃,堪称道地正宗川菜。
知子莫如母。莫怀戚的母亲笑着说:“认真论起来,他爸爸还算得上有点幽默,至于他嘛,顶多有点滑稽罢了。”
的确,幽默并不是莫怀戚的刻意追求,他探索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学。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尚未形成特色,故尔瞪大眼睛,寻找新的坐标。
莫怀戚是老大,二弟在西南政法学院做教研室主任,拥有的诉讼、刑侦等案例不少。莫怀戚本来对这些题材不感兴趣,哪知有次兄弟聚会,他无意中翻了几篇来看,竟一下子心血来潮,好似打开了一座宝藏。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莫怀戚捧着大批素材闭门不出,过上了集中营式的封闭生活。他从社会上销声匿迹,文学圈里也不见他的踪影,不少朋友都怀疑他患上了难愈的“乙肝”,大约正在养病。谁知他已经“疯”了:胡须忘了刮,衣衫忘了换,没日没夜地炮制着他称之为“心理推理”的系列小说。
“大律师系列”就这样问世了。
1987年,当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作品在《芙蓉》杂志问世时,莫怀戚实际上开拓了一个只属于他的领域。截止目前,“大律师系列”已出十多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单行本《大律师现实录》。
莫怀戚的创作进入了收获期,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中篇小说35部,另有若干短篇,声誉鹊起。面对纷至沓来的约稿信,面对拥压而来的辉煌,他照样保持着头脑的警醒与得体的自谦。他不能忘乎所以,还有许多题材没有发掘出来。
笔锋一转,他又回头写婚姻、恋爱、家庭,也写婚变、偷情、性爱。他说:“我甚至想有意挑起关于‘性’的争论,因为我们过去很少对这个问题认真探讨过。”
莫怀戚认为,“理解万岁”并未把话说到家,倒是有人提出的“换位思考”还比较科学,说不定真能增进理解,促进宽容,从而成为新道德、新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楔入点。他还认为,在两性问题上的虚伪是最不可取的,所以才会出现数不清的“围城”。或许,隐私中的一切,才是最深刻、最真实和最美丽的人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发表于《分忧》杂志上的《寻找两全之计》、《浴盆里的睡美人》,以及刊登于《新女性》杂志上的《结构:婚姻之道》等。
他的这类作品,通常不搞注入式的灌输,而是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娓娓道来,与读者一道探讨,以求沟通。
道德人伦包罗万象,难怪这位剽悍孔武的男作家,会拥有众多的女读者。茫茫人海,一叶扁舟,欲觅知音中意的人生伴侣竟万般艰难,结果不结婚后悔一辈子,结了婚又后悔半辈子,因此她们都想听莫怀戚指点迷津。莫怀戚说:“此举并非哗众取宠。我不过是以‘过来人’的体验,以旁观者的立场,多少触及这一敏感题材,至于文学圈内的人说什么,我是不在乎的。”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自己的作品,莫怀戚誓死反对故作深沉之状,行文力求深入浅出。他干脆把魔幻主义束之高阁,将后现代、新写实打入冷宫,尽可能采用来自民间的语言,读者能接受就行。五
磨练他意志的是十年浩劫和上山下乡,引导他前进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在莫怀戚任教的高校里,聘有不少外籍教师,通过频繁的交往,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世界的多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