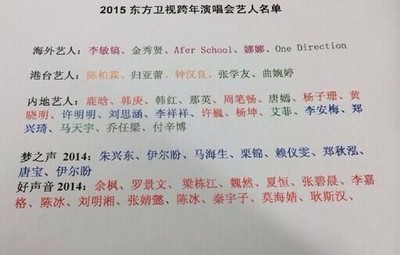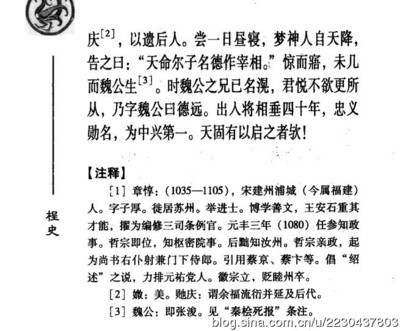摘自:新浪读书频道 连载《真情见证》
《真情见证》一书源自山东电视台金牌栏目《数风流人物》一线记者近距离亲访近百位领袖人物及开国将帅家人的实录。
本书从“亲情家事”这一角度切入,着力展示领袖、将帅生活中普通人的一面,通过描写他们的亲情、友情、儿女情、夫妻情等寻常人所共有的情怀,反映领袖的人格魅力,表现他们的高尚情操和动人情怀。
《我们的“布头”爸爸》一文选自该书第二辑。采访时间2002年1月,采访地点北京,采访对象:董良羽(时年64岁)董必武的长子,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助理;董良翚(时年61岁)董必武的长女,原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董良翮(时年57岁)董必武的次子,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采访记者赵曦。
我们的“布头”爸爸
——山东电视台采访董必武的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清朝的“拔贡”、同盟会会员、共产党的创始人
“那时候我父亲仗着自己年轻无知无畏,在衙门口探了探头,结果让人拉进去打了板子。按理说这在别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触动很大,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这思想在他一生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董良羽
董良羽
记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您的父亲——董必武。在那个时代里,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人生道路,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此后几十年急风暴雨中,当战友和同道者纷纷倒下或落伍后,董老作为硕果犹存者站到新中国最高代表的位置上,又格外令人敬慕。好多书上都有记载,董老在国共两党中的威信都非常高,身份比较特殊,经历十分曲折,是何种原因使董老选择了这样的道路?
董良羽: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不像后来有些同志参加革命,许多是因为家里没饭吃,日子过不下去,从事实上讲是官逼民反的原因。
我父亲原来家里也不富,但还不是吃不上饭的那一种。我的爷爷和四叔都是秀才,还开了个小杂货铺,生活不是多富裕,但还是过得下去的。我父亲读过秀才,后来考入张之洞的“文普通”学堂。在学堂里他的学习比较好,在学校连续几年都考第一。所以最后给他一个“拔贡”,可能就离举人不远了。有了这个资格大概就可以弄个县官做一做了。
但是他看到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就想改造这个社会,所以就接受梁启超的一种比较进步的思想,后来又追随孙中山的思想。到最后他觉得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于是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突出的自觉的革命者。他一直是对现实不太满意的一个人。
记者:我们知道中央曾编一本《董必武年谱》,您从1966年抽调出来帮他们搜集素材。为此到各地搜集了许多有关您父亲的材料,通过这一段,您对父亲的了解应该很深的。既然董老在当时有一定的头衔和地位,应该说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受益者了,那他为什么还对现实不满并要带头去反对呢?有没有具体的事件或诱因呢?
董良羽:他之所以追求马列,是受了几件事情的影响。一个是当年他去黄州考秀才的时候,从府台衙门门口经过,那时候我父亲仗着自己年轻无知无畏,在衙门口探了探头,结果让人拉进去打了板子。按理说这在别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触动很大,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这思想在他一生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另外一件事是,他的家乡附近有一个叫“宋埠”的地方,那里发生过一次“教案”。就是洋人传教士欺负老百姓,百姓们就闹起来了,但遭到官府的镇压。所以他对政府的信心就完全没有了。从那以后,作为一个热血的年轻人,他就在考虑如何消除这些腐败,富强国家,并一直在探索。
当时有一个知识分子叫刘晋安,后来在狱中牺牲了。他和父亲合作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读书会”性质的。读了很多进步的书,接受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包括“康梁变法”的一些理论。后来他又接触孙中山的理论。他也加入过当时叫“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那时恰逢孙中山最不如意的时候,到日本去了。父亲出于救国救民的思想,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经过几次国内革命战争,父亲发现孙中山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再往后,他从日本的同学那里初步接触了马列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坚信马列主义,逐步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实践的历程。
记者:1921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是来自7个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共有12人,您父亲当时是作为湖北小组代表出席的,他是不是其中年纪比较大的人,那时他有多大年纪了?
董良羽:一大召开是1921年,那时父亲是35岁,在代表中算年纪比较大的,还有何叔衡比较大,我父亲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主席那时候年轻,只有28岁。
记者:1934年长征开始时,董老以近50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当时他只是分管30个女红军战士。我想一个共产党的创建者,在长征路上居然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他平时也总喜欢把自己称为“布头”“龙套”。他为什么将自己如此定位呢?
董良羽:“布头”这个我说不清楚。不过这几个说法反映了他的一个概念:作为一个革命者,我这一辈子就交给革命了。革命需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也不去争什么。不记名,不记利,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去做好。
他从不把工作分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他可以是党校校长,也可以是一个家属连的连长。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资本可以调换工作,党交给他的他就做好,再小也一样。他在家属连的时候分房子,他带头要最差的房子。后来毛主席把他调走了,他也每天照常地工作。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的。他有很强的事业心和组织观念,这话到他临终前还给我们讲。他在去世前和我们讲:“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龙套’?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
记者:他去世前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
董良羽:他已经在床上躺着了,很难表述。他还和我们讲:“生活上要向低调看齐,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困难时期大家都没得吃,物资供应很差。当时我在学校,生活也比较差。我当时在哈军工。宋庆龄副主席送给他一只酱鸭,他没舍得吃,就托人给我送来。后来他十分后悔,他觉得别人吃不饱,我在那里吃酱鸭,影响不好,为此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也反映了他对我们的关心。后来母亲给我们讲这件事情。他觉得生活不好,大家都吃不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有这种待遇?其实平时他也吃不上,宋主席送给他,他没舍得吃就是了。
记者:我们知道1975年董老90岁生日时,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90年光阴。在这首诗中他怎样评价自己90年的光阴?
董良羽:那是 1975年3月5日,我父亲过90岁生日,他自己写了一首诗,叫《九十初度》,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总结吧。写完之后,把全家人找到一块,给大家讲。那时距他去世有个把月的时间,当时他病得躺在床上。诗是自己写的,但是其中有两个字改过,那不是他自己改的,他说,秘书帮着改的。铅笔写的,铅笔改的。字迹已经有点抖了。那时他身体已经很差,还是给大家讲了一遍。
诗的前半部是这样的:“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如果这首诗仔细地去分析的话,那实际上是他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他的有些诗句反映他的一些想法。比方说,他是主张法制的人,诗里有一句“一代新规要渐磨”,“规”就是规矩、规则。再推广一下,国家的规矩就是法律。他认为这需要逐渐去磨炼、去建设。另外像最后他说“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伐柯是一个典故。“伐”是北伐的伐,“柯”是木,就是砍下来的枝条。伐柯就是砍树枝。古文上有一句话,“直可以伐柯,齐则不远”。就是拿着一条砍下来的枝条做标准再去砍别的枝条,那就差不多可以很相似了。最后两句诗充分反映了他的马列主义信仰。
记者:您还保存着他以前的那些诗吗?
董良羽:还有一些,他的信我基本上都保存着。
父子情深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明知道生了个男孩,还要买条裙子,一件粉红色的小裙子……
每次吃完饭之后,他往躺椅上一躺,我骑在他肚子上,有一套固定动作,他不是有胡子吗,左三下,右三下,然后脑门对脑门顶几下,最后亲一下,走人了……”——董良羽
记者:据我们了解,像您这样的家庭,由于所处的非常的战争时代,由于父亲所处的非同寻常位置,一般比较缺少和平年代普通家庭那样的天伦之乐和亲密相处,能跟我们说说您和您父亲之间的感情,说说您的家庭吗?
董良羽:我1957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那年我19岁,从此离开家。在此之前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上学我都是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礼拜天回学校。寒暑假在家,从小就住校。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和一般家庭的规律是一样的,老大,父辈肯定是爱,也真爱,但肯定要求比一般人严格得多。所以前次采访我也是这样讲。我觉得和我父亲谈亲情,我觉得就……反正他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敬畏的感觉,那种亲情的感觉,相对不怎么强烈。我父亲他这人太正经,平时很少开玩笑,一贯是很正面的教育。
记者:您父亲有您的时候已经52岁了,可以说是晚年得子,我们很想知道董老是怎样表达他当时的高兴心情的?
董良羽:我出生在延安,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他当时在国统区,得知这个消息他应该是很高兴。当时解放区的经济条件不好,就给我买了点东西,其中有一件就是粉红色的小裙子。那裙子什么样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后来老太太当笑话说给我们听,说父亲明知道生了个男孩,还要买个裙子,她的意思是说,我父亲不会买东西,是个儿子买个女孩子的衣服,看来真是高兴坏了,哈哈哈……
记者:作为父亲,董老肯定很想念出生而不得见面的长子,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大概在您出生后两三年董老才见到您,我想这次父子见面一定留给您很深的印象。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父亲的具体场景吗?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熟悉起来的?
董良羽: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几岁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在延安。延安生活比较困难,家里连凳子都没有,因为他要回来,就临时到邻居家借了长条凳,当时我就在炕上偎着。他拉我,我就死靠着墙角,很陌生的感觉。那次我很不高兴,因为见到一个陌生人来我们家。父亲估计也不好受。情况是这样子,我坐在土炕上,缩在角上对着墙,不理他,因为我不认识他,觉得这个人很陌生!
抗战后国共开始合作,我父亲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所以后来我就到重庆去了。我先去的,后来我妈妈和我妹妹也去了。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在重庆办事处的时候,我是和父亲单独生活在一起的。我这辈子有几次是和父亲单独在一起,大概第一次就是重庆那次。我当时是跟代表团一个叫张小梅的同志,就是徐冰的夫人,她把我带去的。那时我妈妈、妹妹还在延安。我和父亲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最亲密的时候。每次吃完饭之后,他往躺椅上一躺,我骑在他肚子上,有一套固定动作,他不是有胡子吗,左三下,右三下,然后脑门对脑门顶几下,最后亲一下,走人了。他很高兴,有时候我不去他还把我叫过去。好像成了一种惯例,这就是印象比较深的。父子之间最亲近的好像就是这些,其他时间他向我们流露感情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作为长子,在家里他对我的期望和要求是比较高的。我想我弟弟比我那个时候就要好多了。对他们也严格,但不像对我那么严格。战争年代,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全地待着按部就班地上学,只能跟着他们到处迁移。上学就是零零星星,很多知识就是我在他亲自教导下学习的。比方说做人的道理,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也在用的“锄禾日当午”这首诗,从小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比方说家里怎么吃饭,吃豆腐乳都要一根筷子蘸着,不能两根筷子一起夹,要节俭。
董必武、何莲芝与长子董良羽
较早提出“依法治国”的观点
“有一年他到兰州去,发现了一个案子:有几个老百姓给判了死刑。父亲听了之后,认为判得不对。我父亲说,把干部打了就判死刑,这在法律上说不过去。”——董良羽
记者:我们知道董老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大学读法律,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当时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1932年在江西苏区也担任过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建国初董老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到了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他又以68岁的高龄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是不是一生都很注重法制建设?
董良羽:他原来是学法的,他曾经留学日本学过法。因此他一生都主张立法。后来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那时候他立了很多法,不过是比较简单的,后来我整理材料时看到,出入境的金银有多少啦,关于利税呀……都有相关法律出台。
解放后他主管政法委员会,法制是他的一贯思想。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想法在当时没实现,但他的一些观点从历史的进程看,是比较正确的。“依法治国”是他早就提出的,而且一直身体力行。
他在法院期间处理的案子比较多。有一年他到兰州去,听他们汇报工作,发现了一个案子:甘肃省那一年闹旱灾,老百姓有迷信的观念,就去求雨,拜龙王。村干部去阻止,大概方法上生硬了一些,把老百姓弄急了,就把干部给打了。因为这件事情,有几个老百姓给判了死刑。父亲听了之后,认为判得不对。迷信固然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固有的。但要说是反革命,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父亲说,把干部打了就判死刑,这在法律上说不过去。
他就调查这个案子,然后督促他们重新审评。后来很多人都放了。当时的法制不是很健全,不像现在,有具体法律可依。
记者:我国建国初期法制尚不健全。在现在看来,董老的“依法治国”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眼光的。他有没有在一些时候向您透露这方面思想?
董良羽:他当时搞刑法,组织了大批人下去调查案例,总结经验,为具体的立法做准备。但后来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这工作没有搞下去。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彭真同志才把它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果当初我们的法制健全一点,我想就不会出现“反右”“文革”等一些情况,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严格的教育简朴的晚年
“他觉得自己退下来就可以给国家省下很多。所以他给中央打了几次报告,要求退下来,结果中央没有批……”——董良羽
记者:我们知道,董老在上世纪70年代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职位相当高,但他始终都很低调,生活也相当地简朴,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家当时的情况?
董良羽:那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退下来之后,他担任副委员长、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下来之后,主席的位子一直空着,就把他定为“代主席”,一直到他去世。那时他写了三次辞呈要求退下来。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占着这样一个位置,不能给国家做更多工作,国家还会有很多的开销,什么汽车,警卫,公务员啦……他觉得自己退下来就可以给国家省下很多。所以他给中央打了几次报告,要求退下来,结果中央没有批。后来他要求把秘书减掉,后来就把警卫、秘书换成了一个人。他还要求不用专车,但上头没同意,他还是轻易不用车。
有时候他让我把文件从办公室送到秘书那里去,几步远,他就对我说,你不许看,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曾经有很长时间,我们家有个小锅炉,一个礼拜烧一次水,一家人可以洗洗澡。我父母都是用一盆水,就是为了节约用水,就是有条件让他去多消费一点,他都觉得是奢侈、浪费,他不会去做的。
包括我们家,他最后住的房子,那窗子都是木头框,年头长了都翘了、裂了,冬天灌风。单位说修一下,他说,那你们先做个计划。当时机关报了个方案说大概需要三万多块钱。1973、1974年三万块钱太多,他一看,就先不搞了,说太多了。后来用折中的方法搞的。如果裂缝太大了,就用粘条把缝堵住。
记者:我看过一张照片,董老抱着您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幸福的场景特别感染人,都说“隔代亲”,董老晚年是什么状态?在走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董老是不是像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样喜欢子孙绕膝,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
董良羽:晚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他对孙子们疼得不得了,一会不见就想。因为工作时间不多,我的两个孩子基本上是跟着爷爷奶奶。有了好东西他自己舍不得吃,都给孙子吃。
我儿子的名字也是他给起的。我儿子生在1972年,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他用时间、地点来做名字,一个壬广,一个子州,这是小名。他们这一辈是“绍”字辈,他们大名一个“绍壬”,一个“绍子”。
记者:在董老严格的教育下,你们家的孩子也都非常简朴、平实。据说您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很高的职位,也没有像样的住房,是吗?
董良羽:对,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的家就安在我父亲那里,上下班都来回跑。当时机关住房确实比较紧张,很多人都没在机关拿到房子,开始没房子,后来再想找就很难了,直到我55岁退休了,师职干了9年,我还没有一个安置房。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按照我父亲这个级别、这个影响,没有房子住是不可能的,而且职务上也应该往上提一提。有的同志提醒过我,他说:“老董啊,你这么窝着可不行,得找找人。”可我到了离休的那一天,也没找过人,也不想找人。我十几年一直在空军,开始学导弹技术,后来一直在部队从事作战工作,十几年吧,一直在指挥所工作。一般值班比较多,我们三个人,一个礼拜得两天多班。一个班就得24小时。所以值完班后我哪都不去,一般是食堂宿舍办公室,三点一线。老老实实干活,不求官,不求利,也不求人。
父母相差25岁的爱情
“父亲比母亲大整整25岁,这种恰似两代人的婚姻格局,总会有人提出很多疑问……忽然发现母亲已不在我身边,我回头一看,意外地发现父亲正在亲吻妈妈的脸颊,妈妈微笑着,一切那么自然那么温馨……”——董良翚
董良翚
记者:我们知道您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他们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走过了几十年,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家庭吗?
董良翚:我母亲大约是在25岁时嫁给我父亲的,我母亲也是一个革命者,她参加长征走过来的,长征路上也是带兵打仗的人,中指打掉一截。她长征路上有一个外号,叫“鸡公”。北方话就是公鸡的意思,就是挺能折腾的人,挺能干。后来上党校,当时李坚贞他们几位老同志做的媒。在此之前,我父亲曾有过一次封建婚姻,并有过一个孩子,是个哥哥,如果现在不死也该是###十岁的人了,也是病故的,我没见过。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父亲已经快50岁了,党内已经有很多同志叫他董老了,父亲比母亲大整整25岁,这种恰似两代人的婚姻格局,总会有人提出很多疑问,我也曾经怀疑父母的婚姻生活是否和谐、美满。可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的种种质疑逐渐消解,我的结论是,父亲、母亲是相爱的,他们的爱情深厚而坚固。
父亲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那段时间,有两位油画家先后各画了一幅父亲的半身像,两幅画都放在了父母的卧室。一天我和妈妈正比较着哪个更像父亲,当我还沉浸在画像的享受中,忽然发现母亲已不在我身边,我回头一看,意外地发现父亲正在亲吻妈妈的脸颊,妈妈微笑着,一切那么自然那么温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母间这种温情的画面。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毯上铺开被单棉絮,准备做被褥入冬。我在一旁帮助妈妈。那是一床大红底散着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扯,这时,父亲走了进来,我问父亲被面好不好看,父亲回答:“妈妈说好看就好看。”我忍不住打趣:“爸爸,这是妈妈特意为你们俩做的。”父亲很纳闷,我说这是为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做的。父亲哈哈地笑了。
学识渊博的父亲
“我父亲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并且在国外留学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也很深……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我父亲接触,才知道共产党里竟然有这样有学识的人……”——董良翚
记者:在您所写的《我的爸爸董必武》中,有这么一句话:“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我却只看到了花和草。”董老学识渊博是人所共知的,从你们这些孩子的名字里就可见一斑,在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羽”字,这肯定有特别的含义吧?
董良翚:对,这些名字里寄托了父亲的一个梦想。早年,父亲就一直梦想着中国可以自己造飞机上天。生我哥哥的时候,是1938年。那时候非常穷,工业非常落后。我父亲希望我们能造飞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富强了,所以就给哥哥起名“良羽”。等我出生后他又在羽毛的颜色上做文章,我是“良翚”。我弟弟1945年出生,也有个“羽”字。所以我们几个的名字分别就是董良羽(老大)、董良翚(音“huī”,老二)、董良翮(音“hé”,老三)。
我父亲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并且在国外留学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也很深。从抗战开始后,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他以他的学识和风采感动过各界人士。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当时经过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国民党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5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给共产党,我父亲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我父亲接触,才知道共产党里竟然有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了美国后,我父亲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他又用毛笔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父亲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他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记者:董老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据说18岁应试中秀才时就写得一手好诗,有人统计,董老一生留下的诗作达1000余首,很多诗词,应该也给您欣赏过。
董良翚: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休学一年。他工作很忙,年纪大了,又得了肺炎,在家里修养。有天晚上他写了一首诗,就喊:“褚青,进来,我给你念诗。”
那时候说实话,我还不能完全体会他的诗,看看而已。真正理解他的诗也是到后来,通过整理生平资料,从诗中体会到一些他的思想,你要是把他的诗从头到尾连续看下来,也能看出他的情绪。我觉得他写的诗是有规律的,有那么几个专题,一个是每年过年、过生日,他自己要写那么一首诗,在诗里,他总是释怀自己的一些想法,学习呀,很多自勉的话,自己要求自己的话?熏像是“暮来没有颓废惑,毛选诗篇读尚新”;另外我们每年过生日,不管谁他都做一首诗,也是鼓励学习、工作什么的;再有学习英雄模范人物,像雷锋、王杰、欧阳海等都有诗,而且你从他的诗上感觉,他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觉得应该向他们学习,确实对他们是很敬佩的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领导者,发出号召性的话。
两进两出中南海
“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翚,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还是外面的空气自由啊!’”——董良翚
记者:听说你们家曾经搬进又搬出中南海,为什么会这样?
董良翚:对,1953年前后,我们家住在钟鼓楼后一个有很大很漂亮后花园的院子里,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传说这个院子曾是个王府。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葡萄、海棠、枣,冬天银装素裹,别有一番情趣。但是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为什么要搬呢?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那么远来为我送文件;第二,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车,这样需要花费很多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要搬到中南海,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还不应该吗?”父亲解释说。不久,我们家就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
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熏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在“文革”中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当时,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翚,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还是外面的空气自由啊!”我能体会到他当时说这番话的心情。
记者:在对待子女恋爱婚姻问题上,往往能显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处世方法甚至等级观念。据说您的婚姻当时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董老是什么态度?
董良翚:在我的婚姻方面,只有我父亲没有干涉。当时我的婚姻双方家长都不看好,因为我比我先生大两岁。我们的认识很有意思,当时我们俩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预科班的新生,新生报到点名时,指导员按照名单挨个念,他的名字叫张力理,因为没有看见那几个字的具体写法,单从发音上,特别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念到这个名字时,站起来的竟是一个男孩,我们女生顿时哄堂大笑,我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那个眉清目秀的大眼睛男孩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因为我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学生,所以共同的话题较多。每次寒暑假回京、返校,我们都相约一起,为的是互相有个照应。
真正开始彼此有感觉应该是在我弃理从文,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以后,他的专业也从西安校址改到了重庆,我们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没有了天天见面,才有了日夜想念。我比我先生大,最初我是把他当成弟弟来呵护、照顾,时间长了,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已经不那么单纯。
可是我们的婚姻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他母亲认为我年纪大些,个性也强,害怕自己儿子将来吃亏。我妈妈也同样认为妻子比丈夫大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倒是父亲开明,他用婚姻、恋爱自由的理论最终说服了妈妈。我婆婆后来也勉强同意我们结合。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我和先生有过口角之争,但不多。话说回来,我年龄比他大,我不让他,谁让他?所以,在恋爱婚姻方面,父亲讲得很少,基本不干涉,好像没怎么谈过你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他对我讲的就是首先身体要好,再就是志同道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长久地在一起。
记者:您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应该好好整理。这些财富既是属于我的,又不属于我。”在人生经历中,每个人都遇到一些重要的选择,董老的观念在您的人生选择上起到了什么影响?
董良翚:我父亲经常要求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觉得只要你老老实实做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学什么他们都不反对。很多人都认为我后来改学中文是父亲的意思,其实是我自己的选择。后来我到了外文局管辖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从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成长为这个社的主要领导。因为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我终于感觉出了枯燥。于是,有朋友穿针引线,1991年,我调到了中国文联。这一干又是12个年头。
我父亲这个人不管是在处世还是做人上,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普通的位置,这个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比如说有一个领导对我和我爱人讲:“你们有事情来找我。”他是想帮助我们。但我们觉得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我快退休了,有人就跟我讲你要是找什么渠道,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应该说,我有今天,没有找过人,没有谁对我特别关照。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用这样的观念来教育他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但是我想让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要在社会上奋斗,没人会因为你们的外公是董必武而给你们什么照顾。自己靠自己,这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还有就是我对名利是很淡泊的。虽然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跟我们讲过他自己,他从不向我们炫耀自己的辉煌经历。
从监狱到农村到商海
“到了北京站以后,车停了,结果上来一些戴红领章、帽徽的战士,还有个干部。他问,你叫董良翮吗?我说是,就被他铐起来了。一下我就蒙了……后来喂猪、种地、挣工分,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第一年年终结算我们结余7毛钱。目前就我的经商经历来讲,没有搞过欺诈,也没有违规操作过,这是最基本的。”——董良翮
董良翮
记者:一般一个家庭中老小总是最受宠最有特权的,而您在你们家里最小,诞生在解放前夕,几乎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但很多人却认为您的经历最坎坷,在“文革”中曾两度入狱,这是为什么?
董良翮:其实在我家里,我确实是最受宠的。哥哥、姐姐都没有我特权大,他们是不能到办公室的,我可以进。父亲的那个抽屉,我也是可以乱翻的。有的时候,我在办公室的地毯上睡着了。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我是父母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造成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大,从而借此来影响、威胁我父亲。按理,我的80岁高龄的父亲已经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欲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他们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于是他们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们刚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六中,在我们学校是个头头,后来在西纠,也就是西城区纠察队又是个头头。我们是炮轰团中央的第一支队伍,后来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我就到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周总理还接见了我说,你搞得不错啊。那时候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热情激进,不甘人后。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要我“投案自首、交代问题”,当时关起来的有二三百人,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学校的头儿,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最后说我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是主席把我们放出来的。那时候听说北大有个彭小蒙,他通过汪东兴的儿子写了份血书,就说我们这些人,意思就是都是很单纯的啊,搞革命的,走了一些弯路,或者犯了一些错误,应该给个机会什么的,主席一声令下把我们都放了,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当时有总理,接着是江青,然后“文革”领导小组里面还有戚本禹、姚文元什么都在台上。我记得总理站起来,第一个问良翮在不在,我一下站起来了,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以后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说得我当时就哭起来了。这次被关了回到家,我去见父亲,我觉得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而且我觉得我父亲也应该相信我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他认为我不会有什么事。最后他说,我是为他坐的牢。而且他后来也曾感叹“无缘无故地抓人,就像给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
第二次入狱是在我第一次被放回来以后,当时我就成了所谓的逍遥派,几乎不参加任何“文化大革命”的聚会,听到这样的事我都要躲得远远的,基本在家里。1968年3月5日是父亲的生日,妈妈想使父亲的生日过得热闹一点,我们便一起赶到广州。
当时有个副司令在广州,他也是我父亲以前很早认识的,此前我曾跟他提出来要当兵,他说没问题,说你来吧,到广州来参军。结果那次过生日时去广州就变调了,说我不能参军,因为眼睛不好,就是近视呀。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到了3月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我入伍,因此我要回北京收拾行李,要料理料理家务。到了北京站以后,车停了,结果上来一些戴红领章、帽徽的战士,还有个干部。他问,你叫董良翮吗?我说是,就被他铐起来了。一下我就蒙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就突然铐我,稀里糊涂就那样,我就被弄走了。据我家里人讲,后来接到了黄永胜的电话,就说你儿子被抓起来了,就这么一个经过。
这一次又被关了半年,出来后,我去见父亲,我父亲严峻地问我:“究竟为什么抓你呢?”我反问他:“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很奇怪,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当时泪水就流下来了。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去问你的爸爸。”“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当年的那段遭遇正是我们特殊的家庭背景使然。在中###内,我父亲无疑地位比较显赫,而正是这个位置,使得他本人以及我们整个家庭都成为某些篡权者的针对目标。
记者:很少有人在较短的时间里能经历从谷底到巅峰的起起落落,我觉得您的经历就很具有这种类似传奇的色彩。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几年,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一时间,您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大起大伏给您什么样的感觉?
董良翮:这应该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吧。现在回忆起来,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就应该像我父亲那样,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波澜不惊,从从容容。
其实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从监狱出来,一直安安稳稳在家里待着。这时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再次宣传开了。父亲和母亲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我到农村去。我想他们之所以这样决定,除了响应号召,也考虑到我两次原因不明的被囚,认为与其留在城市提心吊胆地工作,还不如到农村踏踏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增加些物质财富;而且,他也相信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不仅可以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让组织重新了解、认识我。就这样我最后决定去河北晋县务农,和我的未婚妻一起去。其实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我是和我爱人一起去的。
当时父亲告诉我,农村没有恋爱关系,要不你们就不要一起去,要不你们就下去结婚,这样农民比较容易接受你们。就这样,我们就赶紧结了婚,结了婚一起下乡去。当时结婚的手续非常复杂,我对我父亲最佩服的是,他那么大的岁数,却没有多少封建思想,他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要开化一些。因为当时我们是老高三毕业,到1969年下乡时,我才24岁。中学办结婚手续以前没办过,我几次到学校去,学校才同意出证明,结了婚以后下了乡。
在我下乡的前几天准备行李的时候,父亲和我长谈了几次。当时主席也说,要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要安心地务农。父亲没有讲今后在农村怎么办,也没有讲是不是镀金,就是要求我安心地到农村去工作,并没有为以后做什么铺垫。他一再和我们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于是我就到了河北晋县周头公社当了普通农民,和这里的普通农民一样,下大田,很苦,好在我肯吃苦,农活开始肯定不太会,都要现学。后来喂猪、种地、挣工分,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第一年年终结算我们结余7毛钱。
我在农村待了大概10年,3年在大队,公社3年,县里3年。
中间很少有时间回北京,父亲从来没有要求我回来。
《人民日报》当时宣传我,主要有两个原因。按我当时的家庭背景、我父亲的资历,这件事情即使放到今天来讲,也是一个热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下乡一年多之后,县里和周边的农民才知道我是董必武的儿子,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
记者:您离开农村以后又开始经商,那时候您父亲已经去世了,这期间您认为以前的那段经历对您有帮助吗?设想一下,假设您父亲知道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您认为他会怎么看?
董良翮:嗯……我从河北后来调到农机部中国农机化服务系统公司,然后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从康华到海南,我在大康华过了一下水,没有在总部待,就等于办了个个人手续。
我觉得经商是对人的品格的一个考验。农民无非就是踏踏实实地种完地就完了。可以说到目前就我的经商经历来讲,没有搞过欺诈,也没有违规操作过,这是最基本的。
至于假设我父亲知道我经商是支持还是干涉,我想他不会反对的。因为从小他就很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我父亲很讲原则,但是不呆板。就是在某些社会问题上,他也很超前。对于我经商他也未必不能理解。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觉得很难想象。在我父亲这个职位上,他不会对社会形成阻力,会支持社会进步。比如说在经济上,他没有管经济工作。他就讲,中国的工业应该搞托拉斯。这和现代工业用的不是一个词,但是概念是一样的。他说你要想生产一个好的机器,要从矿石的品质、冶炼、加工都要固定下来。这样品质才会好。你很难想象用鞍钢的钢做了一件东西,第二年再用武钢的钢做,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叫钢,但是内在的品质不一样。质量上来讲也不会稳定。所以像这些思想,我看放到今天也不落伍。
所以从他一生来讲,他都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从来没有说在一些事情上代表一些顽固的旧思想,维持一些旧的观念。
作为一位革命前辈和开国元勋,董老是伟大的;而董老又是平凡的,那是因为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家庭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从董老的三个儿女的话语中,我们更加感受到了董老对家庭绵绵的深情。这种感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人间无上的。
平凡中流露着伟大,严肃的面孔下掩盖着一颗慈祥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布头”爸爸——董必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