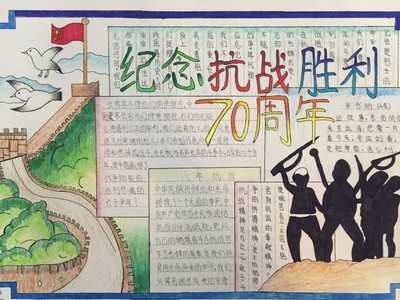一
“六经皆史也。”
《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古怪的一个命题——简单、直接、没得商量。那种独断自信的语气,那种着意要挑衅天下读书人的姿态,确实彰显了章学诚特有的个性。“六经皆史”的提法并非章学诚的首创①,但这并不重要。章学诚并不是一个凭空盖楼的人,他的很多观点都留有前辈思想的痕迹,但往往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这可能是当时的学术风气和章氏的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他受清代学术影响,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里,主张学有所本;另一方面,他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思维,绝不肯全盘的接受某人的观点,而必要予以融锻改造。例如,最早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人是王阳明,《传习录》曾记载阳明与弟子徐爱的一段问答: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示训戒,善可为训史,史以明善恶,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p43中华书局)
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故不赞成将“事”与“道”分成两截来看。章学诚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易教上》)②,又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经解中》)但章学诚并不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理解“事”与“理”的关系的。实际上,“事”在《文史通义》中,是一个频繁出现的重要概念③,理学鄙视事功,“行”大多是指个人的道德实践而言,但章学诚以“事”代替“行”,摆脱了宋明理学的个人中心立场,使得实践指向社会集体的历史运动,具备了“史事”、“政事”等含义。而“事”恰恰是史学可以考证应验的,这就使得宋明理学抽象的实践理论可以落到实处:“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文史通义·原学中》)宋明理学又带有泛道德色彩,王阳明谈“六经皆史”,最终还是落脚于“训戒”,是为道德服务;章学诚则站在史学立场上,主张减少道德对学术的影响,采取价值中立之态度:“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文史通义·习固》)他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
以上只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虽然受前人的影响,但他对这一说法的改造,则更多只能从他自己的著述中去理解。至于究竟何谓章学诚牌的“六经皆史”,一直是个众说纷坛的疑问,章氏自己对这一命题的阐释也是含混不清。我个人觉得,“六经皆史”与其说是章学诚得到的学术结论,不如说是一种治学方法。“六经皆史论”最为后人所乐道的,正在于它打破了“六经”在儒学中的权威地位,解放了史学,这其实也是章学诚所期望的效果,只是其影响在他生前并未显现出来而已。以今天人文科学的标准来看,学术结论和治学方法当然是两码事,学术结论的价值,是建立在清晰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详实的证据之上的;治学方法虽也重视逻辑的上的合理性,但其更为主要的价值,则在于运用此种方法对原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是否可挖掘新的内涵,得出新的结论。
清代汉学之兴盛,正在于发现了辨伪训诂等新方法。章学诚评价自己“高明有余,沉潜不足”,他并不擅长乾嘉学派那种细密的考证功夫,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证也是相当粗陋的。《文史通义》开篇就是“六经皆史也”,这就像是在说:“要从史事的角度看待六经”,略作过一番解释之后,他便急着把这个理论用于批判历代学说和各种学风,并将其融入编志修史的实践之中,这也表明他主要将“六经皆史”当方法论来用,结果是越用越顺手,他也就越发笃信自己“六经皆史”的判断,并认为这就是所谓的“见诸于事”。清儒治学,多半是对一个题目泛览群书,搜集证据,酝酿多年,然后得出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但章学诚恰恰不是如此,他更擅长从宏观入手,先建立一个假设,然后泛求典籍加以印证。他还为此辩解说:“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文史通义·约博中》),章学诚对后世学术的贡献,主要是治史的方法,通过考据获得一些不可动摇的结论,并非其志向所在,他希望以一人之力开创一派学风,与琐碎繁杂的考据学相抗衡。章氏常谓“所论多为后世开山”,其所以自信满满,即源于此。既然章学诚力图摆脱既有的学术体系,人们就很难用传统的标准去解释他的学说;此外,章学诚在学术史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他的著作在身后一百多年里回响寥寥,等到终于受重视了,却又正逢西学东渐,中国全部的学术传统都受到了极大动摇,这也为如何评价他的学说增加了困难。
二
“六经皆史”之所以成立,主要是具备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这有点像中医,虽然在原理上说不清道不明,但有疗效,能治病。但章学诚何以要用这种方式去研究学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对当时的学术背景做一番简略的说明。
清初诸儒于亡国之余痛切反思,深恨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弊病,一方面,在治学的目的上,主张从义理转入事功,追求经世济用的朴学;另一方面,在治学的途径上,开始由四书返归六经,认为“经学即理学”,而要因经入理,又需通过辨伪、训诂、考据等途径,理解经文的含义,才能真正懂得圣人真谛。但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又对学术发展的轨迹产生了极大影响,乾嘉学者为了避祸免灾,只能远离政治,埋首于文献的整理考订,脱离了清初穷经致用的道路,这就导致学术纠缠于对琐碎末节的考证,学者闻义理则掩耳。于是“道”与“器”,“义理”和“知识”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断裂。而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断裂,求得知识和义理的统一。乾嘉考据虽然狭隘繁琐,但因与政治脱节,也由此获得了学术的独立价值,纯为学术而学术。章氏若想打破考据学的垄断地位,则首先需要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即所谓“即器求道”;其次,针对考据学最终的落脚点“六经”,他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道不离器”,“圣人即器而存道”等等命题,“六经”并不是道,而是道的容器,是道运行于三代留下的史籍,并非圣人有意留下的著作:“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文史通义·史释》)因此后儒无论怎么对“六经”经文穷极考索,也无法领悟真正的“道”。这就打破了“六经”在儒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即器求道”实为章学诚学理的灵魂,他正是在运用这一方法针砭时弊的过程中产生了“六经皆史”的观念。章氏用了一种很复杂的方式架构自己的理论根基,他是个哲学气质很浓的学者,而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每当一种学术走入死胡同时,就需要借助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因此要想弄明白何谓“即器求道”,就不能不先对他的哲学体系做一番阐释。章学诚对于“道”的理解,一则源于老庄,二则源于《周易》。概言之,道家对他的理论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章学诚认为道体无名无形,不可被认知。《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照道家的思想,道可以表现为各类形体名称,但道的本体是永远无法被形式化、名称化的,因而也是不可见的。章学诚也说:“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文史通义·原道》,)倘若用这句话来解释经学的地位,则六经只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名称,而非道之本体,世儒之病就在于误以为六经即道,孔子即是道的化身。因此他说:“故学术之未进与古,正坐儒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文史通义·与陈鉴亭论学》),由此可知,义理、考据、辞章都是道的某种表现形式,而非道本体,三者相互攻难,无非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第二,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并无某种目的或意志在起作用。章学诚也以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组织,乃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出自圣人的品德意愿:“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文史通义·原道中》)这就是说,圣人没有设计组织一个理想的社会,并将这设计蓝图写入六经之中,好让后世可以依葫芦画瓢,他只是看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并顺应之。第三,道家复命归一的思想,对章学诚的思想理路有关键的影响。《道德经》十六章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第二十二章又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天下事物的纷扰,都是由于道术分裂,万物并作,道的本体则是隐藏在阴阳未判的混沌之中,要接触这个道本体,就需归复到天地未分前那个一的状态中去。章学诚将这个道理用于思考学术的起源,他认为学术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学术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反思。但在独立的学术产生之前,还有一个学术与社会实践尚未区分开来的混一时代,也就是所谓“道器合一”时期,章氏又将这种状态称为“官师合一”、“治教不分”。他认为三代之学之所以优越,正是因为道器没有区分开来:“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文史通义·原学中》)而三代之学不可复现于后世,则是源自道术分裂,后学诸子像一群打碎了贵重器皿的小孩,各自捡起一块碎片,却怎么也拼不回去。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庄子·天下》的启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豪。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是最早的一篇论述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文章。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启发了章学诚最基本的批评思路:“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驱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文史通义·原道中》,),只不过他不仅仅是用它来批评诸子,还加以改造,两汉经学、韩欧文章、宋明理学,以及后世的一切学术,都被纳入其文史批评的范围之内。
但是章学诚并不是一个追求复古的人,他认为“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文史通义·说林》,,“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文史通义·史释》)他和道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无为,归复人的自然属性而摒弃社会属性;章学诚则始终以日用人伦为立足点,认为人对天理的体悟与社会实践是息息相关的,正所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文史通义·原道中》,)《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章学诚吸收并发展了《周易》的道器思想,在他看来,一方面,“道”不可见、不可知,唯有通过“器”去认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器”,又有可能把“器”误当成为“道”。因此,“即器求道”是一个永不能完成的过程,人的认识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能代替真理。章学诚为人是出了名的争强好辩,生活中常与朋友争得面红耳赤,他在《文史通义》中,几乎把从古到今的学术都批了个遍。但他恰恰是从对各种学说的批判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这个问题后文还要详论)。余英时先生在《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一文中,认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是为了与戴震“经学即理学”的理念相抗衡,这是极有洞见的。④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章学诚之所以绝不苟同于任何学术传统,也有他自己学理上的必然。在他看来,自从官师合一的传统断绝之后,所有的学术都是“器”而不是“道”,因此对各派学说的梳理和批判,正是他“即器求道”思想的一种实践,并非全是出于意气之争。此外,章学诚是个实用主义者,故不会像庄子那样超尘缥缈,这又是他和道家绝不相容之处。他心中的“道”主要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天地生人,斯有道矣”(《文史通义·原道上》)。《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道”不离于阴阳,不囿于形名,不远于日用。章学诚也认为求“道”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存在于著述之中:“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原道中》)那种“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学术态度,都是章氏所反对的。
三
总体来说,章学诚心中的“道”,一方面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具有不可形式化,不具备主观意志等特征;但另一方面,“道”并不像老庄哲学那样是纯思辨的,而是和社会秩序并存的,是人类社会属性的某种综合统称,历史则是“道”在时间中的逐渐展现。对此倪德卫概括说:“章学诚的道似乎是人类本性中倾向于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的基本潜能,这一潜能在历史中逐渐将自己写出,在那些人们必将认为是正确的和真实的东西中实现自身。”⑤“道”作为抽象的本体,在历史的延续和人类的群体生活中得以展开。章学诚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随着人越来越多,社会的组织秩序自然就会越来越复杂:
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同上)
“道”使得人类自发地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实践,这就是从“道”到“器”展开。抽象的“道”因此而具备了可以被认知的行迹,正所谓“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事”是《文史通义》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章学诚反复强调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它主要是指人的一种群体化、组织化、当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正在展开中的“道”和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是一种“日用人伦”。而“六经”实际上就是三代“事”或“言”留下的痕迹,以及圣人对这些痕迹的记录、归纳。章学诚对推动社会文明的“道”的理解,有点类似于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的“扩展秩序”,哈耶克认为,人类在不断交往互动中得到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但是这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人类刻意的计划或追求,而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就是“扩展秩序”。哈耶克借用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知其然(know-that)”和“知其所以然(know-how)”这两个概念来区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所谓“知其然”,是一种人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的遵守规则的经验性“知识”,大家都知道遵循它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对它产生的机制原理却一无所知。因此他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正是这样一种“知其然”的隐性知识,是先于我们的认识存在的,我们通过生活在社会中,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类关系,自然而然地就知道该如何言行举措。这种知识并非是我们通过理性认知,先理解了社会的整体机能和原理,然后才知道该如何选择言行。相反,它是源自于人的社会本能,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能力。
章学诚也是这样看待人对社会秩序的认知,他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文史通义·原道上》),这就是说,人并不能理解道作用于社会的原理是什么,只知道它产生了一些理所当然的结果。但对于这种“当然”,人可以有两种态度,即普通人的态度和圣人的态度。普通人只知道无意识地按照既定的秩序行事,圣人也一样要遵循这种秩序,但与此同时,圣人还意识到了自己是按照某一既定的秩序在行事:“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文史通义·原道上》)这两种人的差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前文曾提到,章学诚的“政教合一”和宋明诸儒的“知行合一”不同之处,正在于他用“事”,代替了“行”,二者区别就在于,“事”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而“行”是一种个体的道德实践。按照近代结构主义的思想,整体并不简单地等于部分之和,这就是说,社会整体的运动并不简单地等于个体行为的累加。而章学诚经常也表露这样的思想:“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文史通义·言公上》)所以普通人把社会看成是个体,而圣人将社会看成是整体。普通人最多意识到有普通人、贤人、圣人这样单独的个体,而圣人则是从整体的社会实践和秩序自觉中反思社会的规律,于是章学诚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也。”(《文史通义·原道上》),他又进一步阐释,只有把社会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从社会实践日用人伦中领会真理,才能领会真正的“道”,相反,穷究典籍和圣人之言,最多只能成为贤人或君子: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原道上》)
“众人”即可视为社会的代表,“学于众人”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人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眼光了。不光如此,“众人”的含义不仅仅是数量众多,“众人”还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并且正按照这种秩序行动着的群体,所谓典籍仅仅是关于这种行动的记录,是圣人从社会整体的实践中总结制作出来垂教于后世的,但只有身在行动中才能完全领会社会秩序的全部意义,因此章学诚说: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文史通义·原学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理解何以章学诚如此看重“事”了。“事”就是运动着的“众人”对“道”活生生的展现,同时也是对典章制度的一种验证。正是这种运动在文献中留下的痕迹。众人在“政教典章之行事”中,直接领悟到社会秩序的意义,而并不是如后世需要从学术中去求得道体。既然“六经”记录的主体是众人,那么“六经”就并非私人著述,而是周官的掌故,类似于一种政府的制度文法或档案资料:
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文史通义·易教上》)

“事”是“道”当下化的展现,因此“事”和“六经”虽然同属于“器”的层面,但“事”却是衔接道和器之间的纽带。章学诚说:
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文史通义·原道下》)
后儒从学术(考据、辞章、义理),而不是从“政教典章之行事”中领悟道,这正是道术分裂的表现。于是“道”与“器”之间就产生了断裂。由于没有“事”作为验证的标准,则诸子各执一词,离器而言道,相互驳斥,这就产生了学术的争端。章学诚在《言公》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古代并不存在私人著作:“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文史通义·言公上》)。这是因为古人讲究政教合一,学术和社会实践浑然未分,事即理,理即事,因此根本不需要私人著作。圣人既然不可见道,而只能见到众人“不知其然而然”,也就不可能私人著述去展现自己对道的理解,相反,他只能让学者“学于众人”,即投入到社会实践中领会秩序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与某位领袖要“将社会变成一所大学”的理论是如此类似。和领袖一样,章学诚颇为赞赏秦朝“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制度:“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文史通义·原道中》)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清政府的文字狱也是赞同的。
如果说“道器合一”是章学诚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主张,那么“官师合一”则反应了他对于学者这一职业的态度。他认为孟子评价孔子为集大成是值得怀疑的,真正称得上集大成者,是周公而不是孔子。这是因为周公有权有德,所以才能制作典章;而孔子有德无位,故无权于制作,但他又担心典章不能传于后世,于是只能采取“述而不作”的做法。章学诚同时也声明,周公和孔子不存在谁比谁更伟大的问题。他们的伟大不是同一类型。章学诚之所以特意要抬高周公的地位,是因为他认为孔子也像周公那样明白“道器合一”的真理,他的思想和周公是一脉相承的,但孔子采用整理典籍和著述传教的方式来传播文化,而不是寓教于事,纯属不得已,这是因为孔子有德无位,故无法因事而制作典章。周公是理想中“官师合一”的化身,而孔子虽然在学识上仍然属于“道器合一”的传统,但他在行为上已经为后世“政教分离”开了一个端。学术从周公到孔子的变化,三代观念和后世观念的分水岭。因此章学诚说:“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古今学术之要旨”(《文史通义·与陈鉴亭论学》)。无论是孔子不得已“述而不作”,还是“六经皆史”,都是章学诚用以削弱经学绝对权威的利器,但他采用了一种极有分寸的做法,表面上仍旧推崇孔子与六经,暗地里已经把六经降到了“器”的层面,而将他本人所理解的“道”偷置孔子与六经之上。
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和“器”的关系主要包括“道不离器”和“即器求道”两种理念。而“事”、“六经”或典章,都属于“器”的范畴。“道”虽然高不可攀,但它既不可见,又无法表现为固定的形式,则实则上只是个虚置的理念,“器”反而因此获得了重大的价值,这正是章氏思想令人纠结之处,“器”值得重视,因此章氏反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可是一旦像考据学一样以“器”为道,同样会遭到他的唾弃。
实际上,一切学术的本质就在于如何处理“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三代以前是“道器合一”,“政教不分”;三代以后则离事而言道,“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一种离器言道的状态。
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六经皆史”这个命题中的“史”,究竟指的是什么,历来有许多种看法。胡适就认为“史”指的是史料,“六经皆史”不过是把六经看成六种史料;钱穆认为“六经皆史”是针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和乾嘉考据脱离现实,提出一种实用的主张,因此这个“史”实有经世济用的含义;还有如仓修良则认为以上两种含义兼而有之⑥。另外余英时先生认为,“六经皆史”是专门针对戴震“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作出的一种反击。⑦章学诚还有“六经皆器”的说法,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不过从对章氏的理论结构进行的分析来看,“六经皆史”和“六经皆器”实属等值的命题,这就是说“史”,是一种“器”,是“道”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和展现。而“器”这个概念,如前所述,既包括“事”,又包括典章,两者不可分割。典章是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去阐明的,但“事”则不断因时而变,是需要身在其中才能领会的,而且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和面对的问题,又和今人完全不同,因此章学诚说: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其大道也。(《文史通义·原道下》)
“器”有一部分得之于典籍学问,有一部分则得之于日用人伦、社会实践,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当下领会。三代以前,官师合一,器的这两个元素融合无间,所以古人才能即器求道。后世学者则只能见到前者而见不到后者,于是道术分裂为诸子百家,分裂为汉代考据学,唐宋辞章治学,宋明理学,又学者以学成名,私人著述渐成风气,这就更使得学术脱离了“学于众人”的三代传统,成为个人思考、研究的结果,这都属于“离事而言理”。章学诚心中的史学则是事理相合,理在事中,因事见理,是一种活的历史。所谓活着的历史,就是需要将典籍记录看做一种材料,而将现实的日用人伦和时代背景当做一种立足点,根据不同的背景赋予史料以不同的意义。事实上,“六经”的本质就是将典籍见诸于行事。
此外,章学诚又认为后世的一切文本全都是源自“六经”,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中提出六经中的《易》确立了以象传教的传统,而后世庄子、佛家的寓言神话,都是从这一传统中来;在《书教》中又主张后世纪传、编年等史学体裁源自于《尚书》、《春秋》所谓“圆神方智”的教诲;他在《诗教》中又认为《诗》确立了以文传道的传统,后世纵横辩论之术,辞章诗赋之学,都由此而出,只不过变得文胜于质,成了文字游戏而已:
同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至于诸子百家的思想,无不出自于六艺:
《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学诚的逻辑是:第一,真正的史学应该是史料和社会实践的综合研究,要遵守“道器合一”、“即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