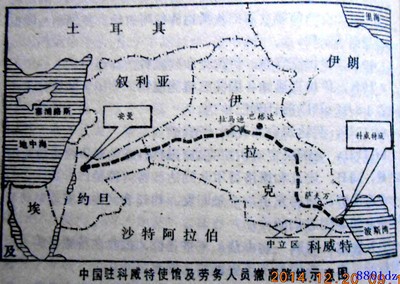我在华东神学院的日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蓦然回首,发现自己离开母校已有十四个寒暑了。接到母校二十周年院庆通知,再次搅动了我深处记忆。《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说:“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此时,作为一位“华东”的校友,我对于自己母校的情感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还记得90年初秋的一个黄昏,那个在农村长大又无缘在城市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活的我,独自提着沉沉的一箱只能保“温度”、不会有“风度”的衣服,心神不定地坐着只需扔五角钱的电车沿着电缆在城中转悠,正当心里暗暗庆幸交通费便宜之际,突然在询问中被告之自己竟然坐反了方向,诅丧地坐回来后终于汗流浃背地找到了五原路73号---我梦寐以求的“华东神学院”。
走进这新的校园,映在眼前的是一个只有二幢类似居民楼的青灰色房屋。没有绿茵茵的草坪,也没有宽畅的篮球场,更没有悠静的林荫道。一切显得如此平和、安静、亲切,简洁但充满着热情和活力,让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难道这里就是我事奉之路的“第二起跑线”吗?
我是88年从浙神江神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会工作了二年后再考入到“华东”插班的,那一年也是“华东”从三年专科改制为四年本科的第一年。我所以选择来“华东”,除了自己能力原因之外,也与当时我们浙江一带教牧同工和神学生中流传的一种现在看来经不起推敲的说法有关:那就是“‘金陵’偏重知识,‘浙江’偏重信仰,‘华东’则在两者之间!”我想,能够在一个信仰和理性追求比较平衡的地方再来深造一定是不错的。但有点是后来可以欣慰的,即“华东”的确是让神学生在属灵生命追求与知识、见识的拓展上力求平衡地努力着。
我进去的那一年,刚好也是苏德慈牧师去美国学习的二年。所以当时身为我们教务长的苏牧师我几乎没见到,我进去的时候苏牧师已经走了,待他学成回国之时,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却已经拿着《毕业证书》离开五原路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学,曾经因为没能亲自聆听苏牧师的教课而深深遗憾!
当时神学院院长是孙颜理主教,由于忙于上海教会的行政及教务,他每周只能来神学院一天。但学校的重大活动只要他在上海就不愿缺席。他留给我们的总是一位谦谦君子的牧者形象。每当见到他慈父般的笑容,总是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赛42:2)。记得一次毕业班的最后座谈会上,他非常诚恳地说过这样的话:“论学问,我比不上沈以藩主教;论才干,我也比不上史奇牧师;论行政能力,我也比不上华耀增牧师……”也许正是这种谦逊,使他甘为“仆中之仆”,因而也就能被拥戴为“牧中之牧”!
神学院日常工作基本上由当时任院办主任的华耀增牧师负责。华牧师是“大忙人”,常常见到他从郊区教会工作回来,拖着疲惫之躯来处理学校各种大大小小事情。我当时被大家推举为学生会主席,所以向华牧师汇报、请教的时候也就特别多。华牧师自己身体并不算太好,更甚的是其师母长期身体不佳,且需华牧师照顾。因此即便回家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他还得做菜烧晚饭料理家务,深夜还得备课,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大约要花一个多小时赶到学校。这是在即将毕业的某一晚上,我和玲斐、发珍等几位同学相约去华牧师家看望师母时才知道的。
在“华东”的二年中,对我而言,听课笔记做得最完整的要算是沈以藩主教的《系统神学》和《基督教思想史》,至今还常拿出来作参考。由于主教上课逻辑富于条理、深邃又不乏幽默,娓娓道来,润物无声。经过他的诠释,原本一些枯燥的神学语言在他的口中变得形象生动。而且沈主教从不强迫同学接受某种观点,而总是用客观的态度向大家介绍各种思想,然后提出他的一些看法用于启发学生心智。记得有一次神学课程中讲到“教外是否存在真善美”问题时,他特意准备了记录片《黑户》让大家欣赏和思考,从中悟出道理。沈主教在毕业前特意将我叫到他所事奉的国际礼拜堂,询问我的工作去向及自己意愿,并且以经句相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平凡而诚恳的场景至今还在眼前。
十二年过去了,每当我闭上双目,去追思逝去的岁月时,脑海中意时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张张熟悉的笑容。时光如流水冲走了我记忆库中许多东西,但可敬的老师不会忘,可亲的同学也不会忘。
上个月我带本市同工们一起去青岛访问,曾经与我同寝室的赵开洁、孙斌热情接待了我们。老同学见面免不了想起我们在“华东”的美好时光,尤其是在寝室里“黑暗”中发生的故事:如果不是定时熄灯制度,在图书室废寝忘食的莘莘学子多数是不会轻易撤回到房间的。熄灯后对当天学校内外大小新闻总要评论一番,包括上课时老师讲的精彩片断加上添油加醋的发挥,不讲到笑翻在床上是不过瘾的。如今已经是闸北堂主要负责牧师的秦小林,常常带一些上海家里为他预备的小吃给我们解馋,让夜自修回来饥肠辘辘的人惊喜有加。也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小林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也正因此,我们这个寝室的‘爱国卫生运动’他搞得最多。不过,他也常常“一本正经”地用“不扫一室,何以扫天下”类似的名言教导我们这些“懒汉”;福建的付天配心格内向柔软,具有女性般特有的细心。常常默默地为其他室友去打热水,尤其是在当时热水“资源紧缺”的情形下着实让人感动一番;室友中若有哪一位身体不适,那我们一定会问寒问暖,同心为其祈祷。同处一室,尤如唇齿相依,“争闹”也是不少。比如为了争先看一本新到的《大学生》杂志也为“面红耳赤”一阵;为了一个南辕北辙的神学问题争论不休唇枪舌剑一番;甚至为了昨天晚上谁的打鼾声“噪音”了大家因而群起而攻之。山东的赵永泉在打鼾这方面很有“特长”,有一天早晨醒来时他的床上多了不少别人的书本,那是因为室友对他的鼾声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半夜三更里“发射”过去的“导弹”!然而,这对他并不起多少威慑作用,早晨他睁开眼时常惊奇地问:“我又打鼾了?不可能。我自己怎么没听见?陷害!”
当时的住宿条件有限,男女生同在一幢楼内。女生在上面几层,她们下楼时叽叽喳喳象一群小鸟飞过。男生在楼梯口相遇,总是礼貌地打打招呼。不过也有笑料,我班的一男生本来英语就“烂”,昨天才刚学会一句,今天一大早似懂非懂地就对着一位刚下楼的女生大喊:“**,go to bed!” 顿时一阵狂笑声把楼层都震动了……
时光真的很快,当年孩子气十足的我们,如今大多都成了孩子们的父母了。
曾经是我们班长的陈玲斐,因为具备较修长的身材而被安排坐在教室中最后一排,故被老师戏称为“那坐在最后面的小姐”。温柔娴淑的她象一位姐姐似的把班内事务打理得有条不紊。毕业后因同在浙江我们常有见面机会,她现在是椒江区三自的秘书长,工作较多但看她还是忙而不乱。目前已经是有了一个上幼儿园的可爱女儿,每次提到女儿和丈夫,和许多别的女人一样,她的话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脸上流露出的都是幸福和憧憬。
发珍也算“幸运”,毕业后没有回到可能“不被人尊重的”家乡教会而来了杭州,先在市郊的览桥堂,近年又“高升”到市中心的思澄堂事奉。与在学校的青春时光相比,十多年的“秋风暑雨”,无论从思想和外表看上去她都“成熟”了许多。最近我在杭州时,听见有人喊她“老大姐!”我忽然有个触动,发现曾经“嘻嘻哈哈”的姑娘竟然开始与“老”字沾边啦!
与我同班的在浙江还有张国美、林冬娟、郑志燕、金柳珍等。去年我开会路过雁荡山,终于有一次机会,请国美“出山”好不容易见上一面,这已是十年没见过面了。除了外表稍显清瘦,她还是快言快语、似乎一切都无所谓的洒脱和干练之气依旧。她说没有在教会“全职事奉”,但教会工作她还是很积极,并且好像也是当地县两会“秘书长”之类的“要人”之一。冬娟是嘉兴两会的总干事,也是我们省两会海外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几次在外地领“培灵会”也与能她同工,几年下来,她还是有些“女强人”的味道,对一些事分析有一定主见。嫁了个是传道人的好老公,不用说,神也是很赐福她的。上个月是玲斐突然通知我,说金柳珍不幸因患脑癌离世归天,我因会议在身未能前去致哀,只好委托玲斐她们买一束鲜花以示悼念!我想,死去的同学留给我们渐入中年的人好象不只仅是一种惋惜,可能还有一种提醒和警示。
十七年前我考“华东”的那一年,妻子正好有孕在身。母亲为了让孩子出生赶在我离家之前,竟然在神面前祈祷让孩子“早产”。果然,孩子提前一个月临世。在第五天,我就整装出发来上海了,依依不舍的我那时才更体会“撇下一切跟随主”的内涵。而今,孩子已经长得一米七个子了,当今天我拿出他二岁半时在“华东”门口与我一起合影的照片,他问“这就是爸您的母校吗?”我说:“是,但也不是。因为‘华东’与你一样,它的‘身量’和‘智慧’也都长大了呀!”
现在“华东”已经离开了当年的五原路狭小的地方,进入了一个全新宽大的环境。但愿母校禀承当年办学时神所托付的神圣信念和使命,为华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教会的人材培养奉献自己,结出累累硕果!也请母校放心,离家以后的学子们一定牢记当年恩师的谆谆教诲,辛勤撒种,忠心工作,誓为基督作见证,也为母校作见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