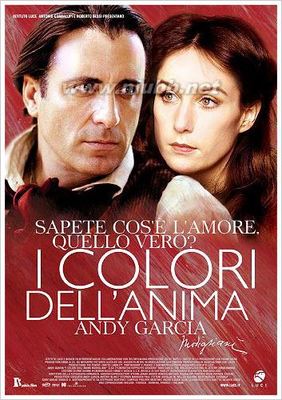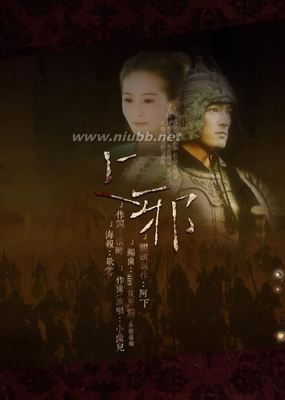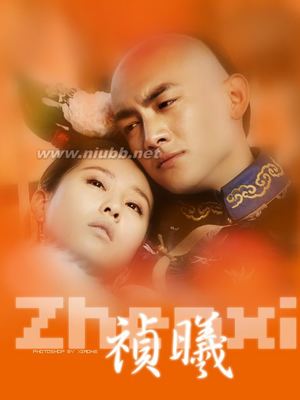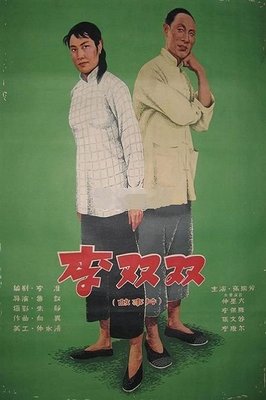孙冬冬,策展人,《艺术界》资深编辑。策划当代艺术展览,并发表大量艺术评论文字。曾策划展览:“你应该学会等待”——龚剑个展(2009年)、“视觉的结构”(群展)(2011年)、“ 陌生人”——陈飞个展(2011年)、“余地”吕振光、李杰(群展)(2012年)。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在策展人风起云涌的今天,孙冬冬可以被称为小众策展人。他学的艺术史专业,在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做过策展行政,现在《艺术界》杂志社以编辑为生,偶尔选择性地做些展览。这样界定他的身份,是跟他的职业规划和艺术态度有关。所谓小众,是他有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他的艺术态度和艺术观念可以被范围内的艺术家所承认和接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冬冬谨慎地面对自己,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影响,在艺术界种种“诱惑”面前,始终自觉地保持低调的态度。这种清醒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将要做什么。他将这种正面的个人定位从容地纳入职业规划。
孙冬冬以策展人身份加入A4当代艺术中心“2012青年艺术家实验计划”项目,收集了在他长期观察范围内的6位艺术家作品,这个展览让我注意到每位艺术家在思路、表达语言、材料运用、观念能动上都相互独立,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仅仅是作品呈现,没有设定统一的展览主题。孙冬冬基于项目的实验性,只是给出了线索,这个线索围绕艺术家个体展开,策展人是退到后面的组织者。
谢帆:《一立方与一公里》
易鸿:了解到你是学艺术史专业的,现在《艺术界》做编辑,编辑和策展人身份兼顾,这两个身份对你来说,有何相关之处?
孙冬冬:学史论的人,是从美术史角度出发,与策展不一样,与批评不一样,有自己的学科要求。艺术批评范围更广,有不同的角度,可以选择文化角度,选择艺术角度,同样是文字工作,还是有细微的差别,这种细微的差别恰恰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决定的。一般来看,策展就是策展人写篇文章,把一群艺术家放在一起作展览。实际上不是这样,个人认为策展人工作分两部分,笼统地讲一个是案头的,分析研究艺术家。第二个是现场的,包括去工作室拜访艺术家,了解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时间和脉络,还有就是展厅,安排作品的摆放布置,结构关系。所以策展人不是我们往常认为的展览组织者,只要写一篇文章就好。相反,好的策展人不需要写文章就能让观众进入一个好的现场,通过现场就可以表达出他对于展览要达到的目的。
易鸿:现场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孙冬冬:对。因为文字是单身的,一些策展人的文字,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往往是“可能性”这类暧昧的词。相反的,一个好的展览现场可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和挑选与展览主题观念相契合的艺术家是有关联的。
易鸿:也就是说从观者的单向感受进入了策展人的立体思维这样一个转变。我注意到,中国策展人各种身份都有,有大学艺术史教授,有画廊老板,还有曾经的画家。而且中国策展人身份是没有行业标准来评判的。好的策展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孙冬冬:应该怎样去表述呢?比如说在大学研究哲学的人也可能做艺术策展人,他完全通过哲学的角度去看待艺术,但是我学艺术史,更多是从艺术范畴去看,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也许学哲学的看来,作品与作品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哲学上看到的都是本质的东西。我们更多的研究表述技巧,语言的搭配,观念的突破,会考虑艺术内部的一些问题。两种不同策展人表达主观不同的东西。
易鸿:策展人的专业和经验,决定了不同的展览方向。
孙冬冬:不管策展人是学文化,还是哲学、艺术,其基础和出发点是要具备对艺术的感受力,这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感受力,做展览,挑选艺术家,展览是成立的,作品对观众有影响,这是最关键的。艺术工作是开放的,如果艺术有门槛,艺术对我们人就没有那么重要,正因为它本身没有门槛,对于视觉,对于身体,对人是根本性的联系,我们不用回避所谓的职业划分,那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方式造成的。
鄢醒:《谋杀电视机》2
易鸿:我注意到这个展览的每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思路、表达语言、材料运用、观念能动上都相互独立,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一般来说,策展人在策划展览时都会提炼个主题,想方设法对展览进行解读。而这个展览仅仅是呈现,之前有设定过主题吗?
孙冬冬:有个线索。这个展览是项目,围绕艺术家个体展开,策展人是退到后面的,不是在前面的。做这个展览更像是个组织者,6位艺术家都是我熟悉的,是我考察视野范围内的,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实践和变化。
易鸿:每个阶段的生产。这个展览之前作品都成型了吗?
孙冬冬:对,因为他们很忙,给这个展览提供了难度。当初对这个展览的设定是从意识的角度入手讨论作品,而不是置于一个作品本身意义不断地阐释,是个回溯的过程。
易鸿:退到艺术家本身的出发点上。
孙冬冬:对。这是我对实验的一个看法。实验不是创新,是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发现自身的局限性,有限性。
易鸿:这6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将不同理念的作品呈现在这里,正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而艺术本身是包容的,所以,他们才同时存在,互相对照,又互为补充。
孙冬冬:是的。没有什么不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系统中,对当代艺术的认识,绘画变成很边缘,装置影像很实验,我认为都不是,单纯以媒介来划分出,这个价值就是在相互的参照中,都是相对来说的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这是我对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理解。
易鸿:做为策展人,选择艺术家时有没有一个标准?偏好哪种类型的艺术家?
孙冬冬:一方面是收集的过程,就是不停地看,去了解。曾经看到作品很喜欢,就打电话去艺术家工作室拜访。
易鸿:打动你的是什么?
孙冬冬:不知道,我对艺术的看法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乎艺术家如何去想一件作品,艺术和行动的逻辑关系,我非常在乎这一点。
易鸿:关注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性,怎样把新的现实问题用艺术的形式转换。
孙冬冬:这也不算实验性,是应该做的。这次展览所有东西都是基于他们自身逻辑来做的,并不是为这个展览主题定制的作品。我很在乎这一点。我喜欢挑作品,更自然一些。
易鸿:何翔宇的“可乐计划”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用掉127吨可乐,工作量巨大。他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以及商业上的回报,毕竟要花一大笔费用支撑。
孙冬冬: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分化,艺术家都是基于自身条件来做作品,他能完成这样的事说明他的家境可以支撑这个作品的完成,这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可乐计划”开始于一次小的实验,何翔宇想看看可乐烧干后是什么,后来想做大,熬了一吨,再后来想再多点,于是回老家继续熬。一个事从量变到质变,看上去简单,其实必须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去解决,不是在工作室里解决。你会去搅动这个社会,你的行动就会让社会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年轻人多接触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些所谓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就会显露出真相来。在做“可乐计划”时,何翔宇了解到127吨是他老家当地一年消耗的可乐量,可乐公司不卖给他,因为可乐公司对销售地有监控,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何翔宇会通过别的方式去解决,他也是在挑衅资本主义的监管。
易鸿:这个计划的进程中,事先何翔宇并不了解会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反而是“可乐计划”有趣的一环,面对这些事去解决同时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孙冬冬:他给自己设定了很多障碍。
易鸿:他的作品把个人行为扩展到社会行为。这个作品投入了多少资金?
孙冬冬:作品都卖了。
易鸿:怎么卖?熬出的碳?
孙冬冬:对。就是有人喜欢。因为可口可乐在当代艺术史属于非常特殊的经典性的符号,所有的艺术家,特别是美国欧洲的艺术家对可口可乐所谓的批判和赞美,让这个符号性的标志深入人心,成为消费景观的表征。当一个中国艺术家做这样的一件作品,将它转换得如此彻底,在艺术收藏系统中影响力非常大,反而让他重新可以找到做下一个计划的钱了。
易鸿:收藏家更喜欢作品的结果——可乐渣,还是整个计划过程的呈现方式也被纳入了?
孙冬冬:连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工具都买了。
易鸿:也就是说不止一个收藏家,不同的收藏家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孙冬冬:将127吨熬出的渣分装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便于收藏。
易鸿: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很成功的商业运作,可能艺术家本人都没有设想到,但实际产生的效果显然超出了计划本身。
孙冬冬:是的。把景观重新又还给了景观。
易鸿:换了一种物质形式而已。
孙冬冬:重新占领吧。真正意义上判断一件作品的好与坏,不是东西画得好不好,做得好不好,而是某种东西打动了别人,他们就会去收藏。
易鸿: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艺术家鄢醒的作品《谋杀电视机》,将他拉大提琴的过程通过投影仪而不是电视播放,艺术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载体的转换吧。艺术家唯美的脸谱和大提琴如泣的音调打动了我,透出某种诱惑的隐秘和不可知的忧愁。
孙冬冬:鄢醒是做行为表演的,他的出发点是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他既是身体的欣赏者,也是表演者,是他作品的媒介。作品取自于美国艺术家白南准现场的行为表演。
易鸿:鄢醒移置过来用自己的身体重新解读经典。
孙冬冬:对,录像艺术之父白南准表演的是美国概念音乐家的作品。录像是基于电视机而产生的。鄢醒有意识打破录像之父对媒介的框定。单纯从媒介来讲,科技在不断进步,这种科技产生出来的媒介反而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最后变成影像画质的不断更新,设备不断变大或变小或变薄,电视机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液晶,变成高清数码了,媒介已替换。本质上,到底是媒介打动我们,还是商人的东西在打动我们,鄢醒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把身体纳入实验的原点,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表现力的,他的重新演绎,依然让人感到沉静,甚至感知到哀伤的情绪。作品本身在观念上的突破还未必,但你静静地站在作品面前,依然会感动,想依偎靠近,是件感人的作品。
易鸿:选择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归纳起来显示出这样的信号,他们试图打破常规,保持怀疑的态度,颠覆一切现行的既定的观念和行为,在颠覆中寻找自己的未知,对关注的对象给出自己的理解。
孙冬冬:在北京很多艺术家都在干这些突破常规的事。我选择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不同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与人性是相关的,就像艺术家陈飞作品中出现的电影坏人一样,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类型片恐怖片,都是基于人性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艺术,是很令人不爽的途径,你可能回避他的观念,他的突破性,但是基于这个层面,你会发现这些作品不是让人感到迷惑,它不会清晰展现出它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说艺术做的事,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替代。我们在说哲学时,可能你不太懂,但这件事用艺术来表达,也许说不出来什么,但可能会一拍脑门说你懂了,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跟其它媒介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懂了,不是说知识的领悟,也许是人性的某个角落起了反应。
刚才有人问我,展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说最大的特点是这6位艺术家一般不会再在一起做展览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