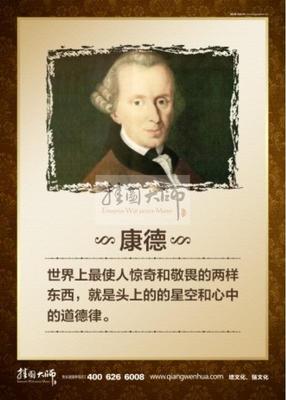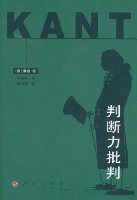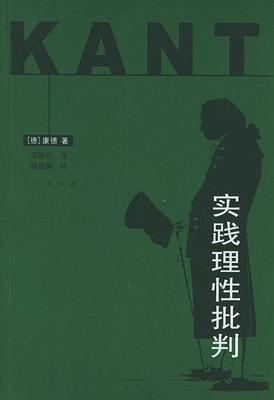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在《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劈头第一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这句话可谓全文之纲。接下去他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人类缺乏理智么? 并不,问题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人的理智被捂盖住了,人因而处于蒙昧状态,即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类当然没有能力对自己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而只能因循既定的社会状况和思维习惯,安之若素而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为此,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同上)。

图片源于网络
19世纪的欧洲,“自由”这个概念已被反对专制与愚昧的各派思潮——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等等——奉为崇高的人类精神;不管其间在解释上有多么尖锐而不相容的分歧,自由的神圣地位是没有人能否认的。集古典精粹思想之大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社会便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概括地说,康德认为,自由、道德、幸福、立法(保证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权利的法律)这些概念是浑然地存在于纯粹理性之中的。他对于这些概念相互关联的分析,逻辑严谨,丝丝入扣。但是这毕竟是理念里的东西,现实生活与之相距甚远,这是一个大矛盾。
康德生活在普鲁士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他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法国大革命曾经给他带来短暂的希望,但在感叹赞赏之后很快就发现这场革命后期竟走上了一条破坏法治准则、残杀异己者的恐怖道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2—153页)。于是康德在理念上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论证时却不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在普鲁士的君主专制的体制下,“法律”绝对不可能保证臣民有公开而充分地运用理智的自由权利。
在这里,康德的理论不可能是彻底的,他终于没有能够摆脱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王国。康德直到晚年也没有找到出路,只能寄望于君主的“开明专制”,至于他所向往的“普遍公民立法的社会”只能保存在理念中或期望于遥远的未来。
康德60岁以前的政治社会环境似乎还允许有限度的自由,因为有个康德认为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腓特烈大帝,他给他的臣民限定的既有“有限自由”又能“保障公共安宁”的限度,就是:“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页)。腓特烈大帝(FriedrichⅡ,1712—1786)逝世,他的侄子威廉第二(Friedrich Wilhelm Ⅱ,1744—1797)继位以后,就连“有限的自由”也不给了。康德最后二十年的日子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虽然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在全欧都已无可争议。康德在宗教和哲学的区别上撞在了神学家的枪口上。其实他无非是主张神学只管宗教的事,哲学来管科学的事,互不干预而已。结果是威廉第二下令谴责康德,禁止他再写这类文章,也不许他在大学讲台上再讲这类问题。于是他的有关著作遭到扣检和禁止。这一年(1794)康德已是七十衰翁了。
康德在致友人书中说:“现在我们这里权势颇大的书报检查机关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横加侮蔑。因此,我决定,把这篇文章(《院系间的争论》)再放一放,我希望,临近的和平也许会在这方面为无害的议论带来更多的自由。”因为康德的这篇文章等于主张在学校里“树立了哲学系作为神学系的反对派”。这在当时的普鲁士是绝对违禁的。1793年他著有长文:《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力图论证理论和实践是可能统一的,但无论思辨如何周密,他也无法摆脱矛盾;其实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或那种冲突中度过的。
终其一生,康德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昭示世人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和争取这种自由权利。这正是《何谓启蒙,答复这个问题》的主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