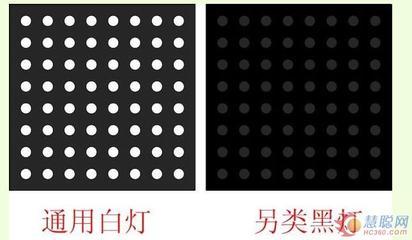我已决定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从这个春节开始……
姚鄂梅,生于1968年,湖北宜昌人,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钟山》《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短篇小说《黑眼睛》等。
黑键白键
文|姚鄂梅
原载|《当代》2005年02期
我渴望下雪的圣诞节
我渴望下雪的圣诞节,可偏偏这个圣诞节很晴朗。下午,学校演出了一场英语话剧,我演的是大灰狼。Iamveryveryhungry.我的开场白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因为我把喉咙憋得比腰还粗。我注意到静在台下不时地用手捂着嘴笑。她的牙齿很好看,可她还是爱用手捂着嘴笑。她知道我们在圣诞节有节目,婕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她,我不想让她们同时来看我。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于婕和静两个人,我分不清谁更亲一些。甚至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与静更容易靠近些,但黑键却与静越来越远。
老师说演出很成功,还说什么有一个搞艺术的爸爸就是不一样。我不觉得这种表扬有什么值得骄傲,但毕竟是表扬,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高兴的。正在暗自得意的时候,静出现在走廊尽头,她穿着淡蓝色的大衣,系着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围巾。我不明白,她这样固执地使用一种颜色是否会觉得单调。
静把我带了出去,她要我去帮她看一个人,这也是我们早先就约好的。
还是吃饭。大人们见面总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像我们,总是在饭后才和同学们在一起。
说实话,那个人和静不般配。我当然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静看他的样子,那样子好像她已经彻底把黑键忘记了。我更不喜欢他看静的样子。以前,黑键也那样看过静;当然,他不如黑键长得好看,他似乎已经不年轻了,而且正在秃顶。他的牙也不整齐,有几颗还被烟熏黑了。静叫他全哥。这我就放心了,这种称呼说明静还没有决定正式跟他谈恋爱。
全哥老叫我小朋友。小朋友,吃点这个。小朋友,吃点那个。我讨厌别人叫我小朋友,这里面有一种轻蔑的味道,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难道年龄小的人智商就低吗?书上说,人的智商生下来就是一个常数,所以,我并不觉得成年人就比我们聪明,他们只是比我们更狡猾而已,因为他们的心眼儿更多。
静告诉他我叫白键,他马上问我父亲叫白什么?芽干什么的?我说我的父亲叫黑键,他正在准备拍一部伟大的电影。
全哥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你的父亲叫黑键!你叫白键!一部伟大的电影!哈哈哈,真好玩!
我没有笑,我觉得自尊心有点受伤。我转头去看静,静也没有笑,她毫无表情地看着全哥。我知道她生气了,她一生气我就高兴,我想,这说明她并没有完全忘记黑键。
吃完饭,全哥还想安排其他的活动,静说不行的,我还要把他送回学校去。他们站在门口说话,我发现全哥的个头也不算高,几乎只有静那么高。我不想看了,一个人转身朝学校走去。
静追了上来,也不问我为什么不等他,我们一起放慢了速度。静说你觉得他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静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沉默着。
静说我觉得他比黑键好,黑键从来没有说嫁给我吧,可他就敢说,他说他等着娶我这个老婆。
而且他很有钱,对我也很好,跟黑键简直不能比。
我还是沉默着。我觉得静说话的样子就像在做一道数学题。
静突然抽泣起来:现在好了,你找到了妈妈,黑键也找到了新女朋友,我可以完全从你们的生活里退出来了,我没必要再坚持在你们的生活中了。我得去找我自己的生活。我原来就知道,我只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驿站而已。可你知道吗?我真不习惯,我不习惯黑键和白键以外的人。
我有点心烦意乱,不知道该对静说什么才好。
静擦擦眼泪说真是的,干吗对你一个小孩子说这些呀。然后她假装高兴地说来,我们来唱歌。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可她的声音一点也不欢快,倒像是隐藏着哭声。唱了几句,她就唱不下去了。
我们在校门口闷闷不乐地分了手。
回到沸腾的寝室,我感到自己就像一粒米掉进了滚烫的锅里,一下就被感染了。说实话,我喜欢我的寝室。这里有着十一个小伙伴,他们当中有的傻里叭唧,有的自以为聪明透顶,有的一副娘娘腔,还有的根本就未脱奶腥气。但他们很简单,很快乐,一截小棍子都能让他们莫明其妙地乐上好半天。我是他们当中的忧郁王子,这是我们班的女生给我取的外号。但在这种氛围中,我再也无法忧郁了。或许我天性并不忧郁,只不过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所以我沉思的时间稍微多了一些而已。
他们正在模仿007里的一场激战,上下两层的床位成了绝好的战场。枕头啊,床单啊,衣服啊,全都成了最好的武器,既有攻击性,又不至于伤人。好家伙,他们把我的床单扯到地上,两三个人站在上面扭打着。还有一个家伙扮成女人,腰上系了条花格围巾当裙子,毛衣里面塞进了两只小馒头权作乳房。看着他那副滑稽的样子,我笑得蹲到地上去。
听到我的笑声,他们呼啦一下拥上来,说白键,你怎么才来呀。这家伙扮女人总是不到位,我们到处找你,我们一致要求由你来扮女人。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扒我的衣服,我哪能让他们轻易得逞呀。奋力反抗中,我打伤了一个人的鼻子,鲜红的血弄了他一脸一手,他哭了起来。这一下,游戏玩不成了,大家纷纷回到自己的床上,只剩下那个家伙独自在那里哭泣。我向他道歉:我不是有意的。
我想带他去洗一下,他一扭身躲开了,他说你这个人真讨厌,我们玩了这么久都没有人受伤,你一来就动粗。真是的,别人说的没错,没妈的孩子最粗野。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我攥着一只硬邦邦的拳头问他:谁说的?谁?说!
他有点害怕了,捂着流血的鼻子支支吾吾地说没有谁说,书上就是那样写的。
哪本书?
生活老师终于来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这意味着,明天班主任将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一场处罚是免不了的。而且,从明天开始,生活老师将和我们睡在一个房间,直到我们重新变得老实起来。
生活老师搡了我一把,说白键,怎么又是你在打人?
我说我没打他,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他。
那些家伙们在旁边围了一圈,生活老师看了一眼手表,大吼一声:几点了?还不睡觉去。话音未落,他们全都闪开了,留下生活老师和我在惨白的灯光下不怀好意地互相瞪着。
要说明的是这个生活老师是个老太婆,她身上总有一股子韭菜的味道,据说她还是一名退休的幼儿园老师。她十分爱讲道理,她经常爱说你们要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体谅别人,你们要在集体生活中学会遵守制度,你们在家都是小皇帝,在这里要学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平民。看来今天她又要对我讲她那些所谓的道理了。
看来我错了,她今天似乎没准备跟我讲道理。她厉声说,你妈妈怎么教你对待小朋友的?嗯?我不做声。
她提高声音问:说呀,在家里你妈妈是怎么教你的?我还是不做声。
她搡了我一下:你说呀!
我大声吼道:我没有妈妈。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怎么能说你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怎么会有你?你妈妈听到这话会很伤心的你知道吗?
有个家伙在床上说老师,他真的没有妈妈,他被他妈妈抛弃了。
我冲他大吼道:放你妈的屁!
我看见生活老师张大了嘴。然后,非常羞愧地,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转身向外冲去。
我们的学校离江边很近,我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泪眼朦胧中我只能向江边跑,虽然我很害怕江边那些黑黢黢的树影。因为害怕,还因为委屈,我坐在江边大声哭了起来。我听见我的哭声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回响,我真的开始伤心了,为什么我总是有这么多的不如意,为什么我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生活老师拿着电筒晃过来了,她边走边喊我的名字,我藏在一棵树后,她没有发现我,一直朝前走去。
我突然有了想逃跑的念头,我知道江边有很多船,他们会一直开到重庆去。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黑键来自重庆。重庆的一个女人生下他后被我爷爷抱了过来,从此他成了我爷爷的儿子。我想不如我坐船到重庆去,替黑键找回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怎么找呢?我不知道黑键母亲的名字,也不知道爷爷的名字,关于黑键的资料我什么也没有,我只知道他叫黑键,真的。我才发现,我对黑键了解得太少了。
生活老师又走过来了,她边走边喊:白键,你在哪里呀?白键,你回来吧!老师不小心伤害了你,老师向你道歉好不好?你今天要是不回去,老师就死定了。老师担不起这个责任啊,老师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头子,还有一个下岗的儿子,还有一个要上学的小孙子。老师要是出事了,老师家里就全完了。白键,我求你了。白键,你出来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她真的很可怜。我想起来了,她身上的毛衣都是旧的,袖口处满是破毛线,冬天里她一直都穿一件旧棉袄,她可能没有钱去买新衣服。她似乎要哭了:白键,你再不出来我只好报警了,一报警你我都完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有意让自己在她的电筒光里露了一下。她发现我了,跌跌撞撞地跑上来,一把抱住我说白键,我可找到你了,你真把我急死了,你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我说我有一个条件,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跟你回去。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她都会答应的。
我说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班主任老师。她想了一想答应了。告诉班主任老师就意味着黑键不久也会知道这件事,黑键的态度让人捉摸不定,我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何种处罚。与其让他知道这事,不如我一个人来扛。
一路上,我们都不再提这件事。生活老师给我冲了一杯热牛奶,我喝下后悄没声地钻进了被窝。
第二天,静给我送来了一些学习用具。我知道这只是由头,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和我扯一些闲话,她喜欢和我扯一些闲话。
静笑笑说白键,妈妈对你很好吧?
我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所有人都对我挺好的。
是吗?那你最喜欢谁?
我说我谁也不喜欢。
静说白键,你在撒谎,你肯定有最喜欢的人,每个人都有最喜欢的人。我说我真的没有。
难道黑键你也不喜欢吗?我不做声了。说真的,黑键离我太远,每当我最需要他、最想念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我身边。而当他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需要反而不是那么迫切了,这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静突然望着我说白键,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妈妈不准备把你留在她身边,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好不好?
我说那黑键呢?
黑键会有黑键的生活,新的阿姨、新的家。
那全哥呢?
全哥也有全哥的生活。
我笑了,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你们大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要跟白键生活在一起,白键是儿子,静是妈妈,你也不用喊我妈妈,你就叫我静好了。我们的小家会很温暖,我要送你上最好的大学,受最好的教育,你会成为我的骄傲。
静还提出让我和她一起过年。她说跟我一起过年吧,我们去海南岛过一个热腾腾的春节,那里有海浪和沙滩,我们坐飞机去。
听她这样一讲,我还真有点受诱惑。这使我重又想起曾经和静在一起生活的好时光。那时她像一个地道的母亲,给我既温暖又严厉的感觉,我有点想重温这种感觉,而且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海。试问,有谁不想去看看真正的海呢?
我说那你得跟黑键讲清楚。
静说应该没问题吧。
同学们正在打篮球,我是中锋,他们正站在操场上眼巴巴地等着我。如果我不答应,静还会继续谈下去。所以我说好的,我们到海南去。
在投篮的瞬间,我想,静说的话是当真的吗?会不会是因为太想念黑键所以才对我说那些话呢?我想不明白,只好放下这些事情,专心去想投篮的事情。
在投篮的另一个瞬间,我想,静真的挺好,看上去和黑键也非常般配,为什么黑键要和她分手呢?现在,这是我最弄不懂大人们的地方。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如果黑键真的想对我好,就应该跟静结婚。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每天有规律地起床,吃饭。但是,黑键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做到对我好而忽视他自己。
一场大雪结束了这个学期
一场大雪结束了这个学期。放假前一天,黑键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好家伙,他的变化可真不小,他留起了大胡子,穿着件大红的羽绒服,看上去像刚刚滑雪归来。一看到我,二话没说,先把我举到空中。然后他就风风火火地帮我收拾行李。我说我们上哪儿去?黑键说你跟我走就行了。
趁他这时候心情好,我想跟他说明一些事情。我再次追问: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
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我必须知道我们要去的确切地方。
跟我走就行了,难道我会拐卖你?
我大着胆子小声说:婕要我跟她去过年,静也要我去跟她过年。
黑键停下了收拾,盯着我问:那么你想到哪里去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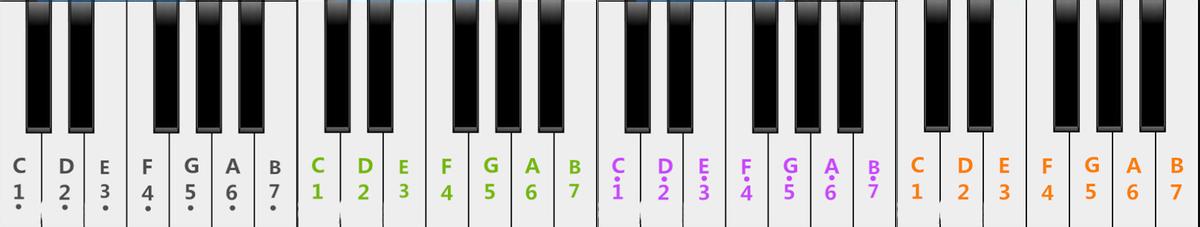
我摇头,我确实不知道。但我觉得至少她们都和我有约在先,我这样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走,显得有点不太礼貌。黑键见我沉默,扔下手里的大提包,说你又被她们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是吧?
我还是摇头。黑键看了我一会,说你别傻站在那里,快来帮我收拾你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必须出发。
我慢慢地挪出去,我得去打个电话,否则,明天将有两个女人到学校来接我,见我不辞而别,两个人可能都要生气,或者伤心。
黑键说你磨磨蹭蹭地在干什么?过来,把这个东西给我扶着。我只好回去。
好不容易等到黑键去洗手间,我一溜烟奔进传达室,对值班的刘爷爷说:如果有女人来找我,就说我跟我爸爸走了。刘爷爷有点老不正经,他说女人?你才多大点,就会有女人来找你?
我顾不上跟他废话,因为黑键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
三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了长途汽车。上车前,黑键把我拉到水龙头前,细细地梳头,喷上大量的发胶,还整好了我的衣服领子。黑键这样一做,我就知道我又要面对一位新的阿姨了。我知道黑键的这套把戏,我就像黑键身上的一件衣服,是他的形象,他向来对自己的衣服十分挑剔,一如他对自己的形象一样。
我在汽车玻璃上看到了自己,我很讨厌这样的形象。我的头发整齐、服帖、乌黑发亮,我的嘴唇有着女人一样的粉红色,我的眼睛像两个电力十足的灯泡,我的面色白得让人羞愧。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些家伙为什么要叫我贾宝玉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形象,我曾经好几天不洗脸,我想让自己变得黑一点,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被生活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
黑键也在偷偷地打量我。他笑了,他说寄宿学校就是好,把你养得唇红齿白的,要是跟着我东颠西颠,恐怕早就饿得皮包骨头了。
果然有一个女人接站。不用黑键指点,我已经知道该如何与他身边的女人打交道了。我走上去,微笑着说阿姨好!我看得出来她很享受我的见面方式,她很夸张地流露出激动的样子,说黑键,没想到你儿子这么大了,几乎比我还高呢,长得真帅啊。黑键对我介绍说,她叫薇。
然后我们去饭店吃饭。我们的背后站满了服务员,我看得出来,薇的财富指数不低。她让我点菜,我毫不客气地点了一道很贵的虾。这也是黑键教我的,点菜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品位,我可不想在这方面给黑键抹黑。果然,薇露出满意的神色。她对黑键说看得出来,你一个人把儿子养得很好,这样的人我喜欢,这说明这个男人有责任感。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表面上看,我似乎是黑键一个人带大的,但事实上,我成了黑键一系列女朋友手中的接力棒。但我不能说出来。
接下来,他们就只顾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只有在想起我的时候,才给我布点菜,加点饮料之类的东西。吃饭真是一项无聊的活动,特别是跟黑键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吃饭,他们要么只顾他们的谈话,视我如无物,要么好好的突然之间风云变幻,最后莫名其妙地不欢而散。
然后他们谈到了过年的事情。薇说我们到东北去吧,我们到冰天雪地的地方过一过真正的冬天,去体验体验寒冷。黑键说太奢侈了吧。薇说你跟我走,怕什么!再说,经过这么些年的磨难,我也该给自己好好地过个年。
你给自己好好地过年关我什么事,你自己去不就得了。
你陪我一起去就是我给自己的过年礼物。
噢,我成了你犒劳自己的礼物了!不去。
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就算是那样,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嗯?去吧,我们一起过个年,在铺天盖地的冰雪之中放肆地过个年。
黑键笑了,他说你不要引诱我,不够坚强是我的弱点。
黑键就这样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薇的赏赐。我真为他脸红,可我没办法干扰他,我只能坐在这里接受他的安排。就像现在,我傻傻地、孤单地坐在饭桌边,听他们安排过年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征求我的意见。等他们决定的时候,我只要像个俘虏似的跟着他们走就行了。一直到离席而去,他们谁也没有问:白键,你愿意到东北去过年吗?
当然,东北也很诱惑我,听说北方的雪像人的手掌那样大,而且落到地上从来不化,我也很想去看看。所以,对于他们的不征求意见我决定不予追究。
薇一招手,侍应生过来恭恭敬敬地送上了单子,薇买了单。她掏钱的动作很好看,涂满指甲油的手指轻轻一捻,几张大钞就从钱包中弹了出来,在空中利索地转了个头,就向侍应生那边望了过去。
吃完饭我们又去购物。薇说白键,我要送你一件新年礼物。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她把我们领到了童装店。我不喜欢衣服,我希望有一套复读机。婕、静,还有以前的那些阿姨,她们只知道给我买衣服,我的衣服已经够穿了,我希望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复读机。班上好多同学都有,每次我向他们借用,他们都会说你那么多衣服,为什么不把买衣服的钱拿来买学习用品。我听了真惭愧,好像我是个只讲吃穿不爱学习的花花公子。
我拿定主意对每一件衣服摇头,让黑键和薇束手无策,然后我假装无意地向文具柜走去。黑键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他大声说白键,我也送你一件新年礼物,你想要什么?我说复读机,我学英语要用。
黑键俯下身来看看价格,说这么贵,我们到别处去买,这里卖得太贵了。
薇果然上当了,她看看价格,说贵什么贵!要买就买好的,否则效果不好。她问服务员: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复读机。确信没有更好的之后,薇再一次掏出钱包。
我觉得自己有点卑劣,但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太想有一套复读机了。黑键是不会买给我的,他总是说不要相信那些广告,学习就是上课,完成作业,好好考试。不要搞那么多花架子,再好的复读机也不如一个勤奋而聪明的脑子,那是广告商用来骗人的玩意儿。他还说他自己就是搞广告的,他可不想让别人用广告来欺骗自己的儿子。我没法跟他讲清楚,为了省钱他总是在对我讲着各种道理,简直用尽了他的小聪明。
买好东西,我们来到了薇的住处。那是一个很豪华的住所,光是卫生间就有两个,简直金碧辉煌。我以为她会让我住众多房间中的一间,结果,她安排我睡客厅里的沙发。
黑键说让他睡床吧,客厅这么空旷,感冒了可不是好玩的。
薇说就睡沙发吧,反正就这么两天,房间收拾起来好麻烦的。
两天?我的假期有差不多二十天呢。慢慢地,我悟出一点话外之音,看看黑键,他根本没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第二天清早,薇笑眯眯地叫醒了我。在靠近窗边的餐桌上,牛奶正在缓缓冒着热气,新烤出的面包散发出好闻的香味,还要其他好吃的东西。我由衷地笑了。薇说白键,我喜欢你笑的样子,你笑起来好像黑键。
黑键也是刚刚起床,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居然还穿着棕色的睡袍。大家的心情看上去都很不错。薇看看黑键,又看看我,说这一幕好甜蜜呀。
黑键说你可以把它定格下来的。
薇微笑着说我很欣赏这一幕,电影中的、生活中的,包括一切我所能够看到的,我都很欣赏。
黑键说叶公好龙而已。
薇大笑起来:黑键,跟你在一起真开心,你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击中我的要害。你在咒我你知道吗?你在咒我永远不能拥有我要的幸福。
这个玩笑过后,薇的情绪明显地急转直下,从此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对我更是看都没看一眼。吃完早餐,我们一起来到街上,我们计划去游乐园,去公园拍照,我们还要去看一场电影。
没等实施计划,我们的情绪在一家旅行社门前彻底遭到了破坏。
黑键指给薇说你看,你的东北大年。薇说真的,该去订票了。然后他们就进去订票去了。
大约十分钟后,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来了。黑键黑着脸,过来揽着我的肩,厉声说:走!丢下薇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我说黑键,又吵架了吧,你为什么总喜欢跟女人吵架呀。
黑键使劲捏我一把,说少放屁!
薇小跑几步赶上来说你也看到的,人家只剩两张票了。
黑键说少来,你就直率一点,说你不愿意带白键去,说你只想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带上一个男人,去过一个他妈的荒淫无度的春节。你就这样直说嘛,我能接受。你这样遮遮掩掩的我反而不能接受,让人觉得特别虚伪知道吧。
好,我就给你直说,我讨厌别人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还他妈的被前夫霸占着,还被他那狗娘养的女人折磨着,我凭什么去服侍别人的孩子?我看他一眼都会勾起自己的隐痛,我给自己的儿子买新年礼物了吗?我跟我自己的儿子去度假了吗?如果我带白键去度假,我会感到我的儿子站在空中谴责我,你明白吗?
薇站在大街上声泪俱下,脸上红一道黑一道一塌糊涂。黑键咬着牙听了一会,突然走上去,把薇揽在怀里,说走吧,我们回去,我们什么也不要想了,我们回去收拾行李,收拾去东北的行李。
我们果真回去了,薇说黑键,我们不去东北了,我们干吗非去不可呢?那里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呢?
黑键却拗上了,他说要去,一定要去,我不想你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唠叨因为我的原因没能去东北。
我不会的,我马上就会忘了这事儿。
得了吧,你要是忘了才怪。
那,就让白键跟我们一起去吧。
他不去,他有他的去处。
黑键提出和我一起去看电影,让薇留在家里准备晚餐。我知道黑键跟我有话要说。我说黑键,让我回去吧。
笑话,你回到哪里去!
每当这时候,我就想起黑键说过的话:白键,我一定要给你弄一个家,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那多半是在他与某个女人分手的时候,我和他搂在一起,穿行在茫茫人海中,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兄弟。而当他从这种情绪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多半又会忘了自己所说的话。可现在,我非常希望他能够尽快实现他所说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那样的家,我们就不用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尽情地睡懒觉,尽情地玩闹。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那样一个家呢?
我说黑键,我能不能回到婕那里去?
黑键不做声,我本以为他会像前几次一样,跳起来激烈地反对我。
你想跟她在一起吗?
我不能说我想跟她在一起,因为那不是我真正想说的,但也不能说我不想,那样的话,黑键会很为难。权衡再三,我说我也应该跟她在一起过一个年吧,我毕竟是她儿子。
白键,你懂事多了。
我知道黑键同意了我的建议。做完这个决定,黑键长舒了一口气,我却惆怅万分。其实,我最希望跟黑键在一起,但黑键有黑键的生活,如果我总是拖着他,妨碍着他,他就会迅速地厌弃我。与其被人厌弃,不如牺牲自己,让人觉得对不起你,这是我与黑键在一起总结出来的经验。
我们去看了“哈利波特”,这场电影更加深了我的惆怅,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待在那个魔法学校,我所遇到的困难,谁也解决不了,也许只有魔法才能帮得上忙。
黑键又在说白键,明年,哦不,就是今年,我一定给你弄一个家,我们再也不用考虑在哪里过年的问题,我们就在自己家里过年。
我说你老是这样说,又不见行动。
黑键叹了一口气,说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建立一个自己喜欢的家并不容易,除了钱,还要感情。可这两样东西都很难弄到手,有时候弄到手的东西不是它自己溜掉,就是保管不善变质了。你懂我说的话吗?
我说我懂啊,我怎么会不懂。
黑键拍一下我的脑袋,说你懂个屁,你要是懂了我倒害怕了。
离过年只剩一天了,我背起了行李,踏上了回程的路途。黑键和薇跟在我后面忙前忙后。我看得出来他们后悔了,他们内疚了,他们好几次差点推翻了自己的决定。但我没有给他们反悔的机会,我要让他们内疚到骨子里去。我像一个急着赶路的大人一样,大步流星地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像两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溜小跑地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着:去死吧,去死吧。
汽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黑键黑着脸一动不动,真的像一根黑键了。薇则小心翼翼地站在离他一步开外的地方,不停地冲我挥手。我懒得举手呼应,我只是盯着黑键看,也不敢眨眼,我怕一眨眼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
天气预报说我们将在艳阳天里过大年
天气预报说我们将在艳阳天里过大年。赶到婕那里的时候,已是除夕前一天的下午了,斜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像一根长长的电线杆子。我敲响了婕的家门,却没有人应声,没办法,我只好来到婕的亲戚家,我曾跟婕来过这里。
婕也不在她亲戚家里,她亲戚,那个我称她为姨奶奶的人说她到李叔叔家过年去了。我说我能不能给婕打个电话?她把我带到电话机前,拨通了电话。婕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她说放假那天我去接你,学校里的人说你已经跟黑键走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婕说我在外省,你跟黑键在一起要乖噢,过了年我就回来,你要不要跟李叔叔说话,我现在在你李叔叔老家。
她居然问都不问我是不是跟黑键在一起!
我说不要。说完忙不迭地挂上了电话,向门外冲去。
姨奶奶说白键,你要去哪里?
我边跑边说回家!
是的,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那个暂时不知道在何处的家。跑累了,我在路边站了下来,脑袋里面一阵乱响。我看见一对中年的夫妻,他们刚刚从超市出来,提着大包小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看着他们,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想结婚,我真想快点结婚;结了婚,我就有了自己的家了,我就能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的家里,想怎样就怎样。真的,我渴望结婚。尽管我才十二岁,但我渴望结婚。
走着走着,我发觉自己来到了静的门口。我想,我就在静这里过年吧,她早就邀请过我,她还说过她的后半辈子要跟我生活在一起。还没有敲门,我就已经对那扇门产生了亲切感,那种普普通通的红棕色,此时是世上最温暖的色调。
正当我举起手要敲门的时候,门开了,门里门外的人都吓了一跳。是那个全哥开的门。显然,我吓着他了,他用手抚着胸口,不停地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静从全哥背后露出脸来:白键,怎么是你?
我一笑,一时间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静把我拉到一边,问黑键在哪里?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告诉我,黑键在哪里,他怎么啦?
我说他要和薇去东北。
静搂着我的手松了,我注意到她的脸煞白,双手发抖。她说你确认那个女人叫薇吗?我点头。
他们现在生活在一起吗?我还是点头。
静说他到底还是欺骗了我,当初他和我分手的时候还不肯承认。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呢?他有什么必要欺骗我呢?难道他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她站在那里,两眼发直,喃喃自语。
我注意到,他们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两个大包就摆在全哥的脚下。全哥说快点啊,再迟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静还在自言自语:再也不要想他了,再也不要心存侥幸了,我恨他,我一定要恨他,我再也不要这样下去了。
她神情恍惚地走到全哥身边,梦游似的挽住他的手说全哥,我们走吧,从今天起,我会永远永远地跟着你走。全哥握着她的手说傻瓜,你不跟着我走跟谁走,我是你老公嘛。看起来她已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
全哥望着我,又望望静。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我急中生智:静,你们先走吧,我要上厕所了,完事后我会给你带上门的。静心不在焉地说好的。我急急地走进卫生间。我听到了他们带上门的声音,接着门又开了,全哥探进头来:白键,注意把门锁好啊。我大声说好的。
他们带上门走了。我忍了好久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然后,我使劲擦去眼泪。现在,这么大一个春节,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得想办法给自己安排一下,哪怕是一个人,我也要过好这个春节。
去你们的吧,还说要跟我一起过年呢,事到临头都自顾自撒腿就跑。去死吧,婕。去死吧,静。去死吧,薇。去死吧,所有的女人们。去死吧,包括黑键。你们都去死吧,我谁也不要,我一个人过年。没有妈妈、没有爸爸,那又怎样,我照样过年。
我掏空了书包,摆好了寒假作业。第一件事,我得把寒假作业做好,像每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一样。第二件事,我得去超市买些吃的回来,幸亏走的时候,黑键给了我一些钱。我准备做完今天的作业之后,去一趟超市,买一些方便面、点心,还有牛奶,也许还有水果。想一想,过年还需要什么?哦,对了,我还需要一些书,我喜欢漫画。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买漫画书了,我可以无休止地看我喜欢的漫画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想到这些,我开始兴奋起来。原来,独自过年,并没有什么值得伤感的;相反,我可能得到更多的乐趣。我还要去网吧里玩玩电子游戏,我已经有好长好长时间没玩那个东西了,现在,谁还管我玩不玩游戏呢?
我在静的小屋里一丝不苟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除夕之夜,我还看起了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节目可真不怎么样,看着看着,我就睡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也就是新的一年了。我吃了一点东西,又准备写作业,没多久,我就感到很闷,觉得再也写不下去了。我想去网吧玩玩游戏。我在锁孔处塞进了一团纸,然后带上门。这样,我就不至于把自己锁在外面进不来了。
网吧里的人真多,热气腾腾的,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这才真像过年啊。我赶紧找了个空位,坐了下去,刹那间,我觉得快乐极了。
我听到旁边座位上的男孩在嘟囔:烦死了,又在叫回家,才刚刚玩了两盘。另外一个附和着说真是的,真羡慕那些孤儿,没有人管,自己当家做主。
我看了他一眼,笑了。
结果,我在网吧里度过了三天三夜,真快活啊,要不是饿得眼睛发花,我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我到一家饺子馆吃了两大碗饺子,才捧着撑歪了的肚子回到静的房间。然后,我一觉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已不知今夕何夕。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写作业了。
语文寒假作业里,有一篇作文名叫“寒假趣事”,我想了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个人没有妈妈可不可能?不可能,除非这个妈妈不要你。
一个人没有爸爸可不可能?不可能,除非这个爸爸不要你。
一个人不过年可不可能?不可能,除非这个日子能从日历中撕掉。
如果妈妈不要你,爸爸不要你,地球也不能因为你的原因把这一天跳过去不算,你将如何度过这一天?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没有妈妈,那又怎样?没有爸爸,那又怎样?只要你还在呼吸,只要你还向往着快乐,你就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哪怕没有年夜饭,没有压岁钱,没有鞭炮,你照样可以有你的快乐。
似乎有点像“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开头,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已决定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从这个春节开始。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