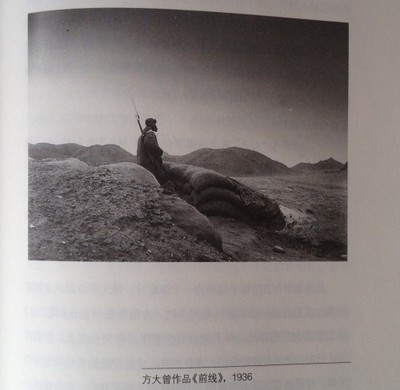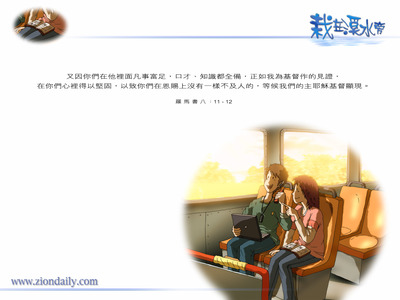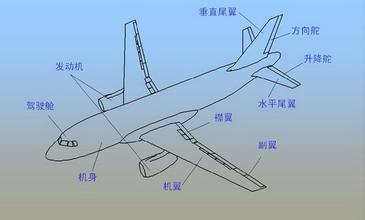就这本书,我谈点个人感受:
1
这部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改科学家们一贯的“温良敦厚”的研究论文作风,尽可能以直接了当的方式罗列证据和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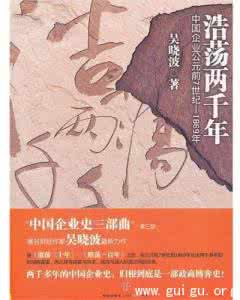
一般的科学论文讨论,即使不同意同学科中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及其解释,大家都会很谨慎的考虑到自己或许也有出错的可能。何况科学问题越是复杂,涉及的因素越多,在没有极其严格充实的证据(这在科学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所谓“越特别的见解,越要求苛刻的证据”)支持,而一个实验只能解释一个理论假设/或验证某个事实时,对于具有基础性的理论的否定或是建立,大家会越是谨慎。另外,对于任何假设或是推论,必须要由坚实的实验或观察证据支持这个大前提,大家都不会不赞同。此外,通常当科学家们要对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研究发言时,也会比较谨慎,因为学科有学科的专业规律和研究路数(所谓discipline),一个学科能建立起来并存在下去,一定有他的道理。这里的前提,是在学术界中讨论问题,大家都互相尊重对方,因为有以下共识:
1)受过良好训练;2)长期从事某一具体问题和专业工作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点是要揭示客观规律或实现其学科固有的科学目的;3)应当按照事实和逻辑来讨论。然而,这本书所批判的“文化研究”“建构主义”对于以上这些共识并不承认。不承认倒也罢了,更其令科学家们无法接受的,是“科学文化研究者”们肆意歪曲、解释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自然世界的某一部分)及其研究方法,而且是以极其狂妄和无知的态度。举例来说,当我们在一篇科学论文当中使用某一专业术语,运用某个特定的数学公式来进行数据分析时,我们的结论并不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术语、公式就自然而然得有了正确性。我们必须定义使用这个术语的条件,也必须给出这个公式的适用范围。而评审这篇论文的专家,也将从这些方面来评价文章的“科学性”是否有问题。然而,在建构主义者那里,“语言”“语词”就等同于有了一切,比如当使用了“混沌”这个词并对之展开各种夸张的修辞和评论,就可以由此引申出大段的对混沌研究及其“社会影响”的结论,这是任何科学工作者都无法接受的。因为在科学上“混沌”这个词的背后,指称的是一系列数学过程及其物理描述。如果要分析、判断“混沌研究”对社会进程发挥了一些怎样的影响,就不能回避对其在数学上和物理上的科学内容的讨论。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位做这种“研究”的”科学文化研究者“都不能正确理解那怕一条最基本的混沌数学定理。《高级迷信》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了大量类似的案例。
2
如果仅仅是玩点学术游戏,大家也就算了,毕竟都要出来混饭吃嘛。最为麻烦和有害的,也因此而不可能得到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原谅的,在于搞“文化研究”和“建构主义”的这帮人,他们的行为,如果不加以严肃的批评,将对社会和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造成具体的伤害。原因无他,否定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将导致各种迷信的泛滥,一旦造成反智和反理性的社会风气,不仅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各种技术进步将极大放慢,对我们生活便利性乃至基本安全有极大用处的技术产品将不再有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我们已经完全依赖于科学的各种产品支撑这个社会的今天,如果大多数普通人不了解科学,我们连民主自由这些今天大家认为最可宝贵的东西都会被绑架。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家试想想看:今天地球上已经有75亿人且人口还在暴涨,然而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怎么喂饱这么多人,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科学上的最佳答案:1)提高粮食产量;2)控制人口。就单以粮食产量来说,科学界一致的共识是:转基因技术是最佳解决方案,因为传统育种技术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而转基因技术无论在其安全性还是技术成熟度上已经都比较完善了。然而,这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涉及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很多知识。如果在一种正常讨论的环境下,大家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相信大多数人会承认转基因技术的确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然而,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我不用赘述,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我只提及一个事实:南部非洲有上千万的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大量儿童饿死,粮食可以救他们的命,有人从美国运去了粮食,免费的粮食,可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宁可要自己的人民饿死,也不要一粒粮食进口,因为这些粮食是美国人餐桌上的转基因玉米。这样的事情今天可以发生在非洲,十年二十年以后也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发生。问题的关键是这样:当你要饿死的时候,是救命更重要?还是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以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统计学概率估计在遥远的未来(几十年后)可能会发生的“风险”而“饿死而不食周黍”呢?你希望你的政府宁愿你饿死也要坚决在家门口把这些粮食挡回去吗?你愿意被一群人选举出来的“民主”的政府,以”我们的选民都讨厌转基因食品“为由而剥夺活下去的权利吗?(有一篇短的,却是不错的新闻写这件事,参看: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9910/266761)
3
语言和偏见:不可否认,这本《高级迷信》的语言是激烈的,有些评论今天看来也多少有些偏颇,比如其中论述有关艾滋病领域的文化建构主义、相对主义和同性恋的章节,看得出来,作者对80-90年代搞同性恋艾滋病运动的一帮人的行动策略很不以为然,其中一些有关艾滋病流行病学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时。另外,在评论Foucault(福柯)时用了“自轻自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Foucault是我早年很喜欢的一位哲学家,Damien大概是很清楚的,算是我人生中某个阶段的偶像),这在今天看来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批评,有失偏颇(但这本书出版是在1994年,毕竟是二十年前)。不过瑕不掩瑜。仍然以两位作者在艾滋病这个章节中有关治疗、预防的主要分析来看,20年后的今天,他们观察到的,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因建构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反科学的运动操作策略导致的危害,今天已经愈演愈烈,并且尤其是在中国正在发生极坏的影响。比如:各种有关保健品中草药的迷信、对正规抗病毒治疗效果的怀疑、亲信各种偏方和验方,以及基于偏见而非科学证据对于抗病毒治疗政策发表见解。。。
4
由此引开来的:为什么爱白应当坚定不渝的传播科学理念,并与科学界结盟?可以肯定,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各种思潮和促进社会变化的运动不断兴起和发展的十年。我们想要这个社会变成怎样?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对同性恋的社会环境、政策和政治气候?这些,都是作为同志组织的爱白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我对此的回答是:远离各种极端主义,通过小的、逐步的进步,与科学界一道来推动同志权益和个体的发展。原因无他,未来的社会政策决策者中的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由科学家来扮演的。
5
我想引用这一段书中的原话来结束这封信,这段话讲的是艾滋病,可是作为例子,极为传神的描绘了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为什么反科学的做法会对受影响的每个人造成危害,以及科学本身对于弱势群体有何价值:“这种对科学的明显敌意-无论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多么合理-使得原本就十分恶劣的(艾滋病防治)局势更为恶化,使得从未明朗过的前景更趋暗淡。总有一天,我们要为行动主义者们日甚一日的无为对抗付出代价-一种将以原本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来计算的代价。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已经开始付出代价了,其衡量标准就是那些拒不接受正规的治疗方法,反而去寻找这样或那样的”替代疗法“(指中草药、特定的饮食、保健品、大量维生素甚至是巫术-江华按)。在目前,当然还可以抗辩说,这样的选择带来的损失还不算大,因为所谓正统的医疗方法对于抵御艾滋病也没有多大效果(有效的多药联合抗病毒治疗是199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才被发现,1997年以后才逐渐在大范围内得到应用-江华按),而这些替代疗法或许至少还能令艾滋病病人保持希望,从多活上那么几个月的宝贵时光。但这种心理平衡总有一天会被打破,因为我们总会找到一种正规的医疗方法(两年以后这种方法就出现了),从而即使不能从根本上避免HIV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至少也会大幅度延缓其发作的时间。到那时,最大的输家就是那些不明事理、热衷于医学江湖骗子所谓的”替代疗法“的人,正如同那些数以千计听风就是雨的癌症患者一样-他们争先恐后地涌向那些配发苦杏仁苷(一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无效的癌症疗法-江华按),或是涌进暗室去接受射线治疗,结果死得更快...正如全部的经验事实清楚显示的那样,在战胜疾病方面,科学是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手段中最有效的一种。我们还知道,作为本书批判对象的那些“科学批评”,尽管染上了各种政治色彩并有着浓重的理论味道,但在这一方面(指解决疾病问题-江华按)却完全无济于事。(“科学批评”)其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哪些志大才疏的文化批评家们的尚方宝剑,使他们在抵御艾滋病的斗争中既可以四处抛头露面充当名流,同时又不必劳神费力地去做那些苦差事,例如:为了掌握医学或分子生物学知识而放弃文学批评的乐趣。就艾滋病悲剧二言,这类“批评”或许也并非毫无作用,他们可以使某些陷入绝境的人们借机发泄郁积的情感,而他们也的确需要发泄。但是,要根本解决艾滋病危机,我们需要在化疗、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免疫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否则就无法拯救世界上数以百万计(如今是数以千万计-江华)的HIV感染者,也无法拯救其余数以千万(如今是数以亿计)面临HIV感染威胁的人们,而上述”科学批评“在推进类似研究进展方面,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
以上浅见,欢迎大家讨论、批评和指正。
作者江华医学博士,外科副主任医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