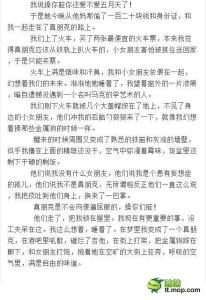年夜饭,一年中唯一一顿需要筹谋的家宴
文/罗毅

年关将近,前些日子老母亲来电,询问过年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竟一时间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无暇去思考除夕那晚的一饭一食。现在想起来,倒觉得那天有些冷了老母疼儿的心思。
与友人聊起除夕的年夜饭,友人说起想念自家还健在的外祖母。闻言,想起外婆还在世时,腊月里给我纳鞋底做新布鞋的样子。深感这俗世洪流,有多少人依然还过着候鸟的日子。梦想与亲人,两边都如山一般重。
不过春节到底是春节,每个在路上的人,内心都应该有一桌最能安心意的年夜饭吧。只要那一晚大家围着圆桌坐下,一年里无处安放的心,总能廓然安稳了。
抛砖引玉,先来说说我家的年夜饭,这顿一年里唯一需要筹谋的家宴。
传统年夜饭中的鱼菜,最首要的是一条鲤鱼,为的是“年年有余”和“跳龙门”的好彩头。
首先鲤鱼要新鲜,通常都是早几天,从菜场买回两斤左右的活鱼,家养几日,让其吐尽腹内的泥腥味。因不给它吃食,“瘦身”后的鱼,肉质紧实,更能做出好风味。
年三十早上收拾鱼,做糖醋鲤鱼的糖醋汁,入锅炸制,焦香脆嫩。
不过,旧时的年夜饭中,整鱼上桌是“看菜”,一般年三十的晚上是不能对其动筷的,为的是图个吉祥兆头,所以不能破了鱼身。
只是一桌饭里,鱼总是要吃的。既然“看菜”不能动筷,便另取老腌菜坛子里的老雪菜,剁得细细的,挤干多余水分,铺在一只大碗的碗底,再垫上片好的冬笋片,最后放上一截新腌制的海鳗——它有个好听名字:“鳗香(即是鳗鲞)”。浇上黄酒,其它调味料全不用,隔水蒸半小时,撒上葱末便能上桌。鱼肉片片紧致,耐品,它的咸鲜味,也最能撩醒了味蕾。
鱼鲜就酒,最能安人心绪。慢咂酒,筷尖细拈——这一年里,最应珍惜的无忧日子。
年夜饭中的冷盘看似并非主菜,其实它的丰盛程度,最能决定满桌的气氛。通常取当年自家腊制的鸭胗、香肠、酱油肉(瘦)、香肚等,蒸熟后改刀切片,依次呈扇形整齐码放入大盘。也有头夜里卤制好的酱牛肉、酱豆干,片好依次排列入盘。
不过,满盘的酱色虽都是美味,总还是少点亮睛的颜色——可以取上好的翠绿苔干(贡菜),泡发后,挤压去多余的水分,热水焯烫,放凉,用盐、醋、糖、芝麻香油凉拌好,整齐码放进冷盘中。一片红酱映翠色,最是能醒眼诱惑家人的食欲。
一桌年夜饭中,总是离不开肉丸子。无论直接蒸食,还是油炸了另作配菜,或是汆汤,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将新鲜荸荠洗净削皮,细细剁碎,与手剁的肉馅按照1:1的比例拌匀。肉馅用猪小里脊为好,无肥,又嫩。若是贪一口肥肉的香,取五花肉去皮剁馅也可。混合好的肉馅中加盐、蛋清、少许淀粉,再加入新酿出缸的糯米甜酒。将肉馅按照顺时针方向不停搅拌,直至肉馅被搅出劲道后待用。
每个肉丸子轻揉成乒乓球大小,滚上淘洗好的三色糯米,装盘后的每个丸子上点一枚枸杞,上锅大火蒸15分钟便可。出锅前,靠着锅内剩余的蒸汽,撒上香葱末,可以瞬间熏出清冽的葱香。
以前每到炸肉丸时,香味飘过,孩子们都会借着“帮忙”的好由头,伺机在厨房里偷食几枚炸好的肉丸。
做完肉丸子,剩余的肉馅留着做蛋饺,这通常是我的份内活。一碗蛋浆,一碗肉馅,几块刷油用的肥肉,一个不锈钢的大勺。煤炉里的火不能大,尚红渐灭的时候最好做蛋饺。
左手持大勺在炉火上烧热了,夹一块肥肉在勺子内壁上,不断抹上渐熬溢出的猪油。取出肥肉,往勺子里浇上两汤匙蛋浆,持勺的手迅速转晃起来,让蛋浆在勺内形成一张圆圆的蛋皮——动作要快,不能让蛋皮彻底熟透了。
筷子挑一坨肉馅,置于蛋皮的中心,小心挑起一侧的蛋皮,迅速包裹起肉馅,并用筷子轻轻压紧蛋饺的四周,直至蛋皮熟透并粘连在一起。这样才算是做好了一个蛋饺。现在想起来,这该是我少年时,做得最细巧的手工活了,有时候竟做得比大人都要好。
“炒素”这道菜的叫法,是随着母亲延承来的。其实这道菜中有荤,不过味道素口,这或许是它的叫法由来。
此菜力求清淡素口,又不能损了各种食材的原味鲜香。首先将笋片和肉皮下油锅大火煸炒,笋片易碎,所以煸炒时要轻些,会颠锅者最好。浇入一大勺高汤,焖烧一会,为的是让笋片渐释出它的自然鲜味,肉皮也能释放些胶原蛋白的胶质。再放入白菜帮子和荸荠片。放入盐、黄酒、少许味精、葱段,勾上一点薄芡即可出锅。装盘后,淋少许香油。
“炒素”在满桌众荤中,最能清口下饭,通常此菜在年夜饭吃到半程后上桌最好。白菜帮子脆口,荸荠清甜,炸制膨化后的肉皮饱吸汤汁,冬笋的鲜美自不必细说。因为加了葱段,全菜清清白白,而金黄的肉皮,和淡黄的冬笋片错落其间,让全家人在已过半程的年夜饭中,再次勾起举筷的强大动力。
“炒素”之味其实是个巧劲,各取了不同食材的原味,糅合着互补在一起,并不做太多重口烹制。这道菜在整桌年夜饭中,虽算不上什么重量级的大菜,但是母亲对上菜时间的把握,却是来源多年里对家人口味的了解——不让难得相聚的一顿饭草草了事——母亲在整场年夜饭中所用的微妙苦心,一晃便坚持了这么多年……
煨好一锅做“热锅子”的底汤也不容易。将剁碎成小块的猪骨,加入泡发好的小香菇、枸杞、黄芪,三两颗红枣,一把泡发好的干贝,还有先前剁下嚼不动的冬笋蔸子,加足水,用过去江南常见的土制砂锅文火煨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汤白骨烂,满屋香气氤氲。
整桌年夜饭里,不能没有个“热锅子”,全家人迎着腾腾的热气,没开吃前心里便是暖着的。
摄影/徐宇峰
通常饭桌的正中间放上一个电热锅,将煨好的骨汤悉数倒入锅内,再加入白菜叶子、蛋饺、粉丝、炸好的肉丸子等。一人盛上一碗,先暖了肠胃。接着在余汤里加入半暖瓶的开水,再扔进一块剔干净肉的腊骨头——因为已经有了个冬笋蔸子在汤里,便算是一汤二吃,等着它变作“腌笃鲜”时继续再战。
酒过三巡,桌上那些渐凉的菜,也可一并锅里涮热了继续下酒。至于到了年夜饭的尾声,用这锅汤泡饭佐味,也绝不输于闽菜里的那道“佛跳墙”。
家常的“热锅子”,不似馆子里的各种火锅和汤锅子,有无卖相根本不重要,只为了一家人聚首,吃着鲜美、暖和便是最好。
父母渐老,已经不似从前那么行动方便,因此操持一桌家常的年夜饭是一件尤其辛苦的事情。早几年我想一旁帮忙,或是代为,母亲都不让,非要亲力亲为。这些年,开始让我一边看着,传递些食材什么的,开始认真教我每道家味的制作程序,和烧制的窍门与要点。
陪父母一起做顿年夜饭,记下几代人默默沿袭的家味。想家了,自己做顿好饭,吃到家乡的味道,就像是回了家。
封面图/黄丰
内文图/《舌尖上的新年》(除署名外)
编辑整理/风物君
END 本文版权归地道风物(didaofengwu)所有,欢迎转发分享,转载至其他平台请于微信后台留言,勿擅自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