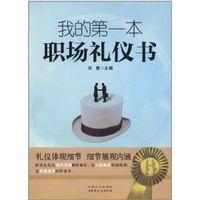今年春节,我回杭州住了几个月。我的母校是杭州大学,今称浙江大学。应副校长罗卫东的邀请,为学生作了一次《红楼梦》讲座,主题是“《红楼梦》是曹雪芹苦难童年的梦”。没有讲稿,也没有充分准备,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最后一节讲的是《红楼梦》与莫言,也只随便说了一点感想。回京后,朋友间有闻知此事的。孙玉明兄对“《红楼梦》与莫言”这个题目很感兴趣,要我整理成文给他。于是才有了这篇浅陋的不成熟的文字。
必须说明,我既非为赶时髦,也不是对莫言有过多少研究。应该老实承认,在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作品我连一个字也没有看过,只看过电影《红高梁》。获奖后,为对这件我国文坛上破天荒大事了解个究竟,我买来十几部他的书,包括他大部分长篇小说,且花时间将它阅读了一遍。
我年轻时曾有过读世界文学名著的狂热,西欧的、旧俄到前苏联的、美国的,任何大部头的作品到手就啃,从来吓不倒我。近几十年,随着年岁增大,读得越来越少了。莫言所提到的对他创作影响较大的许多作家作品,如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都没有读过,视野还是很狭窄的。所以,我读莫言作品,第一个感觉是小说居然也可以这样写。
莫言对现代小说的大流说,是超越的,或者可以说是“异类”。比如死去的人可以与活着的人同时存在、对话,被枪毙的恶霸地主可以凭“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却又经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现实……如此等等。乍一看,好像与《红楼梦》毫无可比性。但再仔细一想,《红楼梦》对当时的小说传统而言,又何尝不是超越的、是“异类”?莫言的超越与异类,是明摆着的,一眼就可看出 ;而《红楼梦》的超越与异类,不是当时人用习惯的老眼光就能看透的,其创新的真相要经过多少年、多少人的错看、胡猜、碰壁和研究探索的深入,才逐渐地显现出来。

我国旧小说是与传记体文学密切相关的。写的都是前人的事、他人的事或传说中的事,与作者并无关系。罗贯中没有见过诸葛亮、曹操,施耐庵也不认识宋江、林冲,吴承恩更与孙悟空、猪八戒搭不上界。《红楼梦》作者却像现代小说家那样,以自己切身感受的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是《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我国古典小说跨向现代小说的里程碑的重要标志。
但在当时,除非是了解作者家世兴衰、尤其是他写作小说情况的亲近者,外界对这种独特的创新是不知道也看不透的。小说故事展开的场景是如此宏大,是“天上人间诸景备”的洋洋大观,而其中的人物形象又是那么生动逼真,以为必有真人真事为原型。于是索隐小说命意的目光便集中于皇家豪门、权贵名流。说是写顺治皇帝与董小宛故事的、写纳兰家事的、写张侯家事的、写当朝名流的等等说法相继产生。所有这些误读,恰好从反面证明了《红楼梦》的超越与异类。
现实是无从复制的,生活是无法实录的。只有虚构才能将它表现出来,而表现出来的已不是现实,而是想象。
莫言在强调想象与虚构在创作小说的作用上,有个看似有点极端却很能发人深省的有趣的例子。80年代初期,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党自成立日起,有 28年都在战争中度过,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素材,但他们的好年华被“文革”耽搁了,已没有精力创作了,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该怎么办呢 ?
莫言写道 :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 ;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 ;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我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我狂妄无知,说我是“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说我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悬崖上。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说。
…………确定了这个框架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的初稿。(《我为什么要写〈红高梁家族〉》)
莫言的创作心灵是极其自由的。敢想敢写,天马行空。他在接受拉美一些著名作家小说的影响后,更敢放胆大展拳脚。一个常被评论家提到的名词,叫“魔幻现实主义”,这倒让我想起曹雪芹来。
“现实主义”且不论,“魔幻”二字,套在《红楼梦》头上,似乎有点尺寸不合。但“幻”字好像倒还合适。
梦幻、虚幻、幻境、幻笔……哪一点不与《红楼梦》相关 ?
脂砚斋在甲戌本《凡例》的末段中解释此书首回回目隐义、被后来诸本误作正文开头的那段话,便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道人持“风月宝鉴”给贾瑞治病,借以喻此书有正反面不同视角,说是此镜出自太虚幻境。脂评说“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点明小说乃虚构而成。(第 12回)
贾宝玉非曹雪芹自己,也非有什么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脂评说得很清楚“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 19回)宝钗、黛玉也是虚构的,也没有什么苏州姑娘为“原型 ”。脂评说 :“(宝)钗、(黛)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第 2回)又有批 : “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矣。丁亥夏,畸笏叟。”(第 22回)所谓“使二人合而为一”,指钗、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疑虑、隔阂而互相心灵沟通、贴近,成为知己。对“合而为一”说不同意,可以讨论。但不可否定的是极亲近作者的批书人并不以为钗、黛真有其人,乃是 “幻笔”,就像书中宝玉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一甄一贾一样,都属“幻笔”。小说的男女主角都是虚构的,其他角色就更可想而知了。
人物是如此,小说中那些经典画面、精彩的细节描绘也无不如此。无论是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卧裀、刘姥姥初进荣府,也都可看出并非出自作者对现实的描摹,而是出自其丰富的艺术想象。黛玉葬花不必说,宝钗扑蝶也是在增删过程中后来加进去的。在明义读到《红楼梦》早期稿本中,尚非如此。他看到的情节还是“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 ;尽力一头还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题红楼梦》之四 )后来才改小蝶为大蝶,变过墙为过河,去掉了遗却扇子的事,而成了无意中听到滴翠亭中私语情节。湘云醉卧的描写,尤值得欣赏。书中写道 :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 : “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第 62回)
这幅充满诗情的很美的图画,并非依照自然环境常态来描绘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别的不说,光是所需飘落的芍药花瓣,再多几十倍怕也难合成。可谁又会去挑剔作者的文笔过于离谱呢,就像人们不会讥贬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诗句一样。刘姥姥初入荣府堂二屋,令她“头悬目眩”的种种景象,更不是长年浸泡在这种富贵环境氛围中的人所能有的。
由此,我更领悟到作者“满纸荒唐言”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仅仅是大荒山的补天石幻形入世、一僧一道、太虚幻境、鬼判索命、风月宝鉴……等等才是“荒唐言”,整部小说从头到尾的描述,无不都是植根于现实的谎话,所以才下“满纸”二字。正是在这一点上,接受《封神榜》《聊斋》影响更明显的莫言小说,才与看似完全另一路的《红楼梦》有相通之处。
莫言写农村、下层人民,在愚昧落后中往往透露出人性的光辉,就像从污泥塘中冒出来的莲花。《红楼梦》中也常能见到这种闪光点。有一次,有人问我,你以为《红楼梦》与《金瓶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红楼梦》能让人感动、流泪,而《金瓶梅》不能,虽则它也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书。莫言小说中的人物,除了那些作者深恶的腐败官吏外,其他人物几乎都揭去了贴在他身上的政治标签。什么恶霸地主、反动部队的头目、匪首、顽固走单干路的钉子户、刽子手等等,都被写成了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秉性邪恶、天生十足的坏蛋、怪人。这又使我想起鲁迅说过的那些话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我国红学受近代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超过半个世纪以上,逐渐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我说过,“反封建”是就作者主观认识上说的,是说作者对作品的命意。其实,曹雪芹哪里知道什么是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叫他去“反”什么 ?至于小说中有很多写到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的种种黑暗、腐朽的不合理现象,尤其是写了一个离经叛道、常常说些嘲讽封建传统观念的“疯话”、“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贾宝玉,让人看到这个大观园女儿国终将幻灭,从而可看出我国封建制度大厦必将逐步走向崩溃的发展趋势。那是另一回事,那是《红楼梦》的客观社会意义和巨大艺术价值之所在,并非作者主观上命意如此。
与认定作者有反封建命意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也被分为两大阵营 :反封建的首领,自然是贾宝玉,被拉入“同盟军”的则有黛玉和晴雯 ;其余大批人物都被划入封建制的代表或“卫道”者,其中被贬斥最多的当数宝钗和袭人。吕启祥君写过一篇相当有深度的评论《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为薛宝钗挽回名誉不少。谈袭人而有新意的文章还少见。倘有时间精力的话,我倒很想试试,题目或可称之为《换一个角度看袭人》。因为我觉得袭人蒙受的冤屈太大,长期来各种评论对她的讥贬且不说,光是小说后四十回续出的描述,也将她糟塌得够了。而这与曹雪芹本意,实在相距太远。我很看重书中写到她的第一笔: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第 3回)
“心地纯良,克尽职任”这八个字真是难得准确的定评。我真佩服得了不得———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许多人的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对我怒目而视地说 : “蔡义江,你这是想标新立异吗?你还记得你自己以前对袭人是怎样说的吗 ?”我老实地回答:我一点也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不过,我以前写的书中确确实实说过不少讥贬袭人的话,看来还是深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所以,我把自己归属于正想从僵化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的人。在这一点上,莫言给了我不少启发。
莫言的童年是非常困苦的。他说他自己是梦想一天能吃三顿饺子而开始写作的。但童年的经历对他创作的影响,却是刻在骨头上的。他在《超越故乡》一文中引用过一些话:
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 :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金蔷薇》)最著名的当数海明威的名言: “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
我在浙大作红学讲座的题目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苦难童年的梦》。应该说明,这题目是早在读过莫言文章前就有的,与十年前纪念雪芹逝世 240周年的拙作《不幸造就了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个意思,只是与近来才读到的莫言文章凑巧合辙而已。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现在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仍存在相反的认识。
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同我“苦难童年的梦”的说法,而认为应该是写他“幸福童年的回忆”。这里关系到曹雪芹的生年早晚问题。我认为雪芹出生于雍正三年( 1725),曹获罪被抄没、家庭剧变时,他才三四岁,什么也不懂,也记不清什么了。而相当多的人则相信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 ( 1715),家变时已十三四岁,很懂事且有不少记忆了。不同的认定原因很复杂,有关考证,这里不谈。从理论上说,考虑雪芹童年应该是幸福的还是苦难的,哪一种对他在创作上更有利,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主张作者早生者,最主要的理由是他有过亲身经历,熟悉“风月繁华之盛”的生活,有利于其创作。而我则持相反意见 :熟悉生活有那么重要吗 ?比起感受生活、梦想生活来,它简直连重要也谈不上。熟悉,便不新鲜,便会麻木,便视若无睹,便漠然了。这对创作是不利的。还是举刘姥姥初进荣府堂屋的例子吧:
才入堂屋,只闻得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 : “这是个什么爱物儿?有啥用呢?”正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到唬得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说: “奶奶下来了。”…… (第 6回)
多么精彩的描述啊 !从这段文字看,究竟是熟悉堂屋内焚过香、有各种摆设,还挂着一口自鸣钟的环境重要呢,还是刘姥姥独特的感受?她的感受是早就熟悉这儿环境的贾宝玉、贾蓉等人所能有的吗 ?刘姥姥的感受不就是创造这一场面的小说作者曹雪芹自己的感受吗?他是从哪里体验到和想象出来的呢?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居钟鸣鼎食之家,久而不觉其风月繁华之盛。这道理还用得着说明吗 ?《红楼梦》中有许多重要场景都是通过旁观者的见闻形式来表现的,即使只是石头见闻,也特加提醒。这实在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角度与技巧问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