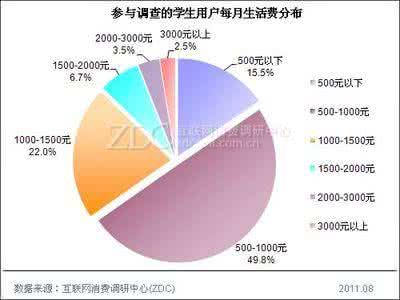
人生、时代与社会学——成伯清教授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2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演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相信,这种设问方式,马上会让你们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的,"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确实,这个时代,用简单的三句话来说,就是: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坏,总之,越来越快!
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有普遍的冷漠,也有爱心的井喷;既有日新月异的沟通手段,也有不断加深的人际隔膜;既容易在人群中陷入孤独,也可以便捷地成为好友;既有知识信息的爆炸,也有灵魂深处的枯竭;既有无数向上流动的案例,也有各类二代现象的盛行;既有无比辉煌的发展成就,也有无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既有民主化的呼声,也有官本位的加剧;既有追求超越功利的美好情感的倾向,也有屈从工具理性的相互算计的趋势;这个时代既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又让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了选择的无奈;这是一个理想可以即刻变为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普遍丧失理想的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人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时代。道在何方?哪种职业最适合自己并能带来最大的幸福?我相信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困惑!在这个时代,自称能够教别人怎么生活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人生,越来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幸福与否,全凭自身的感受。
但是,每个人的自我感受,显然是极为主观的,甚至是不足为凭的。此时,参照和参考别人的观点和评价,也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一个深层的悖论:我们越来越个体化,但是,我们却越来越依赖于别人来判断我们自身。社会学家早就说过,这叫他人导向性格(other-directed character);用今天流行的说法,这叫做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来概括这种特征,它们都显示了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了解人群和人心的重要性。所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代越来越碎片化,甚至有人宣传社会性的终结,但也越是昭示了和证明了社会学的必然和必要。所以,祝贺你们,无论你们是选择了还是被选择了社会学院,你们会因此而更加了解自己的时代,也因此而更加靠近自己的存在和灵魂!
其实,这个时代的最大困境,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障个人自由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又维持美好的共同体生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只是在我们这个急剧转型到所有人都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直接冲撞着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方才有了"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之类的说法。
其实,社会学之在西方的最初出现,也是源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如果不考虑现在社会科学思维的客观性和系统性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毕竟,这种历史条件惟有在启蒙运动之后方才具备--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的第一位社会学家,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潘光旦先生曾经比较过荀子与两千年之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的相似性。严复最初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显然是因为荀子所谓"人能群""民生有群"的说法。荀子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期,一个礼崩乐坏、天翻地覆的时期,也是一个百家争鸣、重估一切价值的时期。庶几与当今类似!所以,社会学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即在动荡和变迁之中,寻求稳定与和谐的可能性。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当分三步走,即首先确立市场经济,然后建立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当然,这个顺序并非简单线性的,而是有着相互回馈、彼此强化的关系。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几乎累积到了临界点的诸多矛盾,显然难以套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予以解决和解释,而必须采用社会学的视角。但是社会学做好准备了么?对于一门刚刚恢复重建三十年左右的学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沿用一个成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或体系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社会学必定是一门永远年青(eternal youth)的科学,需要在应对现实问题中不断发展自身,不断转换理论视角,不断发明新的技术手段。所以,你们不是来学习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工作体系,而是来参与中国社会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创新的。当然,这不是鼓励你们目空一切,而是要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来度过大学生活,即如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不断与学科的大师对话。大学,经常有人引用梅贻琦的一句话,即"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而今天,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所谓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之所谓缺乏大师,并非知识功底不够,甚至也非创新程度不足,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生产的条件,客观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大师,我们已经彻底犬儒主义化了;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从未亲炙过温润而泽的大师风范,无从领略一种让人心悦诚服的魅力;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有些人并不真正希望有大师出来破坏"以吏为师"的大好局面;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太多的人自诩为大师,而且也借助大众传媒昙花一现地炒作成了大师;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学科分工日益精细,难以出现具有超领域影响力的学者;最后,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还不能达到康德所说的启蒙了的状态,还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直面这个时代!呼唤大师,是一种心理的未完全断乳的体现。其实,大师的存在也未必处处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学我者死",不仅是在书画上如此,在所有需要创新的领域,都当如此。大师,就其十年寒窗成为大师而言,或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其功成名就作为大师而言,恰恰是我们应当挑战的!总之,留心去学,三人行必有我师,间或还会巧遇大师;不用心去学,满图书馆的大师巨作,也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社会学,虽然向来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强调社会情境对于个人的影响乃至强制作用。但是,跟时下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从而没有任何人需要对此负责不同,社会学最终教会我们的是自主和自律。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事实上,惟有弄清社会机制如何影响和决定个人行为,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和抵消我们所不希望的社会影响,形成和强化我们所向往的社会效应,找到撬动现实的支点,真正迈入自由之境!
社会学以研究社会如何影响个人为手段,最终的宗旨应是个人的解放。真正的社会学,不会将个人设想为异己的社会势力操纵的傀儡!社会确实以各种方式在我们身上施加影响。譬如,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社会出身,即便是出生于同一个家庭,出生顺序即排行的不同,也将我们放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试想,做老大和当老小,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需要满足不同的社会期待。当然,同一个社会的成员更为重要的差别来自社会阶层。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平等。有人含着银匙出世,有人可能出生低微。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若论家庭的社会分层,肯定也是参差不齐的。出生富贵的同学,是否可以沾沾自喜,庆幸自己的命好呢?出生寒门的同学,是否应该妄自菲薄,埋怨命运不公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出生寒门而能考入南大的,在不利条件下作出同样的成绩,说明你很勤奋,富有进取心,也可能很有天赋;家境优渥的同学,如果真是持有现代理念,讲究个人成就,估计不仅不会以自己父母的社会地位而自我炫耀,反而可能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焦虑;你很不幸,父母已经具备了很高的起点,你要超越,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恐怕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其实,个人出身的差异,相较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潜力,有时真是微不足道!我们不能选择拿到怎样的牌,但我们可以努力打好手上的牌!最终的结果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
当然,上述这番议论是作为励志话语专门对你们来说的,因为南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否属于这个社会所谓的经营,至少你们已经可能获得优越于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机会。别的不说,南大作为985学校,从国家的特殊资助来说,就是特权学校。你们不能只享受特权而不回报社会,你们应当对自身具有更高的要求!对于社会的一般民众,当我们看到牌的分配太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社会公平对待所有的成员。我们目前最为恶劣的现象之一,就是阶层的固化,社会生活的马太效应日子明显,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教育获得的机会以及教育在实现社会流动的作用上,也是问题重重。而这正是社会学可以显示自身社会价值的地方。通过对于邪恶的社会逻辑的揭示,社会学可以成为促进公平和正义的力量的助产士!
大学教育,绝对不是在为你们三年或者四年以后就业做准备,而是在为你们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而作准备。那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需要决定社会的重要选择,而你们的决定可能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简言之,你们的境界将会决定我们这个社会所能达到的美好程度!而我认为,一个人在大学期间,也就是专门的修道时期,能够达到怎样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一生所能达到的境界。同学们,任重而道远,此之谓也!
那么,大学,这个专门修道的时期,也就是接受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的时期,该当怎样度过呢?请让我引用一段列奥-斯特劳斯的话来与大家共勉:"作为与最伟大心灵持续不断的对话,人文教育乃是一种满怀谦逊的训练。同时,人文教育也是一种胆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毅然冲破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名利场的喧嚣、浮躁、轻率和苟且!人文教育要求我们勇敢,这意味着决心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或者将普通意见当成至少与最陌生和最不流行意见一样可能出错的极端意见。人文教育是从庸俗中解放出来,古希腊人关于庸俗有一个绝妙的好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意思是缺乏对于美好事物的体验。人文教育就是赠予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体验。"其实,荀子也说过,"君子之学也,可以美其身"。
当然,作为社会学者仅仅"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为创建美好社会而贡献绵薄之力!
成伯清,男,1966年出生于江苏通州。1985年进入南京大学少年部(现为强化部)就读本科,初习自然科学,后改社会科学,于1989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方向为社会心理学。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进修。1997年开始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情感社会学。主要讲授本科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生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名著选读”等课程。 个人著作: 1、《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消费心理》(与李林艳合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译著: 1、《父亲与女儿》(阿普尔顿著),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与社会政策》(威尔逊著)(与鲍磊、张戌凡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主要学术论文: 1、《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天津:《社会学与现代化》1992年第3期; 2、《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文化差异》(与乐国安合作),辽宁:《社会科学缉刊》1994年第5期; 3、《对话与意义》,北京:《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 4、《价值观念与越轨行为》,载于《当代中国社会越轨行为》(乐国安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5、《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载于《社会心理学理论》(乐国安主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6、《现代西方社会学有关大众消费的理论》,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7、《现代消费与青年文化的建构》(与李林艳合作),北京:《青年研究》1998年第7期; 8、《另一种精确——齐美尔社会学方法论札记》,南京:《社会理论论丛》2001年第1期; 9、《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0、《社会学的修辞》,《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社会学》(第三卷,2004年)转载; 11、《“消费社会”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2、《“风险社会”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3、《社会学的历史与理论》,载于童星主编的《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4、《福科对社会学意味着什么》,《社会》2004年第8期 ; 15、《隐喻与社会想像》,《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7期; 16、《全球化与社会学想像力的拓展》,《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转载 ; 17、《中国文化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现代社会理论研究》(日本),2004年总第14期; 18、《现代性与全球化关系之辨:从地方性的角度看》,《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9、《纪律与现代性》(署名成然),《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20、《新启蒙运动?当代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布尔迪厄的用途”,作为“导读”载于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3、《从乌托邦到好社会——西方社会建设理念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4、《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25、《乌托邦现实主义:可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6、《从他者的他者到文化自觉》,载于周宪等主编《语境化中的人文学科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7、《“不通家法”及其他——学术札记五则》,《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6辑; 28、《世界社会的中国式想象——《大同书》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社会学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29.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30.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31.没有激情的时代?——读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32.“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 33.“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9期; 34.“‘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人民论坛》2011年第6期下; 35.“城市隐喻与发展策略”,《学海》2011年第5期。[2]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