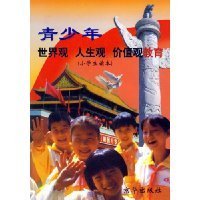战略网、大同网、儒家网……
作者:诸玄识 阅读数:22549 发表时间:2015-04-02 22:38:08
(一)朝鲜战争的十大意义
1.安全震慑。成功抗击头号强国和西方阵营。这也是日俄战争和世界大战之后的“否定之否定”——欧美无法战胜东亚!从此,中国是“军事大国、威慑性强”,因而变得相对安全(减免致命外患);因为自从二战结束以来,都只敢打“边缘战争”或局部战争,而尽量避免“大国交锋”。
2.军事转型。晚清以其“传统模式”,无法应对近现代的“全球战国”。中华之救亡,必需“组织力与动员力最大化”的战争机制。在内忧外患中进行“转型”,难度极大,阵痛致命。国民党是过渡期,共产党完成转型;而朝鲜战争则是对其“检验合格”,确保中国胜任于现代战争。
3.确立主权。中国于1943年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但不包括苏俄;后者却变本加厉地胁迫国共两党再订辱约(1945年和1950年),扼住中国的生存攸关的地缘政治(蒙满回疆)。然而,中国崭露头角于朝鲜战争,变得举足轻重;苏联也觉得其腹背有恃无恐,亚太严阵以待,也就废除了这两个条约(但不包括蒙古)。
4.拯救奇功。朝鲜战争巩固了苏联东线,使之重心向西,亦遏止东欧倒戈;而且尤在军备竞赛上,让苏联“延年益寿”,直到中国能够“接替”为止。此话怎讲?二战的苏联战利品仅是破旧厂矿,美国囊括轴心国的科技,军事潜力乃相形见绌。但作为“二战延续”的朝鲜战争,则耽误美国十多年(常规军工,没有升级)。赢得时间的苏联便反超美国(卫星上天)。
5.奠基强国。通过了斯大林所设计的“中美冲突、战火考验”,新中国就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另类,成为“苏中兄弟”。由此,中国获得苏联的物质和技术的大宗援助,虽是半途而废(担忧中国强大,养虎为患),但也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包括两弹一星及飞机制造),打下了底子。
6.冷战赢家。朝鲜战争使中国从“冷战走卒”升为要角,从而具有自由结盟或变换阵营的价值与可能性,亦形成“平衡两霸、鼎立三分”的潜势。中国站到哪边,哪边就会“得胜”。最后,中美结盟,钳夹苏联,使越战撤军的美国反败为胜,而实际上则是“中国崛起”抵消“单级霸权”。
7.平衡杠杆。自从朝鲜战争,中国在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她总是站在最危险一方的对立面,从而防止战争毁灭;这也使其自身获得两霸的“轮流扶植”,奠基工业与国防(原子弹)。由此,中国能够促进核武的“恐怖平衡”,而致“冷战善终”,实际上是“中俄换位”。
8.霸图梗塞。美国宰制世界,须遏制“大国崛起”;其战略是北约与亚太“合围”,令其对手重蹈两次大战的德国两面受敌之覆辙。但朝鲜战争予以“永久否定”——美国军事无法深入大陆。中俄两国具有岿然之地利,除非它们“内讧”;但那也是“角色互换”,美国虽胜犹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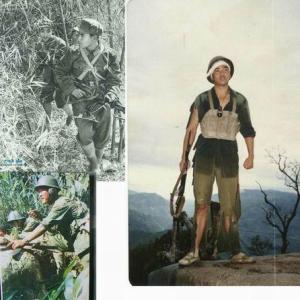
9.海权丧钟。朝鲜战争使海洋霸权被“边缘化”于亚太海洋,而不能向着大陆越雷池一步。鸦片战争以来的炮舰政策基本失灵。麦金德称,大陆一旦能够做到有效自卫和机动联通,则扼制它的海权就会被淘汰。基于同样的趋势,美国在朝鲜战争后所打造的“岛链”,也将形同虚设。
10.亚太纪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加紧营造东亚边缘的“地缘政治”,注入“西方优越性”,成就了日本与四小龙。再因朝鲜战争使美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它只好伺机与中国结盟,而让她参与“全球循环”(市场、投资、技术等)。由此,曾是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心的东亚,而今生龙活虎般地绽放潜力。
(二)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
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新中国不打朝鲜战争,从而不与美国对立;中国很早就会统一台湾,并且很早就有机会进行“现代化”——卷入世界市场、参与西方经济的现代化(如今“和平崛起”)。这都是“以今论昔”的一厢情愿,脱离历史的有机联系之想当然也!
我在此提出,若非朝鲜战争,中国一定会亡国;反之,这场战争预兆了中国成为“冷战的真赢家”!这难道是“耸人听闻、荒谬绝伦”吗?
首先须知三点:第一、对于朝鲜战争,新中国没有决定权,而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直到他死后,苏联当局因为不堪负重,才同意尽快结束战争。第二、这场战争是斯大林策划,让金日成发动“朝鲜半岛统一战争”的;但斯大林的意图不是为了朝鲜,亦非针对西方阵营,而是“考验新中国”这个曾“清洗俄系、钟情美国”的毛派政权。第三、追根溯源,美国是朝鲜分裂与战争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因为罗斯福总统于大战末期设计了这种损人利己、荼毒东亚的世界格局。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因,我们争论南北双方谁侵略谁,或者,盖棺论定于是金日成的“初发难”,这些都没有意义。追源祸始,是美国造的孽(朝鲜半岛的分裂及其战争的火药桶,是美国一手设置的)——当美国决定颠覆中华民国的时候,顺带也就颠覆了流亡重庆的、在当时具有唯一法统的“朝鲜半岛统一政府”。1943年底,蒋介石请求罗斯福总统把“朝鲜独立”写在《开罗宣言》上,被否定。虽然罗斯福建议,朝鲜半岛应由美苏中英“四国共管”;但稍后的德黑兰—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秘密外交”,就使之变成了“美苏分割”——分别挑选了李承晚和金日成作为“代理”。在日本投降时,美国拒绝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光复半岛(其领导人以个人身份返回祖国,却被暗杀)。
在1945—50年间,南北双方都急于实现统一,冲突不断;但都被美苏两霸分别压住,就怕演成新的世界大战。只因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按理说,由苏联鼎力援助的这场革命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共产阵营”(特别是苏联的大后方——东北亚);但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在骨子里是亲美的,这对唯恐“两面受敌”的俄罗斯是生命攸关的,他不能不想方设法让新中国与美国火拼,他才放心。所以斯大林才唆使金日成“实现统一”。恰值苏联有了原子弹,使其国防获得保障。尽管如此,在朝鲜战争中,苏联尽量保持“中立”;当其确信美国不会“大打”,苏联才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实施援助。
我们再看冷战的结果,那就是:苏联解体、美国获胜和中国崛起。然而,美国赢得冷战似是而非,因为美国的冷战目标有三:A.缓解核武毁灭;B.实现单极霸权;C.证明西方优越。第一点是“全球分享”(依旧是核武的“恐怖平衡”),而第二和第三则被“中国崛起”基本抵消。
中国是从绝对逆境中开始“逢凶化吉,龙腾虎跃”的,而且能动性地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站到哪边(结盟两霸之一),哪边就会赢。最后(1970—80年代),在美国越战撤军、西方阵营颓势、苏联势力席卷的情况下,中国发挥了拯救的作用——中美结盟与中越战争则扭转乾坤。中国因势利导,刚柔变易,而使自己成为“冷战的真赢家”!这一切都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因此,就算是朝鲜战争在战场上“打成平局、不分胜负”,其历史影响和它给中国所带来的“战略收益”,皆是不可估量的,乃至“扭转乾坤、开辟纪元”!
(三)新中国捍卫民族独立
对于朝鲜战争,最不想打的是毛泽东,但是,斯大林断定他亲睐美国,藕断丝连,才让他赴蹈炼狱;最想打的也是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把他置于逆境,宰割中国,他必须大有作为。刚从莫斯科“签约脱身”的毛泽东,又被斯大林驱使让他与美国打仗;啊,这岂不是就像《三国演义》曹操让刘备带兵打仗一样,放虎归山,形成鼎立吗!(物极必反,塞翁失马。中国独特的历史感与辩证法)。
新中国的成立,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远未完成“独立”,甚至可以说,在1950年初,中国倒退到了自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的状态。新中国并非“自由国家”——1945年美苏英三强所定《雅尔塔密约》(影响冷战始终的“雅尔塔体系”)不仅把中国置于“铁幕”之中,而且让苏联控扼朝满蒙疆等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何况这时实际上主宰东亚的斯大林是其平生最瞧不起中华民族的!——因为两点:Ⅰ.刚经过世界大战的摧折,又打内战,国力虚脱,经济残破;至少苏联是无法承受如此双重劫祸的。Ⅱ.斯大林原不希望国共易帜、倒蒋拥毛;只是蒋介石没有给他“安全感”(拒绝访苏邀请),他才不得已装备其所厌恶的毛派势力的。
1949年春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很希望投怀于美国(先前有过美好的“延安经历”Yan'an Experience——1944—45年,美国使团在延安);但美苏英三强早把中国置于“苏联体系”(牺牲中华民国),以换取西欧的非共产化。由此,斯大林才把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注入了中国革命,而使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因而,斯大林痛恨毛的“脚踩两只船”;他尤轻蔑“解放战争”,因为是“美苏共谋”:美国捆绑国民党(军火禁运),而让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
194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原本是争取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统一”的,即:他希望达成两点:A.苏联废除它与国民党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蒙古独立、苏控满洲等);B.苏联支援新中国“解放台湾”、遏止美国。斯大林予以拒绝,其理由之一是:苏联与中华民国的条约是依据美苏英三强所订的《雅尔塔密约》的,所以苏联不能单方面予以改变。毛泽东被置于莫斯科郊外“冷宫”近两个月,由周恩来签下“不平等条约之最”才走人。确认旧条约,增添新内容;占中国版图近半的边疆即将分离(第17条),让苏联扼住中国地缘与国家命脉。如果理解成“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军事同盟”,那似乎情有可原。
然而无论如何,两个月的噩梦般的身临其境(犹如“虎穴熊窝”),使毛泽东恰如蒋介石于1923年访苏所领教的那样: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践起来,却也是牺牲弱小民族来捍卫“泛俄罗斯”民族主义(所谓“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是对人不对己)。从那以后,毛在中苏友好时则确保“独立自主”,在中苏恶交时则清理“亲苏同志”。历史重复,如出一辙:蒋介石也是,访苏、并且获得大力援助(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等),数年后反目成仇,另择盟主!
不仅如此,就像斯大林精心设计、促成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那样(防止日德两国夹攻苏联),他安排了令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唆使金日成南侵)。而且,就连中国参战的时间都由斯大林决定的:如果金日成能够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美国不介入),则中国无需参战。这意味着什么呢?苏联在地缘政治上形成对中国的环压钳制、可令其窒息;待苏联从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时,它就会对中国“蟒吞虎咽”——实现其对旧中国未遂和新条约所写的内容。
幸亏美军反击,朝鲜危亡,毛泽东才有了这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虽然武器、后勤极为落后,缺少士气高亢,而赴死悲壮;在军事上算是打个平手,恢复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然而它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这场战争严重地挫伤了超级大国的军威霸气(也间接地震慑苏联)。在军事之外,中国则是“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乃至“一本万利、彪炳千秋”。首先是,因为这次战争几乎是拯救了苏联(下文详述),也使它免于远东的后顾之忧、因而倾力向西(苏联的国际斗争的重心转向其正面——控制东欧、对阵北约);恰值斯大林死,故而赫鲁晓夫政府不仅废除了除了蒙古独立和沙俄割地之外的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内容),而且还大量援助中国的工业与国防(也为两弹一星奠定了技术基础)。其次是,新中国从冷战中脱颖而出,从原先的配角晋升为要角之一;从此独立自主、自由结盟,再经过几个回合,竟然成为冷战的真赢家!
(四)走向“冷战的赢家”
如果中国不打朝鲜战争,或者她在这场战争被打败;那么,在往后的历史中,姑且不谈苏联会易如反掌地肢解华疆这一点,中国也是极其被动和危险的。军事上,中国无疑是处于非常逼近的威胁、恫吓之下,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与时间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的,中国也就无缘于现代化与“和平崛起”。
此须说明:在地缘政治上讲,美国这个海洋霸权是从大洋彼岸来宰制全球的,主要是宰制“旧大陆”——麦金德称为“世界岛”。朝鲜战争在这方面等于是对美国“画地为牢”——它恒被“边缘化”于亚太的海洋一面,而不能向东亚大陆“越雷池一步”。麦金德预测,海洋霸权将会受到“陆权”的致命挑战。朝鲜战争不仅是海权、陆权逆转的前奏,而且决定了越南战争的美国失败。后者是因为美国不敢把战争扩及到印度支那的后方(美国唯恐触及“中国红线”),从而无法切断越南方面的战略补给(越共的战争资源与潜力源源不绝)。美国在此局部,与其说是和越南打仗,不如说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阵营打仗,它怎么能不输呢!从长远的观点看,朝鲜战争犹如是对美国的海洋霸权“预判死刑”。
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两国的“兄弟关系”才确立起来,因而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虽然半途而废,却也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在冷战中崭露头角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谁胜谁负的“关键变数”——中国站到哪一边,哪一边就能赢。
苏联害怕中国“崛起”,而且实际上也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广土众民”之生龙活虎;所以,它很快就中断了援助,中苏分裂。美国先是幸灾乐祸。但在苏联的核武竞赛、星球大战和输出革命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时候,美国从中苏对抗升级中获得了“历史契机”——把中国拉倒自己一边;在毛泽东看来,“脱苏入美”正是久怀夙愿,不亦乐乎。
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和西方对中国的“回报”皆是异常巨大的。西方对中国的回报,众所周知,是参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西方阵营对中国“门户开放”,然后才有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对美国的贡献是:使苏联腹背受敌,拖垮其计划经济;1979年中越战争,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凡此,使美国能够从越战失败的颓势中重整旗鼓,反败为胜。
(五)朝鲜战争是国史的里程碑
让我们回顾一下华夏历史的“军国机制”(战争机制):
A.战国至秦(战斗序列: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B.传统文明(太平模式:仁政德治,民间自治)→C.现代体制(转型阵痛: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
亦即:从“战国七雄”,中间经过两千年的高度文明的“天下太平”的管理模式,到20世纪中叶的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苏俄模式(国民党的半传统的精英机制→共产党的总体战的全民机制);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否定之否定”,旨在使得中国能够克服有史以来的“最大忧患”。若非如此转型,现代中国就会“开除球籍、亡国灭种”(当然,中国人民必须忍受伴随着“转型”而来的惨烈阵痛及其所致的内耗)。
进而言之,这个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为特征的现代中国的战争机制,草创于国民革命与苏区暴动,展开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被“验证合格”于朝鲜战争。当然也是集大成于“列强军事”——国民革命、苏区暴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者,均得力于苏俄;另外,抗日战争及其之前,国民党又分别受到德国与美国的军事训练(稍后大批被“改编”成为解放军);再加上1944—45年,美国军事人员在延安的培训;凡此,在很大程度上都汇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而投入了新中国的对外战争。
解释一下,总动员与一体化的战争机制(动员力、组织性、全民型、除派系和反间谍等)。如果说,中共是95%,国民党是45%,晚晴是25%(传统中国是15%。战国至秦是85%)。所以相对来说,中共适合于现代之“全球战国”之大型战争,此前勉强或相反。另一方面,总动员与一体化的战争机制是双刃剑:其比率越高,则它的负面与社会阵痛,皆越大(人民忍受,学者批评)。西方(西欧、美国)因其“海洋地缘”优越,内部及内外交通免受致命威胁,而人民则一致对外;故而,总动员与一体化的战争机制虽然较低,却能够“事半功倍”。
朝鲜战争才真正使那受害于列强的屈辱国史,划上句号。这话怎讲?晚晴以中国文化传统的“治平模式”来应对“世界战国”,犹如羊入虎口;北洋政府有幸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又不免战后被宰割;虽然国民党北伐统一、抗战救国、废除辱约和参组联合国,但“雅尔塔密谋”则令中国更严重地重蹈《凡尔赛和约》之覆辙;不错,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不久,她就被斯大林强加于“不平等条约之最”,而且被绑上战车,充当炮灰。(根据该条约,中国丧疆大半,人口减亿,军政窒息,经济殖民。参见:诸玄识:如何看待伟人忍辱负重)
鉴于中国不失时机地为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排忧解难,苏联在1954年废除了这个最后的由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前的救亡图存,则得十丧九,或得不偿失,而愈坠深渊;直到朝鲜战争才根本扭转(始于1943年的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波三折,这才画上句号)!
综述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世界各种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总源于战国七雄(如兵马俑)。所谓的亚述和罗马等的军国主义,那都是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被发掘出来的,因而需要“重新固定一切价值”。民族主义在近代欧美达到极致。其部落族群→民族国家,归因于中国,引进“水利社会”的管理机制,而且四大发明为之奠基:纸与印刷使血缘转为地缘,火药与指南针牵引对外征服,带来了组织力与动员力。由此,社会契约(组织动员)→民族国家(争夺霸权)→军国主义(应对危机)。
秦代以后的传统中国是,把国家观消融于天下观,把民族主义消融于世界主义。直到近现代之“救亡图存”,孙中山实行“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从天下观及世界主义退却到国家观及民族主义。国民党是上述转型的中介——力图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朝鲜战争则是转型的“合格检验”:中国的战争机制(仅指组织力和动员力)能够压倒他国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1930年代苏联红军对日本的“牛刀小试”,证明“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天敌。而朝鲜战争不管其本身得失,则似乎确证“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是一切其他战争机制的巅峰与克星。但毛的这种“救亡利器”是双刃剑,因而中国人民不得不忍受剧烈阵痛。
关于朝鲜战争的中国战力的发挥,请允许我“再客观些”;那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天时”,或者说在军事行动上是“最佳时机”。有一则印度寓言说,猎手捕捉巨蟒须等它进食后不久、因而“战斗意志消沉”时,着手进行。国共内战中,共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尚未过瘾,全国解放。休整几个月再打朝鲜战争,这是最佳状态(当然,有些部队尚未充分休整)。而对方阵营距离上次战争已有四年多了,则相对松弛。可否借此机会为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讲些“公道话”?此时,共产党是“养兵千日、血气方刚”(一直拿小股“顽固派”练兵);而国民党则是长年鏖战(例如1944—45年的“一号作战”和西南反攻),无暇休息,抗战转内战,则无疑是强弩之末。
(六)进一步说明朝鲜战争拯救中华
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对于冷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论者都对此认识不清。
新中国之初,她仍是“弱国无外交”:身在江湖,大国棋子,被迫充当马前卒。但朝鲜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一战而定乾坤,从此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于霸主来说,中国可谓“以弱制强”,即:它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一个相对的均势格局与“恐怖平衡”。新中国以军备劣势和巨大生命代价与压倒一切的强霸,打成僵局或“平手”,其意义远在军事之上。朝鲜战争是拯救了中国、苏俄乃至整个世界,这些多为学者们所忽略。
重申: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拯救中国”?第一、新中国把美国的军事威胁推到了她的“致命地缘”之外。自从冷战开始,美国对亚洲的战争冒险仅限于“边缘地区”而非大国本身;而自从朝鲜战争,中国一跃而为军事大国,而美国则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不打不成交”。朝鲜战争证明了中国具有极大的战争潜力和已形成现代的“军国机制”(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先秦战国就是如此。中间的两千多年,中国转入高度文明的“文治”)。从此以后,新中国能够较为主动和平等地利用机遇,而与超级大国结盟——“战国策、以夷制夷”:1950—60年代“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并促成工业化与“两弹一星”;1970—80年代“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遂开始现代化与“和平崛起”。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却鲜为人知,即:朝鲜战争使新中国挣脱了斯大林为她套上的随时可扼死中华民族的“绞索”。实际上,新中国之初乃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最危险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苏联。新中国被催生于形成“冷战”的国际阴谋之下——美苏英三强把战胜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推入“铁幕”。不久,毛泽东访苏,希望废除旧中国与之所订的条约和得到援助于“解放台湾”;斯大林不加理会,反而置毛于“冷宫”,数月后更强加新中国于“不平等条约之最”,并把其绑上金日成的战车。在此情况下,倘若新中国不能有所作为,那苏联恢复战争创伤之际,便是中华民族最惨厄运之始——它根据新辱约而鲸吞之、蚕食之。
假如中国在朝鲜被打败,则美苏要么火拼而变中国为废墟,要么妥协而以中国为俎肉,自然是后者而非前者。坏事变好事。苏联见新中国战力可恃,能助一臂之力,恰值斯大林死;于是赫鲁晓夫于1954年访华,便废除这个大有可能造成“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不平等条约。
让我们从反面来透视朝鲜战争的正面意义。请允许笔者做这样的推测:假如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打败,结果会是怎样呢?当安理会表决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时,苏联代表弃权,而非一票否决;这既是放纵中美冲突,又是自留后路。进而,倘若中国被打败,如果美国尚未下决心发动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话;苏联绝不会为了中国,而与美国火拼的;倒是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与美国妥协——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和1945年《雅尔塔密约》之更全面地故伎重演!果真如此,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很可能是:美国直接控制朝鲜半岛和台湾,苏联直接控制东北、内蒙和西北;剩下来的“汉地”由国共两党“划江而治”,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的“缓冲区”(避免世界大战)。至于策划“边疆灭汉、炎黄相屠”,倒是白人帝国主义的拿手好戏,就像1860年代与1940年代的回疆屠灭,乃至美洲印第安人的悲剧!
斯大林似乎有上中下三策:下策即:中国战败,美苏共管,但这会冒世界大战之风险;中策是:打持久战,消耗美帝,但苏联会越来越卷入漩涡之中;上策为:中国获胜,或复原状,从而苏联确保远东安全,不会腹背受敌。达成“上策”意味着,斯大林消除对毛的猜忌,中国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正式成员”(苏中兄弟),并且接受援建工业与国防。但异乎寻常的是,斯大林倾向于“中策”(不让停战),因为他知道,中国一旦羽翼丰满就会独立自主,乃至“勾结美帝”;斯大林最希望中美两国重蹈中日战争之覆辙——他(共产国际)谋划而促成的、并且苏俄大力援助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以免德日两国夹攻苏联。幸亏斯大林死(1953年3月),苏联也不堪负重于战争援助,所以朝鲜战争按照“中策”收场。然而,中国的势态终究是朝着斯大林“近忧远虑”的方面演变的:苏联援建→中苏分裂→中美结盟→苏联解体!
(七)朝鲜战争拯救了苏联
朝鲜战争拯救苏联与1979年中越战争拯救西方阵营,及其两者对中国的回报之极大,我们可以等量齐观。
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拯救苏俄”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创巨痛深,国力虚脱;而美国实力则急剧膨胀,压倒一切,争霸无敌。根据秘密外交而分赃战果,苏联囊括欧亚大半陆地,美国掌控西欧与世界海洋;这样,苏联不仅处于战略被动,而且面对着西方阵营的东西钳制、两面受敌。
再是抢夺战利品:苏联劫掠德国与满洲的工矿设施,而美国则令西欧科技与纳粹人才(例如冯·布劳恩)“入吾彀中”;这就使美国的军事机器压倒苏联(原子弹相差了4年),斯大林遂换上“恐美症”,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不仅为苏联解除后顾之忧与腹背受敌,而且尤在军备竞赛方面拖住和耽误了美国,从而为苏联赢得时间,使之后来居上、反客为主(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
进言之,战后初期,美国本可以凭借其无比先进的科技,进行军工升级,大力开发航空航天领域,而置它的战略对手于绝对的“落后挨打”之田地;果真如此,“苏联分崩离析、美国不战而胜”至少提前20年(苏联一旦不能显示其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大家庭就会首先从东欧开始解体,而波及苏联内部)。但作为冷战的第一个“热点”的朝鲜战争,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延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的精力财力集中于“常规战争”上;而且朝鲜半岛的复杂山地也使当时的新兴科技“没有用武之地”,这也令西方良久忽略科技与军工之全面升级。
当然,苏联过早垮台,对中国并非是一件好事——中国不可能获得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利用、扶植”,美国也不会让中国挣脱“铁幕”(雅尔塔体系)的,而是始终拒她于世界市场之门外。朝鲜战争后,美国为了巩固其所控制的“亚太边缘”(遏制大陆),就把“西方优越性”予以分享(日本及四小龙等);这是后来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地理”的前提——1970—80年代,为了对抗苏联,中美结盟,美国就把中国引向以参与世界为条件的市场经济之中(西方对华开放和最惠国待遇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