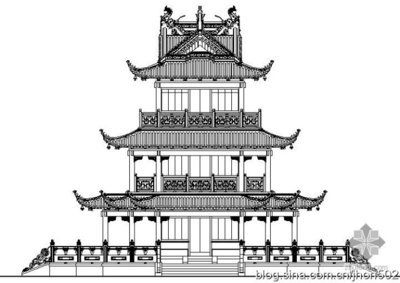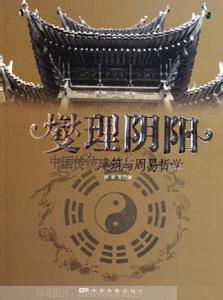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与中国古代建筑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人所认识和体悟到的宇宙,是从古代的建筑推及出来,并从人工的建筑中建立自己的宇宙观。在先民的认识中,宇宙即是建筑的放大和扩张,建筑即是宇宙的体式和模型。
在中国古代关于宇宙模型的学说中,有一种很有影响的学说,即“盖天说”。“盖天说”的思想基本上保存在《周髀算经》中。此书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或秦朝。汉初以前,这种学说长期占统治地位。虽然此书已亡佚,但从后代著书中的称引和文字可以了解大概。
《晋书·天文志》引东汉蔡邕《周髀》说:“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言天似盖笼,地法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聩,三光隐映,以为昼夜。”这种说法是要说明宇宙像是一个覆盖在地上的建筑。由此还出现了三个不同说法,如认为天盖斜倚于地,形成倚(欹)盖说;认为天像拱形的斗笠,成为笠盖说;认为天是平的,像车盖,即方天说。其中笠盖说是盖天说的主流,它认为天地都是圆拱形的,中间相距八万里,中高旁低,中间比四方高二万里。北极是天顶,中国在地中心的东南方。笠盖说就是把宇宙看成一个像蒙古包一样的大房子。这三种说法的核心即在于认为宇宙是一个大房子,日月星辰都悬挂在“天幕”上。这是先民们从建筑中来推想的。
留园鸳鸯厅的南部梁架结构
古人有“天似穹庐”的说法,即是盖天说中所说的笠盖说。“穹”,是指物体中间隆起,四周下垂的样子,“穹庐”即是指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汉书·匈奴传下》:“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因为“穹”的形状与古人所认为的天相同,所以常用“穹”来称引天。如称上天为“穹”,也可称为“穹天”、“穹隆”、“穹苍”,等等。古代的一首民歌唱得很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初原始人看天穹,有如一个倒扣着的锅,大地是平的,这种直观感觉就是天圆地方。这些都一以贯之地反映出古人把宇宙的模型比拟成建筑的形状来说明。
“宇宙”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齐物论》中:“旁日月,挟宇宙。”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一书已佚,当为战国时代的著作,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对于“宇宙”一词最早的解释。《庄子》一书中“宇宙”一词出现过多次,在《知北游》中曰:“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在《列御寇》中曰:“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这里以宇宙为外,又把宇宙与太初对举来论说,显然,这里所指的宇宙指客观世界而言,与今天的“宇宙”一词无大区别。《庄子·庚桑楚》对于“宇”和“宙”提出了很好的解释:“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郭象注:“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宇”是有实在而无定处可执者,“宙”是有久延而无始末可求者。“宇”是整个空间,“宙”是整个时间。综合起来说,宇宙即是整个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经典释文》解释这句话曰:“《三苍》云:四方上下为宇,宇虽有实而无定处可求也。《三苍》云:往古来今曰宙……宙虽有增长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这段话还是在说明宇指空间,空间是实在的,但无定处可求;宙指时间,时间是延长的,但无始终可说。从现代的角度来说,也是相当科学准确的,这肯定了空间的实在性、时间的延续性及两者的无限性。
古人对于宇宙的说法还有几种,但对于宇宙的认识却是从建筑空间来说明的。
《管子·宙合》篇曰:“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急,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出。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橐”即指袋子,“天地” 像一个袋子一样,包罗万象地将客观事物都囊括其中。这个“天地”又被囊括在“宙合”之中。“橐”在“橐天地”中是动词用法。同样的话,荀子也有阐述。《荀子·解蔽》:“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裹矣。”《说文解字》曰:“裹,内衣也。”《急就篇》卷二颜师古注曰:“衣外曰表,内曰裹。”此处的“裹”即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亦即包裹之义。前人多把此“裹”解释为“里”,差矣。“合”即今天的“盒”字,它们是古今字的关系。《说文解字》曰:“合,合口也。”从甲骨文来看,下面的“口”像器皿之口,上面像盖形,用盖儿盖上口儿,本义就是“盒”。这种盒子是方形的,有四个面,再加上上下两个面,即为六个面。古代人又常常把天地称为“六合”。《广韵·合韵》曰:“合,亦六合。天地四方对也。”把宇宙称为六合,也是由“穹庐”演化推衍而来的,“六合”即是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成玄英疏曰:“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唐代韩愈《忽忽》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云。”有时也用“六合”来代指天下,汉代贾谊《过秦论》曰:“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些说法也都是从小的空间向外延伸为大的空间的。

《墨子》一书也论及到宇宙。在《墨子》书中《经上》云:“久,弥异时也。”《经说》:“古今旦莫。”《墨子》中的“久”,相当于“宙”,“弥”即弥满,此处指时间弥满了一切不同的时间,无论是古今还是早晚。《经上》又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东西南北。”也是指空间弥满所有的地方。《墨子》的说法,也即是《淮南子·齐俗训》中所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与《尸子》的说法是一致的。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古人似乎也意识到语言表达的矛盾性,既然宇宙是无所不包的,那它就能够将万物都包裹住,既然能将万物包裹住,那它还是有限的,但宇宙应当是无限的。古人也曾想解释这个矛盾。扬雄《太玄》中称:“阖者,关闭也;辟者,开辟也。”他试图用这样的说法来说明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并不是认为时间有个起点。张衡在其所著《灵宪》中说:“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认为宇宙可以超越人们能够观测到的有限天体达到无限。可以观测到的天体是有限的,而整个宇宙是无限的。
上面主要从古人对于宇宙的论说当中,寻找出古人的宇宙观是从房屋建筑的空间角度出发来看的。我们还可以从语源学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特别是记录语言的文字就更是保留文化信息的信证。汉字是一种尚形尚意的文字,文字形体的创制反映了古人的思想意识,文字形体一旦产生,作为历史的记载就不易改变,通过汉字形体来了解古人对自然、社会等的认识,是相当可靠的探寻途径。
“宇”和“宙”当初就是指房屋建筑的。“宇”和“宙”的表义偏旁为“宀”,发音为mián,《说文解字》曰:“宀,交覆深屋也。象形。”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正像房屋有了顶、墙的形象。徐复、宋文民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一书“宀”字下注曰:“据半坡村仰韶房屋遗址复原,乃在圆形基址上建墙,墙上覆圆锥形屋顶,屋顶中开有通窗孔,下有门。此种建筑外露部分较少,因而深密,故许君云:‘交覆深屋也。象形。’”徐复先生的说法一方面说明了许慎说的“交覆深屋也”的根据所在,另一方面也从考古学的角度说明了古人关于宇宙盖天说的依据,还是根据当时的房屋形状来说的。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宀”字下注曰:“凡屋深者,则幽暗不易见物,故宀之为言也。”
宇,《说文解字》曰:“屋边也。从宀,于声。《易》曰:‘上栋下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豳风》:‘八月在宇。’陆德明云:‘屋四垂为宇。’引《韩诗》:‘宇,屋也。’高诱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引申之,凡边谓之宇。宇者言其边,故引申之义为大。”“宇”作为屋檐来训释,有许多根据。现举几例:《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杨注曰:“宇,屋边也。”《淮南子·览冥训》:“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高诱注曰:“宇,屋檐也。”也有的干脆就把“宇”称为房屋。《玉篇·宀部》:“宇,屋宇也。”《素问·六微旨大论》:“故器者生化之宇,谓屋宇也。”这种径直把“宇”称为房屋的说法是一种引申用法。《诗经·大雅·绵》:“聿来胥宇。”孔颖达疏曰:“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楚辞·招魂》:“高堂邃宇。”王逸注曰:“宇,屋也。”这些都说明“宇”字最初与房屋有关系。按照最初的说法即是《说文解字》的说法,就是指屋檐,与“宙”同样都表示房屋的建筑部分而又有所分工。《淮南子·览冥训》:“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高诱注曰:“宇,屋檐也。宙,栋梁也。”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
也有人从音训角度来区别“宇”和“宙”。汉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李善注引张载曰:“天所覆为宇,中所由为宙也。”把“宇”认为是天所覆盖的穹庐,《释名·释宫室》曰:“宇,羽也。如鸟羽自覆蔽也。”这是音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与古人说法相同。“宙”音训为“由”,也很有见地。
再说“宙”。《说文解字》曰:“宙,舟舆所极覆也。从宀,由声。”这与上面所引《淮南子·览冥训》中高诱注“宙,栋梁也”有区别。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本字下注曰:“《史记正义》引无‘覆’字,馥谓‘覆’别一义。当云舟舆所及也。”桂馥认为“极”为动词,即是说“宙”是指舟、车所达到的地方。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说:“宇宙字从宀,其本义自谓宫室,《淮南子》说是其明证。引申之乃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二中说:“宙字从宀,本是宫室之象,后人借为往古来今之号耳。”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本字下把词义演变说得清楚,他说:“然则宙之本义为栋,一演之为舟舆所极覆,再演之为往古来今。”这是说许慎把演变后的意义当作本义了。“宙”字是形声字,所从声为“由”,“由”声中有义。《说文解字》中无“由”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补“由”字说:“其象形、会意今不可知。或当从田有路可入也。《韩诗》:‘横由其亩。’传曰:‘东西曰横,南北曰由。’毛传:‘由,作从。’”《左传·昭公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杨伯峻注曰:“由,即《说文》之,木生条也。《尚书·盘庚》:‘若颠木之有。’可证。此谓尚将复生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商书》曰者,《盘庚》文。彼作由蘖,古作由。”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曰:“伐木之余曰蘖,复生枝条曰。”由此可见“宙”中的“由”为动词,本义可指枝折复生,引申为一般动词,此处与“极”同,达到义。“宙”字亦从“由”声,可表动词“达到”义。段玉裁在注解此字时也说:“舟车自此及彼,而复还此,如循还然。故其字从由,如轴字从由也。”也是从声训来说“宙”字从由之义。“宙”本义是栋梁。它所达到的“极”高之处,那是没有极限的,由此空间距离引申为时间长短了。
“宙”为栋梁,即为支撑上天的支柱。古人把头以上的部分称为“天”。甲骨文的“天”字形即是如此。中国古代人认为上天是需要立柱支撑的。《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可知所谓不周山即为天柱。《楚辞·天问》:“八柱何当?”王逸注曰:“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当值。”这是说古代相传天柱有八个,不周山即为其一。《汉唐地理书钞》辑《河图括地象》曰:“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上天需要支撑,是为天柱。房屋需要支撑,则为“宙”。
中国古人对于房屋立柱的崇拜,又是中国建筑与宇宙同样构想的证明。世俗生活中居民住宅的柱,古人认为是有神灵的,充满了神秘的内涵。特别是中柱,有的作为家庭供奉的神的依托之处,有的与火塘一起组成严密的镇宅护主的神灵群,成为家宅和宅主的保护神。在建筑房屋时,古人按照他们所设想的宇宙模型来建造。起房盖屋是成家立业的标志,竖柱又是起房盖屋中最重要的仪式。现在云南许多地方遗留下来的风俗,就可见一斑:竖柱时间要请巫师根据主人的生辰八字,择一吉日良时。竖柱当天,本村乡邻全部出动帮忙并送礼,远处的亲友也要赶来。柱脚连地,柱顶通天,为连接天地之物,而梁为连接各柱的通天之点,通天通神的作用又集中在梁上,可将梁比作抱玉柱的青龙。现在中国北方农村还有“上梁”的盛大场面,就是古人对于“宙”崇拜的遗存。横向即为梁,纵向即为柱,纵横交错即为“宇宙”(杨光麟:《原始物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神异经·中荒经》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围如削。”这种立柱也可称为地柱,其实是一样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古本《淮南子》:“共工怒触不周山,天维绝,地柱折。”此地柱与“天柱”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古人的时间空间意识是从建筑物中体会或感悟出来的,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宇宙观,是从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中衍生出来的,可以想像,中国古人们在建造房屋或居住于其中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当时的时空意识。这种意识,一定是在农耕时代产生的,因为如果没有定居,仍然处于游牧、采集时代,则人们就不可能居住在大房子中了,也就不可能把宇宙想像为大房子的样子了。古人们所感知、想像的宇宙,其实就是他们居住的那个房子,只不过把它想像为其大无比,没有边际罢了。又接着从栋梁所及的无限空间,引发出了关于时间的想像,栋梁所及到无限的空间即是无限的时间了。空间可转化为时间,这一点人们没有疑问。试看,一天的时间即是地球自转运行的空间距离,一个月的时间即是月球围绕地球运行的空间距离,而一年则又是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距离。我们的祖先,竟然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体悟到了时间与空间转换的辩证法,这不能不让人惊叹!
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天人合一”,即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周易·系辞上》则发挥《易经》的思想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天地”是从来就有的,后来派生出万物和人。人既然是天派生的,因此就要象天、则天、顺天、应天了。中国古代建筑也体现了这一天人同构的思想,中国古代建筑追求与上天的对应感通。从考古学的材料及流传下来的文献来看,从先秦时代一直到近代,人们在建筑房屋时都追求与天同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聚落遗址有一座呈“前堂后室”格局的大房子,面积有160平方米,坐落在聚落中心,是众多房子中最大的一座,既是氏族酋首的住所,又是举行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场所。房子门道均东向,东西轴线与正东面方向一致,一定是采用了太阳测向的方法,这在古人当中是普遍采用的。《庄子外篇·田子方》曰:“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人们最先认识的方位,即是本之于太阳运动而确定的东和西。《周礼·考工记·匠人》云:“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以正朝夕。”所谓“朝夕”,即东西方向,测定方法很简单,只需在平地上立一标杆,连接日出和日没的影端或上下午周长的影端,就为正东西。在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一组龙山时期建筑,外室呈方形,其内为一直径5米的圆室,圆室有两条垂直相交、与太阳经纬方向一致的十字形纯硬黄土带。在夏商建筑中也有这种情况,二里头夏都遗址发现的贵族统治集团的大型宫室建筑群体,组合有序,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居北部中央,南北中轴线与当地太阳纬度方向一致,是经过全面规度经营的组合建筑群。《尚书·盘庚》中也有记载:“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建设殷都新王邑的头一件大事是类居正位。奠是用人兽奠基,正位是测定建筑物方位,以太阳定座向的。《诗经·风·定之方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朱熹《诗集传》注释谓“揆之以日,是树八尺之臬,而度日出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古人在建筑房屋时,效法天地,试图让房屋与宇宙天地构造一致,正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追求。
对于建筑文化的重视,使西方人产生了“建筑是凝固的音符”这样的名句,这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的。但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说,这又远远不够。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是凝固了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中国先民们的审美理想、民俗情趣以及他们对社会及宇宙认识的最坚实的证明。古代建筑的不同形式的组合,诸如布局、空间、型体变化等建筑语汇无不深刻地渗入了中国先民的文化理想和追求。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