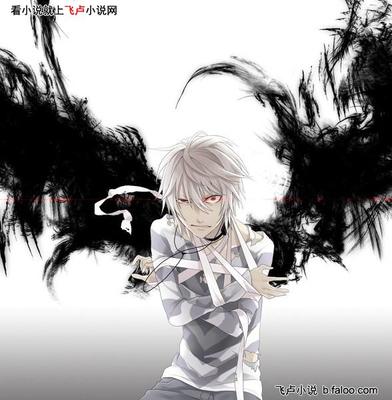孤寂的星,散发着孤寂的光
——论妙玉之文化魅力与文人精神(5)
辛若水
(五)末代儿女情及妙玉之命运
在一般看来,世间最不懂"情"的即是佛门弟子,殊不知,"万物众生皆有情",这正是佛门的绝唱。佛陀本人间一至情至性之人,他若不懂情,又何以会从情中解脱?若为情累,不能解脱,与一凡夫又有何异!"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诚哉是言。妙玉作为空门中人,也是有情的,但妙玉之情与佛之所谓万物众生之情,大异其趣。妙玉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她心里虽然有很深的禁欲意识,但毕竟不会自觉地去劫破情,从中解脱出来。她之情,不是幽尼之情,而是少女之情,孤独文人之情。幽独的梅花掩映着消瘦的玉容,若水的心间泛起道道泪痕,凄楚的琴音摇荡着梦中的花轿,或许这才是妙玉之情,这才是末代儿女情。
末代儿女情本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百花园,散发着文化的芬芳。虽然栊翠庵犹如清幽的潇湘馆,但并不能遮掩妙玉异样的光彩,亦不能淹没她那独特的声音。一缕幽情,透出栊翠庵,汇入了末代儿女情,在孤独中相凭依,在苦痛中相蔚藉。如果妙玉真像曲子中讲的:"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那么她之幽情亦汇入了悲秋的萧萧余韵,在无限悲凉与衰飒中走向了自身的没落。
作为孤独文人,妙玉最需要知已之情的蔚藉。可在"世难容"的悲哀中,谁又是她的知己啊。与她曾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的邢岫烟,应该最了解她,但邢岫烟又何曾真正进入她的精神世界,接纳她的个性啊。邢岫烟也只能半是叹息半是无奈的说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是生成的这等放诞诡癖了",甚至有时就毫不掩饰的说道:"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如果妙玉听到曾经的"知已"讲出这等言语,该是多么寒心啊!可以告慰的是,妙玉曾和黛玉、湘云,完成了接纳,建立了知己情份。中秋夜联诗中,黛玉与湘云那"多不遂心的命运",触发了她的同感,寄人篱下的处境引起了她的共鸣。夜遇知音,怎能不使她深感庆幸,怎能不一诉衷肠。于是她揭开了冷峻的面纱,吟出了自称"闺阁体"的续诗,显露了活泼的天性,展示了少女的才华。在那诗中流动着真正闺阁少女的情致,吐出了真情实感和隐蔽的心声。"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栊翠庵的蒲团岂能蔚藉孤独寂寞的精神。可姐妹们凄凉的情感却温暖了她凉冷的心。"有兴悲何聚,无愁意岂烦"。真正理解她的,并不是什么尼姑道士,而是以末代儿女情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大观园少女。作为文人的代表,作为曹雪芹的化身,妙玉、黛玉、湘云是一例的,她们的文化魅力、文化品格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佛、道是她们的皈依,孤独是她们的处境,精神洁癖与精神自由是她们的追求,人生空幻是她们的归宿。或许,正由了这,大观园文人集团左军、右军,明显地区别于正统的中军。也正是因为她们巨大的相似性,使彼此引为同调,成就了末代儿女情中的知己之情。
作为少女,爱情已进入了妙玉的精神世界里。禁欲,使人不由自主;可爱情,又何曾让人自主过。从贾宝玉进入栊翠庵,得到妙玉的垂青,那微妙的感情不正是藕断丝连么?妙玉心性高洁,自称"槛外人",有出尘之想,隐隐以仙人自居;而宝玉则直把妙玉比作嫦娥,比作观音大士,把栊翠庵当作蓬莱仙境,乞红梅,则说是"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柴云来"。如果在妙玉与宝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爱情,那么也是仙人之爱。妙玉渴望着人间的温情,宝玉期盼着仙子的垂青。为了爱,妙玉可以从仙境走向人间,可以把打坐的禅床变成梦中的花轿;为了爱,宝玉宁可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远远地观赏,让妙玉沐浴在圣洁的光辉里。所以牵挂,总是妙玉对宝玉的牵挂;相思,总是妙玉对宝玉的相思。她与众生无涉,却把宝玉的生日默记于心;她遗世独立,却又"遥叩"宝玉的"芳辰"。宝玉未必是妙玉的知己,他也讲过妙玉"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但宝玉对女儿的尊重,对女儿的崇拜,打动了妙玉的芳心。妙玉之念念不忘,春蚕自茧自缚是也。或许,这种深情冲击了禁欲意识,让妙玉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少女。但妙玉对宝玉的仙人之爱,是找不到归宿的,最终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梦幻罢了。
"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妙玉的命运很不好。续书写她为宝玉害了相思病,而一伙强人觉得把"长得实在好看",动了邪念,于是劫持了她。这种玩法相当糟糕。按续书之逻辑,大抵是妙玉情欲未断,心地不净,因而内虚外乘,先有邪魔缠扰后遭贼人劫持。此无非是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妙玉的悲剧命运是自己造成的。总之,出家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一念不生,万缘俱寂"。程存理学这一套有什么好,真是奇哉怪也。按红学家们的说法,妙玉之结局无非有两种:一是瓜洲渡口遇难后,被强迫还俗,转卖至烟花卷,惨遭蹂躏;二是被拐卖到当时遍布江南,名为尼姑庵,实为变相妓院的处所。对此,我们有个了解就足够了。
妙玉的一生是凄惨孤独的一生。在与世隔绝的寺院生活中,她的心灵孤寂冰冷,她的青春黯淡无光。对于生活,她没有太多的期求,她只望隐身空门,不受世俗的打扰;只求默默的生活,保持内心的平静。她孤标傲世,鄙视权贵,但从来没有触犯过权贵,却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权贵给她带来的不幸与悲哀。她抛亲别友,远离家乡,流落京都,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高洁孤寂的幽尼,然而无边的黑暗终于吞噬了她......
如果妙玉是一个少女,她的性格是一个悲剧的性格,她的悲剧是一个性格的悲剧;从末代儿女情中看,她的悲剧是一个知己之情的悲剧,亦是一个仙人之爱的悲剧。
在我独特的视角里,妙玉的悲剧更大,更有涵量,因为她是孤独文人的代表。他的悲剧是孤独文人的悲剧,是以追求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精神自由为根基的精神洁癖的悲剧,是伟大孤独意识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悲剧。作为左军第二梯队主将,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上空,妙玉永远是一颗孤寂的星,散发着孤寂的光。我特别欣赏妙玉,因为在她的孤独意识里,不仅找到了曹雪芹的影子,亦发现了我自身的影子。或许,在生命的星空里,我也如同她,成为一颗孤寂的星,散发着孤寂的光......
诗云:
依旧窗前破瓦盆,东君无语带晨昏。

此生若少相知者,黄土垄头待郢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