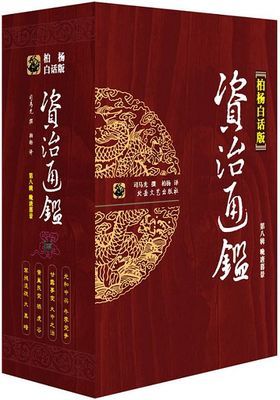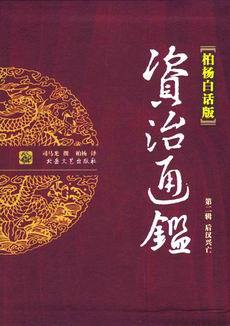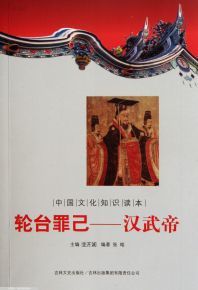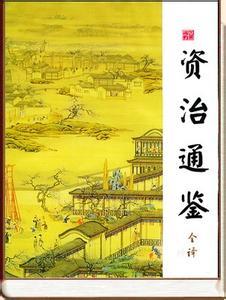『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七季】
汉武帝和他的儿孙们——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与历史形象(共三讲)
【主讲】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地下一层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三讲】
制造汉武帝——司马光《资治通鉴》构建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
汉武帝刘彻,一生在内政与外交上均有建树。但不可否认,他执政过程中存在制度严苛、崇尚武力、好大喜功等问题,中国古代的学者,对此多有批评。但北宋时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为伸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刻意记述汉武帝在其晚年临终之前不久,下诏痛悔自己一生的行事,并且将治国的基本政治路线,由“尚功”改为“守文”,由此构建出一个与历史事实绝然悖戾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这一做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直至今日,仍有一些著名的历史论著,据此阐释汉代政治史的演进历程。本讲将尝试剥离司马光强自涂抹在汉武帝身上的奇异色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主讲人 | 辛德勇
*据现场实录整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谈的稍微抽象一点,我们这个系列讲座核心反映的西汉中期的政治,是谈汉武帝本身,但也不直接谈汉代的具体形象,谈他留给宋代以后很多人,一直到今天,包括今天当代中国的、海外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及其研究者心目中,从他们开始到普通民众之间转化过来、传播过来的汉武帝的形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涉及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问题。

先从汉武帝本人说。汉武帝登基时16岁,在古代天子里也是比较年轻的,而且很能干,特别按照现在很多想弘扬我大中华威风的朋友的想法,特别威风,他是真的四面威风,四面都是打,先打北面的匈奴,打南面的越人,然后打东边的朝鲜,通西域也打,打的很威风,把我大中华的疆土开拓得很大,可以说能开拓的地方都被他开拓出来了,值得中华子孙永远纪念他。但我不是这样想,我觉得老百姓好好生活更重要,国家疆土大小不重要,小国同样可以生活的很幸福。
他一生东征西讨地打,打到晚年快不行了。《资治通鉴》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著名学者司马光写的著名史学著作,有一个记载:在汉武帝晚年征和四年三月的时候,“上耕于钜定”,在钜定这个地方做样子。大家不要以为皇帝是真的耕地的,历代皇帝都做这个事,就像有一些地方一些领导人到哪儿植一棵树,千万不要以为他真植树,他植一棵树的成本大的不得了,比正常植树的成本不知道高多少倍,最好还是不植好。他耕地最好不耕好,但是他做样子就由他做了,他去了泰山修封,封就是封禅。封就是在一个高地跟天老爷说话,沟通人和天。禅是比那山头小一点的山头,跟地说话,天地之间沟通,人是在天地之间的,天地人这样一个关系。
修封之后,“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在泰山上面做了封以后,在石闾这个地方做了禅,然后见了群臣。大家注意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紧密的衔接,封完了就禅,然后见了群臣,讲出了一些很特别的话,原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狂悖,用今天白话翻译出来,我是一个粗人,我上大学之前是干粗活的,用粗话说:我是一个混蛋。“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从今天开始,所对老百姓不好的事情全都停了,洗心革面,像从大狱里刚放出来一样要重新做人。他发了这个誓。
当时大鸿胪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能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田千秋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有很多方士讲神仙想帮助汉武帝成仙,通过哪一种方法、哪一种方子想成仙。人活的特别好了以后就想永远活下去,永远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成仙,生活困苦的老百姓一般不这么想。大家看最底层非常困难的,把儿女养大,有了工作,觉得这辈子差不多了,能活一天是一天了,越享福的人越想永远享福,当皇帝当然享福最多,他就希望永远做下去。
因为这个,他有了另外一些人,这里提到“候神人者”,按照西汉前期的观念,神仙是从东海外面来的,海外是有仙山蓬莱的,秦始皇那时候派徐福出去就是找神仙,侯神人主要在东海海边,从渤海湾一直排到东海海岸,不是简单派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行了,得给好吃好喝,还得有地方住,修了一系列设施,大家都等着万一神仙来了找不到路怎么办,得有人把他领到长安城里,才能引汉武帝成仙,但是耗费巨大。所以田千秋希望把这些人就遣散了,既然现在要重新做人,以前做得都不对,他以前一直弄这一套,都要罢掉。
“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時愚惑,为方士所欺。’”他后来跟大臣们在一起,自己感叹,我以前全被这帮方士骗了。“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天下哪里有成仙的,这些全是胡说的。“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巳。”这一点是合理的,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这样,吃一点养生药、保健药调养调养,尽量把自己晚年过得更幸福一点,生活更健康一点,这是合理的。
司马光的想法好,所以就把汉武帝写得很好,但是司马光写的是北宋中期人写的,并不等于汉武帝真的这样。在《资治通鉴》之前,就有很多人赞叹这个说法,从北宋中期《资治通鉴》产生之后,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学习历史时经常使用的一个书,一方面《资治通鉴》的撰书目的,就像书名讲的资治,就是为了今天怎样治理社会提供一个借鉴,所以官员要学习。但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读不过来,因为到了宋代之后,前面一大堆正史里面,到宋代时,包括五代史,我们不太了解的人会说古人读书多,特别刻苦,读书破万卷,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大多数人读书很少的,一般读完《史记》读《汉书》,有本事的人读到《三国志》也就完了,后面的书不大有人看的。再读就读读到唐朝,把唐书看了,因为唐朝是大帝国,南北朝根本没有人看,《资治通鉴》把它们全都编到一块了,一本书代表所有的书,一个短暂的篇幅可以了解整个历史,所以相对来说从技术的角度也读得很多,就影响了很多人。
这一点影响进入现代学术之后,古代学者的评价一般不直接影响新的学术研究,但是现代学者有人开始重视了。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有一个老的汉学家叫市村瓒次郎,很早就出了一本书叫《东洋史统》,在这里他就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句话,说体现出汉武帝悔过的表现,而且他说自己“所为狂悖”叫“罪己”,体现了汉武帝施政方针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巨大的改变。中国学者唐长孺先生在1956年起开始编写他的《秦汉史讲义》,同样谈到了这一点,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受到当时人民起义的影响,对自己的政治方针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已故的田余庆教授,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叫《论轮台诏》。在这篇论文里,他继承了市村瓒次郎先生以来的看法。但必须说明,田余庆先生没有看到市村先生的文章,不存在直接利用,是同一个思路考虑问题。他说汉武帝的转变是“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此使汉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导致所谓“昭宣中兴”,就是汉昭帝、汉宣帝时出现中兴,使西汉的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当时有一个背景,当时的史学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民起义,汉武帝后期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骚乱,也就意味着人们的起义在推动历史前进,逼迫汉武帝转变了国家政策,基于这个逻辑思考得出来的。
所有这些认识,汉武帝“罪己”的开端,他说“所为狂悖”,对自己进行了谴责。看刚才那段记载确实非常明确,汉武帝就是像一个大狱里刚放出来的人,要洗心革面、金盆洗手了,坚决不干坏事了,一定要干好事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这个观点仅仅是田余庆先生写一篇论文,不会影响非常大,他是北大著名的教授,还有一些著名的弟子,会传播得很广,但更重要的是基本同时田余庆先生在参与由简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这个大学通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影响是特别广泛的,由于北京大学的地位,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编撰的《中国史纲要》的教科书就在学术界流行更广,特别是现在考研,考北大就得看北大的书,所以影响更大。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学术界通行的看法。
这篇文章,我仔细看了一下,感到有些问题,比如刚才谈到:“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清朝一位学者说:“自谓狂悖,自谓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责如是者。”没有人这样说。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南京大学一位叫李浩的博士马上写文章批评我,我自己看了以后感觉完全不是一回事,完全没有讲到这个程度的自我谴责,还是同意这位清朝学者的评价,这是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一个皇帝用“所为狂悖”这样的话来谴责自己,帝王有谴责自己的,有罪己的,但用这么严厉的词句,用“所为狂悖”,用这么难听的话骂自己,是太出格了,让人怀疑会不会真的是这样。
更让人费解的是什么?刚才提醒各位朋友注意,他讲“所为狂悖”这句话,是紧接着他前面讲的“禅石闾”这个话讲的,包括封泰山,所有的行为还是想长生不老。他刚刚封完了,也禅完了,一转身脸变了,马上骂自己干了一些混账的事情,我以后一定要重新做人,这个变化太剧烈了。正常的人这种重大的转折、重大的变化,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们都会有变化,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不良的做法,都会有一些自我更新、提高、改变,但是这么大品行的改变会有一个过程。他这边刚做完,回头转身就骂自己,太反常,不符合常理。所以《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些事情让我感觉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地方,不大可能是真的事情。
为什么一再强调《资治通鉴》?主要是我们研究历史,在座朋友有的可能是做过中国古代文史,有的没有做过,看过一般性论述。做古代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在其他条件没有特别的情况下,依据越早的文献真实性越强,因为书是人写的,越到后来主观的东西可能改变的越多,到一些特殊时期可能有意加入一些主观的东西,所以历史研究这是重要的基本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比如记述汉武帝的《史记》和《汉书》是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还有汉武帝去世之后,在汉昭帝时期编写的《盐铁论》,也是直接关于汉武帝时期事情的记述。在这些书里我们都看不到前面《资治通鉴》的记载,完全没有。不但没有,特别是读《盐铁论》的时候完全相反,不是这么回事。历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在同等情况下,一定要相信比较早出的《史记》《汉书》《盐铁论》的记载,而不能相信晚出的《资治通鉴》的记载。
但是情况比较复杂,也许有的人会说《资治通鉴》可能会看到更早的书呢?从逻辑上讲当然可能,但是历史之所以能够研究,什么时期有什么书,什么时期人能看到什么书,通过很多学者一代代的努力,我们大体是清楚的,特别是北宋中期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哪些关于西汉历史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来编撰《资治通鉴》,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重新核查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资治通鉴》里看到的那样。
一、论轮台之诏性质
田余庆先生的文章叫《论轮台诏》,轮台诏是汉武帝在晚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主题是停止在轮台以西的地方进行屯田。一般史学家称为轮台诏。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解读,轮台诏和《资治通鉴》主旨是一样的,是汉武帝晚年忏悔自己的一个举措。
我们看看轮台诏到底是怎样一个性质。诏书比较复杂,大致来说是在《汉书·西域传》,如果是一道非常重要的、涉及汉武帝大幅度政治转化的诏书,理应载录在《汉书·武帝本纪》里,是记录他一生大事的,实际上不是他的一生,是他主持朝政时国家最重要的大事的编年记录,但是《汉书·武帝本纪》里没有,是在《西域传》里,为什么?发布这个诏书的前提是在汉武帝征和四年,由于军事行动遇到一些挫折,进行反思,然后发布的一些诏书,针对的问题也是在西域轮台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所以在《西域传》里面。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了匈奴。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很能干的大臣桑弘羊提出了建议,要在西域开展屯田。
古代屯田都是军事行动重要的保障,我们一般不了解军事行动的时候,就看哪个将领有名,军队威势有多壮,但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打仗最重要的是后勤保障,一定让这帮人吃饱了,吃不饱,饿着肚皮,打谁都不知道了,就变成打家劫舍了。保证他吃粮时,远距离运输不能长期保障,长期保障就需要在边防前线有一些屯田,让军人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空闲时间种地,保证军粮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让屯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就是多收,多收还不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就在这个方向屯田,就是所谓轮台诏。这些问题我们不详细讲中间的过程,中间过程讲到其中一个西域投降汉朝的将领,还有贰师将军李广利作战的情况。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武帝说我不忍心这样做。“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让一些人护送匈奴使者走,他说这也是劳扰民众的。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翻译过来,简单来说:当今重要的任务是禁止苛暴,政务不要过于暴虐,进一步发展农业,养马。因为马是当时最重要的装备,相当于德国人打二战时的机械化坦克军团,马是最重要的军事主力战斗部队用的,所以要修马备。特别后面这一点绝对不是要不打仗的,但是当时遇到了困难。著名的轮台诏就谈得这个。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注:车千秋是田千秋,后来他的岁数大了,进宫上朝不方便,让他坐着小车,所以就该了姓为车,叫车千秋。)跟这个有关的是现在提到的海昏侯,一般汉代的封侯是用地名,封给你这个县,或者县里某个乡的地名,及特殊情况下用于有象征意义的,像富民侯,这跟地名没有关系,非常罕见,表明了汉武帝要发展生产的某种决心和意志。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重要的标志。
顺便多说两句,有的学者指出刘贺不是好人,昏乱,他的行为很昏庸、荒唐,所以叫海昏侯。海就是黑暗,放在汉代实际和相关南朝时期有关的,比如南朝齐有个东昏侯等等,我自己认为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还是一个地名,就是在南昌有个地名原来叫海昏县,把刘贺封到那儿去,叫做海昏侯。富民侯确实不是地名,是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单纯分析记载,我自己认为所针对的内容不是西汉整体军事方略或者政治行为,而只是关于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一个局部性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主要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之后,针对此做的一个策略调整。李广利之前还是很卖力气打的,过程中作战开始失利,他很害怕,巫蛊事变发生之后,他和丞相合谋想要推刘髆当皇帝,又有类似巫蛊的事情被人揭发,他的老婆、孩子都被汉武帝抓住要处死,他自己希望努力扩大战功来挽救自己的性命,他知道打败了回去肯定会被杀,结果越打越差,一塌糊涂,李广利想这样回去断无生路,他就投降匈奴,自己的命保住了,全家被杀掉。这件事情是汉代军事上的重大挫折。
汉武帝向匈奴用兵,元朔二年取得大幅度进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这之后总体来说是连战连胜,一直是不停地开疆拓土,这是一次重大的失败。面对这次失败,汉武帝觉得需要调整,而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在这之前,国内著名的巫蛊之变刚刚发生,整个追查巫蛊持续了两三年时间,牵涉上万人,牵动面非常大,国内政治出现了不安定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汉武帝需要做一个策略性调整,所以这就是我对它的认识,之所以会写入《汉书·西域传》,而不是写在《汉武帝本纪》里面就是这个原因,是一个局部性、地方性的调整。遇到困难的时候,像汉武帝这样英勇的帝王一定要调整的。这之前有类似的行为,在战争中比这更小的挫折,国内有一些困难,汉武帝都调整过来了,如果那个时候汉武帝就死了,看着这个皇帝好像不错,看着国家他要改变了,但是后面紧接着干起来了,这个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策略性的调整。
汉武帝临终之前安排的这些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田千秋等实际上一直忠实执行着汉武帝的路线,没有进行改革,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关于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所有批评我的人都回避谈这个问题,我到今天也不理解田余庆先生当年的论文里是提到了《盐铁论》的记载,但提到《盐铁论》为什么会认为汉武帝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很多人对我批评的一个根本性原因,除了给我解释汉武帝在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的批评,盐铁会议是汉昭帝始元六年,霍光为了在政治上整垮桑弘羊采取的阴谋手段,但形式上是要由关东各地招来的贤良文学给国家提意见,进行整改。这些贤良文学全面攻击汉武帝一生对外开疆辟土,对内横征暴敛,对他全面进行了攻击。
比如这里提到:“君薨,臣不变君之政。”就是说皇帝死了,我作为大臣,继续执行皇帝的政策,“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就说明他忠实的执行汉武帝的贡献。对他的攻击来说,是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攻击的结果是不是就改变了?仍然没有改变。不太了解的人会说盐铁会议开了,儒生贤良攻击了以后,朝政会改变了,其实是做了非常微小的调整,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以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这些攻击是非常全面的。
因为《盐铁论》的记载,我最后确定了汉武帝晚年没有这样的诏书,也没有这样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我把《盐铁论》反复读了几遍,确认没有问题,其他的东西跟我们前面谈到的卫太子有没有搞巫蛊一样,记载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果抓住某一个词句可以解释为汉武帝改变的,另外一些词句抓住可以说他没改变。但是我们要综合地看,《盐铁论》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如果说汉武帝晚年下这个轮台诏意味着全面改变,他指定这些大臣,从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都在执行汉武帝的路线,他们说没有改变汉武帝的路线,而借这些贤良文学们攻击当时朝政时,就是攻击汉武帝,明确提出汉武帝做了一系列事情,桑弘羊誓死捍卫说先帝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国家。
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假如说汉武帝说我“所为狂悖,向时愚惑”,就全面改了,这些贤良文学们攻击什么呢?汉武帝去世六年以后,国家已经全面都改好了,你攻击什么呢。除非《盐铁论》是伪造的,但没有一个人说《盐铁论》是伪造的,《盐铁论》是铁一样的事实。这样全面系统记载了汉武帝时期晚年政治的东西,不需要费劲解释。我不知道很多批评我的朋友为什么放着最直接的东西不解释,非要抓住某一个片面的词句说汉武帝改变了呢。这就是我后来没有写文章回应批评我的重要原因,没有办法讨论,回避《盐铁论》这个问题不讲,硬说汉武帝非要改了。我就觉得讨论没有太大意义,还讨论什么。如果真的跟我讨论,我列举的核心证据是《盐铁论》,《汉书》里也有一些记载,首先你要对《盐铁论》做一个解释,至少我批评别人一定要解释,哪怕强词夺理也要讲一个理,按我的角度这可以做出另外一种解释,但至今为止全世界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没有另外任何一个人对《盐铁论》记载的东西产生别的解释。所以汉武帝没有转变。
问题是整个论述并不是最重要核心的东西,核心问题是更深一层的,田余庆先生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又向上追溯,不仅仅是一个汉武帝的政策改没改变的问题,是汉武帝和他的亲儿子卫太子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汉武帝代表着一种残暴的路线,他的儿子代表汉武帝转变之后的守文的路线,变成路线斗争了。这个问题还是从《资治通鉴》里来的。
二、《资治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是怎样产生的
司马光是一个老实人,非常老实本分,老实人有时候也会做一点不太老实的事情。有的朋友在网上很不高兴地骂我,说我好像黑了司马光,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我非常敬重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我赞成司马光的主张,我不赞成他的政敌王安石的主张。司马光的想法是王安石别瞎折腾,让老百姓好好过日子,所以我非常敬重司马光,这个必须郑重说明。
这是《资治通鉴》一个非常长的记载,涉及汉武帝和他的儿子戾太子,“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就是说卫太子与汉武帝不一样。这说明两条路线的端倪就出现了,一生下来天性就是守文的孩子。他说“性仁恕温谨”,跟汉武帝的残暴不一样,所以跟自己不相类,然后说到其他一些孩子的情况。
“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汉武帝出去巡幸的时候,比如刚才讲到泰山封禅的时候,京城得有人管,京城大事都托付给太子来处理政务,因为太子宽厚,把汉武帝做的一些残暴的事情都给平反了,所以“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当时具体办事的人都不高兴,我刚替汉武帝办完,你一转身给平反了,我当然我高兴。
“皇后恐久获罪”意思是你总这样做的话,皇帝就怪罪你了。“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告诉太子,你得看老爸的意思,别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汉武帝知道了以后,说太子做得对,应该这样做,反而把皇后进行了谴责,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这个天下,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必须要严刑峻法做的,将来你即位做皇帝就省事了。“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很简单地说,就是比较宽厚的一些大臣都依附着戾太子,然后那些严刑峻法,执行汉武帝的一些老百姓都很恨他。“邪臣多党羽” “君子不党”,所以对戾太子怨恨的很多,“誉少而毁多”,大多数人都怨恨他,在糟蹋他,而不是赞誉。
“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昨天我谈到了,很多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太子有一党,就是李氏集团、卫氏集团,我看不到这个集团,卫青不死也已经没有任何权势。《史记》和《汉书·卫青传》明确记载,在他打了几次大仗、战功累累之后,汉武帝提拔起了霍去病,虽然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但实际上跟他的立场完全不同,卫青手下所有的人跟着霍去病了,就把卫青抛弃掉了,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权势了。因为霍去病一提起来,卫青一看只有一个人没有去,就是任安,任安是一个正派人物,不能那么势力,他对卫青依然如故。一个好汉什么用都没有了,不存在党的问题,而且太子起兵之后,恰恰是任安按兵不动,完全没听太子号令,没有看出任何党的痕迹来。这个我们不管,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卫氏集团党羽依靠的。
这一段记载很重要的说太子是一条路线、汉武帝是一条路线。汉武帝晚年转向守文,就和前面的巫蛊事变有关系,巫蛊事变由汉武帝代表的这些所谓横征暴敛的暴虐的一派把卫太子给消灭掉了,而且构造的是一个冤案,等等。但是汉武帝晚年终于悔悟到,第一是卫太子受冤,第二是政策必须改变,所以就下诏说我“所为狂悖”,就由一个一般性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转变成思想路线斗争。
我们研究政治史时需要一些启发和联想,有些道理古今是一贯的,问题是论证过程中要非常小心,胡适讲了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他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个说法是很对的,还是可以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余庆先生应该做一个更仔细的求证,但这里遇到问题了,像《资治通鉴》这种书能不能用它来否定《史记》和《汉书》,特别是把《盐铁论》的记载全否定掉。这一套东西,太子如何怎么样的,有什么宽厚长者等等完全没有,在《汉书》里一个字的痕迹都没有,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在《汉书》里完全没有,只是到了北宋中期《资治通鉴》才著述,是不是能信得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田先生非常赞成《资治通鉴》,所以特别强调和《汉书》比较起来,《资治通鉴》是比较深刻的,在史实上胜过《汉书》一筹。对历史的认识是这样的,一个学者想要更深刻认识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不能仅仅看到宫斗戏热闹,要看到它背后的东西。但问题是有的时候,第一如果史料不具备,第二如果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为了求深而求之过深,求之过深以后,表面看着深刻,实际上反倒流于浅薄了。假如田余庆先生受到某种现代启示考虑的话,这个启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如果找不到足够证据,足够的证据是什么?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依据永远是材料,尽量用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材料能不能用?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当然能用,但不能跟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手材绝然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相信《盐铁论》记载的话,《资治通鉴》的记载和《盐铁论》就绝然矛盾,完全相反,如果相同或某种程度重合,我们就感觉它的来源可能是可靠的,如果完全悖反的话,绝对不能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完全悖反的。我们必须相信《汉书》和《盐铁论》这样更早的记载。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太乱了,包括有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很多年以前我在西安读研究生时,跟他在一起开会,他说古书,怎么写的都有。我当时听了说不能这么讲吧,古书错有错的规律,变有变的规律,我们之所以要有学者做研究不能谁都研究历史,就在于通过学者的努力,对文献的可信性及其变化做出一个追求,它都是在历史时期产生的,历史学家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史学素养来分辨这些东西,而不是毫无规律可循。
田余庆先生基于《资治通鉴》得出的两点重要认识,第一点汉武帝晚年做了一个痛斥自己所为狂悖非常严厉词句谴责自己,而且政策要做一个大转变;第二点不仅仅是一次金盆洗手的事情,是他要通过这个行为改变他以前的政治路线,这个政治路线是一直存在他和他的儿子之间对立的。假如我这个朋友告诉我田余庆先生受到自己经历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启示和影响的话,我从小学的历史就是中共党史,就是路线斗争史,长大看得多了一点,感觉它比较复杂,我们承认有路线斗争,但是有一部分是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结合的,有的干脆是路线斗争。
我们回到历史时期,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研究唐代,研究结果是以前人认为有两条路线全是狗咬狗,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反动统治阶级,都是权力争夺。我相信我的老师研究这个。对汉代历史我受到我的老师黄老师影响很大,我看的结果就是权力斗争,没有看出政治路线,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看不出一点这个影子,只有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资治通鉴》里为什么能有?在北宋时期,司马光的年代,政治路线斗争成为当时朝廷政治的核心和主流,司马光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有明确出于自己政治路线斗争的目的编写这样的书。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根据已有的书来写,不是直接记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战国时期一直写到宋代,都根据现有的书重编,不是直接记录或者第一次编写历史书。他依据这部分的史料,南宋初年有一个叫吕祖谦的写过一个《大事记》,是编年体的史书,有点模仿《春秋》,非常简略,但是太简略了不行,细节部分又写了一个《大事记解题》,对细节部分加了论述,有点像《左传》。《大事记解题》里明确讲,“《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凡此类皆未尽信。”明确指出这个来源。但有的朋友说:他说诸书,还有别的,你知道是什么?这么说就有点不讲理了,因为这里列举的时候谁都举出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和相对来说最可信的就是《汉武故事》,诸书后面等而下之的就更不行了,如果说《汉武故事》不是的话,就是更下三流的书了,《汉武故事》这个书对吕祖谦来说不可信。
这里面批评我的朋友始终回避一个问题,我论述这个问题是站在宋代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讨论的,我自己读书过程中体悟到一个非常粗浅的认识,北宋中期司马光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简单地说所谓唐宋变革时期之后,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走入政治舞台的核心,司马光是这样,王安石也是这样,包括苏东坡代表的另一派也是这样,这一批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走入政治权力核心,他们充满了对社会的理想,把自己的理想带到施政过程中,也通过一些著述体现自己思想。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是通过经学著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有著名的“三经新义”。司马光不像王安石那么机灵,宋代时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特征都体现得很明显了,南方人相对来说更聪明、更机灵,北方人就比较厚重,厚重的人就适合写史书,阐释经学的东西司马光不灵,写史书的时候,孔夫子说:“与其托之空言,不如见诸实事。”通过具体实施的取舍来体现他的观点。这个书被宋朝皇帝定名叫《资治通鉴》,后来这部书就进奉给皇帝,让皇帝看,古代那些帝王做了一些什么,你这样做行不行,应该怎样做。
吕祖谦讲的话为什么非常重要呢?还有一些文献学的知识。不客气地说,很多批评我的朋友,很多知识他们并不很理解,这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研究,我的研究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很多东西他们并不很理解。像文献为什么会这样,吕祖谦讲了非常重要的说,吕家讲的话必须信。为什么?北宋末年、赵宋王室南渡的时候,吕家带去的文献是特别多的,带了一大批书,两宋之交时,是一大批文献,在南渡过程中毁掉了,吕祖谦家恰恰带去特别多的书,所以有一个称呼,吕家叫“中原文献”。当然不仅仅是有书,但有书是重要的基础,他们家的学术也是强调读书。中原文献就体现了这个特点,说吕祖谦说了就一定是真的,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今天我们看不到《汉武故事》的全文,但是吕祖谦是看到了,所以他说《汉武故事》诸书不可信。
北宋中期时,这些知识分子强烈的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社会实践。为此,他们在学术著作中都是做了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种人为改变。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这样的,王安石写《三经新义》也是这样的。后人特别批评王安石,因为他说:“我著六经。”本来六经应该根据经义来解释,他不是,随心所欲解释经书,从学术角度看王安石的做法不科学,但王安石不是经学家,他是政治家,他的经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你拥护和赞成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他就是好汉,他做的所有都是对的。但是我不太赞成王安石那样做,我觉得司马光的路线更好,两个人都是正人君子,所以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出现了非常繁荣的路线斗争,个人为了权势的争夺占的比例很小。后来不一样,各个党派完全都是以党派化解,你反对我,我反对你,越来越乱。他们这个时期,从欧阳修开始,持续到司马光、王安石这个时期是这样的。
三、《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汉武故事》这部书为什么不可信?本身内容是非常荒诞的,下面会举一些具体例证。比吕祖谦稍微晚一点,南宋初年的王益之,写过《西汉年纪》,也是编年体的,专讲西汉历史的,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详细。在这部书里面,他说:“吕氏《解题》曰,《资治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载其始末甚详,凡此类皆未尽信,今删去之。”他完全继承了吕祖谦的观点,而且这部书里没有完全不引《汉武故事》,个别问题还引了,就证明他也看到原书了,他和吕祖谦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样的观点。为什么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南宋时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朱熹,按照朱熹对道义的追求比司马光时代一点都不弱,可能更强。当然朱熹特别强调事实是事实,你的评价是你的评价,不赞成司马光通过事实来反映自己的观点,先尊重基本事实,把个人主张用议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刚才我谈《汉武故事》全本没有了,但是有一部书叫《续谈助》,作者是和司马光、王安石同一个时代的,北宋中期的人,反过来说他看到《汉武故事》跟司马光看到的是一样的,在这里面他把《汉武故事》节录了一本,《续谈助》这部书就把他感兴趣的一些小说笔记摘了一部分,恰好摘了有一段跟《资治通鉴》能对上的。最初给大家引了一段汉武帝谴责自己所为狂悖的罪己诏的内容,轮台诏里没有这个话,不是《西域传》里的轮台诏,是《资治通鉴》里面写的罪己诏,左边是《汉武故事》的原文:“‘朕即位已来,天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田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侯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总的来说,基本上跟右边是对应的,出自一个来源,没有异议的。
下面这一段:“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故差可少病。’”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下面这一段被司马光没有采录的就不一样了,这一段非常重要,“自是亦不服药,而身体皆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汉武故事》是神仙家的著述,神仙家讲的要修炼,修炼其中有重要的一条是练房中术,马王堆帛书里发现有这一套东西,北大李零教授做了很好的研究,就是汉代这些文献我们都看到了,汉代讲房中术是非常科学的,更接近一些实质性的,就是怎样演练,宋代以后就玄虚化了,宋代以后的千万别试。在座各位男性朋友要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按汉代方法试一试,不一定有坏处,宋代以后不知道会出什么恶果,千万不能闹着玩。
这一段没有采录的话,说“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这就是修炼成仙的结果,而且用含着毒素的丹药完了脸都不会发红,很多服丹药的脸红了都是一个病症,不是好状态,说“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这个之前本来还有前提,就是一个男人跟十个女人同时演练房中术连续一夜不累,没问题,身体非常好。这个时候他不服药了,说“自是亦不服药,而身体皆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什么意思?神仙家这个法术是要炼到底的,汉武帝之所以没成仙,最后埋到茂陵了,是他没有遵照方法练到底,他停了,停了以后就完了,马上就死掉了。
但如果我们不看原文,光看司马光写的,这是多正经的话呀,没有问题的。看原文就知道怎么来的了。司马光是一个老实人,他绝不瞎编,每一句话都有依据,依据是否可靠不知道,是另一回事,但不会乱编。乱编你还真找不到证据,就因为他是老实人,我们就能找到证据,所以可以印证吕祖谦、王益之说它是取自《汉武故事》是有充分依据的。虽然下面讲的一些他和卫太子之间有两条路线斗争,卫太子如何仁厚、如何宽厚长者、复立太子,那个没有找到,《汉武故事》今天看不到了,但是那些东西吕祖谦一律删掉了,然后王益之写《西汉年纪》时又统统删掉了,就证明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认为不可靠,所以没有用。到南宋初年之后,从朱熹到吕祖谦、王益之,整个思想学术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事实雄辩,不能乱来,首先尊重事实,然后再体现你的观念。
也许有学者专门研究,我自己读书过程中,最近十来年体悟到的中国古代学术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迁,就是从北宋中期到南宋,到了南宋时期学术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那些事情。
看《汉武故事》类似的东西,引这一段说为什么不可靠?《太平御览》引了《汉武故事》一段,说汉武帝死了以后,“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就是平常跟汉武帝亲近过的女人,后宫嫔妃太多了,一个男人再强也不可能跟每个人发生关系,常所幸,就是跟他发生过一定关系的女性,住在茂陵,“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汉武帝从坟里就出来,从有官职的宫女里,婕妤以下二百多人,幸之如平生,简单地说像活人一样跟他们男欢女爱。
所以《汉武故事》记载的事情是不能依据的。这种当故事讲讲不妨,能当真事吗?司马光就从这样的书里节取一段编出来的,所以一定会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借用吕思勉先生论述北魏时期“立子杀母”事件,说:“一语既虚,满盘是假。”这句话非常重要,历史研究首先强调不管用多么高妙的办法来解释历史,来评判历史,来看待历史,史实是第一重要的,如果基本史实产生错误就是“一语既虚”,在这个基础上论述的都是零,毫无疑异。如果上面那些东西我们都承认是从《汉武故事》取来的,形成了《资治通鉴》,由《资治通鉴》形成了两条政治斗争,然后形成了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等等,那么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靠得住。说复杂很复杂,我们大家如果认真看书的话就会很简单。
四、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
从基本的、原始的、比较可靠的记载,重新构造成另一种形式,这完全是从人的主观需要在历史构建的一种写法。
明知道《汉武故事》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明知道呢?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还写一部书叫《资治通鉴考异》,考异就是异常、异同,不一样的,现在各位朋友读的《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下面都有,小字里有时候写“考异曰”,就是司马光在写的过程中做的。这个东西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史学著述里历史考据发展历程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体现了非常严谨的科学性,但一旦这种科学性和司马光追求的道义目标不吻合时,司马光绝对放弃科学的追求,更看重道义的追求,这就是当时著述一个重要的特征。从政治斗争角度,从司马光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角度是合理、有益的,从书呆子的角度,我今天是书呆子,作为书呆子看不能这么干,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跟本来是不一样的。
南宋时胡寅说:“司马氏史学尤精,而《资治通鉴》去取有难喻者。”就不明白司马光为什么舍弃这个取了那个,为什么这样写,他说这个东西不太好回答。
看看前人如何评价《资治通鉴》的,先看朱熹的说法,田余庆先生曾经非常赞赏,说“朱熹深谙司马光史学”。田余庆先生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写文章马上批评说:田余庆先生的文章不成立,有严重问题,他依据《资治通鉴》来写汉武帝,而这个记载跟《汉书》是违背的,不能成立。田先生非常认真对待这个批评意见,他说:朱熹是深谙司马光史学,所以朱熹写了一本书叫《资治通鉴纲目》,完全照录了司马光的东西,没有改变,就证明这个东西一定是可靠的。
从学术研究角度这个说法是很无力的,第一《资治通鉴纲目》不是朱熹写的,只是署了他的名字,由他的学生具体操刀的;第二点,即使是朱熹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大书,是为了更强的体现朱熹的史学观念,是对《资治通鉴》现有的工具做改编,不可能对每一处细节都重新审视,这是正常的,不意味着朱熹同时研究了这个问题,不能拿这个做证据。我想田先生自己也明白,找不到更有利的办法为自己辩护了,因为这个事情是切中要害了,严谨的史学家、受过训练的学者用《资治通鉴》本身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不是不能用,一定要慎重思考,处理它和《盐铁论》之间对立的东西,它和《汉书》对立的东西,只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才能非常谨慎的使用。但现在问题不是这样的。
朱熹实际上的评价,田先生回避了,或者田先生没有看到,朱熹评价:“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资治通鉴》此类多矣。”司马光修书,凡是跟司马光意思不同的,就不要,不采录。司马光可以这样,朱熹也推崇司马光,你是正人君子,问题是历史上有很多小人,小人做的就是小人的事,你是写历史书,不能看这个事情不好就不录了,司马光是正大光明的君子,《资治通鉴》里尽量的把那些阴谋诡计小人的勾当能不写就不写,因为他实在讨厌。我也不喜欢这些事,但问题是我们一睁眼就知道君子少、小人多,历史上就有这么多小人,不能因为他们做的事不好,我们历史书就不写了。这是对他的评价。
朱熹原话说:“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司马光这种手法,朱熹是不赞成的,不能用这个事情存在和不存在,你在《资治通鉴》里写和不写来体现你的褒贬的观念,你的褒贬的观念只能说别做论说以断之,不能这样做,这是很严厉的一个批评。
司马光在很小的时候写过《史剡》,是“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他说我读前代的历史,这些历史与其有,不如让它根本就没有,所以叫《史剡》。举例,汉高祖的时候,著名的贤相萧何给汉高祖修未央宫,汉高祖在前方正打仗呢,回去一看他把那个阕修的特别壮观,汉高祖大怒,说:天下这么乱的时候,你不节省一点钱,哪能这么干?萧何说:正因为天下乱才可以这样做,天下安定,再征发老百姓,老百姓就不干,要反了。现在趁乱把它建好了,以后就省事了。司马光就觉得萧何这么好的人,哪能说出这种话,这个事情一定没有。但是最后他写《资治通鉴》时把这个事也保留了,因为否定不了,《史记》是这样记的,《汉书》也是这样记的。司马光当然是好人,但是这么做,作为历史著述是不合适的。
钱穆先生谈读《资治通鉴》时跟他学生讲:注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跟《史记》《汉书》比较起来,添上了什么,删去了什么,能体现司马光思想关键的地方。但实际处理的时候,碰到具体问题,钱穆先生更多关注司马光删掉了什么,而没有多关注他添上了什么,特别是添进去了本来不该添的东西。
有一个成语叫每况愈下,这句成语本来出处是“每下愈况”,就是越极端的例子越能说明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在座大多数朋友,特别是家庭教养比较好的好孩子都没读过的,叫做《赵飞燕外传》,简单来说,我称之为中华第一情色读物。关于这一点,明朝一个学者叫王祎,写了《大事记续编》,是接着《大事记解题》写的,也是编年体的史书。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讲赵飞燕姐妹两个在汉建立时入了后宫以后的情况。“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这句话就被司马光采录到《资治通鉴》里了,但上下文没有。上面有什么、下面有什么,全都不管了。上面有什么、下面有什么是不大能看的。
“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浃藉。嫕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下面就讲“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后来就流传开了,但是来源确切无疑的就是出自于《赵飞燕外传》。
《赵飞燕外传》就是一部情色小说,这个事情不能写在正式的史书里,但是就把这句话被司马光恰恰写到《资治通鉴》里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是一个老实人,他字写的横平竖直,老实人又为了表现政治主张,绝不瞎编。正经书里没有记载,怎么办?他就想出这个办法,反正哪儿有事就从哪儿抄,从《汉武故事》可以抄,情色小说也可以抄,就是这样。相当于用这样一个小说来写历史。
为什么这样?实际上古人提到:“为熙、丰发也。”就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里必须说明一个事情,我没有一个字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我必须澄清这个事,很多人不认真看我的书,在网上说你时间搞错了,他写这个时候还没有变法。第一,最后定稿是在变法之后;第二,我的文章里没有讲过一个字说我认为针对变法的。我是引述别人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过程,正式颁布变法令之前,他的政治主张和变法令是一致的,我是说针对王安石一派人政治主张说的,从来没有直接针对变法。我不怕别人批评,但是很多人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认真看,看到一个字就胡乱讲。对学术问题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看明白我说什么再批评我。我能想到的问题,许多把握的都仔细斟酌怎样写,当然会有错误,但没有想象的错的那样荒唐。
主要的变法问题就涉及两派的斗争,《资治通鉴》印行之后,支持司马光的一派非常赞赏他的书,反对司马光的一派就想“毁《资治通鉴》板”,甚至把司马光应该抓起来处罪等等,跟当时政治斗争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写。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个非常普遍正常的做法。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吉利那些洋人打过来之后,清朝大臣一直感叹:古书上没碰到过这个事,找不到办法了,古书上有的就有办法,所以要以史为鉴。以什么为鉴呢?十七史也好、二十一史也好、二十四史也好,太多不能看,一定要取为借鉴的汉代历史是第一个考虑的,《汉书》的记载是全的。所以说汉朝是第一个考虑的,接下来考虑的是唐朝。比较全面能够清楚看到的就是汉代,汉代有几个帝王是躲不过去的,一定要说他的行为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第一个开国皇帝刘邦,第二个就是汉武帝。汉武帝一生所有的作为都是司马光极力反对的,我也不赞成。司马光之所以这样写汉武帝,就在于汉武帝一生所有的行为不符合他的追求,这不要紧,他跟皇帝怎么讲汉武帝,如果他晚年发生了一个转变,这是非常好的例子,你看汉武大帝这么英武的人,折腾了一辈子,到晚年也知道这事儿不能干,一定要转变。跟宋朝的皇帝一讲,我也得学汉武帝一样,与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样写,就这么简单。
五、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
最后两部分不是论证司马光提到的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两条路线斗争是否成立,也不是论证汉武帝转变没转变,这个问题是在我看来已经很好的论证了汉武帝晚年没有转变,他和戾太子之间不存在路线斗争,在这个前提下来论证《汉武故事》记载是怎么形成的。
有人反对我,你怎么说《汉武故事》是刘宋时期王俭写的?很多人大为愤怒。我特别不理解。我看了看批评我的人举出强烈的证据,是社科院文学所曹道衡先生和他的弟子刘跃进先生,刘跃进先生写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这个书里我看了一下,没有任何明确证据,列举了不同说法,比较倾向于他写成于西晋时期,和我的看法不同,我的看法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写的。还有人批评我:你怎么说是王俭写的,学术界公认的都是三国、西晋写的,你怎么就说是王俭写的。之所以说是王俭写的,刚才提到《续谈助》里,提到唐朝一个张柬之的人明确讲:《汉武故事》是王俭写的。这是我们鉴于历史记载唯一的一个作者,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作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北宋人引述的,唐朝中期人讲是王俭写的;第二点,经过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錫先生反复论证是王俭写的,这个说法是合理的;第三点,我自己读书少,用了电子检索基本古籍库,检索到的所有引述《汉武故事》的书都是在王俭身后的,没有超过王俭之前的。当然这个也可能不全面,但是应该差不多。
我也不是学历史,也不是学文学的,我是学地理出身的,我跟搞文学的人谈,大家就好理解,搞文学的人知道一种体裁、一种著述产生有时代背景,所有这一类神仙家著述,葛洪是一个代表人物,是葛洪之后,东晋南朝成批产生的。以前从日本学者盐谷温到中国的著名的鲁迅先生都这样看,没有人有歧异,一种文体的产生有时代背景,我感觉我这个说法是很充分的。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很奇怪,我们见到所有的神仙家著述不讲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好像是儒家讲怎么治国、立太子那套东西特别多,既然这么多,我试图做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我看了南朝的《宋书》之后,正好看到王俭的母亲参与了刘宋文帝时期的另一场巫蛊事变,跟卫太子事变特别相像,当时宋文帝的情况跟汉武帝特别相像。联系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王俭以一种曲折的形式表示了他对母亲的同情。刘宋文帝是极其暴虐的,晚年是极其荒唐的,最奇怪的是他当时正在宠幸的一个妃子,那个妃子生的儿子,按理说跟他的太子正好政治对立,因为把你干掉我就上来了,他俩竟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宋书》里最后一个传是《二凶传》,任何一个朝代两个儿子都是你死我活的,他俩恰恰合起来要搞政变,把老皇帝要杀掉。什么目的?只能说宋文帝政治作为太荒唐、太猜忌了,人人不安,这个跟汉武帝时期特别像,所以想到这种政治背景激发了王俭,而且王俭的整个思想和他想要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王俭个人的行事是守文的思想,他借神仙家的故事做了一个表述。
六、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故事的原型
我首先把它定义为文学性的创作,任何一个文学创作是要依据一定的条件,有些东西可以称之为原型,完全空想,谁的想象都是有限的,我追溯了一下,在真实历史记载当中,汉朝两个皇帝,特别是卫太子不类己,汉武帝说跟他自己不像,一个是汉高祖刘邦对他当时的儿子,第二个就是汉宣帝,汉宣帝说他的儿子跟自己不像,有点太仁慈。这两个故事正好可以给它构建符合他政治愿望提供一个原型,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推论,我觉得不是我脑洞开的很大。总是要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像王俭这种文人写出著名的目录书,对书籍读的非常广泛,他看看《史记》《汉书》非常正常,他不看也得看,一定会很早的读到《史记》《汉书》,这个形象他不想要也有了,在他创作之前一定有《史记》和《汉书》记载汉高祖是什么样的、汉宣帝是什么样的,他不想拿他做原型都要拿他做原型。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测。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