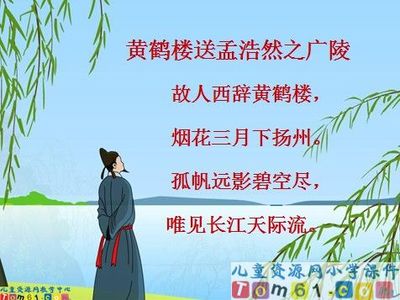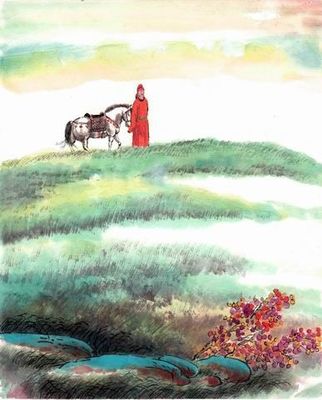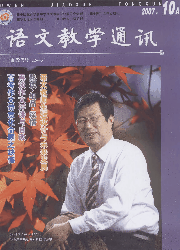作者:林泉忠

今年是《马关条约》两甲子,也是名曲《送别》诞生百年。两者之间,似乎各不相干,却交织出一段近现代中日、东亚乃至东西方社会鲜为人知、影响迄今的文化交流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送别》是无数国人耳熟能详的「学堂歌曲」,近代奇才李叔同(弘一法师,1880-1942)出家前的不朽之作。这首曲子作为驪歌的名曲,常出现在学校毕业典礼,或朋友道别的场景。正因为此曲深入人心,歌词又极富中国古诗风韵,因此许多两岸三地的华人都以为是中国传统歌谣。笔者也曾作如是想,直到在东京求学期间,有一天听到日本人在唱同一旋律的《旅愁》,才恍然大悟。其实,也有不少日本人也以为《旅愁》是日本的传统儿歌。而这一刺激,也使笔者开始了考究该曲来源,追寻此曲如何在东亚传播的故事。
这首歌其实是如家包换的美国歌曲,由美国医生音乐家奥德威(JohnP. Ordway,19824-1880)作曲、作词,1851年诞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曲名为Dreamingof Home and Mother(《梦见家乡和母亲》),此曲曾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流行,不过后来在美国却逐渐失传,如今已几乎成为绝响。
2009年笔者第二度访学波士顿期间,在周末经常在哈佛广场附近看到一位弹奏玻璃琴的乐手在街边摆摊弹奏,并出售她录制的音乐CD。有一次经过时,就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惊喜在Dreamingof Home and Mother诞生的故乡,今天还是有美国人记得这首在东亚广为流传的歌曲。殊不知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一位中国朋友介绍给她的……。
话説回来,这首十九世纪中叶问世的美国儿童歌曲开始在亚洲流传,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1907年8月由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1879-1943)填上日文歌词的《旅愁》在日本出版,收录在《中等教育唱歌集》,从此这首名曲在日本传唱百年,2007年还入选「日本之歌百选」。
中国甲午战败,国人梦醒,万千年轻学子奔赴日本,寻求打败天朝上国的原因与自强之路。百年前第一波留日热潮不乏近代中国指标性人物包括秋瑾、廖仲愷、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釗、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包括了风流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是于1905年负笈东瀛,就读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东京美术学校」,该校目前仍保留着李叔同留学期间的记录及自画像毕业作品。短短六年,李叔同非常活跃,横跨美术、音乐、汉诗等多种领域,让八、九十年后在东京艺大旁的东大留学的笔者惊嘆不已。其间,他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剧团「春柳社」,排演《茶花女》,剧目资料至今仍保存在早稻田大学的演剧博物馆;中国第一本音乐杂誌《音乐小杂誌》也由他在留日期间创办,印刷后带囘中国发行的。五线谱和人体素描也是由他从日本引进中国的。
《送别》正是李叔同在日本求学期间,接触到刚出版的日文版《旅愁》,在回国后,将此曲填上中文歌词,于1915年在中国出版的。犬童球溪在作《旅愁》时,更动了一部分原曲的旋律,以致日文版《送别》与原来的英文版Dreamingof Home and Mother不尽完全相同。从现存的李叔同弟子丰子愷亲笔手抄的《送别》歌谱及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录音来看,李叔同当年所使用的应是日本版本的曲谱。
英、日、中文版的《送别》歌词并不相同,却都在诉说着跨文化、跨国界、人类的共通情感之一---离愁。
《马关条约》后,朝鲜半岛也一步一步地被纳入日本控制的范围,并于1910年为日本帝国所吞併。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旅愁》也被传到朝鲜半岛,有趣的是,战后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这首取自日文原名的韩文版《旅愁》,却因「原曲是美国的曲子」而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流传至今。
甲午马关之后,日本帝国成为东方的新霸主,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新文化传播网络。不仅众多现代汉语词汇如政治、政府、机关、方针、政策、革命、主义、导师、经济、法律、科学、民族、民主、干部、警察、电话、艺术、银行、服务、组织、申请、解决、人权、工业、生产、出版、理论、哲学、原则、共和、国际、广场、环境、体育、形而上学等等来自日本、许多西方思想如《共产党宣言》与欧美文化也透过这些途径散播到亚洲各地,「以日为师」也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自强的坐标。
在中日关系不稳、东亚秩序动摇的今日来回顾《送别》的百年故事,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歌曲本身,对当下世人省思历史、跳脱历史桎梏,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线索元素。
(原文〈《送别》百年 — 超越历史桎梏的省思〉《明报》2015年12月28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