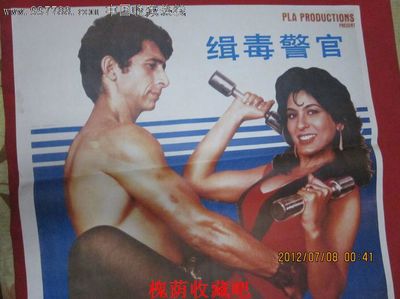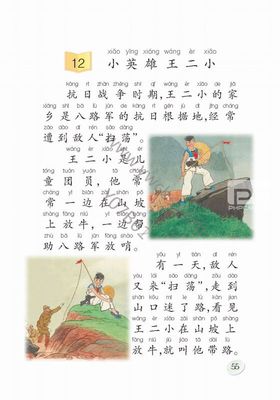近几年来,电影还是一样的电影,艺术却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光怪陆离之间,回眸二十多年前,中国电影的模样迥异于今天。提及张艺谋导演,铺天盖地的“三枪”、“山楂树”等新闻早已将大众影迷轰得晕头转向。“第五代”几乎消失于商业浪潮之中。斗胆将《红高粱》老调重弹,去温故那纯粹而又张狂的“张艺谋”。
显然,《红高粱》是属于“视觉系”的。所有看过影片的观众都会对其中那铺张的“红”难以忘怀。美术学的色彩象征在影片中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能够在国际上摘金夺银实在是合情合理。高粱、夕阳、酒、血、嫁衣、窗花,各种道具(或者是细节)的色彩均为红色,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极度风格化的故事。“红”在影片中象征着粗犷的民族性格,铮铮的铁骨人性。
张艺谋的另一部摄影作品——《黄土地》其主色调则是浑厚的“黄”。同为二十世纪80年代的代表影片,色彩的运用却是如此的类似。这与张艺谋的创作理念,艺术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黄土地》中担任(www.aIhUaU.Com)摄影师的张艺谋开启了张氏风格的先河。(《一个和八个》也可以算作是先河之作)到了《红高粱》,身份变为导演的张艺谋则将自己的美学原则进一步深入。《红高粱》没有了《黄土地》中的陈凯歌似的思辨色彩、压抑的民族性格,全然转变为狂放桀骜的一抹红色,一幅印象派作品。

《红高粱》是豪放派中的写意派。
颠轿、野合、祭酒等无一不淋漓尽致地宣泄着原始而可贵的人性。风吹高粱、斜阳刺目,尘土飞扬,各种景致都镶嵌进叙事的逻辑线条之中。 《红高粱》中的人性高度的写意,不符逻辑的情节在弘扬生命、唤醒野性的主题下都可以得到解释。轿夫为何可以直接进入十八里坡的酿酒作坊和“掌柜的”睡在一张床?做工的伙计为何可以毫无怨言、心悦诚服地协助九儿将作坊运作下去,最后还拼命般地杀鬼子?刘罗汉为何不言声响地离开作坊,投奔共产党?(此处也可以理解成刘罗汉酿出好酒“十八里红”后,对酿酒再无牵挂)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人性的朴素和真诚。十八里坡周围的人都是真诚而朴实的,其人性是原始而化为最基本的原色——红,这一血性至诚的象征色彩。
《红高粱》之前的中国电影(特别是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往往是隐忍而含蓄的。
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黄土地》同样延续着以往中国电影的艺术特色,将民族的厚重,人生的悲凉一幕幕展现出来。历史的进程,民族的性格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样是历史的,民族的因素,在《红高粱》之中积压数年的生命意识喷薄而出,大开大合,完成了民族的一次集体宣泄。
身为“秦国人”(陕西)的张艺谋将故事的地点安置在秦地(黄土地上),让民风尚古的陕北人像祖先秦国人一样彪悍、粗犷地生活着。《红高粱》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的分水岭,其美学风格,故事特色都迥异于之前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也是第一部夺得国际大奖的影片。获奖的原因除了影片本身的高质量之外,也和影片与之前的中国电影“格格不入”有着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