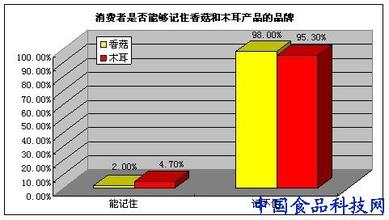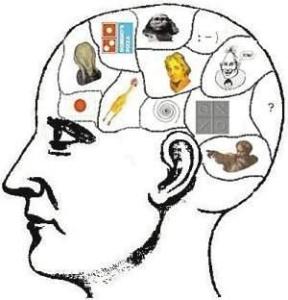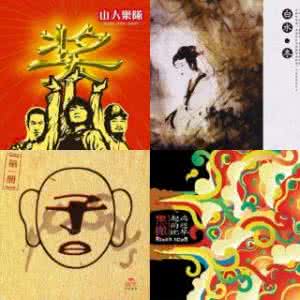
摘 要:孟戏的起源与发展历经一条这样的变迁痕迹:国吊――家吊――巫觋祭祀――佛法超度――文学雅化――民间混融――说唱艺术综合――戏曲终结形态等。孟戏的民俗心理嬗变过程中,沉淀着凭吊亡魂的主题意义偏移、民间审悲心理情结的坚守、以及原始“人头祭”遗韵等诸多民俗化因素。
关键词:孟戏;民俗心理;人头祭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39-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科研项目《古海盐腔的遗存与嬗变》(主持人黄振林)(项目编号:06BJW021)阶段性成果暨2006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共建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孟戏,即以孟姜女传说故事为文本的戏曲泛称,源于民俗口语简称。它作为成熟的戏曲形态,最早见于宋元南戏《孟姜女送寒衣》;它作为民间祭祀剧形态,流传至今且保留较为完善的演出体制,在江西、湖南、安徽及广西四个省份境内的偏僻乡村等仍能找到踪迹。康保成先生认为,“其中湘西傩戏《孟姜女》保存的祓禊古俗较为完整。”②(注: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广西师公戏中的《孟姜女》大致与湘西傩戏相似。安徽傩戏《孟姜女》,王兆乾先生“认为贵池傩戏《孟姜女》无论唱词词格、情节和表演都展露出唐戏特征。”③(注:王兆乾《徽傩启示录(四题)》,发表于《中华艺术论丛》2005年第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承续了唐代将泗州神奉为女性的福佑神(送子神)的传统。笔者即以现存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曾家与刘家村族孟戏为例,探讨孟戏的文本、声腔的源流与嬗变轨迹,并以此为基点阐述孟戏的民俗心理沉淀等相关问题。
一、孟戏文本的源流与凭吊亡魂的民俗心理嬗变
孟戏的文本,当从孟姜女故事源流说起。
孟姜女故事的原形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斗于且于,……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④(注:左丘明,杜氏(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五,《四库全书》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这则史料于孟戏的溯源至少有三大意义:一是时间上可将孟戏文本的溯源至春秋时代;二是故事本质意义已定型,即杞梁战死,其妻行迎丧,受礼教约束而改郊吊为家吊,实际上就是凭吊亡魂的故事主题意义确立;三是揭示了诸侯之间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家破人亡之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却因礼教而被淡化,说明文本立足于上层社会的政治需要,这种政治性的审美视角奠定了孟戏文本的礼教基调。至于杞梁妻“不受郊吊”而改为家吊的民俗,则折射出春秋时代凭吊亡魂的正统礼仪形态与规范。
战国时期的杞梁妻故事出现了偏向情感意义的倾向。据《礼记・檀弓》载:“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①(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十,《四库全书》第1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说明文本基调已经由单一的儒家礼教思想开始点染人性与民本的思想倾向,而折射出孟子的学术理念影响力。故《孟子・告子》中记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有云:“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②(注:赵岐(注),《孟子注疏》卷十二,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其中不难看出孟子对杞梁妻哭夫的正面态度,特别言及借齐人善歌的能力而为哭丧悲歌的风俗形成,既解析了孟戏原于齐人悲歌的另一种传承途径,也说明了孟姜女故事得以广泛流传是伴随着齐鲁大地深厚的民俗与人文环境基础的事实,这是孟姜女故事得以流布的民俗性基础。
因此,先秦时期的孟姜女故事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折射出孔孟礼教思想的交替;二是由重礼的内容(凭吊亡魂)而转向重礼的形态(哭丧悲歌);三是由上层社会的政治性审视角度开始向中下层社会的民俗性审视角度的转换。
有关秦代的杞梁妻故事不见于史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朝焚书坑儒的重法家而轻儒家的治国方略,因此可以推论,作为上层社会流布的杞梁妻故事由于涉嫌儒家思想而遭到抑止,开始随着儒生们地位的变迁带入下层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朝是孟姜女故事由上层社会转入下层社会的转折期。
西汉开始出现杞梁妻哭倒齐城的传说故事,如赵岐注《孟子》“杞梁死于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为之崩,国俗化之,则效其哭,如是歌哭者尚能变俗,有中则见外。”③(注:同上书。)显然,从西汉开始的独尊儒术治国方略,使孟姜女故事重新在上层社会得以传承,只是历经过秦之上下混融后,汉代文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把民间百姓的附会衍化手段用于解注经学之中来了,所以从西汉开始的孟姜女故事中,杞梁妻哭丧的效果被文学性夸张并敷衍出城为之崩的发展趋势来。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从西汉开始,杞梁妻的故事由重凭吊亡魂的祭礼描述转型为重哭丧形态的渲染,这是从史学之法向文学之法的转型,也是一种从正史阙笔向野史杂记文体转型。正是这种转型,使得杞梁妻的传说更加美丽动人,加快戏剧文本化的进程。
从《左传》最初记载杞梁妻哭吊,至两汉时衍绎出她哭倒城墙的情节,后历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范晔作《后汉书・刘瑜传》也说杞氏崩城,直至隋唐时代,杞梁妻哭倒长城的故事才趋于成熟与定型。如唐代的诗人休贯《杞梁妻》云: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④(注:《全唐诗》卷二十六,《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如此,则可看出作为孟戏中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孟姜女送寒衣》、《滴血寻夫》的故事情节至少在隋唐年间已成型。
从宋金时始,孟姜女故事敷衍为戏剧的内容,如金院本《孟姜女》与宋元古南戏《孟姜女送寒衣》,此二者一为北杂剧,一为南戏,代表着宋金元时期孟戏文本的成熟与定型。明传奇有《长城记》、《杞梁妻》,剧中有范杞梁在赵惠王坟内取得和氏璧,献给秦始皇,蒙恬活埋杞梁,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蒙恬又把她悬在百尺长竿上射死等情节。清代有《纳书楹曲谱》所载“时剧”《孟姜女》、弹词《孟姜女寻夫》、《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贞烈全传》、《孟姜女万里寻夫》、宝卷有《孟姜仙女宝卷》等,显然,文本中开始注重贞烈与仙道思想内容。郑传寅说:“就广大的劳动群众而言,宗教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玄妙艰深的哲学,而是来自装神弄鬼、祈福禳灾等世俗化的宗教活动。”⑤(注: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宋元明清四代的孟戏文本的民俗心理沉淀,其归结点在于明清时期的宗教祈福禳灾等世俗化的低层位文化现象,即贞烈与仙道思想的民俗心理沉淀,这是孟戏文本凭吊亡魂的民俗心理本质的嬗变。值得一提的是,江西广昌曾家孟戏文本中结尾时的超度亡魂关目,实际上成为曾家村族孟戏的祭祀本质意义所在,即在民俗心理上回归孟戏文本凭吊亡魂的主题意义。
二、孟戏声腔的雅俗衍变与民俗审悲心理的郁结
孟戏的声腔源流依据文本中杞梁妻哭吊风俗记载,最远可追溯至战国时代的齐人“悲歌”,这是一种曼声哀歌且有抚节伴奏,应该视为比较成熟的艺术表现技能。据记载战国时齐人有“善唱哭调”的传统,如: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白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上,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友,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木丽),三日不绝。……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歌,……(老幼)三日不食。……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放娥之遗声。”――《列子・汤门》⑥(注:张湛(注),殷敬慎(释文),《列子》卷五・汤问,《四库全书》第10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6页。)
东汉时文人五言诗《西北有高楼》中亦有“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可见在汉代就有用杞氏故事谱的琴曲。《西北有高楼》文人五言诗的音乐形态原本抒发征人思妇主题,此曲借齐之悲歌抒发征人思妇情韵,是将民俗乐调雅化的过程,也是音乐主题得以凝炼与升华的过程。
从战国时子周“抚心发声”,韩娥的“曼声哀歌”,到东汉文人“清商”调的“一弹三叹”歌咏形态,是齐歌从民间的“徒歌”“悲歌”向“弦歌”发展的过程,并作为“清商调”沿革下来。“曼声”属于长调,于长调中表达哀号,正如现今蒙古族的长调般有着如泣可诉的特色,而这种歌咏的特色最大的技巧就是以气长吟。值得注意三点:一是清商调一直为民间孟姜女说唱文艺的基调,并沿革至今,即“孟姜女调”或“哭坟调”等。二是这种基调“徒歌”时“慷慨有余哀”、“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想必是高腔的前身了;三是由“徒歌”发展而成文人乐府形式,音乐组织形式变为“一弹三叹”的形态,显然增强了音乐的节奏性或律动的特殊效果,似借鉴了汉相和歌的表现形态,这是否有托腔或帮腔的初级因素则值得深入探讨了。无论如何,至少在东汉时期,孟戏作为说唱文艺形式的音乐基调已初步形成。
南北朝是民歌艺术滥觞时期,以孟姜女故事为民歌的形式传承情况已不得而知了,但从唐代文人张籍拟乐府《筑城曲》和贯休《杞梁妻》歌咏情形来看,南北朝时的民歌仍是承续清商调式的传统,“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的悲歌号哭形式,仍是“一弹三叹”的韵律节奏传承特色。而敦煌曲子词《捣练子》的音乐形式是长短句,说明至少在隋唐时期的民间已经出现述孟姜女故事的长短句式的歌唱形式。而唐代开始出现的《孟姜女变文》,已将歌唱与说白两种形式结合为一体,成为正式的说唱艺术,且为佛教俗讲的范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孟戏后来成为招魂的礼仪,其中便有佛教超度的意义。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说:唐代俗讲中,孤魂祭祀的观念扩大起来。比如,敦煌俗讲中讲述的孟姜女变文(敦煌文书P5039)中,孟姜女拾起丈夫的白骨后,又向其他白骨呼喊,白骨们这样唱道:……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①(注:[日]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结合上文所述,孟姜女文本与说唱形式在盛唐时开始得以结合,并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孟戏形态的孕育阶段,且已深深地打上佛教超度亡灵的民俗烙印,从而完成了孟戏民俗审悲心理的郁结过程。
宋元曲艺说唱更为广泛流传。宋郑樵的《通志・乐略》载: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传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②(注:郑樵撰,《通志》卷四十九・乐略第一,《四库全书》第3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所谓“演成万千言”即指宋话本或各类说唱艺术形态的成熟。而《醉翁谈录》中即有《孟姜女寻夫》公案故事,既对滴血认夫作为公案故事演绎有加。正是宋元各类文艺形态成熟且相互交融的基础之上,以孟姜女故事为内容的戏剧形态便正式产生。
孟戏作为成熟的戏剧最早见于金院本《孟姜女》,以及宋代古南戏《孟姜女送寒衣》,一为北杂剧,一为南戏,可知宋元时期的孟戏声腔分为南、北两种艺术形态。魏良辅《曲律》说:北曲之弦索,南曲之鼓板,犹方圆之必资于规矩,其归重一也。③(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可知弦索与鼓板为北南曲乐器特色的差异。徐渭《南词叙录》曰: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动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
永嘉杂剧(即南曲)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④(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则大致可知北曲与南曲的声调特色的差别,若将这种在乐器与声调方面的差异特色衡量金院本《孟姜女》与古南戏《孟姜女送寒衣》,则两者在声腔方面的民俗审悲心理所表现出的声色差异性便完全不同,北曲更多的表现出惆怅雄壮之气,如铿锵中有悲愤之声,南曲则更多的表现出凄怆哀宛之色,如呜咽中有悲伤之情,这两种声腔特色的描述,前者似乎与正宫唱腔相符合,后者更接近商调和角调式唱腔声色特点。
据《中国戏曲志・江西卷》记载“孟姜女”条:
明传奇有《长城记》(作者不详,仅存曲词残篇)、《杞梁妻》(作者不详,已佚)。清代有《纳书楹曲谱》所载“时剧”《孟姜女》、弹词《孟姜女寻夫》、《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贞烈全传》、《孟姜女万里寻夫》(今均存)、宝卷有《孟姜仙女宝卷》、《孟姜女寻夫》、《哭长城》(今均存)。明代传奇剧本《长城记》,作者不详,故事也取裁于民间传说孟姜女故事,现仅存零出,据《曲海总目提要》所述,剧中有范杞梁在赵惠王坟内取得和氏璧,献给秦始皇,蒙恬活埋杞梁,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蒙恬又把她悬在百尺长竿上射死等情节。⑤(注: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88年版,第737页。)
诚如上文所说,明代的《长城记》中有对蒙恬残暴行为的痛诉,折射出民俗心理从宋元时期的民族矛盾怨恨开始转化为向统治者残暴的痛诉,表现在唱腔声色方面则如北曲的惆怅雄壮之气,即铿锵中有悲愤之声;至清代转化为烈妇贞女与仙道倾向,即怨而不怒的声色倾向较为明显,即如南曲的凄怆哀宛之色,在呜咽中有悲伤之情。如此,则明清时期的孟戏应该属于不同的体系,或一北一南,或清代的孟戏遗存即为北曲受南戏化后的产物。近代各地方的孟戏就声腔而言差异更大,或徽腔,或赣言,或湘调等,但作为傩戏的演制,其村族祭祀正统性与庄重性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必将约束着它们沿着典雅沉重的声色方向发展,即宫调的特色应该为其音乐主题方向,换而言之,受北曲的影响成份更多些。
无论如何,从宋元一直走来,孟戏的声腔中亘古不变的、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其声色旋律与节奏所构造的音乐主题意义,即坚守着那份沉甸甸的民俗审悲心理情结。
三、江西广昌孟戏沉淀着原始“人头祭”的民俗心理遗韵
作为傩文化层面的广昌孟戏,仍有诸多傩祭痕迹遗存,并保存着诸多鲜为人知的远古傩文化信息。最为显著的就是“人头”崇拜与祭祀特点,即以“人面”供奉祖先、生殖神等的祭祀形态,其折射出原始生民“人头祭”图腾痕迹。
刘家与曾家傩戏均敬“三元将军”为主神,即村民称为“大老爷”、“二老爷、“三老爷”,又分别称为蒙恬、王翦、白起。甘竹镇曾家祠堂内供奉的“三元将军”仪态,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三元将军”圣像前摆放着龟,龟头翘首神态,恰是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二是对像前悬挂的“莲花灯”,这是本年内家中生有男孩的村民还傩愿悬挂的,可见“三元将军”在广昌甘竹傩戏祭祀中的生殖崇拜本质;三是三十六枚面具神供奉在神龛中,作为配祀“三元将军”、曾氏祖先和龟头神的重要内容。
就曾家村族祠堂戏台前的祭祀仪态来看,祭祀的主体是祖先曾巩、清源妙道真君和龟神,神龛中的“三元将军”和众多面具神实际上处在配祀地位,虽然“三元将军”面具用龙椅座位安置放在最中心位置,但它们仍然与众面具处在一个层面上,即背景衬托的地位,目的是为突出祖先和清源师。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原始农耕文明时代以“人头祭”方式配祀祖先神灵的仪态,最让人惊讶的是“三元将军”等看似主神,其本身即傩祭面具,而傩面具说到底就是一个个的“人面”形态,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整个曾家村族祠堂内的祭祀仪态中,以三个重要将军的人头祭形态来祭奠祖先和戏神。
“人头祭”是中国原始生民的一种野蛮祭祀习俗。在原始初民认为,死者灵魂的主要座位时常是在头部,因而头部的重要意义,成为巫术力量的中心,故而成为巫傩驱疫的最有力的手段。周以后的诸多文献中,将傩字解释为鬼头、��头等,重点指向一个头字,已经透析出原始生民的人头祭图腾的痕迹。
人头祭与与傩关联一体,如泰勒所说:在查士丁尼王朝时代,瘟疫泛滥成灾,人民在海上看到了铜舟,舟上的人员全是黑色的无头人,它们停泊在哪里,哪里很快就出现了瘟疫。①(注: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因而,制止瘟疫漫延的最好办法就是祭祀性的驱疫,即把四处游荡的“无头人”魂灵集中起来供奉起来,因而“人头祭”图腾崇拜发生了。如中国南方的原始猎头部落的观念中,就有将人头视为一种能沟通人与鬼神的最好祭品、并且作为战争所需的面具与功勋的象征等可以佐证。如宋・李日方等著《太平御览・叙东夷》卷780载:临海水土志曰:夷州(今台湾)……得人头斫去脑,(马交)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②(注:李�P《太平御览・叙东夷》卷780,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56页。)
这是用“人头”作假面状用于战争的源流史料证据,也是傩面具最原始的形态,傩于是在“人头祭”图腾崇拜中得以生发出来,只不过其时的傩面仅用于彰显战功。据此可以推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常常以“人头”的获得为功勋,且有借“人头”制作成“假面”(傩面)作临战时面具的传统,这便能解释最早的傩礼存于军礼的疑惑了。
又如:《二十五史・魏书・獠传》云:“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③(注:《二十五史・魏书・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59页。)
这是用“人面”舞蹈驱鬼祈福,直接解释了傩舞发生借助于人头巫术力量的原始的驱傩雏形态貌。而将“人头祭”图腾直接等同于傩神,有一则非常值得注意的史料,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载:辰州俗供神像,有有头而无躯者,名猡神。一于思红面,号东山对公;一珠络窈窕,号南山对母。两人兄妹为婚,不知其所自始。④(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33页。)将有头无躯者(即人头)称为“猡神”(即傩神),这的确值得关注,它说明傩神本于人头祭。
由上述可知,用人头作傩神进行驱疫,是巫术借人头的法术力量的表征。而广昌甘竹曾家孟戏班社的宗族祠堂内的祭祀仪态中用“三元将军”为主体的众多面具神等供奉祖先和戏神的民俗,可视为原始农耕时代“人头祭”图腾崇拜的遗风,因为,人头祭的目的在于保护村寨平安(无疫)、祈求风调雨顺(丰产)、人丁兴旺(多子),概括起来,即驱邪逐祟、农作丰收和生殖崇拜。这与现存曾家村族宗祠祭祀主题与仪态等意义完全相同。
小结:
从孟戏起源与发展过程可能看出,历经过一条这样的变迁痕迹:国吊――家吊――巫觋祭祀――佛法超度――文学雅化――民间混融――说唱艺术综合――戏曲终结形态等。而在这个过程中,祭亡魂与超度亡魂是本质意义,无论上层社会的靖国之祭,还是民俗哭吊超度,或以歌舞形式的雅,或以民间哭调的俗,或以巫道代表的权威,或以佛法代表的民风,或以故事演变代表的文人情性,或以说唱敷衍代表的百姓兴趣,在雅与俗的较量中,最终却归于俗。从孟戏文本的凭吊亡魂的民俗心理意义偏移,至孟戏声腔的坚守民俗审悲心理情结,以及江西广昌孟戏沉淀着原始“人头祭”遗韵等,其间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广昌孟戏的传承与声腔雅俗化等问题,鉴于本文的篇幅与笔者拙识,祈以来者补正。
(责任编辑:郭妍琳)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