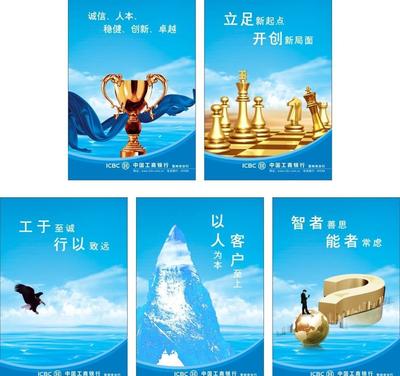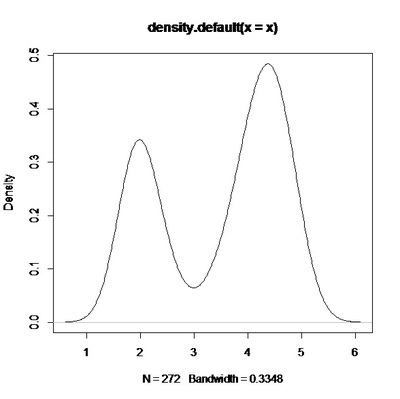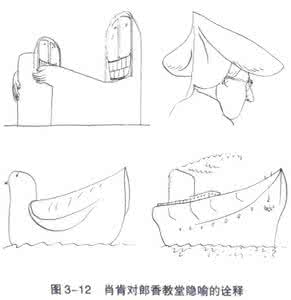
直觉化的形式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里,最不满意传统小说形式的作家,大约要算史铁生和韩少功了。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都完全颠覆了一些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叙事思维,呈现出丰富驳杂的互文特征。这种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彻底破坏,已完全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形式主义实验,是创作主体沉迷于理性思辨的必然性结果。换言之,随着阅历和思想的丰富,史、韩两位越来越看重生活背后的某些理性判析,而要完整地传达这些创作主体的理性思考,一般的故事和人物已难以承载,由是,他们不得不通过多种文体拼缀的手段,来进行叙事形式上的冒险。
在这种叙事冒险中,林白起步虽晚,但也是非常自觉。不过,与史、韩两位不同,林白对小说形式的颠覆则完全来自于自身的感性铺展。她似乎正在走向另一种极端——高度依赖自己的直觉感受,依赖自己的生存体验和灵性的想象,抛开理性对文本结构的控制,也拒绝理性思考在叙事中的渗透。在《万物花开》里,她明确地拆解了故事的整体性,而专攻细节拼接,使叙事显得繁花似锦,一派妖娆。随后的《妇女闲聊录》改以“口述实录”的方式来叙事,彻底放弃了作家的主体意识,通过木珍漫无头绪的闲谈来折射现实的生存镜像。木珍是一个并没有受到多少逻辑训练的乡村妇女,她的闲聊自然是散漫而凌乱的,由此形成的文本,当然也是碎片纷呈。在长篇新作《致一九七五》里,林白又一次颠覆了以往的叙事,完全回到创作主体自身,以一个叫李飘扬的女作家作为主人公进行自我叙述。不仅如此,小说的上部“时光”与下部“在六感那边”也完全呈现出一种彼此分裂的文本形态——上半部像断章散文,下半部才有些故事和情节。而且即使是下半部,其中的故事和情节也是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时空中,并没有非常严谨的内在结构。
林白对理性的这种不自觉的排斥,其实也是一般女性作家普遍尊崇的叙事策略,因为大多数女性对于理性的畏惧总是不言自明的。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阿特伍德就认为,男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在他们自己封闭的公寓里,这里是空间,那里是时间,音乐和算术。右脑不知道左脑在干什么。但擅长有目的地做事。擅长在你扣动扳机的时候射中目标”。而女人的头脑则显得感性,直接,变动不居,不可预料,“刺激一下它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女人通常不写男人喜欢的那种小说,但男人是以写女人喜欢的小说而闻名的”。她甚至还对“女人的小说”进行了探讨,并坦言:“我喜欢读这样的小说:女主角的服装在她的乳房上面谨慎地沙沙响着;或者谨慎的乳房在她的服装下面沙沙地响着——总之必须有一套服装,一些乳房,一些沙沙响,还有就是要处处谨慎。要处处谨慎,像一片雾,一片只能隐约看到事物轮廓的毒气。幽暗中闪现的倩影,呼吸的声音,滑到地板上的缎子,露出了什么?我认为无关紧要。一点也无关紧要。”① 阿特伍德的这些话看起来有点片面,但确实道出了大多数女性作家重直觉轻理性、重细节轻结构的性别化特征。
但是,如果按照黑格尔的理论来分析,无论是过于依赖理性还是感性,都会存在某些审美上的不足,因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②,一切艺术创造中都不能缺少理性,更不能缺乏感性。理性的思想只有通过感性的形式传达出来,才能获得美感,才能成为艺术。我并不打算在此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想说明,如果缺少感性,缺少丰富的直觉体验和想象,小说或许会失去很多鲜活而美妙的艺术质感;反之,过于依赖感性,过于强调创作主体的直觉和想象,小说又会缺乏形而上的精神深度以及文本结构上的内在意味。正因如此,我曾注意到,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出版之后,便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种大杂烩式的拼凑,尤其是上半部,有“注水”的嫌疑。
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对于一个有着成熟经验的作家来说,为一部小说进行“注水”式的写作显然没有必要。有些读者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在于这部小说明确颠覆了人们对于长篇小说叙事统一性的潜在期待——无论是实验性的文本,还是传统的故事文本,就叙事而言,一般的长篇都是采用某种相对统一的叙事方式。有些长篇的内部叙事虽然也呈现出各种分裂状态,像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和韩少功的《暗示》,都是借助了多重文本的融会,但整体叙事的统一性仍是不言而喻的。而《致一九七五》则完全打破了整体叙事的统一性,直接以分裂的叙事方式,使上下部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叙事特质。尤其是上半部“时光”里的二十九节,全是一些事件或场景片断,靠叙述人李飘扬的回忆来进行主观化的串联,其散文化特质十分明显。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小说可不可以散文化,而是如何散文化。在小说的散文化方面,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等都有过成功的范例,他们主要是取消了故事的紧张性,使叙事走向平淡,但人物个性和情节发展仍然获得了保全;而《致一九七五》中上部的散文化,不仅叙述本身不追求故事性,而且还取消了作者对情节发展和人物个性塑造的努力,完全代之以叙述人的个人感受、回忆和情绪,其中的情节改以事件或场景来取代,人物则以散点式的追记为主,并无贯穿性的主要人物谱系。
林白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极端的叙事形式,我以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思考:一是作家个人非理性的叙事习惯,二是不同时间控制下的亲历性场景。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反结构式的叙述确实给《致一九七五》带来了巨大的阅读障碍,尤其是不同的时间介入之后,更加激化了其片断之间的游离,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为创作主体的非理性铺展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叙述空间。林白的优势在于,她拥有极为敏捷的艺术直觉,拥有丰沛的情感张力,拥有阿特伍德所说的迷醉于衣服在身体上沙沙作响的精密体验,所以,即使理性的统一结构并不存在,但在局部的叙述场景中,她依然能够借助不同的时间作为触点,一次次地再现生活的内在质感,包括女生们对孙向明老师的恋慕,操场上飞舞的排球,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厕所旁的腐殖酸铵试验,学农插秧的场景,学军打靶的情形,吃田螺、石螺、鱼块、桂林米粉时的特殊感受……这些少年时代的生活细节,看似凌乱无序,其实也呼应了那个本身并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年代,呈现出狂热的理想主义气息。因此,它的片断化,与其说是记忆本身的碎片拼接,还不如说是纷乱而破碎的历史启蒙所带来的直接感受。它是生活的,又是历史的,是癫疯的历史对个人成长的某种非理性的隐喻。当然,林白可能并没有这种形式上的自觉,但她那非理性的叙事习惯,与历史本身恰恰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默契。
如果细读下部的“在六感那边”,在看似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插队故事里,同样也包含了诸多彼此分裂的叙述,尤其是当叙述者的回忆进入某个具有特质的具象之中,叙述迅速地成为一种情绪的奔泻,如吃胎盘,打鸡血针,知青屋的阳光,安凤美所描述的宝剑,骑自行车,吃胭蚌,写信……这些细节的叙述都游离了叙事本身而成为个人内心情绪的流淌或理想的漫游。它乐观,轻盈,丰沛,为知青生活铺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泽。
因此,读《致一九七五》,我们或许不必过于依赖自身的阅读经验和习惯,而更应该注重小说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丰沛的艺术直觉,尤其是在漫游式的叙述中不断踅入历史深处的各种感受。它不只是一个人对自身经历的回望和肯定,而是一代人对革命历史的亲切抚摸和深情凭吊。
革命语境中的成长
对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成长”一直是他们创作中非常突出的叙事主题。余华、苏童、毕飞宇、艾伟、王彪、海男、东西……等等,都曾将少年成长作为重要的叙事资源,并完成了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在林白的创作中,《致一九七五》或许是她的首部成长小说——南流,玉林,南宁(N城),六感……这些特定的地理名称,尽管也曾在她的以往小说中不时地出现过,甚至成为她在创作上的精神出发地,但是,在这种故土语境中全面展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对她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如果从代际差别上分析,“成长”之所以成为50年代末和60年代出生作家极为自觉的叙事资源,可能不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童年记忆在起作用,还有这种记忆本身与“文革”历史之间所形成的隐秘的精神共振。这种精神共振主要体现为:革命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少年心理上的冒险梦想之间的潜在契合;暴烈而纷乱的革命斗争现实与少年内心的反叛欲望之间的隐秘勾连;家庭教育的普遍缺席与少年心灵上的自由冲动之间的天然互动……它们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使他们在一种无序的自由中成为荒诞价值观的启蒙接受者。而这种悲剧性的历史,又让他们合理地赢得了青春期的冒险舞台,使他们在伤害着别人的同时,不断地在伤害着自己。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他们的一系列成长小说,就会明确地感受到此点。像《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苏宇、苏杭,《刺青时代》里的舒工、舒农,《平原》里的端方,《玉米》里的玉米,《回故乡之路》里的解放,《越野赛跑》里的步年,《欲望》中的蒙,《耳光响亮》里的牛青松和牛红梅,都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尽情地享受着无序的现实所带来的自由、狂想、冒险,甚至暴力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在毫无保护能力和保护意识中饱受各种身心的伤害。他们的成长始终在屈辱和荣耀的双刃剑上奔跑,并以自身的满腔热血见证了科学和道义启蒙的匮乏。
《致一九七五》同样也延续了这一成长主题。并且,它表现的不是一个人的成长,而是一群人的成长,甚至是一代人的成长。李飘扬、安凤美、雷红、雷朵、吕觉悟、邱丽香、罗明艳……这些身处偏远小城的少女们,她们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一方面经受着物质的困顿所带来的清贫生活,另一方面又尽情地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一方面承受着空洞的理想主义价值启蒙,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理想主义而热情地奔波;一方面自觉地膺服于权力意志所倡导的奉献目标,另一方面又为生命中的某种本能意欲而东奔西走。在那里,我们看到,孙向明与神秘的梅花党故事,朦胧而焦灼的暗恋情感,满足虚荣的文艺宣传队,游戏般的下乡支农,狂想式的科学实验,充满刺激的打靶,露天电影,语录歌……在整个上部的“时光”里,那些与革命时代紧密相关的生活场景,始终被李飘扬那新鲜、惊奇、刺激、满足的语调所追述出来。它是记忆的碎片,但又不是纯粹的记忆,因为我们看不出时间冲刷后的沉淀感,也看不出生命回望中的反刍和沉思,而是依然保持着某种原初状态的鲜嫩或轻盈。它不像我们上述的那些成长小说,总是尖锐有余而温暖不足,伤痛有余而欣慰不足,恰恰相反,它的叙述始终笼罩在明亮轻丽的色调中,甚至浸润在一种浪漫式的理想主义激情之中。
在下部的知青生活叙述里,成长仍是一个被延伸的主题。只不过,它变换成青春、爱情、理想与个人命运的自我确认。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步入县革委会的知青办去领取了下乡物资,当他们坐上大卡车奔赴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当他们开始以成长的方式独立地面对生活,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叫“命运”。因此,与“时光”相比,因为叙事的相对集中以及故事性的强化,这里的成长开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生存质色。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安凤美以一种反伦理的享受主义东游西荡,她奔走在爱情和欲望之间,以自我为中心安抚着迷惘的青春。高红艳则全心全意做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标兵。在人人都要有一份特长时,她潜心学习修自行车;解放台湾的口号响起,她立即蓄发以明志。李飘扬热情地穿梭于学校和“政治粪屋”之间,一会儿忙于小学生的教学,一会儿在“政治粪屋”里办夜校、开幼儿班、养鸡,一会儿学二胡。赵战略潜心养磨菇,学木工,冷漠地拒绝二翠的爱情。他们同样经历了身心的磨难,譬如双脚因农田的浸泡而溃烂,饥饿,没菜吃,狗咬等等,但这些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理想和热情,他们依然乐观地面对贫乏的乡村生活。他们可以将一头猪养成永不归家的“猪精”,一个盲动的“自由主义战士”;他们可以让一群私人的鸡变成集体的鸡,而且还让“平庸的鸡变成有觉悟的鸡和快乐的鸡”;他们可以让情书自觉地变成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抒发,让战歌响彻五洲四海;他们在无菜无米的日子里期待着公社的集中日;他们满山遍野地搜寻敌特,甚至时刻等待着准备解放台湾……当他们身心疲惫之时,高考像一声炸雷惊醒了他们对命运的思考。于是,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反省,一切还没有从新奇进入苦涩,他们便结束了知青生活。因此,“下乡”对他们来说,只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味苦难便谢幕了。
这种短暂的知青生活,与其说是给他们的成长进行了一次苦难的诠释,还不如说是让他们获得了另一种青春期的自由体验,使他们在贫乏的现实生活里,重新找到了一条革命理想主义的路途。“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着‘广阔天地’的地方去。”即使没有人为他们送行,他们也“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③。 如果按照“代沟理论”研究者、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因时代剧变所形成的代际冲突——作为冲突的另一方,这些青年人乐于选择无人告别的逃离,因为他们已处在一种“并喻文化”之中,即“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借助父母提供的强制性的价值规范作为准则④ 。也就是说,革命理想主义和伟大领袖的号召作为那个时代最流行、最崇高的行为准则,已完全取代了他们的祖辈所提供的行为规范。所以,《致一九七五》并没有出现知青生活的悲苦色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林白本人对成长记忆的某种宽宥姿态,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文革”后期的知青生活本身已少了早期的艰辛和苦涩。
其实,这也是《致一九七五》的独特之处。它将成长融入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却并没有轻易地赋予它悲剧性的苦烈之质,而是通过这种特殊的革命理想主义语境,激活了青春成长中的冒险、猎奇、热情、懵懂、浪漫和叛逆,使它们相互激荡,彼此簇拥。同时,理性叙事的退场,又让这种成长本身避开了价值判断的尴尬,颇有些早期知青小说普遍具有的诗性格调。这也让我更加相信,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某种荒诞的理想主义与个体生命的单纯、冒险等秉性浪漫性的相遇,会有力地削减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沉重性,加剧历史本身的荒诞发展。
灵性四溢的语言
林白的小说一直保持着轻逸的叙事语言。她总是能够轻松地剥开那些极为庸常的生活外壳,在想象之中赋予它灵光四溢的叙述特质。我以为,这一方面得力于她那敏捷的感官体验和强劲的直觉感知力;另一方面也得力于她早期诗歌创作对于语言的特殊锻炼,尤其是那种瞬间感受的捕捉与呈现。在《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里,虽然人物的活动空间非常狭小,人物关系亦很单纯,但是,她照样能够从各种梦态般的情境中辗转反侧,使叙述显得枝繁叶茂,摇曳生姿。《致一九七五》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显得较为广阔,几乎贯穿了人物从少年到青年、从城市到乡村的成长经历,但是,由于林白摒弃了理性的文本建构,取消了叙述过程中必要的逻辑关联,而完全以回忆的方式,依助直觉和想象进行片段式的叙述,因此,其叙述语言仍然保持着灵性化、轻逸化的审美质感。
更为重要的是,《致一九七五》还明确地展现了林白对现实与历史的坦然姿态,消除了她以往小说中的某些紧张或焦灼的精神状态,使“小我”真正地步入到“大我”之中,为创作主体的自由想象清除了某些潜在的内心屏障,从而更有力地促动了叙事语言的轻盈与飞翔,使叙述显得从容、舒缓。南帆先生在评述该小说时曾说:“仿佛仅仅在纸上随意挥了挥笔,一个叙述开始轻盈地滑行。《致一九七五》很快蔓延成为一簇南方的丛林。各种句子如南方的亚热带植物互相缠绕,茂密繁盛,多汁而蓬勃。”⑤ 我非常赞同这种判断,甚至认为,这是林白全面解放自己的一个标志——在《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里,她通过叙述别人的故事将叙述引入开阔地带,有效地克服了创作主体的过度纠缠所导致的仄逼感;现在,当她重新回到自身的成长语境之中,她依然能够带着梦态般的新奇与坦然来进行漫游性的历史叙述,这无疑是一次令人欣喜的自我超越。如果说“坦然”解除了林白与历史之间的紧张状态,那么成长的激情则为她从容地回到历史、回到记忆注入了一种蓬勃的生机,一种幻象般的叙述质感。“梅花党!这个最让人心醉神迷的字眼从茫无际涯的中学时代、最纷乱最无头绪的年月冲出来,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剑,一下就劈开了乱麻一样的三十年。梅花党的故事,是我们中学时代最传奇、最迷人的故事,它经由孙向明的嘴讲出来,带着他的湛江话的腔调,以及他北大毕业生的神秘感,以及沉浮在河边、沙子、菜地、稻田,绿色秧苗和金黄稻谷之上的悬念,到来。”⑥ 读着这样的叙述语言,说实在的,我仿佛看到作者正在急切地打开一扇扇神秘的记忆之门,向人们展示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存在。它以弥漫的方式,将叙述推向漫无边际的开阔地带,让人有一种心向往之的冲动。
事实上,《致一九七五》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或许正是这种轻盈而又弥漫性的语言。它们相互缠绕,“多汁而蓬勃”,同时纠结着青春成长的某些激情和冒险,想象和自由,在一个个看似庸常的场景中呈现出奇异的光泽,使那些微不足道的事象迅速升腾为极富灵性的生命之舞。它像一场直觉的盛宴,作者的所有感受、想象和激情,被轻松地调配成色泽丰富的鸡尾酒,一杯杯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譬如,面对安凤美“吹牛的剑术”,李飘扬始终以虔诚的姿态,极力想象和推衍着“水泼不进”的剑术状态。在漫长的夜晚,李飘扬想象着自己和安凤美分别骑着一匹红马和一匹白马去杀富济贫,“如果我们知道张志新就好了,或者知道林昭,我们一定会赶去救她们,在夜晚,一红一白两匹马,一白一红两个人,从六感的机耕路上腾空而起”。在回忆那只永远也不长膘的“猪精刁德一”时,作者又赋予它一种自由、狂放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仿佛它就是那个年代里一位永不屈服的斗士。还有那些革命口号和语录歌、样板戏唱词,都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浸润在人物的意绪里,成为他们内心精神的准确映射。这些集灵性与诗性于一体的语言,使这部小说在空寂的历史中,不断地爆发出一团团礼花般的光焰。在此,我们不妨择取几节:
空心菜叶子细长,生长在水里。它脾气古怪,不能用刀切,它伤刀,伤得厉害,用刀切了空心菜就会变得很难吃,必须用手摘。手摘空心菜有一种特殊的快感,即使看别人摘,也有快感,摘成一段一段的,手上握一把,一捏,一种柔软的暴力使空心的菜茎破裂并发出“嗻嗻”的声音,既像撒娇又像欢呼。(57页)
我常常在幕侧目睹这样的时刻,以幕侧为界,那是张大梅的天堂,她一步跨过去,整个人就会飞升,她身体里的物质会在瞬间变化,肌肉、骨头、血液,无声地重新组合,身体的比例仿佛也发生了变化,她的精神更是如此。她的肉身化成了舞蹈的精神,舞蹈又飞升了她的肉身,她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成为无数人黑暗的青春期中无比耀眼的光影。(66页)
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我会有特异功能么?我会力大无穷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想入非非中我兴奋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上像着了火,头脑里的筋也像灼着了,一阵热辣,一阵抽搐。脸是烫的,口干,我起来喝水尿尿,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得像一朵木棉花。(172页)
我应该跟它谈心,嘈嘈切切,大珠小珠。我将对它讲故事,董存瑞罗盛教江姐许云峰,然后,我将一边摸它的毛,一边唱歌,“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抒情,柔软,狗听得舒服。白纸花扎在狗的身上,它在黑暗中奔跑,跟脚,这几朵白花就在黑天里飞动,诗意是次要的,好看更是其次,重要的是,我就不会踩着它,它也不会一着急就咬我一口了。(267页)
从这些精妙的细节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白对瞬间状态的感知方式和拓展能力。它是灵动的想象,又是情感的蔓延;它以反庸常的眼光和心境,激活了现实镜像中所潜藏的某些艺术质感,使一把空心菜都能捏出“撒娇”或“欢呼”的声响。说实在,即使套用那句“化腐朽为神奇”的老话来评价,也许都不算太过分。
人类一次次地回眸历史,不只是畏惧遗忘,还希望寻找归依。《致一九七五》虽然是一个“回忆的文本”(南帆语),但又是一个寻找的文本。它在寻找曾经的青春、梦想和激情,寻找懵懂的岁月和懵懂的成长交织在一起的那种鲜嫩、自由而又无序、狂野的原真的生命状态。“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在小说的“后记”中,林白同样也道出了这种情感冲动。 ■
【注释】
① 布罗茨基等著:《见证与愉悦》,300—302页,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142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林白:《致一九七五》,17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51页,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南帆:《回忆的文本》,载《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10期。
⑥ 林白:《致一九七五》,4—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