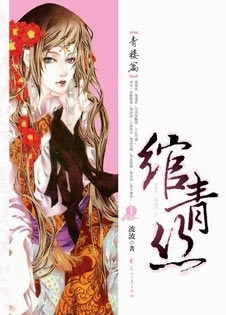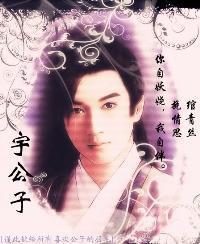青丝(广西)

我属于不太懂欣赏羊肉的人,家里从小到大,从没让羊肉进过门,原因是不善烹煮,怕膻,加之羊肉性温,怕“热气”。十多年前,我在北方得见有人卖羊头肉,是作为一项特色小吃推出的,经过剃须刮毛的羊头,被煮熟后依然神色如常、栩栩如生,像是一堆被摞在一起作为战利品的首级。看得我好生惊骇,旁观了许久,仍无法鼓足勇气进行尝试。
曾在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看他谈及羊头肉。抗战胜利后他还乡北平,冬日夜晚,他本已入睡,听闻外面小巷有人叫卖羊头肉,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叫到自家门洞,当了面现切。小贩用利刃把已煮熟的羊头肉片得飞薄,蘸上椒盐粉吃。由这一段洋溢着浓郁怀旧气氛的文字描述,每一个读者都在“形而上”的想象中,领略到了那种人生快意的饮食美好。我读了以后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为何没有一试羊头肉的滋味,以至于无法产生味觉记忆,获得一种更为直观的美学共识。
推想羊头肉的流行,应带有游牧史的痕迹。《后汉书》载,新朝末年,李轶、王匡二人把持朝政,滥用非人,长安有民谣曰:“烂羊头,关内侯。”时有厨子庖丁把羊头做得软烂可口,滋味无穷,即能赐爵封侯。想见羊头肉在汉时,就已推动了权贵及百姓的生趣,并与权力形成了对偶,擅烹羊头的人甚至能够以此邀功求赏,获授官职。《东京梦华录》里,北宋都城汴京的街市上也有多道以羊头制作的小食,如批切羊头、点羊头、入炉羊头等等。透过这些历史景观,羊头肉已跨越了千年的光阴,至今仍见诸于北方各地的坊市,活跃在食客的唇齿之间,且被烙上了市民主义的标记。
烤羊头想用筷子夹着吃,纯属白搭,再斯文的人也得放低下身段,改用手抓了送到嘴边撕咬,把两腮染得到处是油。羊头上的各个部位,也有不同的味道。羊脑像是稠实的北方老豆腐,很进味,羊眼睛像是吃皮蛋。最美味的是羊脸肉。由于只有薄薄的一层皮,经过烤炙,筋皮尤为油润甘香,吃起来柔韧适口。啃的时候,再呷一小口冰凉的啤酒,那种复杂而美妙的口感,会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湿润,雾化在如梦的夜色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