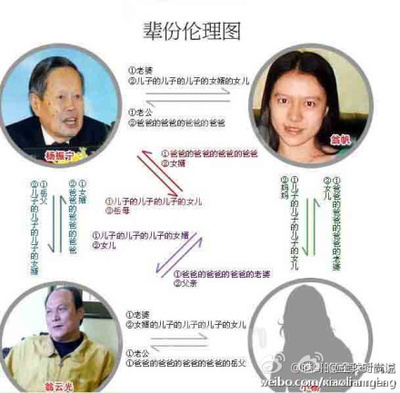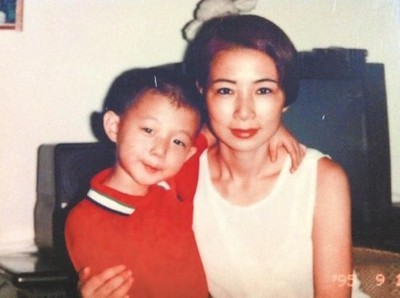那是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事。我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当时父亲轻灵的笔触在心中挑起的那种神奇的感觉。我的名字仿佛不是被写上去,而是幽灵般地被一根魔杖从象牙色的木质深处召唤出来。不过,假如不是因为那两张小板凳本身的一再提示,我的有关记忆恐怕也早已湮灭在遗忘的深渊里了。
说来近乎一个小小的奇迹,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家历经坎坷,数度搬迁,不知扔了多少破烂,可是这两张小板凳却始终完好无损地跟随着,像两只长不大也不愿长大的、忠实的小狗。这和珍惜与否无关,它们是太皮实了。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援引老大老二之例,每添一个弟弟,就添一张小板凳,其“日常待遇”可想而知:高兴起来当成玩具(尤其是当成战争游戏中的攻防武器),不顺心时就是出气筒,真不知被摔踢过多少回。随着岁月流逝,三个弟弟的都先后朽坏,不知所去了,唯有我和哥哥的两张,尽管表面早已被汗渍得发红,背面则霉成了灰黑,却历久弥坚,越活越见筋骨,连打楔子、焊榫头这样的小手术都未曾需要过。南方潮湿,木器常遭虫蛀,奇怪的是,蛀虫从不光顾这两张小板凳,仿佛对它们心怀敬畏似的。
我注意到这小小的日常奇迹是在学诗以后,每每独自对着它们发呆,心想要是能把诗写得像这两张小板凳那样,不松不懈,经得起岁月摔打就好了。有时我会故意把它们轮番拎起来再扔下去,听着落地时笃笃实实的一声响,感受那莫名的快慰和惆怅。我一直怀有一个荒唐的念头,应该见识一下打制它们的那位木匠。对我来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木匠。
但是,这几年再见到那两张小板凳时,我的心绪却全变了。不!首先是它们的意味全变了。先是大哥不耐病痛撒手人寰;紧接着,本已从容挣破病魔扼制的父亲亦遽然离去,其间相隔尚不足一年!我和亲人们满怀连遭命运伏击的悲愤和无奈哭了又哭;泪眼模糊中,那两张小板凳也悄然褪去了原本的诗意,转而成了生命无常、物是人非的惨痛见证。
父亲走得突然,以致来不及留下哪怕一句话的遗嘱。静时不免就想,假如时间允许,他会说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不会说得很多,但我仍然无法代他立言。每逢此时,小板凳就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在眼前,而父亲当年就着夕阳为我和哥哥写上各自名字的情景也随之涌出:轻灵的笔触在象牙色的背板上迅疾移动,默无声地渗向深处……
直到一天我做了个梦。梦中的小板凳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活物。它先是悠悠地升上半空,然后模仿着父亲熟悉的笔迹在空中写着什么。我看得不甚分明,似乎在写我的名字;正待仔细分辨,它却闪电般侧身而下,带着啸音重重地撞在我的胸口。我大叫一声醒来,只觉背后冷汗涔涔,犹能感到心头的余痛。突然我隐有所悟。我想这就是父亲的遗嘱了,它胜过万语千言。大哥若在,定也会同意我的想法。
我开始把我的小板凳当成一个生命对待(尽管它不在身边),并尝试着和气、谦逊、清正以及把这些综合在一起的坚韧。在中国要做一个父亲,广而言之,做一个人,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品质了。同时我也不想隐瞒从中感到的一份酸楚,它来自高不可问的命运。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然而,让一个儿子真实地谈论父亲却要困难得多。孩童时父亲是他心目中的“大人物”、近在身旁的权威和无意识模仿的楷模;青春期父亲是他私下反抗的对象、莫名敌意的所指和检验自身独立性的镜子;而等到他足够成熟,可以和父亲像两个男人那样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却又会因为不深不浅的阅历和意识到的差异而产生某种盲目的自尊,以及不愿彼此伤害的谨慎。这种情形一直要到父亲臻于老境才会有所改变;然而及至此时,理解的渴望早已让位于经过岁月过滤的亲情,他宁愿更多地恪守对父亲的无言敬意。
父亲极少提起他少时之事,我们只能间接地探知一鳞半爪。据祖母说,父亲早慧,读私塾时在乡邻四里颇有点儿名气。“他画也画得好,八九岁时总在江滩上画双枪陆文龙,活灵活现,一位老先生看了说,这伢儿长大了不得了。”我是诸兄弟中唯一见过父亲绘画手迹的。那是“文革”期间,我步行“串联”串到了姨父家。一天吃午饭时姨父突然神秘地说:“快吃,吃完了给你看样好东西。”我三口两口扒完了,跟着他来到卧室的一张旧宁式床前。床迎头雕板上原先嵌画的地方当时照例都贴着毛主席语录。姨父小心翼翼地取掉图钉,揭开语录,露出藏在里面的画。“这是我和你姨妈结婚时你爸画了送给我们的,一共三幅。那时他才十八岁。”姨父边说边如法炮制,揭去了另两幅语录。我凑过去,就着昏暗的光线仔细看了,都是中国画,印象中属青山绿水一路,风格甚为隽秀。可惜数年后我再想看时,那三幅画已连同那张旧宁式床一起被“处理”掉了。
十岁那年父亲去南京插班读小学四年级,寄寓在他姑母也即我姑奶奶家。初中毕业后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谁都没想到他一边在小学代课糊口,一边发愤自修完了高中课程,于次年径直考取了金陵大学政法系。姑奶奶提起这一点甚为自豪,说父亲当时虽然年纪小,又少三年学历,但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两年后父亲转至安徽国立大学,在班上被同学戏称为“小总理”,可见其才、胆、学、识都胜人一筹;此外大约也是喜欢指点江山,很有点儿自以为是的。我曾试图就此请父亲说点儿什么,他含含糊糊对付过去了,显然是不愿谈;但证之以家中保存的他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大概是不错的。照片上他头戴学士帽,身着法官袍,可谓器宇轩昂,英姿勃发。小时常听到父亲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切人生困苦都不在话下”,斯之谓也。
守灵之夜,四周挽联挽幛低垂,我痴痴地看着父亲的遗像。遗像所用照片是一九八六年他第二次心肌梗塞猝发,缓转出院后拍的,当时开玩笑说是“九死一生的纪念”。照片上的父亲静穆、端庄,眉宇间一派与世无争的安详。不知为什么他那张大学毕业照一下子就叠映在上面,泪水禁不住又一次汩汩涌流……
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命运不公。前些年我集中思考前辈诗人的心路历程时,曾问过他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若当初怎样,可能将会怎样。父亲轻轻摇了摇手,只说了一句:“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我不认为在他听来我的提问毫无意义。业已铸定了的历史无从假设是一回事,追问历史是另一回事;就好像历史的选择是一回事,以此作为口实使一切合理合法化是另一回事一样。个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以历史的名义施虐的正当理由。我相信父亲私下里未必没有考虑过这些;那么,我无意间触及了他心头的隐痛了吗?
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历史的选择”。被事后认定为“历史的选择”的,其实不过是当下许多活生生的选择综合形成的大势;而对像父亲这样的一介书生来说,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和道德、正义、良心,和人生地平线上的远景联系在一起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起过大学期间他所经历的反差巨大的心情变化。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刚读完大一,“国民政府”凯旋还都,举行盛大入城式时他是狂热的欢迎人群中的一员。当时胸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心想这下国家有望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他大学毕业时,对国民党统治却早已完全绝望。那时他已偷偷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经常怀想一个叫王亚平的共产党人。此人是活跃在老家一带的新四军某分队的分队长。我曾祖父在当地算是一个乡绅,其时任两面政权的保长。王带着队伍过来时,大都落脚在我家,队部就设在曾祖父的书房里。父亲寒暑假回去,常常能见到他。“王当时不到三十岁,气质风流儒雅,极富感染力。”多年后父亲忆及他时仍然极为倾心,“参加革命前是一个读书人,也喜欢结交读书人。”他称父亲为“大朋友”,无事常叫父亲去书房长谈,甚至抵足而眠作彻夜谈。他显然很看重父亲。父亲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反复动员父亲去延安“抗大”,说可以由他保荐,并为此半正式地与我祖父母进行过交涉。但过后不久,他就在一次鬼子的偷袭中牺牲了。
我问父亲,假如王没有死,他会不会去延安?他笑了笑,说不知道。这毫不奇怪,父亲一直受的是所谓“正统”教育,其时没有疑虑和游移,反倒不正常了。不过,当他一九四八年仲冬独自提着一只皮箱直奔下关码头时,却是不折不扣铁了心的。
其时南京城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不仅封了江,盘查也比平常严苛得多,稍觉可疑,便会被诬为“匪谍”、“通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父亲找在“国防部”做文书的姑爷爷借了一身军装,诡称去上海,却在半途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船,星夜回到老家。
在老家父亲集资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民办小学,自任校长。大军渡江前夕,终于实现夙愿,参加了革命。当时新建的地方政权人才奇缺,像父亲这样的名牌大学生更是“宝贝疙瘩”。从扬州专员公署到泰州专员公署,父亲一直颇受器重;而他也没命地投身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母亲生我们前面弟兄四个时,他不仅从未在母亲身边,而且一再推迟回家探视的行期,以致母亲至今说起,仍有幽幽的怨气。
然而“宝贝疙瘩”很快就宝贝到了头。一九五三年父亲响应号召下基层,到我的生长地江苏仪征参与创办仪征师范,先任教导主任,次年任副校长,然后在类似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五年。
这和通常所谓的“官场失意”无关。真要说失去了什么的话,不如说首先失去了生活价值中最基本的“原始正义”。体制内的升迁与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奖惩手段而使父亲受到这种无言惩罚的既不是他的工作能力,也不是他的忠诚程度。它来自某种莫须有却又像幽灵般摆脱不掉的“信任危机”。“肃反”时某日,我们家租寓的院子里突然住进了一位党员工友,说是夫妻失和,避一避“气头”。既同为房客,父亲也没在意,倒是时常过去劝慰一番,生活上亦百般予以照顾。那位工友感动之余,竟不顾“组织原则”,悄悄找母亲透了“底”:他们夫妻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失和的问题,他来这里是接受了“组织上”的委派,监视父亲日常言行的。
内心磊落的父亲深感震惊。为了报答组织上的关怀,他只有更加勤勉地工作,更加谨慎地生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时他还兼任着学校的“肃反”领导小组副组长。好几年以后才知道,事情起因于我的两个叔叔。说起来那又是一起骇人听闻而又荒诞无稽的“家族敌特集团”冤案,其结论是“案情重大,查无实据”。更年轻的一代人恐怕已很难理解这类玄妙结论的“玄机”所在,充其量只是将其当做某种乏味的政治人类学知识,但对父辈们而言,却是一种足以支配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力量,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其无所不在的暧昧阴影。父亲有所耳闻后曾想找组织上“说清楚”,但该找谁说,又怎么说呢?只有自我消化,“正确对待”了。
我也曾有过多次被要求“正确对待”的经验,对此一类术语的政治—心理学内涵虽谈不上深知个中三味,却也算有所领教。仅仅说此乃一种十足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事者还必须进一步把这种荒诞化做内心的道德律令。正如作为隐喻性修辞,它暗示了某种单行道式的、不可更易的现实关系一样,作为道德律令,它通过提供自欺的升华来掩盖其双重的压抑机制。时至今日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胃,才能“消化”那段历史;需要有怎样的修持功夫,才能“正确对待”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呢?
所谓“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并非如其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过去时意义上的说法。这里“铸定”一词具有逻辑的全部先验性和粗暴意味。它使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了某种三段论式的展开过程,从而使“命运”直接等同于“宿命”。如果说对每一个词的感性体悟都是一次启蒙的话,那么很不幸,我的命运启蒙恰好来自类似的体悟。
那是一九六八冬天,我和大哥赴农村插队的前夕。早两天父亲就关照说,行前要找我们“谈一次”。他说这话时神态之严肃,语气之郑重,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成人感。回头看,也可以说那次谈话是履行了我们的“弱冠之礼”。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独立生活了,今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了。作为父亲,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历史问题向你们交代清楚。当然你们肯定已经隐隐约约听说了一些,正因为如此,就更应该说清楚。”
昏暗的二十五瓦灯泡;窗外西北风尖厉的呼啸;父亲低垂的目光;他枯涩的语流中潜藏着的深深歉意,以及所有这一切交织成的极度压抑气氛……二十八年了,我仍然记得那次谈话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父子两代被“历史问题”这个当时的“大字眼”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在南京读大一时正值汪伪政权濒临崩溃。为了造势壮胆,也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对立面,伪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卑劣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强奸民意,让大学生集体入“党”。是年初夏,父亲班上的一位同学曾往他寄寓的姑母家中送过一张“党证”。当时父亲去了江北老家,我姑奶奶不明就里,便留下了。待我父亲回来说起,因此事既未征求过本人意见,又未履行过任何手续,父亲只觉可笑,随便应一声,转身也就忘了。不料“肃反”过后那位同学为了“立功赎罪”,给我父亲所在单位写了一封检举信。其时父亲刚刚入党,有关负责人遍阅个人履历材料,未及此事,这就足以构成了“欺骗组织”之嫌。于是内查外调,多方寻证,虽无新的发现,然终不放心。一年预备期期满后又延长一年,再期满时,正赶上“反右倾”。
此一期间父亲工作克勤克俭,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却无法阻止那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父亲去世后我曾翻阅过他那一阶段的日记,真可谓字字悲苦,满纸伤痛。见到处分决定的那篇写道:
?摇?摇?摇?摇XX递过文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几个字狰狞地看着我……
另有一篇和我有关:
……电影散场后回家,渡儿突然问:“爸爸,你是共产党员吧?”相询之下,才知白天他和小朋友为此发生过争执,内心不觉一阵刺痛……
此事我虽已毫无记忆,但当时读到,内心同样不免一阵刺痛。我想到父亲的“刺痛”固然部分是出于自伤,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因为不忍孩子受到了无辜伤害?而我当时年幼,伤害了父亲却不自知,虽属无意,终是不懂事;现在感到“刺痛”,已然晚了。
父亲因“历史问题”所受的处分整整二十年后才予以改正,恢复了党籍,党龄从当初的预备期算起。我是在校园里倚着一段竹篱笆读家书知道这一消息的。父亲说到此事时口气很节制,位置也处在信末,属于“顺便告知”一类;但我心里清楚他其实挺激动。人总需要某种归宿感,而父辈中大多数人的归宿感跳不出政治的圈圈;父亲尽管一直努力保持书生本色,且早已宠辱不惊,但在这一点上亦不能外,只不过他和当初一样,更多的是从道德、正义、良心的角度理解政治罢了。现在政治上的冤屈得以澄清,道德上的错误得以改正,良心上的缺憾得以弥补,可见历史到底是公正的,他能不为之激动吗?然而我却激动不起来,或者只是在另一向度上激动。那天傍晚我绕着竹篱又弄什么呢?是算这种“公正”自我证明的演绎程序必要的统计资料呢,还是为了认识这种“公正”,所必须付出的庞大“学费”的一部分?抑或干脆只是一些政治纳税人对这种“公正”应尽的义务?真正思之可怖的是,所有这—切似乎早在一九四五年初夏的某一天,就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通过一张莫名其妙的“党证”预先设置好了。这一纯粹偶然的事件像一颗种子蕴藏着果实那样,把丰富的人生可能性变成了单一的因果关系,所谓“公正”据此把自己显示为某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铁的必然性。
这样的“公正”乃是彻底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公正”。由这种“公正”所支配的命运无非是格式化、公式化的命运。它与其说是生命的运行,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持续诅咒,并且连咒语都是从外部强加的。没有什么比这种“公正”更野蛮的了。必须永远告别这种野蛮的“公正”!
但我真正永远告别的却首先是父亲,念此不禁黯然神伤。正如所有的父亲都希望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儿子,我也和所有的儿子一样,自小就希望有一个非比寻常的父亲,一个可能的、想象中的父亲。假如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我想并不是出于幼稚;因为阅历和成熟并非是泯灭这一心愿的理由。这种心愿根植于人性深处。它可能被遗忘,被扭曲,却不会被泯灭。它比死亡的力量更强大。事实上这也是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始动力。
然而在这篇文字中我只能面对一个平凡而普通的父亲,正如他的一生只是千百万和他一样平凡而普通的父亲的缩影。我无法清晰地勾勒出那位可能的、想象中的父亲的轮廓,尽管他肯定存在,因为我和现实的父亲一样平凡而普通。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最早从父亲口中听说这句话时不超过十岁,当时只觉热血沸腾;转眼我已四十出头了,血的沸点自然也高了许多,知道那样的话终究只能由孟子那样的人来说才有分量,常人引以自励尚可,却不可当真,否则徒然自我喜剧化而已。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不会反对我这样说,至少不会因此责备我“没出息”。
既非“斯人”,作为常人就只能如俗话所说的那样“认命”,就只能混同流俗,就无由见出其“心志”和精神了吗?未必。常人自有常人的心志和精神;他甚至能于寻常处显示出不寻常的心志和精神。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在“文革”中的一次经历。那是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和学校的另一位领导分别做完检查后,照例被宣布为“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此时,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表明其“革命怒火”,竟鬼迷心窍地想出一手怪招。他命令两位“当权派”各自打对方的耳光,以示惩戒。
此言一出,立刻博了个“满堂彩”。那位领导是一把手,当然应该先出手。只见他面如死灰,蹒跚着走到我父亲面前,右手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却迟疑着怎么也举不起来。四周静得能听得到彼此的呼吸。那位造反派头头喝道:“快点,磨蹭什么!”
两位老搭档几乎同时抬起一直低着的头,四目交接。只一瞬间,父亲便平静地合上了眼睛。那位领导小声招呼:“老唐,对不起了。”说完轻轻在我父亲的脸上拍了一下。
周围哄的一阵,有人叫好,有人大喊:“太轻了,重来!”那位造反派头头带着快意的微笑转向父亲:“现在轮到你去打他了。”
父亲不动。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父亲仍然不动。造反派头头恶意挑唆道:“他已经打过你了,你为什么不去打他呢?”
父亲瞥了他一眼,平静但坚决地轻声回答:“不,我不打。不能打。”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头头猛扑上来,揪住父亲的头发拳打脚踢,一迭声吼道:“你竟敢抗拒造反派的命令!去打!去打!”旋即搬来两张木椅,架在一起挂在父亲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不许抬头!什么时候想打了,再把椅子拿掉!”
两张木椅加起来足有三十余斤,只靠一根四棱的横担挂在父亲的脖子上,其滋味可想而知。不一会儿,豆大的汗珠便从父亲的脸上滚滚而下,但他始终骄傲。当然也可以说他只不过做到了人所应该做到的:但我恐怕绝大多数人,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彼情彼景下不易做到。问题不在于能否视强横为无物,在逆境中恪守普遍的道德良知,而在于能否明知可以平衡道德良知仍不改初衷,向内建立起自己的人格尊严。父亲的那位搭档打过游击,曾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说害怕造反派的拳脚肯定是笑话:他真正害怕并最终未能战胜的,其实是无所措置时的惶惑和怯懦。从另一角度说,他招呼在前而轻轻一拍在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暗示自己在做戏,请求配合。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足以成为父亲原谅他的理由,而我相信父亲也确实从一开始就已原谅了他。反过来,假如父亲也轻轻拍他一下,这些同样足以成为父亲自我原谅、同时对方也会原谅的理由。我不认为以父亲之聪敏当时会想不到这一层,正如我不认为他当时内心会一无惶惑和怯懦一样;然而他终于战胜了自己,既没有为强横所利用,也没有为自己的惶惑和怯懦所利用。我心知后者较之前者又不知要难过多少倍;父亲身负暴力的压迫和摧残而能做到这一点,做儿子的能不为之感到由衷的骄傲吗?
写到这里父亲和小板凳的形象忽又重合在一起,但心情不觉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前因有感于命运的高不可问而生的酸楚竟自淡了许多,虽然并未完全消失。经验的盲目性毕竟是阶段人生的本质特征之一;岂但人,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连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也是如此。仅此而言,常言所谓“命比人强”并无大错,像贝多芬那样,能做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终究是极少数(甚至如贝多芬者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之为人的关键不在于强过命运,而在于始终不向命运屈服;不在于超然于命运之手的塑造之上,而在于即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怠地依其本性进行自我塑造,同时又不致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迷失其本性。这就好比我那张小板凳,在被那位了不起的木匠制成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将是什么,犹如谁也不能说那棵桑树长着就是为了被打成小板凳一样;然而它之所以能令我长期萦萦于怀,由视若诗的体现而视若父亲的遗嘱,就因为它始终是一张不松不懈、经得起岁月的摔打、一拍当当响的小板凳。这个比喻的缺陷需要另一个予以补充,即人同时是他自己的木匠和小板凳。
如此说来,那位非比寻常的、可能的父亲也大可不必诉诸想象了。他其实一直生活在我那所去不远的、平凡而普通的父亲体内。
父亲在世时我曾经历过和他的多次告别,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七年初秋为他送秋衣的那次。当时“文革”武斗风正炽,交通中断,我是步行前往三十多公里外他所在的山区中学的。在那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三天形同囚禁的生活,一起分食了母亲捎去的唯一一块月饼。回城时经父亲再三恳求,造反派恩准他送我一程。在一处高坡顶上父亲被押送的红卫兵喝令止步,他第一次像对大人那样握了我的手,然后目送我离去。
长长的、缠足布似的山区公路一眼望去空无一人。我还没走出几步,热泪就一下子涌出了眼窝;再走几步,竟忍不住变成了号啕大哭。我一边哭一边埋头疾奔,一口气下到坡底,其间几度回首,泪眼模糊中总见到父亲笔直的身影伫立原地,对着我频频挥手。
爬上对面的坡顶,我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父亲的身影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正午秋阳晒起的空气涡流中微微晃动。昊天漠漠,四围寂然,我慢慢站定,提足一口气,扯直了嗓子,明知父亲听不见,但仍然不管不顾地喊:
“爸爸——”
现在生离死别皆已成为过去,可我仍常常在心里喊:
“爸爸——”
我想父亲一定能听得见。
责任编辑 晨 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