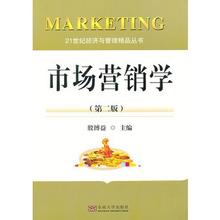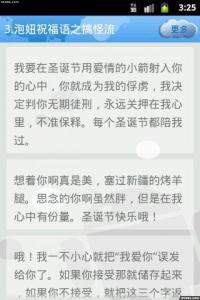你现在看到的是《时尚先生Esquire》12月特刊“年度先生”专题(点击这里查看年度先生全名单)。我们推送的第一篇是年度话题人物马东的封面报道。接下来的两周里,《时尚先生Esquire》将陆续推送其余10位“年度先生”的报道。
2015年,马东主持的《奇葩说》第二季播放量达6.2亿。同年,他带领团队离开爱奇艺,创立新公司。敏于学习,收放自如。让60后的他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娱乐版个人IP。
回看节目时,马东常常“痛恨自己身上的嘚瑟,那个瞬间的得意。往往克制不住,搂不住,事后我特别懊恼。”但他不打算改,因为真实,“不就是拿来恨的吗?就是欠抽,就是贱。”
马东刷糖浆
撰文/钱杨 摄影/陈漫 短片导演/杜寻梦
午夜11点,上海市中心一家餐馆露天的位子上,马东点了一杯红酒。他没吃晚饭,饿了,拿勺子挖一小块巧克力蛋糕。
他刚完成今天的拍摄。刚碰面时,摄影师陈漫举着相机主动上来跟他说,自己特喜欢看一个英国汽车真人秀(Top Gear)。“她不可能不知道我正在做这个节目的中文版。我知道她不过在试图放松我。”做访谈十几年,他自己也这么放松要访问的人。“我们俩要在一起工作俩小时,她有一堆工作人员,我有一堆工作人员,无端的牛逼感会碰撞到一块,这种时候,谁先放松了都有益于我们交流。”他往口里送了一勺蛋糕,“那我就把放松演给她看。”
无论是硬纸折成的巨大蝴蝶领结、闪着晃眼金光的皮鞋,还是一根塞到他手里的仙女棒似的玩意儿,马东都欣然接受。四五个摄影助手大把大把地朝他后脑勺扔碎纸片。他坐在办公桌上,跷着腿,按要求调配表情。
马东常说“角色自由”。这天晚上8点到10点间,他在尽力演一个好脾气的、表情丰富的,甚至兴致盎然的被拍摄者。
几个月前,他是爱奇艺首席内容官;再早一点,是著名的央视主持人;现在,他是创业者,米未传媒的CEO。因为角色一变再变,人们对他好奇又疑惑。在面对“你一个文化人为什么要做娱乐”“你一个正经人怎么调戏女嘉宾”一类的问题时,他总是以“角色自由”作为回答。
“人的角色是外界赋予的,别人给你了,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个事了,刷糖浆似的,一遍一遍往自己身上刷。”他承认自己也在主动刷着,“包括现在什么创业者的身份,什么‘议长’(《奇葩说》主持)的身份,这都是一遍一遍往身上刷糖浆。”
刷糖浆是角色需要。马东说,如果某天糖浆厚了、干巴了,成了硬壳,离真实的自己有了距离,“可以让分身偷跑出来,去干点自由的、放松的、无耻的什么事。”
他晃了晃着红酒杯,喝了一小口,“该刷刷,该溜溜,这就叫角色自由。”
MM马
“MM马”是马东在“新世道”里创建的崭新角色。2013年,他已经成为爱奇艺首席内容官,挖来了牟頔及她的团队,后者是央视最年轻有为的导演。见面时,马东上来就跟她说,“世道变了”。“像我这种人离开央视去了一个网站,那肯定是世道变了对不对?”
牟頔记得当时马东拿爱奇艺独播版权剧《来自星星的你》举例,说服她互联网已经具备独立推火一个IP的能力。“拿事实砸了你的脸说,时代变了”。还有就是著名的风口理论。
“我当下就决定去了,”米未传媒的办公室里,牟頔靠在懒人沙发上回忆,“我就装了个逼,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得带团队一块去,那时候我手下有20多个人。”后来,这些人跟着她来到了马东麾下,他们一起创造了现象级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
这档节目起源于马东和高晓松的点子:把全国的“大喷子”聚到一块儿辩论。
“从他穿苏格兰裙开始,你就知道是一档不一样的节目。”刘煦说。她是马东创业的合伙人之一,爱奇艺时期的工作伙伴。
自《奇葩说》开始,马东画风大变。他穿着大块撞色的西装,坐在大红大绿的布景中间,头发被发胶高高支着,连名字也改成了洋气的“MM马”。节目上,他“调戏”女嘉宾,给选手刨坑儿,挤兑人也被人挤兑,以惊人的反应速度和分寸极强的幽默感,碾压众人。能荤能素,还经常冒出后期不得不做消音处理的敏感词。
第二季开始前,为了好看,他甚至割了眼袋,还在节目上宣布减肥,放话说,减不下来就裸奔。他中午只吃沙拉,吃遍了公司附近的所有种类,还号召所有人跟他一起吃。
观众对“MM马”相当买账,他们称他为“无颜值男神”。每当马东花式口播广告,把贱兮兮的广告词无缝对接在节目中,台下总乐得人仰马翻。
邱晨是第二季的冠军,她说马东私底下总是笑盈盈的,“睁一个大眼睛特别真诚地看着你”,但一上节目,立刻切换成机警状态,“眼珠子滴溜滴溜使劲儿转”。
马东把录制当休息,出了棚,他是老板、首席内容官,得开会、见客户、做决定。进了棚,他是主持人“MM马”,松弛、灵敏、憋一肚子坏,嘚瑟。
爱奇艺CEO龚宇跟马东有一个共识,爱奇艺的行业布局上,得有个“捅破天”的纯网综艺节目。“捅破天”的意思是,“要一鸣惊人,能镇住全行业”。“我答应龚宇,我说我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后来的数字证明他没有食言,第二季的广告收入超过一亿。牟頔笑着说,虽说创业维艰,他们却不怎么为钱的事儿操心,“有客户举着钱来。”
坏小人
“他可算有个地方能撒欢了。”贾清云笑眯眯地叼着烟。他是马东14年的好友,当年《挑战主持人》的策划。他在电脑上看过一期《奇葩说》,“看他那状态,如鱼得水。”
那期节目里,马东开了些下半身的玩笑。“都说到裤腰带下边了。”这让贾清云有点惊讶,“马东是个乖孩子你知道吧?礼数周到、进退有序,很让别人舒服,绝不毒舌。”
他觉得马东脑子里有个“坏小人”,做《奇葩说》的时候,憋不住了,跑出来说了个痛快。“他喜欢那个口腔快感,那是他最过瘾的时候。”
回看节目时,马东常常痛恨不已。“痛恨自己身上的嘚瑟,那个瞬间的得意。往往克制不住,搂不住,事后我特别懊恼。”但他不打算改,因为真实,“不就是拿来恨的吗?就是欠抽,就是贱。”
贾清云跟马东一样,对于夸张虚伪的表达“天生过敏”。俩人一起参加活动,当台上人开始煽情、歌颂,往外甩大词、虚词的时候,他们常常挤眉弄眼地对视。“就是麻蝇儿。”贾云清说。这个词是河北方言,意思是令人恶心得起鸡皮疙瘩。
他做了十几年的电视节目,现在在北大教书。作为老师,他很乐于总结意义。他对我剖析了一番《奇葩说》的意义:“对麻蝇儿的反动”“一场个性运动”“鼓励着一种新的人格”……
听完我转述的意义后,马东哈哈大笑,“请他喝酒”,然而,“追求意义这事本身特别荒诞。”
他反对节目寓教于乐,认为娱乐才是本质。
每一季开始前,他都反复叮嘱,节目要好玩,“好玩就是它的意义”,“有趣这个词都严重了,我要的就是它好玩。”他们也开过一些“人生意义”类型的话题,比如,“长生不老是不是好事”,引起很多讨论。他提醒年轻导演们,别误以为节目讲了些道理,激发了讨论,点击率就多,就得朝那个方向做。“一定是娱乐效果好的那一期看的人多。”
“说实话,我和蔡康永、高晓松,包括金星,我们都不是等而下之的人,我们几个大概都会做自己正常水平的事,所以把这个节目做得不好玩的危险,远大于把它做得低俗的危险。”
插班生
贾清云见到爱奇艺时期的马东,“极疲劳,同时一万多件事要干,脸色、声音感觉到都快不行了”,他提醒马东,“你小心过劳死。”
马东笑了,“其实那个拼命是很享受的状态。我不忙成这样,我才要小心了。我闲下来会恐慌。”
那会儿,他的角色就像一个“插班生”。“我掉队时间比较长,所以得拼命往回补。”牟頔到爱奇艺时,是马东在这个公司的第三年。她看到的马东已经非常自如,“跟技术开会、跟市场开会、跟销售开会,所有的逻辑他都非常清楚。”
刘煦对马东能享受几乎所有角色而惊奇。“他可以enjoy他不同的面,可以enjoy老板的面,可以enjoy主持人的面,可以enjoy制作人的面……这就是爱玩的人才会有的状态。”
刚来时,马东甚至连UV、VV、日活、月活代表什么都不清楚。他曾因为弄不懂电视剧流量预测系统,而叫来工程师,让他们在墙上画图。“我不需要知道你那个公式是怎么算的,告诉我你的基础逻辑是什么。我要是傻子我就听不明白。”当工程师说他们套用了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的公式,然后再做数据纠正时,他一下子明白了,不再往下问。
“我只需要了解到这一层。”他说,“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投入产出的分寸计算。因为你的时间、资源、智力水平都是有限的。”
离开爱奇艺,也是“分寸计算”的结果。做首席内容官,他70%的精力得放在管理上,剩下的才在内容。马东说,内容是一个“摸高”领域,丢人现眼没人看见,牛逼一下,就能被所有人记住。管理则是倒过来的,不许犯错,一旦犯了,代价惨重。对他来讲,丢几回人没事儿,“牛逼一下就很爽”。两相权衡,他走了,成立了专注内容制作的米未传媒。
按创新工场投资总监陈悦天的说法,他们一直在盼马东出来创业。2014年开始,创新工场密集投资内容领域,他们看遍了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各个自制部。“聊过一圈之后,哎,马老师是最好的。其实(投资)目标挺明确的,你知道吧。”
“他比一般创业者成熟太多了。”陈悦天说。在考察创业者时,他们有个评价体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你的内容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马老师那天就坐在我对面,他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明白这个东西,他说我们公司要有一个slogan,叫‘相信说话的力量’。”
7月14日,爱奇艺官方微博宣布马东卸任,即将创业。“我们特别怕这个项目流失。”陈悦天说,他们“特事特办”,双方见了两次面,就定下了。米未传媒成了创新工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民币投资项目。
当他们说出投资数字时,马东没反应。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王肇辉说:“他根本没有期望值,他对自己的公司该怎么估值,还没算好,我们就扔了一个大馅饼给他。”
Trademark
以为马东已经活成了一个IP,可他说自己不是。“有可能在米未的背景下面,我是一个trademark。你把我放在除《奇葩说》之外的其他节目上,就不见得成功。团队非常重要。”
米未公司架构特别,绝大部分员工是90后,马东最大,68年的,70后整个断档。员工们在背后叫47岁的马东“老头儿”或者“马老”,又敬又爱地。
“这个公司其实挺失控的。”牟頔说。坐下来聊天前,她正吼着大嗓门把人往会议室里轰,“别玩啦,都进去。”不打卡,不考勤,冰箱里填满了吃的,一到中午要“杀人'”(游戏),杀到下午2点才上班。
“马老说过,内容工作者超过四个小时以后,工作都是无效的。他是一个努力在营造这种氛围的人。”刘煦说。
公司还在装修的时候,他就琢磨好了,一定要弄两只猫,再单辟个麻将室。猫已经如约进驻,在办公室里蹑手蹑脚地窜。
“营造这个氛围是我的分内工作,营造得不好是我失职。“马东说,“他们必须得是快乐的、浑不吝的、自信爆棚的,在内容行业这才叫工作状态。”
“他非常非常尊敬90后,我说的是从内心真实的尊重。”牟頔说。《奇葩说》刚开始,大家想玩他,说老板我们需要你穿裙子。那时候团队刚凑到一块,都不清楚这个老板底线到哪儿。结果马东兴致勃勃地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团队第一次跟马东开汇报会,90后们想用一句话证明自己随性、嚣张、who care的调性。PPT上来一行大字,“90后: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反正你会死。”
“他一开始是有点蒙的。有点微信里发呆(表情)的样子,但是他马上就笑了。上来他不知道你是这个思路的,但马上他会理解,并且转化成微笑。”牟頔说。
疑议最强烈的时候,马东也顶多说“这样真的好吗?”他甚至不要求审片,“牟頔审就完了。”
“他没说以我从业四十多年的经验,你们如果不这么去干,就死定了,他不会。”马薇薇说,她是米未签约艺人之一,《奇葩说》明星辩手。“他实际上只把控住一个底线,让大家别玩脱了就行。”
马东曾跟牟頔、刘煦说过,他甚至害怕过多跟他们接触,怕约束到他们。“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牟頔说,“虽然他标榜自己很年轻,是90后,但毕竟思维上不能完全地扭转成我们的逻辑,他选择更退一步,避免正面冲撞。”
马东东
这些年,马东的角色形象越刷越多,把矛盾都捏合到一块,勤奋松弛,真诚,一肚子坏,以及,一个性感的胖子。
范湉湉是《奇葩说》画风最突出的选手,米未签约艺人。她是整个团队里除了马东年纪最大的人。她也觉得这个年龄层结构怪怪的,“一帮90后为一个60后和80后的人服务,也是够了。”她嗓门大,动作幅度也大,说话时咄咄逼人地抬着下巴,身上有一股义薄云天的江湖味道,又有可爱泼辣的市井之气。
对她而言,马东是伯乐、是靠山。她说,很多艺人年纪大了都变得现实、认命,她也被劝过不知多少次,“现实一点,你这个类型做不了女主角”之类的。马东跟她说,“咱们就奔女主角去。”她很感激,“马东老师从来没有看轻过我。让我放心跟着他,有肉吃。”
前一阵子,她说话不慎,惹怒了当红组合的粉丝,新闻出来,她在家里哭。马东给她发了条微信,“没事儿,乖”。“我看了以后就泪崩,很简单的话,让人特别安心,觉得他是一个大靠山。”
范湉湉赞美马东是集成熟男人和年轻男人所有优点为一身的人。“他很有人格魅力,所以我们最后都叫他马东东,非常爱他。”
金星是《奇葩说》第二季的导师。马东邀请她加入时,亲自跑到她家楼下等,请她喝茶。做节目时,礼数周到,“太客气,其实没必要,但礼数嘛都到了呀,大家合作起来就很舒服嘛。”
前几个礼拜,她收到马东寄来的一大堆郁金香。“我说哟,干嘛给我寄花,冷不丁地寄那么多漂亮的郁金香,他说哎呀姐姐,你不搞party嘛,给你家周末party添点颜色嘛。虽然我不能去,你得想着我呀。我说好好好。我们家满屋摆的全是马东寄来的花。”
她不知道马东从哪儿知道她先生最爱郁金香,夸他有心。“他知道朋友间需要什么。他会很准确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于你的生活中,告诉你,马东在这儿呢。”金星在电话那端笑得开心,“很聪明的男人嘛。”
除了深受身边女性赞美,马东也俘获了大批年轻观众。女粉丝们叫他“无颜值男神”,说“聪明是新的性感(smart is the new sexy)”,在微博上嚷嚷着要组团睡他。
马东笑出了声,“我身体不好,算了吧。”
走运的家伙
“你说这是设计好的吗?”贾清云分析着马东的事业轨迹。“先去央视,然后出来,进一个民营的网络公司,然后再出来创业,你看人家的人生路线,特清晰,特漂亮,你要看我那乱套了,颠三倒四。”
在庙堂里规规矩矩待过,又在江湖里潇洒来去,他羡慕马东能不停找到事儿干。“你要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四五十岁了,你就知道想做自己有多么迫切。心里要是找不着自己,那慌啊,慌乱不堪。”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攒了半缸,“那种焦虑要你命。”
“央视他可不是一个小走卒,他最后做到综艺频道的总监助理,你知道那权有多大吗?那种辉煌以及辉煌背后要付出的人格和尊严代价,他都品尝过了。经历过这一套他才知道,现在能够这样狂喷、胡喷有多么过瘾。”贾清云说。
“没有(规划)。”在米未公司的一个榻榻米房间内,马东脱了鞋、盘着腿,端一咖啡杯坐在矮桌前。“跟着好奇心走就行了。”他说自己刚来爱奇艺时,真心觉得会在那儿待很久,“我跟龚宇经常交流,说这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后一份工作。”
但就是动了心思。“推动你的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就是一念之差……你这个心思不能动,动了你不做,就太难受了,你会一直带着这个遗憾,我受不了。”
马东说自己一生都没有太大的压力感。他在牌桌上常说一句话,“按照牌理出牌,把输赢交给命运”。运气重要,甚至比“会做”更重要。他承认自己运气实在好,因为父亲马季先生的缘故,从小就被很多人无缘无故地喜欢。
“这给了我好多正向的鼓励,在后来我做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自信,然后因为这种自信,又受到了别人的鼓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他说《奇葩说》就是交了好运。他、高晓松、蔡康永之间,特别快地有了化学反应。“并不是每三个会说话的人放在一起就一定有化学反应,这是我们的运气。”
除了《奇葩说》,在未来,马东和他平均岁数24岁的年轻人们还将推出更多视频内容,这需要他们像以前一样,动用智慧、付出辛苦,再等好运光临。
“一个内容的产生,是战战兢兢的过程,如履薄冰。”虽然他相信数据的价值——“能够使你避免犯愚蠢的错误”,但光靠这个不行。是创作,就有些捉摸不定的部分。“但不就是这样才刺激嘛,”马东声音里透着快活,“如履薄冰的这种感觉,是对创作者最大的奖励。”
他引用乔布斯的话,听起来跟所有创业者一样虔诚,说“过程即奖励”。
“要真正想赢,就像麦家(谍战小说家)说的,”他顿了顿,拿手指在空气中绕了绕,“‘九天之外的一丝运气’。”
“那是什么?”
“鬼知道那是什么。”
提问个人IP的年代
E:大家都说IP元年,你怎么理解作为个人的IP?
马东:IP应该是知识产权的直译吧。知识产权是资产价值概念。对我来说就是个词而已,没什么意义,因为当你转化一个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时候,要付出的劳动可能跟原创那个东西相差并不大,那是一个巨大的、重新创作和付出的过程。
E:五年前你觉得你这个行业,一个人需要的最重要品质是什么,现在有否变化?
马东:没变化,不光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三十年前,从大的尺度上来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在未来也不会有真的变化,都是信息量的变化,知识更新的变化而已。
E:互联网和资本正在通过IP改变你行业的规则吗?
马东:这些词都没意义。互联网,就是市场和渠道。今天都叫资本了,那个时候叫老板。IP不就是创作嘛,写剧本,写歌。就是每个时代叫法不一样,都是一些时髦的东西,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E:行业变化中最让你触动的一件事或者人是什么,是不是也让你有所改变?
马东: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来刺激我。所以既有的观念天天都在被打破。打破得彻底,不见得就成功,但是至少你可以赌。不打破不改变的人,连赌的机会都没有。
E:有取悦90后或者更年轻人的焦虑吗?
马东:我从来没有要取悦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观众是无法取悦的。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误区老是去分析观众,你看到90%的所谓工业废水,其实都是这样产生的。
你花了太多时间去迎合,你不太可能真正知道他喜欢什么,观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被喜欢的东西,永远都是以前没有过,他发现了你,他才开始喜欢你,所以你只能够用智慧和天生的创造力,去想象一些你不知道的,观众也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有可能会死,死了就是运气不好,所以你还需要很多运气。

E:畅想您十年之后的行业变化。
马东:我不知道。我不会去畅想十年以后。我做规划,但是我知道规划是扯淡的。目前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肯定是排名靠前的,但是我不知道五年以后,谁知道谁运气怎么样呢,我只希望五年以后我(们公司)还活着,而且能够排名前十,我就很满意了。
撰文/钱杨 采访/钱杨、李婷婷 编辑/林珊珊
摄影/陈漫 统筹/谢如颖、董冬咚 化妆/淼淼(吴忧造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