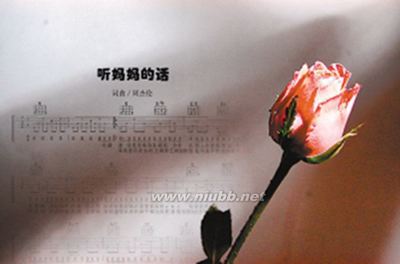因为鲁迅的缘故,德国女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近日,她的大型作品展《黑白的力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共展出120多件包括版画、素描、雕塑和书信在内的藏品。这是中国观众有幸目睹她全部代表作的机会。
珂勒惠支曾毫不讳言: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政治为文艺挂帅”的信条。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文艺“政治决定艺术”的功利主义,似乎早就在市场经济的荡涤中,被摆上了历史的博古架。然而,当你遭遇珂勒惠支作品的那一刻,便会有一种力量感迎面袭来:这不是广告、招贴画、标语的力量感,而是艺术的力量感。借用一位现场观众的话:这不是宣传的艺术,而是宣言的艺术。
珂勒惠支自刻像:珂勒惠支以版画的形式记录下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
“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
为“革命”赋予的正当性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大抵并未注意的,然而这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1931年,鲁迅在《北斗》创刊号上首次刊登了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以纪念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被暗杀的柔石。由于恐惧,当时的报章上对此事均无记载。鲁迅刊《牺牲》,一是因为柔石非常喜爱珂勒惠支的作品(他同时也是其在中国最早的引介者),当然还有上述引语中的“各各藏着一些意义”。——《牺牲》这幅作品也在此次展览之列。如果对比珂勒惠支前期的作品,会发现1920年代开始创作的一系列木刻在风格上有极大的突变:相对于早期的铜板和石板作品中细腻到充满“触觉”感的叙事性风格,她的木刻是象征性的和表现主义的;人物从具体背景中抽离出来,只剩下大块凌厉的黑白线条。
木刻版画《牺牲》
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读解上的暧昧性。事实上,珂勒惠支创作此作品是出于一种对于战争的反对。一战期间,她支持儿子彼得上了战场,结果因此送命。丧子之痛极大地刺激了珂勒惠支,并直接导致了她在创作上的转变。在《牺牲》里,瘦削羸弱的母亲闭着双眼以一种僵硬的身姿奉出熟睡的婴孩。从珂勒惠支当时的日记来看,这幅作品除了控诉战争剥夺一无所有者唯一的所有,更有一种掺杂了痛苦与悔恨的自责。
然而鲁迅所想到的,是柔石那尚不知晓儿子死讯的目盲的乡下老母。《牺牲》中作为背景的那团黑影,便从“战争”转换为了“革命”。而革命的正当性,却来源于这幅木刻所代表的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1930年代,在德国纳粹势力崛起之下的珂勒惠支被迫噤声,基本中断了创作;然而在远东,她的沉默所引起的回声却“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从西方的“现代主义”
到中国的“现实主义”
珂勒惠支在她的时代里,是一个受过正规艺术教育出身的现代派。1898年,她将受到自然主义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纺织工人》启发而创作的系列版画《织工起义》送去“柏林大艺术展”,立刻一举成名。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还是表现的方法上,珂勒惠支的版画都和之前欧洲画坛上的主流迥然有异。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织工起义》还有随后的《农民战争》选择“瞬间”而非选择典型场景作为再现的时刻。就是在这些瞬间之中,她使用“光”和“阴影”点燃画面的戏剧性,并不回避人物由于情绪激动和快速运动所扭曲的面目——织工以及暴动的穷人,并不是作为“美”和“正义”来呈现的。
珂勒惠支,《织工起义》系列之一
在构图以及对人物身形面部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到强大的西方宗教绘画传统所遗留下的痕迹——毫不奇怪珂勒惠支热爱的是“老大师”鲁本斯和戈雅——的确,还有什么能比宗教绘画更能勾起(西方观众)无意识里对情感的记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这次一同展出的青铜雕塑《哀悼基督》,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信奉宗教的珂勒惠支,有意识地弱化了基督的特殊身份,隐蔽掉了此题材中常见的双脚淌血的钉孔和荆棘头冠,而突出了用身体包裹住儿子的圣母/母亲的形象。与其说珂勒惠支是在削减此题材中的宗教性,不如说她是在利用凝结于西方宗教文化中的情感记忆表达自己的主题。
然而,在西方属于现代主义一脉的珂勒惠支,在遥远的中国却是被当做现实主义艺术家来接受的。这主要是由于她作品选择的内容上,大都描绘了19世纪末德国历史中不堪的那一面(正因此她的作品不断惹恼当时的德国皇室),即由于工业化进程涌入城市转变为工人和底层的农民的“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鲁迅语)。珂勒惠支被视为进步艺术家也正在于她持续地赋予了底层与苦难以“可见性”。鲁迅积极地推介她的作品,因为她使人“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同时“也存在着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的艺术家”。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坚实的联结感。第一代现代木刻家江丰正是在珂勒惠支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作品《码头工人》。
江丰《码头工人》(可对比上图的《织工起义》)
木刻艺术与鲁迅的文艺观:
打破生活与艺术的实践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
作为大文豪而被人熟知的鲁迅,其实也是中国现代美术的积极推动者,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木刻之父”。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自己在袁世凯时期由于寂寞“钞古碑”、“回到古代去”,不过这番举动并不简单是为了避开当局的监视。鲁迅酷爱汉代石刻、唐代画像中线条的简洁、大气与生动,比起宋元以来的文人水墨,他在摩崖石刻、墓碑纹饰与古碑拓片中找到了中国古代无名艺术家表现出的强烈生命力,而对于文人画,鲁迅的意见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有发展”。这与他对民间神话传说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并不如那些一味的反对迷信者,而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民众的想象力和创作性。
认为中国民众对线条、对于“黑与白”的艺术有接受的审美基础,是鲁迅推崇木刻的一大原因。更有前面引文中谈到的古代版画的起源本在中国,但古代版画画刻分离(由画师、刻板师和印师共同创作),而流传到西方的版画技艺,也是在丢勒之后才逐渐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像铜板、石板版画,需要软蜡、细针与酸剂等工具的配合才能完成;而由于其复制的本性(这一点接近摄影),为制造一种与商品价值相关联的“本真性”(即产生一种原作的概念),现代版画在印制大约30张版画之后,会将刻板销毁。
“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艺运动不仅是在一种对旧形式的辩证取舍中展开的(旧的贵族山林文学被打倒,而民间的文化和艺术则被以新的目光重新发现),也是在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热情中展开的:尽管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和市场经济都未出现,左翼文化运动却已然包含了一种对于超越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诉求。鲁迅认为木刻版画的好处在于“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同于铜板、石板版画,木刻版画工序简单,只用一把刻刀和一块木板,便可作画。“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种操作上的直接性,是和最终发展为延安文艺的“将现实生活变成艺术”这个乌托邦冲动中的“直接性”相关的。而同样重要的还在于,版画跟纸上绘画等其他美术形式不同,它天然具有大规模复制和传播的特性——在这里,艺术的价值不再与本真性相挂钩,而在于和现实生活的等同性——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达达主义者、构成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们也正运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
鲁迅的肖像版画

内山嘉吉在回忆中写到1931年鲁迅出现在上海木刻讲习会的那个夏日,是穿着一身崭新的白色长衫,一改往日暗淡的旧灰布衫。作为现场翻译的鲁迅,翻译出的内容量却远远多于内山本人的讲解。在鲁迅的影响下,大量木刻团体兴起。他一方面和许多青年木刻家保持着通信,一方面积极编撰出版来自苏俄、日本、欧洲的版画作品集(这其中就包括珂勒惠支的作品选)。直到去世的10天以前,他还拖着病体出现在“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柔石被害后不久,鲁迅曾托帮其购买过珂勒惠支原作的史沫特莱写信给珂氏,请求她为柔石创作一幅肖像版画。珂勒惠支由于未见过柔石本人,又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婉拒。鲁迅却因此更加钦佩这位艺术家严谨的创作态度。在鲁迅看来,珂勒惠支作品中的力量感,正是由于扎根于现实生活。他认为,固然不能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没有一种男性化的煽动力,但如果比照真正的革命宣传画,就会发现不同之处在于珂勒惠支的作品“是和生动的现实生活深深联系在一起的,就会理解这些东西的形式是根植于激烈的葛藤之中的。事物更多的泼刺性赋予它的形式以更强力更本源的紧张感”。
《德国的孩子们饿着》,1924年,石板作品。珂勒惠支最负盛名的作品,鲁迅从孩子们的饥饿中读出了“希望”
“泼刺性”意味着所展现的事物并不能被一些简单的理念加以抽象,换句话说,抽象后的事物的理念并不能囊括它在现实之中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反映在作品上,珂勒惠支的底层人物并不如无产阶级革命宣传画,他们在反抗中流露出恐惧,在哀求中闪现出希望,在挣扎中鼓荡着愤怒——他们在一瞬间是丑陋的,一瞬间又有种深刻的美。这些人物从现实中来,在版画上“抽象化”,复又在现实中、在每一个观看者的记忆中找到自身的落实。
从“五四”时代的左翼文艺
到延安时代的大众文艺
鲁迅在跟青年木刻家的通信中反复敦促他们要训练好素描、速写的能力。想要介入现实是一种愿景,而真的达到则需要技艺上的坚实。他告诫青年们,要看见了什么都画,不要管什么题材;正确地观察,最好看清了本质以后再下笔。“不可开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否则必会与希望相反。这和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意见是相一致的,他讽刺成仿吾那样的革命文学家强调革命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将文学强制地纳入革命的意图中,使得文学失去自主性——而这“无异于八股”。
鲁迅在对木刻为代表的文艺问题上,持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尽管推崇木刻有“文艺化大众”的目的,但他不认为不真正生活在激烈现实中的青年人,能做出关于激烈现实的木刻,那反倒不如尊重他真实的生活世界,哪怕去刻画花鸟、鱼虫和山水。这就是尊重创作者本人的阶级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出的药方,是要艺术创作者在阶级问题上通过自我改造进行“大众化”以进入“大众”的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木刻创作者都赶赴延安投身革命。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一时间成为木刻系,木刻成为了当时紧急条件下艺术创作的最重要方式,并与抗战宣传紧密结合。经过“马蒂斯之争”,木刻创作的题材顿时紧缩,更不必说在表现的风格和手法上。“座谈会”之后,鲁艺的教育体制接着也发生改变。为了适应农村群众的欣赏习惯,原先繁复的阴刻刀法逐渐在对传统年画、剪纸的学习中变为了简洁的阳刻刀法;画面主体清晰,情节性突出。以这种方式创作出的木刻年画放在农村的集市上叫卖,也的确得到了“哄抢一空”的效果。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珂勒惠支式的木刻,大概一定会被归到“非现实主义”那里去吧。
很难想象鲁迅如果活得长久一些,会对延安木刻有怎样的评价。如今也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重新思考延安木刻来启发当代艺术的实践。当然,延安木刻的艺术价值是和它的历史特殊性紧密关联的。而珂勒惠支的作品,之所以超越了国别、民族和时代依然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说来也很简单,那不过应了鲁迅对艺术家的看法,“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真实地置身于民众之中,真实地去刻画己之所见。
 爱华网
爱华网